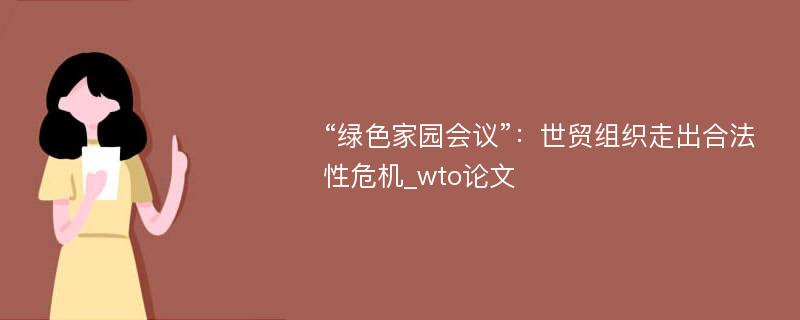
“绿屋会议”:WTO走出合法性危机的一道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法性论文,危机论文,会议论文,一道坎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0)02-0111-07
作为全球经济共治的主要机构,WTO运转良好的状态在西雅图和坎昆部长级会议上受到巨大阻碍,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看出来,不欢而散、无果而终的结果亦是明证。WTO深陷于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 of the WTO)的泥潭之中,① 多哈发展回合依然踌躇不前。WTO面临的这些问题,固然系诸因素之合力所致,但备受诟病的“绿屋会议”没有得到适当改良,② 以致相关成员方被“屏蔽”在WTO决策机制之外的事实,③ 则是WTO尚未摆脱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原因。④
当世界将目光聚焦于国际金融危机之时,我们是否亦应当对WTO给予必要的关注?在经济一体化的当代,鉴于贸易与金融问题之间的相互传导性,2009年4月2日结束的G20伦敦峰会在公报中指出,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行动来促进和推动国际贸易,是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改革“绿屋会议”的意见进行评介,并结合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定位,就“绿屋会议”之改革提出恰当的可行方案,对于WTO走出合法性危机和推进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进而抑制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塑造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现时参考意义。
一、“绿屋会议”及其运行
如所周知,虽然GATT/WTO确定了一国一票的投票表决机制,但在实践中,奉行的却是协商一致决策机制,⑤ 在该机制下,任何提议只要遭到一个成员方的反对就无法通过。为了避免决策时陷入致命的僵局,在面临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时,GATT/WTO一般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排他的磋商,以便就待决问题达成共识,然后再扩大到全体成员方。⑥ 这种非正式的小范围排他磋商,在东京回合期间首次出现,真正将此类磋商命名为“绿屋会议”则系始于乌拉圭回合。⑦ “绿屋会议”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在GATT总部内有一房间曾专门用于召开此类非正式的排他磋商会议,而该房间的墙壁恰好是绿色。⑧ 尽管这种非正式的小范围排他磋商现在不一定在GATT/WTO总部中的“绿屋”进行,但“绿屋会议”的名称却一直沿用至今。
GATT/WTO总干事、部长级会议主席或总理事会主席负责召集“绿屋会议”,与会成员方则一般由美国和欧盟选定,他们和加拿大、日本组成“四方国家”主导“绿屋会议”的全过程。⑨ 基于相关成员方的利益考虑,其他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亦被邀请参加“绿屋会议”,但与会成员方因议题不同而不同。召开“绿屋会议”表面上是为了使与会成员方就待决议题草案达成一致意见,然而事实上,在“绿屋”磋商过程中,制度和规则被弃之一旁,转而由赤裸的权力政治替代,⑩“绿屋会议”形成的文本草案一旦提交到全体成员方大会上,它经常一字不差地被通过或者仅有少部分的修改。(11) 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即使能“有幸”参与其中,但要么没有机会发言,要么发言不被听取和记录,被“边缘化”是“绿屋会议”留给他们的最深刻的印象。(12) 鉴于“绿屋会议”之排他、不透明和不民主的特征,以致有观点直接用“臭名昭著(notorious)”来形容它。(13)
WTO成立后的第一次部长级会议于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会议期间,发达成员方数次召开“绿屋会议”,在没有与绝大部分发展中成员方进行事先磋商的情况下,利用协商一致决策机制,(14) 通过了对他们单方面有利的含有劳工、投资和竞争等议题的宣言,(15) 发展中成员方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6) 原以为发达成员方会因此而改弦更张,没想到在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期间,时任会议主席的美国贸易部长巴尔舍夫斯基(Barshefsky)依然把WTO视作一个俱乐部,依然认为20几个国家可以为其他成员方作决定,又数次召开“绿屋会议”,以期作出新的单方面安排。(17) 在发展中成员方的强烈抗议下,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被迫宣布流产。此后,发达成员方在解决“绿屋会议”的排他、不透明和不民主问题上做了一些表面的努力,(18) 但从后来在多哈、坎昆、香港等地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来看,“绿屋会议”一如既往,(19) 以至于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被迫于2006年中止,陷入僵局。尽管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已重新启动,但至今尚处于徘徊徜徉阶段,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改革“绿屋会议”的建议
在经历西雅图和坎昆部长级会议两次失败之后,发达成员方坚定了无法在众多成员方之间达成共识的认识,并认为,在东京回合期间,“绿屋会议”规模比较小,一般控制在8个左右,而自乌拉圭回合以来,“绿屋会议”得容纳二三十个国家,在小范围内就待决问题达成共识是WTO正常运转的必需,成员方过多是WTO无法作出决策和徘徊不前的重要原因。(20) 基于此种认识,加上发展中成员方要求对“绿屋会议”进行改革以提高WTO内部透明度的压力,(21) 发达成员方学界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
(一)WTO咨询董事会(WTO Consultative Board)模式(22)
早在1997年左右,美国布莱克赫斯特(Blackhurst)教授就认识到,“绿屋会议”不但对WTO有效发挥其功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使WTO遭受合法性危机,并认为,鉴于新加坡与西雅图部长会议的经验教训,有必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常设机构——WTO咨询董事会来解决WTO面临的体制性问题。
在布氏的构想中,WTO咨询董事会共设置24个席位,贸易量在世界排名前四的国家可以在咨询董事会中取得常任席位,剩下的非常任席位则由成员方以与贸易有关的议题为基础,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各利益集团内部推举或轮换。在布氏看来,这种设计能够起到人力和财力资源互补的作用。拿东盟为例,如果轮到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小国轮值时,由于这些国家对某些WTO事务的经验不是很丰富,财力资源也有限,此时就可以汇集所有东盟成员国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尤其是争取那些在这方面有经验的熟练外交人员的智力支持,帮助他们成功地胜任轮值过程中的任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以往被排除在“绿屋”之外的情形相比,其被“边缘化”的感觉将会得到改善。
为了避免咨询董事会具有“不透明”的嫌疑,布氏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咨询董事会在召开会议时,同步直播会议,使未能与会的成员方可以通过闭路电视了解会议内容;第二,在会议室的中心设置一个圆桌会议台,咨询董事会成员在该圆桌会议台就座并开会,在该圆桌会议台的外围安排一些座位,让非咨询董事会的成员方旁听会议,但无权介入到会议过程之中。在布氏看来,这两个办法可以使咨询董事会的透明度得到极大提高,也可以增加成员方相互间达成一致的政治意愿。
最后,布氏设计的WTO咨询董事会没有作出可以约束成员方之决议的权力,它只不过具有磋商、讨论、辩论和谈判性质,但是经咨询董事会磋商、讨论、辩论和谈判出来的结果可以以建议的形式提交给全体成员方,寻求批准或通过。
(二)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informal steering committee)模式(23)
美国学者杰夫雷·肖特(Jeffrey J.Schott)和迦亚斯里·沃特尔(Jayashree Watal)是该模式的主要倡导者。他们指出,“绿屋会议”与会者只有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大国,大多数WTO成员方并不在其中,这一现状是需要改进的;改革“绿屋会议”原本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些通过“绿屋”而获得既得利益的发达成员方是改革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较小的发展中成员方和最不发达成员方,也反对建立一个他们无法介入的“小集团会议”,因为设立任何制度化的“小集团会议”都将可能使他们在WTO决策过程中被正式地边缘化。所以,建立一个小型的、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是明智之选。
依照他们的描绘,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由二十来个席位组成,通过成员方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地理标准,即确保所有大地区至少有两名代表,确保参与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于席位有限,中东地区、非洲法语国家、北非地区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等成员方只有加入或组成集团方可能获得席位。另外,他们还认为,这种席位分配方式的结果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执行董事会更具广泛性,因为在IMF中,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国家都各自占有一个席位,而欧盟在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中只占有一个席位,无形中节约了席位,增加了扩大代表性的可能。
虽然杰夫雷·肖特在文章中强调该指导委员会是非正式的,但他在接受我国学者的采访时,表明其真正愿望是成立一个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我所建议的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构成WTO的一个机制,而不是临时性的。……该成员小组应当有一定数量的限制,比如20至25个席位。参加该小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贸易额,一个是地区的代表性。贸易份额这一标准将保证主要的贸易国能够参加该小组。其他一些国家则可以自愿组合在一起,达到一定的‘门槛’即可参加。此外,该小组成员必须具有地域上的代表性,形成地域上的平衡,比如中美洲国家应当有自己的代表,非洲国家应当有自己的代表。”(24)
(三)联盟、议题平台和代理人(Coalition,Issue Platforms and Proxies)模式(25)
奥地利教授肯特·琼斯(Kent Jones)在综合咨询董事会模式与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联盟、议题平台和代理人模式”。该模式之主旨是,以议题为中心,各成员方根据不同的利益需要组成联盟,在联盟中推举代表参加“绿屋会议”,由代表代为决策。即“联盟”是参加“绿屋会议”的基本单位,每个议题可以设定若干“联盟”,这些“联盟”由对特定议题有共同利益的成员方组成。
鉴于联盟战略在WTO决策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26) 琼斯认为完全可以按照“议题驱动(issues-driven)”的方式组成许多新联盟,并指出,以议题为中心的各种联盟事实上已经存在于WTO之中。如由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对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倍感兴趣的“意见一致国家集团(Like Minded Group)”,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成员方联合起来的“回合之友(Friends of Round)”、最不发达国家集团、非洲集团。
考虑到“绿屋会议”的容量是有限的,琼斯建议每个议题的“联盟”总数也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该模式就会丧失设置的必要性。如,假若农业议题设置一百多个“联盟”,这与让每个成员方参与“绿屋会议”没有什么区别。总的来说,琼斯苦心构想出这么一个模式,主要是为了“合理地”限制“绿屋会议”的参加人数。
在琼斯眼中该模式至少具有两个优点:发展中或最不发达成员方以议题为基础建立的联盟可以提高他们在WTO决策过程中讨价还价的实力;以议题为基础的联盟可以提高联盟的凝聚力、增加成员间的互信和充分交流与分享信息。
三、“绿屋会议”改革建议的评析
WTO咨询董事会模式、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模式和肯特·琼斯模式,均强调最终决策权由各成员方保留,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成员驱动(member- driven)”是WTO的重要组织特性;(27) 然而,它们均不向全体成员方开放,而是通过设定各种标准限制参与者的数量,“绿屋会议”的排他性被“继承”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其统称为“新绿屋”。
布莱克赫斯特教授主张建立一个正式的“新绿屋”,以取代现行非制度化的“绿屋会议”。固然正式的“新绿屋”可以部分缓解“绿屋会议”在合法性问题上遭受的质疑;但是,创设正式的“新绿屋”也同时意味着,绝大部分成员方参与“新绿屋”磋商的权利被正式地、合法地剥夺。(28)
若按照肖特的建议,成立一个非正式的“新绿屋”,在笔者看来,除都具有资格限制和排他性以外,其与“绿屋会议”并没有本质区别。有观点指出,“WTO继承了GATT太多的文化、习惯和实践做法。这让我们想到‘老人穿上了新衣服’”。(29) 确实,GATT时代的“绿屋会议”在WTO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如今遇到了危机,又企图用“新绿屋”来“继位”。“换汤不换药”和“新瓶装老酒”或许可以作为肖特的非正式“新绿屋”的注释。
布莱克赫斯特和肖特均主张应当按照各成员方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确定“新绿屋”与会成员方,并认为该办法简单易行。其实不然:第一,由该方法产生的与会成员方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毕竟各成员方的年度贸易量均是动态变化的。第二,贸易量上升者固然是喜,下降者被剔除出局,反对声音定不会小。其实,西方学者也承认:“组建这么一个机构面临的最大困难就在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成员方的反对。现有的WTO‘宪法’尚无法有效地克服这些反对观点。……很明显这些提出来的建议将会遇到严重的阻碍。”(30) 概言之,以贸易量为基础确定“新绿屋”与会成员方的做法,在本质上是原生态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国际社会的翻版;(31) 它不但对建构和谐国际经济关系没有裨益,反而有助于“霍布斯文化”在WTO中的宣扬和确立。(32)
在“新绿屋”诸建议中,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区域代表制和议题代表制。如果把世界划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选出各自的代表参加“新绿屋”,其优点有二:其一,成员方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代表;其二,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激励“区域代表”为其所代表的区域的其他国家利益服务,因为,倘若“区域代表”只顾自己,而不顾区域内其他成员方的利益,则很有可能在下次区域选举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而被迫走出“新绿屋”,丧失继续成为代表的可能。但细加分析,区域代表制其实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天性缺陷”。
假设某区域共有8个WTO成员方,其中两个对取消农业补贴十分感兴趣,取消农业补贴可以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利益;而另外6个则对新加坡议题中的投资与竞争政策感兴趣,他们对取消农业补贴不但不感兴趣,而且主张对农产品加以保护。按照多数决原则,被选为该区域代表的肯定是对投资与竞争政策感兴趣的6个成员之一,他们在“新绿屋”中采取的立场可以完全不顾另外两个成员方的利益,甚至唱反调。因为只要得到了其他与投资和竞争政策有利益的成员方的支持,就完全可以在下一届“新绿屋”中连选连任。那么该区域中的少数,将永远地成为其利益被忽视的少数,其主张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与保护。简言之,若区域内部的利益不甚一致,那么区域代表制就无法维持下去,如果得以维持的话,也是以牺牲少数成员方的利益为代价的。
解决这一弊端的办法,就是采用议题代表制,亦即肯特·琼斯提出的“以议题为平台的代理人”模式。在该模式下,代表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如果他没有代表利益集团而行为,则下次被选任的可能性很小。从理论上说,该模式确实具有吸引力。但在操作层面上,其弊端也不少。首先,必须对议题进行精确地划分,如果议题划分不够精细,那么希望以议题为基础形成不同联盟的构想就会幻灭。这是因为,议题越是模糊,国家利益也必定模糊;国家利益越是模糊,成员方越难正确地选择自己的利益集团。其次,不同的议题之间也会存在冲突,由此衍生出来新的棘手问题。比如,假设代表农业出口国的凯恩斯集团在农业议题领域胜出,代表竞争政策的欧盟集团在该议题胜出,那么,在“新绿屋”中还必须解决农业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
当然,如果议题与议题之间能够得到有效的协调,那么,肯特·琼斯模式也倒有其可取之处。但琼斯一方面主张应当严格按照议题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主张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应当享有天然领导权。(33) 琼斯的观点其实是精英民主制在国际社会的简单复制。我们不禁试问:在WTO中有没有这样的成员方,因为他比其他成员方都聪明,因此,在处理WTO中最为紧要的事务时,就应当自动地按照他的意见去做?答案不言自明。即使有些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某成员方了解得多一些,但其他成员方都能够学习、掌握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WTO在做决定之前需要全体成员方一起讨论、协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协商、讨论,然后再作出决策,这也是WTO为什么要创设的一个理由。而讨论问题,制定WTO遵循的政策,这样的事情成员方都能胜任。
综上,在制定国际经济政策的问题上,WTO各成员方均应享有参与讨论和磋商的权利,即使某些成员方因为受人力资源的限制,对某些议题有可能带来的利弊不是很清楚,他们也依然享有不被剥夺参与讨论和磋商,以及共同决策的权利。认为美国和欧盟等国在某些领域享有天然领导权的观点,一旦在“新绿屋”中有所反映,其危害不言而喻。改革“绿屋会议”的建议,毫无例外地依然将广大发展中成员方排除在WTO决策之外;解决WTO合法性危机以及“绿屋会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全体成员方均能充分有效地参与WTO决策,参加WTO事务的管理。大概没有成员方会怀疑自己有权自由参与“绿屋会议”的讨论与磋商的巨大价值。
四、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与“绿屋会议”的改革
诚然,“‘绿屋会议’需要改革”。(34) 然而,在WTO体系内,在“绿屋会议”问题上,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立场既有别于发达成员方,亦不同于其他发展中成员方。“大国”的中国应在“绿屋会议”改革问题上发挥“倡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不宜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附和西方国家的改革意见。从“负责任”的大国视角观之,中国应在维护WTO体系稳定性方面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对现行的“绿屋会议”既不宜贸然打破现有格局,亦不宜“抱残守缺”,任其流弊。(35) 为此,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是发达国家的“利益攸关者”,亦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36) 可以积极充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37) 对“绿屋会议”进行三阶段式的循序渐进的改良。
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在提高辨识相关议题与自身利益之间因果关系的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绿屋会议”参与者的范围。召集者并不是毫无标准地确定“绿屋会议”的参与者,而是以“与所涉议题有利害关系”为依据的,发展中国家此类辨识能力的提高,可以为以较充足的理由说服“绿屋会议”的召集者打下基础,(38) 进而参与其中。
第二阶段:在“绿屋会议”参与方扩大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在“绿屋会议”内,在“有得有失,得失至少相当”的策略下,与发达国家磋商、谈判和协调,逐步改变“绿屋会议”被“四方国家”主导的现状。
第三阶段:在上述两阶段目标实现后,进一步扩大“绿屋会议”,直至将其演变成能够吸纳全体成员方意见或向全体成员方开放的会议,在全体成员方共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WTO协调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WTO是成员方驱动的组织,无论是何种改良版或改革版的“绿屋会议”,均不应享有决策权,WTO的最终决策权应当由全体成员方掌控;同时,WTO走出合法性危机,有效执行其功能所带来的潜在的利益期待,为成员方注入了改良或改革“绿屋会议”的政治动力。
注释:
① Daniel C.Esty,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legitimacy crisis,World Trade Review,Vol.1,2002,p.7.
② Jayashree Watal,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TO-New Evidence Based on the 2003 Official Records,in George A.Bermann & Petros C.Mavroidis,eds.,WTO law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46-169.
③ Supachai Panitchpakdi,Global Trade Issues in the New Millennium:Keynote Address:The Evolving Multilateral Trades System in the New Millennium,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33,2001,pp.440-441.
④ Fatoumata Jawara & Aileen Kwa,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WTO:The Real Wor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Zed Books,2003,p.18.
⑤ Mary E.Footer,The Role of Consensus in GATT/WTO Decision-Making,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Vol.17,Winter,1996/Spring,1997,p.668.
⑥ Dmitri V.Verenyov,Vote or Lose :An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Alternatives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Buffalo Law Review,Vol.51,Spring,2003,p.458.
⑦ Margaret Liang,Evolution of the WTO Decision Making Process,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2005,p.126.
⑧ John Burgess,Green Room's Closed Doors Couldn't Hide Disagreements,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5,1999,p.46.
⑨ Brian T.Larson,Meaningful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the WTO,Wisconsin Law Review,2003,pp.1202-1203.
⑩ Sonia E.Roland,Developing Countries Coalitions at the WTO:In Search of Legal Support,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8,Summer,2007,pp.527-528.
(11) Richard H.Steinberg,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Spring,2002,p.355.
(12) James Thuo Gathii,Open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Scheme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Process and Substance In WTO Reform,Rutgers Law Review,Vol.56,Summer,2004,pp.889-900.
(13) Jeffrey J.Schott,The WTO after Seattle,in Jeffrey J.Schott,ed.,The WTO after Seattle,Peterson Institute,2000,p.33.
(14) 虽然在理论上协商一致决策机制使每个成员方均享有否决权,但在实践中,协商一致的实际功效就像加权表决制一样,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主导WTO的决策方向。John Jackson,Sovereignty,the WTO and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12-115.
(15) Tommy Koh,The WTO's Fir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The Negotiating Process,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Vol.1,1997,pp.439-440.
(16) Richard Blackhurst & David Hartridge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WTO Institutions to Fill Their Mandat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7,2004,pp.705-706.
(17) Jeffrey L.Dunoff,The WTO in Transition:of Constituents,Competence and Coherence,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33,2001,pp.981-982.
(18) 如:努力使参与预期的“绿屋会议”的成员方被其他成员方知晓;在选择与会成员方时,在一定程度上照顾那些与所涉议题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成员方;使“绿屋会议”的会议记录在部分成员方中传阅,以便未参与磋商的成员方能够获得一些二手资料;用“小集团会议”取代“绿屋会议”之称谓,以减少成员方对它的排斥心理。
(19) Rafael Legal-Arcas,The Resumption of the Doha Round and the Future of Services Trade,Loyola of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Review,Vol.29,Summer,2007,pp.402-404.
(20) Sungjoon Cho,A Bridge Too Far:The Fall of the Fif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Cancun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Constitu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7,2004,p.241.
(21) Peter Van den Bossche,The Law and Policy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Text,Cases and Material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51-154.
(22) Richard Blackhurst,Reforming WTO Decision Making:Lessons from Singapore and Seattle,in Klaus Gunter Deutsch & Bernhard Speyer,eds.,Freer Trade in the Next Decade:Issues in the Millennium Round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Routledge,2001,pp.295-311.
(23) Jeffrey J.Schott & Jayashree Watal,Decision Making in the WTO,in Jeffrey J.Schott,ed.,The WTO after Seattle,Peterson Institute,2000,pp.283-293.
(24) 张向晨、孙亮:《WTO后的中美关系:与美国学者的对话》,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25) Kent Jones,Who's Afraid of the W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60-164.
(26) Amrita Narlikar,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Bargaining Coalitions in the GATT & WTO ,Routledge,2003,pp.16-23.
(27) Tomer Broude,The Rule(s) of Trade and the Rhetos of Development:Reflections on the Functional and Aspirational Legitimacy of the WTO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45,2006,p.235.
(28) Amrita Narlikar,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26.
(29) Peter Van den Bossche & Iveta Alexovicova,Effectiv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7,2005,p.677.
(30) 前引(26),p.716.
(31) “……而我倾向于称它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生形态。我称它为原生的原因是,它忽略了适者生存法则中的相互合作而完全片面强调竞争。”[美]乔治·索罗斯:《美国的霸权泡沫:纠正对美国权力的滥用》,燕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
(32) 关于霍布斯之“人人为战”的国际关系文化,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328—350页。
(33) “重新选举‘绿屋会议’的成员必将要替换掉一些现行‘绿屋会议’的参与者,为了获得他们对此类改革的同意,必须有一些保证他们利益的方法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补偿,有必要为他们提供补偿安排。例如,让‘四方国家’在特定问题上领导其他国家。”Kent Jones,Green Room Politics and the WTO's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in John- ren Chen ed.,Cooperative Global Governance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Principles and Challenges,Edward Elgar,2009,p.136.
(34) Inaamul Haque & Majid Ali,WTO's July Packag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Preferring Pragmatism to Ideology,Currents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Journal,Vol.14,Summer,2005,p.51.
(35) 宋泓:《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2期。
(36) 李计广:《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务实与互利共赢战略之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3期。
(37) 徐崇利:《中国的国家定位与应对WTO的基本战略: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科交叉之分析》,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11期。
(38) R.Ricupero,Rebuilding Confidence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Closing the Legitimacy Gap,in G.Sampson,ed.,The Role of the WTO in Global Governance,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3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