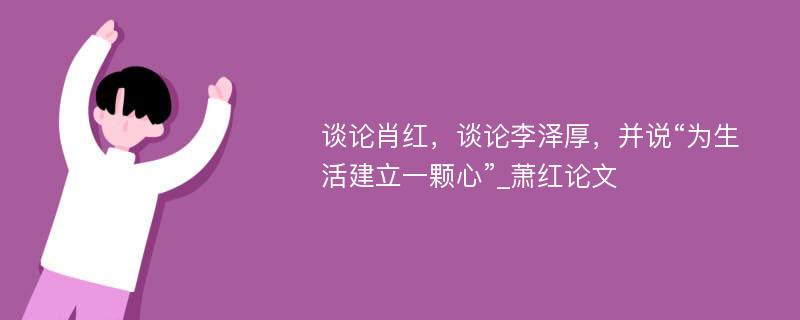
说说萧红,说说李泽厚——兼说“为生活立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泽厚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熟悉中国当代思想学术史和文学史的人们,无论具有怎样的想象力,恐怕也不会将萧红和李泽厚捏到一起。
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念头,竟然奇妙地发生了。《文艺争鸣》在去年就分别拟定的两个重点选题:“纪念萧红诞辰百年特别奉献特辑”与“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李泽厚美学专辑”,竟不期然地都赶排在这一期之内了。仿佛鬼使神差,穿越时空,他们相遇,这在作为编者的我们的确是不曾料到的。纯属偶然,却也令人惊异,令人想到历史的“混搭”和生活的“原态”,竟会是如此地“生活比人强”——谁说历史、谁说生活的时空混沌之体上没长着一颗活泼泼的“心”——谁遇不上谁!于是本期的编辑面貌和机缘遂使我有机会也有理由一起说说萧红与李泽厚,而且不仅机缘时不再来要抓住,让他们来赶一下这新世纪时髦的“混搭”之风也好吧。
萧红生于辛亥年的“北中国”呼兰(萧红有一短篇小说名《北中国》),在湖南宁乡李泽厚13岁那年去世。一生漂泊,孤旅南国,32岁的生命时间,百余万字文学作品,于阔大的中国时空中扬扬洒洒,飘落水边,呼兰河、松花江、青岛和上海的海与黄浦江、黄河、长江、香港的海和“浅水湾”……中国的水,作成了一代文学宗师萧红。而李泽厚为中国当代学问大家,哲学家、美学家,自湘江边而入京城后,就一直与京城相伴,职守数十年作一种“主流”的学问。此所谓“主流”,是说他的学问总居全国的高度,以中国学术的“中心”展开视界,横越中西思想,触及人类性的普遍性而返回中国本土性,建构体系,历60年而笔耕不辍,尤其在80年代中国新时期后大放异彩,可谓一直走在推动中国哲学美学思想的前沿。如今此翁已年过八旬,著述等身,十余卷字数当在萧红的三倍以上。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两人都不搭界。作为萧红的后来者,我们从李泽厚的众多著述中,似乎也没有发现他评论萧红的文字。
这是当然的。因为在既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评价体系中,萧红得不到更高的评价,因此仍然是寂寞得可以。因此也不能怪李泽厚不提到她。只有到了新世纪这些年,回首正在完型和逝去的20世纪,历史的烟尘渐渐落下,我们才意识到有一些价值在浮出水面,比如萧红。这时我们回首,重返多思的80年代,会发现那里不仅有李泽厚,也有萧红。只是历史的脚步过于匆忙,而我们的确有点粗心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开启新时期、走向新世纪的文学创造大潮中,有一句“各式各样的小说”的文学解放的口号,就出自于萧红。1982年第1期《十月》杂志上,发表了钱理群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与萧红诞辰七十周年》一文,首次引述了聂绀弩在《萧红选集·序》中记载的萧红的一段话:
有一种小说家,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由此,“各式各样的小说”一语不胫而走,为当时趋新闻路的探索作家所争传,成为当时小说创作中现代派、意识流探索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1982年第6期的《十月》杂志,又专门发表了李陀撰写的长篇论文《论“各式各样的小说”》,以萧红的这段话为宗旨,全面地评述了当时小说创作解放的情景:
萧红如果能够活到今天,看一看这几年小说的发展,她一定会感到满意的,这位有着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艺术上都不为任何成规所拘的女作家,当年在小说艺术探索中一定是相当寂寞的。不然她不会说出“我不相信这一套”的激言。所幸的是,她的呼唤并不是空谷回音。今天,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不仅“雪消门外千山红”,出现了我国小说史上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而且由于艺术上创新和探索之风越来越盛,小说还在质上处于迅速革新之中。这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作者”和“各式各样的小说”。
这里文章开篇所述的景象,还是新时期开风气之先的初始,如果看看后来的八五新潮和90年代文学,联系中国新世纪以来所显现的汪洋一片的偌大文坛,可以说,正是萧红在她当时的那句“不合时宜”的话,穿越了40年、乃至70年的历史风雨,而撬动了新时期、新世纪文学,那是她早年就为我们预设的一个思想支点。在这个历史意义上看,正是萧红,发出了近30年来中国文学“多样化”论述话语的先声,吹响了艺术解放和风格百花齐放的号角。在此,萧红和当代文学站在一起,和新时期、新世纪文学站在一起,和李泽厚也站在了一起。后来,李泽厚在写于80年代后期的长文《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有关新时期文学的部分,即用“多元取向”标题称之,并得出“选择”后的结论说:“世界、人生、文艺的取向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在文学上,“五四”文学是多元形态的,为人生、为艺术、现代派的等等,林林总总。但是五四文学没有“多元话语”,大家都是持己之见,抨击他人,乃直不可开交。只有到了萧红,才发出了这种容纳“多样”的话语,而这在那斗争激烈方酣的岁月,空谷足音足惜却不知足惜,只是到上世纪80年代,“重回五四”的新时期文学,才又拾起“多样”的文学之旗,不仅有了多元取向的文学,而且还形成了有关“多样性、多元化”的理论话语和共识,后者乃是“新时期”超出五四文学的地方,而属于“新世纪”。也因此,我们方可以说,萧红更多地属于当代文学,属于新世纪,她和李泽厚走到了一起。
有着这种“多样性”主张的萧红,其创作本身也是丰富的,大可以称为“说不尽的萧红”,这并不为过。萧红令人扼腕的人生和个性、才情,是多面发光的晶体,折射在创作上,有温情、叛逆、悲伤、痛苦、讽刺、恨、悲悯和爱,有国民性、抗日、地域、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有家国、民族价值和个人性情与意义,有生活原生态、怀旧、故乡、女性意识、童年记忆、青春、磨难、流浪出走,乃至大地、民俗、季节、自然、空间与时间的生命展开,有“越轨的笔致”与清纯的“童谣”,有现实、隐喻和象征、图画与诗。如此丰富的文学和近十多年来大红起来的张爱玲的冷漠、单调与灰色形成鲜明对比,而问题是我们曾试图把萧红一夜“说尽”,自以为把她已“说尽”,比如把她定格在“抗日”或“改造国民性”上,或新近以来把她定格在“女性主义”上等等,各取所需,也不免认知惰性。现在,认识萧红,从“现代文学史述”到新世纪文学视野,正是一个从“说尽”到“说不尽”的深化,或者说,我认为,萧红的文学世界正在“说尽”与“说不尽”之间。试想如果用李泽厚今天的理论眼光来打量萧红,也会得出如此的认识的。假若将萧红“说不尽”的种种,统一在一个基本面,趋向一个创作生命的整体性来“说尽”,借用李泽厚的概念表述,恐怕正是体现了所谓“吃饭哲学”和“情本体”的追求。正如鲁迅所说萧红的“越轨的笔致”和“力透纸背”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乃是一种具有“人活着”的生存状态性质的文学性的生活世界,维系在生老病死与吃饭过活的“度”上面(生死场),体现了“生活之本”的人类普遍性和中国人生存的历史真实。这是萧红一切写作的基本背景。而这之中,始终如一、全面地渗透、贯穿着一个“情”字,情天恨海的感性世界笼罩和包孕着这个基本生存面向,使之驱离冷漠和残酷,斩获同情和悲悯,乃是萧红为这个基本的“生存、生活、生命”所施立的本体之心。正是在“为生活立心”这点上,我们会看到萧红的文学正可以在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和“情本体”论述之间得到新的解释,作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萧红一生用“情”塑造了独特的以生活为本也以情为本的文学。以此为本,萧红文学向读者敞开了“说不尽”的可能性空间。
对于优秀的文学创作,“说尽”的统一性基层总被“说不尽”的现象喧哗所掩盖。而对于思想理论形态的写作则不然,它总是力图概念清晰、体系逻辑、自洽自足、以理服人,给人以真理“说尽”的雄伟印象。李泽厚的哲学、美学理论体系大厦的建构就是这样,数十年孜孜以求,从马克思到康德,从孔子到杜威,海德格尔,西体中体莫辨,终究建筑了属于他自己的精深而森严的概念体系,因此也可以用来给说不尽的萧红以有效的阐释并出示出一个整一性的独具特色的萧红。但如果我们依萧红的文学创作的“说不尽”性去质询李泽厚,把李的理论建构后现代式地也看作是一种“叙事”,那又会怎样?于是李泽厚毕生图穷竭力要实现的整一性的“说尽”,也终究要呈现出矛盾和裂隙,这同样不可避免。我们要指出的是,李泽厚是以“本体”建构为其“说尽”雄心的,他一方面坚持站在马克思和现代性的立场,以“吃饭哲学”说明“人活着”的根本或本根性质、实体性质,始终如一地将人的物质和生活(生存、生命、生产)作为其历史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的根本、本根;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人文性原则,建构了一个“人活着”的感性实在性向“情感”性倾斜的“情本体”,认为“只有‘心理’才能成为人所诗意栖居的家园。‘人活着’产生出它,它日渐成为‘人活着’的根本”。其实只要这样一摆,李泽厚的体系结构就会陷入难以说尽,就呈现了自身的矛盾与断裂,因为“本体”这个词大概是难以驯服的,孰为本?孰为体用?在物质或生活本体与情本体之间,“本体”一词呈现了有限性和无效性,趋于“本”的语义否定。其实李泽厚还不仅仅是二元论,他还有另一个“本体性”范畴“度”(实用理性),此话不提。但如果我们把李的理论建构同样看作是一场历史“叙事”的话,这样就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正可以看作他撞击时代语境的真实、可贵与情到深处不自已。和萧红一样,李泽厚这里呈现出“说不尽”的一面,而能有“说不尽”的情理意义面貌,这才是最可尊敬的。说穿了,萧红也好,李泽厚也好,他们的叙事仍然受时代语境之激之囿之福,都出示了这个时代的焦虑、分裂与悖论,一方面肯定基本生存和生活,一方面在物质面前说着精神其情何以堪!他们都不过是以情(或曰情本体)要为这生存这生命这生活立一个心罢了。李所谓美学是“第一哲学”,可以由一个“心”字来求解,何苦执一个“本体”之困之扰?
萧红和李泽厚有两种喜爱相同,一是鲁迅二是《红楼梦》。李曾说鲁迅和《红楼梦》是常置案头的。而萧终其生以鲁迅为师,临终表白“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长恨流水东。他们心中都是立有祖国和民族的。李泽厚评鲁迅,说其“提倡启蒙、超越启蒙”,这同样可以用来评价萧红。和鲁迅、萧红一样,1980年代提倡“重回五四”的李泽厚同样也是走出了五四的。如果我们今天“重回80年代”甚至“重回30年代”去寻找或重建萧、李,缘木求鱼不得鱼,最终会发现萧、李的意义正在当代、在新世纪。这就要说到对“国民性”的认识。鲁迅、萧红批判国民性以改造民族灵魂一脉相承,他们更多的是批判。相比之下,萧红可能还将这批判转化成为空间意象,旨向更超越,如她写道:
站在长城上会使人感到一种恐惧,那恐惧是人类历史的血流又鼓荡起来了!而站在黄河边上所起的并不是恐惧,而是对人类的一种默泣,对于病痛和荒凉永远的诅咒。
也许时代语境不同了,李泽厚走出80年代“新时期”,并未将注意力集中在批判国民性上,相反他很大意义上是个建构论者,他用实用理性、积淀、文化心理结构、新感性、乐感文化、华夏美学,以至情本体、生活为本,开掘“心理”,深探“情理”,为建设和开拓新世纪的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关怀现实,探头向未来。与这个时代的语境融在一起,李泽厚的研究实践有助于国人走出20世纪的长期受侮辱者的心理而趋向一个新时代中华复兴的健康人格。在这点上,其实“对着人类的愚昧”的萧红早就用她那已写就的“半部红楼”开始为现代性的困窘或伤害疗伤: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飞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哲学家趋向普遍性高天,而萧红从人类性回到地方,拥抱故乡。萧红发现了地之“理”,发现和阐发了一个全新的东北性为东北立心,也是从地方为中国立心。不是为“天地”立心,而是在生活中、在具体的地方、在东北立心,将天地立在中国生活中。这种天地由生的“心”或“心理”,是一种东北大地生长出来的自由的精神。电视剧《闯关东》的主题歌词:“你的怀抱温暖我冻裂的期盼/期盼在无边/那里命运会改变/千山万水走过只为这一片/自由的天地自由的家园。”说的就是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