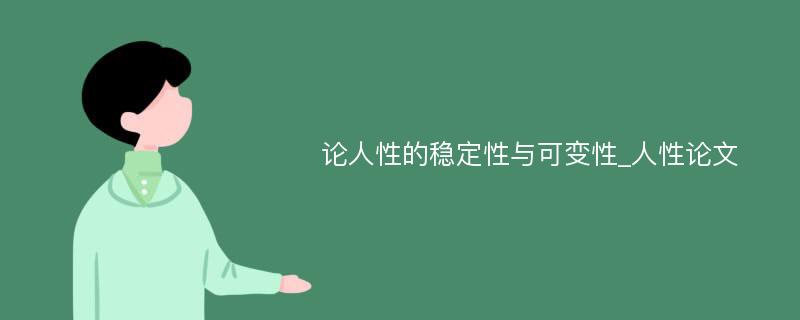
论人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变性论文,稳定性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1]。这是孔子关于人性问题极为珍贵的论断。但是,他既没有说明性为什么相近,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性经“习”之后又相远了。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2]。也就是说人性是运动变化的。但是为什么会“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对此告子没有论述。马克思关于人性的问题有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人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性前提。但是人的本质为什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对此马克思没有详细的论述,他只是说:“人的本质是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身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3]。但人是如何“创造”、“生产”人的社会本质的?他也是没说。现代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关于人性问题有段自相矛盾的论述,他说:“我们应该首先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人性并不改变。我不相信能证明:人们的固有的需要自有人以来曾经改变过,或在今后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时期中将会改变……文明本身便是人性的改变之结果……依我的看法,(他的)关于人性的无限制的可塑性的看法是正确的……人性不变的理论是一切可能的学说中最令人沮丧的和最悲观的一种学说”[4]。
上述这些观点是一个个迷,不断地困扰着致力于人性问题研究的人们,也不断地引发一场场论战。作者拟从人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的角度对上述观点作一些诠释。
一、人性的稳定性
本文所谓人性的稳定性指的是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永恒性、稳定性、平等性和无差异性。这是人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对立统一体的一个方面。
1.个体之间的无差异性
无论哪个民族、哪个集团、哪个国家、哪种肤色的个体,其人性的诸要素、诸层次都是稳定的、永恒的、没有差异的。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不全面,但他们却分别从性善论与性恶论论证了人性的平等性与无差异性。孟子说,性善乃人人具有的天然本质,因此,涂之人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性恶乃人与生俱来,经礼与义的教养,涂之人可以为禹。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认为,天下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无圣无愚,无佛无众,无古无今,人人都具良知,人人都是生知,人人都是佛。人人平等的基础就是人性的平等,因为人与佛都有性。他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人在自然天性上都具有同样的德性,“尊德性”是众人都能做到的,率性而为,即使是圣人所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圣人和凡人没有什么区别。圣人和凡人之所以没有什么区别,就在于都有“自然之性”。李贽说:“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逃荒野也。故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5]。莫尔则从人性自然论的角度论述了人性的平等性和无差异性。他说,人人都是自然产生的有血气、有理性的存在物。自然对人是一视同仁的,“绝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得天独厚,其命运比别人高超”[6]。
2.群体间的无差异性
无论哪个民族,哪个集团,哪个政党,哪个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它们之间的人性完全是一样的,没有差异的,都具有占有欲、生存欲、妒忌心等,这是民族平等、国家平等的人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个民族就会自认为自己优于其他民族,而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一个国家就会自认为自己优于其他国家而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从而导致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及被压迫民族、被侵略国家的人性失衡。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人性失衡势必导致这些民族、这些国家的个体人性的失衡。在人类历史上,这类事情太多了。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鼓吹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民族,这种优劣的差异最终被归根于人性的差异。如今,又有人抬出这种虚妄的差异,为自己的扩张制造人性前提。我在这里有一个悲观而又符合客观事实的观点(论调):有些民族或集团,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其具特殊的民族或集团个性。这种个性,在遇到特殊事件时,容易使这个民族或集团或群体的人性组合出现严重的失衡。我还有一个悲观的论调:群体人性与个体人性一样,尽管大多数个体与群体的人性在总体上和总趋势上能保持平衡,但是总有一些个体或群体的人性出现失衡。这就使得这个世界上总有小偷、强奸犯、贪污犯乃至纳粹、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也就使得我们必须不断地同小偷、贪污犯、强奸犯乃至纳粹、军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性运动变化的结果,是人类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3.历史的同一性
人性历史的同一性是指人性诸要素、诸层次在时间上的无差异性。今天的人性与昨天的人性,今天的人性与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的人性完全一致。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人有占有欲、生存欲、情爱、性爱等,而几万年前的人就没有。如果真的如此,人类早就灭绝了。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今天的人的人性中有个体性、群体性与类性,而几万年以前的人类就没有,如此,人类也早就灭亡了。至于未来呢?可以肯定地说,今天人性中的诸要素、诸层次将永远存在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就个体而言,人性诸要素并不稳定。他们会举出性欲来证明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早有论述。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婴儿同样有性欲(性要求),他们通过肛门排泄,通过嘴含母亲的乳头来满足自己的性要求。弗洛伊德说:“儿童对他的父母和照看他的人的所有感情都很容易转变成一种愿望,它表明了儿童的性冲动。儿童从他所爱的对象上要求所知道的一切的爱的记号,他要求吻他们、抚爱他们、凝视他们。他们声称要和他母亲或保姆结婚——且不管他对结婚是怎样理解的。他要把他的父亲当作婴儿,如此等等。在儿童身上毫无疑问,亲切的和嫉妒的感情完全溶合在一起。这种研究还表明,儿童运用怎样的一种基本方式将他所爱的人变成他的那种还未适当聚集起来的性趋向的对象”[7]。老人同样有性的要求。尽管性器官的功能衰退了,但老人需要老伴,需要依偎与抚摸,以及心灵上的安慰。这就是说,性器官只是达到性满足的重要途径之一。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达到性满足的途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人性中性这个要素的稳定性。
至于群体的人性也是这样。对此,休谟论述道:“在各国各代的人类的行动中都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同样的动机常产生出同样的行为来;同样的事情常跟同一的原因而来。野心、贪心、自爱、虚荣、友谊、慷慨、为公的精神,这些情感从世界开辟以来,就是,而且,现在仍是,我们所见到的人类一切行为和企图的泉源;这些情感混合的程度虽有不同,却都是遍布于社会中的”。你要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感情、心向和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你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就行了。因为“人类在一切时间和地方都是十分相仿的,所以历史在这个特殊方面(人性方面)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新奇的事情。历史的主要功用只在于给我们发现出人性中恒常的普遍的原则来”[8]。
二、人性的可变性
尽管人性诸要素与诸层次是不变的、稳定的与永恒的,但是人性并不是某一个或某些要素,也不是某个或某些层次。人性是由人性诸要素、诸层次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人性各个要素、各个层次之间的组合关系与运动形态又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人性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可变的、不稳定的。这是人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对立统一体的另一个方面。
1.个体与个体之间人性的差异
这种差异性并不是人性要素与人性层次的差异性,而是人性作为一个整体在个体那里的差异性。个体与个体之间,由于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不同,由于所受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由于天生性格的不同,其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组合的形态是有差异的,人性作为一个整体所呈现的形式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就会明显不同。有的人,个体占有欲在人性的组合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或主导地位,这个人就雄心勃勃。如果个体占有欲的扩张伴随着相应的群体责任感、义务感的扩张,此人很可能成为一位公认的领袖;否则,其人性极有可能走向失衡,从而导致犯罪。有些个体的同情心、怜悯心处于主导地位,这些个体的人性可能表现出宽容与同情。
2.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不仅个体人性之间具有差异性,群体人性之间同样也有差异性。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人性要素与层次的组合形式与运动形态是不一样的。因此,所呈现的民族性就具有差异性,有时差异性甚至很大。例如:沙漠民族的人性与草原民族的人性不一样,大陆民族的人性与海洋民族的人性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具体外化为风俗习惯、法律、文化价值、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不仅一个群体的人性组合形式与运动形态与其他民族不同,就是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集团、群体的组合形态也不一样,这些集团或集体因为某些共同的基础,会形成心理集体(或集团)。对此,勒邦论证道:“一个心理集体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无论构成这个心理集体的个人是谁,无论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职业、个性、智力是如何的相似或不相似,他们已组成一个集体这一事实便会将他们置于一种集团心理的控制之下。这种集团心理使他们在感情、思维以及行动上会采取一种与他们各自在孤身独处时截然不同的方式”[9]。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说这些民族、集团的人性要素和人性层次不一样,而只能说人性要素、人性层次组合形式不一样。这是统一中的特殊性,统一中的多样性。这种特殊性、多样性是一定环境与历史背景的产物,应该加以尊重,而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强求统一。当今世界就有这种危险,某些国家自恃自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军事实力强大,就自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具有优越性。这有可能导致新的“人性差异学说”,为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寻找人性依据。
3.历史的差异性
从时间上来考虑,无论个体或是群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其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组合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有时很小气,有时很大方;有时很残忍,有时很慈祥;有时很嫉恨,有时很宽容。一个群体的表现也是如此。唐末思想家罗隐明确指出,人和万物一样,没有一成不变、恒定不变的常性。他说:“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贞〕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日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救彼涂炭”[10]。
一个个体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个体,要面对各种群体,要面对其他的类,其人性的组合方式也不得不随时作出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杀人,你是下不了手的,但是,杀一条鱼就不能不下手了,否则你可能会饿死。一个群体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有不同的利益需要,要面对不同的其他的群体,要维护群体的利益,要维护群体中个体的利益,因此,作为一个群体其人性的组合形态也得不断地作出调整。这里要强调的是,群体的人性表现在个体的行为之中,融化在个体的人性之中,也就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性中都有群体性,都能有群体的认同感,并能维护群体的利益[11]。
4.人性运动变化的几种形态
概括起来,人性的运动变化主要有五种形态。
(1)人性平衡。所谓人性平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性要素与层次的不可缺失性,即任何一项人性要素与层次的缺失都会引起人性的失衡;第二,人性在总体与总趋势上的平衡,即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组合方式在总体上和总趋势上是平衡的;第三,人性中某个(某些)要素或层次的扩张必须有一个“度”。人性平衡是人性运动最为主要的形态。这种形态是社会平衡、稳定与发展的前提[12]。在这种情况下,人性的各个要素、各个层次之间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以使各个要素与层次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之上。对此,文子有比较正确的论述:“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祸福,治心术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贪无用,适情性即欲不过节”[13]。但是,文子想使人性达到绝对平衡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绝对的平衡是静态,而不是动态。我国南宋思想家叶适从义与利,功与志的关系论述了人性平衡的重要性,他认为,仁、义的价值必须表现在功、利上,没有功、利,仁、义就没有具体的内容,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只有把仁、义与功、利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实际的意义[14]。
(2)人性轻度失衡。当个体或群体的人性中某一要素取得相对优势时,就会造成人性轻度失衡,例如,当个体或群体人性中的占有欲取得相对优势,而其他人性要素又没有得到适度的扩张,这个个体或这个群体的人性就会出现轻度的失衡,若在这个时期能出现相应的外在扼制力量,人性仍能回复到平衡的状态。或者,人性其他要素与层次能及时得到相应的扩张,人性则能在新的起点上取得平衡。例如,个体或群体占有欲的扩张伴随人性其他要素诸如责任心、义务感、情爱以及群体占有欲与类的占有欲的扩张,人性就能在新的起点取得全新的、在总体上的平衡。
(3)人性严重失衡。如果轻度的人性失衡得不到及时的调整,就会发展为严重的人性失衡。这时,个体或群体的某一要素或层次完全摆脱人性其他要素与层次的制约,而在人性诸要素与层次的组合中处绝对优势的地位,就会产生自私自利与恶毒。关于自私是什么?贬义上的自私是人性失衡的产物。当占有欲摆脱人性其他要素,诸如责任心、情爱、同情怜悯心、义务感的制约时,占有欲就发展为贬义上的自私自利。关于恶毒的产生也是如此。但是,人性诸要素与层次中并没有自私自利与恶毒的地位。这些都是人性失衡的产物。小偷、强盗、贪污犯、强奸犯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人性使然,而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对此,罗隐有比较正确的论述,他说:“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纵者。苟非其正,则人能坏之,事能坏之,物能坏之。虽贵贱殊,及其坏,一也。前后左右之谀佞者,人坏之也;穷游极观者,事坏之也;发于感寤者,物坏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则为国之大蠹”[15]。
当然,也有受到意外刺激而导致人性失衡的。一般来说,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人性失衡的可能性越小。
这里涉及到英雄的产生的问题。英雄的诞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必然的英雄,另一种是偶然的英雄。必然的英雄其人性中某些要素(如占有欲、责任心、义务感、同情怜悯心)与层次(如群体性与类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人,只要条件成熟就会成为英雄。而偶然成为英雄的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其人性诸要素、诸层次之间的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化与组合,当同情心、义务感取得优势,他便奋不顾身,成为英雄;当生存欲和避害欲取得优势时,他便成不了英雄,而只能成为事件的看客。我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英雄没有贵贱之别,他们都是人性变化组合的结果。
(4)人性由平衡到失衡。这是人性由总体平衡进入失衡状态的一个过程。如前所述,人性某个或某些要素一旦取得支配性的地位时,人性就会失衡,或者,个体或群体在突然失去或得到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时,人性就有可能失衡;或者受到意外的刺激,人性也可能失衡。这就要求个体或群体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在得失之间,在意外的刺激面前保持人性诸要素与诸层次的平衡。有人会说,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个体或群体缺少情感、斗志与勇气?但是,我要提醒读者,保持人性的平衡,不仅需要勇气、斗志,更需要理智与更为深刻的情感。
(5)人性由失衡到平衡。一般来说,人性由失衡到平衡是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不论是个体或是群体都是如此。相比之下,人性由平衡滑入失衡则容易得多。因此,社会道德的约束力、国家法律的威慑力主要用于防止人性的失衡。对于那些已经因人性失衡而走向犯罪的个体与群体只能实施法律的制裁。
三、人性稳定性与可变性之间的关系
人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稳定性是基础、是前提,可变性是形式、是表现
没有人性的稳定性,人性的运动变化就失去了前提与基础。因为,人性的可变性指的就是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组合形式与组合形态。如果人性的某个(或某些)要素与层次出现缺失,人性的运动与组合也就无法进行。同时,人性的可变性则是人性得以外化的途径,是人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这种外化的途径与形式,人性将是一个无法捉摸的东西,人们无法对它进行认识、把握与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不少哲学家对人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有比较正确的论述。文子把人性的稳定性称为静,把人性的可变性称为动。关于动与静的关系,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智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形成,而智能于外”[16]。
2.稳定性是人性的普遍性,可变性是人性的特殊性
人性稳定性与可变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人性的稳定性是人性诸要素与层次的稳定性、永恒性、平等性、无差异性。就是说这些要素与层次是普遍的、一般的,任何个体与群体在任何时期都是具有的。人性的可变性是人性在具体的个体与群体那里的运动形态与组合形式,是具体的个体与群体的人性,是一种特殊。一般存于特殊之中,而不是存于特殊之外,也就是说,人性的稳定性即人性的诸要素与层次存于人性的可变性之中,而不是存于可变性之外。离开了可变性,就无所谓人性的稳定性。在中国人性史上,有些思想家看到人性的稳定性,如孟子、荀子等;有些思想家则看到了人性的可变性,如罗隐;有些则看到了人性的可变性也看到了人性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有力地、科学地论证人性的稳定性与可变性,更不可能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述对人性稳定性与可变性的分析与论证,我们就可以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孔子、告子、马克思以及杜威等对人性所作的论断。孔子所说的“习相远”,指的是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组合形式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孔子所说的“性相近”,指的是人性诸要素与诸层次的稳定性与永恒性。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对人性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告子强调的是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运动变化,所以他说:“性犹湍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人在生产过程与实践过程中”生产人的本质这个论断,在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生产”就是人们由于环境、地位和教育程度的不同而造成人性诸要素、诸层次在个体或群体那里组合形式、组合形态的差异性即特殊性,使得一个人终于成为他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这是个体本质、个体人性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也可以解决杜威的自相矛盾。没错:“人性不变论”是世界上最为令人沮丧的理论,因为人性诸要素、诸层次的组合形式与运动形态在个体与群体那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也没错:人性某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组成人性的要素与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