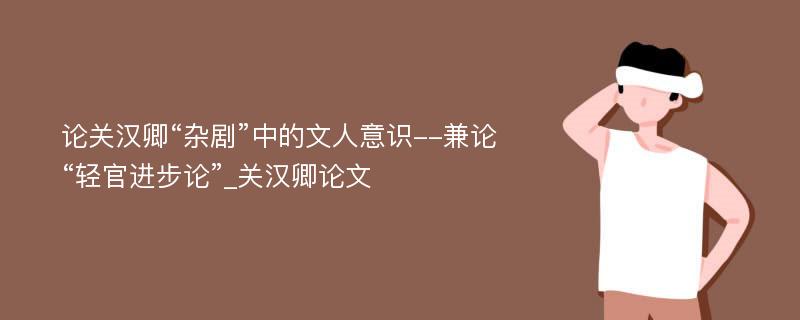
论关汉卿杂剧中的文人意识——兼议“不屑仕进”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剧论文,文人论文,意识论文,关汉卿论文,兼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汉卿杂剧今存18种[1],其中13种都涉笔文人形象。这些文人形象,在具体的戏剧情境中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行为表现,其形象意义各有千秋。但总体上看,都反映了作者一定的文人意识,体现了作者在当时“贡举法废,士无进身之阶”的现实情况下,对文人生存状态的体察和传统理念的认同。了解这些,有利于我们对关汉卿杂剧思想价值的准确判断,也有助于对关汉卿“不屑仕进”的传统说法进行新的思考。
一
关汉卿笔下的文人形象,按社会身份,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未做官的文人。如《救风尘》中的安秀实,《绯衣梦》中的李庆安,《金线池》中的韩辅臣。这类文人在戏剧情境中处于配角的位置,一般起引发故事或推动故事情节向纵深开展的作用。安秀实“央”赵盼儿“劝”宋引章不要嫁与恶人周舍,引出了赵盼儿与宋引章在当嫁何人问题上的激烈冲突,为以后赵盼儿的“救风尘”预作张本。李庆安的蒙冤受审,为显示开封府尹钱可断案的“剖决如流”开拓了戏剧场景。韩辅臣“一心要娶”杜蕊娘、使杜蕊娘的“智赏金线池”有了合理而自然的前提。这类文人形象总体的性格特征,是善良忠厚,重情义,诚实本分。
第二种类型,已做官的文人。如《望江亭》中的潭州太守白士中,《玉镜台》中的翰林学士温峤和王府尹,《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的开封府尹钱可,《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的济南府尹石好问,《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的洛阳太守韩廷干,《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和《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龙图阁待制、开封府尹包拯,《陈母教子》中的莱国公寇准等。这类文人形象,有的是故事的主角,如温峤;有的在全剧的关键关目上起主导作用,如包拯;有的贯穿并左右着全剧的故事发展脉络、几与主角人物的戏剧分量相伯仲,如《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的钱大尹。在具体的故事形态中,这些形象几乎都表现出正面的为官品质:清正廉洁,嫉恶扶善,重友情,尚贤德。温峤故事的演绎重心,不在于他的为官,而在于他如何赢得了称心如意的婚姻。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温峤外在的狡狯,包裹着对刘倩英的一片真情。而以真情求婚姻,同样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质。
第三种类型,经由科举之路终于跻身官员行列、或者必然很快为官的文人。如《窦娥冤》中的窦天章“一举及第”后“官拜参知政事”,又“加……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拜月亭》中的蒋士隆、《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的柳永、《裴度还带》中的裴度都考中了状元,摇身为官指日可待。这些文人,几乎都是在困厄的生活处境中执着于科举,并由于科举的成功,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蒋士隆和柳永,最后各自与自己钟情的女子“夫妻团圆”。裴度更因品格的高尚,在未参加科举考试前,就被洛阳太守韩廷干纳之为婿,与“天资英才”的韩琼英定下了婚姻。考中状元后,他虽因“圣旨”难违接受了御赐的婚姻,却难以抑制自己的“忆旧”情怀,表现出“真良才君子”的志诚心性。窦天章、裴度在困厄中不坠“青云”之志,裴度、柳永在得志后不忘旧日之情,都具有被传统的社会评价所赞扬的文人品质。
上述这些文人形象,在关汉卿杂剧所塑造的文人群体中占绝对多数。这些形象身上所体现出的正面品质,说明关汉卿对他自己所属的那个文人阶层的本能好感,也反映了关汉卿头脑中极具传统色彩的文人意识,那就是:肯定文人的才学,肯定官员的治德,肯定科举。
二
关汉卿对文人才学的肯定,多表现在他所写的文人爱情故事中,韩辅臣“幼习经史,颇看诗书,学成满腹文章”。济南府尹石好问称他为“白衣卿相”,济南府的“上厅行首”杜蕊娘对他情有独钟,“一心待嫁他”。两人成就姻缘后,杜蕊娘高兴地声称“似这等好姻缘”“称了平生愿”。柳永因“拿起笔作诗词,谆才调无瑕疵”能写“钓鳌八韵赋”“折桂五言诗”,被开封府的“上厅行首”谢天香真心爱慕,开封府尹钱可更称柳永是“一代文章渊薮”。正是凭着这等才学,柳永“一举状元及第”,不仅“春风得意”地“夸官三日”,而且最终与“心上人”谢天香“夫妇团圆”。
《玉镜台》根本就是一曲文人才学的颂歌。该剧所写的温峤娶妇的故事,脱胎于《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中的“温公娶妇”,但与原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关汉卿对历史人物温峤的官位、文才,与小说家演义中温峤“假谲”、“娶妇”的故事作了重新整合,整合中有意强化、突出温峤的才学之高,以和他“娶妇”时的年龄之老形成优、劣势臻于两极的鲜明反差。而故事的整体走向,让刘倩英从对温峤年老的嫌恶,转化到央求温峤“丈夫著心在意吟诗”,和与其“一心成其夫妻”,则使温峤的才学优势完全占了上风。作者称道文人才学的态度也昭然若揭。丝毫不难看出,刘倩英态度转变的契因,在戏剧关目的设置上显得非常生硬和突兀,人为捏合的痕迹非常明显。而正是这种人为化的戏剧处理,清楚地表露了关汉卿有意张扬文人才学的主观用心。
与对文人才学的称道态度相一致,关汉卿文人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具有特别的聪明才智。谢天香“能吹弹,善歌讴”。她即时改韵演唱《定风波》词所表现出的对诗词韵律的娴熟,临场创作咏骰子诗所表现出的即物言志的妥帖,无不显示出其文艺才情的养之有素和出类拔萃。韩琼英“天资英才”、“非同小可”,能连作“四绝诗不构思,出语走笔成文”。在这些形象的展示中,谭记儿(《望江亭》)“天然聪明”的诗才展示,特别能反映出作者的主观好尚。与谢天香和韩琼英在顺理成章的故事场景中展示诗才不同,谭记儿是在与花花公子杨衙内调情的过程中与之吟诗作对的。杨衙内最终落入谭记儿彀中,当然首先是垂涎其色,但是其中也不无对她诗词酬对出口成章的“高才”的由衷称羡。这里的戏剧处理实际存在着一种矛盾。杨衙内本是作者批判的对象,可是在他对谭记儿诗才的激评中,似乎又在传达着作者的声音,或者说,作者是在借他的口表达对自己笔下主人公诗才的赞赏。其中原因,只能说是作者太热衷于展示谭记儿的诗才,以至于不惜利用“智赚”的关目,借杨衙内为谭记儿搭建一个让她一展诗才的艺术平台。这种热衷,究其源,还是出自称扬才学的文人心理。
中国的政治,说到底是文官政治。而传统儒家思想对文官的要求,就是有治德,能安民。关汉卿笔下的官员形象,绝大多数都是治德突出,深受百姓爱戴。如地方官员中,郑州太守李公弼“声名德化九重闻”,所辖之地“良家夜夜不闭门”(《救风尘》);开封府尹钱可“陈纪立纲理庶民,聿遵王法秉彝伦。清廉正直行公道,播取芳名后代闻。”(《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洛阳太守韩廷干,“治官廉洁,秋毫无犯,家无囊蓄之资”,“处正道公行”,宁愿得罪上司,也不愿去“科敛民财”(《裴度还带》)。在中央官员中,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天章“廉能清正,节操坚刚”(《窦娥冤》);朝廷钦差李公子“随处体察采访”“拔擢英贤奏帝王”(《裴度还带》)。尽管这些称颂之辞,多是出自于这些人物的上场诗和自诩话语,有明显的程式化和概念化的印迹,但却也表现了关汉卿在这一问题上基本的思想态度;为官就应该勤政爱民、廉洁奉公。
关汉卿对儒家为官之道的弘扬,还具体表现三部公案剧中。《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中的钱大尹,审案有洞幽烛微之能。当被冤枉的李庆安刚一进大堂,他马上做出判断:“一个小孩儿,怎生杀了人?其中必有冤枉。”他鼓励李庆安“有什么不尽词,说来老夫与你做主”。在仔细查看了凶器后,他断定“这小的必然冤枉”。在他的周密安排下,真凶最终被缉拿归案。《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的包待制,判案时有意庇护“贤”、“孝”良民。平民百姓王氏三兄弟因报父仇失手打死了“皇亲”葛彪,依时律当有一人抵命。包待制念其家“为母者大贤,为子者大孝”,私自用掉包计保全了他们的性命。然而,这两个官员形象还不是纯粹的理想官员形象,因为服从于追求离奇故事,曲折情节的戏剧需要,作者让钱大尹曾因“前官问定”而欲将他明知冤枉的李庆安“判斩字”,包待制一开始审案也令手下对王氏兄弟“著实打”。真正纯粹的封建官员的理想形象,是《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包待制。包待制既有为政之能,又有刚正之气。他用拆字法蒙过皇帝,“智斩”“罪有百端”而又是受“皇恩可怜,迁除受职”的“权豪势要”鲁斋郎,完全是为了为民除害。他先后收养了与父母离散的李四的一对儿女和张的一对儿女,并把他们培养成才,又表现出哀贫恤孤的仁慈之德。在包待制身上,真正体现了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父母官”的民本情怀。
科举,在唐代就已经是文人们热烈参与而文学作品多有表现的内容,宋代亦然。关汉卿生活的时代,科举已经停滞,但是在他笔下的文人故事中,科举活动却依然普遍。其中,有文人自身对科举功名的自觉追求:窦天章“幼习儒业,颇看诗书”,为“进取功名”,撇下年仅七岁,又早已失去母亲的亲生女儿去“上朝取应”。柳永尽管十分眷情于谢天香,还是打定主意“今日辞了大姐,便索上京取应去”。裴度虽然“一贫如洗”,却“不肯做那经商客旅买卖、每日则是读书”、“房舍也无的住”,宁愿“在那城外的神庙里宿歇”,心里只想着“青霄独步上天梯”;有登第者的扬眉吐气;柳永中状元后,一面吟着“春风得意”的诗句,一面喝令“左右的,摆开头答,慢慢的行将去”。温峤自诩“首榜上标了名姓”做了翰林学士后,“俺帽檐相接御楼前,俺靴踪不离金阶上”;有社会上各色人等对文人科举行为的大力支持;当柳永决定“上京取应去”的时候,谢天香没有丝毫的忧虑和阻挠,她主动为柳永“准备停当”“衣服盘缠”,还交代他“休为我误了你功名”。开封府尹钱可为了让柳永去“那功名上留心”,故意对他厉声呵责以淬砺其志。裴度的姨父王员外怕裴度“堕落了功名”,表面上故意“相轻视傲慢”,暗中出资支持他“上朝赴选求官”。白马寺长老对“时运未至”的裴度“一日三餐斋饭管待”,“未尝有缺”,还鼓励他“你则是未遇间,久以后必当登云路”如此等等,说明关汉卿对文人科举行为的表现兴趣,也说明了他对科举的基本态度。
在关汉卿的文人故事中,有些表现科举的笔墨,甚至与故事的情节走向已经没有必然关联。如《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该剧在“楔子”中大肆渲染王老汉一家的科举热情,以后的情节进展中,又反复强调王氏三兄弟本应是“玉堂金马三学士”。包拯断案,上有王法,而当时的“王法”就是袒护恶人,包拯自己又崇尚贤孝,哀恤百姓,所以他在明白事情原由后用掉包计保全了王氏三兄弟的性命。这里,王老汉一家是读书之家,还是普通百姓,于故事的开展并没有本质意义的不同。再如《包待制智斩鲁斋郎》。该剧的故事本体,是写“花花太岁”鲁斋郎的为非作歹和包拯对他的惩治,可是作品最后,却写到李四之子“应过举,得了头名状元”,张之子“应过了举,得了官”,完全是可有可无的随意增补之笔。随意增补,却让人物“终亨”在科举成功的大圆满中,作者潜意识中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可见一斑。
三
“不屑仕进”,是历来关汉卿的研究者对其思想行为的惯用评价。这个评价,虽然语有所本[2](P7),但并不完全确切。
所谓“不屑”,从语义上讲,是指行为主体对什么人或什么事的轻视,甚至蔑视。关汉卿的生平行迹,由于历史留传资料的匮乏,现在所知甚少,通行本《录鬼簿》记载他曾为“太医院尹”,经专家辨析,“尹”为“户”之误,太医院户“不是官职,而是元代的一种特殊户口”[3](P39),其它再也没有关汉卿曾经仕进的记载,或许关汉卿一生真的不曾仕进。但不曾仕进并不意味着不想仕进或“不屑仕进”。从现有资料看,关汉卿大约“生于金代末期,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或稍后。”[4](P343)。在这个时间段中,唐宋文人视为“青云梯”的科举考试只举行过几次。第一次是元太宗至元九年(1238),这时关汉卿大约只有十岁左右。第二次是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而这时关汉卿已经八十有余。显然,在客观上关汉卿不可能由科举而仕进。不能由科举而仕进,关汉卿的仕进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因为当时做官主要靠“根脚”,即民族和门第的背景,关汉卿没有相应的背景。另外就是“吏进”,即从吏胥做起,慢慢熬到“入流”为官。但是,这一“熬”的过程实在太漫长了。《元史·选举志》载,“江北提控案犊,皆自府州司县转充,路吏请俸九十月方得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提控案牍,两考正九品,通理二百一十月入流。”二百一十月是十七年半,以十七年半的时间“屈在簿吏”,侥幸“入流”,也不过是正九品的小官,这对于具有“铜豌豆”性格又“博学能文”的关汉卿,实在是不堪忍受的。关汉卿没有去做吏。不去做吏,他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唯一一条可能仕进的道路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从表象上看似乎是绝意仕进,其实内里却潜藏着被动和无奈。
这种受制于现实环境的被动和无奈,反转成关汉卿笔下的文人故事,才会出现如上述那样的故事形态。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指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5](P3)关汉卿杂剧中的文人故事当然不能说是幻想,相反,还有相当程度的写实化特征,但是他在这些故事中,让文人凭着自己的才学,获得称心如意的爱情,或者取得令人艳羡的“状元及第”的科举功名,甚至有的更“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双美并至,则有很明显的主观臆想性。这种主观臆想,当来自于作者潜在的人生理想。清人王季烈在论及《陈母教子》一剧时说:“金末科目甚宽,至元初骤停科举,至皇庆二年而始复,期间无状元者且八十年。汉卿生于斯时,殆以不得科举为憾,有所歆羡而为此剧欤?否则此等文字,大可不作也。”[2](P117)“大可不作”的文字,关汉卿作了,个中原因,只能在关汉卿的思想本源上寻求解释,那就是:对传统的学优而仕的文人价值观的秉承和认同。
关汉卿一生没有出仕,元人熊自得《析津志》却将他列入“名宦传”。这看起来似乎不合事理,但传中的一段话也道出了其中原由:“(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词章者久矣。”原来熊自得是把关汉卿看成了地地道道的儒者文人,认为他所以长久地“淹于词章”,远离仕途,是因为当时的“文翰晦盲”,并不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主动选择。熊自得是元代人,他以当代人的思维意识去理解体会关汉卿的行为,应该比较接近事实。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对关汉卿生平形迹的叙述,习惯引用明人藏晋叔所描述的“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和关汉卿自己在[南吕·一枝花](不服老)套数中的自我情志表白,说明关汉卿的艺术才能和反传统的叛逆性格。其实藏晋叔的原话中还有值得注意的内容。这段话见于《元曲选·序》,其完整的表述是:“元以曲取士,计十有二科。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显然,在这段话中,藏晋叔不是单纯地记述关汉卿个人的行为、而是描述“关汉卿辈”的群体行为。他将“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的行为,放在“元以曲取士”的背景上考察,隐隐约约揭示了他们这种行为所内涵的逞才显能的主观有意性。至“或西晋竹林诸贤托杯酒自放之意”,则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对他们这种行为的心理本因的推断。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服老)套数,无异于一篇宣布与封建正统文人形象割袍断交的浪子宣言,其警世骇俗的强烈程度自不待言。然而仔细品读,那种对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行为的刻意渲染,总是激荡着一股愤然不平之气。从这股愤然不平之气入手去解读这个作品,很容易感觉到,关汉卿自称要“一世里眠花宿柳”、“向着那烟花路上走”,其实是以极端的行为描述,表达对“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的强烈否定,而这种否定中,自然包含有对文人“干禄无阶,入仕无路”的现实境遇的牢骚不满。胡侍在《真珠船》中,曾对包括关汉卿在内的元杂剧作家愤世的创作心态,作了一个很精辟的阐释:“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郁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关汉卿所以以那样极端的浪子形象自命,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关汉卿是伟大的戏剧家,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深受传统的修齐治平思想浸润的文人。他的社会批判,在揭露社会政治黑暗方面很有力度,却不曾有对文人科举行为的批判,由此也可反映他内心深处对仕进的态度。
标签:关汉卿论文; 柳永论文;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论文; 温太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