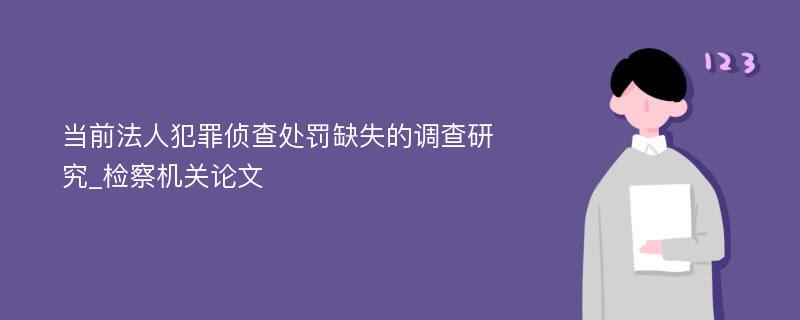
当前法人犯罪查处不力的调查与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87年1月《海关法》颁布以来,至今已有10余部法律和单行刑事法规对惩治法人犯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司法机关查处法人犯罪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然而,7年来司法机关查办的法人犯罪案件却廖廖无几。原因何在?笔者结合1994年上半年参与的对四川成都、乐山、夹江等部分地市县查处法人犯罪状况的专题调查,就此作些分析,并对实践中遇到的若干政策法律问题谈点认识,进而,就如何走出法人犯罪查处中的困境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一、法人犯罪查处不力的现状及其原因
从调查中发现,近年来法人犯罪日见猖獗,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在走私、偷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假冒商标、行贿受贿、投机倒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犯罪方面尤其突出。但对此大都未按法人犯罪案件处理,而主要是“以罚代刑”即仅仅对犯罪的法人给以行政处罚了事;即使对极少数已追究刑事责任的法人犯罪案件,往往也只追究了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没有追究其策划者、组织者的刑事责任,对单位本身也没有判处罚金刑,这实质上是按自然人犯罪来定性和处理的,从而遮盖了法人犯罪的本质。以上便是当前查处法人犯罪的总体现状。
综括这种状况存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法人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人犯罪主体不仅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还包括三资企业、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等。其中假冒法人行为与法人行为交织在一起,法人主体与自然人主体并存,并多采取伪造批件、介绍信、通知书、担保书、资信证明等手段进行犯罪活动,因而,往往难以区分,查处相当困难。如重庆市中区、沙坪坝、江津等9个区(市)、县财政局证券公司负责人和工作人员17人,非法向合川市证券公司拆借出1600万元资金,共收受贿赂47万余元。
2.无法可依的问题严重。现行刑事立法中,仅有一些单行刑事法规或附属刑法规范中对“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作了规定,而刑法总则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否适用于法人犯罪,如对法人犯罪的构成要件,一罪与数罪、共同犯罪、处罚原则等具体问题均未作出规定:尤其是以自然人为基础制定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有关法人犯罪诉讼程序的专门规定,也无任何有关的补充规定或必要的司法解释,从而使已有的法人犯罪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具体适用。
3.有法难依的现象普遍。由于法人犯罪所谋求的企业、部门或地区利益,在查处过程中,往往会因对“三个有利于”的不同理解或者是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作崇而受到地方党政领导、企业主管部门乃至执法机关的种种干扰和庇护,从而,严重阻碍了对法人犯罪的深入查处。
4.检察机关查办法人犯罪案件存在畏难情绪。法人犯罪往往罩着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的外衣,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出现,而且又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因此,检察机关对查办此类案件存有畏难的心理,不愿查、不敢查、不善查乃是当前查处法人犯罪的内部障碍。
5.对法人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存有误区。当前,一些地区和部门为了发展本地、本部门的生产,错误地理解生产力标准,弱化乃至抹杀法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为只要是为企业赚钱,没有中饱私囊,便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犯罪,或者认为虽构成犯罪,但情有可原,应当宽容和理解。加之,法人犯罪通常是抽象性的智力犯罪,其损害性和危险性不容易为人们直接感知,致使人们对其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甚或走入误区。
6.企业运行中政府行为的介入。时处经济转轨时期,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还远未实现,政企结合现象在不少地区、不少企业内仍严重存在。实践中,企业法人往往因受到种种干扰而变形运作:法人犯罪行为的实施多数也是在地方党委或政府支撑或操纵下所为,而不纯粹是法人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对法人犯罪的查处便涉及到一级政府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自然难以深入下去,实践中往往是“绕道走”,以行政处罚或仅仅追究个别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了事。如四川平武县服装厂与深圳某企业共谋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一案中,平武县服装厂起初并无犯意,但在该县政府的一位主管领导亲自召集县财政局、银行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商议并最后拍板后,才参与了犯罪行为,共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164万元,但检察机关最后只能以自然人犯罪立案处理。
7.打击机制合力不足。其一,对查处跨区域的法人犯罪(包括共同犯罪),缺乏统一的协调指挥机制。由于种种原因,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对法人犯罪的认识不一,带来了查处案件时的扯皮现象,甚至相互挚肘,各自为阵,目前检察系统已有的备案制度,也显得苍白无力。其二,行政执法机关越权现象严重。一些工商行政管理或税务部门受利益驱动影响,将一些依法本应移送检察机关处理的法人犯罪案件拒绝移送,而滥用职权,以行政罚款处理(因为行政罚款收入归地方,而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后,赃款则要上缴中央财政)。
二、查处法人犯罪中存在的政策法律问题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滞后性,查处法人犯罪的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政策法律问题,难以取得统一的认识标准,从而构成了法人犯罪查处不力的又一具体因素,所以,急需得到解决。其中,突出存在的问题有:
1.关于法人犯罪主体。尽管单行刑事法规和附属刑法规范对法人的犯罪能力和犯罪种类等已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对法人犯罪主体范围的确认尚无统一认识。有关刑事立法的表述通常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而“高检”在今年3月7日电话会议上则指出:“法人包括‘企业、事业法人’和‘机关、团体法人’两类。当前人们有时称法人犯罪,有时又称单位犯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并不全都是法人,但主要是法人。”两种表述的不同反映出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之间在法人犯罪的主体范围上存在不同认识。笔者认为,将法人犯罪的主体从“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缩小为法人组织、缺乏法人依据。就此而论,称为“单位犯罪”或许更为妥贴,因为单位既包括法人组织,也包括非法人组织,只不过“法人犯罪”这一称谓在现实中早已约定俗成,因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罢了,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远较其字面意思更为丰富的内涵。当然,对哪些种类的非法人组织才能作为法人犯罪的主体,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不可一概而论。
2.企业法人犯罪中的法人意志与法人代表人的个人意志的鉴别问题。犯罪意志本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核心,由于立法的不足,使得在鉴别某一犯罪意志究竟是法人意志,还是法人代表的个人意志时,往往出现认识上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在那些法人代表是唯一决策者的小型企业中。我们认为,如何区别法人组织的意志与法人代表的个人意志,应当结合法人组织的不同决策机构形式,具体情况分别处理。(1)凡属于有董事会机构的,以董事会的决议及董事会的授权内容、范围为确认标准;(2)虽有董事会存在,但执行总经理、厂长的行为却超出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又经董事会认可(包括默认),为本企业谋取利益,并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一律视为法人的意志;(3)没有议事机构,但明确法定代表人或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只要是厂长、经理以法人名义,非法为本企业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一律视为法人的意志。
3.如何鉴别法人行为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问题。如,四川某宾馆下属一企业经理赵某为资助从该企业退出并与自己有暖昧关系的女朋友,便从本企业出纳处拿出8万元,交其女友去“炒”邮票,后仅退回4万元。为弥补帐上漏洞,赵又与一私人老板串通,出具证明作假帐。案发后,赵与其女友都一口咬定是为单位而“炒”,自己并未中饱私囊,以此证明自己的行为是一企业行为。我们认为,衡量一行为是法人行为还是法人代表的个人行为的根本标准是,看行为人是否具有“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这一主观故意内容。如果有证据证明,且该行为又反映了法人的意志的话,应当视为法人行为,相反则应作为法人代表的个人行为处理。而在本案中,赵某事前利用职权之便,事后又盗用法人名义为自己辩护,显然不能认定为法人的行为。
4.能否认定法人共同犯罪问题。如前述共谋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一案中,不仅有两个法人之间的共谋,还有县政府主管领导的参与介入行为,是否成立法人共同犯罪?我们认为,鉴于目前查处法人犯罪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认定法人共同犯罪应慎重研究。不能机械沿用现行刑法关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理论。对两个以上法人事前共谋所共同实施的犯罪,对法人与自然人之间共同实施的犯罪;在犯罪过程中或事后有其他法人参与介入的犯罪等,应具体地分析研究以便确定是否作为法人共同犯罪来处理。
5.不同的法人共同实施犯罪的管辖问题。如前述平武县服装厂与深圳某企业共谋骗取国家出口退税一案中,两地同时立案,分别查处,给全面搜集证据人为地造成困难,不利于案件的查处。此外,因法人犯罪的查处涉及没收非法所得及赃款赃物的收缴,实践中存在司法机关受利益驱动影响,将应该移送异地受理的案子拒绝移送的现象。对此,我们建议,对涉及几个法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应以法人注册登记地为主,以犯罪地(行为地、结果地)为辅的原则,并补充以先受理原则,共同作为确定检察机关内部管辖权的根据。对管辖权有争议的,应本着有利于案件查处的原则,报请共同的上极检察机关协调或由上级检察机关指定管辖,由相关检察机关通力查处。
6.对构成犯罪的法人能否实行免诉问题。比如,乐山市物质经济发展公司法人代表吴某与重庆某公司共谋假冒生产“嘉陵”牌摩托车一案中,法人代表吴某是其所在企业唯一的负责人,乐山市检察机关拟对吴某免予起诉,从而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法人犯罪案件中,如果对法人的唯一责任成员适用免诉,则对该犯罪的法人自身该如何处理?对此,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查处法人犯罪案件,在实体法人应坚持“两罚制”原则,程序法上则应坚持“一致性”原则,即只能将法人及其责任成员一并起诉到法院。尤其在现行法律对犯罪的法人只规定了罚金刑的情况下,对法人免诉缺乏法律依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法人犯罪案件是应当坚持对法人及其责任成员处罚的“一致性”原则,但这种“一致性”有两种表现形态,即一般(而非一律)应将法人及其责任成员一并起诉到法院定罪科刑;但在特定案件中,根据其性质、罪行的轻重,检察机关在对法人的责任成员作免诉处理时,也应对法人适用免诉处分,从而,主张对构成犯罪的法人能够适用免诉。我们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在于,这种处理方式既能发挥免诉制度诉讼经济的积极效应,也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精神。同时,又避免了把法人与其有关责任成员适用不同程序分开处理(即对前者起诉到法院,对后者免诉处理)所带来的诉讼麻烦以及由此冲抵免诉效果的可能性。
三、摆脱法人犯罪查处不力困境的出路
查处法人犯罪不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面临法人犯罪日益猖獗的现实和趋势,司法实践必须尽快摆脱法人犯罪查处不力的困境。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加快刑事立法工作,不断完善查办法人犯罪的法律和法规。为此,(1)应将法人犯罪问题纳入整个刑法修改的范畴,总则和分则对法人犯罪的范围、犯罪构成、共同犯罪、定罪量刑原则以及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等问题,都应作出明确的规定。(2)对法人犯罪应增加资格刑(包括对法人组织的资格刑和对法人代表及主管人员的资格刑)的设置,以增强刑罚的威慑力。对法人可增设解散法人组织或限制禁止其从事某一项或几项职业活动等刑罚,对法人代表则可增设剥夺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或从事法人代表职务进行相关经营性活动的权利等刑罚。(3)对法人适用法律程序、提起公诉、能否适用免诉等也应予以明确规定。(4)对法人犯罪的立案标准,尤其是法人犯罪的数额计算方式等亦亟需明文规定。
2.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解决查办法人犯罪案件中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对法人犯罪的立法还不完备的情况下,一方面要通过调查研究,梳理出实践中无法律规定或界定不清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结合调研情况,“两高”应尽快统一认识,出台一些有关的司法解释,以解司法实践中的燃眉之急。
3.司法机关应把促进、保障《公司法》、《企业法》的贯彻实施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依法支持和保护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企切实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责任的经济实体。
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使人们走出对法人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误区,提高各级党、政机关对查办法人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应强化各级纪检、监察乃至人大的监督和检查职能,多管齐下,铲除地方保护主义的障碍和影响。
5.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对下级检察机关查办法人犯罪案件的领导和指导,特别要加强对跨省(地区)法人犯罪案件查处的指挥协调,以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增强打击机制的合力。
6.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争取各级党委的支持和重视,并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查处那些有影响的法人犯罪案件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法人犯罪案件,慎重而稳妥地处理边缘案件以及因地方政府的政策失误而导致的法人犯罪案件,以此为突破口,打开法人犯罪查处工作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