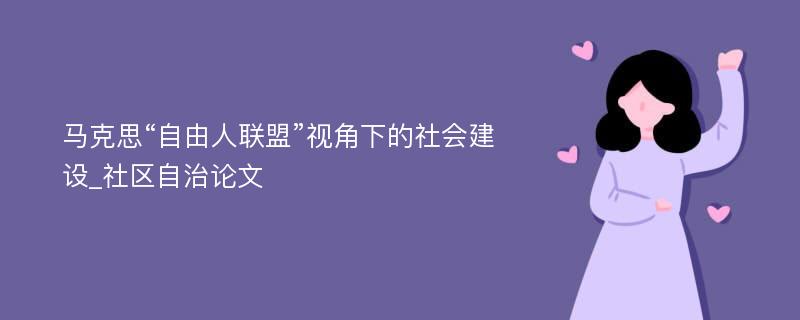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视域中的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联合体论文,自由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社会建设上的生动体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本身来看,推进重在民生的社会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也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日常生活与社会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社会是社会建设的客体要素和主体要素的统一体。正确理解“社会”的内涵,是科学把握社会建设,以合理的逻辑和路径推进社会建设的前提。
社会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存在,是个人的历史载体,个人是社会的现实主体,社会与个人是相互规定的。社会学中的“社会”,基于不同的原则设定,存在着社会实体论、社会结构论、社会功能论、社会关系论、社会活动论等多种定义方式。在西方,自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主张用系统的观点认识和解释社会。孔德认为,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似,是由家庭、教会和国家等组成的整体。迪尔凯姆指出,社会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现实,在逻辑上永远不可能经由个体加以解释。而在俄罗斯社会学者达维多夫看来,社会是由各种相互关联的元素及子系统组成的一种系统类型,其个体建立在反馈机制上,目的在于借助于一定界限内起作用的规律,实现个体活力的极值原则。这些定义或解释表明,学者们对“社会”概念的理解要么超然于现实生活之外,要么以“社会”的名义遮蔽了个体生存的真实根基。实际上,全面地理解“社会”,既要着眼于真实的个体存在,又要从个体的现实生活条件出发去理解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真实状况。这项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马克思反对抽象地理解社会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对社会作实证主义的或纯粹解释性的论证的方法(这正是传统社会学深度迷恋的方法)都是对“社会”的误解。唯物史观是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来说明社会的,认为社会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概念,是个人生活的一定方式和过程,强调“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71。就是说,源于人的直接生活的生存动力直接促成了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实践生成。社会是由个人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正如社会生产作为人的个人一样,个人也生产着社会。社会是以历史整体形成的结构性力量生产并维系着个人的“在世”存在,而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个人则是以“个人联合”的方式生产着社会。作为与个体相互关联的存在,“社会”的概念用以表征个人在实际生活的直接交往中彼此建立联系并共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个体”和“社会”并不是两个分离的实体,社会乃是个体生命或群体生活即人的实际生存的互济互助机构,由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和制度组成,是介乎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个体或群体交互作用的独立空间,包括城乡社区、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网络空间中的cyber(赛博)社会以及由流动人口构成的生存空间等。由此,我们把社会界定为“个人的组织化生活方式”,即社会是“个人谋生的基本单位”。这是对“社会”的狭义理解。换句话说,社会是人的关系性生成和共同生活的空间,承载的是每个人的生活样态和生活质量。
在经验的意义和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与人之间总是表现为一种“关系”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现实个人的共同活动。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自我”要么呈现为一种与他者的关系加以定义的客体,要么彰显为一种依据共同的规范而互助的独立主体。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并不是从伦理的价值悬设出发引出“社会”概念的,而是基于人的生存条件和实践活动的现实建构。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面对人民群众的贫穷、疾苦、污浊、劳累和那些贵族阶层及其代言人对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状况的默然态度,从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实际出发,展开了对他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批判。这种阶级立场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方向。这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条件出发,认识现实、分析现实、解构现实,努力剥离笼罩在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世界之上的意识形态幻象,并由此展望和建构一个“宜人生存和发展”的新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概言之,马克思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伦理关怀并不是建立在历史的起点处,而是新历史观的价值指向性。作为历史真正起点的是“人的物质生活本身”。因此,马克思的“社会”概念,首先是一个实践(历史)的范畴,其次才是一个伦理的范畴。
一般来说,社会建设就是构建人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条件和生活空间,即通过社会事业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社会制度(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乃至社会价值整合等途径,搭建人作为“人”的现实生活的社会舞台。实际上,社会建设就是构建一种承载人的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也就是特指与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的各种民生问题,包括人口安全、劳动就业、社区教育、交通环境、医疗卫生、收入分配、居住空间、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等。这是狭义域的社会建设概念。同包含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内的广义的社会建设不同的是,狭义的社会建设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基本视角,从国家和社会交互作用的视域,着眼于民生建设和推进社会自治,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的普遍福祉,推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区成为社会自治、自主的承担载体。在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中,当社会的自治、自主即社会民主真正彻底实现之时,政治民主和国家将随之消解。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自治、自主的伦理原则在实践中的推进,需要正确地“剥离”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视角审视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和实现社会自治的伦理原则之逻辑关系。
二、国家的伦理自觉与社区自治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四体”中的重要“一体”。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社会本位,社会本位并不是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是以国家的公共权力回归社会为根本目标的。这一逻辑的指向性就是社会自治与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构性,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度。就社会主义的实践维度而言,在公共利益的生产和供给方面,组织化的社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行动单位。现代化条件下,市场经济是人们生存的制度化,其张扬的是理性选择的工具价值。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合目的性的内在价值,需要借助工具的外在价值来实现。但是一旦手段和工具成为目的,人就会成为物的奴隶,被物所统治,人“是其所是”的内在价值就会丧失。人“是其所是”,不仅仅是作为人的内在价值的确认,而且是人成为人的自觉实践活动的范畴。后现代主义者鲍曼,对把一个个社区树起带尖刺的拦栅、武装到牙齿的守卫、家家户户制造的铁笼、居民之间的陌生和毫无情感的共同生活误认为共同体的嘲讽,是有意义的。马克思所说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自觉的道德生活。当下的社区发展指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理想的现实化。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公民化和公民化的社团成为社区自治的承担者。在一般的意义上,公民是指参加国家生活及享有权利资格的人。而在社区建设中,公民是指超越私人性而参与公共事务并承担责任与义务、善自身与善他人的人,公民社团可称之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作为社区建设的行动组织,与政治的国家一起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共福利的生产和社区自主。
人们生活实践的发展和生存空间(生产、交往、交换空间)的不断拓展,驱动着人们的利益追求日趋多元化。在“日常生活”的视域,对于人民福祉的实现路径而言,尽管人们热衷于服务型政府,但仅靠构建服务性政府难以全面实现人民群众多层面的社会福祉和个人自由。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中,实现社会自治和自主,要求恰当地处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界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环绕在“小政府、大社会”抑或“大政府、小社会”的循环之中的,而是基于道德和伦理的视域,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构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现代社会,只有国家在各个层面上为社会“松绑”,自觉推动社会的成长和社会能力建设,才能构建全方位的合作性治理体系。虽然社会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自治主体,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是国家必须以推动社会自治为方向,这不仅有利于减少行政成本,提高政府信任值,而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从而增进社会福祉。这就要求加强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设计。只有具备国家与社会展开合作的制度性框架,社区自治和自主的空间才能真正转变为现实的制度性环境。国家支持社区自治和自主的过程,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伦理相互构建的过程。
自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诉求,也是社会的一项正当的权利。然而,社区实现自治并不只是一种逻辑的设定,更是一种现实的行动。从“社会”起源于人类主体的能动活动而言,社区自治离不开一定条件,这种条件就是社区自治的资源基础。从主体的角度看,社区自治的资源基础在于作为主体要素存在的“社会”自身,包括社区进行自治的意识和能力;而社区自治的客观资源基础则存在于物质、信息和能量中,来源于社会本身拥有的资源和从政府获取的资源两个方面。就资源基础对社区自治形成制约的路径而言,现代中国社会行使公民自治的主客体资源尚显匮乏。这就要求执政党和各级政府着眼于社会建设,就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治安、交通环境等民生问题构建符合“以人为本”要求的制度框架。这里的“以人为本”,就是制度设计本身应“以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和自由发展为本”。在这种制度框架内,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共同体的存在,能够获取一种同一性的自我认知和心理,能够拥有获得社会生活条件的各种机会。这种制度设计应以制度化的道德即程序的正义为基本前提,以制度的正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制度性机会,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和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保护社会公平和制度正义。在以制度化的道德为前提而设定的公平而正义的制度环境中,虽然并非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完全按照美德的要求来行动,但是可以借助这种制度安排,促使人们遵守应当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这样,人们的道德生活就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以道义或义务的利他动机而行动;在正义的制度框架下的符合道德的行动。正是这两个层面的整合构成了社区自治的道德基础。
三、社会建设的历史蕴义:共同体生活
在日常生活视域,以社区自治的发展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活动,不仅是对社会建设的现实要求,而且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就整体或广义的社会而言,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实体存在,在中文的语义学中只是一个体现区域化的地理位置和虚拟网络中的共有空间的概念。英文的community,在中文中有社区、社群、社团、共同体的不同译名,但共同体与其他译名有着本质的区别。共同体是指人们的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生活组织体,并且是一个伦理概念。共同体具有社区、社群、社团的意味,但后者却不具有共同体所指涉的伦理义涵。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有条件谈论个人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代替国家的将是真正的“‘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2]324-325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马克思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时间上将人类共同体划分为古代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纯粹类型,是由母系氏族制度所形成的。父系氏族制对这种共同体的瓦解,男权制与奴役同源(性别的奴役),家长制家庭公社与私有制同源,这正是国家产生的基础。马克思以虚幻的或虚假的共同体指称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国家,就是因为产生于社会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作为独立的力量统治社会,少数人的幸福、自由是建立在多数人受奴役和丧失自由的基础上的。虚幻的共同体不仅是指国家这一实体,还包括一切不平等和有奴役性存在的社会组织体。共同体生活绝对不允许奴役的存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生活的伦理限定。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论述说明人类生存的实践是以复活共同体生活而发展的,“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179这就是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实现,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在社会历史中生成,不是以伦理的应然建构为条件,而是基于人们生存的物质前提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真正的共同体一旦形成,它又必定是伦理自觉的、自足的道德生活。这也是对当下以社区自治的发展生成“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提出的以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建构的正义制度安排来维系的道德生活的可能性问题。
对现代社会是否有共同体生活的存在,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人类的历史时间上,腾尼斯确认共同体是自然而然的、古老的人身依附的礼俗秩序;社会是新的、契约的法理秩序。社会瓦解了共同体,共同体不可人为。显然,腾尼斯所指涉的社会是近现代的市民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把古典古代的氏族制度、家长制家庭公社、乡村公社、行会、宗教组织等团体均视为共同体,体现了他对共同体这一伦理实体的怀念带有强烈的封建主义的情愫。与腾尼斯不同的是,马克思虽然也指出了共同体的演变是客观的历史过程,古代共同体遭遇私有制的瓦解、国家的产生以致消亡是必然的,但在社会历史观上,一方面马克思的生存论的共同体的条件及其伦理形式异质于腾尼斯的意志本体论,另一方面马克思阐明了实践视域的人为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形态更替的类型时,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逻辑,即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史”过程。对此,只有在对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创造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中,才能把握这一自然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解释是,一方面,人们在确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基础,但政治、宗教、道德等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有着正向的或反向的作用。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个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活动并非总是受必然性支配,而往往是受偶然性支配,“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3]697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中的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3]696从历史的必然性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社会对抗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33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揭示这一自然必然性,而是以追求合乎人的目的性生活的共同体为价值目标的。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强调规律性或科学性(历史科学)与价值性的统一,旨在为人们追求和实现合乎人的目的性生活的共同体指明方向。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只是因为受个人生活条件的支配才隶属于这个阶级,因此并不存在阶级的共同体这一生活的组织体。但是,当无产阶级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为能动地、自由地、自觉地创造历史而联合起来时,这种联合就会成为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形式,“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121,并由此超越因人们生存条件而受偶然性支配和受自发式运动的自然必然性的支配状态。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是无产阶级作为各个人自觉联合的政治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以往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而形成的国家,又不同于国家自然消亡后的真正的共同体。只有这样的国家并以其为公器才能使各个人占有生产力总和,达到自己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1]129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或人民的国家消除了历史上国家作为共同体的虚假性。这个共同体不同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也不同于理想的真正的共同体,但正是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为人类解放以至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条件。这样的国家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揭示的“人为共同体”的路径,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合目的性生活,全面推进社会建设。为此,我们党和国家的伦理自觉一方面要指向民生,另一方面要在社会本体上推进社区自治进程,从而把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性与合乎人的目的性统一于社会建设的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