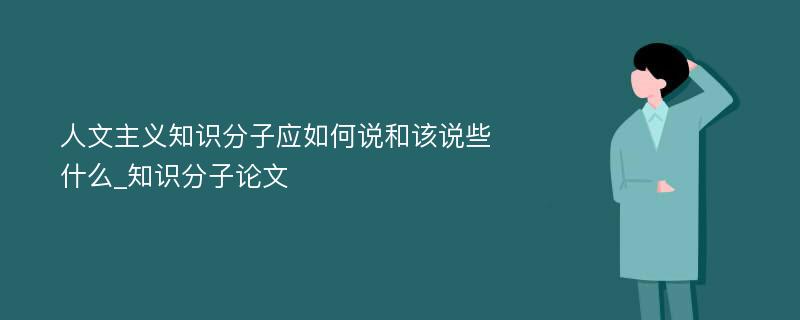
人文知识分子如何说话、该说什么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什么话论文,人文论文,说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宾诺莎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如果一个人非要等到获得食物与饮料有益于他的完全和不可辩驳的证明时才肯吃或喝,那么他早就饿死和渴死了。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以此在她的《日常生活》一书中论证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能根据习惯和可能性,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她举了一个例子:当你赴宴时,你大吃大喝的理由只能建立在惯例上(主人邀请客人吃喝,乃是出于热情的好客之心)和可能性上(食物不可能有毒,而是对人身体有益)。
人文知识分子角色的功能问题当然并非只是个日常问题,实用主义的惯例与可能性规则的应用对之无济于事。但是,当当代知识分子的功能仍被传统地界定为(面向人类、历史、时代)说话时,同样有个类似的问题:我们(人文知识分子)能否说话,如何说话,以及该说什么话?
这里,我们首先遭遇到知识分子功能的合法性问题:社会的其它角色均不以说话为职责(他们的存在合法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可证可见的实用价值),人文知识分子为什么必然要对超越于自己之上的存在物(人类、社会、历史、时代)发言呢?他理直气壮言说的根据何在?
一 合法性问题的产生
从历史看,知识分子角色的功能问题一开始并不存在。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知识便被从其价值形态上分出级别:其最底部是日常操作所需的知识,最高点则是真理知识,后者统领日常生活的实验,这种信念发展的结果,便是日常知识因其卑贱地位,实际上被从知识体系中排斥了出去,所谓知识则成为对高级知识乃至最高知识的专称。
中国古代的情况亦大致如是。“士”不仅鄙薄一般的日常知识,而且对劳动生产实践知识亦不屑一顾。“知识”一词实际指的是那种上可以安邦、下可以修身的“大道”之学。很显然,这种知识作为无形的社会财富,一开始就被霸占在少数人(上层阶层)手中(所谓“学在官府”),追求知识成为这少数人的特权,因而知识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垄断的产物。古代的知识构架是与政治权力结构内在一致的典型金字塔型:知识分子高据知识的塔顶,而连识字都成问题的民众则构成沉默的塔基。整个一部知识的历史便是一部知识分子独语的历史——他们自设自问、自问自答。
这种知识的历史状况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千年面貌。一方面,它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萎缩——既然知识被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所垄断,知识分子便不得不在权力面前臣服,并且知识的最高目的也成为能见用于权力,能被“用世”——孔子、孟子的一生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后世约定俗成的“士大夫”一词,更意味深长:知识载体的“士”与权力载体的“大夫”(它是一种皇庭官职)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种知识对权力的从属关系,固然在知识分子身上形成了如某些论者所指出来的“臣妾意识”;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知识分子地位的传统优越感:尽管知识必须依附于权力,但知识分子毕竟也由此挤入了权力统治的塔顶,他们不但有操纵话语的知识权力,还因此拥有更为现实的权力——学而优则仕,知识的少数人垄断现状使他们与这一少数人集团——统治阶级,自然合流。如此,知识被意识形态化,知识分子亦被意识形态化,二者均成为维护、改良现存统治秩序的有力武器,他们的权威性获得由上至下的普遍认同——一部写满农民起义的中国历史,有过一次由下至上的“知识造反”吗?
知识的这种荣耀地位造成了它的内部循环,一方面,被知识排除在外的多数人集团(下层阶级)中的某些“有志”分子野心勃勃,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知识,以便能购买一张爬上金字塔顶的门票。然而一旦成功,他便迅速被中心化,成为少数人集团中的一员,他的多数人集团的出生背景被引以为耻,千方百计被涂改、遮掩,并且摇身一变为多数人集团的对立面(古代中国从乡村爬上去的官宦有几个不处心积虑为自己编造一份豪门世家的履历,或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呢?);另一方面,少数人集团为了永保自己在知识网络中的绝对优越地位,也采取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措施:第一,为了防止“知识造反”,他们向多数人集团打开一扇知识的窄门,让他们有跻身知识之林的机会(其方式是科举选拔之类)。但由于知识已被意识形态化,因而当多数人中的优秀分子在接受这种既定知识时(如科举考试就规定了“四书五经”作为应试内容),他们其实也在接受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驯化的现存统治维护者(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知识不可能完全被意识形态化,少数知识分子仍能从被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的知识现状中看出其本真的一面,从而识破意识形态知识的虚伪,以及知识中蕴藏的人文真相,明末李贽对“理学杀人”的控诉即一例)。这种结果,在上层统治集团看来,既平息了下层阶级可能会因为被知识拒绝而产生的怨愤心理乃至造反冲动,又能不断为自己的统治添砖加瓦,补充新生力量,真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第二,为了保持知识垄断的永久有效地位,也为了那扇向多数人集团打开的知识之门不被拥护之众挤得越来越大,以至到最后呈现决堤之状,统治集团设置了许多障碍,其一就是语言:他们为知识专门规定了一种远离日常、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语言,并将此作为自身阶层的标签。非日常化的知识语言犹如神奇的天籁,高高回响在大众的上空,令他们顿生膜拜崇敬之情。
这种语言就是文言文。中国几千年的语言史就是一部文白对立史。文言文拒绝了多数人集团的加入,它成为知识的象征和入场券。所谓“之乎也者焉亦哉,熟读七字做秀才”,向知识塔顶(亦即社会权力塔顶)的进军某种意义上转换为对知识语言(文言文)的征服。但是,这种一成不变的知识语言成为规范、成为霸权性语言后,它必然会对不断积累从而要求突破的知识体系自身形成禁锢,因而在统治阶层内部也经常会产生“语言造反”——在此过程中,文白对立一步步遭到削弱,白话文渐渐渗透到文言文中,知识语言的领域逐渐变得广阔,通向知识塔顶的窄门也越来越大(晚清科举考试内容的不断演变就颇富戏剧性),最后终于抵挡不住内外压力,“决堤之势”轰然来临。
这场“决堤”式的“造反”即五四白话文运动。尘封已久的知识大门终于打开了,被禁锢了几千年的知识第一次始见天日,它挣破了意识形态化的牢笼,摆脱了少数人专利品的被垄断地位,随着民主、科学精神的张扬,以及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引进,它俨然找到了自身的真正家园。
但是,在这场深刻的造反运动中,有关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核心观念却并未触及。知识大门虽向广大同众打开了,但能畅通无阻的只有少数智力精英分子,他们占据知识大厦的要位后并不甘于仅仅以智力优秀者身份自足,根据“知识即权力”的内在法则,他们还自然而然地转换了自己的原有角色,将“智力精英”转换为“社会精英”,从而秉承了传统的“代天立言”“替天宣道”使命,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向全社会宣读“真言”,将自己的知识视作最高知识,并理所当然认为社会在倾听、服从自己。这种自信的潜在危险是:一当“天”与社会中的政治对接起来后,知识与知识分子又将被意识形态化,从学坛滑向政坛,从而在可怕的历史轮回中又不知不觉充当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成为现存秩序无条件无原则的维护者(实为牺牲者)。诚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已被历史充分证明。
这种危险来自何方?知识分子传统的“臣妾心理”固是一个内因,但更多的还来自传统、社会、知识分子自身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功能的体认。知识语言造反,知识之堤崩溃后,知识与知识分子走出了庙堂,然而,他是带着过去时代的自信与自任走出来的,他以广场取代庙堂,面对虚拟中的千万听众,高高在上,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布道性演说。这种演说的姿态似乎自然而然,合理合法,以至无人质疑。
然而,真是如此吗?知识分子天然就是个布道者吗,哪怕历史变迁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其实,自语言知识之堤冲决时始,知识分子就已经面临着一个不为他们所察觉的角色功能合法性问题了。悖论仅仅在于:这个合法性难题恰恰是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被解放造成的,他们豪情万丈地为自己发掘了一个足以吞噬自身的陷阱。
在古代,由于知识的被垄断状态,向社会宣讲知识自然而然成为这少数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权力,全社会只有他们拥有知识,由此,知识分子(知识精英)与大字不识的大众之间的二元对立划分客观成立,而由知识高位(知识分子)向知识地位(大众)的输送(这种输送在“五四”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知识启蒙)也就合情合理。不仅知识分子自己,而且社会、历史也认可了他高居庙堂之上向全社会说话的权力和姿态。整个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他(知识分子)说”/“你(大众)听”的“独语/沉默”相互映衬的历史,作为知识主体的“人”则一直缺席——“他”不过是背倚庙堂,“代言”而已;“你”则被动接受,对所听所闻不可质疑亦无法甄别(因为缺少知识)。
但是,知识之堤崩溃后,知识被解放了,知识的传统等级秩序被打破,各类知识及其主体地位发生了一个历史性变化,知识分子所占有的“哲学知识”在知识开放的时代里只不过是知识之林中并不一定绝对高贵、高明(更不用说它还有可能被指责为“无用”的“伪知识”)的一种,而操作性实用知识的地位大大上升。西方近现代科技文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初入国门之际,虽被传统士大夫不屑地贬为“奇技淫巧”,但它发展壮大的趋势毕竟不可阻挡,在今天乃至成为知识的核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知识者的地位日渐显贵,而人文知识者则每况愈下。再者,根据摧毁知识之堤的武器——民主、科学的精神,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人人都有权力去追求知识,成为知识分子;人人可以去追求自由、真理、信仰,追求真、善、美;人人可以有自己对知识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理解,而不必再仰仗于知识分子的唯一合法性解释。如此一来,知识分子或有可能还高踞于知识塔顶,然而却不再因为知识的特权性而成为社会权力结构金字塔的塔顶部分了(除非他努力去使自己被意识形态化),从而也就丧失了高高在上的历史权威性,更不用说由于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事实上也已不再具有对大众颐指气使的优越权力。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解放,真理、价值、信仰、意义……等这些貌似至高无上的“哲学知识”,也已向全体的自愿追求者开放,因而知识分子传统法宝代言人的角色也摇摇欲坠了,他再也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和理解灌输给“大众”,他“启蒙”的合法性依据亦成问题(由于知识的解放,启蒙者—精英/大众的对立区分业已消失),这样一来,他原先的讲坛中心位置和神圣光环就开始黯然失色了,他面向“大众”的演说便常常淹没在“大众”的众声喧哗中,他独语的历史潮流一去不返了,“大众”沉默的时代也终结了:现在他们可以或回应,或反驳,或不理睬,或乃至不屑于倾听知识分子的言说。作为(面向时代、社会)说话者的角色受到了挑战:在一个人人皆可成为说话者的时代,凭什么必须是知识分子“你说我听”?——与历史潮流里“大众”成为知识分子说话对象的“你”相反,现在,知识分子也成为“大众”可以加以诘问的对象化“你”(一个不无恶意的极端化例子是:当代知识分子常常受到“大众”的如此攻击:你们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
以上是学理化的探讨。在现实中,我们当然可以争辩说,一,知识解放的程度尚远未达到理想程度,知识等级秩序依旧或隐或现存在;二,“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只是理论,现实中的不平等或曰知识高位/低位的区分仍严重存在;三,知识大众的“我性”亦即主体性尚大可存疑,至少尚未发育完全,因而他们的“众声喧哗”仅是远景。然而,是否因此知识分子就可以置自己学理上的角色功能合法性问题于不顾(倘是那样,以知识学理探求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置于何地)?还是相反,因为遇到了这个存在合法性难题,知识分子便干脆缄默不语,将自己消融到日常大众存在中去(那样又无疑自动取消了自己的角色)?
当下知识文化界种种争论不休的混乱状况,我以为都是由此二难选择造成的。因而,正视这一难题,实已成为文化界难以避退的燃眉之急。
二 职业与志业之间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是当代知识分子角色困境的另一个原因。
古代中国的“士农工商”既是一种尊卑有别的社会等级秩序排定,亦是一种以“士”高居榜首的不平等社会分工(君主则“受命于天”,不受社会分工的约束)。知识分子的职责从此意义上发展出两个向度:一是为意识形态服务,为统治合法性提供证据;再一是知识分子由对知识的占有中发展出一种天职感,即,将对知识的追根溯源亦即追求普遍知识(为知识立法)视为自己理所当然在所难辞的使命。从第一个向度产生了用世文人,其职责在于建立起与统治相一致的知识体系(包括对传统知识的改造),为维护、改良现存秩序殚精竭虑,上为君主先忧后乐,下对民众施以教化,从第二个向度则产生了某种可称为“学人”的文人,他们将追求知识视作志业,把对比较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真理、信仰、审美……等等的追求内化为自己生命的至高构成,以此来成就自己。然而,在历史上,两种知识分子形态并不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纠缠,互相渗透,互为倚靠,将政治功用与志业追求奇怪地合为一体。走进庙堂,他们心忧天下,是个坚贞不二的忠臣;退回内心,则“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直指知识根本,于终极意义与普遍伦理之间来往驰聘,在价值信仰与真理险途中苦苦跋涉,虽九死而未悔。不过,不同于西方传统哲人对纯粹知识的纯粹追求,知识的天职感在中国古代文人身上是与非个人意图紧密相联的。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个体对“道”的“求索”并非是对纯粹真理知识的探求,而是被置于“修齐治平”序列中,“修身”成为“平天下”这个终极目标的出发点,出儒退道,其志均在天下,因而中国古代并未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志业型学人。相反,由于整个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才占有知识,他们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代表整个社会操作知识,由此将自己个人对知识的思考探索包括个人修养视为决非一己之事,而是关乎国家天下,关乎社稷存亡,这导致他们说话的姿态一开始就是外向的,即指向社会和时代,指向一个虚幻无边的“天下”(如果加上意识形态化因素,这种外向姿态更是显得理直气壮)。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摧毁了知识分子这种自信、自觉的说话姿态。作为一种不带歧视亦不带褒扬的现代分工,知识分子行业与其它社会行业在理论上是平等的,知识分子并不比其它职业者高贵,他对知识的操作与所谓的“神圣天命”并无关系,而只不过是社会的客观选择与他自身的自我成就要求而已。由于与意识形态合流不再荣耀,而是被视为异化,他首先就失去了面向“天下”说话的合法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次,社会分工使知识分子成为一般职业,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则纯然是个人选择,被排斥于社会任命系统之外,又进一步限制了他说话的外向可能性;第三,随着知识的被解放,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独断地位受到质疑,他不无伤心地发现:往日虔诚温顺的听众如今已风流云散,正离开他三五成群谈笑晏晏。如此一来,现代知识分子这个以“说话”为职业的角色,他忽然觉察到传统的说话姿态在今天已行不通了。
这样,在现代分工的意义上就必然明确地分化出两类知识分子:一是作为社会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整理传播积累性知识、以知识技术操作为己任;一是作为个人志业的知识分子,他虽然离开了昔日社会文化中心讲坛的显赫位置,但仍将自己视为人类命运与时代困境的思考者,他亲眼看到:“真理”、“信仰”、“自由”、“美”……这些存在虽然名义上被解放了,然而并没有因此获得蓬勃生命力,相反,它们一旦从牢笼中释放出来,反而消失了往日因神秘而显得神圣的光环,变为毫无吸引力毫无独异处的日常词汇,继而又被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所淡漠、遗忘。有别于历史上的被霸占,它们如今被遮蔽。他还看到:“道德”一旦从传统的普遍规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遭遇的不是自由,而是崩溃,它由历史上的被窒息命运变为了今天的破碎现状……面对凡此种种,他不能不走向痛苦的反思,从而自觉承担起时代信仰、价值命运的思考者角色重任,并将此角色视为知识传统的一种内心召唤,在无所任命中自我任命,毅然选择一种纯粹个人化状态的存在。
然而,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作为职业,他得到社会认可;作为志业,他可以默默将生命贡献于学术与思考,但一当开口,则似乎缺乏面向全社会全时代说话的合法性依据。首先,时代并没有为他预备好听众;其次,即使他的声音能穿透时代的喧嚣,他也得冒被听众指责的危险:你是谁?谁让你来这样和我们说话?我们难道需要你的教诲吗?我们难道不能选择自己的活法?歇着吧你!你以为你比我们高明多少?这种合法性匮乏意味着:传统志业型知识分子的说话姿态尚有待作出某些调整。
的确,在目前状况下,作为个人志业的知识分子角色并不为现存秩序所鼓励,因为他并不份属社会分工的系统中,况且,与意识形态决裂的姿态也很容易导致反叛而不为统治者所喜。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双重被拒绝往往导致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感。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有鉴于此,则非常明智地提出一种“后知识分子”立场,即取消判断,进行文化观望,在“跨越鸿沟、填平界限”中与大众话语狂欢共舞。实际上,在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由于实用主义哲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的流行,信仰、价值、真理……等等已被当作一些不能证实的命题加以抛弃。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当下的文化现状:一方面,在功利实用之风统治下,是对道德、信仰、真理……的普遍遗忘(或嬉戏);另一方面,是一批拜伦式的英雄,高举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孤独悲愤中发出一遍遍绝不妥协的宣言:在此之外,是一些痛苦的沉默者与思考者,他们处于动摇乃至虚无之中,无从构筑自己的立场,……
这是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角色分崩离析之时,也是最受考验之时。他或者中止外向性说话,保持沉默;或者退回内心,喃喃自语;或者缩回职业化的硬壳之中;或者在职业角色的边缘自我话语游戏。
他该作何选择?
三 超离社会分工的自我选择
继知识解放之后,现代社会分工为什么必然将志业型知识分子驱向困境?
无疑,现代社会分工带来了人的一次大解放,但象任何事物一样,它也有自己不曾意识到的消极后果。它对传统人文的一个致命打击是:它拒绝接受现存秩序之外的任何游离存在,换言之,一切非秩序游离物都要被社会分工这张大网整合为秩序链上的一环,才能获得存在合法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认为在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中,被社会分工所遗弃了的诸如妓女、奸细、凶犯、魔鬼、反抗诗人、强盗……等等文学形象,体现了一种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和否定——然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则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转换为现存的肯定性力量形象才得以存在)。由此,个人被职业化、专业化,个人选择被社会选择强行同化。一个分工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如马尔库塞笔下发达的当代西方社会),亦是一个越来越趋向于取消个人的个体性存在与个体性选择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只是社会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只需专司自己的职能,此外不必过问其它。这就是所谓现代社会的结构功能性自我运转。
职业化的个人与个体性的个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前者必须是某种社会角色,有自己的操作极限,生活在一定的角色规范中,并遵从角色规范来行动。他的运行轨道是被规定的,个人无权更改。而个体性的个人则与职业性规定无关,他首先是一个自由的生命存在,拥有自己的感觉和思考,并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以“我”的眼光而非以职业的眼光面对世界并参预进去,他听从自己心灵与思想的命令,而置角色规范于不顾。
然而,现代社会分工的最大努力,就是要把个体性的个人纳为职业化的角色存在,将它变为秩序因素,变为自身结构上的一环。很显然,越具有个体性特征的存在趋向——如自由思考、对社会的个人性批判、对历史文化的独特反思等等——就越难被转换进社会分工的秩序之网中去(现代社会分工可曾为“思想家”留下一个职业位置?!),相反,由于这些个体性存在特征的反职业化、反社会分工性,它们只会对社会的结构秩序形成冲击与颠覆。因此,职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既成文化秩序、体系内操作)能被社会接纳,但个体性亦即志业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思考、批判现存知识文化秩序为天职),却被社会无意识地排斥出分工体系之外,无处安身。
由此可见,如果说现代社会分工在其诞生之初带动了历史潮流的巨大进步的话,那么,今日它已实际上成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它以貌似公允、科学的立场,却无所不在维护着现存秩序的稳定结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为现实统治出谋划策的政治家是一种社会分工,但以推翻现存为天职的革命造反者却决不是一种现代社会职业)。这种意识形态迫使现代知识分子从以前的许多领域撤退(如形而上学领域),一步步将自己职业化,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以期取得这个重功用的社会的认可。这样,个体性知识分子便成为现代社会中失去番号编制的游兵散勇,越来越被排挤到所谓的“边缘”,成为无需加以理会的一群孤儿。
将这种知识分子的出路建立在推翻现代社会分工的伟大设想上是可笑的。指出现代社会分工的意识形态性只是意在说明: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想让自己无条件被职业化,成为现存秩序内循规蹈矩的职业工人,而仍想在个人志业范围内维护知识分子的某些应有功能,那么,他必须采取这样一种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姿态,即:必须努力挣脱完全职业化的牢笼,走向一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为自身的存在立法,而决不能指望能从现存社会中找到自己存在合法性的证据。他必须明白:现存的一切合法性途径都是来自这个只重功利、实效的社会分工,而个人的自我选择——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功利与实用,则完全不需要这种合法性途径的援助。只有当他自觉地把自己从现代分工的成见中分离出来,他才有可能摆脱自身功能合法性的困扰,以个体身份开始真正地思考那些有关人和世界最基本、最原始的问题——意义、信仰、价值、真理、道德……等等,而这些问题,在其它社会职业那里,大都被“思考这些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或“思考这些并不能给我带来实际好处”等等理由被搁浅、拒绝。
由此,新个体型知识分子便很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双重存在:一方面,他不得不是某种社会角色——职业知识分子,以尽自己的社会基本义务;但另一方面,他又是超角色超职业的:他仅仅是一个“人”,一个能够思考、能够选择、能够批判和否定的“个人”,他将文化思考与批判视为自己职业之外的“志业”,以个体性自我为思考与表达的出发点。他只须坚持这个立场:说出我自己。个体化形态是最适合于他的说话姿态,他并不替某个高于他之上的存在物立言,他所说的一切就是他的所思所感,个人文化生命体验和感悟是他说话的依据;他并不以知识垄断者或知识精英自居,向一个虚拟中的“人类”“时代”发言,换言之,他并不是先确定了听众,再来决定说什么话,如何说话。他仅仅如实说出他的观察,他的思考,他的判断,这或许是关涉人类命运的,或许是关涉时代现状的,或许是关涉文化普遍命题的,或许不过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情感体悟……对他而言,说出即一切。而这一切的真实性,均来源于他作为个体性“个人”的存在,来源于他作为一种有限生命在内心所感受到的生命恐惧、愤怒与虚无,以及他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所应具有的良知、理解及公民使命感。
当然,这种全新的志业型知识分子,由于坚持自己的个体性立场,因而不可能接受意识形态化。他无所依附,只是自觉地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思考者;他身处文化传统与历史延续之中,被置身在人类的当代精神境遇之中,他不逃避这一切,而是以“个人”身份参预进去,思考他认为应该思考的问题,说出他认为应该说的话;同时他还明白:自己决非全知全能,决非“精神导师”“中心权威”,他不追求自己的启蒙者角色,更不企求自己成为民众的教化大师,相反,他牢牢记住:自己始终不过是一个“人”,一个未在角色规范中忘记自己本来存在面目的个体存在,一个在这个充满遗忘的世界里仍然执拗地捡拾着一些古老记忆的“拾荒者”。
无疑,由于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不预设理想听众,不求助于社会分工和意识形态,志业型知识分子的这种说话姿态并不必然地具有权威性。这无关紧要。因为他并不想号令听众,更不想以思想的仲裁者自居。某种意义上,这种自我化的言说反而保证了其纯粹性和独特性。它的价值在于:在这个人人忠实于社会对自己的分工的社会里,在这个人人均无法将思考与判断视为一种可加以选择的社会职业的时代,志业型知识分子毅然从社会分工的天罗地网里脱身而出,在精神的意义上主动成为现代社会离家出走的流浪者,怀着独异乃至怪异的目光和声音,以自己那从熙熙攘攘的人群影像中自觉分离出来的真实背影,一声声敲打着貌似天衣无缝的文化现实秩序,寻找其裂缝,以此来守护住那日渐被这时代所抛弃、忘却的自我真实,并在这渐被物质和实用操作主义统治的大地上,为人类精神和思想的超越性存在保留住最后一块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