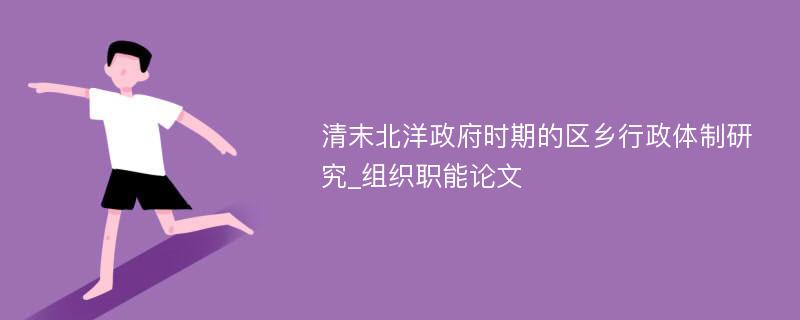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清末论文,时期论文,行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2-0063-13
一、前言
中国自秦至清,正式职官的设置止于(州)县,农村社会虽然存在以各种名目的乡官和职役人员为首领的乡里组织,但没有区乡一级国家行政。这样一种地方体制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一时期,各地陆续生成了各种形式的区乡行政区划和组织,它们尽管缺乏划一性和连续性,但却大致具备了现代行政的各种特点(注:从中外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角度进行界定,现代行政须具有以下不同于前现代贵族、绅士式治理制度以及使用民役办理公务制度的基本特点:(1)具有科层化、普遍化的常设公共机构;(2)行政人员具有职业化的公职身份,并通过法定程序得到任用;(3)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法定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4)在履行政治统治职能的同时,侧重于履行公共社会职能。)。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为此后国民政府乃至人民政府时期全国统一区乡(镇)行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动荡、国家分裂,使得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区乡行政没有统一、稳定的规制,往往因时因地而形态不同,因而极大地增加了相关研究的难度。迄今为止,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制度史家对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和个别地区实行区村制度有简要记述。例如,钱端升、萨师炯等著《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钱实甫著《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述及民国初年山西和云南的村自治制度时,均提到山西省在县之下分“区”;后者并提到1920年代初“联省自治”运动中颁布的《浙宪》和《湘宪》规定县以下划分“市乡”。(2)有关清末地方自治的研究(如马小泉著《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对于当时各地城镇乡自治机构的设立有所记述。(3)近代警察史的研究者(如韩延龙、苏亦工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对于清末某些地方在州县之下划分警区有所叙述。(4)有些区域社会史研究对于这一时期某些地区内的县以下政权组织有所探讨(如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5)海外学者孔飞力(Kuhn,Philip A.)、杜赞奇(Duara,Prasenjit)在他们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社会和地方财政所作的研究中,都指出中国自清末以来存在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深入的趋势,但对于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区乡行政的生成过程、具体形态均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财政》1979年,载《东亚研究中心论文集》第3集,芝加哥,见以下杜赞奇书;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海内外学术界所做的上述工作,或局限于个别地区,或局限于制度设计,虽然可以为我们了解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区乡行政提供一些分散的知识,却不足以揭示其全貌和具体施行情况。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由于缺乏系统的统计资料,本文对于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的考察,只能主要采取中国传统制度史家的常用方法,即以当时中央和各地地方政府的有关制度设计为经,以散见于各种史料中的具体实例为纬,参互搜讨,以见其异同,求其实相。这种方法的使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统计性资料缺乏的无奈,但同时也符合本文厘清一代制度的主要宗旨,且符合当代科学哲学所认同的规范。众所周知,传统史学中的举证方法就形式逻辑而言基本属于简单枚举法,它同其他各种形式的归纳法一样有着局限性,即不可能穷尽各种有关事例,不可能以全称判断的形式得出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论。但是,它也同其他归纳法一样可以给人以新的知识,并且如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指出的,通过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可证伪性,因此可以为有关论题的进一步探讨留有余地。
二、区乡行政生成之缘起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生成之缘起,一方面在于古代尤其是清代乡里制度的历时态演变;另一方面在于20世纪初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的共时态挑战。
史籍记载和近人研究均表明,中国古代乡里组织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秦汉至隋唐,“以士大夫治其乡之事”,乡里组织首领人员(如汉之三老、啬夫,北魏之三长)的性质是乡官,社会地位较高,不仅履行国家行政职能,而且主持乡里事务;唐中叶以后,乡里组织的首领人员(如宋之里正、户长,元之里正、主首,明之粮长、里长)系“以民供事于官”,属于“役”,社会地位卑贱,职责主要是应付官差[1](《职役》二)[2](《职役》一)。清代也是如此,里甲长、保甲长和乡地等均属“民役”而非“乡官”,仅仅在催纳赋税、征发差徭、查报案件等方面支应官差,而地方公益、自卫、教化、教育、民事调解等建设性乡里事务,系由士绅、宗族等私人势力以及某些临时性、自发性会社(如联庄会、青苗会)承担。这样,清代的乡里公共职能系统,就分裂成为了各具利弊的两种机制:一方面是乡地、保甲等,它们由政府统一督建,近似现代行政那种普遍化、科层化特征,然而其首领人员却属于“贱役”,“流品在平民之下”,“不足为治”[3](P92)。另一方面是士绅和宗族领袖,他们因其“乡望”而具有现代行政人员那种受到社会尊重的地位,但却属于没用公职身份的私人势力,没有被纳入(或联为)普遍性的组织机构。显然,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较为理想的乡村公共职能系统,出路在于对上述两种机制各取其利而舍其弊。换言之,这种系统一方面应像保甲、乡地那样具有普遍化、科层化特征;另一方面其首领人员又应像士绅那样具有较高的声望地位。冯桂芬提出著名的“复乡职”建议,其根本内容就在于此。而这种乡村公共职能系统不是别的,恰恰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区乡行政。
19世纪中叶以后,这样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区乡行政,在一些地区萌芽。其途径大致有二:其一,士绅介入各种旧乡地组织,使得后者在本来具有的普遍化特征之外取得了郑重性,从而在无形之中演变为现代区乡行政机构的雏形。清末民政部的一项调查指出:“自咸丰、同治以来,地方多事,举凡办防集捐、供支兵差、清理奸宄诸事”,地方官“无不借乡社之力”,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地在职能和人员构成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职能方面,这些旧乡地组织不再局限于“细故之裁判,公用之科摊,案证之传质,护田防盗之计划”等卑微琐碎的官差应付,而是开始履行较郑重的地方行政职能,主管“新政旧章之颁布”,“且有牧令依以收赋税、集团练者”。在人员构成方面,这些乡地组织的首领除“平人”外,开始有“生贡”和“职衔军功人员”;地方官对乡地首领的待遇,虽然有些仍“贱之如皂隶”,但也有些则“贵之如缙绅”[4](P5639-5640)。其二,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一些地方由士绅主持的团练机构具有普设性,并广泛履行地方保卫之外的其他职能,因而开始兼有地方行政机构的性质。对此美国学者孔飞力指出,咸同年间一些地方的团练“与其说是作战单位,不如说是行政单位”,因为它“是与设防据点相联系的地方管理编制”,有时甚至被赋予征收赋税等非军事职能。据此他认为,19世纪后期出现了“绅士领导的团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的过程”[5](P107,225)。这符合事实。19世纪中叶后各地以士绅为首领的团练,往往具有在州县全境分区普设的系统化特征,从而成为一种准区乡行政,并在以后沿袭下来。例如上海县志书记载说:“吾邑全境区划起于咸丰末之团练,当时城厢内外分十六段,直辖于总局,乡则设局二十二处,就近匀配分领各图,撤防后地方办事仍沿段董、局董名义。”此后直至民国初年,“地方行政区划”“即以二十二乡局定为二十二区”[6](《疆域志》)。又如广东顺德县,“县属十区之划,萌芽于光绪十年甲申,时法攻越南,筹办团防,因创意分县属为十团,募勇以时训练”。第二年战争结束,团勇裁撤,团局解散,但十区之制却沿袭下来,清末推行地方自治,正式成为自治区域[7](《舆地志》,《建置志》)。
办理近代化地方社会事业的需要,构成了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生成的又一背景。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地方公共职能之所以可以由士绅等私人势力来承担,是由当时社会的封闭性所决定的。例如,农业自然经济仅靠农户个体生产和乡里简单交换即可维持,而不需要社会化的市场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依附于科举制度的读经教育仅靠私塾和自学就可以完成,而不需要全社会统一的学制、教材和教学;社会治安的维持只需靠保甲制度监查外来人口和举发盗窃等案件,而不须面对开放社会人口大量流动情况下所出现的各种治安问题,等等。然而至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地方社会兴办的各种实业、教育和社会事业往往具有标准化、专业化等近代特点,仅靠州县官和私人势力承担公共职能的传统机制根本不能与之相适应,必须顺应时势,建立包括区乡行政在内的科层化行政系统。对此当时即有人指出说:
如小学教育所以造就国民,民间子女皆须就学,以户口计之,一县之中当有小学校数十处,造就教员,又当有师范学校。而建筑校舍,则当相度地形,稽查学龄,则当编订户籍。又如水陆道路所以便利交通……工商繁兴,学校林立,市廛罗市,车马骈阗,在在与道路有密切之关系。他如卫生事宜……则当清洁市衢,修建病院。积储事宜……则当收敛米谷,存蓄金钱。自余庶务,至纤至细,更仆难终,断非守令一二人所可独担,亦非绅士数人所能分任[8](下册,P715)。
这样,传统乡里制度的历史演变同近代化的时代要求因缘和合,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就生成了各种形式的区乡行政。
三、区乡行政的各种形态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动荡,朝令夕改;国家分裂,各自为政,各地处于生成之中的区乡行政因而形态各异。大致说来,当时各地的区乡一级行政就生成途径而言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清末以来地方社会近代化进程启动后所新生;其二是由清代旧乡地演变而来。
(一)新生的区乡行政
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纷纷兴办近代实业、教育,建立新的治安保卫体系,推行地方自治。在此过程中,各地在(州)县以下陆续建立了各种为传统社会所从来没有过的区乡行政。这种纯属新生成的区乡行政,就其职能来说又有两类:一类仅履行某种单一职能;另一类则职能全面,宛如一级政府。兹分述如下:
1.单一职能类型的区乡行政
(1)区乡教育行政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时,最初并没有想到要在州县之下普设区乡一级行政。当时,它只是出于推行新式教育和警政的需要而要求在州县之下划分相关的职能性区域和设置相关的职能性行政人员。然而,这却改变了中国二千年来州(郡)县以下不设治的传统制度,使得区乡一级行政得以滥觞。换言之,中国近代的区乡一级行政,是从教育、警察等单一职能性行政开始的。
清末“新政”开始后,直隶、江苏等省在州县之下划分学区,设立劝学人员以推广学务。为了统一规制,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劝学所章程》,其中规定“各府厅州县应就所辖境内划分学区”,“每区设劝学员一人,任一学区内劝学之责”,垂直隶属于州县劝学所[9](《学务官制及劝学所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在建立区乡行政方面的最早官方创制。此后,各地纷纷依照规定在州县以下划分学区,设立区乡教育行政人员,称劝学员或乡视学、学董,还有一度称“议员”者。例如,浙江省定海县1906年分东西南北四大学区,各设劝学员一人;山东广饶县1907年成立劝学所后,置“乡视学四员”;直隶广宗县1908年“全县分学区四,设劝学员四人”[10](《教育志》)[11](《政教志》)[12](《法制略》)。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学务划为自治范围。于是,一些开始推行自治的镇、乡废除垂直隶属于县劝学所的劝学员,设立隶属于同级自治公所的教育行政人员,称学务专员、学务委员,如江苏宝山县月浦里乡、江湾里乡、嘉定县钱门塘乡、疁东乡、真如乡等均属这种情况[13](P125)[14](P36-37,131,484,639)。1914年2月,北京政府下令取消县议参两会和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乡董,而在有些地方乡镇学务委员却继续存在,由本镇、乡经董呈请县署任命。是年12月,北洋政府又颁布《地方自治试行条例》,规定在取消县自治的同时仍实行区乡一级自治,其自治范围包括本区教育事务。与此相适应,教育部于1915年8月颁布了《地方学事通则》、《学务委员会规程草案》和《劝学所规程草案》,规定在县以下各自治区组织学务委员会办理教育事务,每自治区设学务委员1-2人,并且可以进一步在境内划分学区[15](民国四年册,P605)[16](第1298号)。在有些地方,这种隶属于区、乡地方的教育行政人员曾长期存在。例如,江苏省宝山县1914年将14市、乡划为7学区,学务委员每区1员,直至1920年代一直存在;浙江省1914年地方自治取消时各区曾设立职权独立的学董,“代行从前城镇乡董关于教育职务”。后设立隶属于区、乡的学务委员,“各区学董一律裁撤”[14](P131,484,639)[16](第610号,《教育部咨复浙江省长文》)。
据现有资料,区乡教育行政平行隶属于本区、本乡的“块块”体制只存在于少数地区,其他许多地区仍实行“条条”体制,即区乡一级教育行政垂直隶属于县劝学所、视学所、教育局,江苏阜宁县、山东馆陶县、直隶广宗县和福建省各县的有关情况均可提供例证[17](《内政志》一)[18](《政治志》)[12](《法制略》)[16](第1176号)。1923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县教育局规程》,规定各县“酌划学区,每区设教育委员一人,受县教育局长之指挥办理本学区教育事务”,确认了这种体制[15](民国十二年册,P412)。
(2)区乡警察行政
清末州县区乡警察的编练最早实行于直隶、江苏和东三省,各地办理方式不一,通行的是,在州县境内划分警区(相当一部分州县以城厢地方为中区,而以四乡为东西南北区),推举或委任各区乡士绅统带本乡警察,称警董、区董、巡官、巡长,其身份属警察首领,此外是否兼负区域内的警察行政职责,则不得而知[19](《兵防考》)[20](《政治志》)[21](《经制志》)[22](《吏治志》)。“预备立宪”期间,区乡警察行政正式形成。1907年夏清政府颁布《各省官制通则》,规定各州县“应将所管地方酌分若干区,各置区官一员”,“掌理本区巡警事务”。次年4月,清政府民政部拟定《各省巡警道官制》,重申了这一规定[8](上册,P510)[23](P833)。1909年以后各省巡警道陆续设立,各州县警务机构一般称警务公所,由巡警道委派区官,作为区乡一级警务行政首领;委派巡官、巡长作为区警首领。一些地方还保留地方推举产生的警董,负责筹集警款[12](《法制略》)[24](《建置门》)[25](《地域考》)[26](《巡警志》)。
入民国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8月颁布《县警察所官制》,其中只规定在“县区域内之繁盛地方”设立警察分所,而没有提及在县以下普建区一级警察行政。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许多地方仍普遍划分了警区,普设了区一级警察机构,甚至仍存在区一级警察行政。例如,直隶各县均在境内划分若干警区,各设警察分驻所、派出所,置巡官、巡长[27](《直隶各县警务一览表(1917-1918)》第5995-6002卷)。江苏省各县设巡警局一所,“辖区太广的巡警局设若干巡警分区,巡警分区有城区和乡区之别。城区每分区设区长一人,区员二人,巡记一人;乡区每区设区员一人,巡记一人”[28](P403)。
(3)区乡(保卫)团政
清末“新政”裁撤绿营、保甲,建立警察,“嗣警察力有未逮,势不得不借助于团勇”,不少州县因此建立保卫团,在境内划分团区,设立区乡团务机构和人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些省份(如四川),也曾令各县组织保卫团。至1914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地方保卫团条例》,规定各县设立保卫团,负责清查登记户口、检察盗贼赃物、围捕匪徒。各县保卫团“得参照各该地方习惯划分区团”,“每团置团总一人”,由县知事遴委[16](第732号)。此后,许多地方依据这一《条例》设立了区乡保卫团。
除教育、警察、保卫团外,北洋政府时期还曾存在过诸如清乡、禁烟、户口调查等其他临时性行政区划和组织,不一一举证。
2.职能全面类型的区乡行政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职能全面的区乡行政就其主体性质而言又可以分为“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两种。“官治”与“自治”,是清末民初的两个常用词语。“官治”的地方行政属于国家统一行政一个层面,其行政首领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职能是办理各项国家行政事务;“自治”的地方行政,其首领由地方自下而上推举,选举本籍人士担任(往往也需要各级官厅通过一定程序来确认),或由自治性上级机关任用,职能是办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然而实际上,当时的“自治”行政往往也同时执行国家行政职能,“官治”行政往往也同时办理地方公共事务,于是两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就主要在于首领人员产生途径的不同。
(1)自治性质的区乡行政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在州县之下的城、镇、乡实行地方自治,自治事务包括教育、实业、卫生、道路土木工程、慈善救济、公共营业、其他公共事务以及地方财务,基本囊括了近代一般地方行政的基本内容。该制度的实行,使一些地方建立了职能全面的城镇乡自治行政(注:清末地方自治包含议决和执行两个层面,但其宗旨主要不在于两者的相互制约,而在于作为一个整体而实行“以本地人、本地财办本地事”的“自治”,与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尚非一物。因此我们在这里宽泛地将之视为一种地方行政。)。
清末的城镇乡自治行政具有固定的行政区域。《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在各府厅州县境内划分自治区,“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城、镇区域过大、人口满10万者可以再划分为若干区。各区域“以本地方固有之境界为准”,其境界不明者,由地方官“详确划分”。所谓“固有境界”,其实就是清代中叶以来在各地逐渐形成的纯地缘性质的乡地区划。在清末最后两年多期间,各地许多州县划定了城、镇、乡自治区域(注:也有少数地方区界没有划定。如广东开平县当时分10个自治区,“各乡不过就近设局自属为一区而已”,区域并不明确。至民国初年“按区派款”、“举办清乡”,才“将各区划定界限”(余谋修:《开平县志·舆地志上》,1933年)。)。在机构方面,清末地方自治较之当时其他形态的区乡行政更为完善。它不仅设有城镇董事会或乡董、乡佐作为执行机构,而且设城镇乡议事会作为议决机构。据1911年统计,各省1000多个县成立了城议事会、董事会,许多地方选举产生了镇、乡议事会、镇董事会和乡董、乡佐[29]。民国建元后,有些地方对城镇乡自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如江苏省1912年3月颁行市乡制,以县治城厢地方和人口5万以上的市、镇、村、庄、屯、集为“市”,其人口不满5万者为“乡”。
1914年,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办地方自治。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作为地方自治议决机构的城、镇、乡议事会虽然被取消,但其原来作为执行机构或人员的城、镇董事会、乡董却从此保存下来,改换名称而成为区乡行政的首领;原来的自治行政区划也继续存在,成为其他形态区乡行政的区划。例如,1914年自治取消后,江苏嘉定县真如里乡“设置经董办理乡政”,以乡自治公所作为经董办事处;铜山县“每市乡设董事一人办理市乡政务(后设市乡公所,称区董或乡董)”;浙江江山县至1920年代初,仍存在“各乡自治委员”;河南荥阳县清末地方自治划为8区,至1920年代中期“办自治选举一切公事仍作八区”[13](P224)[30](第10辑,P12)[16](《内务总长咨浙江省长文》,第1781号)[31](《建置志》)。
1919年,北京政府再次推行县和市乡两级地方自治,并于1921年7月公布了《市自治法》和《乡自治法》。这两个法律规定,在县以下划分市、乡,选举自治会、自治公所作为自治议决机关和执行机关[15](民国十年册,P29-42)。由于政局混乱,当时大部分省份没有实行。此外,1920年代初南方一些省份倡导“联省自治”,广东、江西、湖南、浙江等省纷纷颁布“省宪法”,其中也都规定在县之下实行自治制度。根据这些“省宪”,1921年广东省订立了《区自治条例草案》,江西省订立了《暂行市乡自治条例》,1922年湖南省颁布了《市、乡自治宪法规则》,这些文件均规定在县以下建立区乡一级的行政。1923年6月,江苏省议会也曾议决恢复1912年曾经实行的市乡制[16](《平政院议决书》,第3291号)。由于政局动荡,这些也均未能认真实行。
(2)“官治”性质的区乡行政
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停办各级地方自治后,一些省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官治”的区乡行政,其中有些是打着“自治”的旗号建立的。
其一,京兆特别行政区。前文已经述及,北洋政府于1914年12月颁布的《地方自治试行条例》规定实行县以下的区自治。次年9月,这一制度在京兆地区试点实行。北洋政府颁布《京兆地方自治暂行章程》规定,京兆地区所属20县每县划分8-16个自治区,每区管辖10-30个村,实行“自治”;自治事项包括县知事委任办理的国家行政事项和地方教育、公共建设、实业、慈善、卫生及地方财务。自治区置区董、副区董各1人,由县知事遴选2人,详请京兆尹委任1人、当时京兆地区20县共划分自治区198个,全部由京兆尹任命了正副区董[32](上册,《法规》,P4-7,《自治区组织》,P25-29)(注:据香河、房山、涿县、三河等县的地方志记载,正副区董确系官方委任,如《房山县志·自治志》(冯庆澜等修,1928年)记该县正副区董“皆官委,非民选也”。)。
其二,山西省。1918年山西省政府颁布《县地方设区暂行条例》,废除乡、镇、图、保,在县知事和各行政村之间设立“补助行政机关”的“区”。各县根据地域广狭、人口多寡划分3-6区,每区设区长1人,由省长委任,直隶于县知事。《条例》发布后各县先后付诸实行。山西全省105县共划分425个区[33](P51)[34](《附录·现行法令》,P59)。
其三,奉天。1922年颁布《议定区村制单行章程》,规定除“边远县分及新设治者”因“村堡星散,暂从缓设”外,每县各就县境划分若干区。区长经县知事保送后而由省长任命,“受县知事指挥”,“辅佐县知事办理地方行政,排解人民讼争”。《章程》颁布后付诸实行,例如铁岭县当时“全境划分八区,每区设区长一人,助理员一人”。1928年12月各县所有区长裁撤,这一制度停止实行。当时即有人指出,这种制度只是“略存自治之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官治[35](《民治志》)[36](《民治志》)。
其四,河南省。1919年河南颁行《市区街村单行法》,规定各县在境内划分数区,下辖行政街村,区长经选举后由县政府“加委”,虽号称“地方自治”,但实际上也属于“官治”性质。该法规颁行后各县先后遵照实行,如西华县划为7区,信阳县划为5区;阳武县划为5区;新安县划为5区[37](《民政志》)[38](《民政志》二)[39](《自治志》)[40](《民政志》)。
除上述几省区外,其他地方也间或存在这种“官治”的区乡行政。如有当时人回忆说,四川江油县1925年曾划分行政区,设置区公所,由县委派区长[41](P15)(注:实际上,“官治”与“自治”的区别不仅存在于职能全面的区乡行政之中,同时也存在于单一职能的区乡行政之中。上文述及的区乡教育行政,其首领人员或由地方推举,或由县劝学所、教育局任用(详后文),就基本上属于“自治”性质。而区乡警察行政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上文已经述及,1909年以后各地警察区官、巡官、巡长由各省巡警道委派,但一些地方还保留由地方推举产生的警董,负责筹集警款,区乡警政的性质因此而介于“官治”与“自治”之间。参见笔者《地方自治与直隶“四局”》一文,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就制度设计而言本来属于职能单一的区乡行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同时履行本职之外的其他各种行政职能,从而演变成为了职能全面的区乡行政,一些地方的区乡警政就是如此。清政府1907年颁布的《各省官制通则》是一个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文件,其中规定在各州县划分警区、设立区官,已含有将警区作为一般行政区、将区官作为一般区乡行政首领的意向。北洋政府在有关文件中也明确说:“警察行政为国家庶政之权,与一切法令,非借警察之力,不足以利推行。”[18](《政治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区乡警察区域和机构除发挥治安、司法、卫生、消防等方面的警政职能外,还往往行使其他行政职能,在地方自治停顿时期实际上成为一般性区乡行政。例如:直隶青县入民国后,“将全境别为五区,其初本为警务新章,后以比年政令纷繁,县府有事类多分饬警局代为执行,以致警政区域几成全部自治区域”[21](《疆域志》)。黑龙江省呼兰县1913年将13个自治区并为6个警察区,“以警察为辅佐行政之机关”,“此后相沿,略无变更”[42](《地理志》)。奉天安东县1914年地方自治取消后,“地方有事动以警察六区为指归”[43](卷四,《区村》)。广东大埔县1918年始划为8个警区,“分配管辖地方”,此后“举凡政治上一切,多以八区分列”[44](《经政志》上)。
这种由单一职能演变为全面职能的情况,在区乡(保卫)团政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民国初年,在有些地方——尤其是鄂、湘、粤、桂、云、贵、川等中南、西南省份,保卫团系统在实际上成为了县以下一级的一般性区乡行政。在这些地区,团政与一般行政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以行政兼团政。最典型的是山西。该省各县1917年后在境内划分行政区,设立区长,而保卫团区域及组织系统与之相一致,每区为一区团。京兆地区1919年颁布《地方保卫团条例施行细则》,也规定各县团区“依自治区为区”[16](第1084号)。山东馆陶县、四川金堂县也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例证[18](《政治志》)[45](P383-384)[46](《疆域志》)。
第二,最初以团兼政,后来演变为以政兼团。例如贵州省仁怀县,民国初年“县以下地方第一级机构叫团防局”,设团总、副团总各1人;“第二级叫团防分局”,设正副团首各1人。至1917年,团区正式成为行政区,团防局改称区公所,团总、副团总为区长、副区长;团防分局改称乡(镇)公所,团首改为保董[47](P106)。
第三,最初区域和机构均为团政合一,但后来机构趋于分立。例如四川达县,1912年各乡设团务处(后改团务局),团、政合一,首领称团务长(又名团总),但不存在保卫团实体;1918年成立自治保卫团,团务局改称团务分局,首领称保董,同时兼任保卫团首领。1925年,团务分局改称团保局,成为单纯行政机构,首领称团正,不再兼任团务首领,自治保卫团另设团长[48](P9)。
第四,最初团政合一,后来废团存政。例如四川江油县,民国初年各乡镇团政不分,设有团防局负责处理行政事务和维持地方治安,其首领叫团总、团正。1925年“废团设区”,设置区公所,由县委派区长。安徽蒙城县清末民初全境划分为2乡5镇(后改为8个镇),各有议长,同时均兼任镇团练分局长。1925年,镇改为区,各区办公处称区署,设区长1人[41](P15)[49](P75-77)。
第五,自治行政与团政相互交替。广西平南县,清末“各团局总揽辖区内军政、民政、财政大权”。1911年后实行地方自治,各乡镇分设议事会、董事会。1914年地方自治停办,恢复团局;1920年又废团局而恢复各乡镇议事会。1925年新桂系统—广西,再次停止自治,恢复团局[50](P71-72,77)。
在有些地方,也存在学区同时成为其他行政区域的情况。如江苏盐城县1908年将全境划分为36学区,“凡办理选举、调查户口,皆沿用之”[51](《舆地志》)。
(二)由清代旧乡地演变而来的区乡行政或准行政
在清代,因普遍化、常设性特点而能够承担某些准行政职能的乡里组织,初为里甲,雍乾以后以乡地(而非保甲)为主,对此笔者已有专文阐述(注:详见《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学、警、团、自治等各种近代区乡行政的生成,旧乡地(及里甲)区划和组织在许多地方寿终正寝。试举直隶的几个县为例:满城县里甲制度在清末已仅具空名,有乡地组织20约,“光绪三十二年厉行警政,划为六区,而社甲之名废。民国元年……约之名亦废”[52](《建置志》)。蓟县1912年划分8个警区,“明清两代里保之制于焉告终”[53](《官师志》)。南宫县清代有里甲24社、乡地48牌,“自清末划全县为八区,皆受成于警官,而社牌之制遂隐”[54](《法制志·建置篇》)。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各种生成之中的区乡行政缺乏划一性和连续性,因此旧的乡地区划和组织仍然大量存在,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区乡行政的重要部分。其形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在一定时期直接转化为履行单一职能或全面职能的新型区乡行政区划和组织。例如:
直隶顺义县的旧乡地区划为10路,清末分设“总董”办理学务,并“渐负各路地方责任”。至1916年京兆地区试办自治,正式将10路和城区变为11区[55](《建置志》)。
四川合江县雍正以来分为17支,1906年依之划17学区,“其后警区、团区皆因之”[56](《舆地志》)[57](P70-71)。
江苏嘉定县旧分若干厂,1909年举办地方自治,“因程期迫促,旧有之厂区猝难变更,仍照从前区数定为一城十三乡”[58](《疆域志》)。
贵州遵义县民国初年“沿用清时旧制,全县分为十三个‘里’”,设正副乡正。1917年前后,“改里为区”,乡正改为区长,“区的辖区仍是原来里的辖区”[59](P61-62)。
旧乡地向新型区乡行政的转化,在有些地方经过了某种调整和重新组合。例如,四川温江县自清康熙以来分为全集、北太平、东太平、东维新、南维新、西维新等6乡。民国初年划分行政区,以全集乡为西区,北太平乡为北区,东维新乡与东太平乡合为东区,南维新乡与西维新乡合为南区,同时将城厢独立为城区[60](《建置志》)。
2.与新生的区乡行政接轨,成为下级区划和组织。直隶景县原有乡地组织84社,清末划分全境为5个警区,“社乃分隶其间”[61](《疆域志》);四川灌县旧乡地区划和组织为41团,清末办理地方自治,将之分别隶属于新划分的7个城、镇、乡;“民国仍之”[62](《舆地书》);浙江桐乡县1913年“根据清代的都图地界”划为6个区,各图分归6区管辖[63](P51);江苏武进县1912年设36个市、乡,其下级组织为旧的都、图,共82都,447图[64](P90)。
3.在学、警、自治等新型区乡行政产生后仍以旧有形式继续存在,承担其他某些传统性职能。例如,直隶正定县原有乡地组织43约,民初虽划分为6警区、自治区和13学区,但办理联庄会等“义举”时,仍“因约集事”[65](《政典志》);山东昌乐县旧分20厂,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时划为13区,“而二十厂之名称依然存在,区设区长,厂设厂长”,两者并行不悖[66](《民社志》);河南阳武县原有乡地组织32地方,“各地方有总大户一人”,“且雇用地保以佐之”;1920年划为5区,各设区长,“然办理杂派摊款粮米正供,仍责成大户地保”[39](卷二,《自治》)。
4.因新型区乡行政的建立而一度被废除或闲置,但当前者因各种原因中断时又重新得到恢复,其职能难免新旧相间。例如,安徽南陵县旧分80都图,清末地方自治时划为10区,倪嗣冲主政后取消地方自治,“基层仍沿用都图制”[67](P51-52)。广西省迁江县清后期分4乡、14墟、64团、578村,分设练总、墟长、团长、保董;1912年分区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及乡董、乡佐等自治机构和人员,“练总之名亦随而取消矣”;1914年地方自治“无形停顿,仍复前制”;1920年一度恢复地方自治,但不久“又复无形停顿,而团总、保董之称因而复有”[68](《政治志》)。以上3、4两种,其职能与清代的旧乡地无根本差异,可以说是一种准行政。
上述各种形态的区乡行政,彼此之间在区划方面有时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上文已经提及,有些地方学区、警区、团区实际上成为自治区、行政区;而除此之外,也有以自治区作学区者。如广东大浦县1910年将全境划分为13个自治区,民国改元后即“因其区”划分13学区[44](《经政志》上)。在有些地方,各种区划在一定时期内并存,如直隶井陉县民国初年“区制甚不一致,有警察区,有教育区,有自治区。区之大小多寡,各随其便利而划分之,彼此不相顾及”[69](《疆域志》);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各种区划之间存在历时态沿革关系,某种新职能区划出现后,旧职能区划即与之统一。如直隶文安县1906年“创办学警”,全县划分18区,后办理地方自治,统一改为8个自治区[70](《方舆志》);江苏盐城县1908年划分36个学区,1912搞市乡自治,并为25个市乡[51](《舆地志》)。
这一时期,有些地方还将区乡行政分为二级甚至三级。山西1916年后实行村制,每县分3-6区,每区辖数十行政村,每行政村辖若干自然村;京兆地区也是如此;广东香山县民国初年分9镇,各辖若干个乡和二级镇[71](P68);安徽六安县民国初年分城区和4镇、8乡,其下又先后分为118、158保;安徽蒙城县清末民初地方自治时分为2乡5镇(1913年改8个镇),1925年镇改为区,每区分5至6个大甲,每个大甲辖4个行政村,行政村管辖自然村[49](P75-77)。一些地方的学区也曾采取二级制,山东临清县1913年将全县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学区,每大学区又划分为“五分区、城区及会乡”[72](《教育志》);江苏嘉定县、奉天开原县的情况也与此基本相同[58](《教育志》)[73](《政治志》)。
四、性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各种形态的区乡行政,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性质,但同时又未能褪尽传统色彩,体现了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的特点。它的这种两重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机构设置。在西方,现代行政体制之不同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以科层化的常设公共机构取代了贵族个人或其私属对于领地事务的治理。在中国,自秦建立君主专制的国家体制后,中央和地方即始终存在由职业官吏组成的常设性行政机构,16世纪以后来华的西方人因此谓中国的行政制度“早熟”。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在县以下却不存在常设性(不因时因事而兴废的)公共机构。明清时期,农村社会靠士绅、宗族等私人势力承担乡里公共职能,靠职役系统办理官差。遇有兴作,成立各种临时性会社,事毕解散。里甲、乡地等职役组织虽然具有常设性,但其首领的身份属于民役而不是职业官吏,且不设职能性机构而实行“独任制”,以一个自然人而不是以一个公共人格来承担区域内公共职能。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生成的各种区乡行政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它们一般均存在常设的首领人员或机构,对此上一节已经述及。“独任制”问题在警察、自治和官治的区乡行政中也基本得到了解决,它们往往依法设立了与首领人员共同负责的副职和其他正式行政人员,以及受雇于机构(而不是首领个人)的事务性人员。例如,清末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即规定,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及乡董均设正副职及文牍、庶务等办事人员。例如,直隶文安县胜芳镇议事会设正、副会长各1人,文牍兼庶务1人,另雇书记1人;董事会设总董1人,董事1人,名誉董事4人[70](《法治志》)。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京兆地方自治暂行章程》也规定自治区设区董、副区董和佐理员。山西省1918年颁布的《县地方设区暂行条例》则规定除区长外,各区必要时可以设临时助理员3人至5人,这种规定基本得到实行。例如,襄垣县、盂县各区均各设区长1人,助理员2人[74](《区村略》)[75](P19)。在当时其他形态的区乡行政中,采用这种制度者也不乏其例,如奉天省1922年实行区村制,铁岭县“每区设区长一人,助理员一人”[36](《民治志》);直隶大名县1923年分13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区佐2人[76](卷四,《自治》);陕西陇县1924年全县编为6个行政区,“各区设区公所,有区长、副区长、文书、干事等专职办事人员”[77](P33-34);四川江油县1925年设置区公所,除区长外,“区公所内分设专人管理民政、户籍、财粮、治安等事”[41](P15)。不过,在区乡劝学员、保卫团团总和由旧乡地演变而来的各种组织中,首领“独任制”的情况仍大量存在。
(二)行政人员任用。行政人员具有职业化的公职身份,并按法定程序任免,是现代行政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清代农村社会,士绅、宗族首领在主持乡里公共事务时不具有法定的公职身份,其权力不是来源于依据成文法律法令的程序化任命,而是源于他们无形的社会声望;里甲、乡地等职役人员的工作性质属于服役,由地方官、甚至由吏胥任意签派。在这方面,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生成的务种区乡行政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其首领人员大多已经属于职业化公职人员,任职具有成文的法律法令依据。
这一时期法定的区乡行政人员任职程序,大致有四种:
第一,由“官治”的地方政府直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首先实行于警察、保卫团等涉及武装力量的区乡行政中。前文已经述及,清末令各州县划分警区,“各置区官一员”,一般由各省巡警道委派。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地方保卫团条例》规定,各区团团总由县知事“遴委”。此外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各种“官治”区乡行政中,其主管官员也均由上级官府任命。如山西各县1918年设区后,“区长由省长委任”[33](P51);奉天1922年实行区村制时,“每区由县知事保送二三人”作为区长候选人,经“省长面加考询,对答合格者乃得充任”,区助理员“由区长择用”[36](《民治志》);四川江油县1925年各区设置区公所,“由县上委派”区长[41](P15)。
第二,由上级自治职能部门首领或同级自治行政首领任命,或由他们提请地方官任命。这种任命方式的典型是各学区的劝学员。清末《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学区劝学员由县劝学总董选择,“禀请地方官札派”;1923年北洋政府颁发的《县教育局规程》则规定,各学区设教育委员一人,“由县教育局长就素有教育学识经验者选任”[15](民国十二年册,P412)。1914年前后,江苏省各县区乡学务委员系由乡董(乡经董)提名,呈请县知事委任[14](P639,484)。有些地方的区乡保卫团首领也是采取这种方式任命的,如四川金堂县清末各区保卫团设团正,由县团总向县官推荐委任[45](P383)。
第三,经由法定的选举程序产生。这种就职方式的典型是清末民初推行的地方自治。清末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议事会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城镇董事会总董、董事和乡董由城镇乡议事会选举产生。1921年北洋政府颁行的《市自治制》和《乡自治制》规定,市、乡自治会由选民选举产生,市参事会(由市长、佐理员、区董、名誉参事员组成)和乡长、乡董由市、乡自治会选举产生。在当时推行地方自治的地方,这种制度一般均得到了实行。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实行以地方官员为行政监督的原则,所以上述自治议决机构和执行机构选出时,往往由国家给以某种形式的确认。例如,江苏省嘉定县钱门塘乡议事会和乡董1910年选举产生后,由知县姚×ד遵式刊发”图记,民国建元后,又由民政长许ד遵新制刊换”[14](P32)。1921年河南省推行街村自治时,各区长经选举产生,然后由县“分别加委”[78](《政治志》)。
第四,经由“地方公举”产生。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区乡教育、团务等行政首领人员往往由“地方公推”、“公举”本地有影响的士绅担任。例如,江苏省嘉定县清末分9学区,各自推举劝学员[14](P131);奉天开原县1907年全境分为5路,由劝学总董招集各路士绅开选举会,推举各路学董[73](《政治志》);民国初年四川《通省团练章程》规定,保卫团各区团团正由“公举”产生[46](《疆域志》);广西平南1931年以前,县团务总局、分局的团总“由当地绅士推选,每两三年选举一次,连举连任”[50](P72);安徽亳县各圩圩长,“由群众推荐”,报县政府批准委任[79](P4)。
上述作为区乡行政首领任职方式之一的“地方公举”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与现代性质的选举并非一物。首先,作为“公举”行为主体的所谓“地方”,不是一种由符合法定资格的选民所组成的团体,而是一个边界不清的、根据无形的传统被认为有资格参议地方事务的地方精英群体;其次,“公举”也不是程序严格的票选,只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公意表达,这种“公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就是一两个权威人物的意志。在这种制度下,士绅之担任区乡行政首领实际上仍然凭借的是传统性声望。这些人表面看具有法定的公职身份,但其实也仍然属于传统的士绅,他们往往没有法定的薪酬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指出,绅士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由于其经济地位,能够作为次要职业,在一个团体里兼任领导和从事行政工作,没有报酬或者只获得名义报酬或荣誉报酬”[80](上卷,P322)。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被“公举”担任区乡行政首领的士绅们也是如此。清末颁布的《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区劝学员“其薪水公费多寡各就本地情形酌定”,《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地方保卫团条例》、《学务委员会规程草案》等文件,则明确规定有关机构的首领人员为“名誉职,不支薪金”,各地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试举几例:
直隶文安县1905年18学区劝学员,“均系义务职,不给薪”;胜芳镇成立议事会,议员、正副会长、文牍兼庶务“概不支薪”[70](《法治志》);青县1905年分20区办理四乡巡警,“每区推举正副区董各一人,以本地士绅为之,均属名誉职”[81](《经制志·时政篇》);1915年京兆办理地方自治时,三河县各区设正副区董,“纯属义务,不支薪水”[82](《新政篇》上)。
广西平南县1931年以前分设33个保卫团,“团总有公事到局,无事则在家”,“无固定薪俸,但从税捐、公产中可得到优厚的报偿”。至于劣绅,则“凭借权力,利用剿匪、办案之机,上下勾结,勒索敲榨,分赃自肥”[83](P72)。安徽亳县1933年以前“民间组织机构称为‘圩’”,各“‘圩’有圩长1-3人,“无副职,无待遇”[79](P5)。
(三)经费筹措。现代行政运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法定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在中国传统的“绅治”时代,由于不存在常设性区乡行政,这种制度化的区乡财务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当时办理各种乡里公共事务的财务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临时性,因事而兴,事毕而息,既无经常性收支,也无常设经理机构;二是私人性,所需经费主要靠私人自愿募捐(及少量公款公产生息),而不是靠以公共权力和有关制度为依托的强制性税费(注:例如山东沂水县民国初年的“自治调查”说:“本县各项公益事业……前清未举办自治以前,均系本地绅士自行办理。”“所有公款公产均由士绅公同筹集,自行管理收支,事峻开列收支清单,张贴周知。事后报县备案”。见《山东历城等三十四县调查自治清册》,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全宗第1001,案卷第969。)。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区乡行政中,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两种法治化的区乡财务机制:
第一,建立形态较为完整的区乡自治财政。这方面的典型是清末民初的城镇乡地方自治。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专列“自治经费”一章,对于自治经费的来源、管理、征收、支出预算、决算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有些地方,这样一种区乡财政曾得到实施。江苏省嘉定县钱门塘乡清末民初自治财政收入为以下6种:1.漕银附加;2.归公无主田地;3.房捐;4.酒捐;5.茶捐;6.路灯、水栅捐。其中第1项系经省咨议局议决,其他各项均经乡议会议决;其涉及财政开支的事项,如重建市西巷门、给发孤贫口粮、雇夫扫除街市积秽、备置义棺、补助桥梁建筑、添设初等小学、添设图书、购置防火设备、疏通河道等,也均经乡议会专案议决[14](P32-34)。
第二,虽然不存在区乡一级财政,但有关行政机构具有法定的经费收支制度,其内容包括:经费来源于公共捐税及其他公共收入,具有公共的经理机构(或人员)。当时的区乡警察、保卫团和部分自治机构曾采取这种方式运作。例如,山东金乡县清末警政和自治经费来自“地方钱粮附捐”,“由四方团长公举妥人设局征收”[27](《山东历城等三十四县调查自治清册》,第969卷);直隶文安县胜芳镇清末成立议事会,以本镇田房牙纪项下提用一分为常年经费[70](《法治志》);四川遂宁县1918年后于各区团常年经费“随粮代征,统筹分支”[84](卷二,《法团》)。此外,“官治”的区乡行政也往往采取这种运作方式。例如,山西各县1918年后各行政区经费由县公款局拨给;奉天各县1922年推行区村制,“经费由清赋、契税提成,不足则以公款补助”[35](《民治志》)。
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区乡行政没有建立法治化的财务机制,其经费虽然来源于公共捐税,但仍缺乏固定性和程序化,系较为随意的临时摊派。例如,直隶昌黎县清末各乡警费由“各乡董摊派”[85](《行政志》);江苏省嘉定县真如里乡成立商团,“一切经费亦由众商担任”[13](P130)。
(四)行政职能。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本来就是适应地方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主要职能从一开始就与作为封建官府之末梢的旧乡里组织不同。它们不像传统里甲、乡地组织那样,主要以支应官差为己任,为封建官府催粮征赋,报案传人。相反,它们主要承担兴办新式教育、发展近代实业、编练新式警察、建设公共设施等现代性社会职能。从实际情况看,它们在这些方面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直隶《束鹿县志》说,该县旧乡地分18疃,“但疃域大小不一,参差不齐”。清末将各疃分为南、西、东北、西北四区,“道路不甚参差。凡劝学、种树、巡警等事,易照应联络,庶于新政不无小补云”[86](《地理志》)。奉天安东县清末裁撤旧乡保,将县境分为7个自治区,各置总董、乡董、乡佐,“除辅助官治外,凡乡里琐事妥为理处,其获益良多”[43](卷四,《区村》;卷五,《选举》)。直隶蓟县地方志说,该县清末地方自治时,“(议员)除少数奔竞者流,多为一般老成耆德,不喜事,不畏事,不迎合官府以损议会之尊严,不要誉乡闾以侵官治之权限,据理而争,遵章而行,运用之妙,可为楷则”[53](《官师志》)。江苏省嘉定县望仙桥乡在清末民初实行地方自治过程中,乡议事会议决了大量有关地方兴革的议案,其中包括:编制12年度预算案、西练祁桥修理筹款方法、催乡董佐克日清查公款案、吴塘×门张洷三桥修理案、马门李家桥重筑案、公款清查后所存公款尽先作消防用案、兴复路灯案、审查乡预算方法案、修正乡预算案、催乡董佐宣布清查公款经过案、迁移小菜摊案、规定出田钱案、防止投物于市河及每年疏浚案、禁止差役私索案、实行冬防案、改正学校名称案、开浚市河案、推选河工副主任案、改选推行方法案、修理西练祁桥案、市河开浚进行案、时局紧张维持秩序案、推选兵灾善后会主任案[14](P1017-1018)。
另一方面,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区乡行政,有时也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性质。有些记载说,一些区乡行政如旧乡地一样仅限于应付官差,甚至糜费扰民。例如,直隶青县清末民初设区官、区董办理四乡警务,“经费递增,兵额迭减,而察其成效,所谓缉盗贼、禁非为以维持地方公安者,适得其反,盗匪日以炽,地方不得宁……街市通衢,平时不见一岗警,而僻处穷乡,反甚畏乎见之(巡警下乡,惟抓赌、抓烟、传案数端,冀得提赏,故乡民畏见)”[81](《经制志》)。这种警察,同清代的差役几无二致。直隶盐山县清末自治选举,“宵小闻之而不寐,争先而恐后,清流望而窃叹避焉,而若浼源之不清”,落入劣绅把持地方的传统窠臼。有些新设的区乡组织,实际上仍同旧乡地一样只是忙于应付各种官差。如河南正阳县1921年选举街村长暨各区长,“自治仅负虚名,未能实行职权”,至1926年区长“全体停职”,“其街村长之仅存者,只以供官府匪军筹款之役,不惟于民治无补,且重加累焉”[78](《政治志》)。广东大埔县在民国初年地方自治停顿期间作为“各区替代之人民机关”的民团局、保安局、保卫团,“遇事则传达官厅之命令而已”。“每遇科派军饷,则军政当局惟责之各区绅董,绅董则负其责,就区内摊族派户,如额上供,对地方利害之兴革所能为力者殊罕也”[44](《经政志》上)。
由于缺乏系统全面的统计性材料,我们对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的实际社会作用还不敢贸然作出整体性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区乡行政的生成,改变了中国县以下不存在科层化行政的传统制度,构成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层面。
[收稿日期]2003-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