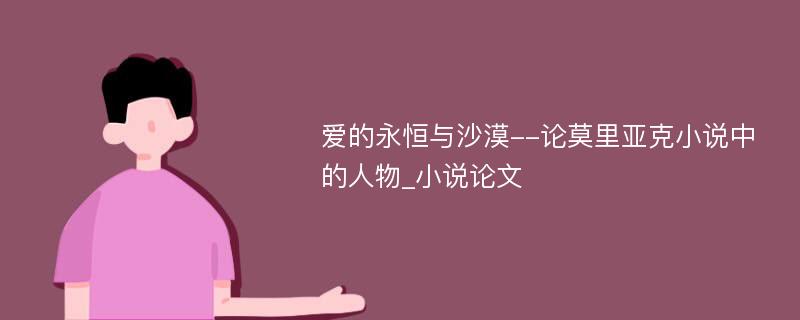
爱的永恒与沙漠——谈莫里亚克小说人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漠论文,亚克论文,莫里论文,人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坛上,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Mauriac)决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这位以描写法国现代社会心理而著称的天主教小说家不但在今日的法国享有众多读者,而且已经并正在不同国家产生着重大影响。
莫里亚克一生创作颇丰,其作品以小说为主。他的每一部小说既是独立的,也与其它小说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人物在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不同故事中的人物互相关联等等。由于这一特点,更由于莫里亚克围绕外省生活来写人的苦闷、矛盾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有些评论家将莫氏的小说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提并论。但是,莫里亚克之所以继续受到现代人的推崇,也许还因为他深刻地表现了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一个共同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
除了二十四部小说以外,莫里亚克的作品还包括四部戏剧、一个诗集、多部短篇小说以及大量关于宗教、政治和文学理论的文章。由于他的文学创作在内容上以深度见称,在艺术上达到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完美,瑞典皇家协会于1952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莫里亚克是至今获得这项文学奖的屈指可数的法国作家之一。
一、天主教徒和小说家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1885年出生在法国中部波尔多市一个笃信宗教的传统资产者家庭。他的母亲是波尔多世家小姐,娘家作批发交易成为富商。父亲则出身于这个举世闻名的葡萄酒产区的经营者。莫里亚克在启蒙时期受到严格的天主教教育,并且在闭塞而保守的外省长大,如此生活环境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他的作品情节不同、人物复杂,但几乎都没有脱离宗教影响和外省资产者家庭这两个主题范畴。
父亲在莫里亚克只有二十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在母亲忧虑的关切和虔诚的祈祷中长大。家庭气氛是单调而严谨的,他的性格这时已表现出后来作品中常见的忧郁格调。这一点在他的早期小说《带锁链的孩子》(L'Enfant chargé de chaines,1913)和《邪恶》(Le Mal,1924)中最为突出。特别是在《邪恶》的最后一部分中,幼年丧父、 在母亲抚养下长大的主人公法比埃几乎就是少年莫里亚克本人的影子。实际上,他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几乎一直都具有孱弱犹疑的特点,而女性人物则性格鲜明,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感情和勇敢的追求。
在莫里亚克早年喜欢的法国作家中,拉辛〔1〕可以说是和他的心灵沟通最深的一个。他感到自己和这位十七世纪的悲剧诗人之间有种看不见的感情联系。拉辛虽然是与莫里哀同时期的古典主义作家,却带有明显的冉森教派〔2〕的宗教宿命论倾向。 他的人物往往因为责任和感情的冲突而痛苦而矛盾,倍受内心折磨。莫里亚克不论在宗教思想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明显受到了拉辛的影响。可以说,拉辛的古典主义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共同为莫里亚克的创作奠定了艺术基调。
莫里亚克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诗集。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个年轻诗人“有敏感的神经”,但说他“感觉多于理解,想象胜过思考……支配他的永远只是情感,因为他是个异常缺乏意志的人。”
对莫里亚克的初期文学生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大作家莫里斯·巴来什。这位他崇拜已久的大师称他为“一位令我钦佩的诗人,一位真正的、有分寸的、温情而深沉的诗人。”1910年3月, 巴来什又在《巴黎回声报》撰文介绍莫里亚克,极力肯定他在诗中所表现的宗教的真诚和乡土的气息。初入文坛的莫里亚克大受鼓舞,于1911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带锁链的孩子》, 然后又接着创作了《贵袍》(La Robe Pr étexte,1913)。
《贵袍》是莫里亚克在历尽曲折而终于尝到了婚姻幸福时写成的,实际上是他两年中陆续完成的五个短篇小说的综合,1914年由著名的格拉塞出版社推出。书中写两个青年同对一个少女嘉米叶倾心,两人互相敌视、嫉妒,在明争暗夺之间反而被这种共同的感情经历联系在了一起。嘉米叶本是雅克的女友,他们在外省小城的平静恋爱被巴黎青年菲利普的突然出现而打破。风度翩翩的菲利普有着大都市的潇洒风度和迷人的趣味谈吐,嘉米叶很快便被他迷恋。菲利普死后,雅克本来可以和她破镜重圆,但昔日天真纯情好幻想的少女已经变成一个热衷金钱和实利的女人。
在这部小说中,莫里亚克再现了他充满童年回忆的波尔多乡间风光,对外省的淳朴严肃的道德观抱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怀念。但是接下来的小说《血与肉》(La Chair et le Sang,1920)将他的宗教观表现得更为鲜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血与肉》写写停停, 直到1918年才完成。小说写三个外省青年人的悲剧。主人公克罗德本来是神学院的学生,但他决定放弃教师生涯,最终回到父母身边,去过农民的生活。他父亲所在的吕克农庄(知情者不难认出莫里亚克家的马拉加庄园的痕迹)有迷人的田野风光,但是新农庄主却是个有钱而粗俗的商人,他的管家又十分奸诈。农庄主的一儿一女,爱德华和美伊都很快迷上了克罗德,虽然他们表面上仍是有钱的主人和租种农民的关系,当爱德华发现妹妹钟情于克罗德时,非常痛苦,出于失望,他和管家的女儿一起离家出走。美伊则时刻处于管家的严密监视之下,没有爱的自由。一次两人正要接吻,被管家发现,美伊只好被迫嫁给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乡绅。爱德华日益陷入复杂的、不为世俗承认的爱情纠葛不能自拔,终于开枪自杀。
除了第一次对同性恋作了隐晦的暗示以外,《血与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写到了死。一个潜在的原因显然是世界大战的背景,莫里亚克思考了很多生与死的问题,另一个直接的原因,则是与他亲密的巴来什的侄子因爱情而自杀。但是这部小说受到的关注还不及《优先权》(Préséances,1921)。
《优先权》是一部带有回忆录成分的小说,故事背景仍是法国外省小城。一个出身富裕但生性腼腆的中学生在学校里常被有钱酒商的孩子捉弄,于是和奥古斯特成为伴侣。奥古斯特出身卑微但聪明漂亮,学业出色,他始终如一的沉默态度激怒了富商子弟,被他们认为是对上流社会的蔑视。中学生请他的新朋友去他家里度假,奥古斯特爱上了他的姐姐芙萝伦丝。骄傲任性的小姐以笼络奥古斯特为手段吸引富商子弟,以攀一门好亲事,但同时也被他隐秘的性格和身世所吸引。不久,芙萝伦丝和一个有钱但愚蠢自负的男人订婚,奥古斯特悄然离去。十年后,昔日的中学生也成了志满意得出入上流社会的商人,芙萝伦丝却在粗俗贪婪的商人圈子里感到窒息,她怀念奥古斯特,日复一日地重温对少年奥古斯特的眷恋。
莫里亚克对女主人公同情多于讽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外省虚荣浮浅的上层社会的反感,同时也流露出一直缠绕他的对自己的出身而感到的隐隐不安。尽管他自己否定这部小说的自传性质,批评家却认为它是最能反映莫里亚克早期思想的作品之一。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莫里亚克虽然开始获得文学成就,却正在经历一场危机:他在宗教观念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他象疯子一样描写人的激情、本性冲动和欲望,塑造了一系列对人和世怀有仇恨的人物,作品中人的感情和宗教信条常常矛盾,宗教表现为阻碍人们相爱和幸福的障碍。于是,在他撰写的《拉辛传》(La Vie de Jean Racine,1928)等一系列文论中,莫里亚克对同时作为天主教徒和作家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似乎二者不能兼得。这种状况令他非常矛盾。一方面,作为文学家,他的宗教观发生动摇;另一方面,他无法背弃从小形成的宗教观点。处在信仰折磨中的莫里亚克写了《天主教徒的痛苦》(Souffrances
duchrétien,1928)对宗教教育中的虚伪、禁欲特别是限制自由表示不满,甚至对“上帝是爱的化身”这句话也表示疑问。
这次危机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末期, 以《天主教徒的幸福》(Bonheur du chrétien,1931)发表而告结束。莫里亚克的朋友们祝贺他“皈依天主教”,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从来没有离开宗教,而是通过危机中的思索离上帝更近了,著名小说家纪德〔3〕曾指责他“想继续当天主教徒,又不需要烧掉自己写的书……既保存上帝的爱,同时又不失去魔鬼”,
莫里亚克便写了《上帝与魔鬼》 (Dieuet Mammon,1929)作为回答。此文阐述了莫里亚克的文学观点, 认为小说家应该诚实地反映人的欲念甚至邪恶;犯罪并不是绝望的,自知有罪便有得救的希望,因为,“一旦获得上帝的恩宠,他的新生便开始了。”
了解莫里亚克这一宗教观点,对于了解他的作品特别是理解他笔下的人物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莫氏不厌其烦地刻画“迷途的羔羊”?为什么他的同情总是在失足的人一边,相反总是让那些理直气壮的人物使人反感?可以看出,他的人物塑造反映他的冉森派宗教观。
二、“深渊中的罪人”:莫里亚克的小说人物
标志着莫里亚克的创作走向成熟的,是他的成名作《给麻风病人的吻》(Le Baiser au Lépreux,1922)。这部作品的发表使莫里亚克的小说第一次拥有大量读者,并被文学界公认为杰作。
小说的主人公约翰·佩鲁耶是波尔多一个大资产者的独生子,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性格孤僻,因而十分自卑。他的父亲是朗德地区首富之一,拥有大片农庄和畜产,年老多病的父亲对儿子既溺爱又管束严厉。佩鲁耶家惟一的亲戚是约翰的姑母加兹那伏太太和她的儿子费尔南,他们盼望约翰父子早死,好继承那一笔可观的财产。老佩鲁耶求助于村里的神甫,让他为约翰寻一门亲事,以避免财产落入加兹那伏一家手中。
自卑而懦弱的约翰早已在心中暗暗爱上十七岁的少女诺埃米·达夏尔。豆蔻年华的诺埃米身材窈窕,有鲜艳的气色和稚气未脱的热情,她的健康活力与佩鲁耶一家的病态恰成鲜明对比。神甫选中她,还因为她恪守本分,笃信宗教。约翰喜出望外,第一个念头却是“她不会要我的”。可是,这一带的人谁都明白,“佩鲁耶家的人是不能拒绝的”。没落穷困的达夏尔一家居然感到受宠若惊,根本想不到女儿是否觉得委屈。
虔诚的诺埃米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却无法克服对丈夫生理上的厌恶,为此她觉得自己有罪。约翰看出她的痛苦,便常常故意躲开,出门打猎。诺埃米更加内疚,拼命用温顺和尽心服侍来补偿。一天夜里,她出于责任感和怜悯,强咬牙闭着眼睛,终于拥抱了丈夫。这一吻无异于一个美好的天使给麻风病人的吻。理智与感情的较量使少女消瘦枯萎,约翰为妻子痛苦却无从解救,只有老佩鲁耶在她的服侍下气色越来越好。
约翰明白自己是诺埃米憔悴的原因,便借口去巴黎学习离家出走。诺埃米表面挽留,心里如释重负,丈夫走后,她恢复了从前的青春活泼。但是不久,她又向神甫忏悔,请求他写信叫约翰回来。
在车站,约翰差点儿认不出容光焕发的妻子。他自己却病倒了,医生认为他患了肺结核。年轻英俊的医生对诺埃米的挑逗使她心跳,但她发誓忠于丈夫并从此让他幸福。约翰自知不久人世,请求父亲在他死后放诺埃米自由。老佩鲁耶却要把全部家产传给诺埃米,条件是她答应一辈子不再嫁,她的父母强迫她接受了这个条件。在朗德地区,人人都把诺埃米看成道德的典范。
在这部小说中,约翰·佩鲁耶的优柔寡断和孱弱自卑为今后大多数男主人公的形象奠定了一个基调。在他身上不难看出少年莫里亚克的影子。在这里,莫里亚克已表现出十分重视情节和景物描写的真实,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佩鲁耶家族就是他父亲的家庭,他能够给每个人物都标上真实的名字。由于写这部书期间所经历的信仰危机,小说中常出现“衰弱”、“孤独”、“寂寞”及“悲伤的心”等字眼,这确是作者那几年心境的写照。
这一年,法国小说巨匠普鲁斯特去世,有人把这一年称作“普鲁斯特从文坛消逝和莫里亚克在文坛诞生的年代”。莫里亚克认为《给麻风病人的吻》奠定了他作为小说家的自我风格,他说:“在找到自己风格的同时,我找到了自己的读者。”
在经历危机的时候,莫里亚克曾有意写一部反宗教传统思想的故事,这部酝酿中的作品就是《火之河》(Le Fleuve du feu,1923)。但最终虔诚的宗教感情仍旧占了上风,他还是把它写成了典型的天主教小说。
《火之河》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小姐,吉瑟儿·德普莱里家境贫困,她和父亲一起住在乡村。在一次去巴黎的短期旅行中,吉瑟儿轻易委身于一个引诱她的男人,不久便生了一个女儿。一位虔诚的女友收留了这个孩子,并试图从道德上挽救吉瑟儿。但吉瑟儿是那种无法抵制情欲的女人,一旦误入歧途便无力自拔,尽管受着理智的折磨却难以割舍感情,这条危险的路被莫里亚克叫做“火之河”。在一个小客栈,她偶遇英俊的年轻商人丹尼尔,两人一见倾心,但吉瑟儿这次决心战胜情欲。她的女友赶来帮助,要带她离开这个充满诱惑的地方。但在她们离开的前夕,吉瑟儿终于来到她深爱但一直坚决拒绝的丹尼尔房中……当丹尼尔再次从巴黎回来寻找恋人的时候,却得知吉瑟儿为自己在欲望面前的软弱而悔恨,已经进了修道院。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拉辛式的内心斗争:主人公始终在道德责任和感情之间受着煎熬。莫里亚克热衷描写的并不是恪守道德规范的人物,而是由于爱而迷失“正途”、甚至走向犯罪的人。他曾这样说过:“我描写深渊之底的人们,是他们虽在深渊之底,却抬头仰望到青天。”他甚至认为只有这种人物才是真正有文学价值的。
莫里亚克笔下的人物象他自己一样,相信爱的永恒——他们把对上帝的爱和对周围人的博爱作为灵魂得救的先决条件,同时不断追求诚挚的纯洁的爱,追求爱的幸福。然而,这些人物却从来都得不到渴望的爱,他们的世界是一片“爱的沙漠”。《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的约翰非常爱他的妻子,诺埃米也一心想使丈夫幸福,他们却只能互相给对方痛苦。在《吉尼特里斯》(Genitrix,1923)中, 菲莉西黛对儿子的钟爱使儿子变得懦弱无能,一方面过分依赖母亲,一方面又对她的专断恨之入骨,但他既不敢反抗也无力摆脱她,终于在两人恨爱交错的合谋和较量中葬送了自己的妻子。在背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邪恶》中,法比埃沉醉于他和芳妮的恋情,但是对肉欲有种犯罪的感觉,认为那是一种“邪恶”。他决定上前线,实际上为了摆脱这种邪恶的引诱。但芳妮以自杀相威胁,阻止他去战场。最后他听从了作教士的朋友奥立维的劝告: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是在战场上捐躯,法比埃于是选择了这条“赎罪”的出路。在这个故事里,相爱的人尽管真诚,也只能互相折磨,互相毁灭。
教士奥立维的形象在这里也有着典型意义:莫里亚克笔下常出现这类引导别人忏悔、充当行为顾问的“正人君子”,他们自以为遵守上帝的意志。这与冉森派强调的“负罪心理”截然相反,因而得不到作者的同情。
爱情无法实现,爱情不能带来幸福只能导致痛苦,这一点在《爱的沙漠》(Le déserde l'amour,1925)中从题目到内容都表现得更加彻底,有人因此认为,这部作品代表了莫里亚克小说的中心思想。
玛莉娅·克劳斯是个漂亮而有风韵的交际花,提起她,道貌岸然的男人们难免作出不屑的神情,但在内心里又都抵制不了她的诱惑。十七岁的雷蒙·古莱日第一次与她邂逅,立刻被她吸引。雷蒙象他那个阶层的许多青年人一样,轻浮而玩世不恭,只把玛莉娅看成一件可以满足虚荣心的玩物。玛莉娅真心爱他,但为惩罚他的轻浮,跟另一个追求者走了。雷蒙恼羞成怒,决心报复。
十七年过去了,玛莉娅的生活经历了许多变故,但依然漂亮。在她一次生病期间,受到雷蒙的父亲保尔·古莱日医生的照料。保尔心地善良,他爱儿子,却苦于无法同他沟通感情。他看到玛莉娅身为交际花,对所爱的人真心相待,因而深深爱上了她。但玛莉娅对他只有感激和尊敬。这时,雷蒙已是风度翩翩的成年人,他对玛莉娅当年的冷淡耿耿于怀,实际上一直爱着她。在巴黎一间酒吧,他们偶然再遇,玛莉娅已经结婚,但看上去依然漂亮年轻。她已经不愿再回顾往事,把唯一的感情倾注在她的继子身上,她对他的母爱中夹杂着情爱的成分。一天晚上,玛莉娅的丈夫喝酒中风,雷蒙帮她送回家,又把父亲请来诊治,于是,同钟情于一个女人的父子在她丈夫的病床前相聚。两个人都回忆起往事,希望和她共度未来,但玛莉娅没有给他们任何希望。第二天,医生乘飞机回波尔多城,儿子为他送行,第一次对一向隔膜的父亲产生了一种温情,父子俩好象被一种新的亲密关系连在一起。但这只是共同的失落感,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失望,对爱的沙漠的失望。
古莱日医生是莫氏小说中仅有的无过失的善良人之一。他对玛莉娅小心翼翼的爱,明知不可能结合却一直衷心地爱护她,和儿子热烈的恋爱及情欲形成鲜明对比。玛莉娅又爱又恨的复杂心理,作为交际花的痛苦和矛盾,也都描写得淋漓尽致,使她成为莫里亚克小说画廊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代表了那些陷入过失并为之痛苦的“罪人”,在她身上,拉辛式的古典主义“情理之战”体现得最充分。
三、“爱的沙漠”:莫里亚克的小说世界
通过写情爱的痛苦和它与道德的冲突来揭示完美爱情的不可能,从《爱的沙漠》开始已经成为莫里亚克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这一点来说,这个书名的确可以作为莫里亚克全部小说的一个总题目。
如果说《给麻风病人的吻》使莫里亚克成名,而《爱的沙漠》确立了他在文坛地位的话,他在创作盛期的两部代表作,《黛莱丝·德斯盖鲁》(Thérèse,1927)和《蝮蛇结》(Le Noeud de Vipères,1932)则将他的艺术成就推向了顶峰。在写《黛莱丝·德斯盖鲁》的时候,莫里亚克的现实主义风格受到现代哲学和现代派小说家的影响,更符合当代人的心态特点。他从不象巴尔扎克那样,注重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不致力于外貌与性格的一致,人物的心理活动复杂而矛盾,思想和行为之间没有逻辑联系,也无法用普通的因果关系来解释。
为了使他的人物接近现实,他注意按人物的自然发展构造小说。他说:“我们的人物越真实就越不肯服从我们的意志。”因此,每当他出于天主教徒的愿望写人物的结局,而人物自身却往另一个方向发展时,他便放弃自己的主观想望。黛莱丝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一个真实人物。在她身上,莫里亚克倾注了最大的同情。他不止一次借助十九世纪大作家、《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样说:“黛莱丝·德斯盖鲁就是我。”
故事的构思来自一个真实案件,谋杀案的情节其实很普通:一个酒商的妻子为达到和情人结合的目的,每天将砒霜放进丈夫的药里,她的计谋未能得逞,被判了十五年监禁。但是莫里亚克笔下的女主人公已和酒商妻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
黛莱丝出生于波尔多一个富裕而有地位的家庭,她的母亲早逝,父亲整天忙于事务,她少年时代的唯一伙伴只有安娜·德拉特拉瓦。安娜刚从修道院学校毕业,天真单纯,黛莱丝却喜欢沉思和幻想。她的童年既不幸福也无痛苦,长大后虽不漂亮,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人人都认为她和贝那尔·德斯盖鲁的婚姻是天造地设的。贝那尔是名门大户的独生子,有可观的田产林产和本地最气派的房子,他精明能干,曾旅游欧洲,是人人羡慕的对象。黛莱丝说不上爱他,但对作名门媳妇感到得意,贝那尔是安娜同母异父的哥哥。
从婚礼那天开始,黛莱丝就感到了压抑。贝那尔实际上是个自私、虚荣而感情迟钝的人,最关心的除了财产就是吃喝和打猎。而安娜自从爱上了从巴黎回乡度假的约翰,也和女伴疏远了。约翰家虽然也有钱,因为是犹太人而不为本地上流社会接纳,安娜求黛莱丝帮她说服家里,而德斯盖鲁一家也要黛莱丝说服安娜放弃约翰。由于嫉妒安娜的幸福,黛莱丝决定站在家族一边。
约翰本来对安娜只是逢场作戏,黛莱丝的任务很容易便完成了。但是约翰的谈吐给她带来了巴黎自由开放的空气,外省生活的保守和沉闷使她更加难以忍受。贝那尔对她毫不关心,婆婆对她的兴趣只限于传宗接代。安娜对她不再信任。
一天,贝那尔无意间将每天吃的含有砒霜的药多服了一剂,黛莱丝出于倦怠什么也没说,晚上他又吐又泄。黛莱丝想弄清究竟是否药量的关系,又偷给他加大了一次剂量,于是又有了第二次发作。后来,出于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她伪造了药方,偷偷给丈夫服用。此事被发现后,黛莱丝以伪造药方罪被起诉,但贝那尔为了家族名誉和妹妹与本地首富继承人德基来姆的婚姻,说服医生撤回申诉,大家都认为他是圣人。
黛莱丝被说成神经不正常而遭软禁,每天独自对着连绵秋雨、奄奄一息的壁炉遐想……由于丑闻平息,德基来姆娶了安娜,贝那尔终于同意让日益憔悴的黛莱丝去巴黎,条件是把她的全部财产留下,永不再回来。
小说在写作过程中几易其稿,起初的结局是黛莱丝忏悔前非,皈依宗教,但人物的自身逻辑最终占了上风。莫里亚克的创作动机决不是要写一个为奸弑夫或图财害命的故事,而是通过黛莱丝揭示时代的社会的悲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黛莱丝·德斯盖鲁》超出了描写爱情失败的故事,成为一部深刻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也不难看到“潜意识”、“双重自我”、“无动机行为”、“病态行为”等现代哲学和文学主题的痕迹。
《黛莱丝·德斯盖鲁》很快成为莫里亚克所有小说中最畅销的一部,继它之后的几个作品都没有获得更大反响,有人认为莫里亚克已经过了创作顶峰。然而,1932年问世的《蝮蛇结》又使公众的反映空前热烈,以致不少人认为这才是莫里亚克真正的代表作。
《蝮蛇结》的故事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一生的回顾。路易是个自私顽固的老头,虽然有钱却一生未享受幸福。他孤独地生活在一大家人中间,对别人充满不信任和怨恨。
他对妻子的怨恨从结婚第一天就开始了。路易出身并不富裕,靠了母亲的善于理财得以有了一笔产业,而出身显赫、挥霍成性的封都代日家欠了路易的母亲许多债。路易虽然自卑其貌不扬,这时也居然大着胆子向傲慢的封都代日小姐求婚,小姐为了家庭流泪答应了。婚后路易很快发现伊莎原来另有所爱,他愤怒而失望,认定世上的人都是以金钱为目的。他以为金钱才使他强大,才使别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对他感兴趣。他明白金钱是邪恶的力量,但用它也许能买到温暖和关心,于是他把钱看得更重,占有欲更强烈。
不久路易已是颇有成就的律师,并有了三个孩子。他认为孩子们也不爱他,只爱他的钱。只有小女儿玛丽天真无邪,但不幸得病夭折,他和伊莎互相追究责任,两人的怨恨更深了。唯一让他欣赏的亲人是伊莎的姐姐,有着孩子般眼睛的玛丽路易丝和她的儿子路克,但他们一个再嫁后去世,一个在战场身亡。
他自己的儿女成家后,都希望从父亲手里多得一份家产,路易觉得,他们卑鄙的暗中算计使这个家象一个你争我夺的“蝮蛇结”。为报复他们,他找到年轻时和情妇所生的私生子罗伯特,打算把财产全给他。胆小萎缩的罗伯特把一切都告诉了路易的亲生子女,条件是他们分给他一笔不大的年金。路易再次尝到被亲人背叛的滋味。
这时伊莎病危,请求孩子叫路易来一见,但孩子们害怕同私生子的交易败露,没通知父亲。伊莎死后,路易才痛心地得知,原来她最初虽然被迫而嫁,这些年却一直是爱着他的,是他的冷淡和一成不变的怨恨使他们未能幸福。路易对自己的成见悔恨交加,决定不等去世,现在就把财产分配给每个孩子。
临终前的路易意识到:他一生的错误在于选错了爱的目标。怨恨使他看不清别人的感情,错以为只有钱才能买到爱和亲情,他因此错过了爱,也未能将爱给予别人。
象莫里亚克的大多数小说一样,作者的同情始终寄托在迷途的人身上。尽管路易自私、多疑、狭隘,读者仍然通过他的内心活动而了解他,从而理解了他。和其他小说一样,《蝮蛇结》让主人公在最后一刻醒悟,看到宗教真谛:在经历了爱的沙漠之后,他终于因为觉悟到爱的永恒而看到了一线光明。
注释:
〔1〕让·拉辛(Jean Racine),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安德罗马克》、《菲德拉》等。
〔2〕冉森教派(Je jansénisme), 十七世纪与耶稣会相对立的天主教教派,崇尚原罪论,认为上帝的恩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冉森派曾因它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被谴责,其信徒避难于Port—Royal 修道院。
〔3〕安德列·纪德(André Gide),法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窄门》,《伪币制造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