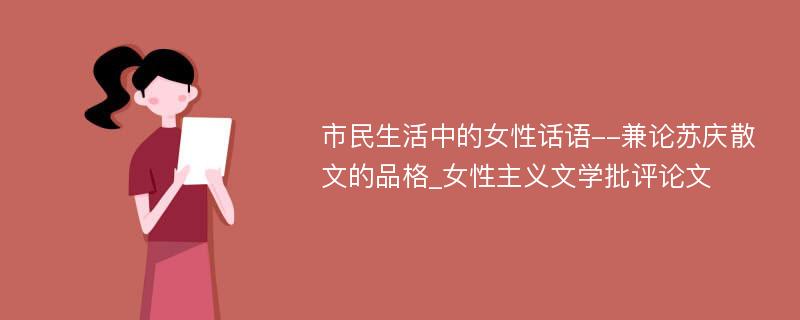
市民人生的女性言说——再论苏青散文品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散文论文,市民论文,女性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这样描述苏青复出的情境:“苏青是在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的那个旧人……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注: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论》1995 年5期。)这番话颇有意味,它一语道破上海这个城市同苏青的依存关系并对苏青被遮掩得如此久远表示了惊诧,“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在现时赢得如此评说,这不能不使我们对她驻足而视。
苏青成名于4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沦陷区,曾与张爱玲齐名。张爱玲其人其作以浓重的“传奇”色彩走上文坛,令时人惊喜之余更添感佩。苏青则以平实直切、清浅俗白的创作风格被社会接纳,并随着当前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文化的发展崛起,愈来愈清晰地走近我们。她出版于40年代中期的散文集《浣锦集》、《涛》、《饮食男女》以特有的苏青话语同我们倾谈神聊各种生活、男女话题。苏青作品能走出尘封的历史,得力于现代市民文化的精神呼唤,得力于其创作内在的文化品格。
本文拟就苏青生活与创作的同步对位关系、苏青散文与市民文化、苏青散文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三个问题,探讨其散文的文化品格,从而评价其散文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
卖文为生、“我”即文本
4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文坛,苏青之所以是个热闹的话题,其主要原因是各类报纸对她生活和创作关系的臆测、比附以及人格高下的评价。“如果要把这类材料搜集起来,有厚厚的两大本。”(注: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30页。)苏青在一次女作家聚谈会上也说:“女作家写文章,有一个最大的困难的地方,便是她写的东西,容易给人猜想到她的身上去……我自己是不大顾到这一层的,所以有很多给人家说着的地方”。作家的辩白一方面说明洋场社会话语的恶俗与无聊,一方面也寓示了苏青创作同个人生活的某些对应关系,即作家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在创作中的显在表现。
苏青的散文创作绝然不是作家私人生活和体验的照录,但其中却有其个人生活的深深印迹,特别是苏青由于生活经验单一,生活环境仅限于报馆、杂志社、电影院、市场街头,就使她的创作题材较难跨越个人生活的积累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取材自我、放眼周遭、以其见识、情性、趣味、性灵照耀和煽动俗常平凡的题材,表露其对平凡世界的感悟和体验,创作周期的局促、为文谋生的亟迫,这一切就使苏青散文同个体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紧密粘连在一起。苏青的创作不是雍容的、恬静的,她无法以从容之心、闲适之态投入创作。文学的才情同浪漫的气质往往同创作的世俗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其创作带有强烈鲜明的私人性和原生性。对此,作者反复说:“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而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至于人物,自然更非父母孩子丈夫同学等辈莫属,写来写去,老实便觉得腻烦。”(注: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第十一等人》,《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 月。)更有意味的是在谈及对个人作品的看法时,苏青说:“我爱《浣锦集》,因为这里的东西篇篇都是我的,没有掩饰,没有夸张,积八年来的心血,继继续续一篇篇凑成的,在这里我回味了过去的生活,有些辛酸却不能使我号啕大哭……假如有人能理解我,同情我,我将因此落泪,爱读《结婚十年》的人,我只是把她们当作读者,而对喜欢《浣锦集》者,都有不胜知己之感。”(注: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第十一等人》,《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 月。)作者对读者如此分类也可见出苏青的散文明显地具有原发的个体性和私人性了。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中曾有“心境小说”和“自我小说”,评论者多以“私小说”概述之。这类小说反对创作虚假模仿,追求原始真实,多将作家的个体生活及生命体验带入创作,把个人心绪小说化、社会化,“通过描写他(叙述对象——笔者注)而尽量使‘我’(叙述者——笔者注)也在其中……”(注:吉田精一,《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月,第10、100页。)作者叙述对象时,与其把对象如实地浮现出来,不如说“更主要的是把自己那种说得简单一些是‘心情’,说得啰嗦一些就是观察对象时从作者本人的人生观而来的感想也表现出来。”(注:吉田精一,《日本现代文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月,第10、100 页。)日本私小说与生活的对位关系,颇能说明苏青散文的创作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苏青创作的“私人性”和“原生性”不同于创作的主观性。主观性创作往往同创作者个人的禀性、才情、气质密切相关,它往往衍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苏青的创作特色既非如此,也不同于一般作家的自叙。她将个人的情感、经历安置在一个“他者”和“我在”的张力场中,使之葆有世俗化的同时又具有类型化的特征,苏青的散文“谈着些侍夫育儿、穿衣吃饭、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芯子里的话……”(注: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论》1995年5期。),因此, 苏青有别于许多作家的是她的角色定位:卖文为生。在她的心理结构中,世俗之欲、独立之意、为文之才,奇妙复杂地糅合在一起,尘世女人、职业女性、文学女人这三种角色形成了苏青人格心理独特的格式塔质,而离乱和漂泊感是首位的。
在苏青散文里有苛捐杂税使主妇难为人媳、难为人母的困境(《断肉记》);有初为人母应变失衡的苦乐感叹(《现代女性》);有租屋不成搬屋反被裹挟的怨怒(《搬家》);有保姆辞归、家庭顿入乱境的尴尬(《王妈走了以后》);有因文化落差而诚心送礼反遭奚落的自慰自解(《送礼》)等等,都是苏青红尘生活的面面,更是女市民面对琐碎繁杂的俗世生活的无奈自语,它们就象生活本身一样鲜活丰富、嘈杂错乱。这些文字反映了苏青散文——“直言谈相,绝无忌讳”(注:实斋,《记苏青》;胡兰成,《谈谈苏青》;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的特点。
苏青为谋生曾担任过“上海特别市政府专员,中日文化协会秘书”(注: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30页。),教过书,做过一般职员。身为女人又置身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境遇格外敏感和专注,过渡时代女人的社会地位,男女关系的新形势,这类话题往往作为苏青言说的中心,也成为她散文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成了五·四新文学探讨妇女解放的另一种声音。这种探讨非为时潮裹挟,它立足现实,着眼都市解放了的“新女性”,考察、抒发和分析她们自由后的“不自由”,及生理心理的秘密,使探讨妇女解放的话题带有更直观深刻的文化反思意味。例如:这里有调侃嘲弄女性旅游的虚伪和浅薄的《红叶》;有疑惑担忧职业女性养家可能性的《写字间里的女性》;有透视女人性格虚荣扭捏和情感压抑的《谈女性》;有对过渡社会女性尴尬滑稽的“平等”与“解放”的抨击——《第十一等人》……如此,苏青作为独立女性自立社会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均流于笔端,带有苏青个人性格和性别体验的显著色彩,苏青文本也成为一道灼目而灿然的女性风景线。
张爱玲曾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过是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因为她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样地也坏,她又有她天真的一面,轻易把人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作为苏青知音的张爱玲对她希望/失望、现实/幻想的爱情心理颇能道出某种真义,苏青的情感历程、心境情绪在她的男女篇章中有大量投影,也造成她为文的峻急悲凉。
苏青以文养生、职业化的写作使她不仅体悟了职业女性这一新兴阶层的苦辣酸甜,还使她特别关注她们的境遇出路,也品尝了特殊职业者——女作家(女编辑)的个中滋味。苏青曾在《做编辑的滋味》、《〈浣锦集〉四版小言》、《自己的文章》中,反复申述女作家为文之外为人的艰难和烦恼,也坦率明了地说明她从事写作的简单无奈的经济原因。这些篇章将作家这一角色世俗化、平民化,将创作起源、创作过程凡俗化、简单化,将女作家独特的生活情感、心理体验一一披露了出来。她分析“美”与女作家无缘的原因(《女作家与美貌》);她向往享有一个心灵放松的空间,随时可以创作的“自己的屋子”(《自己的房间》);她端详为谋生变得纤弱细长的双手而生无限辛酸(《自己的手》)……
可以这样说,没有苏青角色定位的特征,就不会有苏青散文对于中间话题、边缘问题的抒写中那种实在真切的韵味,就不会有创作者同接受者之间似无间距的审美效应,“做到‘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注:实斋,《记苏青》;胡兰成,《谈谈苏青》;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
有人评价英年早逝的梁遇春散文说,他的散文创作是对旧话语的突破,他以俗常的叙述语式表现了现世人生,是散文走向本真人生的标志。(注:李庆西,《梁遇春:摆脱旧话语的一种金经》,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 期。)我们以此来返观苏青散文创作同作家生活的同时态关系,表现在文本中就是谈说抒情近于眉睫的亲切和俗白。这种俗世人生的叙述方式同梁实秋的闲适散文比来,没有有闲文化阶层的优裕、智慧和幽默,没有林语堂生活类小品散文的大度、俏皮和灵动,也不似丰子恺散文拂面而来的童心和爱心,更不同于周作人散文士大夫情调中蕴含的苦涩和优游,即便与她同期的张爱玲散文相比,苏青散文也多了“红尘”意味,缺少某种文化的气息和淡漠的态度,更不用说凌叔华的精致与细密、杨绛的诗意与柔婉、萧红的凄清与伤感、丁玲的热烈和明朗……苏青散文创作的私人性、原生性既有上海文明的潜在影响,也有苏青散文创作的个人欲求,另外还有妇女写作的这个特点,正如苏姗格巴说的:“……这种意识到她自己就是本文的感觉,意味着她的生活和她的艺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可言,妇女作家之所以那么偏好个人抒情的形式如书信、自传、自白诗、日记、游记等,恰是生活被体验为一种艺术或是说艺术被体验为一种生活的结果,就象妇女对化妆品、时装和室内装饰那种世代相传的爱好一样……。”(注:[美]苏姗·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1月。)
赵叔侠根据个人的创作实际和广泛的观察曾提出文学女人这一概念:“……文学女人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类拔俗,因沉浸文学创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同小说情节融为一片,梦与现实真假不分的女性作家,多半是才华出众的才女。”(注:转摘自徐朝晖,《赵叔侠小说的闺秀气》,《赵叔侠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96 年1月。)用这个视角来理解苏青和她的散文创作也是非常恰当的。
市民文化之一种——苏青散文世界
苏青走红于抗战中后期的上海沦陷区,其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逐渐转向解放区,文学直接承担起“救亡”的使命,国统区文学则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典型的知识分子“话语”发出忧时伤事的激愤呼喊,沦为政治文化“孤岛”的上海暂时出现了沉寂。人心的压抑、当局文化政策的导向、市民文化的深厚土壤,就使海派小品在这个时期霎成蔚为大观。“市民话语”也从过去被贬损的地位再次走上文化的前台,苏青散文就在这块土地上茁壮成长起来了。
上海是个西化的城市,这个城市“中西合璧、土洋结合,使上海的市民文化、市民意识庞杂得很……”(注:李天纲,《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批评家俱乐部”,《世俗形象与市民理想》,《上海文论》,1995年第1期。),上海市民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注:许道明,《〈饮食男女类〉苏青集》前言,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3年11月。)这是西方文明长期薰染所致,也起因于上海市民的特殊构成:“上海人口绝大多数是华人,他们是上海文化的主体……中国人中,来自江浙皖小城镇的移民又占了多数,他们带进上海的是‘小市民意识’和‘士大夫意识’……在上海,充满了江南城市的市民意识。”(注:李天纲,《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批评家俱乐部”,《世俗形象与市民理想》,《上海文论》,1995年第1 期。)这种意识不仅“在生活享受上相当会讲究,听书、喝酒、品茶、下棋、孵澡堂、抽大烟,他们比农民的活动范围大,闲暇时间多,因为地方上的事务被官府士绅垄断了,他们就专心吃喝玩乐,手段精致。”(注:李天纲,《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批评家俱乐部”,《世俗形象与市民理想》,《上海文论》,1995年第1 期。)而且还在这些生活享受中发掘乐趣、兴味,以文化的方式装饰点缀它们,品评生活细微处的乐趣,并将这品味咀嚼构成繁杂紧张的市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于是,在茶余饭后、戏散酒尽时就出现了众多细碎话题。这种特殊的市民趣味使伶俐绝顶又聪慧睿智的苏青看取社会、表现人生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
由于苏青创作环境局狭,加之个人谋生的独特境遇和身处殖民地化城市这几方面的因素,使她对过渡时代男女关系这种现代/传统、开放/保守的矛盾格外关注,在她散文世界里,她毫不隐讳地指出: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仅表现在社交场合虚伪的礼仪中。男人谋生养家更巩固了其在家庭中的尊长地位,“婚姻自由”仅给男人提供离弃女人的绝对自由,“休妻”因之找到了最合法堂皇的藉口,男人“蓄妾”改为“情人制”,女人依然留守家庭相夫教子。女性独立必然要求经济自立,但职业女性又面临无情无爱的惶惑,要摆脱此种苦境,必须使孩子有人养、有地方托管……苏青这种男女观,见解锐利明朗、实际浅近,既是恒古的话题也是现代社会常话常新的议题。
除此之外,苏青还关注到都市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她简笔勾勒家庭教师的面目心态、点评世道人心的……(《家庭教师面面观》);她讲说评价牌桌旁几位女性的牌技和赌德(《牌桌旁的感想》);她估摸分析看护小姐美貌由来及貌美可否医病(《看护小姐》);她调侃揶揄小姐的虚荣与虚伪(《小姐辩》)……这点点滴滴,是都市生活角落里的巴掌风景和杯水风波,但叙述者和接受者就在这写与读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娱、娱人,满足了市民娱乐消闲的基本心理需求。
消息传播在都市里速度是最快捷的,公众人物、公共事件也最易形成。市民以其人格的相对独立性较易进入话语评说传播的领域。苏青身处都市红尘,她以一个市民的公德与文人的正直和良心,照录了很多当时社会生活的面影:她写朔风中被遗弃街头的婴孩返观为人父母的责任义务(《救救孩子》);她为震惊上海的杀夫者詹周氏仗义驳辩、言辞推断在情在理(《为杀夫者辩》);她为金钱拜物的社会泯灭人类至性而大声疾呼(《救命钱》)……阅读这些篇章,总能想见作者激愤难捺的情绪及与人驳辩的愤慨神色,显示出市民阶级对重大事件的急遽反应。
苏青散文中还有对吃住睡行之乐趣的品味咀嚼,这也是追求生活兴味的市民文化的专宠。作者祖籍宁波,个人又为职业文人,生活常在悠容潦倒之间徘徊。因此,她赞美待客的点心是家制,期求盛物器皿的简洁精致,向往尝物气氛的热烈融洽,睡要睡得自由自在,垫要垫得宽展舒适,吃要吃得实惠大方、清爽洁净(《消夏录》、《吃与睡》、《宁波人的吃》、《蛋炒饭》)……这类散文就其题材说来,与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相似,却没有他们智者学者的儒雅隽秀,缺少那种纵横古今融汇东西的大家风度和雅文化的品味,集中表现出苏青散文在红尘生活的细微处寻找情趣的市民文化品格。
市民的物质理想、情感理想、人格理想在苏青散文中是以市民的趣味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显见的市俗形象。这个形象“没有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于政治的热衷,而是从市民的生存境遇出发,包含百姓对于人生的要求,思想的寄托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注:李天纲,《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批评家俱乐部”,《世俗形象与市民理想》,《上海文论》,1995年第1期。)它“直接地表现市民的生活, 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以及从中滋生的小智小慧。”(注:李天纲,《近代上海文化与市民意识》;“批评家俱乐部”,《世俗形象与市民理想》,《上海文论》,1995年第1期。)苏青散文就把这“ 角角落落的乐趣都集中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切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愉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死不屈的,这不是培养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注: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论》1995 年5期。)苏青由对世俗形象的塑造,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特殊位置。
女性文学与苏青散文
杨义在《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一书中,将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的创作归为女性文学范畴,评价她们创作的最大特点是:“……写作时带有一种女性思维定向,她们的作品,由于生活所限,题材是比较相近的,狭窄的,或者比较肤浅的,她们都喜欢写妇女题材,儿童题材……她们的小说在艺术情调上都带女性文学的向度……这一代女作家的作品富于抒情性和音乐感,这是对传统文学阴柔美的一种顺向继承。”他的见解颇有新义但忽视了这批启蒙期女作家创作的真实心态。她们不是以女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而首先是以一个觉醒了的“人”的身份带着探询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走上文坛,她们为文的原初动机基于启蒙,妇女儿童虽为她们关注的热点,但又是“五·四”新文学的普遍话题,她们对这类题材的探讨带有启蒙时代价值评判的共同特征。女作家的“言说”趋同着男权社会的话语规范,尽管其不失女性气韵。30年代,丁玲、谢冰莹、白薇、萧红在创作上则更为自觉地向主潮文学靠拢,创作为社会、民族、阶级服务的目的更为明显,表现在题材、主题、风格诸方面女性文学特征的消遁和男性向度的显著增加,这种向权力——话语靠拢的姿态,显示了时代的骤风暴雨对妇女作家的急切呼唤和她们对自我人格、性别角色的重新调适。女性文学的潮流发展到40年代,就由张爱玲和苏青做出新的发展了。
张爱玲以她奇绝的才情和孤胆独心写出对浮华往昔的留恋、对无望时代的诅咒、对病态人性的冷面谛视和温情解剖,以细腻冷漠的叙述演绎了一出出海式言情剧,她以鲜明的家世身世之感,呼应着“五·四”新文学开辟的“人性解剖”和社会批判传统,犀利冷峻的风格暗含着鲁迅先生的峭拔和奇警,又体现了女作家创作风格的一贯性。苏青的出现让人瞠目乍舌,她没有高尚的创作动机,为文既非服务政治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她的创作是个体的、功利的、带有较强的操作性。苏青在《〈浣锦集〉四版小言》中坦率地说:“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几年来,我是常常为生活而写作的。”卖文为生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作家创作时鲜明的性别意识。苏青意识到自己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养家糊口,在求职不成才转写文章的。加之她经历过少年丧父、中年失夫的严峻生活,这些人生情感并合着她个性的豪爽明快、直截了当,无所顾忌,就形成了苏青特殊的心理情结;对女性境遇敏感多思而热切关怀,对男权世界无奈认同又愤而讨伐,它们使苏青的散文创作在“女性文学”的格局中表现出独特的精神品格。
以妇女“言说”妇女,这是苏青散文的突出特征。这是从“菲勒斯中心”话语中解脱出来“阅读妇女”,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石破天惊、撼人耳目。西方社会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男女平权”在政治法律层面的初步胜利、女性主义运动逐步进入对父权制文明的全面审视和批判,妇女欲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中摆脱出来并使用独立的女性“话语”写作阅读妇女,这虽举步维艰但势所必然。苏青则由于创作情境和市民阶层的思维特点,以及人格心理诸方面因素,同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殊途同归并早于她们先行一步了。她立足于一个女人,一个职业女性,一个女作家的现实境遇,通过对点滴细微世事的体悟和切实把握,不追求终极解决而寻求现实问题的现实解决,这样,苏青的男/女观就带有激进前卫的女性主义批评特征,同西方“妇女中心批评”的潮流契合了。
这种纯粹的女性话语,与父权制迥然相对的女性主义态度,使苏青所观女人的角色是被动者(被污辱、被贬损、被欺凌者)、缺失者、沉默者(主妇、玩物、生育机器、看护妇)、有价者(商品、艺术品),是一面镜子,她们温顺麻木、寂寞虚荣、嫉妒无聊……这种溯源于历史又植根于现实的对女性角色的考察,确乎验证了这种思想:“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力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注:[法]埃美娜·西苏,《美杜萨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1月。)同时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她总是被认为是某个本质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可以打动男人的心弦,尽管男人对她的本质特征的解释有多种多样,但她总是客体,受到其它自然或自然现象控制的次等混合物。”(注:[法]埃美娜·西苏,《美杜萨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
而与女性“他者”的本质界定相对照,由摩西一神教的父权文化赋予男人的则是:上帝/创造者/统治者的主人地位,基于此,苏青笔下的男人可在社会、家庭中占尽风光。他们可在名份妻子之外蓄妾纳旦、捧角儿泡交际花,更可在新式文明“平等”“自由”的扶助下随意解除婚姻关系,自由驰骋于情爱世界。他们往往掌握世界即享有女人,占有女人方感拥有世界,对这男权中心的象征秩序,苏青是鄙夷无奈的,往往在激愤的抨击中掺杂深切的悲哀。
对女人角色本质的发现,苏青有“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痛苦和讽渝;对男权成规的审视,苏青有惆怅和愤激,在历史的线性时间和象征秩序中,苏青从女性本体出发,对其性别构造和生命历程的殊异采取正视的态度,在强调女子走向社会取得经济独立和人格平等的同时,她尤其推崇女子的性别教育和社会权利的特殊性,她强调女子教育应侧重女性生命的启蒙、再造和生产,她说:“我以为真正的女子教育可分为二种来讲,一种是预备给完全以婚嫁为职业的女人来用的,就专门教给她们以管家养孩子的职能……另一种是除了教她们与男生同样学习各种职业技能,还得教给她们些管家养孩子的常识……除非她是终身不嫁的孩子,才可以与男子受同样的教育,只不过在上生理卫生课时,还得把‘月经期内的卫生’一章对她讲得特别详细一些……那才是女子教育的万幸呀。”(注: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第十一等人》,《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 月。)她申明女性有类属性别的文化需求,并不完全等同于男人:“我敢说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更甚……”(注:苏青,《浣锦集》四版小言;苏青,《浣锦集与结婚十年》;苏青,《我国的女子教育》;苏青,《第十一等人》,《苏青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正是出于这种鲜明强烈的女性主义态度, 苏青提出女性彻底解放的新思路:生育抚养孩子的国家福利制度的实施。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苏青对女性性别文化的考察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她同西方“妇女中心批评”走得较近又带着后期女性主义批评“雌雄同体”的倾向。她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以强烈的性别意识和显在的情感态度考察象征秩序中的男/女关系结构,特别是对女性性别文化的分析认识实际具体,切中肯綮,言常人之未言,由此奠定了苏青散文在女性文学中的地位。
总之,苏青由于创作心态、动机、过程的女性意识和态度,就使她在强调自我性征基础上专论男女,话说女人种种,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文学”篇在苏青这里就具备了典型的女性主义特征。
这种女性主义特征又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文学。从创作者的身份看,中国古代女作家都是男权文化系统内的“他者”和“缺失者”,创作也必然以“菲勒斯中心话语”表现作为依附者受动者的喜怒哀乐等复杂情感,传统女性文学多的是怨女愁妇的哀吟,多的是近似“男权话语”的吟风弄月,即便在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和李清照的后期词章中,也只是从女性的角度抒发离乱的感伤愁绪。传统女性文学只是“菲勒斯中心话语”的投射和映衬,只展现了女性生命的多种形式,妇女形象存在于男权的写作阅读规范中。苏青的创作则要这样解释:“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注:[法]埃美娜·西苏,《美杜萨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这就是苏青散文创作对男/ 女本质和女性性别文化的考察较之前者深切的原因所在。
有必要说明的是:苏青的“妇女写作”和“女性话语”都是以“市民话语”的模式叙述的,这点点滴滴的实用和对当下境遇求实求切的把握探索,使她的女性主义创作有别于西方同类作家的宏阔眼光和哲理观照,而饱含着市民的聪明和智慧。
最后,对苏青散文文本中潜隐流动的痛苦伤感意绪,恐怕可追溯到女作家创作的共有心态:“如果写作正是‘墨水洒在纸上’正如‘血洒在床单上’,那么,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瀑布》中的女主角一样,女诗人很容易对她的这种牺牲意识感到恐惧,在她的诗中这样写道:‘我很不情愿但十分清楚对自己天赋的无力压抑,我压根儿不该做诗,我怨恨这种无力正如我怨恨一个女人面对男人的无力’。”(注:[美]苏姗·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1月。)正是这种“痛苦”和“无力”造成了苏青散文谈论凡俗人生时的焦灼感,这使她的散文殊异于闲适小品的恬淡从容。
因人生经历痛苦讲说,以女性话语言说男女,以市民智慧看取红尘,这使苏青散文突出表现为:女性主义话语焦灼言说下的市民文化之一种。
收稿日期:1997—11—11
标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 苏青论文; 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张爱玲论文; 读书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