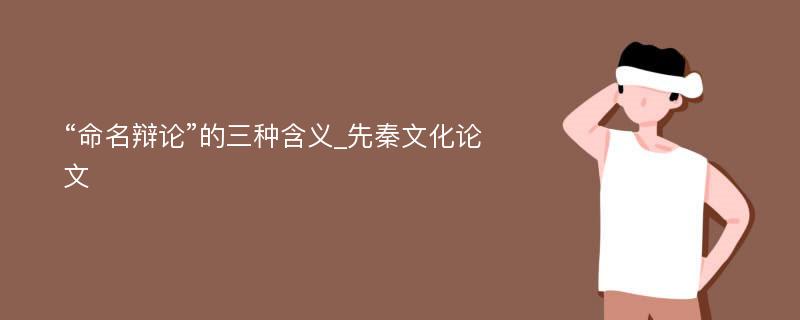
“名辩”三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5-0005-06
20余年来,无论是对以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还是对深化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探索,都跟名辩研究密切相关。就前者说,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对“名辩的逻辑化”这一研究范式的质疑和批判[1][2][3]第四章[4]第三、四章;就后者说,则突出表现为通过重构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体系来开拓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新局面[5][6][7][8]。不过,在笔者看来,当代的名辩研究尽管成果颇丰,但在追溯“名辩”一词的起源、辨析其多重含义等方面着墨并不多,而且为数不多的已有成果还存在不少亟待澄清与修正的地方。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上有所推进,以就教于时贤与方家。
一、“名辩”的起源与成词
关于“名辩”一词的起源,李匡武认为“名”与“辩”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最先出现于《荀子·正名》:“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9]620尽管当代的名辩研究学者颇为推崇荀子的这一说法,但由“名”与“辩”连用而成的“名辩”一词在《荀子》一书中其实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名”与“辩”在同一个句子中并举甚至连用的情形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如《周易·系辞》:“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10]367其意是说:开释卦爻之义,使各卦爻与其所象之名相当;分辨天下万物,以其各所属之类来加以恰当地断定;凭此二事,决断于卦爻之辞就具备了。但是,这句话在当代学者看来与名辩研究根本没有关系。又如,在北宋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中也出现过“名”与“辩”的连用:“有理不言,则理不可明。有实无名,则实不可辩。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实由名辩,而名非实也。”[11]1985所谓“实由名辩”,说的是对象(实)根据名称(名)而得以相互区别(辩)。“名”与“辩”在此虽然连用,但尚未固定下来成为一个双音节名词。同样地,这些文字尽管涉及中国古代名辩极为重视的名实关系,但仍然没有进入当代名辩研究的关注视野。
根据笔者的研究,“名辩”固定成词似乎是在晚清的时候。章太炎很可能就是在名词的用法上使用“名辩”的第一人。在1904年于日本铅印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中,他指出:“惟荀卿奄于先师,不用。名辩坏,故言殽;进取失,故业堕;则其虚誉夺实以至是也。”[12]135“名辩”为“坏”所述谓,与“进取失”相对,当为一个名词;又据前后文意,似指一种恰当的名实关系。所谓“名辩坏,故言殽”,就是说名实关系遭到破坏,导致了言论纷杂混乱。
二、“名辩”的早期使用
周云之认为,张岱年最早从哲学与逻辑的角度提出“名”与“辩”并将二者并列予以讨论。[5]36在发表于1947年的《中国哲学中之名与辩》里,张岱年提出:“先秦哲学中,有关于名与辩的讨论,亦是方法论之一部分。……一般方法论是讲求知之道,名与辩则是论立说之方。”[13]8尽管“名”、“辩”并举,张氏在文中并没有将二者合称为“名辩”。
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在撰写于1916年的《墨辩解诂·再叙》中,伍非百已经明确把“名辩”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来加以使用。该叙的落款为“乙卯岁除日非百又识”。“除日”指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查万年历可知,此乙卯岁的正月初一为公元1915年2月14日,腊月最后一天即除日为1916年2月2日。伍氏认为:“近世德清俞樾、湘潭王闿运、瑞安孙诒让,并治此书,瑞安实集其成。然数子校勘虽勤,章句间误。且不悉名辩学术,诠释多儒者义,颇琐碎不类名家者言。”[14]2此即是说,第一,由于不熟悉名辩学术,俞樾、王闽运、孙诒让等人往往立足于儒家学说来诠释《墨经》,颇为琐碎,不得要领;第二,中国古名家言的本质可从名辩学术的角度来把握。
关于《墨经》以及中国古名家言,伍非百进一步指出:“此《经》系名家言,世为别墨诵习。秦汉学者,病名学艰深难读,篇籍颇多散亡。唯此《经》与《墨子》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周秦文学复兴,诸子之学,间有讨论。而欧洲逻辑、印度因明,蔚然列为专科。中土名籍,赖有此经。发挥光大,责在后学。故于全书中特为分出,别录单本,以复兴中夏旧有名学一派。”[14]1《墨经》为中国古名家言的代表,研究《墨经》的目的在于复兴本土名学以成与欧洲逻辑、印度因明三足鼎立之势。伍氏于前文说不少学者因不熟悉名辩学术而在注解《墨经》时不得要领,故名辩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古名家言的本质;在此处又说古名家言之衰微在于“名学艰深难读”,而研究《墨经》旨在复兴旧有名学。很明显,他所谓的“名辩学术”、“中夏旧有名学”,其实质就是中国古代逻辑。
“名辩”一词还多次出现在《墨辩解诂》一书的目录中。例如,该书下卷的第一编称为“论‘名辩’”,续第一编叫做“名辩”;下卷总第四章的标题为“难诡辩派对于名辩学根柢上所持之怀疑论”,第十章为“名辩要义”。纵观此书,伍非百此时还停留于对“名辩”一词的径自使用,尚未对其进行界说,直到1922年的《墨辩释例》方才对“名辩本论”进行了初步说明:“《辩经》研究之范围,为名、辞、说、辩四事。然亦非仅四者之原理及方法而已。而关于原理之材料,及应用方法解决之问题,亦附其中。……或诘难百家之论,或标明自宗之说,虽非名辩本论,要亦有附论之价值焉。”[15]4《辩经》,即《墨子》一书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共四篇。按伍氏之意,《辩经》既研究了关于名、辞、说、辩四者的原理及方法,也包括关于这些原理的材料和对这些方法的应用,但仅有前者可以称为“名辩本论”。不过,他在此尚未对名、辞、说、辩四者的内涵与相互关系作明确的申说。
在同年稍早时候发表的《墨辩定名答客问》中,伍非百援引《荀子·正名》把名辩本论所研究的名、辞、说、辩四者明确为正名、达辞、立说、明辩,并认为“命(名)、期(辞)、说、辩四者,各有等伦”;同时又将其与《墨子·小取》相互比照,认为:“以名举实者,正名之事也;以辞抒意者,达辞之事也;以说出故者,立说之事也。三者皆明辩之所有事。不能正名,无以达辞;不能达辞,无以立说;不能立说,无以明辩。”[16]2-4
在伍非百把“名辩”作为一个指称某种理论的语词引入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后,郭沫若于1945年发表了《名辩思潮的批判》一文,也明确使用了“名辩”一词,并从思潮的角度对其含义进行了扩展。在他看来,所谓名辩思潮,指的是“儒、墨、道、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辩察的争斗。……这一现象的本身是有它的发展的,起初导源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其后发展而为各派学说的争辩,一部分的观念论者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再其后各家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有恢复到‘正名’的实际。待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的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停止了。”[17]9
1960年代初,赵纪彬在整理其40年代的先秦逻辑史研究时,一方面接受了郭沫若关于先秦名辩思潮的基本论断,另一方面致力于“从先秦各家(从孔子到韩非)的名辩方法里面,发现各家的逻辑思想”,更为明确地把作为指称某种理论的“名辩”一词与逻辑关联起来,认为:“先秦诸子的名辩方法,正是当时逻辑的特殊表现形态。更简括地来说:在先秦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实质上是同义语。”[18]1-3与此同时,伍非百也把其早先提出的“名辩学术”、“名辩本论”等语词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认为:“名辩,乃研究名、辞、说、辩四者之原理和应用的,详言之,就是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有时亦涉及思维和存在的问题。”[19]5-6
三、当代研究中的“名辩”三义
从1990年代开始,伴随着对先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出现了名辩研究的复兴,但当代学者对“名辩”的理解并不全然相同。如前所述,“名辩”的多重含义其实在其早期使用中已经表现出来,伍非百、赵纪彬更多地突出了名辩之为一种理论,郭沫若则更为关注名辩之为一种思潮。综观最近30余年的中国逻辑史和名辩研究,“名辩”一词明显地可以区分出学派、思潮和理论三种含义。
(一)名辩之为学派
明确提及“名辩”之学派义的是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他多次使用了“名辩”、“名辩学说”、“名辩思想”、“名辩论争”、“名辩之学”、“名辩方法”、“名辩学派”等提法。虽未对“名辩”一词给予明确说明,汪氏的理解与赵纪彬的观点类似,即把名辩的本质视为逻辑。例如,他认为《墨子·小取》对于“辩”的论述,其实就是把名辩的逻辑内容具体明确了;荀子在此基础上对名、辞、辩说的界说,则是“把名辩的问题,具体到‘名、辞、辩说’三方面的形式结构,恰是把逻辑科学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对概念、判断、推论形式的研究”[20]56。
《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的标题是“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按汪氏之见,此所谓名辩学派,非《汉书·艺文志》所列“名家”七子范围,还包括了不少热衷于坚白、同异之辩的“辩察之士”。根据该章实际所述内容,名辩学派的主要人物有邓析、宋钘、尹文、彭蒙、慎到、田骈、申不害、尸佼、儿说、田巴、毛说、惠施、公孙龙等人。不难看出,这个“名辩学派”其实就是一个扩展版的“名家”。
除了名辩学派,汪奠基在第一编“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中还用五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墨辩、儒家正名论、道家无名论、法家形名法术的逻辑思想,以及先秦兵书及医书中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按其之论,“名辩学派”应该是一个专名,其所指无疑应当独立于儒、墨、道、法诸家而存在。令人不解的是汪氏又说:“先秦逻辑思想,实际也就是指的春秋战国时代所有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20]55“所有名辩学派”这一提法表明“名辩学派”还可以是一个通名,指任意一个参与先秦名辩论争的学派,如墨家是一个名辩学派,法家也是一个名辩学派,等等。“名辩学派”的这两种用法,既反映出汪奠基本人对“名辩”的学派义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用“名辩学派”来取代“名家”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二)名辩之为思潮
受到郭沫若先秦名辩思潮论说的影响,庞朴、周山等学者以及《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哲学大辞典》(修订本)等著作或辞书则较为充分地触及了“名辩”的思潮义。
在《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中,庞朴用“名辩”来称呼一种始于种种名实相斗的风波而最后波及文化全局的思潮。在他看来,孔子的“正名”是中国第一场名辩思潮的开端,随后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名家(或称辩者、辩士、察士)等均卷入其中。而名家又一分为三: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和墨家辩者派。由于名实之辩在孔子、老庄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故“真正的名辩大潮,是由所谓的名家人物组成并推动的”[21]16。由此出发,庞朴着重讨论了名家三派的思想。这就是说,他所理解的名辩思潮主要涉及惠施、公孙龙和墨家辩者。
周山的《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辩思潮》把名辩思潮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蔚为壮观的学术思潮,其核心是“关于名的理论争辩及论辩技巧规则等的研究”[22]3。与庞朴认为是名家推动了真正的名辩思潮不同,周氏主张在名辩思潮中起轴心作用的是名家、墨家和儒家三大学派。与此相应,该书所论名辩思潮涉及的具体人物更为广泛,主要包括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子和韩非。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也讨论了先秦的名辩思潮,认为其特点是“在相互辩难中注意分析名词、概念和命题,考察名实关系,探讨思维规律和方法,企图改善人的主观认识能力”[23]473。显然,这一看法与周山对名辩思潮之核心的认识不尽相同。在名辩思潮所涉人物的问题上,该书的理解跟庞朴的观点颇为相近:一方面认为名辩思潮并非仅仅为名家或辩士所推动,而是一个包括了先秦各家各派的普遍性的学术思潮;另一方面则强调名辩思潮的高峰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相异于此前诸子的名辩思想与其全部学说浑然一体,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以察辩为专长,对名与辩所涉诸问题进行了独立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说和学派。
《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也从思潮的角度来释义“名辩”:“先秦思想家围绕‘名’的性质、内容、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的辩论以及关于‘辩’的理论研究。”[24]1008作为一个贯穿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潮,名辩思潮始于邓析,在战国中后期达到高潮,传统所谓名、儒、墨、道诸家均卷入其中。据该词目所述内容,除了邓析,名辩思潮涉及的代表性人物还有孔子、老子、墨子、辩者(尹文、惠施、公孙龙等)、后期墨家、庄子、荀子和韩非。这一理解无疑较之庞朴、周山对名辩思潮所涉人物的认识更加宽泛。
(三)名辩之为理论
与伍非百、赵纪彬致力于揭示先秦名辩的理论实质类似,刘培育、周云之、崔清田、李先焜、林铭钧、曾祥云等学者,以及一些研究著作和哲学类辞书对“名辩”的理论义进行了各自不同的诠释。
刘培育在《先秦逻辑史》中提出,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代表,先秦逻辑是通过对名、辞、说、辩等的研究来探讨各种思维形式的性质和一些具体形式,其实质是以名辩为中心,因此“把中国古代逻辑称为名辩学比叫名学或辩学更合理、更恰当些”[25]312。与刘培育的这一观点相近,杨沛荪主编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也认为:“把中国古代的逻辑学称为‘名辩’、‘名辩学’或‘名辩逻辑’更符合实际。”[26]11
在《逻辑学思想史·中国名辩学》中,刘培育更为明确地指出:“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一门学问。它以名、辞、说、辩为研究对象,是关于正名、立辞、明说及辩当的理论、方法和规律的科学,其核心就是今天讲的逻辑学。”[8]1不难看出,这一表述几乎与伍非百在1960年代初的提法如出一辙。不过,相异于伍氏把名辩之学局限于先秦,按刘氏之见,中国古代名辩学大体经过了先秦与秦汉至19世纪末这两个发展时期。就前者来说,邓析、孔子、墨翟、庄子、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荀况和韩非,对名辩理论的萌发、创立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云之在《名辩学论》中对“名辩”的理论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与说明。在他看来,名辩学是正名学(名学)和论辩学(辩学)这两大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包括了历代各家有关正名和论辩的所有思想。就其基本性质和主要内容而言,“中国古代的逻辑学说是全部包括在中国古代的名辩学体系中的,而且构成了名辩学体系的核心和重点”[5]138。不过,周氏多次强调,尽管可以用“名辩学”之名来称呼或代表中国古代的逻辑学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名辩学就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逻辑。
在《名学与辩学》中,崔清田提出:“名辩学只是名学与辩学的合称,并不表明名学与辩学可以互相取代、混同为一。”按崔氏之见,“名学”是先秦名学的略称,以名为对象,以名实关系为基本问题,以正名为核心内容;“辩学”则指先秦关于谈说与论辩之学,基本问题是谈说辩论的性质界定与功用分析。二者虽联系密切,但彼此有别。作为中国古代的两门学问,“名学与辩学不是等同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学问”[6]26-32。
与崔清田类似,李先焜也认为把名辩学归结为形式逻辑有困难。在他看来,名学(正名学)其实是一种研究定义以及防止歪曲定义的方法的语义学,而辩学(论辩学)则是一种讨论论辩的原理、方法和规律的语用学。既然“名辩学中包含着丰富的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内容,因此说它属于符号学研究的范围”[28]17。
在《名辩学新探》一书中,林铭钧和曾祥云主张,作为“名学”与“辩学”的统称,“名辩学”一词“泛指中国本土独立产生的名辩思想”[7]17。其中,名学以“名”为研究对象,辩学以“辩”为研究对象,二者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就名学与辩学所存续的时间跨度来说,曾祥云和刘志生认为,兴盛于先秦的名辩研究虽然自秦汉以降步入低谷,但并未亡绝。因此,对名辩学所涉人物与研究内容的把握,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先秦时期。换言之,“名学、辩学不应是先秦名学、先秦辩学的简称,而应当是泛指整个中国古代的名学、辩学。”[2]200就此而言,曾、刘二人的观点显然不同于崔清田,倒是与刘培育、周云之更为接近。
除了上述诸位学者,一些哲学类辞书在释义“名辩”或相关词目时,也往往着眼于其理论义。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第一版把“名辩”解释为“名学与辩学的合称。主要指先秦诸子关于名和辩的逻辑思想和理论,泛指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9]621。《哲学大辞典》(修订本)则收录了“名辩学”这一词目,将其释义为“中国古代名学和辩学的合称”,认为作为阐述名、辞、说、辩等内容的学说或理论,名辩学的核心和重点是中国古代逻辑,但亦包含大量哲学、认识论等非逻辑的内容。[24]1008《逻辑百科辞典》收录了三个与名辩有关的条目,即“名辩学”、“先秦名辩思想”和“《墨经》的名辩学”,认为“名辩学”是“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总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中国古代有关名辩的学说、理论统称为‘名辩学’或‘名辩逻辑’”[29]338。
四、结论
从上文对30余年来相关材料的粗略评述中不难看出,当代的名辩研究不仅赋予了“名辩”一词以学派、思潮和理论三种含义,而且在名辩思潮的存续时间和代表人物、名辩理论的学科性质与主要内容等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异见纷呈。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名辩”三义的产生及其相互关系?如何看待当代学者围绕“名辩”三义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呢?
笔者对这些问题的简要作答,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毋庸置疑,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先秦哲学)中,存在着一个关于名辩的共同话语:倾向各异的各家各派围绕名实、同异、坚白之争等论题及“辩”之用途、方法、原则等问题开展研究、进行论辩。
第二,以中国古代名辩话语为基础,“名辩”三义的正当性均可得到合理的说明。简言之,“名辩”的学派义突出的是某些思想家对名辩话语所涉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彼此之间具有师承关系或其学说之间具有传承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名辩”的思潮义强调的是这个话语所引发的研究与论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而“名辩”的理论义关注更多的则是这个话语的主要议题与理论实质。
第三,从名实关系来看,名辩之实在先秦即已存在,但“名辩”之名则很可能晚至1904年才由章太炎第一次使用,而其被引入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则又在12年之后才由伍非百完成。“名辩”成词晚于名辩之实长达两千余年,这说明对名辩话语的认识和研究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获得自觉的形态,“名辩”之名及其含义实质上来源于近现代学者对名辩话语的研究。就此而言,“名辩”一词在当代所具有的学派、思潮与理论三义,其实反映了当代学者对于名辩话语之不同侧面的关注;而围绕“名辩”三义所存在的意见分歧,则代表了这些学者对于重构名辩话语的不同尝试,渗透着他们对于名辩话语的存续时间、代表人物、主要议题与理论实质诸问题的不同理解。
*收稿日期:2012-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