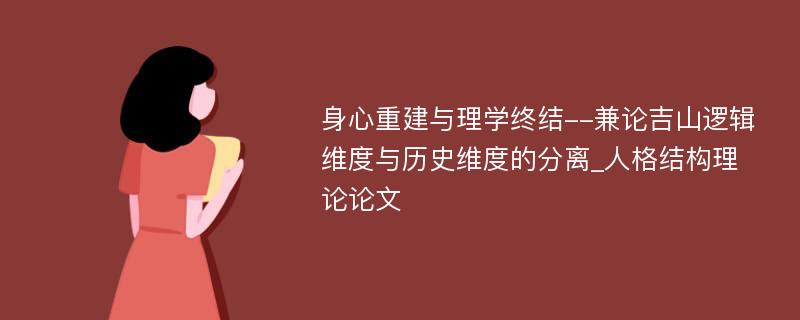
心体的重建与理学的终结——兼论蕺山学逻辑向度与历史向度的离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兼论蕺山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4)04-080-08
一、蕺山学的精神特质与内在结构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的蕺山,学者尊其为蕺山先生。从明代心学发展演变的自然历程来看,蕺山之学是对明中后期心学思潮的一次重大的理论修正和批判总结。蕺山平生学术之最得力处,便是在心学园地的旧基上重新架设一严密无漏的系统。这就需要从心灵深处重新建立一既圆满自足又刚刻严毅的人学价值本体,藉此拴住和堵死决堤而出的王学末流之泛滥。为此,就必须将阳明学说中活泼灵应的良知深藏于时时处于警戒状态的意根诚体之中。此意根诚体即心即性,即人即天,即主宰即流行,是主体意志与超验之理的合一,故曰:“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全书》卷12《学言下》)“一心也,而在天谓之诚,人之本也;在人谓之明,天之本也。故人本天,天亦本人。”(《全书》卷11《学言中》)这种心性合一之意根诚体既是心之主宰,又是性之真宅,蕺山谓之“独体”。蕺山将普遍的伦理原则(性体)与能动的主体精神(心体)双向展开,心性互证,以心著性,以性定心,此种确立人学价值本体(内圣之根据)的诠释方法,牟宗三称之为“归显于密”,即“将心学之显教归于慎独之密教”(《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453页,台湾学生书局版)。此种归结,表明了牟氏对阳明学与蕺山学不同学术性格之看法。在牟宗三看来,阳明以“致良知”为宗旨的心学系统是一种“显教”,意指在阳明学系统中,天理随良知而圆转,泛应曲当,而无滞碍,呈现一圆而神的纯动用,故此谓之“显”。由于显教强调良知自作准则的自发性,若无真实工夫加以贞定,稍有偏差,便会流于虚寂猖狂。牟从袒护王学的立场出发,称此为“人病”而非“法病”。
如实说,蕺山虽力辟王学末流之失,但并未超出王学的总体精神,即以心性论为重心而挺立道德主体性的运思方向。蕺山学性格与阳明学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更用力于德性本体之实证,在心性关系中关注的重心在性体的客观超越义和道德意志的定向性。不似陌明倾向于良知发用流行的自发性;二是更加强调工夫的重要性。阳明学也讲“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工夫论,但不似蕺山那样刚刻严毅地向意根极微处用力。就是说,阳明工夫多用在“已发”上,而蕺山不分未发已发,无处而不显紧缩收敛相。
蕺山之学,不离心性之域。从心性论来看,蕺山一切论述所重皆在性体之显豁,换句话说,蕺山讨论心性问题,时常强调的是以性来定义心,而不是以心来定义性。故其言“性者心之所以为心也”(《全书》卷12《学言下》)。又讲“形而上者谓之性,形而下者谓之心”(《全书》卷10《学言上》)。道德行为是主体能动性与普遍必然性的统一。作为价值本体的心是与性合一之心。性赋予了心以当然和必然的意义。从化心为性到以性主情,以道心定人心,融气质于义理,再到援知人意,以意主觉,化念归思,步步入里,层层归密,处处显示了蕺山在心性之域中凸显和挺立道德理性的努力。与这一运思方向相随的是主体精神的理性化、内心情感的理性化和主体意志的理性化,直到将理性渗入非理性意欲之域。这种泛理性化倾向,在“任情纵欲”盛行,阳明心学先验道德哲学日趋解构的晚明,不失为一种清醒的理论视野。在心体中注入理性本质,这对于矫正王学末流或玄虚而荡,或情识而肆的流弊,恢复道德理性的权威,抑制感性情识的僭越,抗拒意志主义,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蕺山证人之学的内在理路是通过特定的哲学范畴逻辑推演而展开的。蕺山哲学的逻辑结构在其所立的四句教和《学言》关于心、意、知、物的分析中有所陈述。在《学言上》中,蕺山为改正阳明“四句教”之偏失,曾以慎独诚意为宗旨另立四句教云:“有善有恶者心之动,好善恶恶者意之静,知善知恶者是良知,为善去恶者是物则。”(《全书》卷十)这里显然表明,蕺山对心意知物性质之看法与阳明不同。阳明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显然是指超验本心。而蕺山以有善有恶为心之动,则指经验层之心,而非超验之心。“心之动”说明了主体精神之能动性。经验层之心若无道德理性贞定之,则不能担保其必然向善。依阳明,以有善有恶为意之动,将意理解为已发经验意念,蕺山则以未发训意,以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它属于范导和制约已发经验活动的先验意志。对于“知”,蕺山与阳明似相一致,皆以“知善知恶者”为良知。不过文字之同中又有义理之异。阳明以良知之明觉克治和限定意之活动,蕺山援知入意,以突出道德意志的理性特征。最后一句,阳明以为善去恶为“格物”,所格之“物”即意之所在有善有恶之物;蕺山以为善去恶为“物则”,此物既不是心之已发之物,也非客观外物,而是内在于主体之心中的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作为对越在天的理性本体是判断是非善恶的先验价值理性,它要在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中外化为身、家、国、天下的客观法则,故曰为善去恶是物则。
关于心、意、知、物的逻辑关系,蕺山看法是连锁互动的体用圆融之关系。他说:“心无体,以意为体;意无体,以知为体;知无体,以物为体。物无用,以知为用;知无用,以意为用;意无用,以心为用。此之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全书》卷12《学言下》)这里心、意、知、物从“体”的关系层层深化,显示出主体之心向理性本体的深化,此之谓由显入微,由形下到形上的逻辑运演,展示出蕺山以心著性,由工夫上达本体的运思方向;物、知、意、心则从“用”的关系步步外显,显示出超验本体向主体之心的呈现,此之谓由微至显、由形上到形下的逻辑运演,展示出蕺山以性定心,由本体落实为工夫的运思方向。在蕺山心性论逻辑结构中,体的落实与用的提升乃是同一结构内部的两个方面。心以意为体,旨在强调道德意志对主体精神的范导定向作用;意以知为体,将知收藏于意,旨在强调先验意志的理性特质,作为知体之物,此“物”即本体之物(性体)。知以物为体,旨在说明知善知恶之知不是后天的见闻之知,而是来自先天之性。此先天之性蕺山谓之“物则”。从“用”的关系看,物以知为用,知以意为用,意以心为用,则意味着形上之理则通过道德理性之明觉性(知)和道德意志的定向性(意)而在人的主体精神(心)中得到具体落实和呈现。在这种体用圆融无间的关系中,不仅使主体之心得到贞定,而且使形上之性得到落实。如此言心性,高之不归于玄虚,卑之不沦于狂放。故其言:“总之,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谓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而言,谓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无恶归之至善谓之物。识得此方见心学一原之妙。”(《全书》卷19《答史子复》)
从性体的展开来看,蕺山思想的推演则展现为性、命、天、道、教、物的逻辑程式。蕺山云:“心中有意,意中有知,知中有物,物有身与家国天下,是心之无尽藏处。性中有命,命中有天,天合道,道合教,教合天地万物,是性之无尽藏处。”(《全书》卷11《学言中》)心之无尽藏处,指心体的无尽圆融与普遍涵摄,其义理已有申述。性体的无尽藏处,则是蕺山关于性体的阐释。颇为明显,蕺山对性体的诠释,乃是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逻辑引申。依蕺山,性体是“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的形上之理,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验本体。“性中有命,命中有天”,是说作为心之所以为心的性体,自身是一种来自形上之天的普遍必然的善。所谓“天合道,道合教”,与“心率之谓道,心修之谓教”(《全书》卷11《学言中》)同义。依蕺山,性是“本天”的绝对精神,主体之心率性而行便是践行人道之所当然。以天命之性范导、化育人心,则是先王教化之根本。心体清明正直,则参天地育万物的外王之业由是而立,故云:“教合天地万物”。在性体范畴的逻辑结构中、性、命、天属于形上之域,它们以“体”的关系展开,以突出性体的客观性、超越性;道、教、物属于形下之域,它们以“用”的关系展开,以展示本体的内在性和现实性。形上之性命天道与形下之人道教化,亦成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有机整体。
在蕺山哲学的逻辑结构中,性体具有十分特殊的位格与作用。它既与心构成体与用关系,使主体之心在其深层结构上转化为形而上的超越存在;另一方面,又与天命天道构成用与体的关系,将不可致诘的“天命”确认为性之体,这不仅为人的先验理性提供了绝对至上的担保,其理论的特殊意义更在于,不可思议的形上世界通过“性体”之中介收摄为主体之心的内在实质,又经过心体之发用流行,呈现为现实世界的理性规范,这样超验的形上世界(天命)与主体世界(心性)以及客观的现实世界(万物)通过性体的上钩下连而转化为主体世界自身结构的不同层面。这一三维圆融的逻辑结构所要表达的根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核心的宇宙万物的一体化。蕺山在作于崇祯九年的《体认亲切法》中曾言:“身在天地万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心包天地万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体天地万物为一体,更无本之可觅。”(《全书》卷10《学言上》)以价值理性消融涵化宇宙万物,在天人一体中显扬人道的尊严,正是蕺山证人之学的真精神。这一心性回环互证的逻辑结构,使蕺山心性论哲学既不同于朱子将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截然二分的分析的道德形上学系统,也不完全同于王阳明以心说理,以主体精神涵化普遍之理的综合的心学心性论系统,而以其独特的逻辑理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理学与心学的批判综合。
二、《人谱》严毅的“证人”工夫
蕺山晚年曾仿周濂溪《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而作《人极图》和《人极图说》,并续之以《征人要旨》、《纪过格》、《讼过法》、《改过说》,总称之为《人谱》。《人谱》之旨在于通过实修实证之工夫历程,以证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圣贤人格,即“立人极”。其序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总题之曰《人谱》,以为谱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全书》卷1《人谱·自序》)《人谱》的根本宗旨是破除佛老虚无主义和王学末流的自然主义,通过道德实践实修实证,以落实儒家道德人本主义精神实义。依常理说,菜有菜谱,画有画谱,乐有乐谱,则为人便有人谱。菜谱即做菜之理,画谱即绘画之理,乐谱即弹奏之理,人谱即做人之理。通观《人谱》,通篇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和工夫。
在《人谱》中,蕺山对人的品格与行为修养作了近乎苛细的规定。就人格言,蕺山强调由妄返真,这不失为合乎理性之要求,但这种真诚推至极端,便要求“从无过中看出过来”(《全书》卷1《人谱·纪过格》),这就严毅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在《人谱》中,蕺山对人的种种过恶诸如“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等做出冷峻的分析,让人们通过对此种种过恶的反省,产生自讼、自责、自惩的罪感意识,从而在道德实践中确立改过迁善的自觉性。蕺山对道德修养工夫的要求,刚刻严毅,远过前儒。蕺山在《人谱》中所陈述的“证人要旨”,从事亲事兄等社会人伦,到饮食起居日用常行,一无例外都被纳入理性规范。此一过程实即道德理性的人格化,在这种道德王国中,理想人格固然化为纯乎天理的醇儒,而德行反近于苦行。
在《人谱》所讲的明心证性的“六事功课”中,首要工夫曰“凛闲居以体独”。“独”即独体。“体独”即在闲居独处时保持心灵极度平静,通过此静存涵养之工夫,使先验的理性本体(独体)如量呈现于人的后天经验意识中。蕺山云:“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全书》卷1《人谱·证人要旨》)此所谓慎独指在闲居独处时存养未发之工夫。二曰卜动念以知几。依蕺山,念为心之所发,“知几”即在意念最初萌动时及时地加以察识,对不善之念及时加以克治。可见“卜动念以知几”是察识已发时的工夫。三曰谨威仪以定命。此一工夫是指经过未发时存养,已发时省察的慎独工夫之后,性体朗润显发于经验意识中,再将此自觉的道德理性落实在人的外在仪表上,使人的视听言动皆受到道德理性的制约。如足容当重,手容当恭,目容当端,口容当止,声容当静,头容当直,气容当肃,立容当德,色容当庄等(《全书》卷1《人谱·证人要旨》)。在蕺山看来,性不可见,而见于容貌辞气之间,人的内在性情可以影响人的外在形色辞气,而外在形色辞气也可以反作用于人的内在性情。所以威仪严谨可以巩固人的道德性命。四曰敦大伦以凝道。此一工夫指道德理性向五大伦理关系中的落实。在五伦中常怀不尽之心,黾勉以尽伦理情谊,力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庶几无悔于君子之名,无忝于做人之大节。五曰备百行以考旋。此一工夫是指在日用常行中时时处处以道德理性为指南,无时无地不竭尽伦理责任。“君子言仁则无所不爱,言义则无所不宜,言别则无所不辨,言序则无所不让,言信则无所不实。至此,乃见尽性之学尽伦尽物一以贯之。”(《全书》卷1《人谱·证人要旨》)事无巨细地竭尽自己的伦理义务,视天下之事皆己分内之事,视天地间一事未备皆为自己之责任。有了这般伦理义务之自觉,一个人便接近了对自己是人的实证。六曰迁善改过以作圣。这种工夫是证人工夫之极境。蕺山言:“学者未历过上五条公案通身都是罪过,即已历过上五条公案通身仍是罪过。才举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过。即如此是善而善无穷,以善进善亦无穷;不如此是过而过无穷,因过改过亦无穷。一迁一改,时迁时改,忽不觉其人于圣人之域,此证人之极则也。”(《全书》卷1《人谱·证人要旨》)可见,圣人不是现成给予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怀着深切著明的道德理性和自责自悔的罪感意识,长期艰难修炼而成的。
在《人谱》续第三《纪过格》中,蕺山历数了现实中人的种种过恶,从反面论证了道德修养(迁善改过)的必要性及省过改过的方法。他以特有的心理敏感,由微知著,将人的过恶分析为相互连属的六种形式,即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从过、成过,而对“微过”体察最深。蕺山云:“一曰微过,独知主之。妄,独而离其天者是。以上一过实函后来种种诸过,而藏在未起念以前,仿佛不可名状,故曰微,原从无过中看出过来者。妄字最难解,直是无病痛可指,如人元气偶虚耳,然百邪从此易入。”(《全书》卷1《人谱·纪过格》)所谓“微过”即“妄”,“妄”无面目可见,是意根独体极微密之处的“一点浮气”。它甚至可以说不是一种过错,而是“从无过中看出过来”的极微不足道的一点浮妄之气。由于此妄气与独体(意根)相附体,“妄”是“独而离其天者”,就像佛家所说的“同体无明”或“根本惑”,所以也最为微密难治。诚与妄对,心体一真便是诚体,一虚便是妄根浮气。一诚便见意根独体之明,一浮便成妄根微过之惑。意根微密至何处,妄几便微密至何处;诚体是道德理性之终极依托,妄浮之气也与之为终极。所以,妄根浮气看似微不足观,却是众恶潜伏之根,恰似一个元气偶虚之病人,虽看不出病来,而百邪皆可乘虚而入,从而滋生出种种病症来。所以证人工夫当以断妄复明为首义,而断妄治微之方不外“凛闲居以体独”。
刘宗周依据对人的心性行为的分析,来反省人的心性行为展开过程中普遍存在过错的可能性,目的是为实现人的道德生活而预设一道防止人性沉沦的警戒线,以增强防微杜渐的自觉性。为使这一警戒线更加醒目,刘宗周通过对人的过错由微而显层层归纳排列,暗示了一个行为归因理论:原来人间百态的种种过恶,从七情所主的“隐过”,到九容不谨的“显过”,再到五伦不叙的“大过”和百行不备的“丛过”,直到众过而成之众恶,其最初导因不过是微乎微乎,“直是无病痛可指”的“一点浮气”所造。真可谓一念不谨而断送了人间大道。可畏乎!离开意根一步便成妄伪之人,妄伪之世界。本来性体至善,人人皆可成圣,却因一念之微而沦入兽城,岂不可痛可恨!将人类显恶大过归因于心灵潜意识中的一念差失,为的是警醒世人自恨自愧的意识(罪感),从而唤起道德主体自我解救、改过自新的自觉性。有了这种自觉性,“六事功课”便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戒条,而成为道德理性自我呈现的内在的、自律的道德实践。
蕺山为学颇有宗教气象。《人谱》中基本的逻辑格调是,言本体有善无恶,通体皆善;言工夫有过无善,无处不见恶。通过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双向设定,极力凸显善恶之间的冲突,借此使人产生愧疚感,从而走上自我解救的成圣之路。蕺山设计的《讼过法》正是体验善恶对峙,由自愧走上自新的法式之一。他提倡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忏悔的“自讼”精神,让人在道德法庭上将纤毫隐私供认出来,接受良心最严毅的批判:“一炷香,一盂水,置之净几,布一蒲团座子于下。方会平旦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齐手,屏息正容。正俨威间,鉴临有赫,呈我宿疚,炳如也。乃进而敕之曰:尔固俨然人耳,一朝跌足,乃禽乃兽,种种堕落,嗟何及矣!应之曰:唯唯。复出十目十手,共指共视,皆作如是言。于是,方寸兀兀,痛汗微星,赤光发颊,若身亲三木者,已乃跃然而奋曰:是予之罪也夫!……”(《全书》卷1《人谱·讼过法》)在如此自讼之后,由于真诚的忏悔,获得良心的宽恕,从而产生人格自新的向往。观上述“讼过法”,我们仿佛觉得不是芸芸众生正常的道德生活,反而像深山古刹中闭目拂珠的佛家法戒。当丰富的德性内涵为这种干枯的教条戒律代替时,道德或许就失去了内在生命。然而,它的确是蕺山证人之学刚刻严毅性格的真实写照。如此自讼,人格意识中油然产生“若亲三木”悔恨莫及的罪感,而求自新、自恕。通过这样的自我批判,使道德本心常为一身之主。有了这种自觉,便证人内圣之境。
三、蕺山学逻辑向度与历史的离异
刘宗周的自杀从文化价值意义上说是一种“道德涅槃”,它以不惜毁灭自我感性存在的方式实现了心灵境界的升华和内在人格的永恒。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到20世纪初投湖自杀的王国维,其间那无数个具有强烈价值担当精神的节义之士的自杀,与蕺山的死具有同样的意义,那就是“殉道”。他们所殉之道即儒家圣贤标榜的作为人道终极意义的“内圣外王”之道。按儒家成德之教的理解,“道”是贯通天人的生命本体(至善),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道德之本义即有得于道,也就是把普遍必然之道变为自己的德性与德行。抽象地看,即撇开具体的历史功利性用纯道德的眼光去看,一个人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去死,无论在古在今都是悲壮崇高的。但是,被儒家圣人抽象化为永恒原则的“道”只是现实世界伦理政治规范的理想化。只有将其还原于现实世界才能明察和理解此理想世界(道)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用历史的眼光去评价“道”和“殉道”的意义,才能理解其利弊得失。历史地看,人作为历史主体,不是一抽象的价值符号(类本质),而是感性生命(自然性)与理性本质(社会性)相统一的现实存在,是情感主体、知性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当人的感性生命与理性本质(价值理念)发生矛盾而不能两全时,现实中的人是极度矛盾无耐的。不然屈原就不必作那么多忧心忡忡的诗,刘蕺山、王静庵也不必留下遗言表白心迹。在存在(生)与本质(义)发生剧裂冲突时,按照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为了价值理想抛弃感性生命是理性的升华,是崇高;反之,为了苟活于世而背叛价值理想则是灵魂的沉沦,是贪鄙。古典的殉道者大都是不想遭受灵魂放逐而选择自杀的。这是圣人之道为古典士人设定的宿命,它注定了古代士大夫一生的幽怨。扪心自问,何以绝对至善的“道”不能担保现实的人生幸福呢?原因就在于儒家用以塑造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理论基础,即道德人本主义对人性及人道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儒家道德人本主义作为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塑造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第一,把道德看成教育的最高目的。儒家教育的培养对象是“修己治人”推行德治的君子,故其以德教为首务。孟子明确指出,古代教育“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大学》则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些话对后世教育影响巨大,德教几成为教育之全部内容。儒家过分注重道德教化,其最大危害是把人塑造为单向度的道德主体,从而限制了人的能力的全面开发。第二,把立德看成人生理想的最高价值。故自古有“太上有立德”之说,以成德为人生“三不朽”之首(《左传·襄公十四年》)。成德固然重要,但不是人生价值的全部内涵。现实社会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主客关系中,人是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在政治经济关系中,人是权利和义务主体;在人伦关系中,人才是道德主体。把道德价值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压抑了人格的健全发展。第三,先验的人性设定。人性是在人的后天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并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就此而论,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说最为有见。不过,中国儒家道德人本主义,都是依据性善论的先天预设而建立起来的。由于对人性负面因素估计不足,所以在人的社会控制方式上始终实现不了由人治向法治转型,对君权更是毫无限制,致使道统始终成为政统的附庸,士文化成为官文化的点缀。第四,以“复性”为宗旨,向内用力的修养论。内省工夫的发达,一方面使中国人自古养成了强烈的自律意识和内慧早发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不断的反省和道德净化,使人的情感和向外追求的宰制精神为克己灭欲的逆向性意志所抑制,长于德而弱于事,喜静厌动,失去阳刚之气。诚如胡适所说:中国“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功夫,做那向内的修养,越向内做功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如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功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散文》第1集)此话刻薄,却说到了问题的痛痒处。由于儒家把“道”看作人性与社会的绝对根据,期望通过“内圣”而达到“外王”。而“道”并无力承诺这种担保,当理想主义受到现实的无情捉弄时,他们只好去“殉道”。
以上所说是中国儒学道德人本主义之通病,更是宋明理学之沉疴,蕺山之学自然在所难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蕺山所信守的价值理念与时代精神的背反,其恪守的道德人本主义的历史局限较之前儒尤为突出。蕺山生当晚明,面对“天地晦冥,人心灭息”,朱明政权和理学价值体系均发生根本性危机的现实,以“司世教者”自居,居朝则直陈时弊,激浊扬清,苦心竭虑,效忠朝廷;在野则洁身自好,和睦乡谊,集众讲学,倡明世教。最后临难不苟,舍生取义。如站在封建正统论的立场上说,此其一生,真可谓无愧于理学人格期待的铮铮完人。但是道德尺度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尺度。历史地看,16、17世纪之交的晚明,早期市民意识正在觉醒,理学所维护的封建宗法伦理秩序和价值体系已经开始解构和腐烂。封建文化内部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自我批判,活跃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心学思潮与文学思潮便是明证。他们以人的自然权利为核心,在理欲观、情理观、义利观、男女观等方面大胆议论,冲破囚缚,用异端的形式表示了对传统道德人本主义的价值反叛。生当此时,蕺山对异端的权力毫不理解,相反,他以司世教者自居,倡导“证人”之学,努力在已经或正在解体的心学旧基上重建道德理性本体,将已经狂驰于现实世界的人心重新囚缚于冰清玉洁的理性圣殿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隔膜和理性的误导。就此而论,阳明“良知”教虽经蕺山的批判修正而由显归密,而心学的“异端”品格和自裁自决、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却在蕺山的慎独之学中彻底萎缩和丧失锋芒。这同样表明蕺山思想于时代精神的滞后。
蕺山之后,在心性论造诣上无有过蕺山者,其所手创的微密幽深、刚刻严毅的证人之学也随着蕺山之道德涅槃而成为绝响。蕺山弟子中在学术史上名望最著者如黄梨洲(宗羲)、陈乾初(确),对其师心性之学再无发展之热情,成绩远不如蕺山。梨洲虽尊师说,在《明儒学案》中给蕺山学立一显要地位,但在心性之学的阐扬上并未开出新境界。从心学演进看,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黄对本体与工夫的阐释,即“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明儒学案·序》)。在黄梨洲以前,从阳明到其后学,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性本体的先天预设,与此相应的是工夫实践的历史性与本体非历史性之间的紧张。黄梨洲把工夫作为本体所以可能的前提,意味着对先验本体的消解和从心学中的逸出。经明清鼎革,梨洲将学术热情投注于历史与现实之研究,在经学、史学和实学研究中卓有建树,被称为清初“三大儒”之一。其经史之学开浙东史学之先河,而其《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之批判及君臣共治天下之设想,实为近代民主政治之滥觞。它标志着梨洲走出心性圣殿对外王之境的开掘。至于陈乾初则在写给刘伯绳的信中说:“弟与先生,无言不悦,惟诚意、已发未发之说虽极精纯,然弟意欲且存而不论。盖大学断是伪书,而中庸所言尚多出入。”(《陈确集·外编》卷5《与刘伯绳书》)多少流露出对心性问题已无兴趣,且疑《大学》是伪书,以《中庸》义理不纯正,在理欲之辨上主张天理正从人欲中见,等等,其思想价值取向与宋明心性义理已缺少相应之理解。虽为蕺山弟子,思想情感已逸出蕺山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