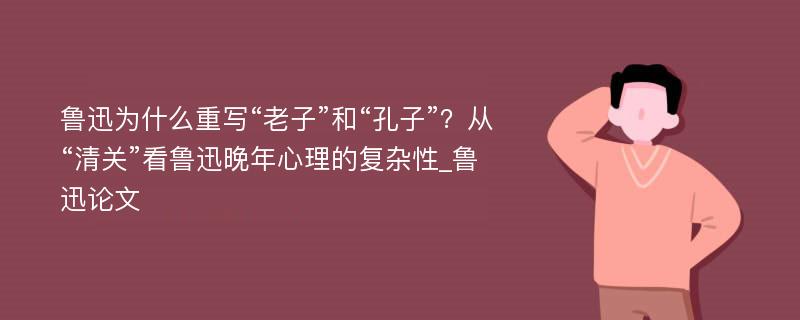
鲁迅为何改写老子和孔子?——从《出关》看鲁迅晚年心态的复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孔子论文,复杂性论文,晚年论文,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5年,鲁迅发表历史小说《出关》,作品发表不久就引起读者的批评和质疑。鲁迅打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①,即刻撰写《〈出关〉的“关”》进行辩解、澄清,这在鲁迅小说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鲁迅小说没有被大面积读者质疑、批评的经历,1920年代,成仿吾全面否定《呐喊》也没有在文坛和社会引起普遍的共鸣,倒经常是作品一发表就引来好评。《阿Q正传》发表的时候,曾经引起读者的猜疑,但是,鲁迅没有当即出面澄清,是后来才予以说明的。鲁迅也谈论自己作品的意图、创作心境、创作方法等等,但往往都是出版小说集或接受报刊杂志采访或给人回信的时候。所以,读者对《出关》的质疑、批评一定极大地触动鲁迅思想,引发他心灵的复杂波动,这就为我们理解晚年鲁迅思想、心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总结读者的猜疑和批评有两种:一是认为影射攻击某个人,一是认为是作者的自况。我认为,前一种与《出关》意指没有关系,这里不进行讨论;后一种却正是关键,我们由此入手来分析鲁迅晚年文化心态及其复杂构成。
《〈出关〉的“关”》颠覆了《出关》的老子、孔子
完全可以把小说《出关》与鲁迅为自己辩解的《〈出关〉的“关”》看做是鲁迅书写老子、孔子的两个不同文本。我发现,鲁迅《〈出关〉的“关”》几乎完全颠覆了《出关》的意指。在《〈出关〉的“关”》中,老子和孔子被鲁迅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写。在《出关》中,孔子形象毫无可取之处,完全是否定性的。他城府极深,心怀庙堂“走朝廷”,他从老子那里学到了“道”却又不能容忍老子的存在,竟然想除掉老子。老子却是一个智者,传道授业,将自己的“道”讲给孔子。他看穿了孔子阴险的内心,决定出关逃离。为了能够顺利“出关”只好敷衍关尹喜等乌合之众,给他们讲“道”。这种结构模式实际上是鲁迅文学的基本结构。比如,在《药》里,夏瑜为大众而献身,但大众不仅不认可,反而把他吃掉。在《颓败线上的颤动》中,母亲靠出卖肉体来抚养孩子,而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却以母亲为耻辱。在《奔月》中,后羿不仅被嫦娥抛弃,而且还被自己徒弟逢蒙暗算。在《非攻》中,墨子帮助宋国免遭楚国的侵略,最后却被宋国的大众抛弃。但是,在《〈出关〉的“关”》中,这种结构被改变,老子和孔子的形象也随之被改变,鲁迅说:
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②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学界对《出关》的解释都是根据鲁迅《〈出关〉的“关”》,都把目光集中在被鲁迅改写的老子和孔子身上,并得出抑老张孔的结论:孔子是实干家,老子是空谈家,进而把鲁迅与儒家文化联系起来:“孔子的进取精神,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实行家风度,是鲁迅所肯定的。”③这种抑老张孔也符合一般国人的心理习惯。在中国社会,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既互补又对立,人们很容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进行一种选择,一旦选择儒家往往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排斥道家。这也许是人们愿意接受鲁迅的解释的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作者决定作品意义、作者高于读者的文学时代,尤其是鲁迅具有权威性的时代,鲁迅的解释自然具有决定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对孔子的肯定放在整个鲁迅思想系统之中,就立刻会发现,它几乎是鲁迅唯一一处直接肯定孔子的文字,与鲁迅一贯的思想习惯极不协调,就像一部乐曲里突然出现了刺耳的杂音一样。我们知道,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者,激烈的反儒家文化者,儒家文化、孔子差不多成了鲁迅匕首、投枪的靶子。鲁迅就是写幽默小品,也要搞一下孔子。比如,鲁迅在给林语堂的刊物写小品的时候,就写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就在写《出关》的同一年,鲁迅还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把孔夫子看做是“摩登圣人”。④前一年还写了《儒术》,讽刺儒学是“无心”之学:它只是一种实用工具,和心灵、信仰没有任何关系。⑤鲁迅对与统治权力关系密切的文化倾向总是极为厌恶。胡适等新月派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鲁迅把他们看做是屈原式的想帮忙而不得。“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⑥鲁迅还写了《隔膜》来嘲笑胡适派知识分子。
对大众的恐惧和无奈
鲁迅为什么要改写孔子呢?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对大众的恐惧和无奈。鲁迅一直对大众/“看客”心怀芥蒂,始终无法完全认同大众,只好像老子给关尹喜们讲学那样“敷衍”一下大众,满足大众普遍的心理需求。鲁迅深知中国社会传统:你不当导师也得当导师,你不当圣人也得当圣人,只有给社会、大众指出一个清晰的历史出路或树立起一个无私奉献的“圣人”偶像,大众才能满意,孤独的个人那些带有鲜明个人烙印的蓬勃多姿、生机勃勃的思想直至被修剪得与平庸社会完全一致,人们才能善罢甘休。大众对于孤独的个人不仅是“骂杀”,还有“捧杀”。“捧杀”就是先把你说成圣人,然后再要求你“应当”如何如何,如果你不按照社会“应当”的法则去做,就会遭到大众的“骂杀”。鲁迅只好收起孤独的老子,掩饰一下自己内心的孤独,拿出一个光辉灿烂的孔子。在对待大众的问题上,鲁迅思想一开始就是同情大众与否定大众的双重结构。鲁迅说自己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就是指这种双重结构。这里的同情只是同情,而不是认同、相通。同情和认同、相通是两回事。留学日本时期,鲁迅一方面说大众会扼杀天才的个人,另一方面又肯定农民的道德纯洁。这种思想结构来自于拜伦式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情结。鲁迅早期接受的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戈尔等人的生命哲学,几乎都是彻底精英主义气质,极端蔑视大众。鲁迅接受的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却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将天才的个人放在首位,也蔑视大众,但是,却不像尼采那样完全拒绝、否定大众。他们在同情大众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自我的姿态。其实,仔细阅读尼采,尼采也有一丝对大众的悲悯情怀,只是他那些批判大众的言论过于激烈、影响过大才被人们忽略了。拜伦式英雄孤独傲岸,蔑视大众,但是,有时却可以扶危济弱,救人于危难之中,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凛然正气。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之中,把自我与大众混成一片绝对是一种耻辱的事情。拜伦在率领希腊人反抗土耳其奴役蹂躏的时候,也同时感到希腊人的难以救药。《唐璜》中的《哀希腊》名句“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把拜伦看做是一种贵族式反抗。⑦
鲁迅绝非如以往阶级论者解释的那样,早期否定大众而晚期肯定大众,走向了集体主义,和劳苦大众打成一片。鲁迅有不少言论是站在大众、阶级的立场之上的,他和梁实秋论战,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他与“左翼”青年作家的交往,与共产党重要人物的秘密会面,与瞿秋白的秘密交往和友谊,包括他的被通缉、对苏联的赞颂等等,却不是那种自觉的阶级意识,也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行动,而是一种浪漫主义英雄的心态。鲁迅曾经感叹自己不善于做政治领袖,其实,鲁迅也很难被组织,被领导。1925年春末,许广平向鲁迅询问是否参加国民党,鲁迅回答说:“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⑧鲁迅无法牺牲自己根深蒂固的自由,或者说他认为已经牺牲了自己若干意见的时候,组织也未必满意。这就有了“横站”的姿势,和私下里对“奴隶总管”的不满。鲁迅加入“左联”就如同拜伦参加烧炭党一样,是政治的诗化,而不是政治本身。从鲁迅留日的经历上看,他虽然无意选择政治,但秋瑾式革命党人的英雄气概在他心中留下了不灭的痕迹。秋瑾式英雄和拜伦式英雄在鲁迅内心交叉共鸣。1820年,拜伦经一位伯爵夫人介绍,在意大利加入烧炭党,勃兰兑斯认为,拜伦对政治并不在行,“烧炭党人的密谋活动在拜伦看来是诗意盎然的政治。英国那死气沉沉的议会政治曾使他极端厌恶,而这种密谋活动却使想象力丰富的拜伦受到强烈的感染。他在密谋团体中被推举到很高的位置,成了一个名叫‘亚美利加’的地方分会的首领。他向密谋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并向那不勒斯的‘立宪’政府捐献一千个金路易,作为对‘神圣同盟’作战的军费。他在书信里直言不讳地痛责奥地利暴君。他无论住到什么地方都是奥地利当局的眼中钉;他的书信被拆开检查,《查尔德·哈罗尔德》的意大利文译本在意大利的奥地利统治区被查禁;而且,正像拜伦自己完全了解的那样,警察也受到唆使要暗杀他。但尽管如此,他仍然镇定自若地每天骑马外出。在这种场合,就像他在另外某些场合一样,他的举止和谈吐都表现出了一种甘愿牺牲的英雄主义和幼稚的无所畏惧相混合的特点”⑨。鲁迅倒没有那么幼稚,他没有参与飞行集会,婉拒李立三要发他一只手枪并请他参加游行暴动的要求,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被刺杀,鲁迅却毫无畏惧,毅然参加杨杏佛追悼会。
鲁迅对老子的复杂心态
鲁迅把老子改写成空谈家,却比他把孔子改写成实干家具有更为复杂的心态。首先,我们会立刻意识到,鲁迅并不喜欢老子。我们很难找到他直接肯定、认同老子的文字,倒是很容易发现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否定性文字。鲁迅厌恶道家文化的“静”与“柔”。认为这不是人性的真诚袒露——人心没有那么恬淡,而是国民生命力衰退的证明,也是道德堕落的体现。它一方面抹去人心中的意志、力量,另一方面又自以为得计,圆滑处世,与时俱化,没有信念,没有灵魂深度和硬度,没有节操,没有责任,是国民劣根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这种国民性造就大量“聪明人”、“伶俐人”,他们甘于平庸、一般,内心卑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奉行一种“处于才与不才之间”的处世妙法,圆滑世故,苟且偷生。为此,鲁迅对林语堂的闲适幽默、朱光潜的静穆、施蛰存的《庄子》和《文选》以及“隐士”都不以为然。在《出关》中,贯穿老子性格始终的是“静”、“柔”、“走”。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随着小说情节进程,这句话被重复了四次。柔,老子用舌头与牙的比喻,告诉徒弟庚桑楚柔能胜刚。然后,就是走,出关走流沙。我以为,这是鲁迅在《〈出关〉的“关”》中否定《出关》的老子形象的最重要原因。鲁迅不愿意以老子自况,更不愿意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一个隐逸、静穆的鲁迅形象。
其次,我们发现,《出关》在写老子的“静”、“柔”、“走”的时候,完全缺乏否定性的逻辑和力量。只是在两次送走孔子的时候——“他才像留声机似的说:您走啦,您不喝点茶去吗?……”才对老子有所讽刺,仿佛老子很俗套一般。此外,我们很难找出对老子构成否定的因素。老子的逃走以及给关尹喜们讲“道”,都无法构成对老子的否定。老子不逃走,难道坐着等死吗?鲁迅自己也主张“韧”性战斗,反对赤膊上阵,更不主张断指流血自焚。关尹喜们怎么能理解老子之“道”呢?这些人除了附庸风雅、沽名钓誉、谋取小利之外,对任何思想都没有兴趣,老子怎么能够认真给他们讲呢?我们根本无法把小说中的老子与“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联系起来。相反,老子的知识和智慧却令人惊心动魄。他第一次给孔子上课是极为真诚的,将自己的最深刻的知识全部告诉孔子。我们通过老子说的“我的话真也说的太多了”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真诚。他整日静坐在那里,遇到上门求教的人却显出一颗赤子之心,而他的观点恰恰说到了孔子屡屡失败的关键所在。第二次讲课,老子发现孔子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道”,同时,也看出了孔子的杀机。这就可以看出老子观察世态人心的深入透辟。他给关尹喜们讲学出口成章,仅仅是随意敷衍,就创造出《道德经》这么深刻的智慧。鲁迅说,老子之所以被读者误解,是因为他对老子漫画化的程度不够。鲁迅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漫画程度不够实际上包含着潜意识的对老子的认同。在小说中,老子被最小程度地漫画化,孔子漫画化程度高于老子。对老子的描述,几乎完全是一种严肃而慎重的写实笔法,没有《故事新编》中普遍存在的“油滑”,这种“油滑”在老子给关尹喜们讲学的时候,才在描述关尹喜们的语言中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
鲁迅与道家文化的深层联系
上述现象表明,鲁迅和老子/道家文化有着更深层的精神联系,如果说反传统的鲁迅也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话,他是对道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中的反传统资源。鲁迅以尼采、拜伦式的激情激活了道家文化之传统。道家文化有狂放的一面,近似于尼采的酒神精神。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说:“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⑩这里的老子和留日时期“不撄人心”的老子是不同的。老子的“愤辞”对社会的批判非常激烈、深刻。《庄子》一面主张心斋,一面却“愤辞”连篇,嬉笑怒骂,那些骂人式批判和鲁迅的一些尖刻文字如出一辙。“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1)这种“汪洋辟阖”来自于庄子的狂放不羁的心灵。嵇康、阮籍等魏晋风度是其终生所爱,尤其是刚烈的嵇康。“魏晋文章”泼辣、狂放、激烈,排圣贤反礼法,乃至无父无君的叛逆精神,鲁迅杂文正是这种精神的展现。那篇被当做遗嘱的散文《死》就是一种“魏晋风度”的刚性体现。杨朱学派把死看得很开,是道家的“随便党”,只要活出自我来,死后一切无所谓,死也要死得特立独行,别具风采。道家文化的“道”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是用心灵建造起来的,是儒家以伦理、政治为轴心构架的世界秩序的对抗。道家文化被静化、净化,乃至被休闲化、犬儒化,是封建大一统专制文化过于强大、个人自由空间日益缩小的必然结果。道家的道/自然未必那么静逸。庄子笔下的柳下跖,“目如星月”,“声如乳彪”。“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庄子·盗跖》)和拜伦笔下的海盗康拉德性格相近,和尼采所钟情的古希腊英雄时代的英雄也有类似之处。庄子的“建德之国”的无知无识的野蛮人包含着“猖狂妄行”野性。
更为复杂的还在于,道家文化狂放不羁的伦理人格来自于道家文化的智慧。鲁迅可以否定它的静逸,却无法否定它的智慧。因为鲁迅的智慧和道家智慧大同小异。老子/道家将世界看做是动态结构、循环结构的“道”,和鲁迅接受的尼采、叔本华、拜伦等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是一致的。道家文化与尼采等人的生命哲学、拜伦等人的浪漫主义是一种文化类型,即生命文化。从浪漫主义开始,一直到叔本华、尼采,以至于后现代主义,它们都呈现出一个没有确定结构的世界图景,以对抗启蒙运动所创造出来的理性的清晰的世界结构。与此类似的是,道家的“道”所呈现的世界图像是生生不息、无法言明的混沌结构,以对抗被儒家文化伦理化政治化所确定下来的清晰的世界图景。尼采的永恒轮回与老子的“道”“周行而不怠”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都将心灵体验、直觉、想象看做是认识世界的最高方式,反对以理性解释世界和人生,都是怀疑主义的。鲁迅《野草》“题辞”的第一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正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鲁迅翻版。鲁迅小说的主体结构是吕纬甫的苍蝇体验:“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什么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住原地点,便以为这是在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么?”“现代史”就如同街头卖艺的“变把戏”一样,永远重复着老一套,而人们依然兴趣盎然地观赏。鲁迅赞成古人这样的说法:“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12)他喜欢那种“推背图”式的对世态人心的透辟观察,鲁迅文学的魅力恰恰得力于这种思维方式。鲁迅喜欢探察人心的深度,一直打入人的潜意识之中。鲁迅的猜疑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在小说中,老子第一次给孔子上课的那段话,是老子哲学的体现:
“你还算运气的哩,”老子说,“没有遇着能干的主子。六经这玩艺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你的话,可是和迹一样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难道就是鞋子吗?”停了一会,又接着说道:“白鸭们只要瞧着,眼珠子动也不动,然而自然有孕;虫呢,雄的在上风叫,雌的在下风应,自然有孕;类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
这里包含着老子哲学的基本思想:一、世界是变动的;二、独一的个体生命是最坚实的社会单元;三、个体生命是不能给予的;四、孔子的知识是形而上学的。鲁迅无法否定老子的这种智慧,因为它伴随着尼采、叔本华们早已融化在鲁迅的血液里。当鲁迅沉浸在小说创作过程之中的时候,他进入了一个更为丰富的活跃的心灵状态,便无意识地流淌出来,从而给读者以“自况”的强烈印象。当读者质疑、批评的时候,鲁迅如梦方醒,又回到了往常的意识中来。读者把鲁迅看做是“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的老人”,无疑与鲁迅存在着极大的“隔膜”。鲁迅年轻的时候何尝不是这样孤独、悲凉?这恰恰是鲁迅文学的基本色彩,在鲁迅任何时期几乎都能找到这种色调。这里,我们倒可以看出鲁迅心灵的丰富、复杂和悖论。
注释:
①②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第520页。
③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④鲁迅:《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⑤鲁迅:《儒术》,《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⑥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⑦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5页。
⑧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页。
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四),徐武谷、江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页。
⑩(11)鲁迅:《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第364页。
(1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3页。
标签:鲁迅论文; 孔子论文; 道家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出关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