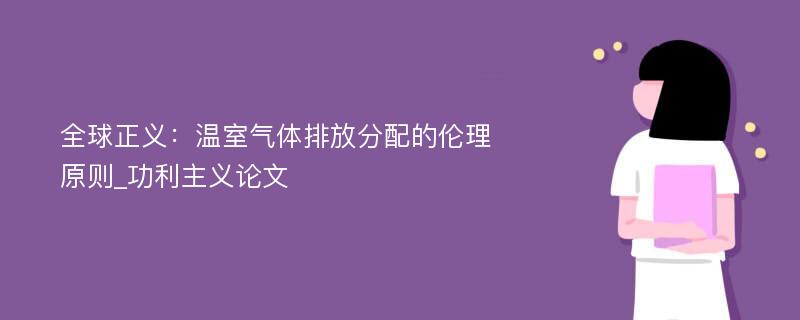
全球正义: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室论文,伦理论文,气体论文,正义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2012年的临近,确认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京都议定书》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如何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框架,已成为“后京都时代”全球气候谈判的焦点。2007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正式开启了“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历程。经过艰难的谈判和两年的准备,为后京都时代的国际减排协议制定框架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终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但是,“风雨过后,未见彩虹”,哥本哈根大会最终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以接替《京都议定书》的“哥本哈根议定书”。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留给人们的是深深的遗憾和痛苦的思考。
长期以来,国际气候政治一直由三大集团(即发展中国家、欧盟以及由美日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的互动所决定。它们在气候政策上的分歧,既源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也源于对不同的伦理原则的坚守。哥本哈根会议之所以无果而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发达国家强调的是形式的平等,它们坚持认为,在应对气候变暖这一共同挑战面前,所有国家都应承担相同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实质的平等,认为在参与应对全球变暖这一全球合作计划时,不仅要考虑各国所具有的不同的参与能力,而且要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全球变暖的主要肇事者应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因此,国际社会要想在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分担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必须首先在“如何分担温室气体减排的义务才是合理的”这一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原则层面的共识是解决政策分歧的基础。
一、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从消极的角度看,国际气候谈判表现为如何确认各国应当分担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从积极的角度看,谈判的目标则是确定各国应当享有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即排放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某些国家之所以被要求承担减排义务,就是由于它们的排放已经超过了它们应得的排放份额。因此,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而依据何种伦理原则来分配排放权就成了国际气候谈判的争论焦点。
目前,对国际社会影响较大的分配排放权的伦理原则主要有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发达国家主要援引历史基数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来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主张把历史责任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这四条原则。
1.历史基数原则
历史基数原则(Grandfathering principle)很难说得上是一条伦理原则,不过,鉴于一些主要的排放大国往往援引这一原则来为自己的较高排放份额进行辩护,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它当作一条“准伦理原则”来加以讨论。这条原则的规范意涵是: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公平分配应考虑不同国家在过往年代的排放规模;一个国家的具体减排数量应当以该国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的排放总量为参考依据。
《京都议定书》对附录中A类国家(部分发达国家)的减排要求就部分地体现了这一原则,因为它要求A类国家依据其1990年的排放水平来确定相应的减排目标。例如,它要求欧盟2010年的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8%,而日本的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6%。
以往的国际气候谈判之所以认可并接受历史基数原则,往往是出于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在制定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总额的计划时,把历史基数作为确定减排目标的出发点是必要的,因为不考虑历史排放基数的做法不会被排放大国所接受,难以实施。所以,为了确保排放大国能够主动配合减排计划,以便最终实现更为公平的排放,我们有必要认可历史排放的合理性,并把它作为分配减排份额的基础。[1]
不过,历史基数原则很难获得伦理上的辩护。首先,即使历史基数原则在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是可行的,也不意味着它就是公正的。排放大国拥有较强的谈判筹码,为了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只能作出妥协和让步,接受它们基于历史排放基数而提出的排放要求。但是,对排放大国作出的这种妥协和让步,并不意味着基于历史基数原则而制定的计划就是合理的,也不意味着排放大国的博弈行为就是正义的。正如罗尔斯所说:“根据威胁优势来分配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正义观。”[2](P103)英国学者巴里也指出:“正义行为不能归结为对自我利益的精致的和间接的追求。……正义不应当是为剥削铺平道路的一种设计,不应当是确保具有较强谈判优势的人把其优势自动转化为有利结果的途径。”[3](P362)其次,历史基数原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原则。历史基数是作为实现一个更加公平之分配的起点而被接受的。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额外的原则来确认,什么样的分配才是更加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历史基数原则需要一个正义原则来加以引导和补充。再次,根据历史排放基数,历史上的排放大国可以获得较大的人均排放份额,而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较小的人均排放份额。这种做法将严重危害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它们的人民难以摆脱贫困和欠发达的状态。这是对后者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基本人权的漠视。最后,历史基数原则是对人们普遍接受的历史责任原则的公然违背。根据历史责任原则,那些破坏了环境的人,应当承担起修复被他们破坏了的环境的责任;那些向人类共有的大气层中排放了较多温室气体的国家,应当承担起清除大气层中多余的温室气体的责任。但是,历史基数原则不仅没有对排放大国的历史排放行为进行惩罚,反而通过给予它们较多的排放份额而对它们的历史排放行为加以奖励,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获得伦理上的辩护的。
2.历史责任原则
根据历史责任原则,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恰当分配应当反映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在向人类共有的大气层中排放温室气体,不仅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存量主要是发达国家长期大量排放的产物,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目前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应大幅度削减其排放量,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继续增加其排放量,直至达到它们应当享有的公平份额为止。这意味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份额。
历史责任原则也被称为“污染者付费原则”,它要求污染了大气层的发达国家承担起修复大气层的责任。正如辛格所说:“如果在上个世纪,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一直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上,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面对由人类行为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了,而且我们会在废气排放达到引起严重问题之前,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来采取措施。因此,用小孩子都能理解的话来说,当人们关注到大气时,发达国家已经破坏了它。如果我们认为,人们应该按照与他们的责任相称的比例来出力修复他们弄坏的东西,那么,发达国家对于其他国家负有解决大气问题的义务。”[4](P32-33)历史责任原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都得到了充分表达。
尽管历史责任原则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在应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时,它也存在着一些实践上的难题。首先,关于不同的发达国家在1990年以前究竟排放了多少温室气体,人们缺乏具体的数据,因而很难作出它们各自究竟应当减排多少温室气体的决定。其次,历史责任原则要求我们确认排放行为的责任主体,但是,在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方面,责任的主体往往很难明确地加以界定。例如,如果甲国以高排放方式生产的产品G被出口到了乙国,乙国是这种产品的最终消费者,那么,究竟是甲国的生产商还是乙国的消费者应当为产品G的温室气体承担责任?①最后,历史责任原则并不是圆满自足的,它需要正义原则的补充。历史责任原则之所以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就是由于它认为,发达国家在其以往的历史中,排放了比它们应得的份额更多的温室气体。但是,历史责任原则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究竟可以排放多少。因此,只有当我们确认了一个国家究竟应当获得多少排放份额后,我们才能确认,一个国家的过往排放是否超过了它应得的份额。②
3.功利主义原则
功利主义追求的是功利总量的最大化。依据功利主义的标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应当这样来安排,即这种分配能够使受到影响的人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净幸福。净幸福指的是在得到的所有快乐中扣除所遭受的痛苦后余下的东西。古典功利主义主要把幸福理解为快乐,现代功利主义则主要把幸福理解为偏好的满足。
尽管功利主义原则在公共决策中被广泛地使用,但单纯的功利主义原则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功利主义只关心偏好的满足,却不关心偏好本身是否合理。然而,只要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所有偏好并非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些偏好也并非都应当得到满足。我们的某些偏好是理智、健康、符合道德或无害的,这些偏好应当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的某些偏好却可能是愚蠢、病态、危险或不道德的,这些偏好就不应当得到满足。一个饥饿的穷人希望得到一片面包的偏好明显要优先于一个富人希望得到一辆豪华赛车的偏好。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偏好都看得同等重要,那么,富国的居民就会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由于其富裕的居民已经习惯于自己开车旅行,[习惯于]在闷热的天气下保持室内的凉爽,[因此]要让他们放弃高度耗能的生活方式,那么,比起那些从来没有机会享受此等舒适的穷人来,他们会遭受更多的痛苦。”[5](P41)事实上,一些人正是根据偏好功利主义来为发达国家不愿意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在他们看来,大幅度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会使其居民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受到影响。但是,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与发达国家之居民的奢侈需求相比,发展中国家之居民的基本需求具有优先性,即使发达国家之居民从其奢侈需要的满足中获得的幸福感,与发展中国家之居民从其基本需求之满足中获得的幸福感同样多甚至更多。
其次,功利主义只关心福利总量的增加,却不关心福利的合理分配。假设存在着一个穷国和一个富国,其中穷国的福利总量是3,富国的福利总量是6。现在,有两种温室气体减排分配方案:方案甲要求穷国减排2%,富国减排4%;此方案给穷国增加的福利是3,给富国增加的福利是2。乙方案不要求穷国减排,要求富国减排6%;此方案给穷国增加的福利是4,给富国增加的福利只有1。这两种减排方案所增加的福利总量都是5。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两种减排方案都是同样合理的。但是,凭直觉我们会认为,方案乙更合理,因为此方案缩小了穷国(甲方案给穷国带来的福利总量是6,乙方案带来的福利总量是7)和富国(甲方案给富国带来的福利总量是8,乙方案带来的福利总量是7)之间的福利差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平等的状态总是优于不平等的状态。
再次,功利主义把功利和效率看得比权利更重要,忽视了权利的不可让渡性。从效率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单位温室气体的产出肯定高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从功利主义出发,把更多的排放份额分配给发达国家似乎就是合理的。但是,从人权的角度看,功利主义这种强调效率而忽视基本权利之不可让渡性的做法是难以获得伦理辩护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之人民基于生存的排放需求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忽视他们的这种需求就是忽视他们的基本权利。此外,功利主义的这种思维方式还忽视了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独特的,我们并不能把甲的幸福从甲的生活中剥离出来,然后把它转让给乙。发达国家从其高效率的温室气体排放中所获得的收益,并不能自动转化成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因此,即使发达国家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的GDP效率远远高于落后国家,我们也不能基于单纯的效率考虑而把落后国家本应获得的排放份额分配给发达国家。
4.平等主义原则
根据平等主义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权利排放同等数量的温室气体,因而,每一个人不管国籍、性别、年龄、能力如何,都有权利获得同等数量的排放份额。这一排放原则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印度学者阿贾韦尔和纳瑞恩认为,地球吸纳温室气体的能力属于全球公共财富,这种公共财富应以人头为基础来平等地加以分配。[6](P13)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前任主席杰姆森指出:“在我看来,最合理的分配原则是这样一条原则,它直接主张,每一个人都拥有权利排放与其他人同样多的温室气体。我们很难找到理由来证明,为什么作为一个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就有权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而作为一个巴西人或中国人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排放权利。”[7]辛格更是明确地指出:“对于大气,每个人都应拥有同等的份额。这种平等看起来具有自明的公平性。……在没有别的明确标准可用来分配份额的情况下,它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妥协方案,它可以使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而不是持续的斗争。还可以进一步论证的是,它也为‘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进行辩护提供了最好的基础。”[8](P34、40)
按照国际气候变化政府间组织(IPCC)2007年的研究报告,地球温度上升不超过摄氏2度是人类可以适应的极限水平,这相当于要求到2050年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50ppm。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应控制在200亿吨。根据联合国的预计,2050年的全球人口为90亿。如果以90亿人作为分配的基本人数,那么,根据平等主义的分配原则,每一个人有权排放的二氧化碳份额是2吨左右。如果2吨是每一个人应得的排放份额,那么,根据2006年的数据,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都超过了他们的应得份额,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则低于他们的应得份额。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人均年排放量分别是5.18吨、4.90吨和4.55吨,日本、德国、英国的人均年排放量比较接近,分别是2.80吨、2.67吨和2.56吨,我国的人均排放量是1.27吨,巴西和印度分别是0.51吨和0.37吨。2006年,全世界的人均排放量是1.26吨。我国的人均排放量于2006年首次超过了全球的人均排放量。[9]目前,很多学者都主张以这一分配份额作为分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重要依据。[10]
平等主义原则最大的优点是简单易行,但是,它也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如果以未来某个时段的人数作为分配排放份额的基数,那么,这就会激励各国想方设法增加人口。人口数量越多,人均可获得的分配份额就越少。这样,人口增加的国家就会给人口不增加的国家带来额外的负担。如果以现行的人口数量作为分配的依据,那么,那些年轻人比例较高且即将进入生育高峰的国家又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次,平等主义的分配方案对于那些生活在比较寒冷地区的人们来说似乎也不够公平,因为与那些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们相比,他们在冬季需要较多的能源来取暖。对于分配正义而言,地理位置似乎是一个任意的因素。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不应因为其居住的地理位置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再次,平等主义原则完全忽视了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事实,把它们的历史责任一笔勾销了,这无疑是对发达国家的一味迁就,违背了历史责任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最后,平等主义的分配原则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的发展压力。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有史以来,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期。在其高峰期,美国(1973年)的人均排放接近6吨,英国(1971年)和德国(1979年)也超过3.5吨,法国(1979年)和日本(1995年)则是人均2.5吨。[11]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其排放高峰期也把人均排放控制在2吨以内,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将背负比发达国家更重的发展负担。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二、全球正义: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上述四条原则既拥有各自的长处与合理性,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与局限性。从全球伦理的角度看,一种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基础的全球正义原则应当是最为理想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正义理论,其所提出的分配正义的两条基本原则满足了人们对权利与平等的价值诉求,反映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基本道德共识,可以作为我们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基本框架。罗尔斯认为,对“基本的社会善”的分配应当遵循两条基本的正义原则:(1)权利原则。每一个人对该社会所确定的基本自由都享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2)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满足两个条件,即这种安排所提供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基于机会的公平原则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平等原则),同时,这种安排能够有利于社会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惠顾最不利者原则)。[12](P47)
就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人类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前提而言,我们可以把温室气体的排放权理解为罗尔斯所说的“基本的社会善”之一。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分配原则,我们可以引申出分配排放权的两条基本的全球正义原则,即全球正义的权利原则与差别原则。[13]
全球正义之权利原则的基本理念是:每一个人,不论其性别、种族、国籍如何,都有权享有最低限度的温室气体排放份额。所谓最低限度,指的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及合理发展所需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这种最低限度的排放权的分享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种权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平等地加以分配。确保这种基本权利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实现,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公民的基本义务。[14]
全球正义之差别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对高于最低必需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份额,可以依据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效率原则)酌情实行一定范围内的、动态的不平等分配,但是,这种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其一,这种不平等分配不构成贫穷国家发展其经济或保护其环境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其二,这种不平等分配符合最不发达国家及其人民的最大利益;其三,这种分配必须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即这种不平等分配是其他国家及其人民自愿接受的;其四,历史上的排放大国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如果我们把200亿吨的排放量作为全球分配的“基本的社会善”,并把2050年的90亿人口作为参与分配的基数,那么,根据全球环境正义的这两条分配原则,我们就可以把人均2吨的排放权作为基本的权利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目前,全球实际人口还不到70亿。我们可以把联合国预计的2011年的实际人口70亿作为分配200亿排放权的基数。这样,在满足了作为基本人权的人均2吨的前提下,全球还剩下60亿吨的排放权。对于这60亿吨的排放权,则可以根据差别原则来进行分配。
与前面的四条分配原则相比,全球正义原则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
第一,全球正义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平等主义的,它首先要求我们把绝大部分的排放权作为一种基本的权利来平等地加以分配。这样,它就满足了人们对于平等的价值诉求。同时,它又允许把另外的60亿吨排放权分配给那些因各种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或国家。这样,它又避免了绝对的平均主义。
第二,全球正义原则以个人而不是国家或地区作为分配基本排放量的基本单位。这种分配方式符合现代社会的这一普遍的道德共识: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与一个人的国籍、种族、性别或社会地位无关),而且都是道德关怀的终极目标。
第三,与历史责任原则相比,全球正义原则对于发达国家无疑要优惠得多。但是,全球正义原则并没有把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一笔勾销”,因为,在对另外的60亿吨进行分配时,它将参考各国的历史排放记录,并要求历史排放大国承担起“污染者付费”的责任。因此。全球正义原则与《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一致的。
第四,全球正义原则对其余60亿吨排放权的分配是动态的。在初始阶段,它可以依据历史基数原则,对历史排放大国给予一定的照顾,以便这些国家能够顺利地转型到低碳社会。在中期阶段,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步入排放高峰期时,则可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给这些国家提供一些额外的份额,以确保这些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惠顾最不利者的原则,这剩余的60亿吨份额还可用于支持那些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以及那些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
第五,如果我们把人均2吨的排放权视为每个人应得的排放份额,那么,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用完了他们的应得份额。“但幸运的是,这里有一套机制,它既充分满足平等的人均份额原则,又使得工业化国家在相对容易地实现过渡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巨大的利润。这个机制就是排放量交易。”[15](P43)那些人均排放较低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售其剩余的份额而获得发展的必要资金,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购买前者的排放份额满足自己的排放需求,并提高单位温室气体的排放效益。
第六,全球正义原则不仅仅是各国之间相互交往的伦理原则,它更是构建国际制度的制度伦理。全球正义是国际制度的首要价值。作为一种制度伦理,全球正义更加关注国际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并把建构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背景制度作为自己的首要关切。只有在这样一种合理的国际制度的保障下,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才能成功地解决包括全球变暖在内的各种全球问题。
由上可见,全球正义原则不仅吸收并体现了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的优点,同时又避免或弱化了它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全球正义原则应当是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最理想的原则。
三、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实现全球正义的文化保障
罗尔斯曾说过,国内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合理的、以伦理意义上的正义理念为核心的“公共政治文化”的支持[16](P8、43);同样,全球正义的实现也要以一种充分发育的、以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念为核心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在这样一种全球公共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国际社会才能够超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思维,把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在内的全球问题都当作“全球内政”(而非“国际外交”)问题来处理,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统一而协调的行动。
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个人是道德关怀的终极单元;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价值与尊严;每一个人既是民族共同体的普通公民,也是属于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公民,并负有关怀他人的普遍义务。③这种全球公共政治文化还要求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认可并坚持这样一些基本的国际伦理理念:人人都享有基本的权利(特别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所有的国家一律平等;国家也是一个道德主体;国家间的交往应遵循基本的伦理规范。
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世界主义态度而言,关键的是要拒绝把政治结构视为终极价值的源泉。”[17](P24)“不论出生或成长在何处,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价值和自由。”[18](P462)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成员。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这只是由出生的时间和地点这类偶然因素所决定;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并享有平等的尊严和内在价值,这才是人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属性。家庭和民族国家固然是我们认同和忠诚的对象,但是,比民族国家更为庞大和久远的人类和人类文明同样是我们认同和忠诚的对象。因为,我们既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我们有较强的义务确保本国公民的基本需要优先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并无特别的或更强的理由把本国公民的非基本福利看得比外国公民的基本福利更重要。辛格认为,把帮助自己同胞的义务当作一种相互性的义务而置于帮助其他国家公民的义务之前,这是好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是把自己同胞的非基本需要置于其他国家之公民的更为迫切的基本需要之上的充足理由。[19](P171、181)赫尔德则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边界不再拥有它们在古典主权时代曾经拥有的那种法律和道德重要性。“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的成员身份,或者空间的接近性,都不再被看做是享有道德特权的充分依据。”[20](P188)
世界主义反对那种把人类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代表上帝的所谓善良民族与代表撒旦(或魔鬼)的所谓邪恶民族——的冷战思维方式。在世界主义看来,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世界公民权利。任何民族都没有权利总是把自己的利益诉求看成是合理的而把其他民族的利益诉求看成是不合理的,更没有权利把其他民族当作先天的敌人来对待。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当通过建立在普遍的世界公民权利之基础上的国际法来加以解决。同样,只有当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把其他国家的公民当成合作者而非敌对者来看待的时候,民族国家之间的所谓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证,数量惊人的安全成本才能真正地降下来。④
作为一种普遍价值,世界主义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世界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21]在儒家看来,所有的人都是天地父母所生,在天地父母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同胞兄弟。因此,我们不仅要关心天下所有人的疾苦,而且要一视同仁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父母,要像关心自己的子女那样关心他人的子女。⑤墨家更是主张平等的博爱,反对战争,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国家与他人的国家。⑥到了20世纪初,虽然民族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中国也因民族主义意识不够强大而遭受着各种耻辱和苦难,但是,康有为仍高瞻远瞩地指出,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破除种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建立世界主义的全球政治制度,才是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连年战争、实现人人幸福的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22]同样,世界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传统之一。[23]在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看来,所有的人都是人类共同体的成员,人作为世界公民的身份是由人所共有的本性决定的。人首先是一个世界公民,其次才是特定国家或城邦的公民。作为世界公民,我们不仅对所有的人都负有义务,而且要关心人类的整体福利。古希腊的这种世界主义理念在近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康德看来,一个自由和理性的公民,不仅属于某个民族国家,而且也属于全世界,是世界公民,他所必须遵从的理性的普遍法则,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公民共同体之间互相的尊重和承认。”[24](P92)康德不仅提出了“永久和平”的理念,还提出了“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25]康德关于通过建立“全球邦联”以实现永久和平的思想,更是成为20世纪的政治家创立联合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人类文明中这些源远流长的世界主义传统,为我们培育和建设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不仅如此,世界主义还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实践的重要主题。正如赫尔德所说:“在某种程度上,世界主义在当前——而不是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已经确立了一系列的规范和法律体系。世界主义已经融入了各种规则体系和制度[之中],后者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改变了主权国家体系。”[26](P465)例如,人人平等、相互认同与公共理性等世界主义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重要法律与制度设计(特别是与区域和全球治理有关的制度设计)中都得到了体现。“人人都应获得平等的对待与尊重”的原则被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随后的《权利公约》(1966年)视为基本的出发点和人权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人权宣言》不仅正式承认“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内在的尊严以及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宣称这一原则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权宣言》的这一价值取向标志着世界主义法律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根据《人权宣言》,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是政治权力的终极基础;个人权利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它超越了国家政体的特殊利益,是判断各种政治共同体之合法性要求的最终依据。因此,可以说,“世界主义观念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和政治重大发展的核心。人类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区域决定的,国家、种族或性别的区别不应成为那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些观念都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当代区域与全球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当中,也渗透到某些跨国治理形式当中”。[27](P46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主义正在部分地制度化与法律化的事实,为我们培育和建设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土壤。
总之,国际合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国际囚徒困境。消除国际囚徒困境的根本出路是培育以世界主义理念为核心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培养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和全球责任意识的世界公民。只有当各国人民及其政治家都具有世界公民的美德和基本的全球正义意识(即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感),国际政治才能真正走出囚徒困境,包括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在内的国际博弈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
注释:
①据估算,在1997-2003年期间,我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7%~14%是用于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而美国在同期如果不从我国进口这些产品并自己生产这些产品的话,那么,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将增加3%~6%。参见Bin Shui and Robert C.Harris.“The Role of CO[,2] Embodiment in US-China Trade”.Energy Policy,2006,vol.34(8).
②一些人还认为,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是由发达国家人民的先辈排放的,发达国家的当代人并未参与那时的排放,因此,要求发达国家的当代人为其先辈的行为负责是不合理的。我们同样可以用“获益者补偿”这一理据来反驳这种观点:发达国家的当代人是其先辈的超量排放的获益者,因此,他们应替其先辈承担起修复大气层的责任。参见Simon Caney.“Justi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ournal of Global Ethics,2009,vol.5(2).
③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世界主义价值观可以正式表述为一组原则,其中八个原则最为重要,它们是:平等的价值和尊严;主观能动性;个体责任和义务;同意;公共事务须通过投票程序集体决定;包容性和从属性;避免严重伤害;可持续性。参见赫尔德:《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22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④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8年6月8日发表的报告,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创新高,达1.464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4%,相当于每人217美元。(参见安国章;《世界军费开支2008年创新纪录达1.464万亿美元》,http://www.chinanews.com.cn/gi/gj-qqjs/news/2009/06-09)如果人类能够把全球的安全与和平建立在以全球正义为基础的全球制度的基础之上,那么,全球从军费开支中结余下来的资金(即所谓“和平红利”)足以用于应对全球变暖(应对气候变暖的全球支出每年只需数千亿美元)。
⑤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观念。成书于西汉的《礼记·礼运》初步总结了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世界主义的基本轮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宋代的张载(1020-1077年)则进一步深化了儒家的世界主义观念:“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冀也。”(张载:《正蒙·乾坤》)
⑥墨子倡导“兼相爱”,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战争是不义之举,因此,他反对战争,主张“非攻”,“杀一人谓之不义……杀十人,十重不义……杀百人,百重不义”(《墨子·非攻上》);而最不义的事,就是侵略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