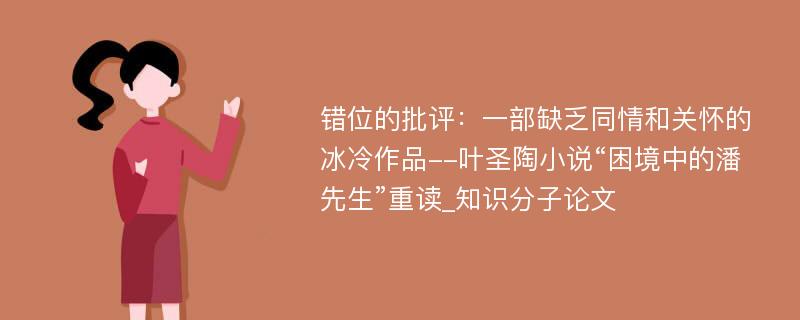
错位的批判:一篇缺少同情与关怀的冷漠之作——重读叶圣陶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作论文,冷漠论文,叶圣陶论文,小说论文,潘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知识分子的名篇,连续多年都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自从茅盾作出“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意识,卑谦的利己主义,precaution,琐屑,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写得很透彻”(注:方壁(茅盾):《王鲁彦论》,《小说月报》1928年1月号。)的判断之后,文学史对这篇作品的评价似乎已经形成了定论。这不是对一篇作品或一个人物的评价,而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人格和性格的批判。其实,潘先生的个人欲望和处境是否应该同情?其社会意识是否清醒?如何评价其行为与思想的矛盾?这一系列问题是有必要重新探讨的。
首先,如何看待和理解潘先生的“卑谦的利己主义”问题,是我们重新评价《潘先生在难中》这一作品的思想焦点。
从抽象的道德原则上看,潘先生的一切举动是可笑可鄙的,但是一切又是无奈的,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的生存的权利。作为潘先生他有权利生活得更安定、更完整。潘先生的人生是“琐屑”的,但是生活和家庭本身就是由琐屑构成的。他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家庭成员的“一个都不能少”,他的一字长蛇阵本身就是这一种期望的象征,也是一种动荡和辛酸的象征。他与妻儿的离散是人生的最大悲剧,求得家庭的完整是人最低的生活愿望,而这些努力和巴结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他对妻儿千方百计的呵护之心和万般体贴之情,渗透着真挚的爱。有爱的人的才可能是善良的人。当他见不到混乱人群中的妻儿时,他“禁不住浸出两滴眼泪来”,这浸出眼泪来的焦急,是值得人们同情和令人相信的。没有经历过真切体验的人是不会体验到其中的切肤之痛的。“无情未必真豪杰”,能为别人而流泪的人一定是可爱的人,从不流泪的人也许是坚强,但也许是可怕。当潘先生从战区率领全家逃出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分散而最终与妻子会合时,不禁感慨万千:“现在好了!”其实这合家团圆本身也是一种不幸,因为这已经成了战乱中的中国普通民众的最高的理想。当他听说火车真的不通了,“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大战在即,独处空旷的家中,“潘先生想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起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此时,潘先生可能想到了平日院子里孩子们嬉戏的笑声和充溢着的家庭的温情。此情此景是催人泪下的,也是让每一个父亲和丈夫动容的。
潘先生是无奈的,其行为也必定称不上高尚。但是,面对那些“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踩,都可以踩做泥团踩做粉”的兵士们,面对即将成为战场的家乡和可能遭遇到的屠城之虞,我不知道作为一介书生的潘先生除了躲避和尽量保全家小的生命安全之外,还有什么更高尚或更稳妥的方法?而作者却在那里冷漠地嘲讽,我不知道此情此景如果是作者自己该会怎样?在那种境况下,难道还要求他抛弃家小或组织民众或自己单干,拿起武器与杜师长或其他什么师长之类的军阀进行抗争吗?
其实,潘先生的行为和心理深刻地表现了军阀混战给底层人民带来的动荡和苦难,而作者嘲讽的对象却错位地转移到了受害者身上。潘先生是受害者,在和平的环境里,他肯定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教师。正如潘师母所说的那样“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潘先生的全部矛盾和弱点其实就是既要“保家”又想“卫国”,实现“保家卫国”的理想是他当下最大的愿望。当他暂时不能“卫国”时也只有尽力地“保家”了。在这混乱的生活状况下,潘先生们本来已经够不幸的了,所谓的“灰色人生”不过是在身不由己的战乱环境中,既想尽到教师职责又想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职责而已。
在一个不能自主的社会里,不能剥夺小人物的生存的权利和生存的方式。要知道,潘先生的行为没有对任何人构成伤害,只是求得对自己和家人的保护,他不是以损人利己为目的就已经是好人了。对于他这样一个小人物来说,他只能用比较卑微的方式使自己和家人避免伤害。潘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根性,谨小慎微,巴结取巧,活得十分辛劳、卑琐,也有些委曲求全。作者应该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使潘先生一家处于危险、动荡、艰辛的社会环境上,放在社会中的支配性的人物身上。个体人格的批判在这时并不重要,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或个体人格的批判的价值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不能把人对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渴望和努力视为一种堕落,更不能把战争中的责任归罪于懦弱的知识分子。是谁制造的了这场灾难?在善恶对峙的社会里,是批判强者还是批判弱者?答案之间是存在着思想的差异和境界的差异的。这也是叶圣陶与鲁迅在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文学主题意蕴上的差异之所在。
无论任何时候,不能保护弱者的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首先应该保护守法者。而在作家的立场上,批判弱者而不去批判强者,同样也是不公平的。《潘先生在难中》在艺术上一直被称道的“冷静地描写”,实质上是作者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旁观的角度,把一种社会灾难中的受害者小丑化了,漫画化了,人间悲剧于是也就成了生活喜剧,所谓的“冷静”之中其实渗透了冷漠。而嘲讽不幸,戏谑悲剧,是不道德的行为,最后必定使社会失去公正与爱。
其次,潘先生是否“没有社会意识”?
毫无疑问,潘先生的思想与行为充满了矛盾,但是他返回学校的决断还是应该肯定的。他重返战场既有怕失去工作的生计之忧,也有怕被别人看轻的名誉之虑,而其中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也是不能否定的。他懂得不能放弃一个男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教师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尽量想将这责任“三位一体”地承担起来。好容易逃离战乱的家乡,好容易经历妻离子散才获得合家团圆,他本可以不从安全的上海回到大战即将发生的家乡,然而他思索再三,不听夫人的苦心劝阻,还是觉得“回去终是天经地义”。能够下这个决心并付诸于行动,即使算不得高尚,但也不能说是卑微吧?相反,我觉得这足以证明他精神深处还保留着一种尊严和豪气。潘先生可能是坚守岗位到最后的教师,“红房子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都是十天前就搬来的”。连教育局长和其他同仁也早就在那里占据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潘先生为胜利者书写那块“功高岳穆”的牌匾,是他缺少骨气和清醒社会意识的最大政治嫌疑和人格污点。但是,潘先生的思想还是清醒的,最后他在为胜利的军阀书写牌匾之时,还能清醒地知道,正是这些军阀造成了“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除此之外,他没有做任何伤害他人和社会的事。他的可笑可怜之外是不是还有些可爱可敬?
第三,“永远高尚”或“不许平庸”的自认角色和社会评价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高远的伦理要求,而知识分子也把过于沉重的社会使命肩于自身,把社会使命看得过于沉重,并在理论上自认了这一角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承传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每一种行动和思想都有了特别的要求,而为人师表的信条更是教师做人的传统戒律。因此,一旦知识分子超出这一道德规范而表现出一种常人应有的欲望时便被人谴责。人的社会存在包含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两个层次的要求,社会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起码的公民意识,是社会规范的一般要求。职业道德便属于社会义务范畴;而社会责任则是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是超越于自己的利益需求而表现出来的崇高。作为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慨当以慷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与天下同忧,和天下同乐也绝不是不崇高的状态。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意识中,“永远高尚”或“不许平庸”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社会的评价尺度和知识分子自身的传统角色。
知识分子的确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弱点,性格具有二重性,行为优柔寡断,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和社会给知识分子限定了过多和过于沉重的道德重负。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两重人格:形而上的道德自律和现实生活具体的需要与诱惑。分裂的人格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更高的道德要求。这道德的要求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向善的要求,有这种要求总比没有这种要求要好。而本能的欲望和道德要求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虚伪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先天的本性,平凡甚至平庸也不能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而应该反思的是被高置和虚置的道德信条。柳下惠的高洁与定力之所以被历代慨叹,就在于其人其事的空前绝后和绝无仅有。当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达到“坐怀不乱”的境界时,那么“坐怀不乱”的虚拟教谕是否合理?是否还有意义?
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没有宗教信仰,来世观念或神鬼意识的束缚较少,以儒学为主体的入世观念是其基本意识。儒教不是宗教,没有严格的教规、教仪,因此没有纯正宗教传播过程中的限定性。所以与纯正宗教相比,儒家观念系统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具备宗教的神圣性而不具备宗教的神秘性,是世俗化的准宗教。神圣性使其获得了纯正宗教的权威性,世俗化又使其获得了纯正宗教所没有的广泛性。所以,儒家道德观念不仅高悬于殿堂之上,亦散布于穷乡僻壤之间,它渗透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承传的生活细节和精神深处。它不仅是人们的知识价值标准,也是道德说教的价值体系。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感来得格外强烈,君子之风度,丈夫之气节,文人之德性,教师之表率,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为人处事的信条。而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共识:知识分子或“读书人”特别是教书的读书人,就应该不食人间烟火,就一定总要比别人高尚。
所以,潘先生的行为并不是因为比别人卑劣,而是因为人们包括作者对其有着更高的人格要求。如果潘先生是一个农民,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伟大的。因此说,社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制定了不公平的道德层次。一个行为并不比潘先生高尚的工农民众或者其他的什么人,也可以凭借历史和社会对知识分子预设的不公正的标准,对其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作为社会中的普通个体,潘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活得更高尚?所以,首先应该怀疑和谴责的是既定的道德规范,而不是潘先生个人。如果说他应该受到所谓虚伪的指责的话,那么也正是这种超越于人的正常需要的道德规范制造了他的虚伪。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因为人的本能欲望是不可遏止的,而被高置的道德戒律和人格风范还必须遵守,因此,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之中,知识分子身上都始终有两个“我”存在:“人”和“神”或“鬼”的较量与并存。既要满足欲望又要适应规范,于是造就了知识分子人格的分裂甚至虚伪,“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现象也就必然出现。反思传统道德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恰恰是急需的,是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分子有比别人更丰富的知识,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也有资格有权利比别人生活得更好。处于战乱中的潘先生们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