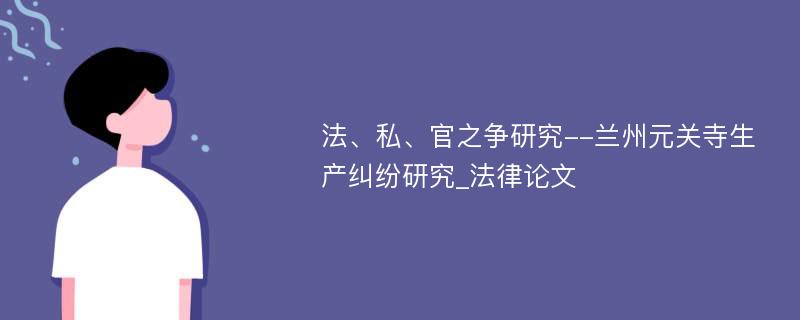
法律、私庙与官官相争:兰州朝元观庙产纷争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州论文,纷争论文,相争论文,法律论文,朝元观庙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作为私产的私庙 在近代中国,庙产纷争与庙产兴学几乎是同一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庙产兴学运动蕴涵了国家扩大财政能力以构建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庙产纷争则反映了这一国家宏伟目标与中国宗教制度的多元性、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发生抵触之后所爆发的旷日持久的社会问题,也是传统与现代激烈冲突的一个缩影。在庙产纷争中,庙产所有权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归属的变化往往能够改变庙产的性质和地位。纵观民国政府对庙产所有权的法律政策规定,可以说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 起初,袁世凯政府沿用清末传统,将庙产统一视为国家公产,以实现将之用来办理各项新政的目的。但这一政策遭到了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在1912年6月颁布保护宗教财产的命令,并在法律条文中开始认可作为“私产”的寺庙。内务部于同年10月19日,颁发了《内务部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长调查祠庙及天主耶稣教堂各表式请查照饬遵文》,这份公文将全部庙产分为官产、公产和私产三类,并强调要保护私立庙产。该公文对三类庙产的判断标准作了明确说明:“如该祠庙隶属于国家祀典者为官产,其有年代碑记无考非公非私者亦属官产,由地方公共鸠赀或布施建设者为公产,由该祠庙住守人募化及以私产建设者为私产。”①1913年的《寺院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一家或一姓独立建立之寺院,其管理及财产处分权依其习惯行之。”②这就确立了家庙、私庙的特殊地位,杜绝了激进人士对这类私庙财产的觊觎。1915年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第一条则将寺庙分为七类,其中第七类为“其他习惯上现由僧道住守之神庙以及私家独力建设不愿以寺庙论的寺庙”③。“不愿以寺庙论的寺庙”仍然暗指的是作为“私产”的私庙。北洋政府1921年5月公布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则提出:“其私家独立建设不愿以寺庙论者不适用本条例。”④1929年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制定了《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也认为寺庙属于由私人建立并管理者,不适用该条例。⑤其后,1930年司法院院字第337号解释也提出,私人出资建立并管理之庵庙,主持中断应由该庵庙所有权人派人接管,该地方官署及团体均不能干涉。之后司法院1934年9月18日第1102号解释以私人建立并管理之寺庙不适用该条例为由,认为私人建立之寺庙不应属于佛教会和道教会。⑥通过对法律条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政府的庙产法令虽然存在不断扩大公产范围从而为征用庙产大开方便之门的倾向,但难能可贵的是,它始终将由私人建立并管理之寺庙视为“私产”,并强调各级官署和社会团体不能干涉这类寺庙的经营管理,更不得擅自占用该类寺庙进行其他活动。李贵连先生在《清末民初寺庙财产权研究稿》一文中,就将民国初年的庙产性质概括为四种:国有庙、公庙、废庙和私庙。李先生认为,私庙指“私人或特定团体出资创设的寺庙。所有权属于私人或特定团体。在这里,‘私人’还包括了‘僧人’。按逻辑推理,这种由‘私人’创设的寺庙和庙产,既冠以‘寺庙’,又指明庙产为所有权之标的物,既然是‘私人’财产之一部,庙产当然也是‘私产’”⑦。 在当前学界对于近代庙产纷争的研究中,许多人都认识到了国家、社会团体乃至私人对庙产的刻意侵占。⑧虽然进入民国以后,政府的庙产政策已经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但是正如付海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国民党民法不仅在条文中做了关于保护财产权的规定,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曾被遵守。然而,与民法新秩序建立的同时,在维护新秩序或抗战的名义下,民法新秩序也公然地被破坏。”⑨因此,近代庙产纷争充分展现了各级官署、社会团体和私人之间斗争博弈的历史实态和复杂面相,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国家、政府、法律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但是,在现有研究中,大家的目光多聚焦于国有庙、公庙、废庙所产生的纠纷上,而很少人注意到国家和社会团体对私庙的侵吞。笔者认为,作为私产的私庙在形态上与真正的寺庙有所不同,它更像是游离于私置产业与寺庙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并可以根据所有者的意愿决定自己是否属于寺庙。私庙不仅不适用于民国各项庙产法律,也不接受政府的监督管理,更不能成为庙产兴学的对象。因而,相对于对国有庙、公庙和废庙的侵夺,对私庙的侵夺更具极端性,也更暴露了政府、社会团体或私人对待庙产的真实态度。本文就试以兰州水车园朝元观庙产纷争为例,分析和揭示政府、社会团体将私产私庙逐渐转化为公产寺庙的历史过程,也借以剖析三级政府之间、两地社会精英之间对于寺庙财产的明争暗斗,进而充分展现庙产纷争中的民国政治生态。 一、私产抑或庙产:水车园朝元观的性质 说起兰州水车园朝元观,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朝元观。兴隆山朝元观是西北道教祖师刘一明(号悟元子)创建的一个道观。清朝同治年间,刘一明的徒孙张复清因行医有术,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私房钱”。张复清认为这些钱财乃自己正当行医所得,不愿按照道观规定将其上交道观,遂招致兴隆山朝元观其他道众的嫉妒和排挤。无奈之下,张氏独身来到兰州市广武门外水车园一带,创办诊所悬壶济世。经营数年之后,他以个人名义购买了水车园田地33.918亩,并在该田地上修建上殿三楹,厢房六间,山门一间,仍名其为“朝元观”。⑩是为兰州水车园朝元观的创始。《水车园朝元观碑记》中有:“光绪五年四月,张复清创修道祖庙院一所”,“永为朝元观来往经理地亩人等常住”等语。(11)碑记用词相对模糊,水车园朝元观既为张复清“创修”,而张复清又特意讲明该观屋舍要用于朝元观派出人员前来管理庙院产业的人居住。那么兴隆山朝元观与水车园朝元观是否构成上下院关系呢? 1933年,司法院曾出文解释北京寺庙上下院之别,对“下院”的定义非常明确。该解释认为:“无论何种丛林,其住持以丛林公共资财购置之寺庙,名为下院”,而“丛林主持退居后,以私人资财所购置之寺庙,不为下院”。当然这里也有特例,除非“此退居主持愿以自购之寺庙归原住之寺庙管理者,亦得名为下院”(12)。在本文案例中,张复清在碑记中明言自己创修了“道祖庙院一所”,但并未明确宣称要将水车园朝元观的管理权交归兴隆山朝元观。且从实际情况来看,水车园朝元观管理权一直由张复清弟子继承。再结合后来兴隆山朝元观主持王元山、兰州白云观主持赵元善皆认为水车园朝元观为私产而非庙产的事实,可以认定,两个朝元观并不具有实际上的上下院关系。从两个朝元观名称的一致上,我们可以推测在张复清出走以后,仍以推广和传播祖师刘一明的道教思想为己任。但是,张复清并未在水车园建立道观设施,也并不承认自己的朝元观与兴隆山朝元观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只可说一脉相承。 要完全认清兰州水车园朝元观的庙产纷争,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它究竟是寺庙还是私人产业。在庙产法律中,民国政府一直都承认作为“私产”的私庙的存在。但换个角度来看,作为私产的私庙与其他寺庙已有很大区别,甚或说它既可以称为寺庙,又可以认为非寺庙而只是公民个人的私产。法律也认可寺庙的这种模糊性,并认为它们可以根据所有者的意愿决定自己是否属于寺庙。何谓寺庙呢?1913年的《寺院管理暂行规定》第一条指出:“所称寺院,以供奉神像,见于各宗教之经典者为限。寺庙神像设置多数时,以正殿主位之神像为断。”(13)这个定义直接认为寺院应供奉有神像。1929年的《监督寺庙条例》第一条对“寺庙”一词的定义是:“凡有僧道主持之宗教上建筑,不论用何名称均为寺庙。”(14)并认为寺庙属于由私人建立并管理者,不适用该条例。其后,1930年司法院《解释监督寺庙条例》第一条疑义中又称:监督寺庙条例所重者,在寺庙之财产法物(15)。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大致来讲,寺庙应包括庙宇(宗教建筑)、僧道主持和神像三个方面。根据这些定义,并结合兰州水车园朝阳观的情况,可以认为,水车园田地乃是私置产业,顶多可以算是庙产中的“私产”。 在本案中,被告人刘子乾就认为水车园朝元观属于私置产业而非寺庙。他认为:“如果是寺庙,必有凭藉的庙宇和供奉的神明。”但反观水车园朝元观,它既无会众会首之组织,又无庙宇和神位。水车园田地,系创建者张复清行医所得购置,并未有任何募化劝捐之举。除了该地仍由道士刘子乾及其徒众耕种出租外,并未有任何与宗教相关的建筑或神位。租耕水车园田地的农民马北平等人及租赁地上建筑的协盛玉、德泰和、海龙号、同兴永、德生明、魁盛祯等商号也都认为,水车园朝元观“确系私置产业,实非庙产所可比拟。既无人施舍寸土,又未劝募分文,更无庙宇□台香火”(16)。兰州水车园绅耆宋金发等人也承认,朝元观庙产“实由前清兴隆山成道刘悟元之徒孙张道人苦力续置,流传数世子孙保管,已有一百数十年之久。与民等有地者共同承粮纳草”(17)。在所有证据当中,最具有说服力的,莫过于道教界的态度。在兰州市和榆中县道教界卷入该庙产纷争之始,兰州市白云观主持赵元善,榆中兴隆山朝元观主持王元山,水车园朝元观现主持张理秀,甘肃著名士绅杨思、杨尊一、汤执权等以甘肃省宗教道德会的名义呈文给甘肃省政府,极其肯定地认为水车园田地为“私产”。他们认为,张复清虽入道门,然而以习医术济世活人为生,纯由个人理念积蓄于前清同治年间先后以自己名义置买坐落兰州水车园田地数十亩,专为每岁收益供应观内香火及道徒生活之需,且立有契约收执为凭。他们引用1933年4月5日司法院第715号解释及同年2月17日国民政府复河北省政府咨文,认定水车园田地“产权应属于个人私有,不应认为庙产”(18)。 张复清创建时的33.918亩地,经过徒儿杨永清和徒孙刘子乾的苦心经营,至庙产纷争发生之时,已至55.781亩。这块土地位于兰州市东关广武门外靠近黄河的地方,土质肥沃,规模庞大,价值不菲。据甘肃省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张登岳的调查,“水车园朝元观已登记之田地购买总价格为4740两,未登记之田地买卖价格为865两,总共5605两。其全部价值,衡以当时的地价,约值50余万元。每年收益,亦不在少数”(19)。水车园田地共租与至少16位农民耕种,地面房屋则分别租与至少7家商号,难怪时人多称水车园庙产为“兰州首富”了。(20)至该案发生时,水车园朝元观已历时百年,传至徒孙刘子乾手中,并由其经营30余年。刘子乾,甘肃通渭人,当时已届古稀之年(1942年时72岁)。虽也有徒众并保持道士装扮和信仰,但刘子乾已以种地为生,与农民并无分别。 1941年,刘子乾前往兰州土地登记处,将水车园朝元观庙产登记于刘子乾及其族侄刘兆荣名下,领取权状。经土地登记处公告数月后,并无人提出异议。因此,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刘子乾及其侄刘兆荣已经取得了朝元观庙产的产权。虽然刘子乾、水车园农民、士绅、兰州及榆中道教界都认为水车园田地应为私产而非庙产,但是纠纷发生后,榆中县政府、兰州市政府乃至甘肃省政府无一不先入为主地将其视为庙产,官方对刘子乾发难的初衷在于“庙产兴学”,其解决之道也在于“庙产兴学”,而对于水车园田地在法律意义上的产权归属问题却往往含糊其辞,漠不关心。 二、财产权之争:榆中县的发难与刘子乾的辩解 水车园朝元观既然号称“兰州首富”,自然引起了众多人的觊觎。榆中县政府及地方精英就是其中的代表。早在1935年,榆中县县长叶超就设立了山林保管委员会,希图清查兴隆山庙产以兴办公益事业,并成立有庙产兴办公益委员会。在兴隆山各庙宇中,庙产最多的即为朝元观。因此,山林保管委员会在整理庙产之初自然从朝元观着手。闻知兰州水车园朝元观与兴隆山朝元观乃一脉相承后,山林会本叶超之谕,着两山(即兴隆山、栖云山)道众推举道长前往接收水车园朝元观。两山道众先后推举了冯道、董道和胡道,但三人都不愿意接手此事。最后,董道被强行推举出来,叶超县长勒令其前往接收兰州水车园朝元观。但董道并不愿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推诿,并不成行。三名道士的推诿也从侧面反映了兴隆山朝元观并不认同榆中县政府的结论。叶超不愿再等,命人将刘子乾拘押受审,勒令交出水车园田产契约,遭到了刘子乾的拒绝。1937年,榆中山林保管委员会被裁撤,整理兴隆山庙产一事暂时搁浅。但是,榆中县政府并未因此放弃对兰州水车园朝元观庙产的追讨,又在同年专门召开县务会议,要求接管该项庙产。虽然其具体情况史料未载,但是无论如何,榆中县在20世纪30年代追讨水车园朝元观监管权的行为并未取得任何实质结果。刘子乾虽曾锒铛入狱,却并未妥协。 1941年,兰州市成立了土地登记处。但由于土地登记要收取大约每亩二分至五分之间的费用,以致布告发出以后,长时间内都无人登记。为了使土地登记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兰州市土地登记处在规则上实行了变通,将所有区长、绅士都聘请为劝导员。劝导员虽无薪给,但在劝得他人来登记时,可以提取十分之一的现金作为夫马费,每逢月底支给。这就激发了士绅们登记和劝导登记的积极性。刘子乾之前往登记并引发新一轮的诉讼,正是受到了陆华甫的“劝导”。 陆华甫是兰州鸿雪相馆的经理,鸿雪相馆则是陆华甫在刘子乾土地上修建的商铺。从法律上讲,陆华甫拥有该土地的地上权,而刘子乾拥有该土地的产权。由于劝导别人土地登记可以提取回扣,陆华甫遂积极劝导刘子乾前往登记。几番说服之下,刘子乾将水车园朝元观田地中的38.918亩,以自己名义向市政府登记,领取权状9张;又将剩余的田地以族侄刘兆荣名义登记。在刘子乾登记土地产权的同时,陆华甫也登记了其房屋的地上权。但是,陆华甫“得陇望蜀,贪图益甚”,意图完全获得他修建房屋所占土地的所有权,遭到了刘子乾的拒绝,遂引发二人的冲突。盛怒之下,陆华甫转而“串令榆中绅耆,意将完全提作校产”(21),将此事告知了友人——榆中县士绅、同时也是榆中县县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的薛上之(22)。薛氏在领命负责县立中学筹备工作之后,选定榆中县城隍庙庙院作为校址,但学校除争取了一些县拨仓粮外,并无固定经费,全靠薛氏四处奔走筹措,因此甚为拮据。闻悉该消息后,他立即萌生了将此项庙产作为兴学基金的念头。 薛上之很快致函兰州栖云学会。栖云学会是榆中县人士在兰州市成立的具有同乡会性质的诗文组织。该学会于1942年7月21日呈函给榆中县政府,公函中认为,水车园朝元观“系朝元观道士张复清于前清咸丰同治光绪诸年先后购置,备作补修栖云山庙宇及朝元观道士往来兰垣居住之业”。然而自刘子乾接管后,即霸为私产,每年收益,尽入私囊,不复为朝元观供给补修费用,致使兴隆山“山景颓败,乏资修理”。栖云学会认为,由于刘子乾的霸占行为,早在光绪年间兴隆山朝元观就与其发生诉讼,刘子乾“每讼均输”。(23)1942年8月30日,榆中县政府又收到了薛上之以县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身份写的信。薛在信中重新描述了刘子乾将所有田产登记于自己名下的过程,并认为水车园庙产历来是与兴隆山朝元观庙产一体向榆中县政府登记,所有权属于兴隆山朝元观,管理监督权则归榆中县政府。因此,薛氏提出应将水车园朝元观田地“拨充教育经费”,作为筹设榆中县初中的基金。 由于水车园朝元观位于兰州市,榆中县政府不能直接处理此事,因此将事件经过转呈给了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政府则转饬兰州市政府进行查复。兰州市政府继而委派甘肃省地政局全权调查此事。省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张登岳领命前去调查,并要求刘子乾出示登记之前的老契。但刘子乾以防空期间老契被盗为由,拒绝出示。刘子乾引用土地法的相关规定,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有权状,在法律意义上已经获得了该地的产权。 1942年9月4日,刘子乾向甘肃省地政局递交呈文,详细叙述了兰州水车园朝元观田地的由来。刘子乾指出,兰州市土地登记处章程中有“权状领得即作产权凭据,用心保存,其他契据即可作废”等语。因此,刘子乾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有权状,在法律意义上已经获得了该地的产权,不再需要老红契的佐证。他强调水车园朝元观并非庙宇,而是私置产业;水车园土地也并非庙产,而是私产。刘氏还颇为用心地从信教自由的角度提出,国家法律从未明文规定道人不得置产,更没有道人私置产业必须是庙产之理。(24)1943年初,甘肃省政府得出了水车园田地中的33.918亩应为庙产的结论,这个结论以及长年诉讼给刘子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在同年6月29日,他再次呈请甘肃省地政局,出示了水车园田地的老契,称“民之产权来源以及面积坐落与买价,均有买契,一一可按”。他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坚称,自己已经按照土地登记政策登记土地,且在公告期间并无人提出异议。刘子乾强调水车园田地是其祖师三代费尽多年血汗,陆续零星购买而来,并未向他人募化分毫或接受他人捐助。因此刘子乾认为土地所有权状和产权并无问题。同时,刘子乾提出祖师三人是自修道教,并不属于其他道观,故田地实为私置产业。他引用行政院颁布之监督寺庙条例第三条第三项的条文:“由私人建筑并管理者,不适用本条例之规定”,认为:“以此项条例论,监督尚不能,民之自置财产,更何能收为公有。倘为公共庙产,地方人士绝不容民三世主持保守而不过问,此浅显之理也。”文末刘子乾高呼:“伏思政府对人民财产,莫不合法保障,惟对民私有财产,何能如此之处置”,并指责榆中县方面为了获取教育经费而故意将水车园田地定为庙产。虽然刘子乾认为自己在法律上占理,但是面对不利的形势,他还是做出了妥协。在文中他声明自己响应国家抗战建国复兴民族的旨意,愿意出钱出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并承诺“以私有土地二十亩捐献兰州市政府(因地在兰州)专作兰州兴学之用,聊表拥戴”。(25)之后,1944年6月,刘子乾曾再次呈文甘肃省地政局对司法院的解释做出辩解,但不久即病故。 刘子乾终老后,由其徒弟张理秀接任水车园朝元观主持。刘子乾的病逝使案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司法判决结果出来之前,兰州市政府利用水车园朝元观主持更替的机会,下令由兰州市公产管理处接管水车园朝元观庙产,并提取了全部收益。面对兰州市政府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榆中县士绅表示了强烈的反对。1946年初,榆中县旅兰同乡会呈文甘肃省政府,催促尽快解决这一起纠纷。榆中县旅兰同乡会是与栖云学会类似的同乡组织,但其成员多在兰从政(26),从而增加了其言辞的分量。 水梓等人认为,兰州朝元观乃兴隆山朝元观的附属道观,“朝元观选派道人管理,历有年所,向例以其收益,除管理用费外,均送交本观充香火资费”。这一说法比栖云学会的观点显得更为详细,认为水车园朝元观的收益除正常开支外,都上交给了兴隆山朝元观。他们还认为,水车园朝元观应在兰州市政府进行庙产登记,“至于管理权问题,朝元观现有主持及道人数名,自不能认为荒废寺庙,由地方自治团体管理,亦不便由政府直接处理”。榆中旅兰同乡会主张根据1934年12月20日内政部第59号咨“寺庙在甲区而田在乙区,则其管理权属于甲区”之解释,采用“属地主义”,将水车园朝元观划归该兴隆山朝元观直接管理,以确定产权。“将来该项庙产登记确定后,拟即请由榆中县依据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组织委员会,斟酌本县需要,及朝元观经济情形,妥定出资标准,兴办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庶几以地方庙产之收益,补助地方事业之用费。宗教既得以维持,寺庙又藉以保存。”(27) 从榆中县方面来看,他们不仅认为两处朝元观是上下院关系,其关于水车园收益的言辞,也从“备作补修栖云庙宇”变为了更详细的“除管理用费外,均送交本观充香火资费”。但事实上,水车园朝元观田地规模不断扩张的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其收益并没有上交给兴隆山朝元观。用词的不断细化,正说明榆中县精英与政府一起重构了一个水车园朝元观的历史,以使自己庙产兴学的目的合法化,从而使榆中县获得监督管理水车园朝元观庙产的资格。而刘子乾的去世,使其私产主张戛然而止。兰州市政府趁虚而入,迅速接管和控制了水车园朝元观产业,使其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公产寺庙,进而将案件拖入了新的阶段。 三、从支持到反对:甘肃宗教界和兰州士绅的态度 甘肃省宗教界加入水车园田地的争夺,对于理清事件的脉络也对事件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眼看兰州水车园的庙产变成了公产,脱离了道教人员的管控,1945年12月10日兰州市白云观主持赵元善,榆中兴隆山朝元观主持王元山,水车园朝元观现主持张理秀,甘肃著名士绅杨思、杨尊一、汤执权等以甘肃省宗教道德会的名义给甘肃省政府联名上书,要求认定水车园田地为庙产而非公产。在呈文中,虽然诸人都承认张复清师承兴隆山朝元观的刘悟元子,但特别指出,“以事实而论,当系私置私有,并非庙置公有”(28)。道教界直接指明榆中县政府“官与民争”,为了设立县立初级中学,不顾法理事实,抢夺水车园田地。但是由于刘子乾逝世所造成的影响,该私产已然变成了公产,道教界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甘肃省政府还致电兰州市道教协会,就此项产业如何处置进行商议。道教界认为,自公产管理处接管该田地后,收益均被拿走,所有观内香火以及道众生活均陷停顿,无法维持银粮税款。因此,从现实的情况考虑,道教界要求发还水车园田地为庙产登记,进而维持香火,保存道教。 1946年2月11日,赵元善、张理秀、王元山等人再次呈请甘肃省政府,对事件的经过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呈文中一再强调兰州水车园朝元观与兴隆山朝元观“祖脉贯通,原属一气”。传至徒孙刘子乾“经管主权,行为悖谬”,在陆华甫的唆使下,“贪心忽炽,将其庙产大半登记于刘子乾与其侄刘兆荣私人名下”。陆华甫勾串榆中绅耆,呈请提拨朝元观庙产为榆中学校基金,“不顾理法之管辖,符合与否,隔山吃柳,似觉贪罔”。道教界这次完全认同了行政院和司法院对该田地的解释,认为确系为庙产,“无所狐疑,深感主席功德,察事神明,佩服万分”(29)。 道教界意欲将公产管理处接管的水车园田地33.918亩重新复原为庙产并发给庙产登记证的要求,由于关涉到水车园朝元观道众的生存问题,变得越发棘手。兰州市政府无法定夺,不得不再次函请甘肃省政府示下。甘肃省政府于1946年3月20日回复中称,其早已饬令榆中县政府交涉办理,而榆中县政府一直没有具报前来,又饬道教会冯理事长召集道众会商办法,但历经数月毫无结果。鉴于此,甘肃省政府令兰州市政府将该33.918亩土地恢复为庙产登记,将刘兆荣私人登记之21.863亩也归为庙产,并将所有收益一半兴办榆中教育,一半兴办公益慈善事业。(30) 兰州市水车园士绅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他们先是承认水车园田地是私置产业,却又要求将其认定为荒废寺庙,由他们组成地方自治团体接管。水车园士绅宋金发等9人于1946年2月19日呈文甘肃省政府,叙述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并将事件归因于刘子乾与榆中士绅薛上之的互相攻击。他们指出,刘子乾为了避免兴隆山和兰州白云观各处道人干涉水车园,并没有将产权转移给族侄刘兆荣经管耕种。他们批判榆中县政府和榆中士绅对刘子乾的羁押逼迫,并认为正是这场牢狱之灾使刘子乾病故。兰州士绅还批评榆中绅耆“侵越疆界无理争夺,莫非帝国主义”,认为“我兰州市与水车园不乏智谋之士”,可以将水车园田地就近提作校产,焉能让榆中士绅染指。他们引用监督寺庙条例第四条“荒废之寺庙由地方自治团体管理之”规定,要求将水车园田地由本地绅耆共同经管与办理公益慈善事业。从支持其为私产到重新认定为庙产,道教界和兰州士绅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一转变与当时的现实情况密切相关。在官方已在事实上将私产化为公产的时候,道教界力图认可公产从而保存宗教,兰州士绅也意图认可其为庙产进而阻止榆中士绅染指。 四、监管权之争:兰州市政府与榆中县政府的暗斗 张登岳领命前往榆中县政府、兴隆山及兰州市政府田管处、栖云学会、水车园等处分别进行调查,依照碑刻资料和刘子乾登记信息确定了水车园庙地的亩数、房产等。张登岳得出的调查结果认为,“水车园庙产共55,781亩,其中有33.918亩,确系庙产……惟碑文未载而已登记之田地21.863亩,其产权来源因年代湮远,移转分合,较难明了”。他认为刘子乾徒弟王海云“终日优游,不事生业,寻花问柳,秽声四闻,以多数公共庙产供一二人挥霍之用,揆诸情理,已失平允。抑与本党平均地权政策有所违背”。(31)既然是庙产,则应该用来办理公益慈善事业。因此,他提出,应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十条“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之规定,将已查明确属兴隆山所有之庙产33.918亩,收归公有,作为兴办公益事业之用。而其由该道及其族侄刘兆荣登记之21.863亩所有权来源,无法查明,拟请饬市政府警察局勒缴老契以凭核办。同时,张登岳认为兴隆山朝元观全部庙产有900余亩,水车园庙产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且兴隆山朝元观早已对水车园不置闻问。言外之意即是,即便要办慈善事业,也应该拨归兰州市,而非榆中县。于是,张登岳给出了收归公用的庙产的具体用途,“拟拨归市政府作为建筑市民住宅之用,抑作为榆中县兴办教育之用”。 张登岳的调查结果为甘肃省政府处理此事定下了基调。1943年2月16日,甘肃省政府发文要求教育厅、社会处、地政局开会审查水车园一案。审查结果认为:“水车园土地,其中33亩9分1厘8毫既经查照,确系庙产,自应依照原签处理办法办理。”但他们又认为,“惟为杜免流弊及适应兴办公益救济等事业之迫切需要起见,所有前项庙产应即收县公有,并应采‘属地主义’之原则,暂由兰州市政府接管,为建筑市民住宅之用”。而建筑市民住宅的收益,“拟以一半拨作榆中兴学经费,一半拨作其他慈善救济事业之用”。(32)甘肃省政府据此次会议报告于1943年3月20日去函榆中县政府,告知处理结果。但对于碑文未载而已登记之田地21.863亩,甘肃省政府也不知如何处理,遂呈文行政院寻求解释。 1943年5月8日,甘肃省政府收到了行政院对朝阳观水车园田地的指令。行政院认同将其中33.918亩作为庙产并提拨其财产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决定。对于刘子乾及其族侄刘兆荣以私人名义登记之土地,则要等候司法院的查核。7月14日,行政院又来函给出了司法院的解释:“监督寺庙条例上之主持在寺庙管理之不动产,通常为寺庙之财产,故此项财产属于寺庙,抑属于该主持或其亲属不明者,推定为寺庙之财产。若主张为该主持或其亲属之财产,必有确切之反证而后可。”(33)1944年6月,刘子乾对此回应到:“(反证问题)现民有土地均有老红契及权状可证,自当认为确切之反证,故民之私有土地依法不能没收充公。”(34)但之后不久,刘子乾病故,此反证也并未获得官方的认可。 甘肃省政府、兰州市政府乃至榆中县政府对水车园田地的态度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他们的初衷都是要拿这块土地的收益兴办公益慈善事业,扩充政府创建现代机构的财政能力。因此,他们在这块土地产权归属上的态度非常一致,但对其最终用途却各有打算。甘肃省政府于1946年4月23日发出了废止刘子乾登记庙产的指令,并要求以庙产资格重新登记。两个月以后,榆中县政府组织了以县长、参议会议长等为主任委员、委员的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致力于提取庙产收益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但是,在庙产登记过程中,兰州市政府遇到了新的问题。8月17日,兰州市政府再次上书甘肃省政府,提出了庙产登记中的四个疑问:“一、可否准由赵元善(兰州市白云观主持)以代理人名义依法登记?二、究应登记为榆中县兴隆山朝阳观之庙产,抑应登为兰州市水车园朝阳观庙产?三、该观财产收益原决定一半兴办榆中教育,一半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但未指明作榆中或本市办理慈善事业之用,可否明令指作兴办本市公益慈善事业之用。四、查奉令饬由榆中县政府将该寺庙产全部调查登记,克日组织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自无异议,惟此项财产远在本市,似应由本府会同该县政府合并组织,俾便共同监督其收益及分配办法。”(35)这些疑问透露出了兰州市政府的真实意图。以白云观主持赵元善为代理人登记,可以规避承认水车园朝元观属于榆中兴隆山庙产,从而使兰州市享有了正当的监管权。第三个疑问则直接提出希望排除榆中县方面的诉求,将水车园田地收益用于兴办兰州市公益慈善事业。 针对这些疑问,某人在6月24日的《据报组织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等情的指令》中,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从下笔的口吻来看,此人应为甘肃省一级的高官,很可能是地政局或社会局的局长。在指示中,此人要求,应以兰州市白云观主持赵元善为代理人登记,而不应是水车园朝元观现主持张理秀;应登记为兰州市水车园朝阳观庙产,而不便登为榆中所有;要以一半收益拨作甘肃省办理慈善救济事业之用。此人还指示,应饬令兰州市组织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他认为,兰州市庙产很多,但均为该庙道人把持滥用,“毫无正当公益慈善事业”。(36) 若以赵元善为代理人,那么赵元善代表的是兰州水车园朝阳观还是榆中兴隆山朝元观呢?兰州市政府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事实上仍是想请甘肃省政府对水车园朝元观到底应归属兰州市还是榆中县做出明确的判断。但是甘肃省政府却拒绝做出这种判断,在1946年12月24日的回复中,甘肃省政府改口说应由水车园朝元观现主持张理秀依法登记,再次规避了这一问题。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地结束。既然要将庙产收益用作榆中、兰州市乃至甘肃省政府办理慈善救济事业之用,那么三者之间如何进行分配,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分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1947年4月19日,急于从中提取收益兴办中学的榆中县政府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还巧妙地将兰州市水车园庙产的55.781亩地与兴隆山庙产的742.6亩庙产放在一起向甘肃省政府询问提取收益之标准及分配方法,希图将水车园庙产和兴隆山庙产混在一块以蒙混过关。甘肃省政府在一个月后的回复中,则更为巧妙地转移了话题,称“兴隆山各庙庙产既达七百余亩之多,迄未依法兴办公益慈善事业。依照内政部三十二年八月第二次修正公布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第7条规定,全部收益自己超过五万元,应按照百分之五十提取。盖或征收实物至应举办事业应饬分别造具详细计划及预算呈报”(37)。文中只提及了兴隆山的700余亩庙产,而绝口不提兰州水车园田地。 五、小结:化私为公背后的政治生态 就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中国的庙产征用政策无疑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在各级政府财政债台高筑、普通民众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进行国家现代化的改革,征用民间庙产自然成为各地官绅的最佳选择。从历史结果来看,大规模征用民间庙产,也确实大大缓解了各级政府改革所需的资金和场地困难,对推动中国现代化政府机构建设和新式教育事业发展,乃至社会风气的改进都有着莫大的意义。但这并不代表说,近代中国的庙产征用政策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由于对民间庙产的大规模征用,是在强权政治的主导下依靠强迫甚至暴力的手段完成的,因此不断激起了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反抗,也使庙产纷争成为一个牵扯到现代性国家的司法、行政、社会乃至思想风潮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各级现代性政府和激进士绅在对待庙产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偏向性的态度。为了更大限度地获取改革发展所需的资金和场地,他们往往武断地将所有庙产都视为公产,无视甚至公然违反民国政府制定的各项庙产法令。从兰州水车园朝元观庙产纷争的案例中,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存在偏向性态度的政府和士绅。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庙产纷争案件,从始至终都是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呈文和指令中进行的,而没有通过司法途径提起诉讼和判决。这样一个处理模式,直接影响了这起庙产纷争案件的发展走向,也是各级政府无视司法层面上庙产的财产权问题,而直接过渡到庙产收益提取分配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对水车园朝元观庙产性质的认定上,榆中县政府和兰州市政府虽都认定水车园朝元观为庙产,但二者的态度大为不同。榆中县政府认定两观之间存在上下院关系,水车园朝元观应归兴隆山朝元观,故其管理权也应归榆中县政府,其收益自然也应拨付榆中县政府支配。他们引用内务部1933年12月20日第59号咨“寺庙在甲区而田在乙区,则其管理权属于甲区”之解释,认为水车园朝元观应归兴隆山朝元观管理,榆中县政府也理所应当获得管理监督权。兰州市政府的态度则较为暧昧。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两观之间的关系,以认定水车园朝元观为庙产。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直接承认水车园朝元观是兴隆山朝元观的下院,不愿意把管理权和收益支配权拱手让给榆中县政府。因此,兰州市方面提出应采取“属地主义”原则,即水车园朝元观坐落于兰州郭外,自然应由兰州市政府管理监督,并要求排除榆中县政府的相关权益。面对榆中县政府和兰州市政府的明争暗斗,甘肃省政府的态度则摇摆不定。一方面,它努力避免对管理权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又意图将收益提取一半作为省办公益事业之需。可以说,三级政府之间各有打算,各有欲求,但其前提则是一致的,即要把作为兰州首富的水车园朝元观定为庙产,而非私产。 榆中县士绅和兰州市士绅之间的地域冲突值得我们留意,而道教界的态度转变,则更值得深思。尤其是兴隆山朝元观主持王元山在一开始承认水车园为私产,就明确否定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上下院关系。但是在官方的主导下,水车园朝元观还是从私产变成了公产。道教界在后期虽然积极介入了庙产纷争之中,但却只能应和政府的结论,在话语权上显得相当无力。 从方志来看,笔者遍翻清同治以后的兰州地方志、甘肃省地方志及各种金石资料,在对兰州道观的记载中都未提到过水车园朝元观。(38)但是,在1951年兰州市政府对兰州地区的道观、道人和有关道教团体的专门登记中,出现了“朝阳观”。资料显示该朝阳观地点在广武门外,其负责人为孙玉芳,有道士2人,房屋22间,土地55.78亩,所有财产已于1950年全数交给省人民政府行政处。(39)《兰州市志民族宗教志》在对1965年兰州道教主要宫观的统计中,也出现了朝元观。内称朝元观位于立功巷20号,属全真派系,占地68平方米,房舍4间占地47平方米。(40)从地点上看,广武门外与立功巷20号,都位于水车园南侧,地理位置与我们上文所称的朝元观符合。1951年兰州市政府统计的土地55.78亩,与民国时期的调查也吻合。这基本可以确定,在官方的主导下,至1947年5月案件结案时,兰州水车园朝元观已经从私庙变成了供政府兴学的公产寺庙。 纵观这起前后绵延数十年的诉讼,兰州水车园朝元观从可以依自己意愿认定为寺庙或非寺庙的私庙,被迫变成了为政府兴办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来源的公有寺庙。对私庙和私产的侵夺,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各级官署和社会精英对待庙产的真实态度,也从三级政府、两地士绅之间的明争暗斗中,进一步揭示了近代中国庙产纷争下的复杂社会面相和历史实态。 ①《内务部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长调查祠庙及天主耶稣教堂各表式请查照饬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第171号,上海书店、南京古旧书店、华东工学院教学服务中心等出版,1988年,第6册第541页。 ②(13)《法令全书》第9类,内务,印铸局刊行,1914年。 ③《管理寺庙条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政府公报》第1249号,上海书店、南京古旧书店、华东工学院教学服务中心等出版,1988年,第70册第441页。 ④《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99页。 ⑤(14)朱鸿达著:《大理院判决例全集:监督寺庙条例》,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1、1页。 ⑥(15)内政部总务司第二科:《内政法规汇编礼俗类》,内政部总务司第二科编印,1940年,第117—118、111页。 ⑦李贵连著:《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⑧庙产纷争一直受到学界重视,其中影响较大者有牧田谛亮著:《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索文林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李贵连:《清末民初寺庙财产权研究稿》,李贵连著:《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杜赞奇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陈仪深:《民国时期的佛教与政治》,弘誓文教基金会主办:《第四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2003年3月;陈金龙:《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佛教界(1927-1937)》,中山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付海晏:《1940年代鄂东寺庙财产权初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高万桑:《近代中国的国家与宗教:宗教政策与学术典范》,黄郁琁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4期,2006年12月;霍姆斯·维慈著:《中国佛教的复兴》,王雷泉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村田雄二郎:《孔教与淫祠——清末庙产兴学思想的一个侧面》,沟口雄三等:《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杨庆堃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⑨付海晏:《1940年代鄂东寺庙财产权初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6页。 ⑩(39)在档案资料中,存在着“朝元观”与“朝阳观”混用的现象。所有史料中,榆中县兴隆山朝元观都被记录为“朝元观”,在名称上没有疑义。但在部分史料中,兰州水车园朝元观也被记录为“朝阳观”。如在1943年甘肃省政府的各项呈文很多处都记为“朝阳观”,之后逐渐改为“朝元观”;再如在1951年兰州市政府对各庙院的统计中,也使用的是“朝阳观”一名。到底是因为资料记录的时候出现了差错,还是兴隆山朝元观与水车园朝元观之间存在名称上的分别,由于史料证据不足,我们难以进行判断。在本文中,笔者忽视了两个名称之间的差别,都将其视为“朝元观”。《甘肃省道教会所属各庙院统计表》,1951年,甘肃省人委宗教事务处档案115—1—4,甘肃省档案馆藏档。 (11)(19)(31)省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张登岳:《调查兴隆山朝元观庙产报告》,1943年2月1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8,甘肃省档案馆藏。 (12)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卷8《宗教志名迹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16)(21)水车园农民:《马北平、王笏臣、康玉芝、白子元、陈恭孝、王万和等公呈刘子乾田地确系私有的呈》,1942年7月,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8,甘肃省档案馆藏。 (17)兰州市水车园绅耆:《宋金发、崔耀亭、刘龙义、段得心、张德成、第得寿等呈朝元观庙产的呈》,1946年2月19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 (18)(28)省宗教道德会:《赵元善、王元山、张理秀、杨思、杨尊一、汤执权为发还朝元观田地的呈》,1945年12月10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 (20)榆中县士绅、山林保管委员会委员孙克发曾指出,国民军入甘后,横征暴敛,在历次“买车马捐富户”运动中,兰州东门水车园庙产都指为首富,屡次大规模纳捐。《调查兴隆山朝元观庙产报告(附件八)》,孙克发记述,1942年12月24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8,甘肃省档案馆藏。 (22)原文为薛尚之,但经考证,该薛尚之应为薛达,字上之。1938年起担任教育厅第一科科长,1942年卸任,成为榆中县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23)榆中县政府:《为转请依法收回水车园朝元观庙产拨作县立初中基金的呈》,1942年9月2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8,甘肃省档案馆藏。 (24)刘子乾:《为重视所有权状的呈》,1942年9月4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8,甘肃省档案馆藏。 (25)刘子乾:《为恳祈澈查免予没收产权的呈》,1943年6月29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9,甘肃省档案馆藏。 (26)在其成员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水梓,时任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陇右公学董事长、兰州大学特约法学教授等职;汉烜,时任榆中县参议会议长;李平之,曾任榆中县参议会议长等。 (27)水梓等人:《水梓、汉烜、谢璞、李平之、岳忠、高成名等为兰州市水车园田产的呈》,1946年1月23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 (29)兰州市白云观:《赵元善、张理秀、王元山为证明虚伪更正错误保护庙产的呈》,1946年2月11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档。 (30)甘肃省政府:《为收前接管之朝元观土地发还及刘兆荣私人登记之一并为庙产登记的训令》,1946年3月20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档。 (32)省地政局:《为奉交审查水车园土地纠纷的呈》,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9,甘肃省档案馆藏。 (33)行政院:《为水车园朝阳观庙产的训令》,1943年7月14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59,甘肃省档案馆藏。 (34)刘子乾:《为请即发还没收水车园土地的呈》,1944年6月,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 (35)兰州市政府:《为发还水车园朝阳观庙产登记的呈》,1946年8月17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 (36)甘肃省政府:《据报组织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委员会等情的指令》,1946年6月24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 (37)甘肃省政府:《据呈兴隆山庙产权益提取一半办慈善事业的指令》,1947年5月18日,甘肃省地政局档案26—1—260,甘肃省档案馆藏。 (38)笔者翻阅了光绪十八年的《重修皋兰县志》、光绪三十四年的《金县新志》、道光二十三年的《皋兰县续志》、宣统元年的《甘肃新通志》、民国二十五年的《甘肃通志稿》,其中大多详列了兰州市的诸道观,但都未提到朝元观。甚至兰州市道教协会会长袁宗善编著的《兰州道教概编》中,亦未提到这一道观。 (40)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民族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兰州市志》第42卷《民族宗教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