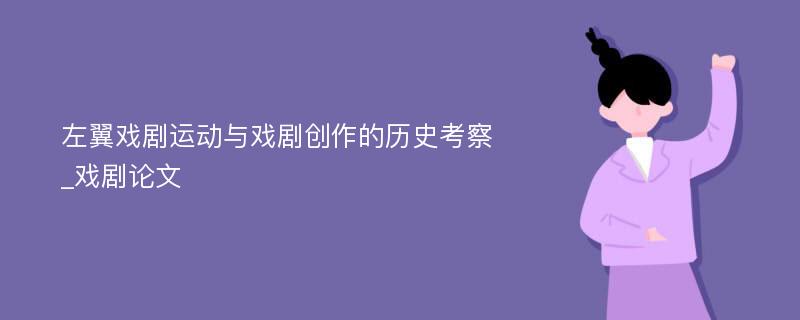
对左翼话剧运动和话剧创作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左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所说的20世纪中国话剧的“战斗精神”,最集中、最突出地体现在1928-1936年左翼话剧的发展史上,正是以它为先导,话剧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斗历程”——作为特殊的武器,与国民党战,与日本侵略者战,与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战,与“走资派”战。在某种程度上,左翼话剧在20世纪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打开研究中国话剧的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既是早期话剧反帝反封建和五四话剧张扬启蒙的历史延续,又是抗敌御侮(1937-1945)和作为阶级斗争工具(1949-1978)的历史铺垫。从现实原因来看,它的发生、发展,既与当时血与火的现实密不可分,又与世界范围内文艺界普遍高涨的左翼思潮息息相关;从历史原因来看,它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采撷西方政治学说和文化学说的理性总结和行动转向。对它的现实生存状况和艺术表现特征进行实事求是的梳理,对于正确认识话剧发展史,尽量避免失误地指导和从事当下“主旋律”戏剧创作,将不无裨益。
1930年,郑伯奇著文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轨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紧紧围绕戏剧与社会人生的关系指出:“旧剧现在一天一天加速度地崩坏下去了……跟没落的旧社会同着道儿。”原因在于,它“十足地表现着‘封建的意德沃罗基’”,形式上“幼稚拙劣”,因而,随着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侵入和新兴艺术(电影)的冲击,没落不可避免;早期话剧的“发生固然以清朝末年新兴的资产阶级为背景,可是没有力气的资产阶级开始了退却,文明戏也便堕落下去了。同时,既然没有理论,没有主义,机械地伴随发生的文明戏,到了资产阶级第二次抬头的时候,已经成了枯草化石,完全没有适应的能力了”。他就此断定:“无自觉地追随着时代后面跑的那种戏剧运动,带着堕落的危险成分更多。”“五四运动以后的戏剧运动还没有得到什么成果就逐渐消灭下去了……运动的方法也许有错误,环境不用说是十分恶劣,根本上当时的文化,已经开始了总退却,戏剧运动如何能支持单独战线。而况从事运动的人们自己就没有过斗争的意志呢?”1927-1929年的话剧运动也不甚顺利,因为“民众受着无限的压迫、掠夺、屈辱,而我们的先生苦心孤诣地给他们写‘爱之花’、‘青春之美酒’,他们能够接受吗?”通过历史回顾,他总结道:“戏剧也同其他艺术一样,不站在前进的阶级的立场上,绝对没有发展的可能。若是规避斗争,不敢站在时代的先端,那种艺术一定没落;若是跟着落后的阶级,那种艺术一定流为反动。戏剧比任何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更密切,因而表示更为明显。”鉴于此,“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是普洛列塔利亚演剧”。(1)
同年,田汉在《我们的自己批判》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戏剧应该贴近时代、贴近民众;戏剧应该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戏剧创作应该用先进的世界观作指导;戏剧应该代表下层阶级的利益。结合郑伯奇的文章来看,左翼人士所理解的“理论与主义”,即是戏剧要以无产阶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武器。
这种认识深深地烙印在次年3月通过的《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宣言草案》和9月通过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中。《草案》指出,戏剧必须跳出“唯美的圈围”,肩负“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从巍峨高矗的象牙之塔,而向着群众艺术的路线”,只有“依托着群众的推动、仰仗着集体的力量”(2)才能焕发新的生命。《纲领》要求,剧联应采取各种演出形式“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演剧运动”;剧本内容应“从日常的各种斗争中指出政治的出路——指出在半殖民地中,中国无产阶级所负的伟大使命,指示他们彻底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黄色与右倾的欺骗,拥护苏联及中国工农红军”;在城市,“剧本内容暂取暴露性的,指示出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底尖锐化的斗争过程中,中间阶级之没落底必然与其出路”;在白色恐怖下的农村,“剧本内容底共同原则是暴露在封建的剥削及与外国金融资本紧相勾结的中国商业高利贷资本底榨取之下中国小农经济底急剧的破产,指示他们彻底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扫除出一切封建残余的势力……配合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在已有革命基础的农村,“剧本主要的内容应该是宣传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的意义及拥护中苏政权与红军”。(3)
在中国共产党的有意识引导和强有力领导之下,左翼戏剧运动从以艺术观念为基础的自由组合的草创时期(上海戏剧运动协会)终于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政治信念的组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28年11月,“上海戏剧运动协会”虽然在组织上成立了,但对戏剧运动的观点和具体做法上却存在分歧,就是那份宣言,“实际上也不能作为共同的意见,仅是起草人田汉个人的论点”(4)。由于此时田汉并未“向左转”,所以他在回顾了近代欧洲戏剧运动的三个时期后,虽期待着由罗曼·罗兰所倡导的民众剧场运动(第三期),但目下切实要做的却是“为着廓清剧界的旧势力,建设坚实的新艺术,当作安托昂、勃朗一般的自由剧场运动”(第一期)(5)。就戏剧而戏剧,这与共产党员和激进的作家对戏剧的要求显然是不合拍的。1930年成立的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虽然强调“群众”和“集体”,但其组织形式依然本着艺术的目的:领导戏剧运动、联络会员之间的感情、研究中国戏剧艺术、宣扬社会的戏剧和反抗妨碍戏剧运动的恶势力。由“联合会”改组而成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和情感的联合体,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它要求盟员具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目标。但是,由于各剧团成员政治见解并不一致,时间很短,就又改组为以个人名义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至此,团结在左翼大旗下的戏剧家在政治倾向和奋斗目标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从组织上保证了戏剧运动的无产阶级方向和共产党人对戏剧创作具体而有效的领导。左翼“剧联”的领导核心是“党团”,上级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的上级是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则直接受命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剧联”的下级是剧团总组织——上海剧团联合会和上海学生剧团联合会,既有直属的基干剧团——工人剧团约8个,农民剧团1个,业余剧团约13个,大学生剧团约15个,中学生剧团约13个,儿童剧团2个,(6)又有一般联系、属于业务指导性的剧团;总盟所在地之外的其他城市还设有分盟:“最先建立的是南通分盟……第二个是南京分盟,以后是北平、武汉、广州3个分盟在当地党的指导下成立了。”(7)“剧联”的党团成员和所属剧团的负责人必须是党员且由党组织来任命:“‘剧联’属群众组织,论理非党员也可以担任部分领导工作的,但当时党团却认为领导工作都该由党员担任,郑君里不是党员,虽然当选任宣传了,却必须说服他辞职。”(8)个别人虽不是党员,但可根据其表现吸收入党(如田汉)。在严酷斗争环境中,这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能够充分发挥其强有力的政治功能,使“剧联”成为政治斗争的坚强堡垒,确保戏剧运动能够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和扩大了戏剧的力量,推动了戏剧的发展。
这种组织形式,要求盟员必须遵守铁的纪律,夏衍回忆道:“在白色恐怖下工作,保密和纪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做法实在有点过分。常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老去参加那种赤膊上阵的飞行集会?’我只能回答:‘当时上级布置的一切任务,不仅党员,甚至非党的盟员也是必须服从的。’每次运动之后,小组长和支部书记都得向上级汇报:哪些人没有参加。田汉和蒋光慈就是因为很少参加飞行集会而不止一次受过批评,乃至公开警告。”(9)赵铭彝也说:“‘剧联’成立后,首先着手的即是恢复戏剧活动,成立基干剧团大道剧社,并把盟员渗透到各剧团里去,在那些剧团里起核心作用。从南国社被封以后,上海的戏剧队伍差不多处于半停顿的状态。‘剧联’本身忙于整顿队伍,同时,当时正是‘左’倾机会主义当政时期,领导上对戏剧的特殊性质和作用重视不够,把所有文化团体几乎都包括在‘总暴动’的活动里,文艺工作者丢下他们自身的武器来经常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以及上海反帝同盟所领导的各种行动,这当然也是使戏剧活动停止的一个原因。”(10)虽然有时“不惜强制性地动员群众到指定地点举行示威,谁若不服从就绳以铁的纪律……每一次支部会都和我们的业务无关,并且每次剧烈行动总不免有同志被捕入狱”(11),但是党的指示、组织的决定必须绝对服从,换言之,在“组织”那里,“剧联”成员不仅仅是戏剧工作者,更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且能够亲自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
左翼戏剧的演出体制同样体现了它的“群众”性和“集体”性:“深入都市无产阶级的群众当中,取本联盟独立表演、辅助工友表演、或本联盟与工友联合表演三种方式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演剧运动。”(12)左翼戏剧实际活动期间,演剧活动远远不止于上述三种形式,也不仅仅局限在“工友”的范围之内,他们组织剧团既到工厂演出,也到大中学校和郊区县城演出。
工人戏剧运动——
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又相应地建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这是一个开展斗争的指挥部,是直接领导我们行动的机构。当时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发动“剧联”领导下的基干剧团,面向工人进行宣传演出;通过赤色工会,组织工人来看戏;或者,为支援工人兄弟的经济斗争举行募捐公演。此外,是组织“剧联”盟员,到工厂和工人夜校去组织蓝衣剧社,为他们编剧和导演,并组织演出。通过以上工作,结合当前斗争进行教育,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觉悟,鼓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反资本主义压迫的实际斗争。(13)
学校戏剧运动——
摩登社举行的这次“学校戏剧运动”的巡回公演,第一晚在大夏大学,第二晚在光华大学,最后一晚在交通大学……为了总结这次“学校戏剧运动”巡回公演的经验和教训,并进一步扩大“学校戏剧运动”的宣传起见,摩登社在1930年3月,通过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编辑的《中国学生》杂志第3期的“戏剧专号”,发表了一系列的探讨“学生戏剧运动”的文章……正如赵家璧在《编者的话》中所说的:“1929年,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又一段落。从这个年头起,中国的为民众之戏剧运动,由学生作了在民众与艺术间的一个过电器,展开了戏剧史上光明灿烂的一页。在北平、南京、苏杭、广东,由上海摩登社的登高一呼,各处学生都共同的奋起。”(14)
送戏剧到县城——
1933年春季,骆驼演剧队应邀到嘉定演剧……由于剧情与当前时局紧密结合,又点染了一些地方色彩,在这个直接受过日本军队蹂躏的县城里演出,很受学生、店员和市民的欢迎……大约在1935年的春天,我们还曾到上海近郊南汇县城演出过……在上海市内演出以外,那就是组织一二十人的轻骑队到近郊大场、闵行和邻近的几个县城去演了……后来我们又一次到过嘉定演戏。(15)
从理论认识、组织形式到演出实践,左翼戏剧紧紧地围绕着“理论与主义”且日渐成为其附庸——既以“理论与主义”为指导、为武器,又在一定程度上不顾甚至牺牲艺术性而极其虔诚地为“理论与主义”服务。
“理论与主义”的着重强调注重群体性的戏剧运动,必然导致紧紧围绕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和政治操作的戏剧美学形态的单一;必然导致剧作重群体、轻个体的创作倾向。从戏剧的角度而言,左翼戏剧最大的特点不单单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战斗性和革命性,因为这些,文艺的其他体式(如小说和诗歌)也能做到,问题的根本在于它美学形态的单一——正剧极度繁荣而悲剧创作相对薄弱。
由于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维护现存秩序便成为其信仰者、追随者共同的政治理想和行动指南,相生相伴的则是和谐中庸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因而,正剧始终占据中国古代戏曲美学形态的主流,悲剧很不发达。就是学术界公认的、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的作品,如果以纯正悲剧的概念及内涵来衡量的话,也有不少可商榷之处。(16)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先驱对以“瞒和骗”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旧戏大团圆结局的批判与否定和对悲剧精神的自觉建构,悲剧作品以及虽以正剧甚至喜剧面目出现的作品中的悲剧精神才得到弘扬和创造,出现了田汉、郭沫若、洪深、白薇、欧阳予倩和王独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悲剧作家,其作品如《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三个叛逆的女性》、《赵阎王》、《潘金莲》和《杨贵妃之死》等,均以悲怆、感伤的笔触抒写个体在命运难以把握时的悲剧性抗争及悲剧性结局。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末,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左翼剧作家对悲剧不感兴趣了,剧作中的悲剧精神消退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正剧的被推崇,突出的是工农大众热烈的反抗行动、坚韧的斗争意志、强烈的复仇精神和积极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不要说新进的左翼作家是如此(如冯乃超、左明、适夷、袁牧之、阿英和于伶等),就是五四时期擅长悲剧创作的田汉、欧阳予倩和洪深也同样转变了戏剧创作的美学追求:丢弃了个体灵与肉、情感生理需求与社会既成观念的悲剧性冲突,将创作的重点移位于表现群体的苦难生活、反抗斗争并在对历史必然性的暗示中透露出灿烂明天即将到来的政治信念,如《梅雨》、《回春之曲》、《同住的三家人》和《农村三部曲》等。
从五四到左翼,时间不过十几年,但中国话剧的美学形态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其中的原因与左翼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独特要求有着直接的关系:且不说后期太阳社和周扬等人将“生活”直接理解为“阶级生活”、将世界观直接等同于创作方法、以党性取代真实性的偏执,如周扬就说:“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百分之百地发挥阶级性、党派性,这样,你不但会接近真理,而且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唯一的具现者”。(17)就是坚持典型化创作方法的茅盾,也扩大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表现范围,呈现出理想化的理念色彩,1932年,他在《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这样说道:“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重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所以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18)无疑,阶级性与党性要求于文学的,首先是为阶级搏杀和党的最高目的服务,这就必须表现或预示无产阶级的光明前途、政治主张和政治运作的正确性。显然,悲剧和悲剧精神与此是相悖的——在政治家眼中,它容易引起观众对现实、对未来的悲观甚至绝望,不利于激发群体的政治激情和战斗豪情,只有正剧通过庄重、严肃的形式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才符合阶级性和党性在政治层面上的要求,这就是必须将“反映生活”作为“创造生活”的前提和出发点。其实,所谓“创造生活”的实质就是将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和向往作为理所当然的历史必然性展示给观众,以戏剧的形式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营建自身合法性的政治期待。
同时,话剧美学形态的转向也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认识上盲目乐观的“左”倾激进思想有关:正是在左翼文学时期,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先后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旨在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工农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左”倾冒进,无视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单纯强调革命的突变性,盲目地要“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9)。这便从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助长了肤浅的历史乐观主义。因而,作为一种戏剧美学形态的悲剧和作为一种美学理想的悲剧精神遭冷便在所难免。
左翼戏剧家的共同特点是,在创作方法上推崇现实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式的现实主义),浮光掠影地观照现实,以观念编造压迫(剥削)—忍耐(反抗)—斗争—胜利(或预示胜利)的故事,缺乏叩问现实的力度,更没有透过现象表面深入挖掘生活的本质进而对现实以及现实政治进行具有艺术力量的监督、质疑与批判。因此,“急就章”、“等米下锅、等薪发火”式的作品便应运而生,左翼戏剧运动期间,只有田汉的《回春之曲》和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极少数作品能够体现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绝大多数的作家(就是1930年至1934年的田汉和《赛金花》、《秋瑾传》时的夏衍也如此)在审视生活、处理生活、表现生活的方法上有大致相同的套路:大幕拉开,革命的或进步的政治力量在与反动的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虽然处于劣势,但却因其顺乎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日益壮大并取得最后的胜利;或者由于力量悬殊前者虽然暂时失败,但必定暗示出革命最终必胜的政治信念,以乐观的历史创造精神鼓动人们扮演摧毁现存政治秩序的历史主动者的角色,如《到明天》(左明)、《工场夜景》(袁殊)、《梅雨》(田汉)、《车夫之家》(欧阳予倩)、《农村三部曲》(洪深)和《阿珍》(冯乃超)等。与此密切关联的则是二元对立的戏剧结构、是非分明的戏剧冲突,非此即彼式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宣泄式的或是宣传说教式的戏剧语言。至此,“主义与理论”不但统一了剧作家的政治信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而且也“统一”了他们的艺术追求、艺术实践和艺术个性。
由于剧作家执著于戏剧的政治功利性,由于左翼文艺思潮机械地搬用与个人主义相反的集体主义意识,规定文学作品只能写“我们”,只能表现整齐划一的主义与理论,否则就被认为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自我的浪漫表现”(20)。个体让位于群体、个性让位于共性,而这里的“群体”和“共性”无疑又是“阶级”和“阶级性”的同义语,所以,左翼剧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往往只是具有单一政治信念和政治品格的阶级的代言人,只有筋骨(主义和理论)而没有血肉(个体的情感、痛苦和自我矛盾);尤其是为了塑造觉醒了的工农英雄群体,为数不少的作品只是“群像”展示,人物连名字都没有,成为单纯符号化的阶级代表,适夷的《S·O·S》中的人物是:“无线电职员王、陈、李、陆,——女职员周,胡,史,仆役,卫兵,日本兵。”田汉的《乱钟》中的人物除“女大学生黄,梁”外,剩余的十数个人物全部是用英文字母标识。
左翼剧作中的正面人物普遍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强的斗争意志和坚决的反抗行动,一切个人行为都必须统一到集团的行动之中,个人只能是也必须是集体的一员,游离于群体之外的个体既无价值更无意义。因而,原则和共性消融情感和个性就理所当然。
无论是作家个性的缺失还是作品中人物个性的共性化,对于戏剧来说,都是莫大的悲哀,因为它们的社会意义明显高于审美意义,站在美学的立场对其作实事求是的剖析与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将左翼戏剧放在产生它们的社会土壤之中进行认真细致的历史的考察,情况显然会有所不同。在血腥的阶级搏斗中,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左翼剧作家来说,抛开自己擅长的反映自己阶层的生活和情感世界而去描写不甚熟悉的工农生活与斗争,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勇气,对历史上的作家及作品作单向度的价值判断并不能代替对历史情势的艰难追寻。从审美的角度看,单纯的政治鼓动与政治宣传是有些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的因素在,理性冲淡了甚至泯灭了情感,个体让位于群体,功利超越了审美。不过,为了大众的解放和阶级政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我的创作个性在当时是普遍的、也是值得的,冒着生命的危险投身到阶级解放的洪流中以戏剧为武器呐喊搏斗,毕竟比躲在“象牙之塔”中精雕细琢来得艰难,也更令人敬重,此其一。其二,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依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此时,任何个体的哀哀切切、顾影自怜、悲愁感伤,都有可能产生离心力,有损于群体的团结和目的的一致,实际上,感伤和个人等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随时会危及群体的战斗意志和凝聚力,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就左翼阵营来说,他们首先反对的也不是“感伤”和“个人”本身,因为如果没有大多数“个人”的努力,就不会有革命的群体,他们反对的是感伤和个人的结果——极端重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泯灭群体意识。其三,作家创作个性的消退和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类型化,同样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左翼时期,由于社会矛盾的趋同性、现实斗争任务的一致性和时代号角的同一性,阶级解放是最强烈的主题,任何具有阶级意识的个人都必须为此而奋斗而努力。共产党信奉的是“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敌人”,为什么要“战胜自己”?怎样“战胜”?首先,个人的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克服私心,树立公心,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必须从群体的利益出发;其次,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铁的纪律,防止任性散漫、我行我素的自由主义作风;最后,必须无条件地压抑甚至消弭个性而服从共性,使群体成为一个具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其四,因为为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而创作,时间的紧迫和内容的应时性便在所难免,这就决定了作家们来不及对剧作进行精雕细琢,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题材和擅长的情感领域而去描写与创作主体的切身生活具有一定距离但却能反映时代呼声、斗争意识明确的“急就章”。
左翼戏剧是左翼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门,左翼戏剧的生存状况和表现特征,与左翼文学的生成机制息息相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左翼文学的参与者在众多的主义、思想中为什么要选择共产主义而走向“左翼”?其中除却现实的刺激、激发之外,是否还有更为隐蔽也更为坚韧的支撑力量?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末的部分知识文人在传统的立身(科举)与信仰(儒学)遇到双重危机时,他们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文化学说和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军事悬殊极大的国共生死较量中,他们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选择从文学领域加入到弱者的战斗序列?作为文艺家,他们为什么忍痛舍弃艺术而钟情于在作品中宣讲政治理念?
事情还要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说起。随着帝制的被推翻和精神枷锁的被打碎,20世纪初年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遭遇到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与一时不能适应的尴尬:失去了传统的出路模式(中举做官),虽然人生的出路选择更加丰富多样,但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尤其是在时局变幻莫测的兵荒马乱之中,怎样“立身”确实是个大问题;随着“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呐喊,儒家学说在文化思想界的正统统治地位被彻底摧毁,封建的伦理意识被彻底否定(至少在理论上和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信念中是如此),传统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这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深处留下了某种空白,用什么填补这种空白?怎样填补?因此,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蜂拥而至,但大都是昙花一现,生命力极其微弱。民主与科学一度领风气之先,也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出路,但在一个专制与迷信占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多年的古老国度里,它们也只能是部分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倡导,不要说专制统治者不会答应,就是没有觉悟起来的民众灵魂深处的传统惯性这一汪洋大海也会轻而易举地将其淹没。追求个性解放,对社会当然具有一定的切实冲击力量,但这同样不是解决生活出路与精神信仰的根本,再说,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个性解放是有限度的,超越了社会所能普遍容忍的限度,各方面的干涉必然随之而来,“解放”的结果只能是或者回到原有的束缚或者灭亡(鲁迅就曾深刻指出过并以《伤逝》形象地回答之)。
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来看,辛亥革命试图通过武装暴动以现代共和的国家制度取代封建专制统治,使用的武器、效法的对象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及其指导下所创建的国家体制;五四运动希冀通过文化的革故鼎新而“立人”进而强国,其武器则是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学说:以民主取代专制、以科学取代迷信、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从实际的社会实践来说,政治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之后的现实依旧黑暗、腐朽,由于军阀混战,下层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化启蒙虽然对20世纪乃至当下依然具有精神层面的影响,但对当时整体的社会生活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改造措施,国家和百姓同样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恩惠,正因此,不久就落入低潮势在必然。1927年,联合作战、协力荡平各类军阀的国共两党由于政治主张、更由于文化观念的分歧而反目成仇,用最常见的话语表述,就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人鉴于辛亥革命和五四启蒙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以武装革命对抗国民党的屠杀与围剿,一方面则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民众、唤醒民众,尽量扩大、壮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武器是已经得到实践检验、已经形成国家体制的经列宁主义改造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学说,也就是说,共产党人的革命是武装斗争(辛亥)革命和文化启蒙(五四)运动齐头并进的,只不过这里的文化启蒙带有更加浓烈的政治色彩,属于政治行动导向型的启蒙而主要不是文化心态塑造型的启蒙。怎样评说这段历史及其选择的是是非非是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事,但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胜利了,中国共产党胜利了,社会主义制度胜利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现实。事实胜于雄辩,上述胜利本身便无可辩驳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学说比辛亥革命所效法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五四运动所引进的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更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改造中国社会更有效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中的谋略、运作机制和实际操作手段要远远高于孙中山和陈独秀等人。
由于重视军事斗争而轻视文化建设,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学说只植根于个别领袖的思想与行动之中,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只是抱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信念而战;五四启蒙的人本主义学说也只局限于部分先觉知识者,即使在当时的知识界,反对的声音也很嚣杂,几年的时间,连先觉者也纷纷转向他投:陈独秀、李大钊沉浸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胡适“整理国故”去了,周作人走进了“自己的园地”,就是坚韧如鲁迅者,也不免“彷徨”,不知路在何方。事实证明,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学说,都不是解决20世纪初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
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启蒙却吸引了大批的知识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且信念坚定、至死无悔。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战胜其他学说对知识者形成巨大感召力的深层次原因究竟何在?这其中,是否与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积淀有关呢?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否比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共通之处呢?对长期接受传统文化培育熏陶的中国知识者是否更有亲和力呢?正像李泽厚所说,自从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发生了迅速的改变,首先是知识分子而后是广大百姓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原因便是“在于中国现代救亡图存即反帝反封建的紧迫的时代任务,使进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尝试错误之后,选择和接受了这种既有乐观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的改造方案,又有踏实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思想理论”(21)。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政党格局和惨烈的现实斗争中寻找答案: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镇压工农运动,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共产党则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以上农为主体的绝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因而获得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者的理解进而参与;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国际上左翼文学运动的高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的角度寻找答案:参加左翼文学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是留日学生且在日本就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干将(如后期创造社成员),或者是从苏联回国(蒋光赤),或者是受苏联文学影响、受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指引的知识者(如周扬、夏衍,甚至包括鲁迅)。然而,如果抛开现象而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来看,这些影响(不管是国内血淋淋的现实还是域外的文化文学)总要有一个使二者取得共鸣的中介,因为,在同样严酷的国内环境中,为什么有为数不少的文化人对国共两党的纷争采取中立的立场?不要说自由主义文人是如此,就是那些民主主义文人也如此,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对百姓的痛苦无动于衷,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次,如果说从日本和苏联回国的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受到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的影响的话,那么,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大部分文化人为什么却依然采取本土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如“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学衡派”同人、偏右的梁实秋等新月同人,甚至偏左的老舍和巴金等均如此。
针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巨大感召力,李泽厚曾就它与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格、文化精神(亦即文化心理结构)和实用理性是否也起了某种作用呢?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思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与许多其他一种近现代哲学理论如新实在论、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等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也许是更为亲近吧?!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结合传统,进一步中国化当非偶然插曲,而将成为历史的持续要求。相反,那些过度繁琐细密的知性哲学(如分析哲学)、极端突出的个体主义(如存在主义),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倒是相距更为遥远和陌生。”(22)
另外,共鸣源(马克思主义)与共鸣对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取得共鸣的中介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其中的群体观念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还是五四启蒙的人本主义,其中心是作为个体的“人”,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的人,主要是从人类总体出发,然后讲到个体。制造工具的‘从猿到人’的‘人’并非个体而是群体。”(23)而这,即是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民主、个体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集体转变的内在原因。
传统文化的惯性和稳定性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注重群体性、从群体中寻找个体的地位,这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理智上向往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征服部分知识者的一个方面的原因。早在20世纪初年,鲁迅将“立人”进而强国的希望寄托在“任个人而排众数”,但是,太阳社和创造社的围攻“逼迫”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从而成为左翼的精神领袖。田汉也是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文艺观点,尤其是话剧创作,注重的是“个人的感伤”,1930年他主动地发出了“集团的吼叫”,旗帜鲜明地“向左转”。其中的原因固然极其复杂(如共产党的主动争取、对国民党的绝望、左翼文学的影响等),但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却是他当时的心境:自1925年的南国影剧社开始,田汉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浪漫而有才气的“波西米亚”青年,他们一起工作,同吃同住,事业干得轰轰烈烈,生活过得浪漫多姿。然而,到了1929年,因为他迟迟不肯抛弃个人转向集团,陈白尘、左明、陈铭彝等患难与共的南国门人竟然离他而去、另立门户,并且称他为南国社的“king”,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无情地向他袭来,是坚持“自我”还是投向群体,田汉选择了后者。
虽然左翼戏剧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弱点或缺点,但我们丝毫不应怀疑参与者的真诚态度和牺牲精神,他们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与政权敌对的艺术活动;作为政党,充分利用具有群体效应的戏剧宣传共产主义、唤起民众参加到自己的集团之中也无可厚非。因此,这场由政治所导引的戏剧运动和戏剧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政治取代艺术、违背戏剧创作规律、政治意义大于戏剧意义的缺失,但它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是不容否定的。
注释:
①郑伯奇:《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艺术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16日。
②《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宣言草案》,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③(12)《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④赵铭彝:《左翼剧联成立前的几件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6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⑤田汉:《上海戏剧运动协会宣言》,《田汉全集》第1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⑥⑦⑩赵铭彝:《关于左翼戏剧家联盟》,《戏剧论丛》1957年第1辑。
⑧赵铭彝:《左翼戏剧家联盟是怎样组成的》,《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⑨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3页。
(11)凌鹤:《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及其它》,《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3)姚时晓:《“剧联”领导下的工人戏剧运动》,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14)鲁思:《关于摩登社》,《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4期。
(15)葛一虹:《回忆左翼“剧联”二三事》,《戏剧艺术论丛》1980年第3辑。
(16)参见施旭升主编:《中国现代戏剧重大现象研究·政治思维定势与中国现代话剧》,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7)周起应:《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0日。
(18)茅盾:《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10日。
(1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2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20)祝铭:《无产阶级文艺底特质》,《青海》第3期,1928年11月21日。
(21)(2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299页,第299页。
(2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标签:戏剧论文; 中国话剧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田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