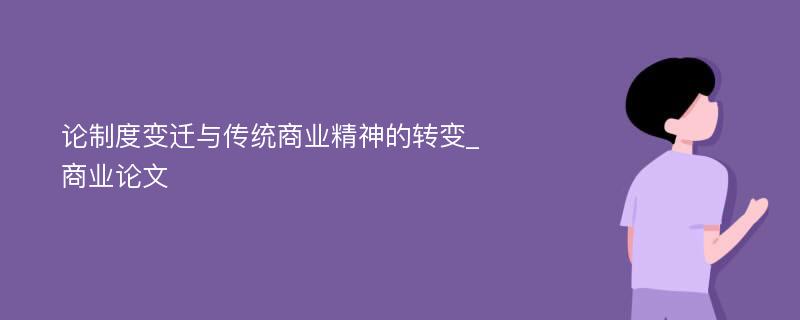
论制度变迁与传统商业精神的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制度论文,商业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制度是指制约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系列规则。它是人们在社会领域发生交换的激励机制,也是人类应付不确定性和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制度又分为正式制度约束和非正式制度约束。正式制度约束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整套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约束指人们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习俗、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制度变迁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一般说来,当一种制度安排不能以最小的交易成本为社会提供服务,变革制度安排的要求便会产生。尤其是当人们预期变迁后的制度安排下个人净收益超过现行制度安排下个人净收益时,改革的呼声会更加强烈。但由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在旧制度安排下和预期新制度安排下的收益不同,或者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会使改革难以顺利进行。尤其是当改革成本太大时,制度变迁会更加困难。本文试图对中国传统商业精神向现代商业理性转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关系作一初步探索。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总结制度变迁对中国传统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商业精神
尽管中国曾是一个以宗法伦理观念为法理基础的专制国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一直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但传统商业精神仍然艰难地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
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提出欲望论,以作为其性恶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人生而有欲”①,“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②,他认为人皆有好利与好义两面,好利是天生的,好义是后天才有的。坦率地承认人皆好利。司马迁也论证过人是天生好利求富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③,无论贤人、渔夫、隐士、猎人、医生、赌徒都为经济利益而活动。这种为利的追求是合理的,所以他不赞成董仲舒“以教化提防之”的观点,也反对国家干涉主义政策,主张“善者因之”顺应人们的求利要求。他进一步发展了《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将致富与仁义道德联系起来,认为富胜于贫。所谓“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亦足羞也”。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提出了“富无经业”,对经营方法也有论述。他注重资本积累,认为“无积聚而贫”,讲求商品质量“务完物”,强调流通领域的流畅,“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明代丘濬所著《大学衍义补》论及了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问题。他反对国家过分搜括民财,提出“生财有道,取才有义、用财有礼”⑤的原则。不但反对侵犯地主利益,也反对侵犯商人利益。主张给商人以充分自由,不赞成国家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⑥。针对明王朝禁止与私人进行海上贸易,丘濬提出开放海外贸易。虽知中国市场会给外国提供利润,但认为国家从中抽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来帮助,是亦足够用之一端。”⑦明代张居正对于封建政府常常在财政困难时加强对商人征税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农商是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⑧历史上,中国传统商业精神有时表现得很强烈,尤其是明清时期,不仅理论形式更加丰富,并且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商业活动也非常频繁兴盛。
二、制度化的官方商业思想对民间商业精神的压抑
中国传统商业精神本来是有机会转化为近代商业理性的,但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和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究其原因有二:首先由于制度化的官方商业思想的压抑。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所依赖的财政支柱主要是农业赋税,为了主权的稳定,将人们束缚在土地上比让其自由经商更容易维持统治秩序,也更节约政府的监督成本,因此,抑商作为一项政策始终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第二个原因来自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说。从整体上说,儒家具有重农抑商的伦理思想,因为它是从家庭、宗法、血缘关系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治国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商人的致富会造成贫富悬殊,商人的经商计谋则是不符合儒家公平诚信原则的。又由于儒家学说取得了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地位,一系列抑商政策的配合使民间商业精神遇到扼杀,或者是狭缝中求生存。
古代中国抑商制度以官方政策表现的形式有重农抑商、禁榷、官工、土贡、轻重等。战国时期,秦国商鞅推行农战政策,明确提出抑制打击商人。商鞅虽然承认人有好利好名之本性,认为“民之于利”,就象“水之于下”一样“四旁无择”,势所必然。但他又认为“民之所欲”万不能听任人们追求欲望的满足。要用法治、赏罚政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限制人们只从事农业生产为战争服务。在他看来“能事本而禁末者,富。”⑨他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其一“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禁止商人买粮卖食。其二“重关市之赋”,加重商人赋税负担。其三,商人要服徭役。
秦统一中国后仍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除继续对盐铁等重要商品的经济实行管制政策外,还征发商人戍边并大规模迁徒六国富商大贾于咸阳、巴蜀之地,其目的是害怕商人势力的增强而与政府对抗。两汉初,政府吸取秦王朝施暴政于民而遭毁灭的教训,在惠帝、文帝时尊崇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对商业管制有所放松,民间商业比较繁荣。但后来由于各种矛盾激化,“无为而治”政策不能应付形势变化,“轻重论”便应运而生。“轻重”作为管理经济的目标集中表现于“予之在君,夺之在君、富之在君、贫之在君”。⑩封建统治阶级要将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如通过商品专卖剥夺商人对商品的经营权,压缩、排挤、取代商人的经济势力,保持对商人和对人民的轻重之势。桑弘羊竭力推行与民争利的禁榷制度。他认为“山海之利,三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如若放于民营,则“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明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11)。禁榷的范围由盐铁矿扩展至茶叶,对私贩茶叶者甚至可以处以死刑。可以想象对商人的限度之严。
唐初改变了秦汉以来重本抑末的政策,对民间商业活动给予鼓励,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但唐后期德宗继位后又开始了对商人的抑制。如加征关津税、交易税、屡加盐赋、提高盐价、加征茶税,后来又实行酒专卖,加征铜铁矿冶税,经济呈现出凋敝状。元封建政权也对商人采取种种歧视政策。对“汉人”“南人”(南宋遗民)经商有种种限制。如江南一些地方夜间一至三点钟商人不准出门买卖,“南人”外出经商须经官府“会问邻保”取得“文引”。江南地区的铁货,铁器不准贩往长江、汉水以外,违者,严刑峻法处之。明初政府对商人也在制度上进行了限制,甚至不许商贾着绸纱,只准穿棉布。农民之家有一人为商贾也不许着绸纱,在政治上则给商人以困辱以防止农民经商。
另外,由官府所设作坊和工场生产的大量公用物品、必需品和奢侈品不通过商业经营途径直接上交政府。各地的土产品都必须无偿上贡给国家。这些不通过市场卖买过程而带有强制性的官工、土贡制度大大缩小了商品经营范围,抑制了传统商业精神的发展。
三、传统商业精神向现代商业理性的转化
从历代制度化的抑商政策和以干涉主义管理国民经济的思想可以看出,真正抑制传统商业精神弘扬发展的主要还是制度化的官方商业政策。桑弘羊在实行轻重政策时,具有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们还提出过批评。即便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取向也并非一定依赖于某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而更多决定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失。中国为什么即使在明清商品经济有明显发展的情况下也未能使制度变迁得以实现,主要还在于统治阶级不愿意失去既得的权力和利益。那些依赖于土地的权贵们是不愿意商人资本的壮大而危及自身地位的。但是,儒家学说也为封建政权提供了“法理性”的顽固基础,以致使传统商业精神无法向现代市场取向的经济伦理转化。儒家学说“内圣外王”的修身治世之道塑造了统治阶级王者即圣的专制性格;重义轻利思想抑制了人们合理追求利益的进取精神;“三纲五常”更是为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仅仅抛弃儒家学说便可进入现代社会一样,我们也无法说仅是儒家思想阻碍了传统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毕竟封建社会的制度性约束是阻碍这种转化的最主要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向纵深发展。我们认为,我国前一段改革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能实现传统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那种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形态、交换分配方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历史的继承。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安排生产,控制销售,在这样严格的制度约束下,企业和个人无法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调整经济行为。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经济效益,致使有些人偏离正规制度约束进行投机和欺骗,阻碍了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正是传统商业精神的扭曲的表现。
经济改革使传统商业精神最终以制度变迁的趋势发展,并以此为自身的理性化创造着制度环境。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个体私人企业的壮大,各种产权形式的出现,人们纷纷“下海”经商,知识分子的技术成果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一定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但也应该指出,当前的民间商业精神主要还是以非理性的形式存在的,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还相差甚远,比如有人利用制度不健全,进行机会主义甚至违法活动以实现自己的利欲满足,这是由于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滞后的矛盾所致。
我们过去的改革是从制度约束较为宽松的农村开始的。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体制内的改革形成了巨大压力。民间商业精神走向理性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我们制度变迁、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要依赖各个经济主体在以产权制度为中心的法律和秩序的建设中使其超越传统伦理观念,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在合作中促成制度化的完成。要解除儒家思想仅仅局限于价值理性的“内圣”之学给人带来的道德束缚,培养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和经世报国的有效手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实现传统商业精神向现代商业理性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个旧的制度约束曾经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进行这样的制度变迁,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注释:
①《礼记》
②《荣辱》
③④《史记·货殖列传》
⑤《制国用·经制之义》
⑥⑦《制国用·市籴之令》
⑧《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三
⑨《君臣》
⑩《管子·国畜》
(11)《盐铁论·复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