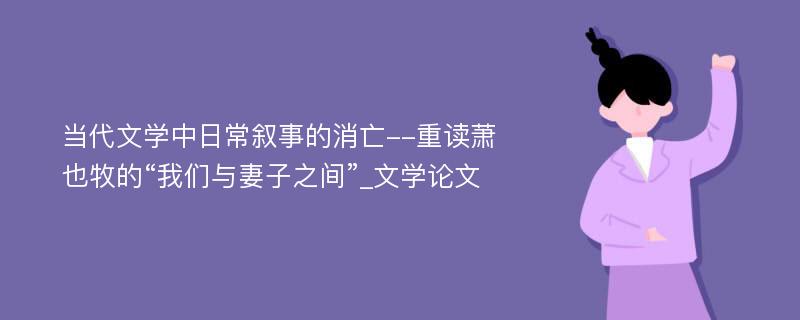
当代文学中日常性叙事的消亡——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夫妇论文,当代论文,日常论文,文学中论文,萧也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众所周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发表的小说之一,也是最早受到批判的作品之一,对它的批判,也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但到了80年代后,这篇小说又被冠以“表现新中国城市与乡村意识的冲突”的美誉,被视为解放后第一篇具有城市意味的小说。其实,批判也罢,赞许也罢,对这篇小说的内容,对它被批判的原因以及这场批判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城市题材文学的影响,似乎都未能廓清。
我们看到,在50至70年代发生于文艺界的重大批判运动中,《武训传》与《我们夫妇之间》尽管同样遭到厄运,但情形是不相同的。对于前者,批判所涉及的,是对历史真实不同阐释的合法性问题,即作者是否拥有对历史虚构的权利,因之,还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专门到山东省进行调查,其得出的结论,是“反人民反历史”、“反现实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注: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人民日报》1950年8月8日。)而《我们夫妇之间》作为表现一对国家干部夫妇之间争执、吵闹琐事的虚构作品,既不涉及历史,也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却遭受到来自冯雪峰、丁玲、陈涌、康濯等文艺界头面人物的大规模批判,批判动因究竟来自何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篇小说在发表后所受的不同反应。首先是一片赞誉之声。小说原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此后便有多家报纸转载。《光明日报》刊专文大加推崇,而且上海的昆仑影片公司立即拍成电影,甚至连萧也牧的另一篇小说《锻炼》也有人动议要拍成电影。连后来的批判者丁玲也承认,这篇小说“很获得一些称赞”,不仅是“专家”,而且“很多青年人都喜欢”。(注: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4卷8期。)在赞扬这篇小说的批评家中,有肖枫、白村等人。但自1951年6月起,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开始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其间有李定中、叶秀夫、陈涌等人的文章,也有丁玲、力扬、康濯等作家的文章。为此,《中国青年》编辑部还召开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对这场批判发表了综述(即综合稿)。至1951年10月,萧也牧不得不在《文艺报》上发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为这场批判画上了句号。
不管是赞誉也好,还是批判,对《我们夫妇之间》的评论基本上落脚于其描写的“日常生活”上。赞誉者说“所描写的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但这篇小说写出了两种思想态度的斗争和真挚的爱情”,“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注:白村:《谈“生活平谈”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批判者的论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萧也牧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间的“思想斗争”庸俗化了;二是歪曲了革命知识分子,丑化了工农干部。细究之下,便不难发现这两个方面的批判,事实上都来源于作品的日常性表现,因为“萧也牧无原则地拼凑了李克与他爱人之间的矛盾。他把二人之间政治思想上的矛盾与非政治上的矛盾等量齐观”,“集中和夸大了的描写我们女主角的日常生活的作风、习惯”,如同丑角,洋相出尽。丁玲的批判文章认为,小说暴露了萧也牧不良创作倾向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萧也牧反对的是“解放区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拥护的是“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切不好的趣味”。(注:批判文章见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4卷5期。叶秀夫《萧也牧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文艺报》4卷8期;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4卷8期。等等。)
赞誉者显然是肯定了《我们夫妇之间》的日常生活描写,其所遵循的,是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超验意义的现实主义典型观念。而批判者则从否定日常性描写出发,其内在逻辑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一类“无产阶级科学思想”根本上就不能建立于“非政治性的矛盾”这一类日常琐屑之中,因为这属于“小市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与“噱头”。假如仅仅从评论者的理论素养来说,赞誉者完全不得要领,那一套“以小见大”的所谓现实主义评论路子放在对《我们夫妇之间》的理解上根本无法说通。倒是丁玲等人的批判文章更见敏锐与功力,因为这篇小说确实没有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这一宏大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大力举荐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这是一篇取自农村日常生活的小说。在发表时的《编者按语》中说:“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编者显然肯定了《结婚》中表现出的以日常生活表现重大政治的“现实主义”道路。
由此看来,日常生活,如同“中间人物”一样,是极其敏感的。能够反映重大政治问题的日常生活是被允许的,否则就堕入“趣味”、“噱头”乃至“歪曲”的丑相。其中,最易遭致恶谥的即是城市日常生活。萧也牧遭致批判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对日常题材作出“正确的”政治判断,以致出现“丑化干部”这样的立场与倾向问题。看来,此“日常”并非彼“日常”。同样是日常题材,境遇却大不一样,关键在哪里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个概念:“日常”与“日常性”。
“日常”,指的是作品所使用的题材。而“日常性”则是作品在使用日常题材时,遵循日常立场而得到的符合日常逻辑的判断。日常性也是一种现代性,产生于现代市民社会,与英国经验主义中追求“直接的有限价值”的世俗化传统有关。在中国,这种日常性被认为是城市现代性的一种。从晚清小说开始,基于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便在城市文学中建立,经由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创作,现代城市文学中已经显示出一种传统,即以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特别是城市经验抵制乌托邦意义系统的小传统。这种传统既与左翼叙事不同,也有别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叙事。我在一篇文章中谈道,同样对待消费性,茅盾等左翼作家阐发的是阶级的意义,而海派作家则承认经济属性对于人的合理价值。对于“大众生活个人空间的世俗生活常态的体认”,使海派都有经验性乃至常识性写作的倾向。(注:张鸿声:《都市大众文化与海派文学》,《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5期。)对这一小传统,创作于1949年的《我们夫妇之间》可说是当时文坛最后一个承继者,当然,也是终结者。
那么,萧也牧是怎样对日常题材作“日常性”处理呢?
二
客观地说,《我们夫妇之间》算不上优秀的作品。小说明显具有两个系统,一是叙事系统,二是意义系统。叙事系统中,作者叙写了李克身上不同于战争时期的生活趣味,并与具有乡村背景的工农干部的妻子张同志发生冲突,也写到了张同志的改变。而意义系统则是“大道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以及这种融合在解放后城市生活中的新状态。小说的确如丁玲所说,作者“把二人之间政治思想上的矛盾与非政治上的矛盾等量齐观”,也就是说无法从非政治的日常叙事系统的琐屑、日常中推衍出“政治”上的意义,因为两个系统在作品中呈分裂状态。如果说作者是有意为之恐怕牵强,问题在于作者在处理日常题材时,呈现出与“意义”指向相反的倾向,也即作了“日常性”处理,导致作品属意于日常性意义体现而不是超验性意义体现。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常常被赋予超越经验的神圣意义。五四以来的文学,特别是左翼与解放区文学传统中,日常生活常常被赋予“本质”、“动向”等意义要求,日常题材一次又一次地被理解为追求不可见的公共意义秩序,意义系统决定了叙事。而在现代城市中的市民社会中,则肯定日常生活的“有限价值”,呈现出城市平民的世俗性与市民主义的合理性。瓦特在论述西方现代小说的兴起时,指出小说的兴起与“个人具体的生活”即“私性”成为中心有关,表达“私性”是合理的。“私性”建立于城市个体日常生活中,并不具备公共超验意义。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所谓“知识分子工农结合”是一个属于“公共”的政治话题,但却被日常题材中一再出现的“私性”叙事所颠覆。
小说第一部分以“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为题,但其所叙的李克与张同志的婚姻并无战争中革命夫妻的情义,也没有更多的爱情内涵,因为“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而只是写到男的忙于公务,而妻子则相夫养子的平静而传统的生活。进入城市后,张同志对城市充满了敌意,敌意的出发点首先来自生活方式,即看不惯女人穿皮衣、抹嘴唇,人们扰扰攘攘的。而且,她马上归之于政治与伦理层面上意义价值的诘难,即“我们要改造城市”,“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而丈夫李克则完全不把日常生活方式置于意义的拷问中。身为解放区来的干部,却从生活方式上相当习惯于城市的欲望:“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甚至还是“强烈的诱惑”。如果按照通行的左翼写作模式,大可以化为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干部受资产阶级腐蚀的宏大主题,但萧也牧并未让这个情节基础升华。小说并不把李克的物质欲望与消费引申为阶级意义或道德意义,其与妻子的冲突,仅仅作为家务事处理,不断降低为夫妻间因习惯不同而争吵的常识空间。张同志的工农感情也不断被降低到“私性”的地步。比如报纸上刊载冀中大水灾,张同志听说后只是在地图上寻找自己家乡,将丈夫的稿费不经同意便汇给了自己家等等。以日常题材展开,却又以“日常性”为结,这便是丁玲所说“丑化工农干部”的含义。
我们看到,作品中原本对张同志言行在公共空间的意义阐释,是一个不断消失的过程。李克与张同志的矛盾冲突逐渐消弥,但其方式却是张同志相当程度上的容忍,认同了城市日常生活方式。作品中虽然不断描叙两人的争吵,而且一再提到李克对妻子朴素、热情、奉献精神的感动,但读者感受到的却是李克明显的精神优势。这便是丁玲提到的小说的“虚伪”之处。结尾处,李克对妻子一番含义暧昧不清的宣叙,貌似赞扬,实则批评,而妻子则“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妻子张同志的工农道德优势全然瓦解。最有细节表现力的是结尾一段,张同志在听完了丈夫的说教后,缩回到妻子的日常义务之中,她推开了想要吻她的丈夫,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啊!”小说在叙事中不仅没有导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冲突结合的意义,也没有导出城市与乡村生活冲突的意义,而是径直从可能的意义阐发中退回了日常性。这样一个与左翼解放区文学相反的运动过程,当然是批判者不能容忍的。
要弄清张同志认同城市方式的内容,先要看一下李克。李克身上的市民主义合理生活的“有限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消费的欲求(如上饭馆吃饭并不太计较价格);二是“公”与“私”的分离(个体价值应当被承认,稿费既然为自己所得,理应由自己支配);三是组织化观念(社会问题,比如掌柜打小孩要纳入到组织化形式中解决)。其核心是阶级立场上的公共道德与个体私性的分离。
再看张同志。初入城市的张同志,其价值体系原本建立于“公共”的道德意义之上。从外在形态看,是对于城市生活的仇视,其内核,则在于乡村伦理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道德立场。她看不惯城市的享乐、消费生活,原因是:“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或者是:“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作为干部,她的工作方式原本具有建立于道德价值系统的非职业化与伦理化。比如对于打人的胖掌柜厉声呵斥,其实这事本不属于她的工作范围。为此,作者专门在这一部分中插入她对有钱人憎恨的出身基础的介绍。但渐渐地,伦理性在她的工作当中慢慢变成了职业特性,并化为一组中性的社会化原则。她担任女工工作。“在那些女工里边,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也有不少脑袋像个‘草鸡窝’的……可是她和她们很能接近,已经变得很亲近……”同样是训斥掌柜,但第二次却引起了她的自我检讨:“工作方式太简单,亲自和掌柜吵架,对学徒也没好处,有点‘包办代替’,群众影响也不好!”这中间不独有处理人际的非伦理性,也有几分久居城市的世故与老练。
关于组织社会,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组织社会,“经济生产借助合理核算的企业家而成为资本主义式的,官方的管理借助有法律教养的专业官员而成为官僚主义化的,这样,这两样活动就按企业形式或机关形式组织起来。”韩毓海对此解释说:“人的社会成为一个客观化的自我控制的系统,它像机器一样自行运转,因而人类普遍价值和主观情感很难对它进行干涉。当然它也不是将人类普遍价值完全排斥掉,而是对其筛选后,将它消解为一系列的客观化的社会功能。这样,人类普遍价值就被客观化、工具化、功能化,或者说是‘形式化’。”(注: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9页。)张同志作为一个新政府的管理者,她的工作方式,有一条通过将农民式的爱与憎逐渐“客观化”的过程,逐渐具有的教养与城市经验使她职业性起来。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关于阶级、道德的普泛已经被日常性城市生活完全取消。作为左翼作家,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品,不太可能全然无视解放区文学的传统。比如张同志接受女工的过程,仍然被置于“解放她们”的需要;向小保姆道歉,也同样是检讨自己“小看穷人”的道德水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作者笔下,关于阶级、国家的宏大理论与“鸡毛蒜皮”的日常性相连,两者的结合最终构成了一种普泛的国民人格与精神文明问题,从而与阶级、道德等问题剥离开来。张同志最终被城市的组织化生活塑就成了一个新国民,逐渐具有尊重他人、讲究体面的人格形态,打上了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烙印。比如,原本土气十足的她买了一双旧皮鞋,每逢集会、游行便穿上,回家又赶忙脱下。工作与闲暇的分离不仅保障了她的国民义务,同时又兼顾了其作为农民出身、反对过多消费的旧式伦理,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被分离开来。同时,农民习性被极大地克服。小说中张同志的一番道理颇能代表民族国家精神建立中的日常性基础。
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面走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
衣着也好,生活习性也好,在日常的层面被工具化了,而不是像先前那样被伦理化、意义化。
正因此,李克与张同志的矛盾冲突,最终没有上升为意义冲突。李克仍然对城市生活方式抱有相当的热情,张同志也许并没有完全成为城市人,但她的存在,已经不构成对“干部进城腐化”或“城市乡村”冲突的意义判别。就像结尾两人谈话后张同志说的:“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像今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啊!”两人的不同之处也许依然存在,也不能造成爱情,但作品将一切都化为了一夫一妻小家庭严格的市民伦理,即相互体贴、忍让,重大政治伦理终于降至日常性工具层面,并最终得以解决。
三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表与被批判,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萧也牧被认为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中国城市生活并尝试以城市题材创作的作家。有论者认为,萧也牧“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注: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它的被批判表明“进入城市的革命者和左翼文学家对于城市,也对于产生于都市‘旧小说’的深刻疑惧。”(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想,仅仅从城市题材方面去理解《我们夫妇之间》是不够的。尽管解放区文学传统对表现城市的确存在着某种禁忌,但事实上,城市题材在整个50至70年代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由于表现了作为“领导阶级”的产业工人的生活,一时间,城市“工业题材”的创作还蔚然成风。不过,它们大都被化为“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模式。这不仅在周立波、雷加、罗丹、草明、艾芜的长篇小说中大量存在,甚至于也是经常表现日常城市生活的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人的创作模式。由此看来,城市题材固然与乡土题材文学存有等级差而受到抑制,但这种抑制,从根本上来说,还不仅是题材问题,更重要的,是题材本身表现出的是重大政治问题,还是日常性问题。
《我们夫妇之间》的被批判也可看作是一次标志性的事情,它意味着新中国当代文学对城市日常性叙事的一次清除。我们还是回到丁玲对萧也牧的批判文字中。丁玲说:“这篇小说正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是一种什么趣味呢?“就是他们喜欢把一切严肃的问题都给它趣味化,一切严肃的、政治的、思想的问题,都被他们在轻轻松松嘻皮笑脸中取消了。”(注: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4卷8期。)以丁玲的敏锐,已经察觉出对日常生活是进行超验性的意义挖掘还是仅仅以日常性来处理是问题的核心。陈涌也认为,“作者在这些地方是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因为“写了她经常为了日常的琐事而争吵,而且这后一方面在这作品也是占了主要地位”。
我们看到,上述批判者所指涉的种种情形在《我们夫妇之间》中的确存在,只不过当时的批判者与我们今天的评论者在价值取向上已经发生位移。这篇小说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中的异数,原因即在于,它第一次在当代文坛上显示出日常性与左翼文学中革命主题的分离,表明了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个人性“私人空间”存在的可能,也就表明了城市日常性所包含的合理性。因而,作品中的城市生活没有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构成想象关系,对抹口红、烫头发、爵士乐、高楼大厦等后来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生活符码的东西也一概给予容许,并以“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作了非阶级、非伦理的评断。在日常逻辑的层面上,城市生活中的城乡意识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也并不被想象成你死我活,至多是在某种国家想象中构成和谐,城市资产阶级传统竟与“大国家”的国民精神统一起来。这无疑是在文学中留给了日常性一定位置,虽然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个人趣味,但它无疑构成了对解放区文学传统的某种抵制。这是相当“可怕”的,也是当时文坛对其进行围剿的主要原因。
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连同早此一年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以及此后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城市日常性被杜绝。此后的城市题材作品,都以从日常生活洞悉政治思想问题为模式,将日常性中的私人生活领域归之于社会公共性的敌人,也即有日常生活,但没有了“日常性”。《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还有“文革”时期的《海港》,都将生活方式在阶级的意义上展开,在公共空间(时间)与私人空间(时间)架构起意义的连续性。人物的物欲、闲暇(即八小时以外)都被取消,人物的行为也不再职业化,人际构成政治伦理关系,甚至包括家庭,都在公共性的意义上建立起生活的道德化性质。诚如丛深在《〈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一文中说的,他原本所拟定的是“批判习惯势力”的主题,但通过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现了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来分析工厂日常生活”的方法。诸如丢掉布袜子(《霓虹灯下的哨兵》)、工作分配在城市(《年青的一代》)、下班后打野鸭子(《千万不要忘记》)、下班后看电影、调动工作(《海港》)、不戴老式帽子(《家庭问题》)等等,都成为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符号,在非日常逻辑上展开。城市生活的日常性,从此退出文学。这种情形,甚至持续到80年代,直至80年代初才有了扭转。这便是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所标志的当代文学的意义。
标签:文学论文; 我们夫妇之间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丁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