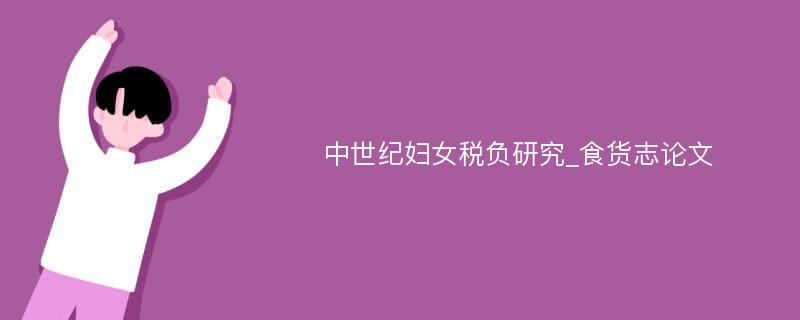
中古时代女性赋税负担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税论文,中古论文,负担论文,女性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9)05-0112-06
一、背景与概念: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宋元以降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变迁的影响,对女性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知识界一直持低估的态度①。女性的形象和地位成了中国形象和地位的隐喻,在中西方知识界的描述中,她们是受压迫的和待解放的(当然,这也是部分事实)。即使较开明的人士如梁启超也认为,女性之大半是属于社会的“分利”者,而不是生利者②。
而这一观点又为紧接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五四史观”所强化③。高彦颐最早提出“五四妇女史观”的问题④,她认为“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序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要“消除这种非历史的偏见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中国女性历史研究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女性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最重要的是,女性历史必须被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1]。
当然,现代知识界对女性史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致,胡适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共五讲,一讲提及中国传统女性,其中指出传统中国女性地位并非想象之低[2]。此外,还有费孝通,他在《江村经济》中讲,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江南产丝地区,“从丝业得到的收入可与农业收入比拟”[3]。可见,当时女性在家庭经济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这种观点被湮没在以革命史为核心的历史撰述之中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女性史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深入,对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的探讨进入相关学者的视野。
白馥兰在《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中指出了纺织(妇工)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象征性意义,女性生产的布帛在中国社会不仅有其金钱价值,而且还有社会(嫁妆、德性)、政治(丧服、人兽区别)功能;并认为,在宋代至清代纺织业向商业化、扩大化和专门化的转变进程中,女性的贡献被边缘化。“在宋末以前,除了很小比例之外,所有的纺织品是农家和地主庄园家里的妇女织造的简朴织物,不仅劳动力是女性,乡村纺织品生产整个是一个女性的领域,其中,技术知识,连同生产责任都由女性控制、管理,而且,尽管女性生产的大部分织物是简朴的,但它们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具有被认可的很高的价值:可用作赋税,纱线和绢又是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农民家和庄园家庭里的女性制造了大批用于日常穿着的低价布料,以及流通中的高价布料的主要部分。”[4]
曼素恩在《缀珍录》一书中指出,盛清时代儒家主流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女性从事生产(女红)的提倡,也提及了女性所从事的家庭纺织业的金钱价值和赋税价值[5]。
以上均为宋元以后的研究,而本文则欲以中古时代的女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生产对国家赋税的贡献比重。本文中的中古,略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基本上相当于西方汉学界所指的早期帝制中国阶段。之所以选择中古时代,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的典型性。自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赋税制度出现“调”的概念,即以户为单位,缴纳一定的绢或布等纺织品;唐代又出现以织物代役的“庸”,庸同样也是以人头为单位。唐中期两税法以后,中国赋税制度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由税人转为税地;逐渐以财产税取代人头税,以金属货币取代劳役或实物税,因此,一个家庭中男女的赋税负担水平难以匡算。而中古时代则不然。古代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存在性别分工,即一般而言的“男耕女织”;这样,在有“调”、“庸”的情况下,更易于计算男女的赋税负担。“男耕”当然也包括纺织作物的“耕”,而女性有时也是参与大田劳动的;但基本而言,桑蚕则是以女性劳动为主的。
在古代中国,纺织品的价格往往高于粮食的价格,在战乱或经济衰退时,纺织品往往还起着通货的作用,成为商品的等价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纺织品的作用。然而作为国家赋税主要组成部分,纺织品和粮食的比重到底如何?尚有待于仔细的考析。比较中古时代纺织品和粮食在国家赋税体系中的比重,则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在中古时期,没有专门的物价记载,我们不得不从传世的文献以及考古的材料中进行仔细的爬梳,择出能反映当时物价的资料来,可以想象,这些记载是极不完整的。其次,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物价是变动不居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变化还非常剧烈;粮价尤其如此。同时,影响粮价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气候变化、天灾、战乱等;另外,物价也有地域性,不同地区的物价有高下之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纺织品和粮食的价格进行比较,并不能得出绝对准确的结论,而只能是相对准确的估计。为了使结论更为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我们采用估算的办法,一般不会给出确定的值,而是估出这个值的上限和下限或平均数。
最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各地的物价不同,而我们择出的物价资料又是随机的,那么姑且忽略地域差异,以材料所见物价权作全国的平均值。
以上是本文对相关概念以及思路所做的界定和说明,以下即对三国以至唐前期女性对赋税贡献的数额进行估算。
二、中古时代女性赋税负担的估算
据童书业先生根据《九章算术》的记载研究,汉初,一斤生丝的价值在240钱至345钱之间;一匹绢的价值(如果按照赋税标准则以斤计量)在512钱或者比低质量的生丝高两倍多。麻布的价值每匹只有125钱。在汉代,田租之外,算赋、口算、更赋均征钱,以人头计,算赋120钱,口赋23钱,更赋300钱。如此,西汉初年,女性生产一斤生丝就可以承担一个成年人人头税的一倍,另外,她们还以生产的纺织品赚取的收入补贴家用[4]。因此,汉代的女性所创造的价值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较高的。
东汉时期,由于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发展,导致商业萎缩,货币的功能降低,以物易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加之社会动乱不息,谷、帛逐渐取代了金属货币的功能。毋庸置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生产的重要性。
(1)三国时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收户调,始于东汉建安六年(204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发”。三国时期,战乱不止,粮食紧缺,史书动辄记载“米斛万钱”,当然这并非是确指米价,而只是指言米价腾贵而已。那么,这一时期粮与绢的比价是多少呢?汉晋之际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云:“今有买绢一匹,直粟三斛五斗七升”。如此算来,即使按西晋时的赋税制度,一个家庭每丁课田五十亩,按每户百亩计,则三国时期女性的赋税负担高出近男性一倍,这还没有算进二斤绵的价值。
史书无载绵的价格,根据《宋书·沈怀文传》:“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钱,绵一两亦三四百”,大概绵一两价相当于绢一匹1/7左右,那么绵二斤的价值大约与米8斛同,则女性赋税负担高出男性3倍有余。
(2)西晋时期
西晋实行占田制及课田制。《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
又按《初学记》卷二七《绢第九》:“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如此,则合亩收8升,较曹魏高出一倍。
按王仲荦先生《金泥玉屑丛考》估算,西晋绢价一匹在二千至三千间;而谷价一斛则在二千左右[6]。西晋田租亩收8升,五十亩则400升,合钱8 000;如果绢一匹以2 500计,则三匹合钱7 500,三斤绵价合1万7千余钱。这样,女性负担高出男性3倍。
(3)东晋南朝时期
东晋南迁,赋税制度基本袭西晋之旧。成帝咸和五年(330年),按《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东晋度田收租,按亩收税,南朝宋、齐承之。
在户调制方面,东晋、南朝宋、齐仍沿袭西晋,只是在征收上采用九品混通,按户等高低增减。
而根据王仲荦先生《金泥玉屑丛考》搜寻的资料,东晋的粮价和布帛价在元兴初(400年左右)为“米斛五百”,义熙八年(412年)“米千钱三斛”;南渡之初(317年左右),布一匹折千文,米一斛六十,太元中(376-396年)布匹折千钱,义熙四年(408年)亦然,晋后期布帛多为千钱。这样看来,东晋一朝粮价变化很大,低至一斛六十,而高则“谷石数万”、“米斗值五百”。这是粮价极端时期的价格,估计东晋正常粮价大约仍如西晋,以一斛2 000钱为常;而布帛价也与西晋时期相比变化不大。
这样,东晋按田收税,如果仍如西晋一家以百亩计,收3斛,合6 000钱;不计九品混通,以绢三匹计,则只需7 500钱,绵价三斤合计17000钱。如此,女性赋税负担高出男性4倍有余。
根据《金泥玉屑丛考》,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东土大旱,“米一斗将百钱”,“甚者米一升数百”;泰始二年(466年),“建康米贵,斗至数百”;同年,荆州米“一升一百”。南齐昇明二年(478年),荆州米贱,“优评斛一百”,甚至“斛值数十”。这都是灾荒时期的特殊现象,南朝宋的粮食产量应该比东晋时期要高,除了满足本地的需求之外,还有大量粮食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情况⑤。整个南朝,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新农田的大量开辟[7],粮价的总体趋势应该是不断降低的,所以,综合考虑,南朝宋的米价大约在每斛百钱左右。
再看绢价的情况,宋大明年间,“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钱,绵一两亦三四百”,而在平时,如永初时,大约“官布一匹,直钱一千,民间所输,听为九百”;元嘉时“私赋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南齐时,“斛直数十,匹裁三百”。所以,这一时期绢布价大约在500钱左右。
这样,同样以户有田百亩计,田收三斛,则合钱300;绢则合1 500钱;绵仍按七分之一计,约合钱3 500。如此,女性赋税负担高出男性16倍之多⑥。
至南朝梁、陈,租调制度开始发生变化。《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岁已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以嫁者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为丁……其田,亩税米二斗。”
则对丁男而言,其赋税负担为:绢布共1匹,计500钱,绵3两2分,计1 120钱;米14斛,计1 400钱;合计3 020钱。丁女半之,即减半。那么,女性的赋税负担为1600钱,不计丝三两的价值,高出男性200钱。
(4)北魏和北齐时期
北魏实行均田制后,《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载:“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按《魏书·食货志》:天兴(398-404年)中,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另:天安皇兴间(466-470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另:太和九年(495年),诏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匹为钱二百。又永安二年(529年),绢匹止绢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
《张丘建算经》(约成书于北朝后期)载:“丝一斤八两,直绢一匹。今持丝一斤,裨钱五十,得绢三丈。”
另《魏书·杨椿传》载:“米斗几直一千”;《隋书·食货志》载:“谷斛至九钱”。
另按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搜寻的资料,粟帛的比价计有:匹布折二斛五斗粟;匹绢五百文;匹帛折二斛五斗、二斛、六斛,十五匹合一千文,三匹合米十石;匹布六百文,另有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
如此,北魏绢布价约300钱;米价当在百钱左右。这样,一夫一妇的总赋税分担为:帛负担300钱;粟负担200钱。女性赋税负担高出男性100钱。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重颁均田令,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而北周则:“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
按王《金泥玉屑丛考》:北齐匹帛折五斛;北周匹布六百钱,斛谷百文。
北齐之时,粮食的负担增加了5斗(0.5斛),而丝织品也增加了绵八两,女性的赋税负担较北魏是有增无减。
(5)唐前期
唐前期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根据《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
绢布价资料如下:
《资治通鉴》武德四年(621年):唐兵围洛阳,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一匹直盐一斗。
《贞观政要·政体篇》载:一匹绢才一斗米。
《新唐书·食货志》载:贞观初,绢一匹易一斗。
《新唐书·马周传》载:贞观五六年(631-632年)一匹绢,粟数十斛。
《通典·食货典》载:开元四十三年(725年),斗米至十三文,青齐斗谷至五文,绢二百十文。
《唐会要》载:开元十六年(728年),李林甫奏请:绢每匹五百五十文为限。
《资治通鉴》等书的资料都是非常时期的物价,则取《唐会要》载李林甫所奏为宜,绢布匹价500钱。
而关于粮价,根据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卷四《唐五代物价考》所择粮价史料:丰年一般斗米四五钱,荒年米斗三四百。⑦正常年份的资料难求,如果丰、荒年粮价较平时均以波动10倍计,则米斗取约50钱为宜。
那么,粟2石,即4斛,亦即40斗,计200钱;丝织品6丈,计750钱,布价约与此等;绵三两,麻三斤,价无考,不计。则女性赋税负担高出男性4倍,且过之。如果再加上“庸”,一月按30日计,共9丈,二匹有奇,共计1000钱有余。这样女性赋税负担比重会更高。
总之,从上述的估算看,一般而言,在中古时代,女性的赋税负担为男性的3-4倍。
三、余论
如前所述,唐朝中期实行两税法以后,对男女的赋税负担更难估算。但是,我们确知的是,宋代女性在纺织领域中的作用未必减弱。因为,由于宋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纺织品的需求量增大;再者,由于纺织技术的革新,如出现脚踏缫丝车(需要5人一组接受操作两架缫丝车),一般家庭虽然没有能力提供劳力和资金来从事生产,而政府则开始组织官营的工场,富人也开始开办私营工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纺织品需求,于是大量的女性被雇佣,她们创造财富的市值仍大于家庭中单纯从事农耕的男性,这“不但增加了她们的收入,也把她们从家庭的小社会吸引进一个开放的大社会里”[8],不仅开阔了眼界,也提高了她们的财产权⑧。程民生先生认为,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女性实有力焉,不少南方家庭中,妻子是经济支柱,从而形成男主内女主外的情况⑨。
然而,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到了明代,随着生产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纺织业手工工场的规模和劳动强度亦加大,并出现踹匠、染匠等工种,为提高劳动效率,手工工场开始大量使用男性劳动者。女性以前在纺织品生产领域中的全程参与、管理的地位丧失,她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采棉、纺线、采桑、养蚕、缫丝、纺纱,只处于散作生产体制中的辅助位置,报酬最低,技术含量也最小。而且,在元明以后,由于“礼教”的规训作用,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动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也是男性开始进入纺织生产领域的原因之一⑩。这种变化,到了明代中后期以后,趋势更为明显(11)。
那么,女性对政府赋税贡献的大小变化,是否关涉其社会地位呢?女性社会地位即女性“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机会及其从社会得到的认可程度”;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主要由法律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教育地位和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等几个要素组成[9]。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分配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平等;男女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平等。”[10]这四方面的平等同时也就涵盖了上述五个要素。如此,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经济地位是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标识。
从整个的历史发展看,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提升了她们的社会地位,这从汉唐女性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是,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对应关系也并非是直接对应的,如前所揭示的,中古时代,女性的赋税负担一般高出男性3至4倍或以上,但其社会地位绝没有超出男性,言其地位高,只是相对于前后时代,尤其是相对于女性自身地位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高低变化而言。之所以如此,我们只能从古代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入手,找出个中的原因来。那么最明显地,是父权制的影响,是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吞噬了女性在经济生产中的成果,使男性的地位仍远高于女性之上;而女性地位的降低,又反过来加强了父权制的权威。这样,整体考量历史时期女性的地位问题,就会涉及到“礼教”的文化建构和制度的政治建构。
然而,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及其与社会制度和礼教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论题,非本文所能遽然解决,本文只是提出一个视角和思路,以图为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研究提供前期资料。
注释:
①白馥兰(Francesca Bray)提到,研究晚清经济和手工业的学者,将近代中国纺织品生产中的劳动力变化描写为“纺织业的女性化”,殊不知,女性曾制造过全中国所有的纺织品。见其著《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②梁启超说:“中国妇女,则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仅十三四,何以言之?凡人当尽其才,妇人之能力,虽有劣于男子之点,亦有优于男子之点。诚使能发挥而利用之,则其于人群生计,增益实巨。”见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8页。
③“五四史观”在20世纪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新文化运动承担着“反封建”的任务,为了给改良或革命寻求“合法性”,新文化运动把元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特征扩展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并强化了其专制、落后的一面,从而为新的社会改良或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和文化动员。革命成功以后,这种思路进入主流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体系,最终成为“历史的常识”。
④曼素恩(Susan Mann)也提到这样的观点,见其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⑤《宋书》卷82《周朗传》载:“自淮以北,万匹为货;从江而南,千斛为货。”可证。
⑥对比上下文的所估算出来的数值,这一时期男女赋税负担的比重是相当夸张的,不能否认粮食和绢布价格可能会估算错误,而问题极有可能会出在粮价上;但是为了保持本文估算原则、方式的前后一致,本文仍取这一可能是失真的数值。
⑦参见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卷四《唐五代物价考》,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3—189页。王仲荦先生书卷六为《唐西陲物价考》,多取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吐鲁番地处唐代边疆地区,不足以代表整个唐代的物价水平,因此本文暂不取其中资料。
⑧很多研究者认为,宋代女性有较高的财产权,几成定论。相关成果有袁俐《宋代女性财产权述论》(载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所编《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即《探索》1988年增刊),柳田节子:《南宋期の家产分割にぉける女承分について》(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社,1989)和《宋代女子の财产权》(《法政史学》第42期),永田三枝《南宋期における女性の财产权について》(《北大史学》第31期),游惠远《宋代民妇的角色与地位》(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8)等。与此相关的宋代女性地位研究的总结,可参阅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⑨程民生在《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第一章“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中叙述了北方和南方风俗的特点及概况,并由此指出了南方女性在经济中的地位。
⑩实际上,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宋代以后,中国女性“缠足”日益普遍,大多数女性由于畸形的脚已不便上机纺织。
(11)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研究宋代女性的婚姻时,已注意到了这种从宋代既已开始的女性地位总体状况的变化,详见《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第十五章“关于妇女、婚姻和变化的思考”。
标签:食货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