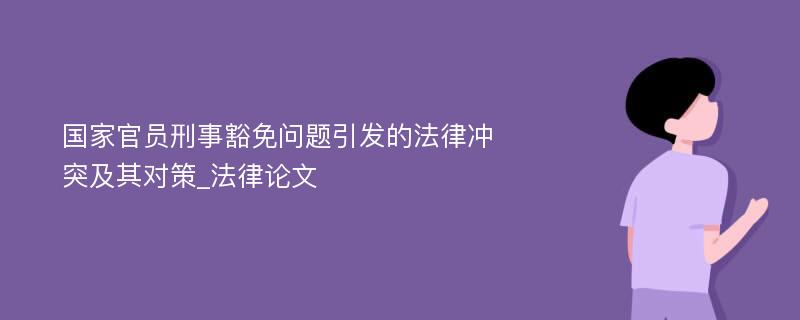
国家官员刑事豁免问题引起的法律冲突及解决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员论文,途径论文,冲突论文,法律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815(2008)05-0083-06
一、初步问题
1.问题由来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于2008年7月14日决定以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以及战争罪等共计十项罪名起诉苏丹现任总统奥马·哈桑·艾哈迈德·艾尔·巴希尔(Omar Hassan Ahmad Al Bashir,以下简称“巴希尔”)。①这一举动再次引起学者对国际刑法领域一个热点问题——国家官员刑事豁免权引起的法律冲突问题的讨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2007年7月20日决定,将国家官员的豁免问题(Immunity of State Officials)列入其编纂习惯法规则的计划之中。②这一简单的事实说明国家官员就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国际罪受到起诉时豁免问题的复杂性。
本文讨论的法律冲突,是国家官员的豁免特权与国际刑法上“与官职无关”(Irrelevance of Official Capacity)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官职无关”规则,即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罪行的罪犯不得因为担任国家官职的原因而免除其个人刑事责任,也不得因为担任国家官职的原因而享有豁免。这是国际刑法自纽伦堡审判以来确立的规则。③
2.讨论范围界定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笔者想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主题范围。首先,虽然国际法委员会使用的“国家官员”这一措辞会让人联想到很多层级的国家官员,但从已有案件情况看,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以及派遣驻外的常驻外交代表的豁免问题引起的争议最多,因此本文“国家官员”仅指代这几类官员;第二,普通犯罪的豁免问题,国际法理论没有疑问,因此本文中涉及的罪行仅指代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战争罪等国际法上的罪行;第三,已然卸任的国家高级官员的豁免问题不在讨论之列,本文仅探讨现任的国家高级官员是否对其任期之内的被指控罪行可以豁免;第四,豁免从广义角度看,可以包括程序豁免和实体豁免。实体豁免,即从实体法上免除个人的刑事责任。本文仅探讨狭义上的豁免——程序豁免。
3.与国家主权豁免的区别
享有外交豁免特权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外交官员等,其豁免权利与国家主权豁免是不同的,明确这一点是本文讨论豁免问题的基础性前提。主权豁免来自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的古老法则,而给予外交人员一定豁免特权是为了保证其行使职权、保持正常国际交往秩序。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于这一点已经给予非常明确的阐述,④在此没有必要详加论述。
4.职权豁免(functional immunity)和属人豁免(personal immunity)
职权豁免和属人豁免是外交关系法中相对应的两个概念。职权豁免,即相关人员在其行使职权的范围内,其行为豁免于刑事、民事或其他性质的诉讼,但不得就职权范围之外的事项提出豁免请求。基于职权豁免的理念,习惯法上可以将相关人员的行为分为公性(official capacity)和私性(private capacity)两类。对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意义上的普通外交代表而言,公性行为和私性行为的区分是存在的,并且对能否豁免于诉讼会产生实质性影响。⑤而根据国际法院的观点,对外交部长这样的高级官员而言,在豁免问题上区分公性行为和私性行为没有意义。⑥
属人豁免,即相关人员因为担任某种较高职位而在任职期间享有豁免,豁免持续时间从担任该职务时起算,至卸任之时或卸任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消失。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对此规定得非常明确。国家高级官员的属人豁免由习惯法调整,⑦属人豁免自其担任相应职务始,止于其不再担任该项职务之时。本文对豁免及其引起的法律冲突的分析从职权豁免和属人豁免的分类展开。
二、职权豁免:国际罪行是构成豁免的例外
1.国际法院逮捕令案
国际法院2002年判决的逮捕令案是反映本文阐述的规则冲突的典型案例。时任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阿普杜拉耶·耶罗迪亚·努多姆巴西(Abdulaye Yerodia Ndombasi)受到比利时法院以“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罪行”和反人道罪发出的逮捕令的逮捕⑧。本案争议的实质是:一国外交部长能否豁免于外国法院以战争罪、反人道罪等严重国际犯罪为罪名的起诉。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没有明确区分职权豁免和属人豁免,但综合法院判决和少数派法官的观点可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官是有分歧的。两类观点运用不同的方法,得出大相径庭的结果,这为我们分析职权豁免问题提供了两条基本思路。
2.规则调和的方法
规则调和的方法是逮捕令案中国际法院判决书的观点,即在不否定任何一条规则的规则基础上,尽可能地防止规则之间产生冲突。
该案涉及外交部长豁免权,但两国都不是涉及外交部长豁免权的惟一条约——1969年《纽约特别使团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缔约国。国际法院认为:这些公约对于豁免问题的某些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指引,但是它们并没有包含关于外交部长豁免的特定条款,因此法院决定本案中外交部长享有豁免的问题应该在国际习惯法的基础上考虑。(Ibid,at para.52.)
国际法院首先分析了在任外交部长所享有的豁免特权的性质。国际法院认为,根据国际习惯法,授予一国外交部长刑事豁免特权并非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保证他能代表其国家有效地履行职责。为了确定外交部长享有的豁免特权范围,国际法院必须首先考虑其行使职权的性质。外交部长对其代表政府的外交活动负责,并且作为其本国的代表出席政府间会议,代表其本国政府进行谈判。外交部长的行为可以直接约束其代表的国家,而且对于外交部长的职权存在着这么一种假设:外交部长有权全权代表他的国家行事。在履行职权方面,外交部长频繁地往来于各国之间,因此他处于一个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任意行事的地位。外交部长需要经常和他的政府以及本国外交使馆保持联系,并且在任何时候与他国外交代表进行沟通。法院进一步考虑认为:由于外交部长对其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负责,因此他具有一种与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相同的地位,在国际法上外交部长仅仅因为担任这一职务而成为其本国的代表。外交部长没有必要向他国递交全权证书,与此相反,外交代表的全权证书所载的权限由外交部长的授权决定。最后,外交代办的任免也是由外交部长来决定。(Ibid,at para.53.)
由此,国际法院得出结论:外交部长履行职务的情况是,在其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当他身处别国境内的时候享有完全的刑事豁免特权。这些豁免和不可侵犯的特权保护他不受任何其他国家可能妨碍他履行职务的行为的干扰。(Ibid,at para.54.)在这一方面,不可能以“公职行为”和“私人行为”为标准而对在任外交部长的行为进行划分。所以,如果一国的外交部长在另一国家被逮捕进而卷入刑事诉讼程序,那么很明显他(她)履行职责的行为被妨碍了。不论该外交部长在被逮捕时是以官方身份还是以私人身份在逮捕国境内访问;不论被指控的行为是在该人担任外交部长前就发生还是在他出任外交部长以后才发生;也不论这一行为是以履行公职的名义还是以私人名义进行,这种对外交部长履行职责造成的阻碍作用是同样严重。更进一步说,当该外交部长因履行其职责而来往于各国之间时,他就有可能暴露于他国的刑事程序之下,从而不能完成其外交任务。(Supranote,at para.55.)
在确定外交部长豁免权的习惯法地位之后,国际法院考虑了国际刑法上“与官职无关规则”是否在本案中适用的问题。⑨国际法院认为:这些规则不能使法院得出外交部长在国内法院面临战争罪等指控时也存在豁免规则例外的情况。而且,国际法院发现:在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案件中,没有一个关于现任外交部长在国内法院面临战争罪、反人道罪指控的案例。(Ibid,at para.58.)
国际法院在此肯定了外交部长在一国法院前就国际罪行的绝对豁免权,但也提出了追究责任的四种途径:(supranote,atpara.61.)“一、由享有豁免特权人的本国根据相关的国内法对其起诉。二、如果他们所代表和曾经代表的国家决定放弃豁免,那么这类人则停止享有针对外国管辖权的刑事豁免特权。三、享有豁免特权的人不再担任外交部长职务,该人就不享有由国际法和他国法律赋予的豁免特权。只要一国法院在国际法下有管辖权,那么该法院可审理该人在担任外交部长前和卸任以后所从事的行为,还可以审理其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以私人身份从事的行为。四、在任外交部长在某些国际刑事法庭有管辖权的情况下由该国际刑事法庭审理。例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还有即将全面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等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可能赋予某人官方身份的豁免或特别程序规则,不妨碍本法院对该人行使管辖权。”
上诉途径的提出似乎为国际法院回避外交部长享有豁免的规则和“与官职无关”规则的冲突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本案多数法官的意见是一种尽可能避免法律规则冲突的调和性方法。但是,笔者不得不说,这种调和的方法有很多漏洞,某种程度上有“和稀泥”之嫌,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院在得出外交部长在习惯法上是否享有豁免权以及是否等同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豁免权时,没有依据习惯法的基本要素来判断,说服力欠佳。事实上已经有少数法官提出,外交部长的豁免,与其说是习惯法规则所致,不如说是国际礼让的结果。⑩第二,国际法院没有把问题分成职权豁免和属人豁免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三,“与官职无关”规则是习惯法的规则,国际法院没有解释为什么该规则在国际法庭适用,却在国家的法院不适用。
至于第三种解决途径,从职权豁免的角度来看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按照这一观点,国家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只要以公职的名义行使即便是属于种族灭绝罪的行为,也不在追究责任之列。这个思路和五十多年前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各战犯以担任国家公职作为免责理由如出一辙,却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确立的国际刑法基本原则根本对立。(11)仔细分辨,这个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卸任的国家官员能否就其任职期间的罪行免除刑事责任,因此此类情况早已突破了本质为程序法属性的豁免问题,到了实体法中国际罪行的免责事由这个范畴里来了。
3.效力位阶(Normative Hierarchy)的方法
国内法结构非常严密,其效力等级呈现出金字塔结构。故而解决国内法规则冲突最为直接的方法是借助这一金字塔结构,根据法律规范所处位阶的高低来判断哪一条规范优先适用。国际法规则中没有这么严格的金字塔结构,但是不同法律规范之间也存在着效力位阶的差别。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三条和第六十四条肯定了强行法规则的存在,并对强行法与一般国际法规则冲突的情况提供了处理方案。强行法理论为我们思考豁免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A.法院判决回避了国际法规则冲突的问题
本案判决第六十一段认为:“与官职无关”规则并不构成外交部长在国内法院诉讼中享有豁免特权的例外规则。作者对这一观点在方法论层面的解读是:多数意见把“与官职无关”规则和刑事豁免规则放在同一效力位阶上分析,进而通过假设四种责任追究途径来避免两条规则之间冲突的产生。一条规则构成另一条规则的例外,从逻辑上判断,两者之间是同一效力位阶上“或”的关系,非此即彼,到底适用哪一条取决于个案。但是,“与官职无关”规则源自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实践,国际法委员会将其编入《纽伦堡原则》的那一刻起即具备了强行法特征。我们的问题是:本案中,面对战争罪、反人道罪的指控,两条规则之间真的是同一效力位阶上的选择关系吗?很显然,国际法院的判决没有运用效力位阶的方法分析两条规则之间的冲突。
B.少数法官的异议意见
如果运用效力位阶的方法,便对国际法院的判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除非有关豁免的规则取得国际强行法的地位,否则,国际法院凭什么认定豁免规则的效力一定会优于“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呢?相反,惩治战争罪、反人道罪等罪行恰恰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所在,因此这一规则应当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效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强行法的特征。Al-Khasawneh法官在他的反对意见中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规则的效力位阶的分析上,他认为,“与严重罪行作有效的斗争这一规则已经带有强行法的特征,反映了国际社会的重要利益以及其寻求增强和保护的利益。因此,当这一处在更高效力位阶之上的规则与豁免规则产生冲突的时候,它应当优先适用。”(12)Van Den Wyngaert法官也表示:如果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认为违反了强行法,而在任外交部长享有豁免并非强行法规则,那么“惩治这些罪行的规则在其应具有的地位上和豁免规则之间便会产生更为紧张的冲突。”(13)上述两位法官的观点与其他多数法官在判决中所采用的方法可谓大相径庭,因为这两位法官不仅谈到了规则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而且也阐述了依据效力位阶解决规则冲突的方法。因此,有人认为,如果国际法院采用了这两位法官的思路并认真地思考普遍管辖权的法律基础的话,国际法院很有可能就耶罗迪亚是否对比利时法院的普遍管辖权享有豁免作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判决。(14)
C.晚近的国家实践
晚近以来国家的司法实践,开始倾向于运用效力位阶分析的方法解决国际法规则的冲突。在诸如检察官诉泰勒案(15)、皮诺切特案(16)、费雷尼诉德国案(17)以及希腊的司法实践弗伊沃提亚县诉德国(Prefecture of Voiotia v.Germany)案(18)中,尽管这些案件并没有直接涉及外交豁免规则和“与官职无关规则”的冲突,但是就冲突解决方法而言,它们对于本文探讨的问题有相当的参考意义。
由此,笔者认为:在职权豁免的层面上,国家官员的豁免权不能作为其免于国际罪行指控的抗辩依据。
三、属人豁免的问题
1.二分法的运用
属人豁免的问题似乎更为复杂,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习惯法上的问题。从逮捕令案来看,虽然国际法院没有明确阐述这个问题,但其基本观点我们可以从其判决中推断出来:在一国国内法院,外交部长只要还担任职务,对其签发任何逮捕令的行为都是对外交部长享有豁免的侵犯;在国际性刑事法庭面前,外交部长的豁免权应受到“与官职无关”规则的约束。由于国际法院认为国家元首的豁免与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的相同,因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情形也可以据此推断。至于常驻驻在国的外交代表,则受到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约束,国际法院的观点如是。(19)综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分情况讨论的二分法:保持国内法院面前属人豁免的稳定性,是出于维持正常国际交往的考虑。如果国家元首、外交部长在出访、谈判过程中,在外国面临不可预知的诉讼风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接受此种国际交往的环境。当一个国家的元首被邀请去国外参加国际会议,而邀请国趁机将其逮捕,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在国际刑事法庭面前,相关人员受到“与官职无关”规则的约束,似乎可以从条约法的角度得到合理解释。我们可以从法庭规约这一宪法性文件出发进行分析。(20)在安理会单独设立的国际刑事法庭——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前,被告人之所以没有豁免是因为法庭规约的效力来自于安理会的职权,而安理会的职权由《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予以强制保证。对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而言,“与官职无关”规则的优先适用仿佛可以解释为联合国与塞拉利昂政府之间关于建立该法庭条约的授权。(21)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豁免问题则比较复杂,下文予以阐述。
2.属人豁免的中止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常驻代表在外国法院面临国际罪行的指控时,其属人豁免什么时候中止?或者说,这些严厉的指控是否使得相关人员的属人豁免立即失去效力?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前提性问题——指控所依据的事实是否被证据充分证明的问题。以战争罪为例,1949年日内瓦公约要求“或引渡或起诉机制”的启动必须满足有初步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事实上实施了“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这一类战争罪。(22)抛开证据法问题不谈,属人豁免是否直接被中止呢?
让我们根据适用法律的不同分两种情况来讨论。在条约方面,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常驻外交代表豁免的存续时间。根据公约的规定,外交代表面临刑事指控,驻在国政府可以选择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待其不再享有豁免时另行起诉。
对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我们在习惯法上找不到立即中止其属人豁免的明确理由。国际法院提出四种追究耶罗迪亚先生刑事责任的替代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了维也纳公约第十四条和第三十九条的思路。卡札菲案中,利比亚在任领导人卡札菲面临恐怖主义罪行的指控,然而法国最高法院却肯定了卡札菲享有豁免权。(23)
由此,笔者认为相关国家官员在外国法院面临国际罪行诉讼的时候,其属人豁免并不必然因为战争罪等国际罪行指控的提出而立即中止。相应习惯法规则和条约似乎更加支持属人豁免持续到该官员不再担任相应职务之时。
3.非法律因素的影响
属人豁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非法律因素的影响。国际法院在逮捕令案中强调,豁免并不等同于有罪不罚的状态(impunity),并且列出了四种追究耶罗迪亚刑事责任的途径。从法理上说,国际法院提供的途径并没有错,但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仔细辨别之后,我们发现判决书建议的这些途径没有一种是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例如,第一种情况是,由享有豁免特权人的本国根据相关的国内法对其起诉;第二种情况是,他所代表和曾经代表的国家决定放弃豁免。通过这两种途径追究耶罗迪亚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他所代表国家的意愿或能力。如果刚果不愿意对之调查并起诉,或因为国内法方面的问题不具备起诉战争罪、反人道罪的条件,那么这种困境就相当于刚果为耶罗迪亚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天堂。事实上,在本案审理时,耶罗迪亚已经从外交部长的位置上卸任,改任刚果教育部长。(24)但对于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刚果政府有任何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动向。由此可见,所谓“意愿”、“能力”本身并不是法律框架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其本质是政治问题。在考虑到这个背景的情况下,再来观察一下逮捕令案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作什么样的决定,国际法院都会面临困境:作有利于比利时的决定,国际交往的正常秩序有可能遭到严重破坏;作有利于刚果的的决定,国际法院可能受到诸如不保护人权的指责和非议。
另一方面,传统或许也能用来部分地解释国际法院的态度:国际法院一直保有维护既有秩序稳定的传统,司法实践较为保守;而各国际性刑事法庭,其目的是要追究国际罪行犯罪者的责任,代表的是国际法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会作出较为激进的判断。
四、国际刑事法院的豁免问题以及巴希尔案的前景
从条约的角度来看,国际刑事法院的豁免问题更为复杂。罗马规约中涉及豁免问题的条款是第二十七条和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是对习惯法上“与官职无关”规则的总结。在此之前,不论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七条第二款,还是《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六条第二款,都对这一规则是属于程序性规范还是实体性规范语焉不详。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条第二款,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自动放弃了国家元首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豁免特权。但是,罗马规约只能处理缔约国内部的关系问题,根据条约法的一般原理,条约无法为第三国创设义务。(25)因此,在豁免问题上罗马规约还必须为国际刑事法院和非缔约国的关系作出安排,这就有了规约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即若缔约国向法院移交案件导致其违反对非缔约国在豁免方面的国际义务,法院不得要求该缔约国这么做,除非法院能够首先争取第三国放弃豁免。由此可见,“与官职无关”规则的运用不是绝对的。但是笔者必需澄清两点:第一,第二十七条和第九十八条的适用并不构成对国际刑事法院判断案件可受理性方面的附加性条件,案件是否受理还是应当按照规约第十七条规定的条件来判断;第二,造成“与官职无关”规则适用不完整的状况,并不是豁免规则本身的问题,而是罗马规约效力的问题,毕竟条约对第三国没有约束力。
本文开篇提到的苏丹总统被诉一案情况十分特别,如何解决哈希尔的豁免问题在罗马规约中没有明确规定。苏丹目前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检察官起诉巴希尔总统的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苏丹答尔富尔地区安全形势的1593号决议(26)以及罗马规约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联合国安理会动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权力提交案件的情势。因此,巴希尔案是否被国际刑事法院受理以及巴希尔的豁免问题,落脚点要看安理会1593号决议的效力和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本身的效力。
一方面,1593号决议以非常强硬的措辞要求苏丹政府为国际刑事法院及其检察官提供完全的合作和一切必要的协助。(27)由于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决议是有强制力保证的,因此理论上讲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决定起诉任何一个与答尔富尔地区事件有关的人。由此问题演变为:安理会是否有权以决议的形式剥夺一个现任国家元首享有的豁免特权。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恐怕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
另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是独立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罗马规约为安理会提交案件打开了一条通道,但这并不表明国际刑事法院必须按照安理会提交的情势来决定受理案件。我们假定巴希尔案的初步证据表明案情符合罗马规约可受理性的判断标准,法院还将考虑第二十七条能否对非缔约国适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决议的效力,能否让国际刑事法院突破其宪法性文件的限制而将罗马规约的条约效力强加给一个非缔约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巴希尔案的豁免问题通过法律机制自动解决面临很多障碍。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苏丹总统被诉案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可能性更大。
五、结语
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和保护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追究国际罪行越来越多地指向依照国际法享有豁免权的个人。这些现象必然导致国际刑法上“与官职无关”规则与一般国际法上刑事豁免规则的冲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决定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就是上述法律冲突愈演愈烈的信号。对于这一法律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从职权豁免和属人豁免两个层次展开,同时区分国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庭两个类型进行讨论。笔者认为上述法律冲突的成因、表现以及解决途径十分复杂,远非让一条规则服从于另外一条规则那么简单。目前可以比较肯定的一点是,在职权豁免的层面上国际罪行已经构成职权豁免的一个例外;但对于属人豁免而言,需要按照国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庭的不同情况来讨论。而且,由于被诉对象享有豁免的法理基础不同,我们最后不难发现豁免问题其实是一系列条约规则和习惯法规则综合推理的结果。除此之外,还需要明确:豁免问题虽然是程序问题,但极有可能造成指控对象的罪行实质上不予追究的状态,这些情况都是非法律因素造成的,这也是每一个个案法官需要充分衡量的。
注释:
①国际刑事法院2008年7月14日消息,见:
②ILC Report,A/62/10,2007,Chp.X.A.4,para.376.
③参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七条第二款、《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六条第二款、《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七条等。
④ILC Draft Articles On Diplomatic Intercourse and Immunities with Commentary 1958, Introductory Comments to Section II,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958,vol.II,pp.94-95.
⑤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⑥Case Concerning the Arrest Warrant,judgment,at para.55.
⑦如为特别使团组成人员,受《特别使团公约》保护。
⑧Judgment of ICJ Arrest Warrant Case,at para.11(1).
⑨《纽伦堡宪章》第七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七条第二款、《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六条第二款、《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二十七条。
⑩Arrest Warrant Case,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Al-Khasawneh,at para.1; 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e Van Den Wyngaert,at para.15.
(11)Antonio Cassese,International Law,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at p.200.
(12)Judgment of ICJ Arrest Warrant Case,Dissent Opinion by Al-Khasawneh,J.,para.7.
(13)Judgment of ICJ Arrest Warrant Case,Dissent Opinion by Van den Wyngaert,J.,para.28.
(14)INTERNATIONAL DECISION: Arrest Warrant of 11 April 20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Belgium),Alexander Orakhelashvili,Jesus College,Cambridge,Edited by Bernard H.Oxman,The American Journal International Law,July,2002,at 683,684.
(15)Prosecutor v.Charles Taylor,Appeal Chamber Decision On Immunity From Jurisdiciton,at para.1,53.
(16)The speech of Lord Browne-Wilkinson,in R.v.Bow Street Stipendiary Magistrate and others,ex parte Pinochet Ugarte,House of Lords,Judgement of 24 March 1999,in [1999] 2 All ER,at 112-115,as well as those of Lord Hope of Craighead,at 145-152,Lord Saville of Newdigate,at 169-170,Lord Millett,at 171-191 and Lord Phillips of Worth Matravers,at 181-190.
(17)87 RIVISTA DI DIRITTO INTERNAZIONALE at 544,545..
(18)See Ilias Bantekas and Edited by Bernard H.Oxman,International Decision:Prefecture of Voiotia v.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Case No.137/1997.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Leivadia,Greece,October 30,1997,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October 1998,at p.765.
(19)《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20)Malcolm D.Evans,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2006,at p.417.
(21)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erra Leon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Artcile 1.
(22)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公约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三公约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公约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
(23)Malcolm D.Evans,International Law,at p.414.
(24)Arrest Warrant Case,judgment,at para.18.
(25)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三条。
(26)S/RES/1593(2005),at para.1.
(27)Ibid,at par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