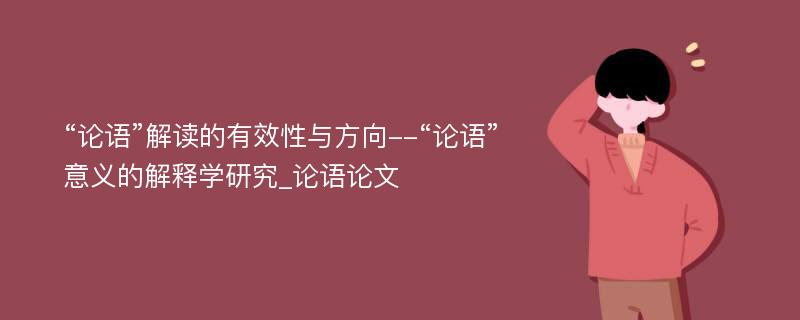
《论语》诠释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对《论语义疏》的一种诠释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有效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8)03-0004-10
《论语》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自从它诞生以来,就不断有硕学鸿儒为之作注,从而出现了诸如郑玄的《论语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多部《论语》学经典之作。其中南梁皇侃(488-545)的《论语义疏》是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底本而作的注疏,所以,透过《论语义疏》,我们便能一睹两汉、魏晋以及南北朝这三个时期《论语》诠释的不同风貌。本文的目的正是要循此路向来对《论语义疏》做一诠释学角度的考察。
一、文本与意旨
《论语》一书本是孔子去世后,由其弟子和门徒集编而成的语录体著作。该书记载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语,所以历来被视为研究孔子思想最原始、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然而问题是,《论语》这个文本到底能否真实地传达孔子的意旨?或者说,通过《论语》这个文本,我们能否把握孔子的真实意图?这是一个诠释学的问题。皇侃在《论语义疏》里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主要见于他的两条疏文: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皇侃疏:“颜既庶几与圣道相邻,故云钻仰之。子贡既悬绝,不敢言其高贤,故自说闻于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圣人之筌蹄,亦无关于鱼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著焕然,可修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闻也。’”①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论语·公冶长》)
皇侃疏:“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禀以生者也。天道,谓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②
按皇侃这两条注的意思,六籍(即六经)的确是圣人或夫子言语的记录,但这种记录只是间接的、固定化为文字形式的圣人之言,它与圣人实际的言语、尤其是圣人原始的意旨是不一样的。六籍只是圣人之“筌蹄”,而筌蹄“无关于鱼兔”;文章只可修耳目,而无关于圣人之旨。总之,皇侃的观点是,《论语》或者任何别的经典都只是作者意图的间接、浅层的表达,作者的真正意图和深层意旨是不能通过该文本而获得的,在《论语》文本所蕴含的孔子的意旨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孔子意旨。这里所包含的诠释学问题在于:一个真正的孔子的意旨,如果不能通过文本(比如《论语》)而获得,那么又从何而获得?文本如果没有真正表达作者的意旨,那么它表达的是何人的意旨?在文本之外,我们是否还能谈论所谓孔子的真正意旨?这些问题在诠释学上都是值得讨论的。
首先,我们注意到皇侃用了《庄子·外物》篇“筌蹄”与“鱼兔”之说,但是他歪曲了庄子的意思。《庄子》原话是这么说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按庄子的意思,他并不否认荃(筌)、蹄的作用,筌、蹄是可以得鱼、兔的,只是重要的是得鱼、兔而不是得筌、蹄。而皇侃则将其曲解为筌蹄“无关于鱼兔”。这实际上是把“言”与“意”分作两截,彼此无关联了。而无论是西方浪漫主义的诠释理论还是中国后来的儒学大家,都不否认通过文本可以把握到作者的意图。文本所言说的意义,就是文本所指称的作者的意义,虽然这个意义还须经由读者的视域“过滤”而表达出来,但无可否认的是,它总是与作者借文本形式而表达的意义密不可分。
其次,当我们解读《论语》而讨论孔子的思想时,我们总是在据《论语》这个文本而来谈论孔子的思想。皇侃在注解《论语》,同时又假定一个在《论语》之外的、不能为我们所把握的所谓孔子的真正意旨,这显然是矛盾的。他既已承认《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语的,自然就应承认《论语》就是孔子思想的表达,假定在这个文本所表达的孔子意旨之外有一个原始的孔子意旨是毫无意义的,它终究只是假设。
最后,在文本之外我们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谈论所谓孔子真正的意旨。谈论一个人(比如孔子)的思想,总是根据某种承载了其思想的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些形式都称之为“文本”,不管它是口头的、文字的、传说的还是任何别的形式,都是我们得以讨论某人思想的唯一有效的根据。如果不是根据任何文本形式而谈论所谓某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解读者纯粹的个人独白——如果不是信口胡说的话。
实际上,皇侃在以上两条自己的疏文之后,又引用了太史叔明的注,其注与皇侃不同。太史叔明注云:“文章者,六籍是也。……六籍即有性与天道,但垂于世者可踪,故千载之下,可得而闻也。至于口说言吐性与天道,蕴藉之深,止乎身者难继,故不可得而闻也。”③太史叔明承认六籍与性及天道之可踪、可闻,也就是肯定《论语》这个文本可以传达孔子关于性与天道之说。在太史叔明看来,难继者只是孔子亲口言说时之道。这里,他分别了六籍作为书面文本与口语言说之间的界限。实际的言说与经由文字而固定下来的言说之间的差别是存在的,太史叔明和皇侃都注意到了这点,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故存而不论。总之,正如太史叔明的注所说的,《论语》即是孔子思想的表达,通过诠释《论语》,可以把握到孔子的意旨。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总结:
其一,《论语》就是记录孔子思想的主要文本,舍此,我们别无可求。脱离具体的文本,我们不可能理解和解释所谓孔子的思想学说。再者,《论语》本身是有其意义的,这就是说,《论语》有别于《春秋》《周易》等一切其它的文本而有其独特的含义,这是《论语》诠释有效性的基础。虽然后来的读者会把《论语》解释成各种不同的面貌,但《论语》作为独立的文本,仍有其意义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它有一个不同于任何历史境域下读者解说意义的自身意义,这也是《论语》诠释有效性的题中之义。
其二,《论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原始意义”(“原意”)。就像任何文本一样,《论语》总是经由读者看到的《论语》,只要有读者阅读它,它的意义就是经过读者解释过的意义。所以《论语》的意义是向历史敞开的,并在历史的解读中呈现出其意义的可能性。加达默尔说:“理解的每一次实现都可能被认为是被理解东西的一种历史可能性。……对于同一部作品,其意义的充满正是在理解的变迁之中得以表现。”④所以尽管汉代儒者对《论语》可以有皓首穷经的注释,魏晋人士仍可以作出不同的《论语集解》,而南北朝各家学者更可以讲疏不断,从而形成《论语义疏》这样的新文本。我们也许可以指出哪些注释是对《论语》的过度或不足诠释,但我们决不能断言哪部(或哪些)注释是真正符合《论语》“原意”的标准注作。解释是无止境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总是在历史的诠释中不断呈现,“阐释总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它的任务,所以一切理解总只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被完成”⑤。
其三,对《论语》的诠释,合理的进路既不是天真的历史客观主义所谓的还原、再现作者或孔子的原意——因为本没有所谓的原意,也不是文本虚无主义式的任由读者随意妄说——因为文本总有其相对确定的意义,任何解释都不能无视这个文本意义。这正如加达默尔所说,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⑥。合理的解释进路是面向《论语》这个文本,在与文本的历史性对话中生成新的意义。就《论语义疏》而言,解释不应该旨在还原或探索构成《论语》中谈话主体的孔子的本意,而是通过与《论语》文本的对话,揭示、生成《论语》在魏晋六朝时期可能的历史意义。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仅就《论语》这个文本来讨论孔子的思想意旨,而不是在文本之外去找。通过诠释《论语》从而把握孔子的思想主旨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
二、《论语义疏》的三重结构
作为南北朝仅存的义疏体著作,皇侃《论语义疏》在体式上是既释经文、又释注文,所以其文本包含了三重结构,就像是三个由小到大的同心圆:最里一层的圆是《论语》原文,中间的圆是汇集了汉魏八家注释的《论语集解》,最外层的圆则是包括皇侃自己的疏在内的、由皇侃汇集的三十多家六朝注释的《论语义疏》。这种注疏体式的结构特点,使该文本包含了三层义理结构,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论语》本身的主旨是什么?包含了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二,汉代注家主要在哪种方向上对《论语》作出了诠释?何晏作《论语集解》又对此作了怎样的调整?第三,皇侃及六朝儒者又是怎样作出时代性的诠释和转换的?
《论语》一书,无非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书,其中涉及孔子的形象、情感、思想和学说,所以任何《论语》注释之作,都是在考察、解说、定位孔子的形象和思想。汉人解释《论语》会塑造一个孔子形象,阐说一套思想义理,魏晋南北朝人又会塑造另一个孔子形象,创设一套新的思想系统。但是,无论后人对《论语》的注释如何地重点不同、方向各异甚至众说纷纭,《论语》作为《论语》学共同的文本对象,总有其自身基本的结构和内容。简略地说,《论语》一书包括这样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构成《论语》符号系统的典章文字,即《论语》全书的字词章句、名物典制、历史文献等等;第二,是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所倡导的仁道思想,也就是他关于君子、仁爱、忠恕之道等的道德学说,以及对圣贤君子人格境界的设定;第三,是在臧否时政当权人物的言语中吐露出来的关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设想,也就是孔子的王道思想和礼制名教学说;第四,是关于天道性命的思想。《论语》中孔子虽然较少谈及天、命、性等概念,但也绝非“不可得闻”,只是讲得平实而少作阐发而已。
《论语集解》保留的汉代注释有四家,分别为孔安国《古论训解》、包咸《论语章句》、马融《论语训说》和郑玄《论语注》。孔安国的注重在训诂,兼及大义。包咸的《论语章句》重在离析经文、疏通句义,着眼于交待背景知识。马融的《论语训说》既注重对名物制度的诠释,又好援引纬书解释《论语》。郑玄的《论语注》既重字词和名物制度的训诂,又善以礼说《论》,侧重于对《论语》道德、政治方面义理的阐发。总之,汉代《论语》注释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诠释《论语》的:一是训诂,一是章句或义说。训诂是就文字的形、音、义来做解释,章句则是整段逐句地解说,指括其文,敷畅其义。训诂侧重于对《论语》第一层内容即典章文字的诠释,章句学侧重于对《论语》第二和第三层内容即仁道思想和王道、礼制的诠释。训诂学的解释旨在还原文字、文本的“原意”,围绕文本、文字的可靠性、真实性而全力考证,可以说是着力于具体方法或技术操作的层面上。章句或训说并不局限于对文本零星字词的解释,而注重对《论语》中史实及篇章大义的解说。汉代章句、训说并不以辨名析理的方式演绎思想,而是多用实证的方法,故而详于对实事的铺陈或对史料的搜罗,所以这种解释又难免显得滞重而烦琐,对于《论语》更深层的思想仍然缺乏发掘。
既是基于对于汉儒烦琐学风的厌弃,也是对于汉儒注释缺乏理论深度和不能应对魏晋之际变乱时世的不满,何晏等人于是试图通过编辑整理过去的《论语》注释来改造旧学、缔创新学。《论语集解》改造旧学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即“集诸家之善”和“有不安者,颇为改易”。所谓“集诸家之善”,就是于汉魏众多的注释中,有所鉴别和选择地摘取一些存留下来。所谓“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则表示编者已经对某些注释作出了有目的的改易。“从他所集的前人的成说来看,多半是属于儒家的政治准则和伦理规范方面,这些已经形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次,何晏对此并未持有异议,……从他感到不安而加以改易的部分来看,多半是属于天人之学即高层次的哲学思想方面。”⑦何晏等人开创新学的方式,则是“自下己意”,即舍他人之注不用而自己作注,并且往往于微妙处搀夹玄言。用何晏自注和郑玄的注解做一比较,即可看出:“郑玄纯为汉儒说法,重章句训诂,主张以经解经,典章制度必明白切当,且偶有灾异谶纬的说法。何晏则一扫依傍,纯由老、易入手,遇有可染指处,则语涉玄理。”⑧因此可以说,《论语集解》是在有意转换汉学、开启玄学。
构成《论语义疏》第三重结构的,是皇侃援用的一部分江熙的《论语集解》以及当代通儒的注释。这些注家中既有如范宁、颜延之、贺玚等名儒硕学,也有如王弼、孙绰、李充、殷仲堪、顾欢等善解玄理之名士,更有如沈居士、释惠琳等佛家硕学之流,基本网罗了魏晋六朝几乎所有重要的《论语》注家。《义疏》所集注释仍保存有不少汉代注释的风格,但总体上摒弃了烦琐的名物考证和冗赘芜蔓之风。而体现出《义疏》不同于汉儒注释、从而反映六朝思想新特点的注释,主要是受玄学思潮影响的玄儒的注。众所周知,玄学是通过重新诠释“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并着重开发其中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而拓展其思维路向的。以玄学注解《论语》成为六朝时代一种自觉的、占主体地位的方法。“三玄”与《论语》的交汇,体现出儒道会通的时代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论语义疏》对《论语》的解释就趋向于把《论语》平实、现实的旨趣往思辨、玄远的方向提升,所以它侧重诠释的是《论语》第四层内容即天道性命。
“道”这个概念在《论语》一书中本为孔子的仁道,在玄学时代则多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天道。王弼率先搀入《老子》义,称“道”为“无”,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⑨把实体性的道诠释转换为无名无相不可名状的“无”,使道具有了虚灵玄通的灵动性。王弼以后,在《论语义疏》中所收集的后玄诸家谈“道”,多着重渲染“道”形上而虚玄的一面。如皇侃说:“道者,通而不壅者也。道既是通,通无形相。”⑩在《论语义疏·为政》篇里,皇侃又进一步把道、无、有等概念作了理论的关联,发展了王弼以来的道论,其中写道:“自形器以上,名之为无,圣人所体也。自形器以还,名之为有,贤人所体也。”皇侃以形上与形下的区分来界说“无”与“有”,显然是本王弼以“无”解“道”的思路,把《论语》中的“道”彻底形上化、非实体化,这与汉儒的宇宙论迥然异趣,而进到了形上的本体论。
性情之论也是《论语义疏》着笔甚多且颇有新意的主题。汉儒多以阴阳元气说论性情,又多言性善情恶,趋向于把性情对立起来,故多否定情而肯定性。魏晋六朝人则多抛开阴阳谈性情,而以体用、动静谈性情。因篇幅之限,兹仅引皇侃在疏“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时所论性情之义,论曰:
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动彰事,故曰成也。然性无善恶,而有浓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为恶,亦不可目为善,故性无善恶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恶之名,恒就事而显,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以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此皆据事而谈。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迁,其事则邪。若欲当于理,其事则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热,而即火非热。虽即火非热,而能使之热。(11)
这里,作者论述了三点:(1)性无善恶,而有浓薄。(2)情为心之欲,有邪正。(3)性与情,犹火与热。这些都与汉代阴阳生成论的性情说不同,而火热之喻,更是用体用关系来解释性情。对《论语》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文本不曾言出的内涵,而是六朝注家在诠释中创造性地作出的引申。正是这些引申而出的性情论,继续成为宋明儒学所热烈讨论的主题。
从以上对《论语义疏》三重结构的分析可知,《论语》本身的意义与汉儒对它的诠释以及与魏晋六朝时代的再诠释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了文本诠释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表现为文本诠释者处在不同的诠释立场和诠释境域中,诠释者所接受的知识传统、学术背景以及个人资质等等构成了他的诠释境域,海德格尔称之为“前理解”,加达默尔又把它叫做“前见(偏见)”。加达默尔指出,这些“前见”就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传统,它构成为我们观看事物的“视域”。理解和解释总有两个视域,一是理解者自己身处现实中的当下视域,一是文本的视域,诠释最终是这两个不同视域的融合。由于读者是历史地变化着的,所以文本也就始终向新的生活经验开放,允许每一代人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延伸它,从而生成新的意义。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方式的诠释所生成的不同意义,又不是各自独立地封闭的圆圈,而是在效果历史的作用下共同构成为传统。《论语义疏》以其三重结构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诠释学意蕴。作为最原始、最核心的文本,《论语》是被《论语集解》包裹着的,而《论语集解》又被《论语义疏》包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已经使三者浑然一体而难于分辨所谓“本来面目”了。
三、两种向度:知识与意义
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的读者会作出不同种类的解释,这些解释可分为语法的、文献学的、语义学的、心理学的和哲学的解释等等。这种种解释又大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向度,即知识的向度和意义(价值)的向度。这方面,西方传统诠释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为了清楚地考察《论语义疏》中所包含的诠释学意蕴,有必要对西方诠释学关于“意义”一词的辨析做一梳理。
“意义”一词在英文里对应有两个词:Meaning和Significance,它们在文本诠释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德国的阿斯特(Friedrich Ast)那里,就注意到了这两个词的差别,他说:“对于每一个需要解释的段落,我们必须首先问文字在陈述什么;其次,它如何在陈述它,陈述句具有什么意义(meaning),它在文本中具有什么意味性(significance)。”(12)他的意思是“意义”是陈述句陈述的内容,“意味性”是陈述句内容与整个文本所具有的关系性。后来意大利的贝蒂(Emilio Betti)也区分出了确定意义(meaning)和价值意义(significance)(13)。而真正以meaning和significance的区分作为其整个理论基石的,是美国的赫施(E.D.Hirsch)。赫施认为有两种“意义”,即“含义”(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14)。含义是由文本呈现出来,通过固定化的符号而构成经久不变的东西,是稳定的、相同的;意义则是与一个人、一个概念、一种情境或任何能真正想象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是文本与读者发生交融时所产生出来的东西(15)。赫施说,含义这个术语是指一个文本的整体的言词意义,而意义是文本在一个更大的上下文——即另外的心灵、另外的时代、更大的主题、不同的价值系统等等——的关系中的意义。
含义与意义的区分,已经标示出知识与意义(价值)这两种向度。所以赫施说:“含义与意义这两个概念与知识与价值两概念相似。含义是解释中稳定的知识的目标,没有它,更广的人文主义的知识将不可能。另一方面,意义的主要兴趣则在不稳定的价值领域。……因为,意义命名了文本含义的关系,而价值是一种关系,不是实体。”(16)阿斯特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文字、意义和精神是解释的三要素。文字的诠释(hermeneutics)就是对个别的语词和内容的解释;意义(Sinn)的诠释就是对它在所与段落关系里的意味性(Bedeutung)的解释。精神的诠释就是对它与整体观念(在整体观念里,个别消融于整体的统一之中)的更高关系的解释。”“对语词和内容的解释是以语言知识和考古学为前提,换句话说,就是以古代的语法知识和历史知识为前提。”(17)要之,对文本含义的解释指示的是知识的向度,对意义的诠释则指示出价值的向度——或叫意义的向度。知识的向度保证意义(价值)向度的有效性,但有效的解释是不够的,有些知识性的诠释是不必要的,而意义或价值的诠释则增加了文本意义的丰富性。
文本诠释中知识与意义向度的区分,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论语义疏》中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向。大抵说来,汉式注解多为知识性向度(18),六朝玄儒的注解多为意义性向度。让我们先举一例以见其区别: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
皇侃疏:“呼曾子名,欲语之。参,曾子名也。所语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贯,犹统也。譬如以绳穿物,有贯统也。孔子语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贯统天下万理也。”
王弼注:“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19)
皇侃的疏是在解释这句经文中各个字词的意思,即便有“贯,犹统也”这样的引申解释,也是援用了王弼的注。把文本的字面含义一一说清,这就是知识性的注释。王弼的注则不然,他抓住一个“贯”字,演绎其关于事与理、约与博、君与民、一与众的理论,不再拘泥于单个字词的含义,而是借此阐发出其中的哲学意蕴。这就是意义性诠释。下面这个例子更能体现汉式注解与玄儒注解在理趣上的差别: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郑玄注:“告人以善道,曰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恕也。”(20)
王弼注:“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唯恕也。”(21)
郑玄只是对“忠”“恕”二词作出字面的解释,王弼不仅对“忠”“恕”二词有自己新的见解,更能就名词进而谈名理。名词的解释是知识性的,名理的解释则是意义性的。知识向度的诠释,是在原文整体关系之内做的梳理,基本没有产生出新的意义。意义向度的诠释,则总是要比原文“多出”一些东西来,它是“依靠文本的非表面指称而引起理解的东西,就是那个指出一种可能语境的东西”(22)。这些多出的东西不能在文本之中得到,所以它恰恰延伸了文本的生命力。
让我们再举一例以作为对知识向度与意义向度区别的总结:
子畏于匡。(《论语·子罕》)
孙绰注:“畏匡之人,说皆众家之言,而不释‘畏’名,解书之理为漫。夫体神知几,玄定安危者,虽兵围百重,安若太山,岂有畏哉?虽然,兵事阻险,常情所畏,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23)
孙绰的这个注释极为珍贵,含有深刻的诠释学意蕴。它的意思是,不抓住“畏”这个关键字,则对这句话的解释都不得要领,是为“漫”。漫,即是漫衍,不着边际,不关宏旨。而孙绰的解释又不是简单的文字训诂,而仍是义解,是辨名析理。他所谓的畏,是有所畏、有所不畏。这样,“子畏于匡”就从一个叙事性的话语诠释上升到一个形而上学的意境上去了。这是典型的意义性诠释。而其他诸家对这句话的注释,多为讲故事、陈史实,如:
苞氏注:“匡人误围夫子,以为阳虎也。阳虎尝暴于匡,夫子弟子颜克时又与阳虎俱往,后克为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与共识克。又夫子容貌与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围之也。”(24)
苞氏的注重在解说“子畏于匡”这个历史事件,而并没有真正解释孔子何以为“畏”。即便如皇侃说苞氏的注乃是“释误围之由者也”,此处的“由”,也只是“事”由,而非“理”由。由此可见,汉代普遍的注释方法——章句学,是侧重于把文本中阙如或不详的情节、情境、背景补充进去,把诸多要素交代清楚。而正是由于这些史实性知识的增加,使章句学日趋烦琐滞重。玄儒意义性向度的诠释则显得清通简要、虚灵生动,使《论语》的意义呈现出更多的韵味。
总之,知识性向度的解释是必要的,但是它对于文本意义的生成是不够的。诚然,没有知识性向度的解释为基础,意义性向度的诠释便失去其根基,容易流于“过度诠释”,有蹈空的危险。《论语》诠释的历史,正如中国哲学经典解释的历史一样,是在知识向度与意义向度的辩证互动中不断延伸的。
注释:
①②皇侃:《论语义疏·公冶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0,380页。
③皇侃:《论语义疏·公冶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第380页。
④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⑤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见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⑥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8页。
⑦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⑧陈金木:《何晏论语集解用玄理注书问题的检讨》,《孔孟月刊》,第23卷5期,第29-30页。
⑨邢昺:《论语注疏·述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7页。
⑩皇侃:《论语义疏·述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第396页。
(11)《论语义疏·阳货》,《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第497页。
(12)阿斯特:《诠释学》,见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12页。
(13)参见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143-144页。
(14)关于这两个词的汉译,并没有统一的用词。Meaning一般译为“含义”、“意义”、“意思”;Significance一般译为“意义”、“会解”、“意味”。实际上,在汉语系统里,“意义”一词的内容丰富,已经囊括了这两个英文词的涵义。为方便阅读,本文统一将meaning译为“含义”,将significance译为“意义”。
(15)E.D.Hirsch,Jr.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8,P.63.
(16)E.D.Hirsch,Jr.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146.
(17)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12-13页。
(18)这里所谓的汉式注解,并不仅仅指汉儒的注解,也指魏晋南北朝时带有汉儒注释风格的注解。
(19)(21)《论语义疏·里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第371-372,372页。
(20)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22)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23)(24)《论语义疏·子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第417,417页。
标签:论语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论语义疏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渊阁四库全书论文; 论语注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