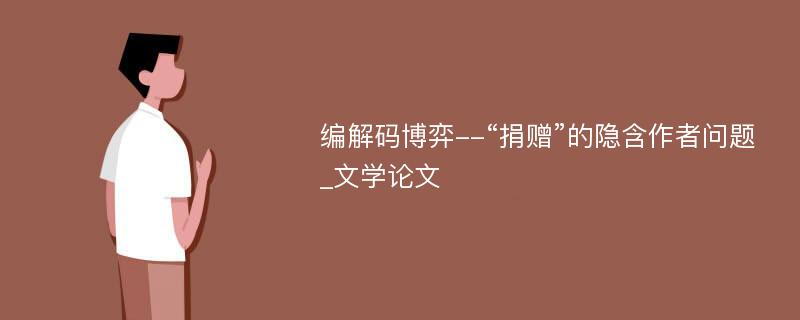
编码与解码游戏——《恩主》的隐含作者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游戏论文,恩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珊·桑塔格(1933-2004)在20世纪60年代初登上美国文坛,作为知识分子的新锐力量,跻身于纽约文人集群(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其小说处女作《恩主》(1963)是她奉上的第一部长篇敲门之作,翌年随着《反对阐释》和《关于“坎普”的札记》这两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问世,“桑塔格时年31岁,就已成了明星。”①尤其是《关于“坎普”的札记》将桑塔格先锋张扬、独特敏锐的智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美国作家菲利普·洛佩特(Phillip Lopate,1943-)由衷感叹:“好一个随笔家!”②并颇为失落:“这使得我不由怀念起仅凭一篇随笔就能功成名就的那段时光”。③但是众所周知,桑塔格真正看重的是小说家的身份,不过从《恩主》引起的反响来说,怀揣着小说家梦想的年轻的桑塔格似乎并未能在试笔之作中得到多大的鼓舞,因为“评论界对《恩主》坚持否定的意见,结果,人们都几乎想象不出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出版它的理由是什么”。④其实这样的评论未免有失偏颇,至少汉娜·阿伦特、约翰·巴斯、弗雷德里克·摩根等人不会加入到这样的苛评中,相反,他们对初出茅庐的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⑤40年后,当桑塔格为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写序言的时候,她还是强调了它对自己的重要性,认为她从此开始了真正的生命之旅和精神之旅。⑥
一、编码游戏:隐含作者的焦虑
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当桑塔格正在苦苦构思《恩主》的时候,韦恩·布思(Wayne C.Booth)一部影响极其深远的论著《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问世,他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中包括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一个中心话题——“不可靠叙述/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ion/narrator),申丹称其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对表达主题意义、产生审美效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⑦按照布思的论述,不可靠叙述又与另一个关键概念“隐含作者”(the implied author)密不可分,衡量叙述是否可靠的标准是当叙述者在讲述或行动时,与作品的思想规范,也就是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是否相吻合,如果吻合,那就是可靠的,反之就是不可靠的。⑧而隐含作者乃是作者的第二自我,申丹教授用一个简化的叙事交流图解释了隐含作者的概念:作者(编码)—文本(产品)—读者(解码)。
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立场和方式来“写作的正式作者”;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申丹教授进而指出,所谓故事的“正式作者”其实就是“故事的作者”,“正式”一词仅仅用于廓清处于特定创作状态的这个人和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⑨这种表述笔者尤为赞同。如果撇开桑塔格特定的创作状态来研究《恩主》,那么无论解读出什么样的结果至少都是不全面的。桑塔格后来把为自己赢得巨大声誉的那些随笔看成是“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那种焦虑,既有一个起点,又有一个终点”。⑩这种焦虑是一个文坛新手的不安,正如40年后她回忆的那样:“我也在想,选择作家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要知道,没有人请你当作家,逼你献身文学。是你自投罗网,以为自己是块作家的料)。”(11)在忐忑和焦虑中,她的第一个决定是一反多数作家在处女作中自传式的写法,刻意抹去真实作者的信息,如此为之“或许是因为谦虚的缘故,也可能是我不像常人那么自恋、虚荣;也许我根本就是胆怯或者克制;也许,比起大多数刚起步的小说家来说,我更有抱负。现在,我所能说的就是,当时我就清楚我想要虚构小说、虚构人物。我不想画地为牢,仅仅讲述自己的故事。”(12)为了最大程度地偏离真实作者的特征,她索性去塑造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以便“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地处理一个个吸引我的主题”。(13)于是,小说演变成了一场编码的游戏。《恩主》讲述的是一个梦想与现实迷离不清的故事,采用第一人称的同故事叙述,叙述者希波赖特沉迷于自己的梦幻世界,利用梦中的情景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被颠覆,变成“夜有所梦日有所为”,梦的荒诞导致了生活的荒诞。但是到了小说的尾声部分,却出现了逆转,希波赖特所讲述的梦境与现实进行了互换,到底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真实就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阿尔伯特·莫德尔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即使没有记录梦,其本身仍是一个梦,即作家的梦。(14)更何况《恩主》还充斥着一个个怪异的梦境呢?打开这部小说,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两段意味深长的引文,其一是波德莱尔论睡眠:“谈到睡觉,每晚可怕的历险,可以说,人们每天大胆地去睡觉,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睡觉有什么危险。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他们的大胆。”其二是德·昆西论梦:“要有什么差错——就让梦去负责任。梦目中无人,一意孤行,还与彩虹争论显不显示第二道弧形……梦最清楚;我再说一遍,该由梦去负责任。”如果说写作是大胆的睡眠,作品是一意孤行的梦境,写作时的桑塔格则可谓是借由作品里扑朔迷离的梦来编织自己的作家之梦,至于梦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位小心翼翼的梦想者只能“让梦去负责任”。
梦或许可以一壮声势,但《恩主》的目录部分还是袒露了隐含作者选择叙述方式的犹疑之情。小说共计17章,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标题分别明确地标出“本书叙述之种种难处”和“本书收尾之种种难处”,而在中间部分的第八章则探讨“梦的恰当叙述形式”。对叙述的关注是这部梦想之作的一个特点。菲利普·洛佩特指出,准备向小说界发起冲击的桑塔格对于四平八稳的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手法不感兴趣,而不可靠叙述是当时的一股写作风潮,她也就被吸引进去了。(15)的确,作为一个时刻关注批评界和文学界动向的青年学者,桑塔格对不可靠叙述的现象不会没有察觉。她还特意提醒读者:他(希波赖特)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叙述者。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但我希望读者别因为他是怎样的人,或者他自称是怎样的一个人就对他的话信以为真。(16)在《恩主》中不可靠叙述的运用为这部作品预留了无限的阐释空间,而这一点与桑塔格高擎的“反对阐释”的旗号并不抵牾,因为她反对的是“反动的和僵化的”(17)阐释,也就是“惟一的一种阐释,即那种通过把世界纳入既定的意义系统,从而一方面导致意义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却导致真实世界日益贫瘠的阐释行为”。(18)《恩主》的开放性挑战了这样既定的意义系统。
二、解码游戏:形式选择的自由
在《恩主》里,“读者”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词,叙述者时时不忘与“读者”交流。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该小说的形式有其独特之处:整部小说是假托希波赖特之手写出来的,也就是叙述者写出的一部自传。如此一来,小说里时时提及的“读者”首先应该是叙述者的读者,是作品里的“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即希波赖特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因此从表面来看,当隐含作者隐身于写作之中时,她的理想读者也不得不接受挑战,在一声声“读者”的呼唤中辨明所指的对象并推导出隐含作者的形象。1962年,桑塔格在日记中写道:“我以写作来确定自己——自我创造的行为——成长的一部分——与自己对话,与我倾慕的健在或故去的作者对话,与理想的读者对话……”(19)对理想读者的期待由此可见一斑。诚然,无论是在国籍、年龄、性别还是婚姻状况等等方面,希波赖特确实与隐含作者有着天壤之别,但这并未妨碍他兼具叙述者与作者代言人的功能。桑塔格下面的这段话能够说明不少问题:
希波赖特不是作家,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一个作家的意识。所以,他认为,他自己的生活由“一个完全是自投罗网之人的两难和烦恼”所构成。这部小说可视为对“自省工程”的一个讽刺。我猜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拿自己开涮,取笑自己的严肃认真。我想,当时我也透露了许多有关自己的信息;同时,我发现,不管我对世界有着怎样的认识,我总感到世界具有无限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为此,我感到痛苦,并在小说中加以表白。(20)
按照桑塔格的提示,既然希波赖特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一个作家的意识,而小说也包含着她本人的“表白”,那么理想读者的解码游戏也由此展开:在希波赖特所谓的自传里,哪些表述是隐含作者的表白或者展示了隐含作者的立场?桑塔格提及的“严肃认真”是她写作的一贯态度,而在布思看来,“当严肃认真的作家把作品交给我们时,有血有肉的作者创造出来的隐含作者,会有意无意地渴望我们以评论的眼光进入其位置”。(21)我们不妨接受《恩主》隐含作者的邀请,进入其真幻交织的奇异世界。
在《恩主》形形色色的梦中,第一个梦“两个房间之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梦里一个穿黑色泳衣的男子在其后的梦境中反复出现,使整部看似支离破碎的“自传”有了一条串连的纽带。这个梦是希波赖特——“我”痴迷于梦的开始,启动了“我”一系列寻梦、释梦、演梦的荒诞之举,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梦揭示了隐含作者对小说表达方式的看法。布思晚年依然坚持隐含作者在研究文本中的必要性,并总结了他首次论述隐含作者时的四个动因,第一点就是“对当时普遍追求小说的所谓‘客观性’而感到苦恼”,(22)他描述了当时的批评状况:很多批评家都认为小说家若要站得住,就必须“展示”(showing)而不是“讲述”(telling)故事,以便让读者做出所有的判断。而小说家若要得到好评,就必须摒除一切公开表达作者观点的文字。从这一点上,《恩主》恰恰是作者在面临与布思同样的苦恼中作出了抉择,在追求“客观性”的普遍现象中执意写出了“可以当成关于主观性的长篇大论”(as an extended treatise on subjectivity)(23)的小说。就“展示”与“讲述”的问题,“两个房间之梦”亦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大多数梦是展示,而这个梦是讲述(Most dreams show,this dream said)。(24)
在“两个房间之梦”中,“我”先是身处一个极其狭小的房间里,墙上挂着几副镣铐,“我”试着带上它们,却发现它们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适合。在突然出现的黑泳衣男子的指挥下,“我”通过一扇非常小的门进入了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房间。黑泳衣男子逼迫“我”跳舞,“我”拒不服从,据理力争,遭到毒打。后来黑衣男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和的白衣女人,“我”主动跳起笨拙的舞蹈,心甘情愿地让她把镣铐铐在“我”的手腕上,但是“我努力想以一种很策略的方式,告诉她我虽感到幸福,但我仍然想离开这儿”。(25)得到许可后“我”反倒轻松了,不急于离开房间,希望能与白衣女人吻别,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和厉声的训斥。“我”在沮丧中企图对白衣女人施暴,梦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似有所选择,实则没有什么不同,“我”都是被囚禁的,失去自由的;从黑衣男子到白衣女人,看似有所改变,结果都是一样,“我”都是被训斥,心灰意冷。这里透露出隐含作者采取主观性写作的辩解:无论顺应还是偏离主流话语,一部新作的接受情况都可能会不如人意,选择了写作之路的作者都无异于“自投罗网”的囚徒。但是小说应该采用何种形式是否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呢?在“主观性”与“客观性”、“展示”与“讲述”之间一定要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吗?很显然,隐含作者无意于认同这种对立,也不愿纠缠在取舍之间,小说中的最后一个梦“木偶之梦”对此做了一个交代。“木偶之梦”在许多方面“都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是“对我做的第一个梦——‘两个房间之梦’——的回应”(259页)。在这个梦里,“我”被人用链条铐在一个只能容下一人的地窖里,黑泳衣人将“我”带到一个公园,以主持人的身份请“我”为观众跳舞,“我”尽力配合,不想辜负他的称赞。在他的怂恿下,“我”去亲近一个小孩,却无意致其身首异处,带小孩的白衣护士毫不责怪,反而和黑泳衣人一起为“我”开脱。这两个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有黑泳衣人和白衣女人,我都被要求跳舞,又都被铐着,在监禁之中”,不同的是,“第一个梦里我感到羞愧,而在这个梦里,我不感到羞愧,而是心平气和”(259页)。究其原因,“在这个梦里,我最后会与自己和解——我真正的自我,我的梦构成的自我。这一和解正是我所认为的自由自在”(260页)。隐含作者至此已超越了形式选择的障碍,在不断地挣扎中达到了平静的心态,通过与自己和解得到了一种自由,因为过于关注外界的认可才是真正的束缚,而“人为了真正自由,只要宣布自己是自由的就行了。要摆脱掉这些梦而获得自由——至少达到所有人类成员有权享受的自由程度,那么,我只要认为我的梦是自由的和自治的就成了”(261页)。
其实在用“木偶之梦”对“两个房间之梦”作出回应之前,小说里由希波赖特自编的《隐身丈夫》的童话已经将隐含作者任由梦境一统全文、我行我素的写作姿态袒露出来了。这个故事说的是视力很差的公主嫁给喜马拉雅山的王子,王子一袭白衣,与周围的冰雪世界浑然一体,所以公主几乎看不见王子。有一天一头黑山熊来到公主家里,由于公主只能分辨出它是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并不能清楚地看见它的容貌,它便假冒王子,说自己在一个山洞捡到了一件黑色的皮衣,它是为了让公主能看到自己才穿上别人的衣服的,但它非常讨厌这么做,所以不允许公主跟任何人,包括它自己提起衣服的事。狡猾的熊总是白天来找公主,而当真正的白衣王子晚上回家时,受骗的公主因为尊重“丈夫在道德上的顾忌”(206页),也就信守诺言,从不提及黑衣服的事,然而她起初因为有所看见而得到的喜悦逐渐地消逝了,她不能忍受同一个丈夫在白天和黑夜竟会如此千差万别,于是冒着生命危险摸索着寻找存放所谓黑色皮衣的山洞。三天三夜的寻找后,她终于摸到了一扇石门,她刺破自己的皮肤,以血为墨,留下了一封信,请求这个子虚乌有的山洞的主人不要再把衣服搁在洞里了,之后又摸索着回到家里,大病一场,王子精心照料她恢复健康,虽然她眼睛因病全瞎了,但是她感到非常幸福,因为从此以后“她再也不用为选白衣丈夫还是黑衣丈夫而犯难了”(207页)。这个故事的公主深受“黑丈夫”和“白丈夫”之间的差异带来的困扰和痛苦,她的解决之道是消除差异,尽管付出了完全失明的代价,但与“木偶之梦”里的“我”一样,获得了安宁和平静。
三、不可靠叙述:读者解读的自由
当隐含作者觅得了内心的宁静时,她自由自在的思想倾泻已经摆脱了焦虑:“我并不就是默认自己的焦虑,而是经过几番斗争、危机以及多年的反思,我从焦虑中悟出了某种意义。”(7页)她用开放的不可靠叙述回报理想的读者,体验文本赋予的愉悦。在桑塔格眼里,写作是一门美妙的艺术,它创造出某种日后会给予他人快乐的东西。(26)当然,解读的自由也是快乐的一部分,正如希波赖特所言:有读者当然好,但要看作者的运气。读者应当是自由的,他有权发表与作者观点相左的意见,也有权做出其他选择。因此,要是我试图说服读者接受本书的观点,那是不合适的(13页)。读者在推导隐含作者形象的同时,将会继续接受解读不可靠叙述的挑战。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和玛丽·帕特里夏·玛汀(Mary Patricia Martin)补充和完善了布思的不可靠叙述理论,扩展为三个轴向的不可靠叙述: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读解;伦理/评价轴上的不可靠评价。(27)当我们细察《恩主》的具体文本时,不难发现基于这三个层面的不可靠叙述,不过按文本的涉及顺序,以下的分析将略作调整。
1.不可靠读解
《恩主》的不可靠读解比较典型地集中在希波赖特对情人安德斯太太的认知上。依照梦的指示,“我”俘获了安德斯太太的芳心,与她一起出门旅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一座阿拉伯城里,“我”与一名垂涎她的商人讨价还价,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不菲的价格出卖了她,但“我”这么做却不是贪恋金钱——这笔钱一直不曾动用,后来还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安德斯太太的女儿转寄给她;“我”的动机出乎意料地单纯:因为“我”认为沦为阿拉伯人的玩物乃是安德斯太太的愿望,“我”是帮助她实现对性自由的追求。尽管出面花钱购买她的人是个身材肥壮、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但“我”宁愿相信他真是像自己声称的那样是为了治疗儿子的相思之苦,所以对于这桩生意,“我”做出了这样的读解:对安德斯太太产生欲念的是一个雄性十足、长着一口白牙的阿拉伯小伙子,而她则高高兴兴地委身于他……我认为对那个永远充满期待的身体不会有暴力、恐怖、强奸和摧残行为发生(86页)。只是事与愿违,安德斯太太饱受凌辱,落得个身体残缺,狼狈回国后又无家可归,所谓高高兴兴更是无从谈起。“我”的感知不仅与其后的叙述不符,而且也受到隐含作者尖锐的批评,反映出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之间存在的差异,这里是通过“我”在送安德斯太太去商人家之后的内心独白反讽性地表现出来的。“我”让蒙在鼓里的安德斯太太先进了门,但是“我”并没有跟着进去,她就这样被当成一个物品被出售了,此时“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让她清楚歪曲了欧洲男女间关系的那些对妇女表现出的正式礼节的真实价值。假使男人在女人前面进门,假使进门不分先后,那么,情况就不会这么简单了”(86页)。体现西方男性对女性的谦让和爱护的“女士优先”的礼节成了一个陷阱,无情地吞没了像安德斯太太这样轻信的女人。“我”促成她堕落的一番“美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在安德斯太太伤痕累累地再度出现之前,“我”的臆想甚至染上了愤愤不平的色调:安德斯太太远在沙漠国家和她的穆斯林情人尽情地享受生活,而我却待在房间里,孤枕难眠,聆听我的梦(127页)。在如此怨天尤人的哀叹里,隐含作者冷峻的讥诮不难分辨。
2.不可靠评价
在布思提出隐含作者的四个动因中,其中一条是对伦理的强调,他“为批评家忽略伦理修辞效果(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而感到‘道德上’的苦恼”。(28)桑塔格与布思不可不谓同声共气,她称自己是“与世隔绝的道德家”,(29)她盛赞加缪,认为虽然在加缪那里,既找不到最高质量的艺术,也找不到最高质量的思想,但是“能够解释他的作品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即道德之美,此乃20世纪大多数作家无意以求的一种品性”,(30)她自己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品性。在创作《恩主》的过程中她在深入希波赖特内心的时候“不得不允许自己成为最不愿意成为的那种人”,(31)正好也表明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小说里有一个不容忽略的情节,“我”特地交代“这是真人真事”(263页):有天夜里,一个持枪青年闯进家里盗窃,“我”发现之后,几乎是兴高采烈地邀请他用手中的枪去射击他想要的任何物品,凡是击中的都统统归其所有,子弹不够的话“我”可以提供。青年的战利品多得无法搬动,第二天叫了一辆卡车才把他挑中的东西拉走。“我”对此事的评价简直就是荒诞不经了:挺体面的一个小伙儿,真的,多亏这下认识他,要不,我会后悔的(264-265页)。面对窃贼采取如此荒唐的做法在桑塔格30年后的剧本《床上的爱丽斯》(1993年)中神奇地再现了。因病卧床不起的爱丽斯在房间被年轻的小偷光顾时,竟然不慌不忙地起了床,为其掩饰形迹,而且还慷慨地任其拿走值钱的物什。她对小偷畅诉心曲,展开言语交锋,在一番雄辩之后陷于自我陶醉之中,只能想象自己成为胜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爱丽斯的胜利都是子虚乌有的,在与小偷的这次相逢中爱丽斯获得的是拒绝、贬低和深深的失落。(32)《恩主》中的“我”何尝不是如此呢?由衷赞美一次与窃贼危险的相遇只能是“我”自欺欺人的表现,其评价的不可靠性甚至无需求证于隐含作者和理想读者,调用基本的伦理常识便可解决。倘若读者真的如布思所担心的那样,认同叙述者的道德观,那么“我”的效仿者就连最起码的判断力都缺失了。利用“我”的不可靠评价,隐含作者延续了不可靠读解的反讽风格。
3.不可靠报道
《恩主》的第17章将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推到了最高峰。耐心的读者追随希波赖特梦里梦外的人生读完前16章后才在这最后一章里发现前面所叙述的梦境和生活完全有可能恰恰相反:梦成了我真实的生活,生活则成了梦(288页)。也就是说,将前16章颠倒了看或许才是本来的面目。此处的焦点在于叙述者“我”的精神状况:“我”哥哥证实“我”有六年的时间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朋友们也都相信这一说法,而“我”也终于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来。为了说明这一点,本章提供了一些信函和日记,它们“彻底否定了我记忆的正确或准确”,至于情况是否真是如此,需要“让读者自己来判断”。比较有趣的是,有一本笔记本记录了“我”这部自传的草稿,与前面论述的隐含作者的焦虑相呼应,“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我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这份草稿“也许就是一部小说”,与实际存在的《恩主》那冗长的标题一样,“拟用的标题列在一起占了好几页,看得出来,作者是在尽心尽力,希望写出一部大作品”。(33)透过这份草稿,“我”本意要写的自传的内容与“我”已经讲述的内容彻底置换,是对讲述中的梦的清点,而在另外一封不知写给何人的信件上提到的信息不仅确认了草稿的内容,而且补充了已讲述到的生活的细节,这一切原来不过是梦中的情景。如果读者以为自己只是遭到了作者的戏弄,掩卷一笑,那么年轻的桑塔格日后也不会以常人难以企及的深邃和宽广的思想一再地引起轰动和争议了。事实上,“我”精神是否正常不是一个能够明确的问题,在颠覆性的结局中,何为梦,何为现实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我”在信函和笔记面前没有心慌意乱,在“考虑了很长时间以后,我坚持认为我当时没有精神失常”(288页),“我”认为自己不过是“古怪”而已,“我”的依据不乏哲学思辨的味道:也许古怪的人行动起来跟疯子一样。但是古怪的人有所选择,精神失常的人则没有……我认为我当时做出了选择,而且还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我当年选择了我自己(288-289页)。隐含作者借助“我”对不可靠报道的分析倾诉了个人的立场,重申了写作的自由选择。
《恩主》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之作,就像它虚虚实实的离奇情节一样,需要读者作出自由的判断。至于标题中的恩主是小说中的哪个人物,凡是通读小说的读者都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因为书中明确指出“我”乐善好施,在经济上经常对他人给予资助,“我”的作家朋友让·雅克屡屡得到我的接济,干脆直呼“我”是“老恩人”(238页)。遗憾的是,有的研究者在蜻蜓点水式的阅读之后竟然为这个简单的问题提供了风马牛不相及的答案——安德斯太太,这也许是桑塔格反对的一种劫掠式的阐释吧。桑塔格期待的自然不是空穴来风的解读,而是如洛佩特这样的评论:希波赖特,简言之,是空洞的。他很难说是什么人的恩主。他插手人们的生活,毁掉人们的生活……这也就是标题的反讽之处。(34)不得不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桑塔格离异后拒绝接受抚养费,携子在纽约艰难而倔强地为生计、为理想奋斗,在这个阶段完成的第一部小说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塑造出希波赖特这个充满着讽刺意味的恩主形象不啻是桑塔格起草的个人的独立宣言,她选择笔墨人生,选择独立自主的生活,从焦虑逐渐走向平静,与理想的读者进行智性的交流,这就是《恩主》的隐含作者所钟情的“罗网”,而她在这张巨大的网里不忘欣然呐喊:“写作,我至深的快乐!”(35)
注释:
①④⑤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108,88,88-89页。
②③(15)(34)Phillip Lopate,Notes on Sonta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9,p.37,p.135,p.37.
⑥(11)(12)(13)(16)(20)(33)苏珊·桑塔格:《恩主》,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中文版序,3,2,1,2,1-2,2,281页。
⑦⑨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77,36-37页。
⑧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159.
⑩(17)(18)(29)(30)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英国版自序,1,5页,译者卷首语7-8页,正文355,63页。
(14)阿尔伯特·莫德尔:《文学中的色情动机》,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6页。
(19)(26)(31)(35)Susan Sontag,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ed.David Rieff(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8),p.295,p.280,p.280,p.290.
(21)(22)(28)韦恩·布思:《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载詹姆斯·费伦、彼得·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67,63,65页。
(23)Liam Kennedy,Susan Sontag:Mind as Pass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37.
(24)Susan Sontag,The Benefactor(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63),p.21.
(25)译文参考《恩主》,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19页。其后引用皆用该参考译文,仅在文中标明页码。
(27)详见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玛汀:《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后〉》,载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41-43页。
(32)柯英:《狂想与沉迷:论〈床上的爱丽斯〉的性别反抗意识》,载《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108-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