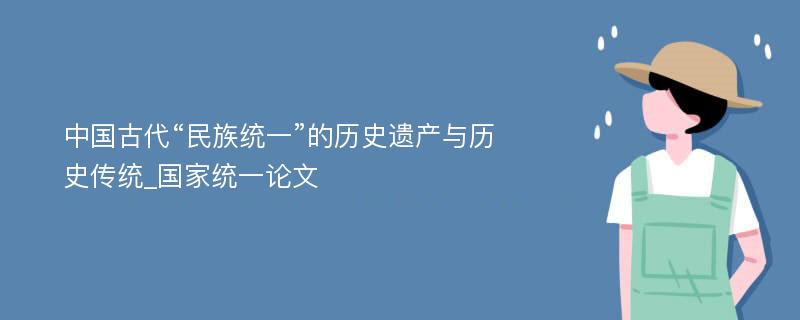
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中国论文,遗产论文,古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1-0132-06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后完成的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是当代中国“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以后,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的“重中之重”就是实现大陆、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合”,圆已经延滞了几代人的中华民族“大团圆”、“大统一”之梦。
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进行当代中国“国家统一”模式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进行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必须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清理和总结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从中汲取积极的思想营养。
一
自公元前2070年姒启建立夏朝,肇以“中国”为文明元点的“天下观”发轫,至1840年西方列强以资本主义文明的“血与火”叩开封建制的清朝“闭关锁国”之门,灌输给已经边缘化的近代中国以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世界观”,有近四千年明晰纪年的古代中国,虽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天下“定于一”的“大一统”却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价值观。
综观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即夏商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1年),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隋唐(公元589年至公元907年),元明清(公元1279年至公元1840年)。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三分之二略强。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即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三国、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五代十国、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公元907年至公元1279年)。分裂时间逾一千二百年,三分之一略弱。可以说,古代中国“国家统一”是主流、是常态,分裂为支流、为变态。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国家统一”史。
据考古学推论,中华文明缘起本土并多元,其凝聚力的核心是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汉族[1]。“三皇五帝”时期,华夏族已经兼容并蓄周围各异族,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实体,并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各部落联盟。夏商周时期,禅让制的“公天下”嬗变为世袭制的“家天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疆域已经“分土而治”,自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当然,这个大统一时期的所谓“国家统一”是幼稚的,其统一的范围、规模和程度非常有限,西周逾千诸侯国林立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案证。但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的“天下”统一观已经开始萌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已经成为西周有野心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憧憬的政治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春秋五霸的“弭兵”至战国七雄的“合纵”、“连横”,在诸侯“尊王攘夷”的兼并战争中,“中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各国的“分土而治”的封邑制也逐步向“分民而治”的郡县制过渡,各国内部的“小统一”率先实现,为秦始皇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因困厄于大分裂的政治现实,“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萌发。孔子“笔削”《春秋》的原则就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孟子释疑“天下恶乎定?”亦云“定于一!”(《孟子·梁惠王》)。在“百家争鸣”中,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视“国家统一”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具体阐述“大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尚书》的《禹贡》讲大禹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和“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周礼》的《职方氏》也讲西周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和“九服”(侯、甸、男、采、卫、蛮、夷、镇、番)。此一图景并非夏商周历史的写真,而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假借前人话语对未来“大统一”国家进行的理想设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古代中国第一个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统一史上的里程碑。秦朝直接辖土北至河套平原和阴山山脉,西至陇山和云贵高原,东与南至东海和南海,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所设计的“九州”的范围,基本上奠定了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以两河流域农业区为中心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秦朝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变贵族制为官僚制,“行同仪、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也基本上奠定了古代中国以华夏—汉文化为“正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定于一”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模式。
涉及秦朝的统一问题,有一个被有意无意湮灭的但是其重要性并不逊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年份必须重拾,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几乎与秦朝统一长城以南的各农业民族同时,匈奴的冒顿单于也消弭了蒙古高原的四分五裂状况,统一了长城以北的各游牧民族。古代中国以长城为界的农业区与游牧区“统一”的格局第一次分别成型,为逾千年后的元朝和清朝统一万里长城内外的农业区和各农业民族与游牧区和各游牧民族,实现中华各民族的真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说,秦朝是古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的发端。
秦朝虽然灭亡了,但其奠定的中华帝国的统一基业为西汉和东汉所继承并光大。古代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成就了汉武帝步秦始皇后尘的“南征北伐”,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县东北至朝鲜半岛(有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西南至黔、滇,南方至越南北部(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2]。西北在河西走廊打通以后,将西域也正式划入汉朝的版图。汉朝的疆界以秦土为基础,向四方展拓了近一倍,约五百万平方公里。
汉朝直接为“大一统”服务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统一模式也进一步彰化和强化,倡言“大一统”的“公羊学”成为朝野之“显学”,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提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滥觞,以华夏—汉民族、华夏—汉文化和中原农业区为元点的“道统”和“君统”合一传袭的“天下”统一观和合法性理论,成为影响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不可违抗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南方的各农业民族和北方的各游牧民族割据政权林立而征伐不休。其间,南方的长江流域和北方的黄河流域曾经出现过范围、规模和程度不等的多元“小统一”,包括西晋一度数十年的南北一元“大统一”,但是都没有改变分裂的主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中国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各农业民族之间、各游牧民族之间以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征伐不是弱化而是彰化、强化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战争中,各民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几倍几十倍地放量,大量游牧民族进出农业区,被农业化或将农业区游牧化;大量农业民族进出游牧区,被游牧化或将游牧区农业化。汉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逐步为中华各民族所趋同,在融合各农业民族成分和各游牧民族成分的基础上,汉族的人数越聚越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开始初具规模。
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各方无不以“中国”的统一为战略目标而进行征伐。为了其“大一统”的合法性,各农业民族和各游牧民族都溯祖“三皇五帝”,言其“授命于天”,以中华“正统”自诩。南北的多元“小统一”成为隋唐至元“大统一”的“前奏”。
隋唐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大统一时期。由于有“开皇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物质基础,隋唐两朝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气磅礴。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经济上的大运河和均田制、租庸调制,均是强化国家竞争力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功能的浓墨重彩。对于威胁到国家统一的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侵略势力,隋唐朝弃“守势”取“攻势”,文武之道张弛,一一荡平。唐朝的盛世疆域曾经西至咸海,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北纬18度[3](P57),约一千万平方公里。
五代十国割据和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对峙的近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大分裂时期。从此开始,传统农业区的汉族政权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的征伐都没有成功,不得不取“守势”,无力再圆汉唐的疆域,重铸“大一统”的辉煌。自14世纪至16世纪的明朝,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人”的“统一”王朝,其“统一”亦不出封闭的万里长城。汉民族的勃勃生命力被专心于“内圣”的宋明理学所阉割,忧患中不绝如缕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悲歌已经走不出狭隘民族主义的死胡同。
元明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四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在汉族政权丧失了“开疆辟土”的锐气后,天下“定于一”的“外王”之功就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胡骑”所立。在古代中国,是文明程度低的游牧民族而不是文明程度高的农业民族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南北的农业区与游牧区、南北的各农业民族与各游牧民族的“大一统”。当然,“边缘化”的游牧民族一旦将其统治重心转移至传统的“元点”农业区后,武力征服了“文化中国”的“新主人”就不可避免地被“旧主人”的“中国文化”所征服,逐步“汉化”和“儒化”,以谋其“改朝换代”并统一中国的“正统”和“合法性”。
元世祖所“开疆辟土”的元帝国之疆域版图超过秦汉和隋唐,是古代中国的最大值。北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西南则不仅将青藏高原正式划入,而且控制了现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3](P67-68),约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其中央集权制也由于各地行中书省的设立而进一步彰化、强化。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清朝时期走向巅峰的。一次次统一又一次次分裂,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近四千年的分分合合所积淀的自小至大、自弱至强的向心力、凝聚力终于将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华大地整合为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以1683年至1684年清朝收复台湾并设立台湾府为“收官”之作,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最后成局:北至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随着直接统治的行省制、间接统治的“羁縻制”和户籍制、赋税制这些中央集权政策的成熟,清朝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管辖权和控制力也达到封建社会的最大值。近代中国之中华民国、当代中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就是以清朝自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最后奠定的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为基础而勾勒的。
二
为什么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国家统一”史,“国家统一”始终是常态,是主旋律和不可逆的大趋势?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够孕育出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到清朝时期臻化为“大团圆”的鼎盛,为走向世界的接替者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历史的合力”!
第一,环境因素。在世界的几大文明发祥地中,中华文明是惟一没有断流的。一样的“大河文明”,自古至今,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恒河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古埃及人和古埃及语、古印度人和古印度语早已经消失在一次次被异族和异族文化征服的混血人流和烽火硝烟中。而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和凝聚力核心的中华各民族,分裂统一也好,“改朝换代”也好,则始终没有离弃他们的母亲河——黄河和长江。由于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如一座进出不易几近“封闭”的“围城”,中华大地四周的高山和大海是对外的障碍也是对内的屏蔽,所以,中华各民族的“大一统”基本上没有对外防患的压力或对外“中国化”的动力,是内敛的,演绎成局、成定势的难度小。
第二,政治因素。古代中国的文明之槛就是禅让制的“公天下”嬗变为世袭制的“家天下”。自夏商周至元明清,“王朝国家”的“大一统”的“主人”是汉族也好,是少数民族也好,其基本的政治选择都是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自秦朝至清朝的近两千年中,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以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达到极致。自三公九卿制至三省六部制,自郡县制至行省制,自羁縻制至改土归流制,显性的或隐性的“割据”离心力被逐步消弭,中央政府对地方及基层的管辖权和影响力、控制力与整合的疆域版图并进。夏商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演变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大一统”的政治现实。
第三,经济因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华文明代表了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与欧洲中世纪“割据”的、“封闭”的领主经济不同,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以土地私有制和“国”与“家”之间赋税徭役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的自然经济具有“早熟”的货币化、商品化、市场化的特点。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各经济区整合为一个“互通有无”、“以盈补亏”的“共同市场”。而庞大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机器和自夏商周逾千万人口至元明清逾万万人口的重厄,亦非“大一统”的“规模经济”不足以解。古代中国的几个“太平盛世”都出现在大统一时期。
第四,文化因素。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以华夏—汉民族和华夏—汉文化为“正统”而“化四夷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史。华夏—汉民族和华夏—汉文化在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和“和而不同”的中华各文化格局中的凝聚力及核心地位,为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先进文化的代表”的绝对优势所奠定。分分合合也好,“改朝换代”也罢,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始终是中华各民族趋同的主体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华夏—汉民族统一“中国”也好,“汉化”和“儒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也好,亦无不自诩“正统”之所在,天下归之,无不宣言“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来“合法”地消弭割据者“闰统”的离心力。
三
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正义性”是“道统”,不是“血统”。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以华夏—汉民族、华夏—汉文化为凝聚力和核心的中华各民族的“和为贵”。一方面,“华夷之辩”的标准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汉化”和“儒化”的“四夷”就是“中国化”的炎黄子孙;另一方面,“正统”与“闰统”之争的标准是“道统”,无论是华夏—汉民族政权“改朝换代”,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改朝换代”,其“顺天意”、“顺民意”者,均具“合法性”。秦始皇“平天下”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国家”,是“君权神授”而“替天行道”,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是“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元世祖、清世祖“平天下”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国家”,也是“君权神授”而“替天行道”。隋朝、唐朝修前朝“正史”——《南史》和《北史》,将前朝分裂的多民族的南北双方均奉为“中国”以“正统”传袭之,是“道统观”,不是“血统观”;少数民族“大一统”的元朝修前朝“正史”——《宋史》、《辽史》、《金史》,将前朝分裂的多民族的宋、金、辽三方均奉为“中国”以“正统”传袭之,也是“道统观”,不是“血统观”。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和辉煌的中华文明史就是“同心圆”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第二,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标准模式”是“武力统一”,而不是“和平统一”。没有所谓“仁”伐“不仁”的一次次战争,就没有古代中国的一个个“太平盛世”,就没有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就没有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大融合。自乱至治,自分裂至统一,“改朝换代”是战争,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的“四海归一”;“开疆辟土”是战争,如秦始皇的收岭南、汉武帝的收西域、清圣祖的收台湾。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武力统一”具普遍性,非“常态”的“和平统一”的“常态”是大军压境的“城下之盟”,如三国的西蜀后主的“乐不思蜀”和五代的南唐后主的“胡不归”。在所谓“仁”伐“不仁”的战争中,谁的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谁就是“王”,谁就是“仁者无敌”。
第三,古代中国“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是“双轨制”,而不是“单轨制”。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的五个大统一时期,除夏商周的“王”为“诸侯共主”,是“分封制”的弱势的“国家统一”,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都是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势的“大一统”。由于中华大地自然条件的复杂性,由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各民族的行政管理不得不“因俗而治”,自近至远,多种制度并立。所谓的“中心区”是直接统治,即自秦汉的郡县制至元明清的行省制,政策基本不变;所谓的“边缘区”是间接统治,如隋唐的羁縻制,元明清的土司制,以军事控制为主的都护府制和将军府制,政策呈“多样性”。在维护中华“正统”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授权”所谓的“特别行政区”或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包括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高度自治”),“土官治土民”,免赋税徭役,尊重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原生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
四
涉及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有一个基本概念必须厘清,即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天下观”,而不是“世界观”。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无论是统一为一个国家,还是分裂为几个国家,无论是汉族作为统治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所谓的“国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曰主权国家,都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体。在传统文化中,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就是文明的元点和惟一的文明社会“中国”并御四方或纳贡称臣或自荒自弃的夷、戎、蛮、狄。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其“天下观”是矛盾的、封闭的。呈强势时,“中国”就是“天下”,疆域无限;呈弱势时“中国”版图则仅仅容“华夏—汉族文明”和“农业区”,就是“中原王朝”。而且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放眼的“天下”大都是孤立的“惟我独尊”的“单极世界”,没有各国、各地区和各种文明“互动”的意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的意识。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最初为天子的都城或王畿之意。《诗经·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春秋战国以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就逐步演变为“华夏—汉文明”的代名词。秦汉、隋唐、元明清历朝历代均循此一“道统”为,“正统”。明朝时,中西交通,来华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开始称封建社会的明朝为“中国”,已经渐无尊崇之意;清朝晚期,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大潮冲击下而日益边缘化的清王朝亦自谓“中国”(即“中央帝国”,Central
Empire),不过是聊以“自慰”。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辖土有了明晰的边境线,其简称“中国”,才第一次演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法主体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内驱力并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
收稿日期:2003-07-07
标签:国家统一论文; 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民族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汉朝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隋唐论文; 明清论文; 经济学论文; 隋朝论文; 唐朝论文; 突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