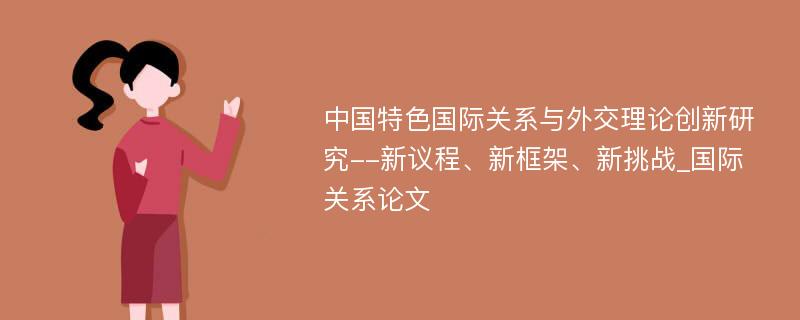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程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有关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政治影响的讨论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政治家、学者和评论家们纷纷发表相关言论,分析和判断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国际权力与财富结构和全球经济的影响。①但中国究竟将以何种方式影响世界,各种观点莫衷一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中国崛起的意义不仅是民族的、区域性的,更是全球的;中国崛起的形式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中国崛起的内涵不仅仅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力量投送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崛起,更应该是中国文化、观念、价值、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崛起。中国崛起的特征之一,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多元崛起的潜力。②综观人类历史,只有在物质力量、精神意识及价值观念等实现全方位和多元化崛起的大国,才是真正可持续的、足以引领人类未来里程的大国。作为这种全方位、多元化崛起过程的一部分,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应该实现“中国化”的崛起。这一新形势,赋予近十多年来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讨论以崭新的时代涵义。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关联与差别
在中国,通常的理解是存在着两个“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独立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外交理论”。这两种理论确实有所区别。“国际关系理论”是整体性地解释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现实及预测未来的知识体系,应当具有严格的学术性,其理论的范式发展、假设的提出和论证各种因果关联,是以政治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与界定的;而“外交理论”则是基于国家和政府对外交往的战略需求及利益需要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和政治含义。这“两种理论”存在着服务对象、评价体系及应用范围等诸多方面的差异。③
西方学者通常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为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背后的观念与认知的逻辑系统。④中国学者将外交理论置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具有深刻的“中国根源”:一是中国话语环境中“泛理论化”的现实,即中国人常常习惯于将重要的、具有思想统一性的观念直接等同于理论,并不深究是否真正具备“理论”的标准含义,⑤中国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外交思想、观念和指导原则就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二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背景变化巨大,中国外交从政策到思想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的不断提高,更是造成了“形势变化比预想得快”的新挑战。中国外交迫切需要在观念、思想上产生系统性的论述与解释系统。建立和建设中国的外交理论,反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指导思想“求新顺变”的内在需求。其根本动力在于摆脱形势变化迅速所导致的被动应付,在思想、观念和认知能力上“变被动为主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才从传统的“天下观”中惊醒,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枪炮、战争与掠夺强行拉进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从那时开始,一直存在着支配中国人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三大主流认知:弱国与历史悲情、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不仅中国国家定位从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兴大国”,而且,未来中国究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区域大国(regionalpower)、全球角色(g1obal actor)还是一个“全球大国”(global power)?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中国不断更新和发展自身的外交思想与外交指导原则背后的认知系统。⑥中国外交的“理论化”努力就是要依据中国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利益,确定中国外交新的认知要素和观念体系。这一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是要借以确立中国的利益观念,通过对国际规范的学习和总结,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关系清晰而又科学的认知。⑦
这一任务是艰巨的。中国外交的理论化努力或者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工作不仅需要对新中国外交思想与指导原则的总结与发展,更需要反映政府和社会这两个方面对国际事务与世界政治的关切,需要科学与准确地分析与把握中国面临的时代环境。与此同时,这一理论将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如“礼”与“仁”的思想,重“关系”而轻“利益”的处事方式),总结中国古今外交思想与实践(如王道/霸道、朝贡体系),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适应性,并最终对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与战略选择形成一定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在民国还是新中国时期,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程一直受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是世界发展潮流的冲击与对中国外交理念的“外生性”冲击,二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文化与社会行为对中国外交的“内生性”影响。中国外交实践基本上是这两种力量碰撞、妥协与融合的过程。⑧结合这两大“力量”,依据中国的利益、推动中国所认同和可以贡献的规范,进而形成和确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认知系统,是理论“中国化”创新进程的重要环节。
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一方面,不仅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基础上的“中国化”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外交理论的“中国化”提供智力支持,也是外交理论不断更新与发展的“台阶”。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的界限。动态地对全球事务所做的国际关系研究、并进而形成的理论积累,是得以科学地认识和解释外交事务的依据。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教授甚至认为,整个国际关系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因为无论是经验性实证研究、规范性的学理研究还是政策性的对策研究,其本质都是为了丰富与完善世界对国际问题与现象背后的规律、法则与支配力量的研究。⑨对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前沿的了解和把握,并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寻找中国的“适应性”,不仅是发展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后西方”(post-West)进程的需要,更是从中国的定位和认识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中国贡献”的需要。⑩
另一方面,外交理论的“中国化”创新研究同样也是推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对外交政策从观念到实践的总结一直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动力。(11)第一个成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雷蒙·阿龙(Lemon Aron)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就是在深刻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形态冲突与两极对抗格局的新局面而产生的,是在批判性地总结西方国际关系历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能够成为西方大国外交实践的主导原则,同样是因为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在当时最大限度地符合了西方大国的外交利益和战略目标,并对自己的理论保持开放立场,甚至部分兼具了“康德主义”的要素。(12)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理想——让自己的思想成为“外交行动的基础”、用于规范和指导外交实践,更是成了现实主义流派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新古典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的特色。
开创了美国和西方外交现实主义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外交理论。外交理论远比一个时期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要复杂得多。外交理论不仅是一个“科学范畴”,更多地还是一个“政治范畴”,需要兼顾政府形象的塑造、政策合法性的包装、政治动员所需要的道义力量,以及在对外行动时如何占据“道德与法律高地”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古典现实主义可以直接将道义因素列为权力的从属性因素,而美国外交永远都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个“面”的根本原因。这种兼顾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面的外交实践哲学并非美国独有,几乎所有国家的外交原则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设计和实施的。
然而,即便外交理论侧重于政策领域,同样需要国际关系理论这一知识领域的指导和支撑。任何强大的、有生命力的外交理论都必须兼容“科学范畴”和“政治范畴”这两个系统,需要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扩大国家外交哲学的科学内涵。国际关系理论则是“科学范畴”与“价值范畴”的结合,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研究是外交理论作为“科学范畴”的保障和源泉。然而,任何有关国际事务的理论性见解并不自动带来外交实践的进步,外交实践需要的理论规范同样必须符合外交领域的规范和要求。(13)
时代的变革、国家实力地位的变化及国际关系研究对新的全球外交实践的总结,常常带来外交思想的革新和扩展。最重要的是,外交思想和指导原则必须经常反映和跟随国际关系研究和理论总结的更新步伐,才能真正地实现“进步”。(14)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后冷战时代的多边主义研究的迅速兴起,推动了多边主义话语在外交领域内的迅速扩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交理论总是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常变常新而不断调整、充实和加强。由于政府施政方针、权力背景和领导团队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政府具体所使用的外交主导方针,常常表现为对更为宽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选择性运用。因此,在进一步回答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的关系时,必须研究的问题是:世界各主要国家是否存在着自己独特的外交理论?如果有,那么这些国家是如何来构建外交理论的?它们又是怎么更新的?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有自己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那么,这些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又是如何“理论化”的?与学术意义上所说的国际关系理论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例如,在美国并没有独立于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外交理论”,但不同的政府都有自己的外交实践的理论支撑和理论侧重,美国是如何来解决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思想与原则之间关系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结论可以成为建立起对实行外交思想所需要的国内共识,成为一种外交原则是否能够成型的理论论证过程。
二、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角度与方法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和对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过去30年间有了巨大进步。对于起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介绍和分析已经基本成型,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开始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首先,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的“国家定位”问题。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国家不仅构成了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必然在“单位层次”上产生各种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国家根源。研究中国理论的“国家定位”问题,不仅是研究中国利益、中国战略、中国风格,同时也需要研究影响与决定政策与观念的“中国变量”。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外交历来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一边倒”到“一条线”,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三个世界”,从“反霸”到“不干涉原则”,从“坚持问题的是非曲直出发”到“韬光养晦”,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些中国外交的“特色”是与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基本认识和判断相结合的,反映的是在一个充满冲突与竞争的“权力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对于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认识和选择。这些思想和指导原则体现了托马斯·C·谢林(Thomas C.Schelling)所概括的以计算收益与成本为核心、主要追求物质成就、关注国家间博弈为主题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思考方式。(15)今天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中国不仅与世界的关系在变,自身的发展需求更在变。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在思考和研究方式上必须超越单纯“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局限,将目光不仅紧盯理论的“理性主义”范式,同样也需要关注“理念主义的”(ideational)、以社会化进程和认同培养为导向的国家行为和利益的思考方式。例如,“和谐世界”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积淀的社会认同。“和谐世界”理想的实现,本质并不取决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而应该取决于是否能形成以“和谐”为导向的共有观念。(16)如何从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家利益与战略需要的角度,从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的角度,完成对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国家本位”建设,仍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例如,西方眼中未来的“超级大国”的中国又如何定位未来的国家目标,在外交与防务能力发展进程中如何整合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中国应如何打造各部门配合紧密、反应灵活、对策有效的“国家安全机制”?中国应该如何适时而又灵巧地使用“胡萝卜”和“大棒”,在确保有效的战略威慑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利益?这些问题不仅在政策层面存在着争议,在理论层面更有澄清的必要。
其次,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价值定位”问题。任何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都必然体现出某种价值,例如,美国对外政策常常强调反映美国人对自由与人权的尊重。而中国外交的“和谐世界”观念本质同样是基于中国历史与传统的价值表达。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吸收和反映多元价值的存在。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导向过于强烈,在一个全球政治时代,这往往会驱使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过于追求权力和“高位政治”(high politics),而忽视全球事务中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和人文关怀。另外,中国没有完成国内体制变革同样给中国看待世界方式带来了诸多复杂的影响。(17)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必须思考,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应当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定位”,这关乎我们对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看待自身国家利益等问题的基础性思考。此外,我们也需要思考国家间是否真正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这关系到如何认知“价值”特性、任何处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关系等重大问题。
第三,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标准定位”问题。“标准定位”带有两层含义,一方面针对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用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和原则的“理论化”。首先,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我们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标准体系”评价和筛选研究成果。“标准定位”还能够起到规范研究、鼓励争鸣的作用。其次,中国外交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我们的研究需要全面了解和深入认识这些指导思想和原则。但是同时,也需要结合当前和未来国际关系发展及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制定相应标准,对这些外交指导思想和原则进行检视和修正。例如,我们过去常常习惯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划分“敌我友”,但目前在不同的议题之下(反恐、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国家阵营的划分也表现出变动不居、含糊莫辨的特点。此外,也应认真思考“多极化”国际格局可能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做出明智而又长远的战略选择。
为此,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去寻找突破点。
首先,探索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中国视角”。在什么议题上和什么范围内中国的崛起能够更新和发展现有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的理论认识,这是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中国化”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例如,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而权力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军事同盟的重组和通过战争来重新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但在21世纪的国际背景下,大国战争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国所强调的和平崛起,就是要打破国际政治中“崛起引发对抗”的固有成见和历史模式,开创在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实现权力结构变动的崭新历程,实现大国间的“双赢”局面。“中国视角”代表了中国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以往大国崛起常常引起大国冲突或者传统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假设,按照中国特有的战略思维、制度机制和思想观念,重新审视以往的理论积累和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外交哲学。例如,研究表明一个崛起的中国更愿意尊重、而不是挑战国际关系现状,中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适应性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崛起的全球政治结果更趋向于合作、而不是对抗。(18)
其次,分析和概括“中国经验”。现有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主要是源于西方的历史、宗教及哲学等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来自“欧洲经验”(如宗教战争)和“美国经验”(如霸权稳定和国际制度),同时也为解释和维护既有的国际体系服务。目前,中国对外交往不断扩展,对世界事务影响力日益增强,总结“中国经验”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理解,亦能为描绘世界政治的未来发展图景提供启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事务影响的日益扩大,具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中国必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变革性因素之一。(19)
如果今天的国际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是由过去400年历史进程中西方的主导地位来形成的,那么,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来重新审视和分析“西方中心主义”模式下的国际事务的理论总结和经验依据。例如,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和意识形态常常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并非是战争的根源。西方认为“文明有可能导致冲突”,而中国认为“文明的多样化”有助于“世界的和谐”。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究竟如何才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中建立共存?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否可以在理论和外交事务中都可以被超越?抑或价值的差异是根本无法超越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理论创新研究和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再次,探讨紧扣未来中国战略需要与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兼容世界发展、稳定与繁荣大局的“中国特色”。一个国家的成长经历、文化、传统及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常常主导一个国家的“外交特色”。而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特色则不仅同“国家特色”有关,更与该国家看待国家利益与外部世界及基本的战略选择有关。(20)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需要依据中国的国家利益、未来世界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确立以“中国特色”为导向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规划。这一“中国特色”既为中国和平崛起贡献理论支持,也为中国外交与国际行为提供智力支撑。
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框架与结构
“中国特色”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紧紧把握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国家发展中,去寻找创新性理论研究的依据和内涵;二是应该时刻把握时代特征、世界进步潮流及中国旨在争取推动全球政治走出大国冲突历史窠臼的战略需要,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中国特色”并非是单纯的反映中国人的看法,或者反映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国家利益,“中国特色”首先应该反映在我们有高度明晰的理论的“国家定位”,能够深入反映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对理论的“价值追求”,并能够在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建立和发展中国评价和筛选理论研究成果、在规范化基础上深化学术研究水平和队伍建设的“质量标准体系”,鼓励不断涌现和产生高质量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科研产品,引导建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团队。这样,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一定能真正产生“中国特色”,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一定能不断保持其创新性。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可以在以下的框架中去寻找未来重点研究的具体日程。
(一)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适应性
通过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梳理和总结,分析“西方经验”基础上的西方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可能不适应中国的发展,而哪些已有的理论积累适合中国的理论建设。通过对当前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与外交理论的比较研究,总结和发展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应该具有的“理论化”进程。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俄罗斯、英国、印度、法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为此,进行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弄清世界主要大国在看待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应该探讨和总结究竟什么是“中国经验”,即影响和主导中国国际行为的权力结构、科学技术、地缘政治及其他各种变量关系,究竟如何能够打破已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积累和因果系统,并以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的和平、合作、进步与共赢的实践,来推进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多元化发展。此外,一些原本就没有进入既存国际关系理论探究视野的现象和问题,也将是产生创新性的研究重点所在。例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积极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国际体系,这种近似悖论的现实如何解释?此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颇具特殊性的中国在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交往时难免产生归属困境与认同危机,这种棘手难题如何处理?“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peace)或者“主导国家和平论”(leading power peace)究竟如何能建设性地结合进中国的外交思想?
(二)世界主要大国外交思想与外交理论比较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这是比较和研究美、英、法、日、俄、印度等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总结和剖析中国近15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特色”争论,明确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可以建立和发展什么样的“国家定位”问题,回答在国际关系的实践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究竟如何相互配合和相互联系的问题。同时,重在立足于“中国国情”,就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如何发展未来的“中国特色”提出系统的研究结论。
理论的“中国特色”必须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更需要在“国情”基础上科学和准确地分析和认识什么是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应该争取的发展轨迹,中国可以综合运用的政策手段,以及中国可以达到国家目标等大战略层面的思维。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特色”都与其“国家特色”紧密相连,中国也不例外。美国外交的干预性“自由国际主义”,欧洲外交的价值主导的“民主自由主义”和中国外交的多元共存的“国家中心主义”,形成了三种颇具代表性的“外交特色”。缺乏对中国“国家特色”的研究,便无法准确定位和构建中国的“外交特色”。中国“国家特色”既包括对当下国家实力、政治体制及资源潜能的评析,也应涉及对未来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各种挑战及国家目标的预判。例如,当今世界民族与宗教问题日益突出,而恐怖主义危机也多因此而起,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如何在“反恐”进程中汲取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的教训,并形成自己的“外交特色”,运用“巧实力”(smart power)便是需要着重思考的一大问题。为此,理论的创新研究需要从符合中国未来利益和战略的“国家定位”出发,突破现有的理论窠臼。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研究,应该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新的共识建立的过程。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未来究竟想要成为及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中国的国家期待决定我们的行为、还是中国的战略环境塑造未来的国家行为,或者是中国的“精英认知”主导对外行为?但至少,“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兴起正在增加中国外交政策分析的多样化。这同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外交理论说到底是一种“政策哲学”。确立中国外交的政策哲学,不仅需要了解其他大国的外交理论,也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崛起与世界战略格局之间互动关系,能够对这种关系进行比较准确的描述与总结,探讨中国对国际制度、大国关系、区域合作、国际安全、世界意识形态和宗教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可以建立起的理论认识。同时,也需要从其他大国的兴衰存亡的经历中寻找中国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反映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中来。例如,什么是中国可以不断建设和发展的“软权力”?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可以给世界带来具有什么样的感召力的“中国梦”?
(三)理论的“中国特色”: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
此项研究需要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2000多年来的中外关系史里程,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中探索“中国特色”理论的内涵,其目的在于发现和整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特别是以往东亚秩序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认识,以便从中找出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研究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同时,需要通过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从中找出并发现中国已有的外交实践能够给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创新带来的宝贵经验、思想财富,分析新中国外交已经形成的理论性总结,并研究和寻找中国的外交实践所要求的外交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原则。其重点是根据今天中国外交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任务,总结新中国外交史给中国外交所提出的理论使命和所要求的理论贡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外交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宝贵财富。例如,传统的“天下观”、“怀柔政策”、“朝贡体系”表现出了中国人“重关系”、“重次序”而不是“重实地”、“重实利”的思想认识。再加上中国人历来强调的“王道”和“霸道”之辨,这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的对外关系认知,反映的是中国人具有历史传承性的集体心理和行为认同。即便在今天中国外交实践中,也能够找到其或明或暗的痕迹。(21)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外交关系的历史模式与现实意义的分析始终存在着争议,但中国人基于自身文化与传统而形成的传承日久、根深蒂固的文化品性和集体认同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发展中具有何种意义?(22)中国对外关系多大程度上在受中国的“战略文化”的影响?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过程中如何吸纳和利用这些挥之不去的思想资源?作为中国扩展“软实力”的象征之一,目前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可否考虑在传授汉语技能的同时,适当地介绍中国上述外交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来说,这种中国人从传统就开始延续的行为认同,如何可以在今天全球政治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和发展?是否存在着一种可以基于中国人“集体主义”的思维与行为价值基础之上的外交理论?显然,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四)中国的国际环境:利益、形象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应重点研究国际关系与世界事务今后有可能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及中国所面临的新任务,这些研究既有政治性的,更包括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所进行的分析,这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今天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例如,多极化的趋势未来究竟能出现什么样的演变;多极化是否就一定有利于中国持续的稳定和发展?未来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在中国崛起的今天,究竟什么样的形式更符合中国利益?
该项研究议程是为了深刻而又全面地把握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的国际政治经济根源,研究国际经济与金融局势的演变究竟给世界事务、外交实践及国际关系理论课题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剖析国际体系和国际战略格局未来的演变,围绕一个自身实力增强,但对外部市场、资源和能源依赖更深的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政策调整、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和未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财富与权力结构等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当前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将对中国自身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美元地位的相对下降是否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形成助力,中国应当在未来国际经济机制和秩序的重建中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为此,需要准确地定位和展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地研究世界政治当前的现实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演变图景。重点是要深入和系统地论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中国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世界权力结构、国际制度与未来中国的外交走向与安全努力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在这方面,加强对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实践、法制主义的研究,是理论创新应该大力投入的重要内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发展认识中国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探讨在现存的共同利益之外,是否有可能建立各国可以相互认可的共同价值,中国的崛起究竟将会有助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权力结构,全球市场、能源和资源供求关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应该如何设计与实施等问题。
四、结论
时至今日,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建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的重大现实意义。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既是发展中国人开阔、高远的国际意识的需要,也是同欧美话语霸权相抗衡的需要,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继往开来的需要。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特点鲜明的外交思想和指导原则。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期待的显著变化,这些思想和指导原则如何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的外交需要,并对今后的外交实践具有前瞻性的规范意义,迫切要求中国的外交理论在“科学范畴”和“政治范畴”中进行创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科学范畴”和“价值范畴”中升级,实现秦亚青教授所说的,将“行动导向”的理论与“知识导向”的理论的结合。(23)中国在发展,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总结需要发展,支撑中国外交在新时代、新环境和新任务中继续保持“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更需要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的基本的目标是能够形成一整套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分析和支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主张,拓展和深化中国人的国际视野,科学和准确地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与实践理论化。这些创新应该反映和表达中国政府与社会的主流关注,体现中国不断调整、摸索和发展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追求,切实代表一个崛起的中国对国际与外交关系的系统理解,这将不可避免地打上的国家和时代的烙印。
注释:
①美国有关中国崛起及其世界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分析中国“今后究竟想要干什么?”代表性的作品有: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Winter,2003,pp.5-56; Aaron 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Summer,2005,pp.46-83; 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Spring,2006,pp.81-126;二是研究中国“国内变革究竟会让中国做什么?”代表性的作品有:M.Taylor Fravel,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James Mann,The China Fantasy,London:Penguin Books,2007; Avery Goldstein,Rising to the Challenge: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三是探讨“世界与中国的互动究竟能让中国做什么?”代表性的作品有: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1980-2000; Evan S.Medeiros,et al.,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anc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 Press,2008; Robert N.Ross and Zhu Feng,eds.,China's Ascent,Power,Security and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Jeffrey W.Legro,"What China Will Want:The Future Intentions of a Rising Pow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5,NO.3,2007,pp.515-534.
②Jonathan Spence,"China's Rise: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sia Society Speech Series,March 16,2006.
③近20年来,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外交学”的研究和贡献颇为深入。但“外交学”并非“外交理论”,“外交学”更倾向于对外交实务、制定和执行外交原则和目标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概括。参见〔英〕克里斯托夫·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陈寒溪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序言。“外交理论”则是支撑和反映这些外交原则、目标和使用手段的观念和认知的逻辑系统。
④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总结视为为各国外交政策提供对不断变化中世界局势及时、深刻的认知系统的代表性作品,请参见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5th edition,New York:Longman,2001; 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Pluralism,Globalism,and Beyond,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98; David Boucher,Polit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⑤关于中外学者对“理论”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参见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0页。
⑥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153页。
⑦在“行为者”与“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当今的国际关系存在着三个不同、但又彼此关联的世界:“利益的世界”(world of interests)、“规范的世界”(world of norms)和“认知的世界”(world of identities)。这三者的关联决定了一个国家从判断、到决策、到行为的过程。参见:Daniel N.Nelson and Laura Neack,eds.,Global Society in Transition: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er,Lond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 Daniel N.Nelson."World Shift:Interests,Norms and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9,No.2,2002,pp.353-359.
⑧笔者的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牛军教授的启发。
⑨Hedley Bull,"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19-1969," in James Der Derian,ed.,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182.
⑩国际关系学术界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都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依据西方的文化、历史和为了保证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能够糅合非西方的国别经验和文化传统,是理论能够多元化与深入发展的必要。因此,“后西方”时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就是强调不是单纯在“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基础上对西方主流理论的批评,而是要依据“非西方经验”进行创新。参见:Giorgio Shani,"Towards a Post-Western IR:The Umma,Khalsa Panth,and Critic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4,2008,pp.722-734.
(11)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认为,外交实践不单是理论研究的“经验来源”,更是理论得到检测和发展的牵引力。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Vol.51,No.1,October 1998,pp,144-172.
(12)Murielle Cozette,"What Lies Ahead:Classical Realism on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3,2008,pp.667-679.
(13)琼·霍夫(Joan Hoff)在总结布什政府外交失败时指出,新保守主义理论的信奉者搞混了理论上的“唯美主义”与政策实践上永远的“缺陷主义”。Joan Hoff,A Faustian Foreign Policy:From Woodrow Wilson to George W.Bush,Dreams of Perfectibilit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01.
(14)理论与观念范式的不断更新通常被理解为是国际关系与外交实践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而并非只是单纯的增加道义因素。参见:Colin Elman and Miriam P.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3.
(15)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
(16)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范式认为,世界的“和谐”本质只能产生于稳定的“权力结构”。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McGraw Hill Companies,1979,p.13.
(17)"The New World Order:How China Sees the World?" Economist,March 21,2009; Minxin Pei and Jonathan Anderson Debate Beijing's Rise,"Are China's Fifteen Minutes Up?"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000,March/April 2009,pp.13-30; Susan L.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8)Scott L.Kastner,"Glob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4,2008,pp.786-794; Christopher A.McNally,China's Emergent Political Economy:Capitalism in the Dragon's Lair,London:Loutledge,2008; Jeffrey Lewis,The Minimum Means of Reprisal: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in Nuclear Age,Cambridge:MIT Press,2007; Avery Goldstein,Rising to the Challenge: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Alastair l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 ,Spring,2003,pp.5-56.
(19)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基于中国文化、历史和制度观念的“中国选择”或者“中国模式”及其国际影响的研究正在方兴未艾。代表性的作品有:William A.Callahan,"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Post 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4,2008,pp.749-761; David C.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New York:Routledge,2008.
(20)有关对美国外交与战略观念的“美国特色”的分析和总结,请参见: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Tony Smith,America's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21)“战略文化”是研究一个国家观念与行为模式的一项重要的研究议程。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中国的战略文化的研究,请参见:Huiyun Feng,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Confucianism,Leadership and War,London and New York:Loutledge,2007; Alastair l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China's Strategic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22)除了“战略文化”之外,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政治文化、建构主义理论中的“观念”文化在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开拓的重要研究领域。已有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请参见:Lucian 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Ann Arbor:University Michigan Press,1991; Valerie M.Hudson,ed.,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7; Valerie M.Hudson,"Cultural Expectations of One's Own and Other Nations' Foreign Policy Action Templates," Political Psychology,Vol.20,No.4,1999,pp.767-802.
(23)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理论创新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新挑战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学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