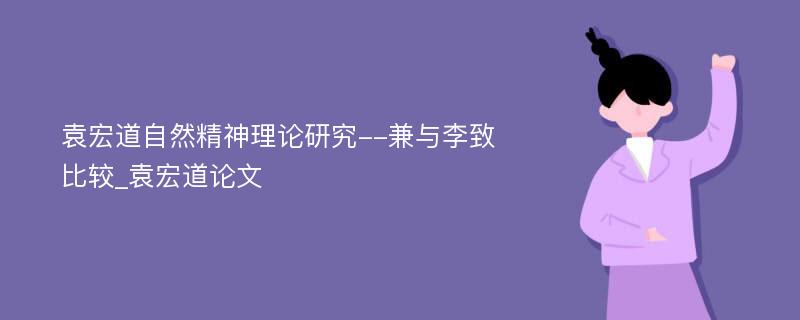
袁宏道性灵说研究——兼与李贽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李贽论文,袁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袁宏道深受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认为性灵是构成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真则是使人的性灵外化为文艺作品的特定形式,质又是表现真的特定方式。李贽的理论具备了作家论的基本框架,袁宏道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作家论,整理出了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结构——生产、流通、消费——相适应的作家、作品、读者的文艺运作结构,为其后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袁宏道 性灵说 童心说
明末是思想文化变革和经济变革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萌芽,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领域,出现了以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尤其是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是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艺理论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深入探讨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一、性灵的涵义
关于性灵,除了袁宏道以外还有很多人也曾探讨过,但它所具有的涵义却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袁宏道的性灵也跟他们有所区别。他的文学主张主要反映在他的性灵论之中,因此,探讨他的文学主张的时候,阐述他的性灵之涵义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他所主张的性灵,到底具有什么涵义?这不仅与当时社会盛行的思想体系有关,也与袁宏道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而且,在明末很长一段时间持续讨论关于性灵的问题,也对他的性灵说的形成有密切联系。他讲的性、灵与宋明理学的性、情很相似,二者既各具独立性,又相互联系。因此,从宋明理学着手探讨袁宏道的性灵的涵义,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很必要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把心分为“性”与“情”的,是宋代的张载。从张载首次提出,到朱熹集以大成的“心统性情”说,把“心”分为“性”与“情”两个部分,认为“性”则“天理”,来自于本体世界,或云“未发”,或云“道心”。它包含着“仁、义、礼、智、信”等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是纯粹的理性;“人心”者,“情”也,亦云“已发”,它所指的是“善恶,辞让,是非”等主观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因此,应该把“性”和“情”的区分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等同地看待。但是,朱子进一步发展了“性”与“情”的区分;提出心应该包括“性”“情”的观点。他讲“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心者,充性情之主”[1]。这种宋明理学的“性”与“人心”两者中“性”主宰“人心”的主张,到王阳明时有了变化,“道心”依赖于“人心”的思潮开始占了上风,也就是说,原来的理非心变成了心则理,伦理性的规范也越来越向心理上的需求转化。“心即理也”中的理,也越来越从外在的天理,规范,秩序转变为内在的自然、情感,乃至欲求。这也正是朱熹所担忧的“只言知觉者,……弊在于把欲求为理”,然而,这就是向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人性是人类自然的情欲、需要,欲望——发展的过程。
根据上述的思想背景,规定袁宏道性灵涵义的关键在于他对人生的态度。袁宏道是为了做官,才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的,他的生涯是隐居与居官相互交替的生涯。当时要做官必须学习朱子学。因为那时朱子学是官学,所以,他长期的官僚生涯是离不开朱子学的。但是,他通过袁宗道接触到了把儒、佛、道三者合为一的新学说——“性命之学”,并且,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撰写了《广壮》——“新一部《庄子》”——阐述了儒、佛、道三者合为一的“性命之学”理论。袁宏道力争想以“性命之学”来解脱儒家一贯的绝对性。他与李贽交往,又曾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这些与袁宏道的性灵说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对于他来说,既能过儒生生活,又能采取用某种方式表现性命之学和心学,是很重要的,这些恰恰表现在他主张的性灵说之中,他追求三教合一,却又因官僚的局限性,他的性灵说未能脱离朱子学的范围,只以佛、道、心学等来表现,尤其是把重心放在心学之上。即,与张载区分的“性”与“情”非常相似,把“性灵”分为“性”与“灵”,认为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即“道心”和“人心”是同样的层次。问题在于,“性”和“灵”与宋明理学的“性情”主要差异表现在“人心”部分,在上面也提到过,宋明理学中的“情”包含“善恶,辞让,是非”等主观的情感和心理状态,是群体的道德意识,与此相反,袁宏道的“灵”指的是“私心,情欲等个体的感情”。因此,袁宏道的“性灵”区别于“性”主宰“情”的宋明理学,又区别于“性”依赖于“情”的阳明心学。在官僚生活,以及从地方到中央的升迁过程中,袁宏道积累了朱子学派的思维方式,并深受李贽、徐渭的启迪,进而形成的心学派的思考方式,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对性灵的追求;等同地看待“性”与“灵”,和以“灵”为中心的两者之间的和谐。这一点,在与李贽的交友过程和袁与李的差异中显得更为明确。下面是袁宏道评李贽的一段话,这也正是李与三袁的不同之处: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稚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汨没类缘,不断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展,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2]袁宏道虽深受李贽的影响,他常把李贽比为释伽或老子,但不久就觉察到了与李的间隔,开始疏远了李贽,并且,李贽自行了断以后,便对他无所涉及,这可能与他多年的官场生涯有关。李贽一向是逃避群体的道德意识,甚至对此持有否定的态度,而且,他是因政治的迫害而自杀的。所以,袁宏道这时也难对李贽表示关心。由此可见,袁宏道的性灵说在对待个体的感情上没脱离群体的道德意识。他认为“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强调了情与灵的相通,李贽也曾提及过与袁宏道的性灵相近的概念—“自然之性”。如前所述,袁宏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倾向心学,而李贽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禹在镐《袁宏道诗歌研究》48页1991年8月汉城大学博士论文),把哲学体系的重心放置在心学之上了。在他的内心儒学和心学的强烈对立,使其生活空虚,他便以佛学作为自己的志向。当时朱子学作为官学制御着人的欲求,然而,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人心的肯定越来越突出。问题在于,与李贽的自然之性的关系,他的意识形态来自于单纯的体系“修身能治国,明明德能自亲民”。不过,他与袁宏道相比在官场的时间较短,做官也就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因此,没有太多地受宋明理学束缚,尤其是在接触心学之后,李贽的意识形态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以心学为据反叛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儒学思想体系,肯定了人的感情,甚至肯定了食欲、色欲,表现出了向极端发展的个性。李贽内心的儒学和心学的对立,促使他选择了脱离现实的道家的人生,促使他去追求佛家的解脱,因此,他的自然之性中的自然显露出肯定个人的情感和欲求的心学倾向,反映了未完全脱离儒家概念的矛盾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心安理得的状态应该是对个体感情与欲求的极端的肯定,也就是说,对包括食欲和色欲在内的所有欲望肯定时才有可能实现,因而,他认为性是天赐的秉彝,也对此寄予厚望。
总之,如果袁宏道的性灵所追求的是以灵为主的性和灵的和谐,那么,李贽的自然之性是未完全脱离儒学的极端的心学志向。虽然两者都以心学为中心,但两者间存在着差异,主要的原因在于两者间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不同的人生观。
二、性灵与真
袁宏道追求以灵为主的性灵之和谐,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性灵学向文艺方面发展的方向。因为,他的性灵决不是为挣脱传统儒学的束缚,强调灵所表现的对个性、情欲、自我需求的志向。因此,他只能探论与政治不相关的文艺主张。当时朱子学派认为,文学是道之末,只不过是传统儒学的道具而已,但是,袁宏道、徐渭、汤显祖等“没有去把传统儒学强调的人伦教化强加于自己,也没有从属于它,却标榜争取自身的独立性,公开要求‘文’与‘道’的分离。不过他们还是持有“名教才是极乐”“劝善惩恶的补充”等观念,还没完全丢弃儒学的美学观。袁宏道也不例外,也只能在朱子学的保护伞下表现心学。他注重个人情感,主张性灵说,以内容而论足以成为他的文艺主张,其中,他能够把性灵和诗创作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是因为诗体本身的特殊性与性灵的涵义较为一致。
袁宏道说:“其为诗异甘苦,其直写性情即一”,他以表现性情的方式谈论诗。他认为诗应该能够把作者内心的欢乐与悲痛象征性地表现出来,散文应该能够把作者外在的现象叙述性地表现出来,根据这些,散文可分为雅与俗,但是,不管什么文体,都具有共同点,那就是“真”。这一点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真与性灵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下个部分要讲的质也与他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未曾把性灵与真相提并论,但是,从在他经常探讨的真中也可以推断出与性灵的关系。
如果先讲结论,袁宏道指的真与其说是单纯的真实性,不如说是性灵即将展现在作品之中时的状态。也就是说,真,意味着性与灵的存在,成为文学创作的依据,因此,“我与曾可前相同之处只能是‘真’”。在这里,性灵,是构成人内心的因素,真,是性灵成为具体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因此,性灵只有通过真,才能表现出来,又因灵之间的差别,表现在诗、散文等不同形式中,就会产生“甘”,“苦”,“雅”,“朴”等不同的特点。公安派一员雷思沛称“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强笑者不欢,强合得不亲。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这句话说明的不仅仅是单纯地追求文学的真实性,袁宏道在文艺创作中谈论的真不是认识论层次上的真实性,而是性灵即将转化为文艺创作时的状态,是“精诚之至”而显现的性灵的存在形式,根据以上的思路他对真诗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旦夫天下之物,孤行即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即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即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尤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愁极即吟,故当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3]在袁宏道看来,性灵的面貌应该是“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因为,他讲的当时的诗文依据的是带有恢复汉传统目的的创作理论,复古主义十分强烈,诗,很难反映性灵的全貌,“雷同即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即虽欲存焉而不能。”在上面对诗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真,是没有超出任何本体意义的也没有对性灵附加任何含义的文学创作的根据。
袁宏道的性灵和真两者的关系与李贽的清净之心和童心两者的关系十分相似。但是,李贽却追求通过“文”来实现“道”,把诗歌创作过程当作为明明德的修身过程。如果修身是为觉悟内在本质的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进程,那么,诗是这种内心的流向借助语言所体现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李贽的清净之心和童心与袁宏道的诗论虽有相近之处,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李贽认为清净之心是童心产生以前的状态,是童心产生的基础。如果说清净之心是心具备具体形态以前的状态,那么童心就是具备具体形态的心,即文艺创作。那么,自然之性与清净之心到底有何关系呢?概括地讲,只有把自然之性作为基础,清净之心才有可能实现。李贽说:“清净本原,即所谓本地风光也,视不见,听不闻,欲闻无声,欲嗅无臭,此所谓龟毛兔角,原无有也,原无有,是以谓之清净也,清净者,本原清净,是以谓之清净本原也,岂待人清净之而后清净耶?”[4]所谓的清净,指的是无任何事物或无任何打扰的状态,如一面镜子,静静的湖泊;因为一无所有,就“不能丢、弃、放置”,这种清净之心因某一对象的作用而转化为与文艺创作直接相关的心,所体现的状态就是童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性灵与清净之心是非常相似的概念。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5]李贽讲的童心,与其简单地解释为“孩童之心”,不如与“明明德”的倾向联系在一起解释更为妥当。他称童心为“最初一念之本心”,强调了“初”的重要性,如果与他所强调的自然之性联系起来,以儒家的角度解释童心,指的是秉彝状态。不过,因为李贽的童心还受偏重于自然的极端的心学倾向之影响,所以应该把童心理解为不仅包括儒家因素,还包括心学因素的概念。也就是说,李贽的童心是通过修身可能成为圣人的根本因素,是与心学中的心结合在一起完成一个完整的人的过程。总之,李贽和袁宏道的真,都与文艺创作有直接的联系,这是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志向有所差异,李贽的童心,不是文与道的分离,而是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状态,这一点在他的自然之性中曾出现过,就是极端的儒、心合为一的意识形态的延伸。
三、质的运用
袁宏道认为,真是性灵的存在方式,质是把它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形式。所有的文学作品只有通过质的运用,才能把真表现出来,创作出更能体现性灵的作品。他之所以认为“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日不工,质不至也”,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文章没有运用质而所成,那么它像“无果之木,不知回报的人”,只徒有其表,有名无实。袁宏道不但强调质的重要性,还提示了能够达到质的层次的方法:“博学而详说,吾已大其蓄矣,然犹未能会诸心也,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虽然,试诸手犹若制也,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三变而吾为文为意忽尽,如水之极于澹,而芭蕉之极于空,机境偶触,文忽生焉。风高响作,月动影随,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为文也,曰是质之至焉者矣。”[6]要达到质的层次,简单地依靠“博学而详说”是不可能的。只有以真为依据,经过一定的变化过程,“为文之意忽尽”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质的层次,所谓的质应该是“风高响作,月动影随”这种极其自然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为文”时把性灵的存在形态,真,原本不动地搬过来,只有把性灵用语言表达出来时才能成为质。
但是,袁宏道把质作为性灵的表现形式,他没有排除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在“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极也”中也能看出这一点,袁宏道虽为进步的文学家,但中国的传统文学中自古就存在着文和质的问题,从这方面考虑,他也没有完全丢弃传统的文学观。“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为文也”,这段话虽然体现了袁宏道的质的内容、注重个人情感,有所欠缺,但是,这足以说明与古人所追求的质是大同小异的。这就是他的性灵说的局限性。
李贽也认为表现童心时最关键的要素是自然性。因此,在化工(天赋的工巧)和画工(人的技巧)中,他推崇刻画人的内心世界、未加任何修饰,或技巧的化工。通过这些化工,童心才能体现为文学形象,这时他把它叫做真文。与此相反,见闻和道理阻挠童心的文学叫做假文。他之所以批判拟古派,是因为他们把见闻和道理作为创作行为的主要依据。
由此可见,袁宏道与李贽的质和化工在作者和作品之间起的是媒体作用。如果说,袁宏道的质具有传统色彩的性灵之表现形式,那么,李贽的化工是努力否定和消除道理和见闻的反传统色彩浓厚的表现形式。
有趣的是李贽比袁更为明确了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他以性、格、调、律来说明作者和作品的关系:“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沈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即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逐以自然也。”[7]首先,李贽认为性与格是作者内在的问题。但是,他还假定,个体之间的差异就是格,格的拟人化的共同点就是性。在这里,性,相当于本然之性和清净之心,格,相当于童心。以性和格为基础使之具备作品之模样的就是调和律。具体地讲,格,决定作品的内容和风格的调,性,作用于诗的共同形式——律。从中可以看出,李贽认为的作者和作品的关系,是在个性立足于童心,以文字来体现,形成调之后才产生。要求立足于童心之上,是因为律是作品内在的共同性,又必须与格和调相应,因此,既要保持形式上的统一性,又要因作家和作品有所变化。总之,李贽的创作论具备了以童心为主体的单一的体系,这与他的意识形态中反映出来的一元论的思考方式是有密切联系的。
四、趣、韵、淡的追求
前面论述性灵和真、质是有关于作者和作品的问题,趣、韵、淡是谈论作家和作品和读者之间的问题。袁宏道的趣指的是接触作品时最初产生的兴趣,趣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读者的问题,但是它反映的是作者的内心,因此,不应该是读者的问题,而应该认为它体现了作者的兴趣。在这里他还在强调趣依据的是性灵和真以及质的关系,所以也不能人为地造就。袁宏道认为,具有高深学问的人写不出好的作品,就是说,作者不加任何修饰,只依靠性灵创作时,他的作品才会具有趣,如:孩童不知道什么是趣,却拥有真正的趣,作者自己创作时,能够无意识地在作品中体现兴趣。不过他还讲道:“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兴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着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8]从中可以看出,袁宏道认为的趣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兴趣,趣指的是,在真的状态中能够感觉,性灵以真的形象通过质来体现的作品;分明知道有色、味、光等但是表达不出来时的内心的感应
因此,趣不仅是作者、作品及其读者的问题,还是关于人的内心的问题。从是否依据性灵,发展到是否感觉趣,开始探论了对创作主体的最初步,最根本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分析韵,就能知道这有关作品的问题了。
韵跟趣不同,具有很多形式,也能明确地规定。趣,是接触作品时的最初的感觉,那么,韵,是读作品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出来的韵致。袁宏道说:“山有色,风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学道有致,韵是也,山无风即枯,水无波即腐,学道无韵即老学究而已……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而现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稚子韵也,嬉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由斯以观,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从心即理绝而韵始全。”[9]在这段话中也能看出,韵比趣更为具体,袁宏道认为韵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为形式上的韵。在中国的古典诗中想象不出没有韵的诗,但是袁宏道把韵与性灵联系起来,认为纠缠于韵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用道理来取韵是不可能的,拘泥于道理尤如陷进是非之窟宅,只有“人心即理绝而韵始全”。人,不管是谁都具有性灵,也都可以具有韵,但同性灵一样,只有自然而然的时候才有可能具有他讲的韵。其二,指经过押韵的作品中感觉得到的韵致。韵致指人(灵)的表现,或者是醉人或者是稚子等不同的形态,读者会从中得到的不同的感受。袁宏道认为,读同样的作品,每个人的感受会不一样,但只有像醉人、稚子一样处于无尘俗观念状态时才能感觉出自然的韵。他认定“嬉笑怒骂”为韵致,甚至称为“大解脱之场”为韵致,这在当时而言可谓是惊人的进步之举。不过考虑上述性灵的每个环节,那么这个主张也是理所当然的。总而言之,袁宏道的韵具有两种意义,韵,既是作品必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是读者都感觉到的韵致。因此,这是趣的进一步的发展。
袁宏道认为,淡是规定作品的水平的标准。趣和韵是作品的基本构成因素,还不能据此评价作品的高低。他把淡作为评价作品高下的标准:“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惟淡也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得薄,甘者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变态也,风值水而波生,日薄山而风生,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逐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於理,一累於学,故皆望岫彦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10]在袁宏道看腊,趣、味、淡都是以性灵为主体、为中心的,它们虽属于不同的层面,但都属于一个体系。所说的淡是一种很难达到的艺术境界。淡既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东西,也是评价作品高下的主要的标准;同时,淡还是读者应该感受到的东西,同样也是评价读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的“神与物游”、物我感应的审美方式的集中体现。这里应该看到的是,不论是苏轼还是对之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朱熹,他们在审美追求上都十分崇尚淡的境界。二人在审美趣味上如此惊人的一致,实是出于“当时的时代精神”。朱熹的情感本体是要将“天理”情感化,即邵雍的“名教之乐”;而苏轼的情感本体要将人的情感合法化、“天理”化。在审美情趣上同样是追求“淡”,却隐藏着思想上的本质区别和巨大矛盾。苏轼事实上是明中叶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先声,明代的董其昌说,王阳明的心学“其说非出于苏(轼),而血脉则苏(轼)也”。[11]因此,苏轼、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的淡与朱熹等正统理学家的淡很不相同,必然会发展出“愤激决裂,拏戾关节”审美要求,终至以冲突的美来对抗对传统的和谐原则。
袁宏道虽然深受心学和李贽的影响,但作为官僚,并没有完全摆脱朱子学的影响,因此,在他的性灵说中有着矛盾的一面。袁宏道认为,性灵是构成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而真则是使人的性灵成为文艺作品的特定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质又是表现真的必由的方式。然而,袁宏道并没有沿着这条人开掘人的心灵自由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倾向于群体的道德意识。李贽强调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使其理论具备了作家论的基本框架,袁宏道则进一步发展了作家论,整理出了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结构——生产、流通、消费——相适应的作家、作品、读者文艺运作的结构,为其后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朱子语类》卷五。
[2]《焚书·李温陵传》。
[3]《叙小修诗》。
[4]《焚书》卷四《观音阁·澹然师》。
[5]《焚书·童心说》。
[6]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
[7]《焚书》卷三《读律肤说》。
[8]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
[9]《寿存齐张公七十序》。
[10]《叙氏家倡集》。
[11]沈德符:《野获篇》卷二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