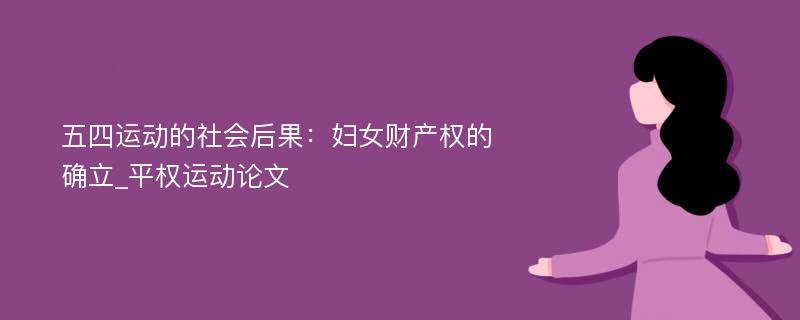
五四的社会后果:妇女财产权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产权论文,后果论文,妇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1-0101-09
近年来有人提出,五四的一些文化命题是否过于激进?过于超前?脱离了中国实际因而导致一些负面效应?这种质疑虽然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提出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在文化重建过程中如何处理理念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男女平权”、“妇女解放”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形成了高涨的妇女解放思潮。对于五四“男女平等”观念在思想变革上的启蒙意义,以及妇女精英倡导女权运动的实践活动,历史学者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与肯定。然而,“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只有落实到妇女大众的实际生活当中,变为现实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才能够真正在社会中扎下根来,变为活在民众生活中、具有生命力的社会伦理。因此,我们需要考察“男女平等”观念是否落实到了社会生活当中?落实的程度如何?有怎样的实际效果?对妇女实际生活具有怎样的影响?
人独立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是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占有权与支配权,亦即财产权。自清末开始仿效西方修定法律,在1909年至1931年短短二十余年间,共有四次修律,关于妇女财产权的法条规定也有所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法律上女性财产权的变化状况,观察五四“男女平权”理念落实到法律制度层面,从而对社会生活发生实际影响的一个取径。
在新文化运动展开以后,伴随着女权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争取妇女财产权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对妇女的法律权益问题进行比较专门的研究①。在一些法律史论著中,也有涉及到近代妇女财产权利的内容②。但对于妇女财产权历史演变的记述比较分散和简略,还难以看出妇女财产权演变与社会文化变动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有关妇女财产权的演变问题缺乏专门研究,多为法律史或妇女史论著中一般性地、分散性地有所涉及,而很少专门论著。美国学者白凯所著《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③,是关于这一问题最为集中和专深的研究专著,对中国传统法律和民国新民法中有关妇女财产权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但对清末民初几次修律所反映的妇女财产权的演变脉络并未关注。本文即通过考察从传统法律到清末直至五四前后的几次修律,追踪妇女法定财产权的演变,以探索五四提倡的“男女平权”理念,在妇女法律财产权演变上是如何反映的,怎样由理念落实到法律制度上,以及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
一 儒经与历朝律法中的妇女财产权益
五四时期妇女争取财产权,是针对中国传统礼法中妇女几乎没有财产权这一状况而提出的。那么,中国传统礼法中关于妇女财产权是怎样规定的呢?
先秦时期形成的儒学经典,既是记录当时风俗礼法和伦理观念的典籍,也是汉唐直至清代历朝奉为官方理论的经典。虽然这些经典中还没有如后世意义上的正式成文法典,但却贯穿着礼法精神和礼教规范,是后世制定法律处理民事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我们要探究中国传统法律处理民事的立法原则,便不能不追溯到儒学经典。《礼记》就是专门记述周代礼法礼俗制度的经典。
周代在家庭小农经济基础上,已形成宗法家族制度,同居共财的父家长制血缘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经济生产生活共同体。妇女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成员,因而也是礼法制度所要规范的对象。《礼记》的《内则》篇,就是专门阐述妇女在家庭中的职责和规范的,而且内容条理相当详细严密。在《礼记》等先秦典籍中,对于妇女的家庭财产方面的权益有一些规则。
首先,妇女不许有私财。
在同居共财的家庭中,所有的资产财物都属家庭共有,只有家长(当然是男性家长)作为家庭的代表而有支配权和处分权,并以家庭代表——家长的身份而握有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在一个家庭之内,除家长之外,其他所有家属都属于“卑幼”,都没有财产权,作为处于附属性经济地位的妇女就更是如此。所以《礼记·内则》中说:
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即作为家属、由家长统领下处于卑幼地位的儿子和媳妇辈,不得有任何私人专有的财物,不能将家庭里任何财物据为个人私有,也不能擅自处置家庭财物,如不能把家里的财物私自借与或赠送他人。不仅家庭共有财产不得视为个人私有,擅自支配,而且作为妇女来说,别人赠送的物品,包括一些供妇女个人所用的衣物饰品,也要上交给舅姑(公婆),作为家庭的公有财产。对此《内则》篇中有详细的规则:
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
妇女得到别人的赠物,不仅要首先献给舅姑,还要表现得心甘情愿,即使舅姑发还给她,让其个人享用,作为媳妇,也要“藏以待乏”,保存好以供家里紧缺时供尊长和家人享用。可见对于妇女来说,一切财物用品都是属于家庭共有的,自己没有任何专属于个人的私财。妇女在家庭中只是作为家属之一,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拥有家庭财产。
其次,妇女对家庭财产有一定的用益权。
从先秦典籍中看,妇女作为家庭成员和家属,对于家庭共有财产有一定的享用权益。女子嫁入夫家,成为夫家家庭中的一员,礼法以夫妇一体为原则。故《礼记》中在尊卑上下的家庭关系中,常将“父母”、“翁姑”、“子妇”等夫妇并列作为尊卑辈分序列中的同级主体,夫妇的生活待遇基本相同。如妇女在年老丧失了劳动能力时,也仍然享有与其夫一样的生活资料的用益权。如《礼记·内则》中说: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馂。
也就是说,作为子妇,每天要侍奉父母的饮食,即父母享有受儿子、儿媳赡养生活的权益,在这里,父和母是没有区别的。不仅如此,即使父亲死去,而母亲仍健在,子妇还要像父亲在世时那样继续侍奉母亲的日常饮食。故《内则》篇在上句之后接着说:
既食恒馂,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妇佐馂如初。
这里强调即使“父没母存”,子妇仍要侍奉母亲的日常饮食就如父亲在日一样。这里一方面强调母亲在夫亡后仍然有受子妇赡养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可推测,现实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父亡后,子妇对于母亲的侍奉有所怠慢,故而要特别地加以规定。这从反面说明,虽然父母有同样受子妇辈赡养的权利,但母亲受赡养的权益比父亲为低,而且要依附于父亲。
先秦儒家经典中的这些原则精神,贯穿于唐以后直至清代一千余年间历朝的礼法制度中。④在历代的成文律法中,关于妇女财产权益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妇女对家庭财产基本上无所有权和处分权。
在家庭结构稳定时,家庭成员同居共财,父家长代表全家握有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而其他家庭成员则不许私自拥有或处分财产,故历代律法都有禁止“卑幼私擅用财”的条文规定。如《唐律》规定:“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疏义》对此条注解道:“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故应治罪。⑤ 沿袭明律的《大清律例》在“户律·户役”门有“卑幼私擅用财”条,其中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每十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该条后面的注释中写道:“卑幼与尊长同居共财,其财总摄于尊长,而卑幼不得自专也。”⑥ 由于男性子孙长大成家分家立户以后,也会成为一家之长,因而也会有对自己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而妇女由于终生不可能成为家长,因而也就终生不可能对家庭财产拥有所有权和处分权。在这个意义上,妇女是彻底、终生的没有财产权,而“卑幼”男子的“无私货”则只是暂时的、有限的。
第二,妇女有极为有限的财产继承权和代管权。
妇女对家庭财产既无私有权和处分权,当家庭结构出现变动时,如家长死后发生家庭财产继承问题,或妇女与家庭的关系发生某种变动,如分家、出嫁、离婚等,发生财产分割,这时才会出现妇女的财产权问题。由于历代习惯法和律法都沿行男性继承、诸子均分的制度,即使家中无子,也要选择同宗男子来承嗣过继,因而妇女没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但也有一点有限定的权利。
首先,在室女子在分家和出嫁时,可以由父母家得到一点嫁资,但数量有限。
如宋代律法《刑统》“户婚律”门“卑幼私用财”条载明,分家时兄弟均分而女子无份,但可得到少量的嫁资:
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⑦
明清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民间习惯是给在室女一定的妆奁费,成为习惯法。虽然具体数额没有如宋律那样明文规定,一般由各家依情况而自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嫁资,只能是从家庭财产中分割出的极少部分,远不能与其兄弟分得家产的数量相比。而且这些嫁资在女子嫁入夫家后,便成为夫家财产,妇女不再有所有权及处分权。如明代《大明会典》和清代《大清律例》都有明文规定:寡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⑧。
其次,当分家时家庭内没有男性继承人,也没有同宗应继者,即所谓“户绝”时,历代都规定妇女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这在唐宋至明清律法中都有相关规定。如沿袭明律的清律规定:
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⑨
除了女子继承亲生父母财产之外,还有寡妇对于其夫名下财产的继承问题。如《大明会典》规定:
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⑩
也就是说,寡妇在夫亡后如不改嫁,可以承继其夫名下的家庭财产,但只有代管权,在选择同宗继嗣人之后,还要归还应继之男性继嗣者。而如果寡妇改嫁,则无论夫家财产还是自己从娘家带来的原有妆奁,也都归前夫家作主,听其处分。《大清律例》也有与明律文字完全相同的条文。(11)
再次,长辈妇女有受子孙扶养之权利。
历代沿袭“父母一体”的原则,长辈妇女与男子同样享有受子孙扶养的权益。如《唐律》“斗讼”门“子孙违犯教令”条规定:对于祖父母、父母,“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12)。所谓“供养有阙”,即“家道堪供而故有阙者”(13),子孙对祖父母和父母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在这里母与父是同等待遇的,为母者在有生之年有受子孙赡养、享用衣食生活所需的家庭财产的权益。
由上述历代律法可见,关于妇女的财产权,一直贯穿着先秦《礼记》等儒家典籍中的基本原则,作法往往历代沿袭,较少变动。在传统礼法制度下,妇女的财产权益与男性相比,可谓至低,除了依附于家庭维持生存之外,几乎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益。这正反映了在男性血缘家庭同居共财制度下,礼法制度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妇女只是作为家庭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和经济地位。这种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礼法及习俗,在近现代直至今天的农村地区仍然具有一定影响。
二 清末修律与妇女财产权的初萌
庚子国变以后,清廷迫于形势,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开始仿效西法进行制度改革。法律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自然也在改革之列。在此后清朝存续的短短十年时间里,共修订出了两部新法律。
由于庚子国变的强烈刺激,社会上形成了日益强劲的学习西方、改革社会的舆论热潮,一些西方新观念引入国内,“男女平等”的思潮开始涌动,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舆论呼声也开始出现,由女子的教育权到就业权,成为舆论热议的内容。同时,也开始出现争取妇女财产权的呼声。最早公开提出妇女财产权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是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金天翮撰写的《女界钟》。在此书中,作者以热烈激昂的笔调,为争取妇女权利大声疾呼,在他列举的女子应当恢复的六种权利之中,有关经济权益方面,除了女子营业权利之外,还明确提出女子应有“掌握财产之权利”。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也意味着女子争取财产权开始进入女权运动的范围。
清末这些文化思潮的动向,对于修律中的妇女财产权益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通过新修订的法律条文作一考察。
第一部新修订完成的是《大清现行刑律》,这是在修订新律未成的情况下,由于应实际需要而先在原来的《大清律例》基础上进行删订改造而成的,于1909年修订完成,次年予以颁布实行。
在这部历时七年、号称仿效西方、趋近“文明”的新修《大清现行刑律》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废除了被视为“不文明”、“野蛮”的笞杖、枭首、凌迟等旧式体罚酷刑,对于较轻的民事犯罪,则以经济处罚(罚金)取代了笞杖。就有关家庭民事的具体条文内容,则改动很少,关于妇女财产权和继承权方面的条文,如《户律·户役》中“卑幼私擅用财”条及“立嫡子违法”条等,则完全沿袭旧律,甚至连文字词句都没有作任何改动,只是在原文下作注解道:“臣等谨按:此仍明律,顺治三年修改,应仍其旧,惟笞杖照章改为罚金。”(14) 关于妇女财产权益问题除全部沿袭旧律之外,也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条文。
可见,虽然这一时期正值男女平权社会舆论涌动时期,而在实际影响妇女生活和基本经济权益的现行法律上,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权益问题尚没有被触动。这不仅反映了在清廷主导下的法律制度的改革具有相当强的保守性,也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妇女经济权益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而沿袭了两千年的传统礼俗礼法制度仍具有相当强的惯性。
清末第二部修订的新律是1911年修订完成但未及实行的《大清民律草案》。
1909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基本上仍然沿袭旧清律,没有体现近代“文明”的新价值理念,显然与当时的社会新思潮相背离。同时1906年清廷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宣布预备立宪,而旧律显然与君主立宪的价值理念也不符,所以清廷又令修订法律,将原来一直统合于综合法律中的民事部分单独分出而修订了《大清民律草案》,并于1911年修订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民法典,也是第一部按照欧陆民法原则和理念起草的近代性质的民法典。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草案并未实行,但这一草案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法律观念所达到的程度,其中也反映了妇女财产权法理观念的变化。
由于《大清民律草案》以西方近代法理为基本依据,力图体现平等、人权等近代价值理念,所以其法律条文与旧律相比有着根本性的改变。关于妇女财产权的规定也是如此。同时,这一时期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在社会舆论中日益高涨,女权运动开始涌动,也促使修律者在立法原则上加以考虑。《大清民律草案》关于妇女财产权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妇女拥有了私有财产权。
“亲属”编“家长与家属”一节中规定:“家属以自己之名义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15) 家属即除家长之外的所有家庭成员,自然也包括妇女家属。此外在“婚姻之效力”一节中也特别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但就其财产,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夫管理妻之财产,显有足生损害之虞者,审判厅因妻之请求得命其自行管理。”(16) 在“离婚”一节中规定:“两愿离婚者于离婚后,妻之财产仍归妻。”(17) 这些条文里关于妇女对自己所得之财产为其个人的“特有财产”,拥有所有权和处分权的规定,与旧律不许妇女有私财,以及嫁入夫家后其由娘家带来的妆奁也由夫家支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相对于以往家庭共财制下妇女“无私财”,新法承认妇女有归个人所有的“特有财产”,即私有财产权。这一条使妇女的原有财产或劳动收入及结余可以归其个人所有,而不再完全被代表家庭的家长所占有,虽然其个人特有财产“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但所有权和处分权仍归于妇女。这些规定使妇女第一次在法律上有了独立的个人财产权,而且在个人所得归个人所有的私有财产权方面,妇女已经与男子达到了理论上平等的地位。
第二,妇女的家庭财产继承权扩大。
“继承”编中虽然规定继承人仍为“所继承人之直系卑属”,即所继承人的直系男性子孙,但还规定父亡后家庭财产由母亲监管,儿子虽有继承权,但需经母亲允许才能分割财产:“有母在者,若各继承人欲分财产,须经母之允许。”如所继承人无子,则其妻可以继承其夫之财产:“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为继承人。”同时规定如果所继承人无子,其他亲属继承其遗产的顺序为:
(一)夫或妻;(二)直系尊属;(三)亲兄弟;(四)家长;(五)亲女。(18)
据此规定,妇女虽然还不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但如所继承人无子则首先妻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其继承权比旧律的仅有代管权有了很大的扩展。而亲女为第五顺序继承人,继承权益比旧律只有“户绝”时才可继承相比有所扩展,但相对于儿子来说仍然很小。可见在这一民法草案中,在家庭财产的继承权方面,妇女的继承权,特别是作为被继承人妻子的继承权有了明显的扩大,但是距离男女具有完全平等的继承权还有较大距离。这与法律规定男女对于家庭经济负有义务有所不同相呼应。在“亲属”编中规定了男女结婚组成家庭以后,“由婚姻而生一切之费用,归夫担负。但夫无力担负者,妻担负之”(19)。即男子对于家庭经济负有主要责任,妇女负有次要责任。这也是对民间习俗现实状况的一种认可和迁就。
第三,确立了男女具有对等的相互扶养权。
“亲属”编中规定:“家长家属,互负扶养义务。”(20) 还规定:“夫妻互负扶养义务。”(21) 这一规定明确了妇女无论作为女儿、妻子,还是母亲,都有受家庭成员扶养的权利,而且明确了家庭成员无论男女、家长还是家属,都有平等的相互扶养权。这就使自先秦儒经确立而后延续了两千年的只有为长辈妇女可享受子孙扶养的权益,子孙扶养母亲、祖母以尽孝道这一“软性”的义务规则,第一次明确地扩大到所有女性家庭成员,并予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使妇女的被扶养权得到了法律保证。
由上可见,《大清民律草案》对于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规定,虽然与男子权益仍有一定差距,但总体来看,特别是与旧律相比,已经基本上体现了以个人为本位的财产制度及男女平等的近代法理原则,保障了妇女的基本财产权益,这是中国法律史上一次根本性改革,是法律近代化的一个标志。但这一草案刚修订完成,清廷即被推翻,这部《大清民律草案》便只停留在了草案上。
三 五四时期民国民法草案中的妇女财产权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因未及重修民法,司法部便将《大清民律草案》更名为《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颁行。北洋政府执政以后,认为《大清民律草案》太西方化,太偏重个人利益,与实际生活和民间习惯距离太远,实行困难,因而决定继续援用1909年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中民商事部分,亦即沿袭明清时代的旧律,作为司法机关适用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只是在实际执行时酌情予以变通办理。(22) 所以,在民国初期的司法实践中,妇女的财产权益问题,还是基本上沿袭男女极不平等的妇女没有财产权的传统法律。这一司法现实虽然迁就了民间习俗,避免了社会生活的一些新生矛盾和动荡,但显然与民国所标举的男女平权理念相违背,因而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北洋政府也不得不加紧进行修订体现民国立国精神的民法。自1914年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开始修订民律草案,着手进行民事习惯调查,次年编成了《民律亲属编草案》,后直至1925年才全部修订完成了《民国民律草案》,经司法部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理适用。
在此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的呼声弥漫于社会,充斥于媒体舆论,在新文化人和知识青年中成为主流观念。同时,在清末民初出现了兴办近代工商业的热潮,在一些丝厂、火柴厂、茶栈等工商企业里女工的人数增多,她们成为较早走上社会独立谋生,并能够得到劳动报酬的城市劳动妇女群体,也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提倡女性社会就业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在五四运动时期,男女平权的议论更多地集中在女子要进入以往被男性垄断的中上层社会领域,如争取女子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和职业权等方面,而且较多地处于呼吁、宣传阶段,对于关乎妇女切身生存权益的财产权问题还没有太多的关注。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政治理念上趋于保守,因而修律时对于妇女权益问题更多地着眼于已有的民间习惯,特别是对妇女财产权这一关涉到千家万户实际利益的问题,更多地迁就民间的习惯做法。1925年修订完成的《民国民律草案》,作为民国成立后修订实行的第一部民法,也标榜秉持民国的立国精神,体现近代法理原则,但有关妇女财产权益方面的条文,却比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有所倒退,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妇女个人财产权限制增多。
《民国民律草案》“亲属编”中,规定了“夫妇财产制”,即区分夫妇共有财产和个人所有的“特有财产”。关于妇女的个人财产权虽然承认为妻者享有特有财产权,但又规定需受丈夫的一定限制。如规定道:“专供妻用之衣服、手饰及手用器具等物,推定为妻之特有财产。其他动产所属不分明时,推定为夫之财产。”“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但就其财产,夫有使用、收益之权。”妻“婚后所得之财产”亦即妻之就业或营业所得收益,而对于妻之就业营业则规定需得丈夫之同意:“妻得夫允许为一种或数种营业者,在其营业范围内,对于一切营业事务,有自由处决之权。前项允许,夫得撤销或限制之。”还规定:“妻之特有财产,由夫管理……夫不能管理时,由妻自行管理。”“在夫管理期内,妻欲处分其特有财产,夫无正当理由不与允许,而妻能证明其处分为有利益者,无须经夫允许。”并仍规定丈夫对于家庭经济负首要责任:“由婚姻而生之一切费用,归夫担负。但夫无力担负者,妻担负之。”(23) 可见对于妻之个人财产权,更明确、详细地规定了丈夫享有一定的限制权。
第二,妇女财产继承权有所减少。
《民国民律草案》关于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益,一方面在“亲属编”中规定:“父于女成婚时,有准其资力给与嫁赀之责。”(24) 明确了女儿享有由父母家给予嫁资之权益,但由于并未规定具体数额或比例,而只是由父做主,“准其资力”,所以女儿由父母家所得的作为嫁资的财产数额当十分有限,不可能与兄弟分家所得份额相比,因而女儿与儿子的财产继承权仍然是十分悬殊的。另一方面,在“继承编”中对于妻的财产继承权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在立继以前,得代应继之人,承其夫分,管理财产。”(25) 这一条与《大清民律草案》中“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为继承人”的条文相比,显然有了很大倒退。夫亡无子守志之妻由直接财产继承人,变为应继者的代管人,基本退回到明清传统时代的旧律。只是在无应继之人时,妻才享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之权。还规定:“妇人……(亡故)而遗有财产者,其遗产归夫继承。”显然,夫与妻对于配偶的财产继承权是不对等的。对于作为第五顺序继承人的亲女,增加了“所继人之亲女,无论已嫁与否,于继承开始时,得请求酌给遗产归其继承”。使出嫁女的财产继承权得到了明确保证。对于寡妇的被扶养权益也增加了规定:“所继人之妻,于继承开始时,得按遗产总额及其本人与遗产继承人之需要情形,酌提遗产,以供养赡之用。”这一条使寡妇的扶养权益得到了一定保障。(26) 这些都是有利于保障妇女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的规定。
可见1925年的《民国民律草案》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相比,对于寡妇的财产权有了较大的倒退,只是对保障妇女有限的财产权方面作了更细化的规定。民国后修订并部分实行的第一个民律,妇女虽然享有了有限的财产权,但与男子财产权相比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并留有传统礼法的明显印迹,距离男女平权的近代理念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反映了在五四时期修订的这部民法,五四的男女平权理念还未在立法原则上得到彻底贯彻,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立法理念有一定的保守性,民间习惯风俗的惯性力量也还相当强大,足以影响立法原则。
四 五四后民国新民法与妇女财产权的确立
五四运动以后,在思想启蒙的强力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妇女直接参与到争取女性权益的实际行动中来,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进入蓬勃深入发展时期。同时,一批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成长起来,并开始进入教育、新闻、城市服务业等社会就业领域,她们的社会力量开始壮大。在这一时期,各地进步妇女纷纷成立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权的妇女组织,她们开始以群体的力量,从妇女自身更切近的实际权益上开展争取男女平权的活动,并开始以妇女群体的声音向社会发声,推动着“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由笼统的口号趋向具体的实际权益,由思想理念趋向社会实践。中华民国以民主、平等为立国理念,而男女法律上的不平等显然有悖于这一理念,所以北京政府一直实行男女明显不平等的司法状况,受到进步人士的不满和批评,也成为日益高涨的女权运动所针对的目标,一些妇女团体开始明确提出了争取妇女法律财产权的问题。
1922年,北京各学校女生成立了争取女子参政运动的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和“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各省也多有这两种组织,认同和拥护两个组织提出的主张。两个组织在发布的成立宣言中,提出了争取妇女权益的主张,其中都提出了争取妇女法律上的财产权问题。如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发表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女权运动的奋斗目标,在所列举的七个目标中,就有一条为:“私法上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承继权、财产权、行为权等一(律)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大加修正。”(27) 北京女子参政协进会也提出主张:“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28) 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同年提出的请愿书中,也明确提出要求政府:“速定民律,俾女权于私权上得一平等地位。凡关于夫妻权义(利)、婚姻、继承等问题,务期不偏不倚。”(29)
除了这些民间妇女群体组织之外,当时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党内妇女团体的推动下,也相继提出了争取妇女法律财产权的问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提出了女权运动的10个口号,其中一个就是《女子应有资产承继权》(30)。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关于青年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提出了青年妇女运动的12个口号,其中也提出了“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31)
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确认男女平等的宗旨:“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在国民党控制区的地方司法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施行增强妇女财产权益。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1926年1月16日通过),内中指出,“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之规定”,在法律方面要实施“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和“规定妇女有财产承继权”。并在“妇女运动适用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男女职业平等”、“男女在法律上绝对平等”、“男女工资平等”、“妇女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等。(32)
这一决议案通过之后,其原则虽然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贯彻,但在法院实际执行过程中却贯彻得并不彻底,如对出嫁女于父母的财产继承权便多因循习俗而不予保证,因而并未实现男女财产权继承权的一律平等(33)。此后不久,随着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伐成功及北洋政府统治结束,这一国民党决议的原则成为国民政府指导修订民法的一个依据。
1929~1930年间,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民法亲属编》和《民法继承编》于1930年12月颁布,并于1931年5月正式施行,这是第一部基本上实现了男女平等的民法典,其中关于妇女财产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夫妻享有基本同等的财产权。
《民法亲属编》中规定实行夫妻财产制,除了规定结婚时及婚后夫妻共同所有之财产为共有财产外,夫妻双方都可拥有其个人所有的“特有财产”,包括:
一、专供夫或妻个人使用之物;二、夫或妻职业上必需之物;三、夫或妻所受之赠物经赠与人声明为其特有财产者;四、妻因劳力所得之报酬。(34)
这一规定中,妻的个人财产权已经没有以往受夫一方的限制,夫妻基本上享有同等权利。
第二,妇女享有与男子基本相同的财产继承权。
《民法继承编》中规定:“配偶有相互继承遗产之权。”(35) 配偶被作为首位遗产继承人,其中配偶无分男女,这样夫亡后妻也可享有夫之财产的继承权,夫妻权力同等。这与1925年《民国民律草案》规定只是夫可继承妻之财产、而妻不能继承夫之财产的夫妻权利不平等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中“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才可继承夫之财产的限定性规定相比,也是更加彻底的男女平权。
至于配偶以外的其他遗产继承人,《民法继承编》规定:“遗产继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顺序定之:一、直系血亲卑亲属;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36)
其中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由于取消了以往专指男性继承的宗祧继承权,而强调血亲,所以女儿与儿子享有同等继承权,而且也不再区分已嫁未嫁。其他各顺序继承人也都是男女并列,权利同等,不再有所区别。这些法条规定彻底实现了男女拥有平等继承权的原则。虽然在民间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传统习俗的强大惯性影响,男女平等继承权往往得不到彻底贯彻,但由于正式颁行民法标举男女平权原则,对于民间风俗也起到了一定的矫正、示范和引导作用。
五 结语
由上述对传统礼法到民国时期五四前后法律制度中关于妇女财产权演变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延续二千余年的传统礼法以家庭为本位、男性垄断财产制度下,妇女几乎没有财产权。自清末修订法律后,开始向个人为本位财产制度及妇女享有财产权方向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过程紧密相连,同时也与近代女权运动的发展密切相连。这一转变过程主要发生在清末民初短短二十余年间,经过四次修律,渐行渐进,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虽然确立了民主、平等的立国理念,但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现实制约,传统习俗的惯性及执政者的保守等原因,并没有马上实现法律上男女享有平等财产权。只是在五四运动启发下女权运动勃兴,经过五四思想启蒙,“男女平等”、“男女平权”观念在社会舆论中成为主流,这种经五四启发而形成的男女平权思潮和女权运动,成为推动在法律制度上完全实现妇女享有平等财产权的重要动力。最后在确立了男女平权宗旨的国民党执政后,于民国成立20年后,才最终修订颁行了实现男女平等财产权的法律。修律的反复过程,实际上也是在立法原则上男女平权理念与民间习俗的博弈过程。可以说,妇女财产权在法律上的确立,是五四运动的男女平权理念,落实到社会实践的一个社会后果,通过这种法律制度的中介,五四所倡导的男女平权理念,才转变为影响妇女大众实际生活的现实社会成果。
然而,妇女财产权虽然在法律上得到了确立,但这只是表明这一原则在社会价值理念上确立了正当性和主导性,由于城乡、阶层之间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存在着巨大差异,一些法律条文的适用性也有很大局限。如关于保障妇女“劳力所得之报酬”所有权的规定,由于只有城市职业劳动才能够获得可计量的“报酬”,而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家庭经济,妇女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劳动,以及城乡妇女的家务劳动,都无法得到可计量的“报酬”,就只能被排斥在“劳动所得”的财产之外,因而妇女的这部分劳动的收益,就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护。这仍然是对于妇女经济权益的不平等对待。此外,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习俗,及土地和住居的不可移动性等限制,广大下层贫穷女子在出嫁、离婚和分家等家庭财产分割时,仍然普遍沿用民间习惯,女子不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财产权。这种情况,直至今天许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反映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的城市生活与小农经济的农村生活二元并存的格局下,法律制度的立法原则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法律制度适用于现实生活的困难和局限。
中国妇女法律财产权的这一历史变迁过程表明,政治变革、观念变革、制度改革和习俗演变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交错和梯度的。“男女平权”的理念与实践之间有一定距离,理念和制度有些“超前”,使得法律的可操作性较弱,其实际效用大打折扣,因而存在着法理上正确而操作性差的缺陷。但是,妇女财产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使“男女平权”的价值理念通过立法原则而确立为社会制度的主导价值,对广大民众的观念及民间习俗会起到有力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从这种理念与实践、制度与习俗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在初期以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为主的社会转型阶段,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及不协调性。其中现代价值观念的引入与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率先与引导作用,而其确立则需要通过社会制度化,进而规范和影响有着极大传统惯性的社会现实生活。因此,观念、制度和习俗变革之间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梯度,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的特殊性,要求社会确立目标后跳跃式前进所必需的。但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制度与现实之间不能脱节,需要有一定的勾连关系,以保证操作性和效用性,由此使社会形成系列连接递进式变革,既推进社会转型的发展,又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理念与实践、制度与现实脱节而出现大的曲折。
收稿日期 2009—09—20
注释:
① 如赵凤喈:《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
② 如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潘震亚:《女子继承权的起源和经过》,《法规》创刊号,1933年7月。
③ 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中文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前人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赵凤喈著《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白凯所著《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都有比较专深的研究,本文在此结合一些其他资料作概括性的梳理。
⑤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⑥ 胡肇楷等纂:《大清律例统纂集成》卷8,“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本,第1页。
⑦ 《刑统》卷12“户婚律·卑幼私用财”。《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⑧ 李东阳、申时行纂修:《大明会典》卷19,“户部六·户口总数”,明万历刊本,第20页;(清)胡肇楷等纂:《大清律例统纂集成》卷8,“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第1页。
⑨ 胡肇楷等纂:《大清律例统纂集成》卷8,“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第1、2页。
⑩ 李东阳、申时行纂修:《大明会典》卷19,“户部六·户口总数”,第20页。
(11) 胡肇楷等纂:《大清律例统纂集成》卷8,“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条附例二,第101页。
(12)(13)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24,“斗讼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2册,第290、291,291页。
(14) 沈家本、俞廉三等编:《大清现行刑律》“户律·户役”,宣统元年秋法律馆印,第34页。
(15) 《大清民律草案》第四编,亲属。第二章第二节,家长与家属,第1330条。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16)(147)(18)(19)(20)(21)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第173、175、187~188、173、170、173页。
(22) 1915年10月30日司法部《司法公报》第三次临时增刊;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五十年来中国之法制》。均参看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点校说明”,第7页。
(23)(24) 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第353~356、362页。
(25)(26) 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第382、383页。
(27)(29)(30)(3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4、68、72页。
(28) 潘震亚:《女子继承权的起源和经过》,《法规》创刊号,1933年7月。
(3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6~507页。
(33) 有关这一方面的情况,白凯所著《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一书第六章“民国民法中女儿的继承权”中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析。
(34)(35)(36) 蔡鸿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66册,第12、19、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