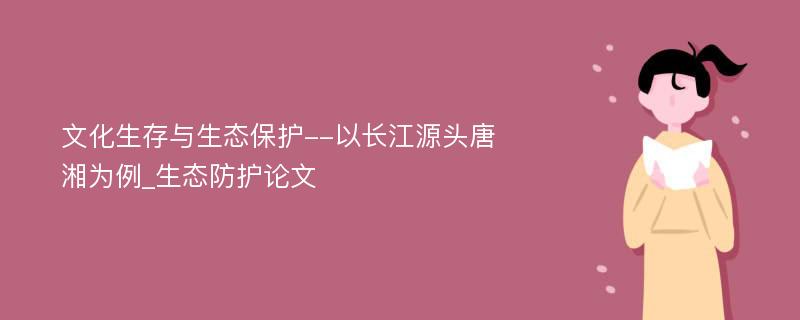
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为例论文,源头论文,生态保护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生存是近年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研究内容,意指小民族或者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过程 中,保持其民族传统的权益战略。在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之下,生态保护日渐成为21 世纪的全球焦点,中国政府也于2004年明确提出“绿色GDP指标”、“科学的发展观” 等将环境因素综合在内的崭新概念。文化生存与生态环境保护这两个看似无甚关联的话 语,在中国国内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本土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 境之间历经时间考验形成的适应性关系,曾确保了当地环境的平衡稳定。当传统文化受 到外来因素冲击,生产方式等发生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前的诸多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常令本土文化处于消亡的边缘。由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 绞结在一起,丧失其一也意味着两者共同失败。
在地域分布上,中国国内生态环境危机较为严重地区大都与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 —相对于主体民族而言的少数民族地区相重合。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部长江源 头的唐乡,是长江发源后流经的第一处人类聚居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着全球气 候持续变暖对高原地区的负面影响,加之更为严重的人为因素,本地草原生态环境持续 恶化,集中表现于草场退化、沙化和鼠害肆虐,不仅给世代游牧于此的牧民生产生活带 来许多困扰,而且间接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探讨本地区环境恶化 原因与保护途径,已成为国内诸多学科的关注内容。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类学研究的特长在于注重理解文化在人与环境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面临生态环境危机时,主流社会在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态环境保护途径 时,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与保护作用 。采取具体保护措施时,将本土生态环境与本土人群分割开来,忽略了生态环境恶化的 表象背后,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原有文化连接的重要性。本论文力图通过考察唐乡当地 游牧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形式等文化构成要素的时代变迁,阐述高寒草场退 化与本土文化受到冲击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从本土人群主体性出发保护生态环境的重 要性。
一、适应于高原生态环境的当地人文构成
唐乡位于青海、西藏交界处,现有乡属面积3200平方公里,大部分属三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长江、黄河、澜沧江),同时有一部分土地位于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 围之内。青藏公路“109”国道纵贯乡政府驻地沱沱河沿。该乡下辖7个牧业队,273户 牧民,1178人。本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年均温零下4.4度,空气相对湿度为52%,含 氧量仅有海平面的48%。
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高原草原生态地域广大而植 被稀疏,牧草再生能力较低。海拔、风力、日照、草质等先天因素决定了本地传统生计 方式以游牧为主。对于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而言,游牧生活是与自然生态环境适应性相对 而言最佳的生产方式。除了很好地适应于干旱大风的草原气候外,游牧对于脆弱的草原 生态环境也不构成太大压力和破坏,它的流动性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环境压力,而且在流 动中解决了垃圾这一令人类头疼的问题。游牧人游牧的地方,自然形成了天然的生态保 护区,不仅仅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而且促成了文化多样性。[1](P133)
作为从藏北那曲地区迁移而来的安多部落后代,唐乡牧民对于高寒、高旱、低生产力 、缺氧等生存环境发展出一套文化适应性,如以部落为组织形式、按季节近水草而居、 以小规模家庭为生产单位、谨慎适应与合理利用为主要特点的游牧生产方式,以及以佛 教教义为核心、苯教仪轨为外壳的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影响下,形成惜杀惜售、不追求 经济增值的传统畜牧业价值观念等。历经千百年时光磨砺,这些适应性因素共同组成草 原生态系统与牧人之间和谐共存的文化链条,使藏族牧民群体与高海拔自然环境达成一 种默契,不仅保证了牧民的繁衍生息,而且使生态环境处于平衡发展状态。
游牧生计方式包括一些最基本成分,如游牧人口和比较固定的大范围牧场,游牧民族 居无定处,以松散而有序的组织形式,按照季节不同利用着不同地域的草地,给各处生 态环境留出自我恢复的时间。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等学者考察新疆北部游牧民族后指出 ,作为一种获取自然资源谋得生存发展的生计方式,季节性使用草场资源体现了在时间 —空间更换的范围中对资源的有序使用。[2](P13)唐乡高海拔生态环境更要求牧业生产 具有足够广阔的地域,以保证再生能力较低的草场生态休养生息。民主改革之前,以部 落为单位游牧使牧民们可以在藏北高原广大地域之内,选择水草相对好的地域分季节放 牧,将需要恢复的草地空置出来,有效避免了同一地区的过度放牧。
在高海拔牧区,藏族牧民们以牦牛、藏羊等牲畜为主,营造着自己的生存空间。草原 生态环境决定了只有啃食绿色植物茎叶的食草动物才能生存,同时食草动物的反刍功能 使它们可以充分利用高原地区珍贵牧草。在高海拔草原生态系统中,为了保护草场,本 地藏族牧民在生产中对畜产品的提取仅仅满足于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不求高产丰产。 在畜群数量、畜产品收入、畜种比例、自身需求等方面,都体现了顺从自然规律、保护 自然生物融入自然环境的特点。
因海拔高度条件不允许种植牧草,唐乡牧业生产完全依赖天然牧草。在游牧生产周期 中,牧民们要完成抓膘配种、保膘保胎、接羔育幼一系列牧业环节,并以牛羊为生存必 需品来源,发展出一套制作、保存畜产品、奶制品的方法。虽然牲畜是人所役使、饲养 的动物,但在高原牧人心目中,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权利与生命尊严。藏民族普遍具有 的理念认为动物与人同生同长,因此在牧业生产中惜杀惜售,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并保持了自身心灵的祥和平静。牦牛、藏羊等青藏高原特有畜种自古以来生活在高寒草 原,作为牧人,只希望维持这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想为谋得经济利益而人为控制某 种动物,所以各个牧户的畜群中都是绵羊、牦牛、山羊、马等按一定比例共同存在。虽 然牧民们都知晓山羊绒经济价值高,但为保证草场质量,依然理性控制山羊数量。每年 出售的牛羊数量也控制在一定数量中,单纯追求商品率本非牧民本意。
从生态平衡的意义看,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要有互补、互助功能,才能维系生态平 衡。牦牛可利用牧场中最高最冷地方的牧草,亦可利用绵羊不能利用的湿生植被,牦牛 粪便又可以为植被提供养料,所以牦牛与绵羊的资源生态位置有错位,可以保证一个地 区的牧草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同时,由于牦牛对于寒冻、雪灾、大风等高原恶劣天气的 抵御能力较强,大量牦牛与绵羊共同生存,有助于绵羊生长得更容易、更健壮,而单群 绵羊成活率就较低。
生态学家研究青海湖地区草场资源利用状况后指出,在同一块草地上单纯饲养一种家 畜,牧草利用率低且浪费很大。实行牛、羊、马混合放牧,则能收到较好效果。结合各 类家畜的市场价值、投入的劳动力成分等因素看,合理的畜群结构比例中,绵羊应占80 %,牦牛占17%,山羊和马占2%~3%为宜。[3](P112)唐乡的畜群结构基本符合这个研究 比例。牧户饲养的绵羊最多,牦牛和山羊数量相差不多(部分牧户牦牛比山羊稍多),马 匹最少。如唐乡一队永玛家(贫困户)畜群比例为绵羊92只,占总数69%;牦牛24头,占1 8%;马2匹,山羊16只,共占13%。一队白玛达吉家(富裕户)畜群比例为绵羊900只,占 畜群76%;牦牛140头,占12%;130只山羊和15匹马共占12%。牧民们在生产中自然形成 并保持的这种牲畜品种和畜群比例,实际上具有生态学、经济学和游牧文化等方面的根 据。
唐乡的牧业生产单位——家庭或家庭联合体可分为四类组成形式:平辈家庭相连、上 下辈家庭相连、扩展/扩大家庭、核心家庭。两三家亲戚结成的家庭联合体是现实生产 活动中的互助体系,也是对于牧业生活广阔草原的适应形式。高原牧区牧户之间分散程 度与草场好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牧草高密的藏北当雄一带,草场载畜量大,牧户 之间相距较近。[4](P244)唐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牧草稀疏低矮,载畜量低,人们 分散程度较高。再者,牛羊每天的放牧半径是有限度的,早出晚归不能超出半天的路程 。自然环境要求牧民只能通过调整家庭规模、牧户之间距离和增减游牧搬迁次数来适应 草情变化。牧户家庭联合体并不是随意联结,有其内在必然联系。格勒等学者考察民主 改革前藏北牧区主要以两种关系聚居:几户亲戚住在一起;以一富户为主,加上一些穷 户聚居。[4](P247)唐乡现存家庭联合体则全部为亲戚聚居,形成了庞大亲属关系的雏 形。家庭财产管理听从家长支配,重视家庭成员的分工协作。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 家庭联合体既是放牧单位,也是互帮互助的群体,这种组织形式既能满足草场大小、质 量对家庭规模的限制,又是对家庭劳动力的有力补充。
青藏高原宗教历史久远、积淀深厚是游牧文化能够延续发展至今的原因之一。无论民 间苯教还是后来居上的藏传佛教,在藏民族传统社会精神文化中一直处于中心位置。在 藏族人文—自然生态关系中,通过宗教、神话、禁忌、象征符号等调整方式,证明自然 与人类社会是统一体,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感应、互为因果。民间苯教通过一系列宗教 仪式,使对神山神湖的崇拜成为永久的固定模式。藏北高原作为苯教文化发源地,虽然 佛教寺院相对较少,但遍布高寒荒漠的神山神湖使这里处处成为吉祥之地。佛教传人藏 区后,将青藏高原佛教化,人们以佛的眼光看待诸地,赋予万物以神圣色彩。在青藏高 原,高山成为神山,湖泊成为神湖,地下成为龙神领域,蓝天则由天神主宰。整个高原 自然面貌与人文精神和谐地组合为一体,成为相互依存的完美整体。唐乡宗教面貌延续 了藏传佛教信徒的虔诚之心,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原因,牧民中共存有去拉萨朝 圣、请僧人到家里念经、到乡政府驻地沱沱河沿拜过路活佛、自己在家从事宗教活动等 不同形式。本地神山崇拜、牦牛崇拜等民间信仰较为深厚,还发展出一套亲人转生说法 ,即某家的成员去世后转生为另一家的孩子。宗教信仰向劳动、生息于高原的牧人们提 供了一种有序的宇宙模式,给予他们与高原严酷、险恶的自然环境抗争的勇气和信心, 并通过善恶观维系了社会稳定,为牧民共同体的平衡所依赖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 了基础,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高原牧区脆弱生态环境的作用。
二、当地生态环境退化的社会文化探因
近些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直接影响着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如厄尔尼诺现象连年 发生,致使高原腹地气温不断升高,气候区域干旱,沙尘暴增多。但是,气候变化对草 地植被的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大面积的,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短期内很难造成 大面积退化。人类活动对本已旱化的草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草地生态环境的影 响更为直接和严重。唐乡人为活动主要体现为季节性放牧过度,即夏秋季草场状况较好 ,基本能够满足牲畜食草需求;冬春季由于牧草稀少、草原载畜量降低,且持续时间长 ,造成牲畜对草场反复啃食,破坏了草根,影响草地再生能力,造成较为严重的畜草矛 盾。
探究高原草场生态退化的原因时,如果仅归结为人口增加、草场超载等未免失之偏颇 。原本和谐的人与草原生态之间具有的适应性关系受到冲击亦是重要原因。草原生态系 统与牧人之间的固有文化连接如前文所述,包括游牧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珍惜万 物的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这些文化构成因素共同组成一个和谐共存的链条,保证 了严酷生存环境中牧人的生存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和谐。
民主改革之前,虽然部落地域大小不等,但草场面积相对今天而言不可同日而语。唐 乡所处位置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仅是藏北安多部落的冬季牧场,光热水条件较好的夏 季完全能够保证再生能力较弱的高原牧草休养生息。自1958年6月本地建立唐古拉山工 作委员会后,先后历经多玛人民公社、乌丽人民公社、唐古拉山人民公社。1958年本地 建立公社后,牧民们开始一年四季固定在唐古拉山以北地区放牧。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 ,本地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基层政权体系替代过去的部落组织。1958年多玛人民公社成立 时,将不足200人分成三个牧业组。1984年唐乡实施包畜到户时,将原有三个牧业组分 割成五个牧业队,按照牧业队划分草场。1994年由于人口和牲畜增加,又将五个牧业队 分割为七个。2000年按照各家各户放牧的位置,以60亩/人的标准将草场边界划定为牧 户。
基层组织形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草场使用、放牧方式等。曾经的大范围牧场逐渐变成 以乡、队、小组等阶梯式分割,游牧社会原有的部落、特殊技能者、老人等组成的权威 中心,由国家行政中心取代。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分配和使用权力转移到权力更集中、 规模更大的国家或国家代表机构——县、公社、大队手里,权力中心运用国家赋予的力 量在过去从未有过的规模上干预自然生态系统。
唐乡牧民可放牧草场范围变化如下:民改前,部落地域之内放牧→民改后,三个牧业 组各组地域内→1984年包畜到户后,五个生产队各队地域内→1994年,七个牧业队各自 地域内→以家庭为单位的牧场范围之内。1984年牲畜包产到户后,由于再不能够大范围 迁移,临近冬季居民点和饮水点的草场,由于利用时间长,放牧强度大,草场退化趋势 严重。彻底实现以牧户为单位分配草场后,将牧民与他们的牛羊牢牢绑定在一块不足60 0亩的地域中(按照一户十口人计)。草场范围不断减小及人口和牲畜持续增加,直接造 成现存的草场季节性超载。
2000年划分草场时,政府保证划分地域50年不变,今后新成立的小家庭草场由新人双 方父母家庭负责解决,即在牧民家庭内部进行资源再分配。如果男女青年均为本地人, 则双方父母家庭从有使用权的草场中各划出一块,加上分出的部分牲畜,小两口按季节 分别放牧。如一队小伙子扎西昂曲入赘至二队布巴利家,扎西昂曲的家长、哥哥白玛达 吉家同布巴利家商量,两家从现有草场上各划出一片草场给小两口,小两口在分给自己 的这两片分属一二队的草场各呆半年。如果仅有一方是本地人,则要么与父母共同生活 ,要么父母划出一块自家草场分给小两口。当草场面积固定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新组 建家庭和人口的增加使草场越划越小,假以时日,它们之间的矛盾必愈发尖锐。
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转换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于原有乡土价值理念 和文化价值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原本和谐共处的人与环境关系产生动摇。唐乡只 是当时广大中国的一个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30年间,国家以接连不断的政 治运动形式,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与文化整合,统一制度,统一信仰,统一学校教育, 统一娱乐方式,缩小消费差距等措施。对于方便居民生活、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做出了重 大贡献,如全社会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人民身体健康在增强,人口的预期寿命在延长。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通过前30年推行的政策,全国各地、各个民族无一例外地经受了 从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到价值观等的全方位洗礼,造成各民族特殊性内容几乎毁弃殆尽 ,原有民间信仰、宗教活动、吉祥物图案、饰物等大多被归入“四旧”而摒弃。在这样 的背景下,原有经济组织形式下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发生断裂成为不可避免。研究社会 主义中国国家建构对环境影响的美国学者朱迪斯·沙芘若(Judith Shapiro)认为“毛泽 东时代强化了中国传统中将自然视为人们可利用对象的观念。同时,又通过压制地方知 识,破坏了传统实践中鼓励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容。在这方面的强度和冲击力,无论与 毛时代之前比,还是和毛之后的经济改革比,毛时代都达到了一个顶峰。”[5](P9)
20世纪50年代后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后,国家随即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开展宗教改革。[6](P83~100)“破除迷信”等一系列政治宣传淡化了当地宗教及民 间信仰,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固守对于自然万物的珍惜敬仰。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意 识形态强力宣传对牧民心理有较大影响,现在本乡牧民家中还挂有社改时的“听毛主席 话,跟共产党走”红绸标语。在国家政权发动的持续性社会一体化运动中,不论地区和 民族处于何种状态,都无一例外转向相同的制度和文化,因而达到普遍的社会同质性。 多年之后,与基层政权影响力相比,本土文化与宗教已经退居次要位置。
随着部落传统习惯法和宗教信仰的约束能力,随着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消失而逐步弱 化,过去由习惯法和宗教信仰约束的行为,改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约。在制度的意义 上,原有乡土社会秩序和价值标准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经济建设的同时没有建立与 此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体系,遵循理想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们在变革的现实 社会中没有找到可以对应的坐标,新成长的一代人既不懂得原有乡土社会秩序体系,又 不能完全理解并遵循共产主义道德准则,于是,经济发展之后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深入 人们的社会生活。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经济建设犹如一剂经济革命催化剂,给本已受到破坏的人 与自然关系带来新的冲击。遵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政策, 各级政府将经济增长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也当成政治任务看待。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中 国国情,这本身没什么错误,问题在于,这样一来“经济发展指标”成为评价各级政府 领导人的主要依据。[7](P111)高原牧区不仅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工业垃圾,片面追求商 品率与出栏率等行政指令,又导致季节性放牧过度、鼠害成灾、草地“黑土滩”触目惊 心等灾害。在经济发展,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失去平衡的生态环境面临崩溃边缘,加 剧了高原传统游牧文化不断弱化趋势。
更大的冲击体现在观念方面。在追求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背景中,原有“惜杀惜售”观 念被批为落后陈腐。鼓励牧户发展牛羊、提高出栏率、商品率是从乡政府到牧业队层层 强调的工作重点。这些发展目标将牛羊等原本被牧人视为同伴的角色,变更为现代社会 视角下人类可以任意征服、使用的资源性工具。虽然可能会使部分牧民短期内发财致富 ,但将永久破坏草原生态环境。行为的背后必定具有理念认同的支撑,当牧民们根据国 家政策安排,开始扩大畜群规模、提高出售比例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新的理念将逐 渐占据主导位置。这样,原本深存于本土民族内心的草场——牲畜——牧民的和谐共存 链条,由于片面强调其中代表着经济收入的牲畜一环而呈失衡状态。以谋利为目的的现 代生产观念如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成为盲目追求增长数字的非理性行为,随之 而来的人性恶化、社会正义衰落,必将导致本身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恶化,也动摇了游 牧社会的观念基础。
无论是前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建设中心,基层政权始终与国 家大背景保持一致。在此过程中,牧民们原本熟悉的生产体系被置换,曾经深存于人们 内心、表现于牧业生活中的诸多自然禁忌与习惯法不再具有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党、团 、妇联等国家建构及意识形态宣传。从这个角度而言,本地的草场退化等环境危机,不 仅是人与草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也是它们之间本身具有的文化发生断裂的 结果。
三、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
进入21世纪,国家认识到环境危机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从而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并于2004年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令人遗憾的是 ,与国家建构、经济发展过程中忽略本土人与当地生态之间固有的文化连接、忽略当地 人主体性地位相似,国家逐步建立起的环境保护法规和管理法则,带有明显的经济发展 优先倾向;实施具体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与自然之间文化 关联的重要性。
从唐乡个案可以看出,现代社会通过提倡均质的国民文化而把地方、民俗和少数民族 文化边缘化,造成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建国后大规模开展的制度革命中, 现代国家按照苏联模式的进化论,将少数民族社会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 制等,并根据主流社会制定的时间表和发展方向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80年代 之后,又按照自身理解的市场经济,指责少数民族不懂经济且对自然环境充满迷信,这 类观点至今日仍颇有市场。前后的理念及行为均忽略了本土人群作为弱势群体的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者利用自己的能力来能动地认识、理解和影响社会 和自然界的能力。[8](P221~222)当生态环境危机不容忽视时,主流社会在思考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态环境保护途径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本土民族主体性,认 为少数民族的难处就是贫困,他们需要的只有温饱,故而注重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不注意 对方的主动参与和能力建设,不尊重地方性知识,将本土生态环境与本土人群分割开来 ,不仅环保效果很难令人满意,而且威胁到本土人群的文化生存。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常将民族地区经济水平落后、生态环境退化归因于当地人。政府推 行的脱贫致富政策如开发矿产、增加山羊比例等,均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当生态环境恶 化到不容忽视时,又将“无序管理、超载放牧”的原因加之于当地人头上,正如有的唐 乡牧民不解地说:我最搞不懂的就是上面一会儿说不要懒惰,要大力发展牛羊;牛羊多 了,又说我们破坏环境,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我们怎么做。无论是在之前的经济发展还 是在之后的环境保护中,本土藏民族的主体性被忽略而过。
2004年,“三江源保护区退牧还草”工程拉开序幕,国家计划逐步投入位于江源核心 区的唐乡3000万元资金,给草场退化、沙化严重的牧户一定补偿,迁移至别处生活,并 最终实现全乡整体移民。移民后的长远生计将由“省政府利用三江源专项经费培训核心 区的青年牧民提高文化素质,加强务农、经商、旅游服务等方面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一 些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等,为今后生存做好准备。”国家制定政策时,对于通用性原则 的注重,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当地民族的文化优先选择权,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生活水平 提高,但从长远观点看,本土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及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将面临重大挑战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社会形态转轨、经济发展或者环境保护等目标,政府多 次动用大量财力,对不同地区、不同族群进行移民搬迁。解放初,象征着从“原始”跨 入“现代”的鄂温克下山定居,为配合农业开发对裕固族等民族进行的“经济移民”, 当前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开展“生态移民”等,无论出自政治意义、经济转型还是生态保 护,移民都成为重要手段之一。经多年实践证明,国家开展移民的美好初衷往往收不到 相应的效果,有些甚至影响到移民后的文化生存。历次移民实践及其效果促使我们反思 ,难道只能将当地人从本土地域剥离出去,使其与自身环境的适应性断裂,转变成为全 国一致性的农业社会或者城镇居民,才能实现当地的社会发展,才能保护生态环境?
虽然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偏远的长江源头,但“世界第三屋脊”的高峻群山依然遮挡不 住现代化的冲击。对于唐乡牧民来说,世代绵延的牧业生活也许将从此画上句号。在宏 大的时代背景中,顽强据守在高寒牧场的牧民及其本土文化被不容分说地挟裹进去,去 留之间本土声音都微弱不堪。唐乡牧民谈到即将面临的搬迁,迷茫之情溢于言表:一个 吃肉的马背上的民族,不会盖房,不会从事建筑,不会使用锄头,搬迁以后怎么办?我 们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年轻人则兴高采烈:好啊,以后不用放牧,可以进城了,而 且国家还给补偿的钱,多好。虽然唐乡全部人口仅1178人,即便国家花钱将他们全部养 起来,也只需要有限的财政支出。但是,从民族文化生存角度考虑,移民并非良策。土 地状况、对于居住及生活地区拥有的可持续权利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本土人群的 生计安宁息息相关,而且与他们的文化生存也有本质联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认同常常 同具体的地域和地区联系在一起,与特定的生态系统、自然和文化资源联系在一起。当 他们丧失对于土地和生计的自主性,当他们的独特文化和认同的环境基础被毁坏,他们 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人的持续存在就受到了威胁。文化生存、文化多样性与环境保护及 生物多样性常常如此绞结在一起,丧失其中一种都会导致两者共同消失。[9](P4)学者 的表述正是唐乡即将面临的危险。
“文化生存”不仅是服饰汉化、民族语言弱化、精神迷茫困惑等内容,还应包括本土 民族与自身环境之间世代发展而成的协调生产、生活方式。“生态保护”也不应只考虑 野生动植物栖息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应关注作为牧业社会基础的高原草场生态环境。“ 发展”的真正含义,不在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数值和速度,而在于社会是否更加“安 居乐业”。正如出自本土的环境保护人士扎多所说:虽然我们这里的牧民比不上北京、 上海的人有钱,可是我们脸上的笑容比他们多,我们心里的幸福感比他们更多。当然, 这不意味着当地人应该被排除于追求生活水平提高的人群之外,而是希望在思索当地的 发展途径时,摆脱纯经济增长决定论,给予本土民族主体性以其应有的位置。
人类学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分析有助于揭示是些什么样的世界观支持良性的或有害的做 法,而且又转而为后者所支持;有助于理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需要的是什么,不仅弄清 楚应当怎样对待环境,而且弄清楚什么样的价值观、信仰、亲属结构、政治意识形态以 及仪式传统会支持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行为。[10](P320)通过对唐乡自然环境与牧业 生活诸因素及其关联性的调查与分析,笔者认为,当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游牧藏族 本身具有的本土文化受到冲击具有直接联系。在人与自然之间,不仅是依存和攫取等功 用性关系,还存在着通过时间建立的文化默契。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群,以自身千百 年绵延的文化理念及行为同当地环境达成协调一致。当这种文化关联被外来文化冲击至 岌岌可危甚至断裂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本土文化的存在危机都将是难以避免的。在唐 乡个案中,民主改革之后,由于国家建构和文化变革等原因,本土文化中的组织形式、 生产方式、观念与信仰等原有符号体系受到冲击,为生态环境恶化与文化生存危机埋下 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至今,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使脆弱不堪的高原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近年来开展的单纯性生态环境保护,又直接威胁到当地游牧文化的生存延续。
希望在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中,注重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 对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族主体性地位忽略的结果;并以此为鉴,在当前 呈蓬勃之势的环境保护浪潮中,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关注本土民族与其 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从而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生态、经济与 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标签:生态防护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长江源头论文; 牦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