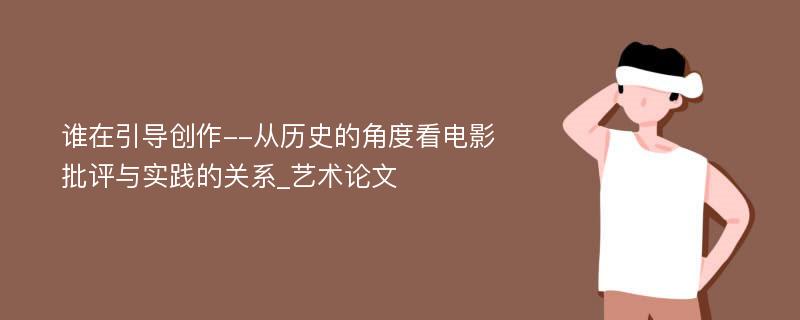
是谁在为创作指路——从历史的角度看电影批评与实践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在论文,看电影论文,角度论文,批评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公认的事实。然而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的电影中,电影批评的具体地位、具体存在形态及其与电影创作的具体联系形式又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电影历史的发展中,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呢?当然,要搞清这一点,并不是这一篇几千字的短文所能做到的。本文只想对中国电影历史一些众所周知的现象做些简单的归纳,以此出发作些初步的探讨。
什么是电影批评?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定义。我想,对电影批评的认识,离不开对电影理论、批评和评论关系的认识。理论通常试图从普遍规律的角度认识电影,影片在其表述中一般只是作为论据出现的。批评和评论虽都是从具体影片出发,电影批评应是主要以电影评论的形式出现,但其关注点又往往超出具体的影片,而表现出作者的理论思考,以区别带有较强个人感性色彩的电影评论。至今仍有人认为,中国电影长期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而只有电影评论。的确,在中国电影历史上,较少有以纯理论形态出现的理论表述,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对电影做过理论思考。事实上中国人对电影的理论思考大多是通过电影批评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创作者对自己电影主张的表述等其它的形式,我们在此不多做讨论)。因此讨论中国电影批评与实践的关系多少反映出中国电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中国的电影批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它:一是其存在形态,二是其在整个电影中的位置。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在中国电影的近百年历史中,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着不同的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影批评主要是以政治和社会性批评为主的形态出现的,这也是与中国电影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当然,在这些批评中也夹杂和渗透着艺术批评的成分,反映着批评者的电影观和对电影艺术规律的认识,然而作为批评的自的则首先是政治和社会性的。即使那些以艺术批评为主的形态体现出来的批评实践,也常常是在以曲折的方式表达着批评者的某种社会或政治性要求。同时,在中国传统的电影观念中,剧作是电影艺术表达的核心因素。这一点也反映在电影批评中,艺术批评的重心也往往是在剧作艺术的方面。而对叙事艺术的讨论离不开叙事的内容。这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电影批评中艺术批评和政治社会性批评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特点,我想是认识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的出发点。
中国电影评论的历史与电影本身几乎一样长,但在最初,这种评论在更多的意义上只是观片随感或电影宣传的文字而已。在二十年代,绝大多数电影刊物都是电影公司办的宣传性刊物,评论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创作者艺术主张的反映,因此几乎谈不上什么对创作者的影响。电影批评作为一种艺术现象的出现,应当说是从三十年代电影运动兴起之后才开始的。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最活跃、辉煌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也同样表现在电影理论批评方面。就电影批评的地位而言,这是中国电影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在党的领导和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一批左翼电影批评家活跃在理论批评战线上,占领了上海各主要报刊的电影评论阵地,有效地左右着电影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影创作的走向。左翼批评家对《粉红色的梦》等影片的批判给蔡楚生的创作转变带来的巨大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从创作思想的角度影响电影工作者的同时,电影批评在艺术上也给了创作者以很大的帮助,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一个在这一时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这与三十年代电影的整体环境是分不开的。
先让我们看一看三十年代为什么能成为电影活跃和辉煌的时期。首先是“九一八”、“一二八”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变促进和造就着中国电影的转变。对民族危机的直接而深切的感受,已使广大电影观众对脱离实际、逃避生活的二十年代商业电影的厌倦明显地表露了出来。由此造成的“明星”公司斥巨资拍摄的《啼笑姻缘》在商业上的惨败也逼迫着电影公司的老板们改弦更张。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开始其争夺电影阵地的努力的。所以,三十年代电影首先是作为一场政治性的电影运动而兴起的。左翼电影运动是在国民党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围剿的严峻政治形势下产生的一场以从政治上变革中国电影为目的的电影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左翼的电影创作还是其批评,在其价值取向的基本追求是一致的。能不能、敢不敢直面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的社会现实,并真实、具体、细致地把这种时代生活呈现在银幕上,这是他们进行创作探索,也是他们认识和评价一个艺术家或一部影片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左翼电影批评的关注重点首先是在影片的思想意义的表达方面。左翼电影运动作为一种以爱国、进步为宗旨的艺术统一战线,要争取最大量的艺术家参加,就不能只以共同的艺术旨趣、艺术追求或共同的电影观来划线。何况当时大多数左翼艺术家和批评家都是些刚刚踏进影坛的年轻人,谁也不具备足以在艺术上领导潮流的艺术经验和威望。因此,左翼电影批评在政治上锋芒毕露、唇枪舌剑的同时,却不能不对那些有爱国进步倾向而在艺术方面与自己有着不同的艺术旨趣和追求的艺术家和作品显示出极宽容的胸怀。至今仍有人批评三十年代左翼评论往往失之过于武断,这并非全无道理,但我以为这主要适用于政治方面。虽然的确存在对一些被认为有背于左翼思想追求的影片,如吴永刚的《浪淘沙》、费穆的人生三部曲等所做出的艺术探索重视不足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在见诸于文字的艺术批评方面,三十年代的电影批评可说是近百年中国电影批评中最心平气和、力求公正准确的。由于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电影批评和创作之间保持着一种良好友善的关系。在左翼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之间不乏艺术方面的讨论或争论,有时还相当激烈。虽然其间不免有偏激之处,但这种争论多是在肯定艺术家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的前提下,在比较平等的气氛下展开的。例如对于著名的左翼影片《春蚕》、《小玩意》等,人们都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从风格追求到细节处理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批评还相当尖锐。但在讨论中人们大都充分注意到了艺术家追求的合理性,并努力注意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这些意见本身的确难免偏颇、粗陋,甚至含有误解或错误,但其采取的方式却是较易为创作者所接受。三十年代电影还处于中国电影的童年时期,人们电影创作的经验和对电影艺术规律的认识都还很不足。那些今天看来十分粗浅的艺术批评和讨论,在当时对创作者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的。这是三十年代电影批评得以较大地发挥其正面效果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活跃局面迅速平静下来。电影批评的作用和影响也远不如前了。“孤岛”和沦陷区逃避现实、粗制滥造的商业电影泛滥,电影评论除极少数继续着三十年代的批评精神顽强地奋斗着外,大多数又沦落到二十年代的宣传和游戏文字的水准上去了。而在大后方,抗日宣传鼓动片几乎成了唯一的影片样式。而且由于战争形势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局限,都无力在造型、声光技巧等方面精雕细琢,电影表现上主要依靠剧作的现象更明显地凸现出来。反映在电影批评中,三十年代已露端霓的将批评重点放在内容和剧作方面的问题更清晰地暴露出来。这种现象在战后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如果说三十年代是一个活跃探索的时代,战后电影则是一个稳健和成熟的时代。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和对中国电影观众及市场的了解和认识,一套以戏剧式剧作为核心,以叙事蒙太奇为主要技巧特征的电影方法已被大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普遍接受。这不仅成为一套创作经验,同时也成为一种批评标准而被广泛运用于批评实践之中。这时的进步电影批评所采用的话语形态虽然与三十年代的左翼批评没有本质区别,可是其对电影的艺术把握已开始更多地渗透到了这些以社会性批评语言所作的表述之中了。当然,做出这种选择也是与当时电影市场和观众的现实需要分不开的。四十年代的电影批评在总结中国电影的创作经验,推动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情节剧史诗电影为主要代表的戏剧式电影创作高潮的出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然而就批评的活力及其视野方面比之三十年代却不免有所逊色。例如对《小城之春》的批判便多少反映了这种批评视野的狭窄。
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电影事业掌握到国家手中之后,运用电影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即成为新中国电影的首要任务。这样,如何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成为新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出发点。这是电影工作者关注的最主要命题,也是观众和电影市场提出的要求。此后中国长期的电影批评之所以更明显地表现出其政治和社会性批评为主、以叙事艺术批评为主的形态特点,也正是基于此。这种电影批评在几十年新中国电影历史中所产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深远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必在此赘述。更引起我兴趣的是在这时艺术批评的位置和功用开始发生的一些微妙变化。在政治前提确定了以后,对电影创作的大政方针提出见解和对影片政治上的评价实际上已不再是批评家的任务,而是领导的事了。虽然也曾出现过如《电影的锣鼓》这样的直接对抗,但其命运是不言而喻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批评家所能做的似乎只是阐释和发挥既有的方针评价。但在此批评家是否无所作为了呢?当然不是。我们常常可以从其艺术批评的缝隙中发觉他们的个性和主张。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新中国电影批评中的艺术批评也在发展着。它们在交流和总结艺术经验的同时,也曲折地反映着作者的社会和政治主张。《创新独白》中提出的“破三神”、“创三新”既是一种艺术宣言,也是一种政治宣言。从反面看,“记要”所列的“黑八论”里把一些从艺术角度提出的主张上升到政治的纲上来批判。也正是因为这些主张的确反映了人们在思想上的某种异议。在那时的不少电影评论中,艺术批评的确是作为人们“艺术”地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手段。这使中国的电影批评在日益严峻、频繁的政治动荡中保持着自己的思想活力。它们在与艺术家交流艺术经验的同时,也在交流着他们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随着“文革”的到来,不仅政治上的异议会招致杀身之祸,艺术上也成了“三突出”荒谬规则的一统天下,电影批评也同创作一样,沦为了荒谬政治的附庸。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又迎来了一前所未有的活跃、探索和丰收的时代。在这当中,电影理论和批评也扮演了前所未有的活跃角色,其所呈现的局面也远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纷繁、复杂。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有力地冲击着电影工作者的思想。刚刚从浩劫的恶梦中醒来的人们,谁也无法预见到其后十余年中国社会会发生那样巨大的变化。这个时代以重新寻回被“文革”丢弃的传统开始,但人们发现,这一传统的权威力量已经无复以往了。时代变了,人们对电影的期望发生了变化。电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都变了,电影也在寻求着新的发展道路。这十几年的中国社会,变革是如此的迅速、频繁,以致于使人们目不暇接,几乎跟不上这不断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随着社会的变革,新时期的电影批评也在不断地出现着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从七十年代末中国电影新浪潮的兴起开始,电影理论批评就和创作实践一起,创造和迎接着中国电影新的辉煌。八十年代的前中期,在以第四代和第五代登上中国电影舞台为标志的两个探索高潮中,理论批评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在中国电影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电影的理论批评也不得不面对同样的、甚至更为严峻的局面。
改革开放大大开阔了中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视野,也为他们对电影理论批评自身的反思提供了新参照。在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最早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中,对人情、人性等以往的主题题材禁区的突破,对创作主体意识的关注,对艺术批评的突出重视,以及艺术观念上的多元化等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切都与同时的创作探索指向了同样的方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创作和理论批评探索的具体命题可能不尽相同,但它们总是以特定的方式互相呼应,相互促进的。八十年代初,由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开始,先后围绕“戏剧性”、“文学性”、“纪实美学”等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有关电影本体论的理论探讨,作为电影理论勃兴的标志,也反映着对论评合一的传统方法论形态的突破,这些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电影规律的理论尝试从批评实践中分离出来。对亟待挣脱“文革”的思想束缚,寻找中国电影新出路的电影工作者们来说,这些理论尝试在更大的意义上起到了巴拉兹所说的那种“在地图上未来的哥伦布画出尚未发现的海洋”的作用。它们在相继迭起的创作探索浪潮中都得到了反响和呼应。在电影理论与批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分流的同时,电影批评也在表现形态上做出了变革努力,它力图脱掉穿了几十年的社会政治批评的外衣,而代之以艺术或文化批评的面目出现,努力从审美功能的角度来把握和评判电影艺术的社会效益,使电影批评真正承担起在思想和艺术的各个方面全方位的推动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重任。尽管从整体上看这一愿望远未实现,但相当多的批评实践为此作出的努力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艺术和文化批评视点的建立,在对第五代的新探索的肯定及推动其影响的扩大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对八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上的飞跃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但是,电影毕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媒介,它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一种建立在商业娱乐基础上的文化工业。在三四十年代的进步电影批评中,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一点。电影事业掌握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电影资本家手中的现实,迫使人们时刻牢记电影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最广大的中国观众接受和承认的基础上。但在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国营电影体制的建立和强化,国家、政治上的认可成了电影成败的关键。虽然为了保证最大的宣传效果,“群众性”仍是对创作的一项要求,而其含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电影批评来说,其任务也首先是对国家对电影的意识形态要求负责,引导观众对影片传达的思想内容的接受。长期以此为目的的批评实践,使人们渐渐淡忘了观众和市场在电影运转中的基础位置。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由于电影作为最广泛而方便的大众传媒,在人民的娱乐生活中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观众别无选择,电影市场自然也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79年新时期电影新潮兴起的时候,正是中国电影观众达到296亿人次的高峰时。在思想艺术上都力求创新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们却都在不自觉中继承了对电影媒介的这一重要特性的忽视。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电视的兴起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多样化,电影的市场在不断地缩小。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电影市场的潜在危机已日益明朗化地凸现在了电影工作者的面前,迫使无论创作者和批评者都无法再无视观众和市场的需要了。与此同时,由于电影批评视野中长期缺乏明确的观众意识,它和观众的关系已渐渐疏远。这种现象虽已引起批评界的注意,但还远未从根本上出现改变。因此,在商业大潮的冲击面前,中国的电影批评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了解了电影批评在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形态与位置,就不难了解批评与实践的关系了。电影批评的作用和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一种参照和启示,帮助创作者更好地认识时代、社会和观众对电影创造的期望和要求,至于它到底能对创作者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则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电影批评本身与电影市场和时代意识形态主潮变革前沿之间的吻合程度。批评能够跟上和正确地把握时代主潮时,就有可能对实践产生较大的影响,反之则将为创作者所疏远甚至抛弃。在我们看到三十年代电影批评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的同时,必须注意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环境所造成的。理论批评顺应了观众和电影市场的变革要求才会产生如此的效果。批评扩大了左翼电影创作的影响,并为创作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然而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观众和电影市场期望和接受这种影片,大多数创作者才会跟着走。这一点在新时期以来电影批评地位的巨大变迁中反映得更加明显。八十年代前中期的中国电影批评紧跟着从政治反思到文化反思的社会思想主潮,为电影创作掀起的一个又一个创新的浪潮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是电影评论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也是一些批评家最风光的时期。但曾几何时,当理论批评的热点还集中在艺术电影探索上时,迅速变革的中国经济形势却把电影骤然抛向了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洪流。在电影生产面对的现实压力下,创作者很快便选择了创作道路的转向,并没有顾忌批评家们的不以为然和抱怨。当第五代的探索电影的热潮悄然流逝的时候,电影批评却还沉溺于对艺术电影的狂热恋眷之中,一边为它唱着挽歌,一边期待着它的再生。由于批评没能迅速地跟上社会要求电影做出的这一转变,人们便很自然地对其表示出了冷淡。当然,看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只有随波逐流、迎合时尚才是批评家的生存之道,而是说不能过高地估计电影批评对创作者的影响力。它并没有什么扭转乾坤的力量,能把创作引向哪里去。真正在为创作指路的是社会的需要和期望。电影批评最多只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给创作者以某些提示而已。就电影批评的整体而言,只有批评和实践在对社会对电影的要求和期望具有某种共识的前提下,电影批评才有可能对创作者的创作思路产生有力的影响。
当然,从流派的意义上讲,电影批评无疑会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但这同样是建立在批评与实践的思想和艺术共识基础上。可是,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流派意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尤其是在社会意识方面,人们往往习惯于新与旧、对与错、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很少考虑到多元并存的合理性。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当中,价值取向当然是十分明确的。新时期以来,电影多元化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形成。八十年代围绕着相继迭起的探索浪潮展开的一场场批评争论,就其本质而言,就已经是流派意义上的争论了。无论创作者还是批评者,作为个体事实上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每种选择其实都只是一种流派意义上的电影主张。问题在于习惯势力使人们仍然更乐于把自己所做出的选择看作是普遍真理,面对其它选择进行批判。其结果恐怕只能是既搞乱了别人的思想,也搞乱了自己的思想。这里并非只是指批评者,创作者也同样如此。人们往往只是由于看不到自己做出的选择本身就是有其局限性的,超出特定的范围就会不再适用,才会努力去充当那种为整个电影创作指路的角色,或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抱怨被引错了路。
相对于在创作思想方面的整体性影响而言,在电影艺术的具体层面,批评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它远远超出流派的意义,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促进着人们对电影艺术规律的认识。批评从作品出发,对影片艺术表现的任何真正准确、精到的读解和分析都可能给细心的创作者带来启发和灵感,从而推动他们未来创作中在艺术上的提高。这是电影批评与创作实践中建立友善联系的最广阔的天地,也是电影批评最能对创作者产生直接影响的领域。对此,我们不用详细展开论述。我想每一个电影工作者都会深有同感的。
总而言之,从对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发展的简单回顾中,我想说明的只是电影批评和创作谁也不是哪个艺术家头脑孤立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和电影的复杂结构网络中的一个有机元素。两者都是在社会和电影的整体形势的决定和制约下扮演着自己的特定角色的。批评和创作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相互制约。批评从创作中吸取营养,创作从批评中获得启示,两者都相互从对方获取灵感。尤其是对电影批评的作用和影响不必期望和评价过高。电影批评不能、也不应承担为实践指路的重负。真正能够给电影规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只能是社会、市场和观众的需要。批评的启示可能会有效地推动创作。但创作的发展往往不必、也不一定会沿着批评所期望的方向进行。巴赞的写实主义理论批评不是就孕育出了与其赞赏和期望的理想电影风格迥异的法国“新浪潮”吗?(“中国电影九十年:历史与现状”研讨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