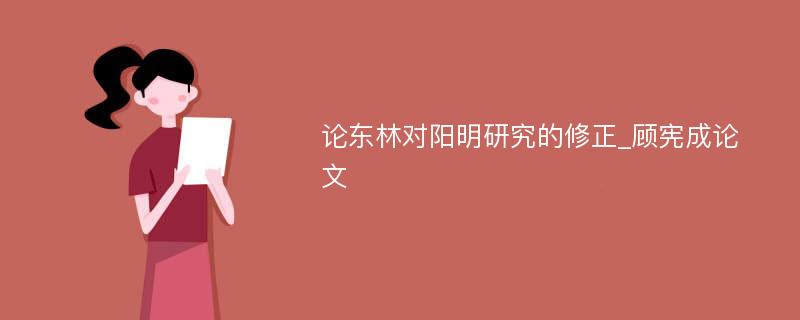
论东林对阳明学的纠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林论文,阳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942X(2000)04—0106—04
王门后学,收拾不住,悉归释氏。这种归趋,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自愿的。但这种自觉自愿显然不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生活觅一安身立命之所,更有以佛教的超然恬淡、清规戒律来破除士林陋习和世俗流弊的动机[1]。然宋以后,尤其至明代, 社会的平民化色彩越来越浓厚,与这种社会变迁相应的是平民教育机构的大量建立,读书人不必再往佛寺中求学,佛寺在士林中的地位逐渐下降[2],佛教欲在社会中求发展,只能于上乞灵于朝廷的庇护,于下依赖着民众的信奉。要使佛教成为引导社会风尚的中坚力量,其实于明代是根本上缺乏可能性的。而尤为糟的是,晚明的佛教不仅不足以承提救世的责任,其本身尚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明季佛教,本处于衰微之中。因朱元璋与佛寺的夙缘,佛教在明代得到了朝廷的着意崇奉,而呈勃兴之象,但终究创新少、因袭多,无生气可说。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促使了明中叶以后的思想大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对佛教的发展无疑同样具有着刺激,明中叶后的禅风日盛,即其显例。明代佛教的四大家,祩宏、真可、德清、智旭,相继出于晚明,也是与这种思想大环境分不开的。但是几位大德的崛起,并不足以挽救日益衰颓着的佛教。黄宗羲批评当时流行的禅宗:
朱子云:“佛学至禅学大坏。”盖至于今,禅学至棒喝而又大坏,棒喝因付嘱源流而又大坏。就禅教中分之为两,曰如来禅,曰祖师禅。如来禅者,先儒所谓语上而遗下,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是也。祖师禅者,纵横捭阖,纯以机巧小慧牢笼出没其间,不啻远理而失真矣。今之为释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师禅勿贵,递相嘱付,聚群不逞之徒,教之以机械变诈,皇皇求利,其害宁止于洪水猛兽哉![3]
这种沉痛的批评并不是来自纯然儒者的偏见,而是真实的佛门时弊,佛门中的真正宗师也有相似之见。有明代禅教殿军之称的鼓山元贤讲:
近日禅人……惟相与学颂古、学机锋过日。学得文字稍通,口头稍滑者,则以拂子付之。师资互相欺逛,而达摩之旨,又安在哉?不特此也,曾见付拂之辈,有颠狂而死者,有罢道还俗者,有啸聚山林劫掠为事者。他如纵恣险恶,为世俗所不齿者,在在有之。灭如来种族,必此辈也。呜呼危哉![4]
佛教虽讲教义,但宗旨毕竟在修行。禅宗不立文字,不尚苦修,注重的是内在精神的开悟,于日用当下接引人,开了极方便法门,但禅宗的开悟,决非是导向现实生活的荡然失守,而仍然是要于现实的生活中来踏实地增长智慧、破除无明。而据引所见,晚明的禅宗,不仅是禅风虚浮,完全已从以作用见性,流为徒呈棒喝机锋而无真性可见,且更为严重的是修持极差、僧德全无,那些“啸聚山林劫掠为事者”,则几近于草寇群盗了。王门后学的逃禅,缘于心学、禅学相似的学风,以及学者开放了的思想,同时,佛门中不乏一、二高僧大德,僧俗的个人感情促进了儒释的合流。但是,整个颓败了的僧风,凭恃着在社会中有功名声望的儒生的影响,其对社会产生的负效应,决非是一、二有德性的禅师的力量所可相抗衡的。更何况,在王门后学处,儒家的立场其实已黯淡,在思想上也是弥近理而大乱真了。因此,欲以晚明时候的儒释合流来整治失序了的晚明社会生活,殆有甚于缘木求鱼。
晚明学术思想与社会意识出现迷离与衰颓,自然便有反思的要求,所以就有学者站出来,在思想上作出反弹,要拨去云雾以见白日。这个代表就是顾宪成与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者。
纠弹的切入点在于对心体——性体认识的反省。因为在顾宪成看来,王阳明之后,学者盛谈玄虚,归趣禅宗,根源就在于阳明四句教的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他说:
管东溟曰:“凡说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窃谓惟“无善无恶”四字当之。何者?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为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个混。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改过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捡择,圆融者便而趋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袭非为中庸,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心者矣。由前之说,何善非恶?由后之说,何恶非善?是故欲就而诘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问,彼其所握之机缄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复作,其亦奈之何哉?[5]
“无善无恶心之体”在王阳明处是否落成个“空”与“混”,这是大可怀疑的。与顾宪成相呼应的,不唯东林学者,当时众多学者都众口一词,对阳明无善无恶之说“明白排决不已”[6]。这种认识, 实质上是完全因为纠弹王门后学的流弊而引申出来的。由流之浊而疑源之清,这是思想史转折中常有的事情,其或为思想新创之必需,但却并非定是事实之真相。黄宗羲讲:“当时之议阳明者,以此(指无善无恶之说)为大节目,岂知与阳明绝无干涉。”[6] 黄宗羲完全将无善无恶说归之于王畿之《天泉证道记》,这固然不对,但黄宗羲以此说明王阳明思想之不同于后来流于性情化了的阳明学末流,洵为的评。当然,东林学者及当时学者,将晚明的玄谈妄作泛滥的思想根源归于“无善无恶心之体”,却无疑也是切中要害的。晚明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颓波靡风,源于道德精神的失落,以及由此失落而带来的价值观念的迷离。王阳明哲学中的良知本体,本是道德主体性的标举,而后世却无限推拓,直将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彻底变成个体基于空灵的非真实性与基于感性的随意性,即顾宪成所说的“空”与“混”。因此,重建道德精神是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而这个道德精神的重建,集中体现在善的心性本性的确认。顾宪成强调,“自昔圣贤论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则,曰诚,曰中和,总总只是一个善”,倘若“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7]。
至此,东林学者算是收拾住了王阳明以后蜕变着的晚明思想。但是,这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回到了王阳明,尽管在表象上是在批评与修正着王阳明。如何将善的心性本性化为具体的价值观念来规范人的现实行为,也就是致良知,仍是一个问题。而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东林学者才真正以返归朱熹哲学的形式,跳出了王阳明哲学的门墙。
东林领袖顾宪成的学术渊源在阳明学,这是不必争论的,但他不囿于阳明学,并能洞察到王学的弊端,进而超越阳明学,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顾宪成的超越阳明学,在形式上,表现为复兴朱熹思想,但因他的思想是直面于现实的产物,故断不宜以为只是简单地返归考亭而已。继承顾宪成事业的学生高攀龙,以及那许多归于东林旗下的同志,学术思想上的门径均宜作如是观。
顾宪成尝比较朱熹与阳明的学说,他认为:
以考亭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性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昔孔子论礼之弊,而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此其所以逊朱子也。[7]
王阳明思想重在良知本体的自觉,但致良知功夫却显得疏略,使得后来的学者无规矩可学,以致于摆去拘束,流于纵恣。而朱熹哲学务求功夫上着力,虽显拘谨,但决不至于放浪。顾宪成看到的晚明景象,并不是拘谨得自缚手脚,而完全已是任性所发,以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为可喜,故东林学者虽出于阳明学,但却知阳明哲学已不足于引导社会,需引朱熹哲学的格物功夫来加以纠弹。
顾宪成对朱熹的格物说推崇备至,他说:
朱子之释格物,特未必是《大学》本指耳,其义却甚精。语物,则本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谓性与天道,子思之所谓天命,孟子之所谓仁义,程子之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张子之所谓万物之一原。语格,则备举程子九条之说会而通之,至于吕、谢诸家之说,亦一一为之折衷焉。总而约之以四言,曰:“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盖谓内外精粗,无非是物,不容妄有捡择于其间。又谓人之入门,各各不同,须如此,方收得尽耳。[8]
按照顾宪成的这种理解,物便是秉于天而根于人的道德精神,其具体的内容是仁义,而格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于行为、于言谈、于意识中去体会与落实这一精神。这个体会与落实,顾宪成是确定了一个标准,而于这个标准中,我们便能看到他实际的方法。黄宗羲讲:
先生(即顾宪成)论学,与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6]
可见,是否学以致用、济物利人,是东林学者评定学问,自然更是做人的标准。这里实涵着两层意思。一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学问,尽管东林学者是侧重于人的道德成就上来提出此见解的,但他们同时也高度肯定着有关民生经济之学的价值。因此,学问在他们这里,便溢出了形而上的性命之学的范围,而包容了诸如历学、算学与农学这样的形而下学。二是仍就道德的论域来看,由这个标准,顾宪成落实道德精神的方法必然就是要强调现实生活的践履。他厌弃悬空去谈论宇宙性命,而要切实来成就道德人生。因此这践履决不仅是一个人的践履,而应是一群人、许多人的践履,更要据此而讲论世道人心,以清议来影响社会。
显然,这就不是朱熹哲学的格物思想的简单翻版了。重名节是明季一个极显著而重要的风尚,如今在目睹了晚明人心放于节义之外,而落著在功名富贵之中的种种世相,加之朝纲混乱的刺激,东林这一堂师友,他们的思想学术,尤其是他们的风骨魅力,无疑成为醒世之木铎。故一时间,大江南北,以及陕、滇一带,追慕之风顿然骤起。
不过,顾宪成毕竟没有点出行为合乎道德性的具体要求,他仍只是在道德自觉的层面上强调“各各成就其是,而因使各各反求其所未至”[9]这样无法使人操作的话语。虽然在他本人,这是极为真实亲切, 但并不足以用来规范世人。实际上,王阳明哲学欲作为指导现实人生的伦理学,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出理论的高楼,而落足在行为的层面上。
东林学者依旧没有完成这一步。在顾宪成,问题尚未呈现,而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心性学问的玄虚色彩复又变得耀眼眩目。高攀龙曾自述自己为学的一段经过:在一次山水清美的舟行中,他感于身心与道体的分离,遂于舟中设席,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自律。如此二月,终于猛省得,道体与身心的分离,是因为精神的牵累。于是,
一念缠绵,斩然遂绝。忽如百斤担子,顿尔落地。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腔心是其区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也。[10]
这天人合一的恢宏气象不能不令人心摇神往,但实在是太高远,勿论平民百姓,即便是饱学士子,真又有几人能抵斯境。更何况,其中还有如此浓重的主观性因素。后来,被称作明代儒学殿军的刘宗周,认为高攀龙是半杂禅门[11],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至于那些与民生日用直接相关的有用之学,虽得到东林学者的认同与肯定,并因此使晚明思想在纠弹心学流弊的过程中,突破了以往一味沉迷于道德话语的旧格局,营造出一种新氛围,有助于当时科学的兴起与推进,但他们自己,却并没有因此而留意于科学。他们的精神,是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的心声,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的言谈,是裁量人物,讽刺朝政。总之,东林学者们志在世道,政治是他们全部意识的聚集点。东林最终由数人之讲学,而变为改造政治的运动,于东林学者而言,诚为得其所在。
因此,晚明思想的裂变,到东林学者处,依旧是没有结出一正果。但东林学者功不可没,因为他们不仅扭转了风气,而且也拓宽了论域,使后来的学者可在一个务实疾虚、以道德精神为核心而又不自限于道德话语的环境中,来为明代近三百年的思想作结。
[收稿日期]2000—03—10
标签:顾宪成论文; 阳明学论文; 读书论文; 心学论文; 朱熹论文; 黄宗羲论文; 哲学家论文; 佛教论文; 东林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