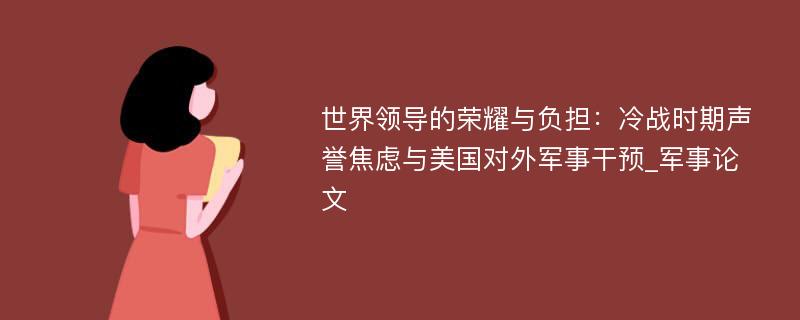
世界领导地位的荣耀和负担: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冷战论文,焦虑论文,负担论文,信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地区冲突和他国内政的频繁干预。美国使用道义谴责、军事援助、经济制裁、隐蔽行动、准军事干预和直接的军事入侵等各种手段,对第三世界进行干预,并卷入多场地区冲突。而干涉的结果,正如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主席威廉·富布莱特所言,不仅不符合美国“自己的最大利益”,“在许多情况下对被干涉的国家也没有达到有益的目的,反而事与愿违”。①然而,就在冷战开始之前的七八年中,面对中国和英国等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遭受侵略,当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甚至不敢提出援助的倡议,更不用说实施直接的军事干预。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在冷战时期走上全球干涉之路?学者们一般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认为与苏联进行战略争夺以维护美国安全、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市场以及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促进民主是美国全球干涉的动力。但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多数干涉并非发生在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核心地区而是发生在对全球战略平衡几乎没有影响的边缘地区,受到美国干涉的很多国家也缺乏对美国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这些国家和地区,例如南朝鲜、南越、台湾、安哥拉,也并非民主体制,倒向苏联也未必会威胁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因此,以往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显然是不完整的,只能解释美国对外干预的部分动机。这些研究实际上忽视了一个重要维度——荣誉,没有看到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除了追求安全、(经济)利益以及试图促进其价值观外,还追求好名声、避免丢脸或受辱。不仅如此,传统的研究也过于笼统和浮泛,没有深入到决策者的心理层面和具体的决策过程去探寻美国干预的动机。事实上,在冷战时期的诸多案例中,美国领导人在做出干预的决策时主要关心的是美国的声誉,而非干涉对象本身的战略和经济价值(美国干预的很多地区并没有多少经济和战略价值)。换言之,美国干预行动的最直接目标是维护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信誉,而不是追求直接、有形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自杜鲁门主义把美国的国际角色确定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从而承担起保卫“自由世界”安全的责任之后,如何履行这一责任和兑现承诺从而维护美国的国家信誉就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忧心和焦虑之事,为此美国决心对任何地方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进行干预,不仅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灾难,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本文尝试引入荣誉和信誉作为分析范畴,把美国的信誉焦虑与战后美国的自我认知和国际角色相联系,通过考察美国领导人的决策心理,对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军事干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动机、后果以及决策者关注信誉的根源进行阐释,以期深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逻辑。②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是关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干预的补充性解释,而非替代性解释。换言之,作者并不否认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目标,而是承认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干预的根本动力是遏制共产主义和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维护信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手段。但是,仅仅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宏观视角不足以解释美国冷战外交中的一些反常现象:任何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都会权衡代价和收益,并选择性地、有重点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但冷战时期的美国却在一些微不足道的边缘地区投入巨大的力量,甚至在明知无法取胜、代价远远超出收益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地进行干预。因此需要深入到微观和心理层面去探寻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根源。 本文无意说明,美国卷入冷战时期的地区冲突完全是为名誉和信誉而战,美国做出军事干预朝鲜和越南的决策显然有着非常复杂的甚至比维护信誉更为深刻的原因,维护信誉的考量在不同的干预行动中,其分量也是不同的。笔者强调信誉的重要性,也并非认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是利他主义的。无论决策者提出的口号是维护美国的国家信誉还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无疑都是追求决策者心中的国家利益。 一、信誉与国际关系 对荣誉和声望的追求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力之一。良好的荣誉和声望可以使人赢得他人的尊敬,让自己感觉良好,并因此获得自尊以及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在失序或无政府的社会里,荣誉还是保障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在古代世界,决策者和外交官就把荣誉作为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关注如何维护国家声誉和保全面子。修昔底德曾指出,雅典之所以建立和维护帝国是出于三个最强烈的动机——恐惧、荣誉和自我利益,“主要是出于恐惧,然后是荣誉,最后才是自我利益”。③ 那么,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荣誉(honor)”?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认为,荣誉包含如下要素:追求名望(fame)和荣耀;避免受辱、丢脸和难堪;复仇或雪耻。④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迈克尔·唐兰博士认为,“荣誉”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追求荣耀、名声和威望;获得尊重和自尊;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尊严获得承认;以及拥有美德。⑤大体言之,国际关系中“荣誉”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方面,指的是良好的声望并因此受到他国的尊重和赞扬;二是消极的方面,指避免丢脸或受辱以维持国家的尊严。 国家荣誉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与荣誉相关的声望、荣耀、尊敬、敬重本身就是国家在对外政策中追求的目标。国家同个人一样,渴望获得认可、称赞和尊敬,也就是获得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承认和较高的评价。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曾言:“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个人从其同伴那里追求对自我评价的确认,只有当别人称赞他的善意、智慧和权势时,他才会完全相信他自以为是的这些优越品质并且陶醉于其中”,国家也是如此,“渴求威望”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固有因素”。⑥19世纪后期普鲁士杰出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曾言:“如果国家的旗帜受到侮辱,国家有责任要求(侮辱者)赔罪,而如果对方拒绝赔罪,那么就宣战,而不管事情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因为国家必须竭尽全力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尊严。”⑦ 二是荣誉在争夺权力和各种有形利益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国家的荣誉受损,声望和获得的尊敬就会降低,其力量也就会相应地受损,特别是在一国被认为缺乏使用自身力量的意志和勇气时,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也就是说,荣誉构成一个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是国家力量中的“无形要素”。良好声誉可以促进国家安全,帮助国家获得财富,乃至权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家常把维护荣誉作为获得利益和权势的手段。基辛格曾指出,“一个国家的信誉可以使其不必使用力量就可以影响事态的演变。而当一国的威望下降时,其他国家就不会愿意把其未来寄托在这个国家的保证之上,这个国家也会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公开挑战。”⑧ 无论一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其声望总是决定其外交政策成败的重要因素,没有国家特别是大国,胆敢忽视自己的声誉,也就是别国对自己的评价与看法。对荣誉和声望的追求是国际权力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为国家或君主的荣誉而发动或卷入战争的例子并不鲜见。在16~17世纪,荣誉和声望是一个君主的生命,丢脸——无论是没有信守承诺还是在战争中败北——都会损害君主的地位和权力。用西班牙国王菲利三世的首相唐·苏尼加(Don Balthasar de Zuniga)的话说:“一个失去声望的君主即使没有失去领土也等同于没有星星的天空、失去光线的太阳和缺少灵魂的躯体。”⑨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并不是为了保卫俄国的安全和重要经济利益,而是为了维护俄国在巴尔干的声望,捍卫帝国的荣耀。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话说,“国家生活就像个人生活一样,总有一些时刻需要忘掉一切为捍卫荣誉而战。”⑩一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荣誉而战。牛津大学经济史家阿维那·奥弗认为,一战期间,无论是在民族主义主导的塞尔维亚、中东欧诸帝国还是在共和制的法国,“从皇帝到军人,从总理大臣到普通战士,每个层次的决定都受到荣誉观念的驱动”。(11)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至少部分为了追求荣耀,他将获得埃塞俄比亚“作为荣耀法西斯政权的手段”,是复兴罗马帝国的第一步。(12) 在美国历史上,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荣誉而诉诸战争或准备诉诸战争的例子。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军舰劫掠美国商船,联邦政府于1797年派代表赴法国交涉,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向美国代表索取巨额贿赂,作为继续谈判的条件。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来,这是对美国国家尊严的冒犯,为了避免耻辱,美国必须准备与法国战斗。他说:“对于一个有能力抵抗的国家来说,在压迫面前屈服……既愚蠢又可鄙。一个国家的荣誉就是它的生命。放弃荣誉等同于政治自杀。……宁愿受辱也不愿冒险的国家迟早会遭受奴役。”(13)美法之间一度进入准战争状态。一战期间美国对德宣战至少部分是出于维护美国荣誉的考虑。在1917年2月3日的演讲中,威尔逊称,在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情况下,美国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与其尊严和荣誉相一致”的行动,即与德国断交。(14)在两个月后的对德宣战咨文中,威尔逊指出美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荣誉”而战。(15) 截止到一战时期,欧洲国家大多数领导人、外交官和将军属于贵族阶层,其观念深受先辈荣誉价值观的影响。一战后,伴随着君主制解体和民主化浪潮,君主和贵族特别在意的荣誉观念遭到批评。为了国王或领导人的荣誉而战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会对国家利益和共同体福祉构成损害。“荣誉”一词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封建残余而被抛弃。但是,“荣誉”一词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再追求声望,不再担心国家的形象。作为对“荣誉”一词的替代,“声望”(reputation)、“威望”(prestige)、“信誉”(credibility)和“形象”(image)等词汇开始流行,特别是“信誉”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的热词。 对“信誉”最简单的定义是言行一致,特别是恪守承诺以及不违背自己宣称的原则。国际关系中的信誉是“决心(resolve)、可靠性(reliability)、可信性(believability)和果敢(decisiveness)的混合物”。(16)“决心”和“果敢”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愿意冒险发动战争来履行承诺和兑现威胁的程度”。(17)“可靠性”和“可信性”则是指国家履行义务和兑现承诺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国际关系中的信誉实际上就是指抵御侵略和信守对盟友承诺的意志和能力。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意冒险来抵御外来威胁和履行保护盟友的承诺,那么就会被认为缺乏决心和软弱,就会失去信誉,其他国家就不会认真对待其威胁或承诺。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信誉实际上成为国家荣誉和声望的委婉语。 与一战前的荣誉一样,信誉是一个国家非常值得珍视的无形资产。国家信誉的好坏可以影响敌国或盟友对自己未来行为的预期,一个国家的信誉越高,就越能阻遏敌国的行动,并可以用非战争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信誉低,那么敌国就不会认真对待其威胁,盟友也会怀疑其承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认为良好的信誉和崇高的声望“具有极大的威慑作用”。(18)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更是直言“信誉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大的资产……一旦被获得,它就可能带来(其他国家)行为的改变。”(19)麦凯恩的这句话虽然夸大了信誉的价值,但也道出了信誉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 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国都把维持信誉和树立声望以及打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以保持盟国忠诚,削弱敌国的意志,以及赢得中立国家的追随。 二、信誉焦虑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军事干预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特别咨文提出,“无论通过直接侵略还是间接侵略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都会瓦解国际和平的基础,并因此威胁到美国安全。……我们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国家的人民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外来势力的征服企图”。杜鲁门告诉美国人,“形势的急剧变化已经把伟大的一责任赋予在我们的肩上”,“如果我们在承担领导责任方面动摇胆怯,我们可能危害世界的和平,而且我们也肯定会危害我们自己国家的福祉。”(20)通过这篇在美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杜鲁门实际上把所谓的保卫“自由国家”抵御“共产主义进攻”的责任揽到了美国头上,这成为美国领导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而能否履行这一承诺成为美国是否守信的标志。从杜鲁门到老布什的美国历届政府都表示愿意承担这一重任,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信誉都与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击退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威胁”和保卫盟友安全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威胁(对敌人)的可信性和承诺(对盟友)的可靠性构成冷战时期美国国家信誉的主要方面。 美国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敌人和盟友乃至中立国家会根据美国过去的行为来预测美国未来的行为。如果美国在面对共产主义“威胁”时表现强硬和信守承诺,那么就会被认为在未来也会这样做;相反,如果美国表现软弱或未能兑现保护盟友的承诺,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相信美国。里根总统的一段话典型反映了美国领导人的这一心理。他在1983年4月27日要求国会拨款支持亲美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以推翻亲苏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权的咨文中说:“中美洲的事态事关所有美洲国家的安全,如果我们不能在那里保卫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要指望在其他地区获得成功。我们的信誉将破产,我们的联盟将瓦解,我们国土的安全也将处于危险之中。”他问道:“如果美国不能对边境线附近的威胁做出反应,为什么欧洲人和亚洲人还相信我们会认真对待他们遇到的威胁?如果苏联认为,只要不进攻美国就不会遭致美国的反击,那么还会有哪一个盟国、哪一个朋友相信我们?”(21)里根的问题实际上自冷战开始以来一直萦绕在美国领导人心头,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内心的巨大焦虑。 在冷战时期几乎每一项主要的国家安全政策中,美国决策者都要认真估量美国的言行会给敌人和盟友造成什么样的印象。(22)在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两次军事干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领导人都把维护国家信誉作为重要理由和主要说辞,声称美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依赖于美国的对手和盟友相信美国具有抵御侵略和保护盟友的决心、意志和能力。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前,南朝鲜在美国决策者心中并没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的演讲中,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开始到日本列岛,然后通过琉球群岛至菲律宾,南朝鲜并不在美国的太平洋环形防御圈内。(23)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却迅速做出军事干预的决定。这不是因为美国重新发现了南朝鲜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极端重要性,而是因为美国认识到朝鲜半岛的事态在考验美国的国家信誉和世界领导地位,而这远比南朝鲜本身的战略和经济价值更重要。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北朝鲜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进攻”南朝鲜是对美国决心的重大考验,涉及美国的威望、联合国的声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国,都在关注美国的反应,用当时美国驻法国大使戴维·布鲁斯(David K.E.Bruce)的话说:“所有的欧洲人,更不用说亚洲人,都在密切关注美国将做什么”。(24)如果美国默认南朝鲜的陷落而无动于衷,那么美国的信誉将丧失,欧洲和东南亚的盟友将对美国丧失信心。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说: 这是对我们作为南朝鲜的保护者这一国际社会已经接受的地位的公开挑战。……鉴于我们具有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如果面对这一挑战时后退,将对美国的权力和威望造成极具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重要地区被苏联代理人征服。(25)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听任南朝鲜陷落将在两个方面损害美国的信誉。一是被苏联认为软弱,从而鼓励苏联在其他地区实施同样的“侵略”。杜鲁门后来回忆说:“我确信,如果容忍南朝鲜陷落,共产党领导人将更加大胆地去征服离我们海岸更近的国家。如果容忍共产党以武力入侵大韩民国而不遭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小国会有勇气抵抗来自较为强大的共产党邻邦的威胁和侵略。”(26)二是损害美国在盟友中的威信,打击盟友抵御共产主义的信心。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的情报评估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在朝鲜不采取行动或苏联在朝鲜获得胜利,将在盟友中产生如下严重后果:(1)在日本,“业已广泛存在的中立渴望将增强”;(2)在台湾,“投靠或倒向共产党的倾向将得到加强,军事士气和政府的效能将下降,被共产党接管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3)“东南亚领导人将失去他们原有的对美国援助抵御共产主义的有效性的信心”;(4)“美国在西欧的声望将遭受巨大打击,如果众多欧洲人发现,苏联的一个小卫星国有能力进行军事冒险,挑战美国的力量和意志,这将导致对这一力量和意志产生严重怀疑”;(5)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将利用美国无力或不愿有效支持与美国共命运的国家来大做文章……提高宣传的调门来强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主义是未来的潮流。”(27) 美国的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欧洲确实在观察美国是否有决心履行保护“自由世界”盟友的承诺。荷兰外交大臣、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主席德克·斯蒂克(Dirk Stikker)告诉美国驻荷兰大使,“如果美国‘允许’南朝鲜陷落,对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影响将绝对是灾难性的”,对西欧的影响也将是“可悲的”。斯蒂克还特别指出:“北朝鲜的进攻是对美国亚洲政策的‘考验’,整个亚洲都将这样做出判断”,“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美国”。(28) 而美国的强硬反应和坚决干预将极大地提高美国的声望,促进美国多项政策目标的实现。陆军部规划与行动司司长查尔斯·博尔特少将在6月28日给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的报告认为,美国的强硬反应将产生如下积极效果:(1)使世界各国对美国以实力支持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决心产生尊敬;(2)提高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声望;(3)给日本留下深刻的积极印象;(4)加强西德政府亲西方的倾向;(5)很有可能使英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6)增加北约采取更具体行动的兴趣和努力;(7)巩固法国在印度支那行动中的士气。(29) 无论选择干预还是不干预,美国决策者最关心的是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可信性,即美国的政策选择可能产生的心理后果。从根本上说,美国最终选择军事干预主要不是因为南朝鲜本身在地缘政治上的极端重要性,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声望和信誉。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1950年9月17日在纽约的演讲反映了杜鲁门政府干预朝鲜战争的心理动因:“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朝鲜对美国并没有特别的重要性,我认为,对联合国其他52个成员的任何国家都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象征,她具有重大意义——她是所有自由国家决心的象征:侵略将遭到坚决的抵抗,对联合国的进攻不会受到鼓励。”(30)美国战略家、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在1966年出版的著作中道破了杜鲁门政府干预朝鲜战争的动因:“我们在朝鲜损失了3万人是为美国和联合国保全面子,而不是为南朝鲜人拯救南朝鲜。这无疑是值得的。苏联对美国行为的预期是我们在世界事务中拥有的最珍贵资产之一。”(31) 越南战争 冷战时期美国实施的代价最高昂的军事干预是对越南的干涉。美国在越南实际上并没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南越倒向共产主义并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危险,也不会改变全球战略平衡。用基辛格的话说,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最遥远”,也与美国的“直接利益最没有明显关联”的战争。(32)美国之所以以代价远远超出收益的方式不断扩大对越南的干涉,甚至在明知不可能获胜的情况下还要把战争打下去,主要不是为了保卫有形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信誉。在美国干涉越南的过程中,有四个重要的关键节点: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取代法国承担起维护南越反共国家的责任;1961年11月肯尼迪总统决定扩大对越南的援助,实行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特种战争”;1965年3~7月约翰逊政府决定扩大对越南的干涉,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入越南;1969年1月尼克松上台后在计划逐渐撤军的同时决定继续援助南越以抵御北越的进攻。在每个节点,维护美国义务可信性的考虑和担心美国放弃南越将导致美国信誉受损的焦虑,都是美国决策者扩大干涉的主要动力,而这成为美国深陷越南而不能自拔的最深刻根源。 1954年4月,当被记者问到印度支那对西方的战略意义时,艾森豪威尔提出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有三个方面:一是其资源,主要是锡、钨和橡胶;二是如果共产党控制东南亚,将有大批人口被置于敌视西方的“专制统治”之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印度支那“沦陷”,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你竖起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块,最后一块肯定也会迅速倒下。因此一旦开始瓦解,就会产生最深远的影响。……这一损失(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控制)带来的后果对自由世界来说将是难以估量的。”(33) 为什么南越陷落,其他东南亚国家,乃至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会倒向共产主义?换言之,多米诺骨牌隐喻的依据何在?在艾森豪威尔等人看来,因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如果美国不能帮助南越阻止共产党的“侵略”和“颠覆”的话,那么就会造成美国没有能力和决心保护盟友的虚弱印象,这将鼓励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气焰,使其更加“胆大妄为”,“征服”其他国家;而那些指望美国保护其安全的国家将会对美国丧失信心,进而倒向苏联的怀抱,出现所谓的“追随”(bandwagon)效应。因此,美国必须在法国撤出越南后承担起保卫南越的重担,阻止北越征服南越,防止第一块骨牌倒下。作为塑造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核心思想,多米诺骨牌理论背后是美国对自身信誉的焦虑:美国必须维护自身承诺和威胁的可信性,为此需要对每一次共产主义“进攻”进行坚决的回击。 这一点,被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道破。两人在1961年11月向肯尼迪提交的绝密备忘录中指出,“美国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对南越负有(保护的)义务。此外,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正式声明中,美国代表曾宣布美国‘将把任何新的侵略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因此,“把南越丢给共产主义不仅会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名存实亡,而且会瓦解美国在其他地区承诺的可信性”,“我们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印度尼西亚与共产主义完全和解(即使不是正式加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可能性”。(34)这一思想成为肯尼迪政府在11月15日决定美国采取除派遣地面战斗部队以外的一切军事措施援助南越、实施“特种战争”的基础。 肯尼迪政府升级对越南的干涉实际上是在美国声望的赌注上加码,特别是随着南越形势的日益恶化,美国更承担不起干涉失败带来的声望和信誉损失,解决的办法是继续扩大对越南的干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1965年2月7日给约翰逊总统提交的主张扩大干涉的备忘录中说: 我们在越南的赌注是很高的,美国在那里的投入也是很大的,美国(对越南负有)的责任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能感受到的无法回避的事实。美国的国际威望和我们很大一部分影响力在越南都处于直接的危险之中。没有办法能让我们卸掉对越南人承担的责任,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离开越南。(35) 1965年3月8日,经约翰逊总统批准,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营在南越的岘港登陆,这是美国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南越的开始。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讲,解释美国“为什么在越南以及为什么越南的形势与美国相关”。约翰逊给出三点理由。一是美国“要恪守承诺”。“自1954年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向南越人民提供了支持。我们一直帮助这个国家进行建设和保卫自己,因此多年来,我们已经做出了国家承诺:帮助南越捍卫其独立。……拒绝履行这一承诺,把这个勇敢的小国丢给其敌人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将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二是“为了巩固世界秩序”。“从柏林到泰国的世界各地的人民把他们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如下信念上,即在他们受到攻击时可以依靠我们。把越南丢下不管将动摇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美国承诺和美国言辞重要性的信心。”三是为了避免“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我们在越南退却并不能导致冲突的结束,战斗将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中重新开始。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教训是侵略者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从一个战场上撤退仅仅意味着为下一个战场做准备,在东南亚就像在欧洲一样,我们必须用圣经的言辞大声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36) 约翰逊三点理由的核心是美国信誉的重要性,如果美国不能履行保护南越的承诺,那么美国的信誉将丧失,其他国家就不会再相信美国,共产主义的“侵略”就会得到鼓励。国务卿腊斯克1965年8月在回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关于“我们的国家荣誉如何与越南相关”提问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腊斯克称,“我们对越南承担了非常明确的义务”,“南越人知道我们有这一义务,共产主义世界知道我们有这一义务,世界其他国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一义务。……如果我们的盟友,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发现美国的义务一文不值,那么世界将面临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危险”。(37) 约翰逊和腊斯克的这些说法并非仅仅是公开场合应对舆论的辞令和为政策进行辩护的说辞,实际上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其私下谈话和决策会议记录表明,约翰逊等美国领导人真心相信美国信誉的重要性,对多米诺骨牌理论深信不疑。1965年7月21日,在讨论是否派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入越南的内阁会议上,国务卿腊斯克担心,“如果共产党阵营发现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承诺实施到底,我不知道他们会在何处停手。”约翰逊也有同感,“确信他们不会停手”,并认为“这是我们越南政策的关键”。约翰逊告诉内阁成员,“如果我们逃离东南亚,未来在地球的每一个地区——不仅在东南亚,还包括中东、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会有麻烦。我相信我们面对这一挑战时后退将打开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38)会上,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担心美国在越南无法取胜,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而“漫长、持久的战争将’暴露美国的弱点而不是力量”,并使国内的支持逐渐减少,因此损害最小的方式是“让南越政府做出决定不再需要我们留在越南”,然后美国撤出,听任南越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约翰逊反问鲍尔说,如果按照这一建议来行动,共产党国家将会说“山姆大叔不过是个纸老虎”,“我们违背了三位总统的诺言,将丧失信誉,这将是无法挽救的打击。”(39) 一言以蔽之,约翰逊政府在讨论美国是否扩大对越南干涉的时候,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越南本身的战略和经济价值,而是不干涉导致的美国信誉损失。用曾广泛报道越战的美国知名记者和作家乔纳森·谢尔的话说,1965年后,“维护美国的可信性实际上已成为战争的唯一目标”。(40)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瑙顿在1965年3月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美国卷入越南的目的“70%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对我们作为越南保护者的名声而言),20%是为了使南越(以及邻近地区)不落入中国人之手,10%是为了让南越人民享有更好和更自由的生活方式”。(41) 在越南问题上,美国领导人对信誉和形象的焦虑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在他们心中,美国的干涉能否成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表现出有决心获得成功,以坚定盟友对美国的信心。也就是说美国的“表现”比“结果”更重要。约翰·麦克瑙顿称: 最根本的是,无论东南亚的形势在未来一至三年内有多糟糕,美国都必须显得是一个“好医生”。我们必须信守承诺,保持强硬,敢冒风险,不怕流血,严重损伤敌人。我们必须展现诱人的外观,避免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会影响其他国家对未来美国在出现影响这些国家利益的情况时将如何行动(包括美国政策、实力、决心和应对这些国家问题的能力)的判断。在这方面,相关的观众包括共产党(他们肯定感到了强大的压力)、南越人民(其士气必须得到鼓励)和我们的盟友(他们必须相信我们可以充当“担保人”)和美国公众(他们必须支持以美国人的生命和威望作赌注的冒险)。(42) 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抱有类似的信念。基辛格在1969年1月撰文指出,越南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虽然不值得美国投入巨大的力量,但美国既然已经做出承诺,承担了义务,那么美国就必须坚持下去,因为这“牵涉的是(盟国)对美国承诺的信心”以及建立在这一信心基础上的世界秩序: 无论嘲笑“信誉”或“威望”等词汇的做法现在多么时髦,但它们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空洞词语,其他国家只有在相信我们坚定可靠时才会采取与我们一致的行动。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失败并不会使很多批评者停止批评,他们会简单地在批评美国判断失误之外加上美国不可依靠的指责。那些将其安全和国家目标寄托在美国承诺基础上的国家只会灰心失望。在世界很多地区——中东、欧洲、拉美,甚至日本——稳定依赖于对美国承诺的信心。因此,单方面的撤出或无意间等同于单方面撤出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抵抗力量的削弱和更危险的国际形势,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决策者能够丝毫不考虑这些危险。(43) 尼克松“越南化”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护美国的颜面,实现所谓“体面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基辛格称,到1969年,“我们在国外的信誉,我们承诺的可靠性和我们国内的团结”都受到越战的“损害”,“在将近一代人的时间里,自由人民的安全和进步依赖于对美国的信心。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一项牵涉到两届政府、五个盟国,造成31000美国人死亡的事业中走开,就像我们是在换电视频道一样。”“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美国不被羞辱,不被打垮,选择一种反战者事后也会认为体现了美国的高贵和自尊的方式离开越南。”(44)在尼克松政府的盘算中,“越南化”战略可以制造一个美国撤军和南越倒台之间的间歇期,让南越而不是美国承担失败的责任,从而维护美国的国家自尊和在盟友面前的信誉即颜面。为此,美国不能在战事不顺时撤出越南,相反,应该通过短期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制造战事顺利的表象,并尽可能地为南越政府赢得喘息的时间。因此,尼克松上台后不仅没有立即将美军撤出越南,相反,还扩大对越南的军事行动,轰炸老挝和柬埔寨,并于1970年4月30日宣布派遣地面部队进入柬埔寨,清剿共产党在柬埔寨的“庇护所”。这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又一次战争升级行动,在美国国内引起极大的争议。尼克松在解释美国为什么入侵柬埔寨时,再一次强调维护美国信誉和颜面的重要性: 如果在摊牌的时候,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关利坚合众国,像一个可怜、无助的巨人那样行事,极权主义和无政府势力就会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今天晚上考验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实力而是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性格。所有美国人今天晚上必须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世界历史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是否有决心面对一小撮人的直接挑战……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这一挑战,其他所有国家都会注意到,尽管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美国是不能指望的。……对美国来说,丢脸的和平将在未来导致更大的战争或投降。”(45) “越南化”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战略,并不能挽救南越政权。美国虽然清楚这一点,但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信誉还必须做出努力挽救的样子。在西贡陷落前夕,福特总统继续用维护美国信誉的重要性来论证美国向南越和柬埔寨提供进一步援助的必要性。他认为,这并非是美国是否卷入印度支那事务的问题,因为美国已经撤军,不会再派兵进入这一地区,这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是否值得依赖的问题”。福特说:“如果我们停止帮助我们在印度支那的朋友……我们将背弃我们自己,背弃我们的诺言和我们的朋友。”(46)基辛格也认为这是其他国家如何看待美国的声誉问题。他这样对记者说: 关于印度支那,我们没有认为世界每一部分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我们也不是说,世界的每一部分在战略上对美国都同等重要。……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我们是否在危机时刻取消我们的援助从而故意让盟友毁灭的问题。这是一个其他人将如何看待我们的根本问题,与我们是否还会卷入那里的事务没有任何关系。(47) 三、信誉焦虑的后果:“帝国的过度扩张” 同“声望”、“形象”一样,“信誉”的实质是他人(国)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存在于他人的头脑中,是无形的和难以测量的,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同时也是自己无法掌控的。这种评价的形成有两个机制:一是观察者通过被观察对象过去的行为来预测其未来的行为;二是观察者透过被观察者的品质或性格来解释被观察者的行为。(48)也就是说,如果被观察者出现失信或软弱行为,观察者通常不会认为这是被观察者在特定情势下的偶然失信和权衡利弊后的妥协,而是将其归因于被观察者的性格或品质,并认为被观察者将来也会如此。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指出了这一点。根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在战争爆发前,雅典颁布麦加拉法令(Megarian decree),禁止麦加拉人进入雅典帝国内的一切港口和市场。斯巴达人向雅典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废除该法令,如果雅典拒绝的话,将导致战争。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演讲,反对接受斯巴达的最后通牒,指出废除该法令虽然是小事情,但雅典也不应该让步,因为这并不能避免战争,相反可能招致更大的灾祸。他说: 不要以为我们不应该为这一点小事情而作战。……对于你们来说,这点小小的事情是保证,是你们决心的证据。如果你们让步的话,你们马上就会遇着一些更大的要求,因为他们会认为你们是怕他们而让步的。……向他们屈服,就是受他们的奴役,无论他们的要求是怎么大或怎么小。(49) 在冷战时代,美国领导人遵循的也是伯里克利的逻辑。他们相信,美国的声望和信誉主要来源于过去和现在的行为记录,如果在面对苏联集团或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扩张”时优柔寡断,违背承诺,就会失去盟友,并鼓励敌人得寸进尺,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因此,美国在面对每一次“共产主义进攻”时都必须恪守承诺和强硬应对以保持其信誉,即使这样做在短期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用约翰逊的话说,“对我们的盟友而言,我们必须是最可依赖和最长久的朋友;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我们则是毫不动摇的坚定的对手,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个地方的妥协很可能导致在所有地方的失败。”(50)如上所述,这种信誉焦虑贯穿于冷战的始终,带来两大后果:一是鼓励好战精神和强硬政策,使任何妥协和退让都变得不可能;二是使美国无法分清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导致美国频繁实施对外干预。强硬政策和频繁的对外军事干预让美国在很多无关紧要的国家和地区耗费大量资源,使美国的实力到70年代后期已不足以保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和履行承担的义务,出现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帝国的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51)美国的战略地位和国家信誉不仅没有提升,反而下降。 维持美国信誉的需要常常被用来反对任何妥协的主张,其背后论证的逻辑是:如果美国不做出强硬反应,实际上是对“侵略者”的绥靖和鼓励,并因此在未来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在每一次挑战面前美国都必须保持果敢和强硬,哪怕挑战很小。惯常的说辞是:这是对我们决心和意志的考验,妥协退让将导致我们的声望和信誉受损,未来将不会有人再相信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强硬以证明我们的决心,并击退侵略以证明我们的能力。(52)在这一说辞下,哪怕在最不重要地区的最微小的妥协也会带来长远的后果,用基辛格的话说,“不能应对今日的挑战将在未来诱发更严重的危机”,(53)因此任何让步都是不可取的,展示强硬是美国的唯一选择。其结果是小问题经常被放大,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小问题被视为对美国决心与意志的考验。正如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观察到的,“在世界政治边缘地带的很多争端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至关紧要的是,在这些争端中,美国和苏联是否被认为履行了其承诺的义务”。(54)而一旦实施了干涉,实际上等于在声望的赌注上加码,为了避免失败,只有继续增加赌注,即增加军队和资源的投入。约翰·麦克瑙顿在1966年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讨论美国干涉越南的代价时说:“在每个决断关头我们都在赌博,在每个关头,为了避免不履行我们的承诺对我们的效能带来的损害,我们都提高了赌注。我们没有不履行承诺,因而现在的赌注(和承诺)非常之大。”(55) 对信誉的重视使美国把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党势力的壮大或苏联的渗透都视为对美国决心的考验,美国都必须干预,而不管事态本身究竟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有多大影响。肯尼迪总统在被暗杀前两个月曾说:“我完全知道,每一次,一个国家不论它距离我们的国界有多么遥远,只要消失在铁幕之后,都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56)在1961年5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卷入一场东南亚丛林边缘地带的战争是否明智,腊斯克回答说: 如果你不关注边缘,边缘就会发生改变,接着你就会发现,边缘即中心。我的意思是说,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是相互依赖的。这在今天——也就是世界革命必然发生的理论通过具体行动正在与自由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对抗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不影响到另一个地方的事态。(57) 这导致美国不能分清哪些是重要利益,哪些是边缘利益,美国要承担起保护所有“自由国家”的责任。艾森豪威尔总统言道:“就像没有任何武器渺小得可以忽视,没有任何地区遥远得可以不顾一样,没有任何一个自由国家卑微得可以遗忘。”(58)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冷战时期美国会在并不牵涉美国重要战略利益和全球战略平衡的边缘地带与苏联进行激烈的较量。正因为这些地区是战略地位并不重要的边缘地区,美国领导人往往选择无形利益即美国的声望和信誉,而不是有形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来论证干涉的必要性。 金门和马祖无论对美国西太平洋的防御还是台湾的安全都无足轻重,但这并不妨碍美国做出以武力保卫这些沿海岛屿的决策,因为展示美国的决心非常重要。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到,“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沿海岛屿在军事上对保卫台湾并非是必需的,但除一人外的所有人都承认这样一个压倒性的事实:这些岛屿的陷落将产生糟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心理影响,因此他们相信我们应该保护这些岛屿。”(59)萨尔瓦多是一个对美国没有丝毫战略和经济价值的国家,但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把自己的声望和信誉押在西半球一个最弱小、最残酷也是最不得人心的萨尔瓦多政府身上的时候,萨尔瓦多就被赋予重大的国际意义,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如里根的一位外交政策顾问所言,“萨尔瓦多本身实际上并不重要”,但“我们必须建立信誉,因为我们处于麻烦之中”。(60) 对任何一个理性的领导人来说,世界各个地区不可能对美国都同等重要,总有一些地区属于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属于边缘利益,但是对信誉的重视使美国把各个地区看得同等重要,无法区分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8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承担义务过多’是很有感染力的说法,但是我们如何能从南朝鲜或南越撤军?我不知道哪些地区不重要。”(61)基辛格在1975年3月的演讲中称,美国必须在所有情况下维护美国的信誉,让美国的盟友相信美国值得信赖和依靠,因为“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国不可能执行一项有选择地维护美国可靠性的政策。我们在世界某一地区抛弃朋友不可能不损害其他朋友的安全。”(62)乔纳森·谢尔称美国的这一信念为“信誉教条”(doctrine of credibility): 为美国信誉而战不是追求有形目标,而是在保卫一种形象——国家实力雄厚而且有决心使用这一实力的形象。根据信誉教条,美国是在从事一场全球公共关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世界任何地方的挫败,不管这个地方有多么小,都会瓦解美国的整个权力结构。(63) 这导致证明美国的可信性和维护美国的信誉成为永远没有尽头的任务,甚至在明知无法获胜的情况下美国也必须进行干涉,因为不履行承诺,也就是拒绝做出干涉的努力,将表明美国的失信和软弱,而这比干涉失败对美国信誉和声望的损害更大。这就是麦克瑙顿所说的“好医生”方式:即使美国明知道无法拯救南越,但是也必须做出努力挽救的样子,以保持美国作为“好医生”的名声,因为这一名声对遏制对手、安慰盟友非常重要。 为了防止失败而造成的信誉受损,美国必须投入巨大的资源,甚至不惜代价。多位美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愿意为捍卫盟国的自由付出任何代价。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不仅在国内而且还要在全世界“捍卫人类的权利”,而“为了保障自由的生存和胜利,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一切重担,面对任何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和反对一切敌人”。(64)在1964年9月白宫内阁会议上,国务卿腊斯克称:“他非常希望不要为(越战)开销制定上限,他感到只要能赢花多少钱都值得”。(65)当被问到美国要为信誉付出多大代价时,腊斯克说:“在履行光荣的义务时会有代价,过去一直有代价,将来也会有代价。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看一下过去30或40年的历史,不履行义务的代价要比履行义务付出的代价大得多。”(66)在196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约翰逊直截了当地说:“在三位总统领导下,我们的目的一直是支持越南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实施我们的战略和推行我们的政策需要一大笔防务开支。世界最富裕的社会当然能承担得起为其自由和安全必须付出的任何代价。”(67) 但是,不惜任何代价以维护美国信誉的政策是不可持久的,因为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美国承担过多“义务”、在次要和边缘地区(特别是越南)花费大量资源的结果是美国遏制苏联的能力被削弱,战略地位下降,其信誉——威慑敌人和保护盟友的决心和能力——受到严重损害,导致出现厄尔·拉夫纳尔所说的“信誉悖论”(paradox of credibility):(68)为了维护美国信誉而实施的干涉政策反而削弱了美国的信誉。越战失败带来的信誉损失以及“过度扩张”导致的战略优势的丧失使尼克松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国的政策,试图减少美国的承诺和义务。 四、信誉焦虑产生的根源 在国际关系史上,重视声望和信誉是大国常有的现象。小国自身的安全缺乏保障,需要依赖大国的保护,一般不会在意其行动传达的信息。小国通常也不会承担保卫其他国家的责任,自然也不会担心不履行责任造成的信誉损失。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普通国家会把千里之外的地方性冲突视为自己的重要利益而予以关注或进行干预。只有大国或帝国才会因其利益的广泛性和责任的普遍性而把边缘地区的动荡与帝国核心地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荣誉和信誉的重视通常与大国地位,特别是帝国身份相关。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曾谈到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与西班牙为维护信誉而陷入长期的战争有关。西班牙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多次用兵尼德兰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反叛地区脱离西班牙统治引发其威望的受损和多米诺骨牌效应,担心如果丢掉尼德兰,哈布斯堡王朝就会失去德意志和意大利,接着就会是美洲、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其结果就是西班牙“陷入广泛持久的消耗战”。(69)罗马帝国历史上也曾出现类似的现象。因此,国际政治学家杰克·斯奈德认为:“把对帝国边缘的威胁与对帝国核心的威胁紧密联系起来的倾向并非美国所独有,大多数主张捍卫广泛义务的帝国战略家都担心多米诺骨牌会倒下”。(70) 但是,没有哪个大国像冷战时期的美国那样如此重视声望和信誉。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虽然受美国的保护,但并没有对美国承诺的可信性表现出美国领导人那样的关切,并不认为美国有必要对共产主义的每一次推进都做出强硬反应,他们甚至反对美国扩大对越南的干涉。同样,作为冷战时期的大国,苏联在冷战时期曾多次面对与美国类似的挑战,但苏联并不认为做出让步会损害其信誉或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1946年在伊朗、1949年和1959年围绕柏林问题以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都做出了退让;在几次中东战争中,苏联也听任其代理人失败而没有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71) 如果把冷战时期的美国与二战前的美国做一纵向比较,我们会发现,战前的美国也是一个大国,但美国领导人似乎并不在意美国的信誉。在珍珠港事件前,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的战争似乎都与美国没有关系,美国人也不觉得希特勒在西欧大陆对民主国家的征服损害了美国的声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无疑直接破坏了美国一手建立的一战后远东国际秩序,威胁了美国在《九国公约》中倡导、美日都承诺恪守的“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原则,但美国拒绝干预中日战争,甚至拒绝停止向日本出口可用于战争的物资,实际上是不认为美国拒绝维护自己倡导的原则和秩序会损害其国家荣誉。 那么,为什么冷战时期的美国如此焦虑自己的形象,把声望与信誉看得如此重要?美国领导人信誉焦虑的最深刻根源在于二战后美国人对其国家身份和世界角色的认知——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冷战的性质与核时代的来临则加剧了美国领导人的信誉焦虑。 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和领袖身份 荣誉感与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和身份意识密切相关。战后美国把自己视为世界领袖,承担着抵御共产主义“扩张”、保卫“自由世界”和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责任,这种自我身份意识和世界领袖地位是美国信誉焦虑的最主要原因。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相信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国际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承担着领导世界的责任。实际上,到二战结束时,美国人,无论是决策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已经下决心要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1945年12月19日,杜鲁门在关于建立国防部的特别咨文中明确提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家间起领袖作用。”(72)乔治·凯南也认为,“美国人民应该感谢上帝给他们带来(苏联)无情的挑战,让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全部安全依赖于他们的团结和接受显然是历史希望他们承担的道义和政治领导责任”。(73) 作为世界领袖,美国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而“荣誉承载着一系列的责任,如果要获得荣誉,那么就必须恰当地履行责任。”(74)那么,世界领袖的责任是什么?战后初期,美国人心中的世界领袖责任是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际秩序,通过大国合作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以避免20世纪30年代悲剧的重演。随着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和东西方分裂,美国的角色变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其领导责任逐渐变成支持和保卫“自由国家”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进攻”。也就是说,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有责任保护“自由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安全。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的演讲是美国承担这一责任的开始。根据杜鲁门主义的逻辑,美国的责任不仅是保卫“自由国家”的安全,还包括维护战后美国一手缔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的安全不仅仅依赖于均势和结盟,还依赖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稳定;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破坏和平和威胁自由的事态,无论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家内部的冲突,美国都有责任过问。 在美国领导人心中,这一责任异常重大,如果美国不能履行好这一责任,不仅美国的安全,还有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战后国际秩序也会崩坍。肯尼迪称:“我们是自由之门的柱石。如果美国退缩,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倒向共产主义集团。”(75)腊斯克认为:“美国承诺的完整性是整个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76)基辛格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鉴于我们的中心地位,我们失去信誉将导致国际混乱”。(77) “责任”“义务”“承诺”成为冷战时期美国领导人频繁使用的字眼,而为了履行美国承担的领导“责任”,美国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直到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后,美国才开始检讨领导地位的代价。从70年代初开始,美国试图逐渐减少其承担的保护“自由世界”的义务。 美国夸大自身地位和作用的背后是对中立国家和盟国的不信任。美国领导人通常认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制度脆弱,领导人天真幼稚,缺乏经验,不了解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易被苏联操纵。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认为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领袖在政治上不成熟、外交上无经验、意识形态上不可靠,“具有走向泛亚主义和极权主义哲学的危险”。(78)其盟友包括西欧盟友在美国人眼中也缺乏抵御苏联进攻的坚定意志和决心,甚至见风使舵,美国在履行承诺时的优柔寡断和对抗苏联挑衅时的软弱无力都可能导致这些国家与苏联妥协。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称:“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缺乏团结的意识、信心和共同的目标,即使是在自由世界最同质、最发达的地区——西欧,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决心,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几乎肯定会士气低落,我们的朋友不仅会成为我们的负担,而且最终会增强苏联的力量。”(79)虽然美国做出了保护欧洲的承诺,并建立了北约,但由于美国与欧洲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历史上美国又奉行过孤立主义政策,因此欧洲人还是会怀疑美国承诺的可信性,担心美国可能会抛弃欧洲。为此,美国需要不断地通过语言和行动让欧洲盟国放心:美国会信守承诺,值得信赖和依靠,不会抛弃盟友。 现代政治学认为,“信誉是领导地位的基础”。(80)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声望可以换来被领导者的忠诚、尊敬、信赖和追随,“取得通过其他方式很难取得或甚至不可能取得的目标”,因而是领袖人物维护其领导地位不可或缺的“道德资本”。(81)而“信誉是通过领导人不断采取的日常行动来赢得的,信誉不会因为职务或头衔而自动到来。”(82)领导人必须不断地通过言语和行动坚定地捍卫原则和履行承诺来积累和维护其道德资本,否则就会被认为不值得信赖,从而失去其道德资本,甚至领导地位。 公民社会中的领袖如此,国际社会中的领袖也是如此。美国领导人坚信,信誉是美国领导地位的基础,为了维护这一地位,需要不断地证明美国的可信性和决心。也就是说,美国在“自由世界”中的领袖角色要求美国承担起保护“自由国家”安全的责任,卷入世界各地冲突,并且尽一切手段来获得胜利,以便维护美国的信誉。这是冷战时期美国信誉焦虑的最深刻根源。维护美国的领导信誉实际上成为美国冷战时期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领袖”不过是“世界警察”的委婉语。 对冷战性质的认知 美国领导人对信誉的重视还与其对冷战性质的认知有关。冷战不仅是一场地缘政治之争,更被视为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竞赛,即一场“争取人类心灵”的战斗,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认为苏联的威胁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更是心理上的,预测苏联“不会放弃”“任何使美国受辱或丢脸的机会”,“特别是可以被用来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方法丢脸的情况”。该文件还指出,苏联“正在寻求向自由世界显示,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在克里姆林宫一边,那些缺乏力量的人将衰朽无望,注定败亡”;“在一些地方性事件中,苏联威胁或蚕食的目的不仅是获得当地的利益,还旨在增强整个自由世界的紧张焦虑和失败主义”。(83)一直到1980年,该文件的主要起草者保罗·尼采仍然坚信冷战本质上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战争,称“政治—心理竞赛是这场扩大‘我们’阵营和缩小‘他们’阵营的斗争的核心”。(84) 而在对人心的争夺中,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主要代表的美国的形象和声誉就显得异常重要。美国的坚定、果断以及言必行、行必果可以极大地振奋“自由世界”的士气,产生向心力;而一个轻诺寡信、优柔软弱的美国则无法赢得人心。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在争夺人心的斗争中,美国信誉的下降会带来两大后果。 一是美国的软弱将造成美国力量衰落的表象,而这种表象等同于实际,会在盟国和中立国家带来恐慌心理。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采访中,肯尼迪曾解释说,危险不在于苏联人真的会从古巴发射导弹,如果苏联真想发动一场核战争的话,那么苏联在自己国内部署核武器就足够了。危险在于,如果苏联在古巴成功地部署了导弹,而且被公开披露出来,那么“将造成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改变的外观,而外观将促成现实”。(85)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Thomas H.Moorer)1972年初在参议院作证时说:“仅仅是苏联战略优势的表象就会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和谈判地位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即使这种优势对一场全面核战争的结果没有实际的影响”。(86)也就是说,对权势的看法比真实的权势本身还重要,美国受到羞辱或未能履行承诺将会造成美苏权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印象,继而在“自由世界”和中立国家带来恐慌的连锁反应。约翰·加迪斯对美国领导人的这一心理评论说, 这里的含义令人惊愕。世界秩序,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安全已经变得既依赖力量对比的实况,也同等程度地依赖对这一对比的认知。而且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习惯上被责成来制定政策的国务活动家们的看法,还包括大众的看法——国内的和国外的、知情的和不知情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在这些观众面前,即使是权势关系变化的表象也可能产生灰心丧气的后果。基于诸如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或军事潜力的传统标准的判断现在不得不对照形象、威望和信誉考虑予以权衡。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被认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利益的数目和种类,并且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区别。(87) 二是美国信誉受损或声望下降会给人留下共产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活力、历史在苏联和共产党一边、共产主义代表未来潮流的印象,而一旦这一印象形成,就会促使其他国家追随苏联而不是追随美国。正如1950年4月杜勒斯在一份反对美国放弃台湾的备忘录中所言,美国的退却只会给敌人造成美国“不打算在北大西洋美洲以外的地区坚守阵地”的印象,会让人们得出共产主义代表未来的结论,而“一旦人们感到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连我们在这一潮流面前都在退却”,那么地中海、近东、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就“支撑”不住。相反,“如果我们在一些充满疑虑的地方迅速采取果断和强硬的立场来展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那么这一系列灾难就可能被防止”。(88) 正是美国领导人对冷战乃是人心之争的认识使其格外重视美国的形象和声望,把美国的信誉与冷战的成败联系在一起。 核时代的来临与核威慑战略的运用 冷战是核时代出现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由于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可能导致交战双方共同毁灭这一可怕前景,核时代的来临和核武器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国家的行为方式,也改变了外交决策者的思维方式,核威慑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基本军事与安全战略,通过争夺边缘地区以展示强硬形象和建立信誉成为确保核威慑战略成功的主要手段。 威慑战略的成功通常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实力,二是可信性。所谓实力是指防御者具有让进攻者付出巨大代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可测度的,也是比较容易让对手感知的;而可信性是指防御者让潜在的进攻者相信防御者有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进行报复的意志和决心,军事报复的威胁越可信,威慑政策就越可能成功。报复的能力固然重要,让对手相信自己有报复的决心更重要。威慑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其实质是影响对手的心理与认知过程。 那么,如何影响对手的心理?那就是通过自己现在的行为影响对手对未来行为的预期。威慑理论认为,外交政策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任何外交行动都会传达出信息,他国根据这一信息来预测该国未来的行动。在危机中优柔寡断的国家等于告诉自己的对手和盟友,自己未来也不会直面挑战和风险,而这只会鼓励对手提出更多的要求,甚至冒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不涉及重要利益的情况下都果断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就会给潜在的进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威慑理论家托马斯·谢林(89)的著作和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他对威慑理论的研究特别重视可信性的建立和维护,并把一个国家的过去行为与其可信性,也就是信誉联系起来,认为过去的行为记录建立起来的名声和信誉对遏制战略的成败至关重要。他在谈及美国为什么必须与苏联在一些边缘地区进行争夺时说: 我们卷入这些地方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威胁是相互关联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告诉苏联人,我们必须在此地做出反应,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当我们说我们将在别处做出反应时,他们就不会相信我们。……丢脸的最大危害在于苏联不会相信我们以后会在其他地方做我们目前在这里坚持要做的事情。我们的威慑能否成功取决于苏联(对我们行动)的预期。(90) 因此,他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不能丢面子,而“需要不断地用行动来证明其决心、接受对其意志的考验”。他说: 经常有人认为,“面子”(face)并非值得维护的资产,它是不成熟的标志,一个政府不可能因为忍气吞声而丢面子。但是有一种更值得认真对待的“面子”,现代的术语把这种“面子”称为“形象”,指的是别国(其领导人)对一国未来会如何行动的预测和看法。这与该国的重要性、地位或“荣誉”无关,而与该国的行为声誉有关(reputation for action)。如果有人问这种“面子”是否值得为之战斗,我的回答是这种面子是极少数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之一。(91) 也就是说,名声和可信性成为遏制战略能否成功的保证和阻止对手挑衅的防波堤。不仅谢林,冷战时期的绝大多数威慑理论家都对此深信不疑,这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数十年来,维护信誉的必要性成为几乎(美国)每一位外交政策从业人员训练的一部分,成为类似既定法则的政治学常识。”(92) 对声望和信誉的关注无疑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被放大了。关于核战略的基本事实是:核战争是不能启动的,因为没有人能在一场核战争中获胜。威慑的目的就是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而要实现这一目的除了壮大自己的核武库之外,更依赖在敌人心中制造这样一种印象:你足够强悍,甚至不惜与对手同归于尽。那么美苏之间能做的,一是打“口水战”(rhetorical battle),在象征和符号领域进行争夺;二是在边缘地区表现强硬和战胜对手以建立信誉,因为在边缘地区进行较量不会引发核大战,越南战争就是边缘战争的典型。一旦决策者坚信这一点,那么在越南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值得。这正是美国深陷越南而难以自拔的根源,正如乔纳森·谢尔所言: 既然越战这样的有限战争是你唯一能进行的战争,那么你就必须获胜,因为你已经把全部的美国力量的可信性都押在这样的战争上。因此,不论这场战争多么疯狂,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论你在战场上追求的目标多么没有意义,你都会觉得除了以维护美国力量可信性的名义继续下去外别无选择。(93) 简言之,显示决心和维护美国的可信性成为美国核战略的核心。核武器的出现强化了美国对国家信誉的重视,加剧了美国的信誉焦虑。 五、结语 二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众多国家所追随和拥戴,成为对国际局势和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全球帝国”和“世界领袖”,享受着“帝国”的光辉和“领袖”的荣耀。但帝国身份和领袖地位也给美国领导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和道德负担:如何在一个核时代扮演好领导国的角色,维护美国作为盟友保护国和“自由捍卫者”的信誉,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历届领导人忧心和焦虑之事。这一焦虑与对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传播的恐惧相互促进,共同促使美国走上全球干涉之路,并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冷战结束后,尽管苏联的威胁和意识形态竞争不复存在,但美国仍然重视信誉问题,把信誉作为领导世界的重要道德资本。在维护地区稳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对人道主义灾难、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美国都把维护自己作为世界领袖和国际秩序捍卫者的信誉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而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和南海争端更是被视为是对奥巴马政府信誉的考验。只要美国仍然以世界领袖自居,美国对外政策就难以摆脱信誉因素的影响,美国领导人就会继续为如下忧虑所困扰:如何在一个纷乱的世界上,让各国相信美国仍然有决心和能力保护盟友安全、应对各种威胁、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从而赢得盟友的追随和阻遏潜在对手的挑战,继续享受领导地位的荣耀以及这一地位带来的种种实际的好处。 注释: ①J.威廉·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吴永和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 ②关于“荣誉”“声望”和“信誉”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对荣誉的追求如何塑造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际关系学家已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方面出版了不少成果,但历史学家将其运用到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成果还寥寥无几。罗伯特·麦克马洪1991年发表《信誉与世界权力:解释战后美国外交的心理层面》(Robert J.McMahon,“Credibility and World Power: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in Postwar American Diplomacy,”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Fall1991,pp.455~471)一文,对维护美国信誉的考虑如何影响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考察,是目前仅有的研究成果,给笔者以启发。但该文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和透彻,对美国决策者重视信誉的原因的解释过于简单。关于多米诺骨牌理论与威慑战略的研究也与本文主题有一定的关联,对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帮助,但这些研究只是间接涉及信誉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干预问题。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有:Geoffrey Best,Honor Among Men and Nations:Transformation of an Idea,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2; 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Elliot Abrams,ed.,Honor among Nations:Intangible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1998; Barry O'Neill,Honor,Symbols,and War,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 Daryl Grayson Press,Calculating Credibility:How Leaders Evaluate Military Threa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Michael Donelan,Honor in Foreign Poli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Christopher J.Fettweis,The Pathologies of Power:Fear,Honor,Glory,and Hubris in U.S.Foreign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关于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威慑战略的研究主要有:Robert Jervis et al.,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eds.,Dominoes and Bandwagons: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③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ol.1,trans.Charles F.Smith,London:William Heinemann,Ltd.,1956,p.129. ④Donald Kagan,“Honor,Interest,and the Nation-State,” in Elliott Abrams,ed.,Honor among Nations:Intangible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p.2. ⑤Michael Donelan,Honor in Foreign Policy,p.1. ⑥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50. ⑦转引自Avner Offer,“Going to War in 1913:A Matter of Honor,” Politics & Society,vol.23,no.2(June 1995),p.216. ⑧“The Challenge of Peace,” Address Made by Henry Kissinger before the St.Louis World Affairs Council at St.Louis,Mo.,May 12,1975,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72,no.1875,June 2,1975,p.206. ⑨Geoffrey Parker,“The Making of Strategy in Habsburg Spain:Philip II's 'Bid for Mastery,' 1556~1598,” in Williamson Murray,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States,and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26~127. ⑩转引自William Wohlforth,“Honor as Interest in Russian Decisions for War,1600~1995,” in Elliott Abrams,ed.,Honor among Nations:Intangible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p.35. (11)Avner Offer,“Going to War in 1913:A Matter of Honor,” p.214. (12)George W.Baer,The Coming of the Italian-Ethiopian Wa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169. (13)“The Warning No.3(February 21,1799),” in Harold G.Syrett,ed.,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vol.2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1979,p.520. (14)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Germany,February 3,1917,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65397&st=&st1=.(2014年9月13日获取) (15)“For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April 2,1917; Woodrow Wilson,War and Peace:Presidential Messages,Addresses,and Public Papers(1917~1924),edited by Ray S.Baker and William E.Dodd,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2002,vol.1,p.14. (16)Robert J.McMahon,“Credibility and World Power: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in Postwar American Diplomacy,” p.455. (17)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5. (18)Dean Acheson,Present at Creation,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69,p.405. (19)John McCain,“No Time to Sleep,” 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24,2002,http://www.mccain.senate.gov/public/index.cfm/opinion-editorials?ID=18eSa491~5583~4cbc-bfa2~33f7e928f601.(2015年4月6日获取) (20)Henry S.Commager,Documents of American History,vol.2,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58,pp.705,706. (21)Reagan' s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Central America,April 27,1983,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1245&st=&st1=.(2015年3月29日获取) (22)帕特里克·摩根认为,对自身形象和信誉的关注至少对以下四种国家安全决策产生了影响:一是为支持盟友而对军事冲突实施干预的决策;二是发展武器系统的决策;三是关于如何部署美国整个武装部队的决策;四是关于在何时以及如何与对手进行谈判的决策。Patrick M.Morgan,“Saving Face for the Sake of Deterrence,”in Robert Jervis et al.,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p.136. (23)Dean Acheson,“Crisis in Asia:An Examination of U.S.Policy,”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22,no.551(January 23,1950),p.116. (24)The Ambassador in France(Bru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26,1950,FRUS,1950,vol.7,pp.174~175. (25)Dean Acheson,Present at Creation,p.405. (26)Harry S.Truman,Memoirs of Harry S.Truman,vol.2,Years of Trial and Hope,New York:Da Capo Press,1956,p.333. (27)Intelligence Estimate Prepared by the Estimate Group,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5,1950,FRUS,1950,vol.7,pp.151~154. (28)The Ambassador in Netherlands(Chapi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June 26,1950,FRUS,1950,vol.7,pp.185~186. (29)Charles L.Bolte to Frank Pace,June 28,1950,091 Korea,Record Group 218,National Archives and Federal Records Center,转引自William W.Stueck,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188. (30)John D.Hickerson,“Preserv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through General Assembly Action,”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23,no.587,October 2,1950,p.544. (31)Thomas 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pp.124~125. (32)Memorandum from Henry Kissinger to President Ford Concerning“Lessons of Vietnam”,May 12,1975,p.1.http://www.fordlibrarymuseum.gov/library/exhibits/vietnam/750512.pdf.(2015年7月10日获取) (33)President Eisenhower' s News Conference,April 7,1954,Senator Mike Gravel,The Pentagon Papers,vol.1,Boston:Beacon Press,1971,p.597. (34)Rusk/McNamara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November 11,1961,Senator Mike Gravel,The Pentagon Papers,vol.2,Boston:Beacon Press,1971,pp.110~116.引文引自第111页。 (35)Lyndon Baines Johnson,The Vantage Point:Perspectives on the Presidency,1963~1969,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71,p.126. (36)Address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eace without Conquest,” April 7,1965,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877&st=belief+that+they+can+count+on+us&st1=.(2014年9月8日获取) (37)“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U.S.Policy in Vietnam,” An Interview with Secretary Rusk and Secretary McNamara on a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Television Program on August 9,1965,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53,no.1366(August 30,1965),pp.343~344. (38)Lyndon Baines Johnson,The Vantage Point:Perspectives on the Presidency,1963~1969,pp.147~148. (39)Notes of Meeting,Washington,July 21,1965,FRUS,1964~1968,vol.3,Vietnam,pp.194~195. (40)Jonathan Schell,The Time of Illusion,New York:Alfred A.Knopf,1976,p.362. (41)First Draft of Memorandum from McNaughton to Robert McNamara: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Re Vietnam,March 24,1965,Senator Mike Gravel,The Pentagon Papers,vol.3,p.695. (42)First Draft of Memorandum from McNaughton to Robert McNamara: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Re Vietnam,March 24,1965,Senator Mike Gravel,The Pentagon Papers,vol.3,pp.700~701. (43)Henry Kissinger,“The VietNam Negoti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47,no.2(January1969),pp.218~219. (44)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Brown,1979,pp.227~228,229. (45)“The Cambodia Strike:Defensive Action for Peace,” Address by President Nixon,April 30,1970,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62,no.1612(May 18,1970),p.620. (46)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Statement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Cambodia and the Republic of Vietnam,March 6,1975,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4767&st=reliability&st1=.(2014年9月11日获取) (47)Secretary Kissinger's News Conference of March 26,1975,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72,no.1868(April 14,1975),p.462. (48)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p.6. (4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2页。 (50)Remarks on Foreign Affairs at the Associated Press Luncheon in New York City,April20,1964,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168&st=&st1=.(2014年9月8日获取) (51)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London:Unwin Hyman,1988,p.515. (52)此为唐世平的总结。Tang Shiping,“Reputation,Cult of Reputation,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ecurity Studies,vol.14,no.1(January-March 2005),p.43. (53)“Implications of Angola for Future U.S.Foreign Policy,” Secretary Kissinger' s Statement made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frican Affairs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January 29,1976,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74,no.1912(February 16,1976),p.175. (54)Robert Jervis,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p.39. (55)Senator Mike Gravel,The Pentagon Papers,vol.4,p.47. (56)Kennedy Remarks at the High School Memorial Stadium,Great Falls,Montana,September 26,1963,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435&st=&st1=.(2014年9月8日获取) (57)Secretary Rusk' s News Conference,May 4,1961,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44,no.1143(May 22,1961),p.763. (58)Eisenhower Addres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Minneapolis,Minnesota,June 10,1953,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871&st=too+humble+to+be+forgotten&st1=.(2014年9月3日获取) (59)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Mandate for Change,1953~1956,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63,p.463.持不同意见者是陆军参谋长李奇微(Matthew B.Ridgway)。 (60)William M.LeoGrande,“A Splendid Little War:Drawing the Line in E1 Salvado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6,no.1(Summer 1981),p.27. (61)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Schuster,1994,p.220. (62)Secretary Kissinger's News Conference of March 26,1975,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72,no.1868(April 14,1975),p.461. (63)Jonathan Schell,“I Had My Notebook Right There in the Plane,”Christian G.Appy,Patriots:The Vietnam War Remembered from All Sides,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p.208. (64)John F.Kennedy's 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1961,Arthur M.Schlesinger,Jr.,ed.,My Fellow Citizens:The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2009,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2010,p.327. (65)Memorandum of a Meeting,White House,Washington,September 9,1964,FRUS,1964~1968,vol.1,Vietnam,1964,Document 343,p.753. (66)“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of U.S.Policy in Vietnam,” An Interview with Secretary Rusk and Secretary McNamara on a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Television Program on August 9,1965,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53,no.1366(August 30,1965),p.344. (67)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s Defenses,January 18,1965,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6974&st=&st1=.(2014年9月3日获取) (68)Earl Ravenal,“Counterforce and Alliance:The Ultimate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6,no.4(Spring 1982),p.27. (69)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p.51. (70)Jack Snyder,“Introduction,”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eds.,Dominoes and Bandwagons: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p.3. (71)参见Patrick M.Morgan,“Saving Face for the Sake of Deterrence,” in Robert Jervis et al.,eds.,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pp.142~143. (72)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Recommen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December 19,1945,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259&st=&st1=#axzz1UPG6mKfy.(2011年9月2日获取) (73)X,“The Source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vol.25,no.4(July 1947),p.582. (74)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75)Kennedy Remarks at the High School Memorial Stadium,Great Falls,Montana,September 26,1963,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435&st=&st1=.(2014年9月8日获取) (76)Senator Mike Gravel,The Pentagon Papers,vol.4,p.23. (77)“The Challenge of Peace,” Address Made by Henry Kissinger before the St.Louis World Affairs Council at St.Louis,Mo.,on May 12,1975,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72,no.1875(June 2,1975),p.706. (78)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Netherlands,May 16,1947,FRUS,1947,vol.6,p.924. (79)A Report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NSC 68),April 14,1950,FRUS,1950,vol.1,p.255. (80)James M.Kouzes and Barry Z.Posner,Credibility:How Leaders Gain and Lose It,Why People Demand It,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11,p.16. (81)John Kane,The Politics of Moral Capit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 (82)James M.Kouzes and Barry Z.Posner,Credibility:How Leaders Gain and Lose It,Why People Demand It,p.21. (83)NSC 68,FRUS,1950,vol.1,p.264. (84)Paul Nitze,“Policy and Strategy from Weakness,” in W.Scott Thompson,ed.,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1980s:From Weakness to Strength,San Francisco: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1980,p.449. (85)Television and Radio Interview,“After Two Years: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December 17,1962,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9060&st=&st1= 9.(2014年9月8日获取) (86)U.S.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United States Military Posture for FY1973,Hearings,92d Cong.,2d Sess.,February 15,1972,pp.505~506.转引自Terry Terriff,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S.Nuclear Strateg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24. (87)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90. (88)Memorandum by Mr.John Foster Dulles,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8,1950,FRUS,1950,vol.1,p.314. (89)谢林在1948年到1953年间先后为马歇尔计划、白宫和总统行政办公室工作,其60年代出版的著作《冲突的战略》、《武器与影响力》等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谢林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90)Thomas C.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pp.55~56. (91)Thomas C.Schelling,Arms and Influence,pp.93,124. (92)此为学者克里斯托弗·费特维斯的观察。Christopher J.Fettweis,The Pathologies of Power:Fear,Honor,Glory,and Hubris in U.S.Foreign Policy,p.102. (93)A Conversation with Jonathan Schell,http://www.robertboynton.com/articleDisplay.php?article_id=1538.(2015年3月25日获取)标签: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越南共产党论文; 越南总理论文; 越南民族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