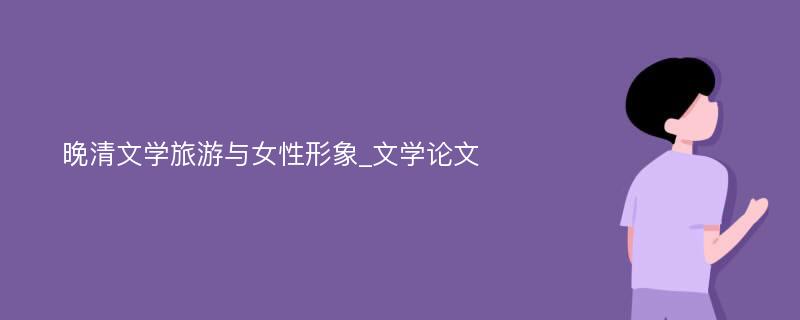
晚清末期的文学行旅与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旅论文,晚清论文,形象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时代,中国开启了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历时漫长、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也步步血泪。晚清文学乃至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就是在见证、跟随、召唤和推动这古老民族艰难嬗变的过程中,确立着自己的意义,变化着自己的面貌。
晚清中国的转型,并非起自本土王朝的盛衰更替,诚如严复所言,是来自外洋的“舟车之利”,“闯然而破”“数千年一统局”:
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①
于是传统天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观,随着天朝帝国地理秩序的变动渐渐崩落。其实早在变局之初,李鸿章便敏感于此,感叹遭遇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②
晚清中国的转型,从一开始,便与“舟车之利”、“印度”、“南洋”这些“行旅”概念紧紧相扣,何况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运动中,人们遭逢乱世,往往被时代裹携而颠沛奔走。黎民百姓的闯关东、走西口、奔逃离难、背井逃荒,帝王将相的“两宫回銮”、海军远征、出洋考察、留学归来、躲进租界等等异于往昔的行旅形态密集出现,强有力地标志着国运变迁、风云流转。相应的,晚清文学也在见证、推动这些崭新行旅形态的过程中,挥别传统,确立自己的风貌。因此,通过“文学行旅”这一视角,观察晚清中国文字书写姿态的嬗变与转型,可以在地理秩序、意识形态、国家想象、心理与书写模式的结合处,获得进一步的思想与文化纵深。
一
晚清末期,即庚子国变之后,“女学”赫然兴起。上至朝堂政纲,下至文人笔墨,都倾注热情,着力推动,女性形象也在晚清文学行旅的书写姿态和勾划脉络中迥别以往。
观察晚清末期中国文学的行旅书写,有一个倾向颇可玩味,那就是在彼时作者笔下,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和高深的判断,附加于旅途中萍水相逢的女性人物身上。例如,当时颇负盛名的小说《邻女语》(连梦青),以“庚子国变”时有志少年金不磨挺身北上解救黎民的行旅为线索。金不磨旅途中,偶至一尼姑庵,遇老尼空相。空相一登场,便是高人之相。书中写道:
空相已是眉长发白,貌于古松;昙花是素脸淡妆,颇似闲云野鹤……空相大师是一个经过洪杨大乱奔走江湖的老妓女剃度来的优婆尼,眼光如电,久能识人。
当空相与金不磨言及“庚子国变”的惨状时,空相所出之言,正是作者心中的所想:
空相又说:“……虽然老衲出家以来,心如槁木死灰,业已置此身于度外,却已看得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分不出什么人鬼的境界。施主做事,将来必须学到这个地步,方得大无畏的好处,大解脱的真相。施主不要忘了,这就当做今日老衲的见面礼罢。”不磨听得这番议论,不觉毛骨悚然,连声答道:“蒙老师父指点,这真真可以做我的前途引针。”③
晚清作者面对庚子国变这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已难从以往的“夷夏之辨”中找到济世良方或自圆之道,佛法的概括事实上成了彼时大多数作者的意义旨归。而此时,连梦青将自己对这场灾难的最重要的理解,托一“奔走江湖的老妓女剃度来的优婆尼”之口说出,叙写姿态颇耐人寻味。
刘鹗《老残游记》中子平于山中迷路而遭遇的屿姑,更是引起历代文学史家瞩目的人物。林语堂曾在《老残游记二集》的序言中专门言及屿姑:“具有这样出色的议论风采的女性大概是合乎铁翁最喜欢的才识,屿姑和逸云同是开悟隐遁、隐栖自适的才女。想起这样的人,有如于幽谷中闻兰花之香。”④ 阿英和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还专门著文考察屿姑的人物出处。屿姑的各种特点确实迥异常人,不仅容貌殊丽,“眉似春山,眼如秋水”,而且通达本土国学,亦洞悉外洋耶稣、伊斯兰之教义,谈儒论道之间,所抒正是作者怀抱:
“至于外国一切教门,更要为教兴兵接战,杀人如麻,试问,与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后世学儒的人……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于绝了。”子平听说,肃然起敬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真是闻所未闻!”
不惟此也,屿姑所烹之茶,也神乎其技,标识着隐逸之美:
茶叶也无甚出奇,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
屿姑与黄龙子合奏之“海雨天风曲”也如天外之音:
久之又久,心身惧忘,如醉如梦。于恍惚杳冥之中,铮纵数声,琴瑟俱息……屿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风》之曲,是从来没有谱的。不但此曲为尘世所无,即此弹法亦山中古调,非外人所知。”⑤
这样的人物,如梦如幻,已若天外仙女,使得即便文中言及后世“北拳南革”的惨状,作者仍似有理由寄托理想,免于绝望。细品之下,子平遇到屿姑的山谷,宛若桃花源之境,但传统中国文学中“桃花源”之引路者,或为“渔人”,或为白须长者,像屿姑这样艳丽多姿、通晓外国教义并侃侃而谈的女性形象,实为传统文学所鲜见。
苏曼殊的《断鸿零燕记》也有同工之妙。三郎在赴东洋寻母的旅程中得遇东洋美女静子。静子学养丰瞻,“慧骨天生”,佛学旨趣与作者苏曼殊和作品中的三郎正出一辙。静子言梵文典:“其句度雅丽,迥非独逸、法兰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语。”而且,她佛学深厚至“固究心三斯克列多文久矣”,不禁令三郎感叹:“善哉,静姊果超凡入圣矣!”⑥
陆士谔著《新中国》中,“我”恍然一觉由“宣统二年”而至“宣统四十三年”,在好友李友琴女士的引领下,访游富强民主、令外邦臣服的新中国。这个理想世界,完全是在“女士”的带领下展现,由一个又一个“女士道”开启的女士语言加以介绍。李友琴女士侃侃为“我”讲述“汽油车”、“电汽车”等新奇物件,言谈话语间,对现代科技信手拈来,直让须眉男儿的“我”咂舌不已。
这些被晚清作者寄托莫大理想的女性形象身份各异,被赋予的理想也各不相同,但她们都是在行旅书写中与作者的笔触相遇,一朝萍水相逢即被惊为天人。奔波在乱世旅途上的小说主人公,他们的迷茫和理想经由这些女子形象画龙点睛。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女性及其身负的晚清作者的理想,蕴含着巨大的颠覆性意义。她们的身份或为隐逸(如老尼空相和屿姑),或为外洋(如静子),或为未来之人(如“李友琴”)。隐逸,对抗着庙堂;外洋,质疑着本土;未来,敌视着当下。而这些女人身上负载着晚清作者的理想,或为佛法,或为西学,或为被称为“于今已绝”的中国古典传统。这些理想无一不与彼时的庙堂秩序强烈冲突,同明君忠臣的旧理想南辕北辙。当晚清作者的这些理想被女性形象堂而皇之地代言时,一个时代的王纲解纽便也呼之欲出。
二
前述若干女性人物,都是小说主人公在行旅中遇到的,往往灵光一闪而现理想之辉;也常因其灵光一闪,而成为行旅书写中引人注目的配角。但晚清小说的行旅书写中,还有一种女性形象属于另外的情况,那就是女性本身即为行旅叙事的主人公。她们不再是配角,不再需要行旅中的男性去发现,而是如须眉男儿一样奔波于旅途之上,与纷繁的乱世景象迎头相撞。
晚清作者在叙及这些女主角形象时,作者的笔触常会格外具有夸张的、理想化的色彩。如吴门天笑生所著《碧血幕》中的秋瑜,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融入晚清作者浓郁情感的理想化人物。书中叙道:
(秋瑜)是浙江山阴县人氏,本来是个世代簪缨,不过一个宦门千金罢了。却自幼随着他祖父某公,出守闽中,又长居在台湾地方。这秋姑娘儿时游钓之乡,便是二百余年前,有个郑成功,张拳弩目,要保住这亡明一寸山河的地方。如今故老传闻,灵魂接触,不知不觉,在这小姑娘脑髓中,留下一个影子。后来他父亲弃幕改官,宦游湖南,那个三湘七泽之间,本来是个种性不灭的地方,这也是地理上的关系,衡岳嵚奇,类多气节磊落之士,所以以前有王船山一班逸民遗老,结茅空山,著书穷谷,专播这种子,后来又有浏阳二杰,持着流血主义,要想普救苦恼众生。中间还有许多枭雄怪杰侠客大盗,时时出没,根尘所接,却能使人变化气质。那位秋姑娘不觉脑中这个影子,渐渐放大了……加以近年来,欧美学说横渡太平洋,却从日本间接儿传至中国,什么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一进了人的脑子里,再也不能出去。
作者又写秋瑜后来又随这做官的父亲到了京师。她目睹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百姓野蛮,不免咨嗟太息,错愕不平。秋瑜便“在这冷灰星星中爆出第二个绝大希望来,却是舍身救国,要做一个震天撼地的人”。正如秋姑娘诗中所说的:“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⑦ 为此,第一层便须“冲决家庭罗网,从此锦装玉裹的天囚,变成了个破槛冲藩的野鹤”。于是秋瑜赴日本游学。
追寻秋瑜这个女性主人公的羁旅之痕,真可谓行程万里。小说字里行间实可见作者的用心良苦:秋瑜足迹所至,几乎囊括晚清民族、民主革命的各方面资源:台湾郑成功的血性呼唤着“驱逐鞑虏”;人文鼎盛的浙江和湖南遗老的著书,正是“恢复中华”的绝佳根底的结合;“血性主义”和“枭雄怪杰、侠客大盗”的豪情赋予秋瑜勃勃英姿,正可作为革命军中之女豪杰;通读卢梭、孟德斯鸠,意味着获取了现代文明思想;游历京师而见腐败、黑暗,见证着革命之必须;游历东洋,可做真通西学的标志;“舍身爱国”之志,更是令人感动的革命激情。作者以粗糙的笔法,在短短篇幅之内便赋予秋瑜这个人物所有革命事业所需要的光辉符号,活脱脱一个夸大了的“鉴湖女侠”秋瑾,也是晚清作者在行旅书写中理想化女性的典型。
作者抒发理想、确立标杆之志,往往急不可耐。又如苏曼殊《碎簪记》中写到莲佩,称其“恭让温良,好女子也”;同时又“于英法文学,俱能道其精义,盖从苏格兰处士查理司习声韵之学五年有半,匪但仪容佳也,此人实为我良师”。陈啸庐著《新镜花缘》中年轻女子们的新学见识简直惊人:“诸位小姐,不但于天学地学算学绘学,以及声光化电静重格致理化各科学,研究得剖晰微芒,连那政治法律,下至路矿农桑植畜牧,同一切生计制造等实学,亦无不切实讲求。”至此,虽为小说而几近神话。一望而知的虚构背后,是晚清作者难以压抑的表达理想的急切诉求。
晚清作者倾注如此急切的理想,究竟所为何来?一位“小姐”口陈之心意可谓言之无遗:
倘能有一个出色人材,替我们黑暗女界发一异彩,岂但压倒中国男权,亦使外洋各国知道中国并非真真睡狮。即使是睡狮,只要一觉睡醒,那一声“河东吼”已尽够叫他肝胆坠地的了。⑧
晚清小说的作者们笔下,“新学”、“科学”的符号,成为行旅书写中女性形象的重要亮点之一,而作者急切赋予、描摹、夸大这一符号的背后,心中念兹在兹的,其实质是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宏大旨归。
回想晚清之初的19世纪60年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兵工厂的一代名臣曾国藩,日记中还流露出如此心迹:“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⑨ 而四十年之后的文学景象中,“内人”们却已出门在外而新学渊博,晚清前后期的分际亦从中可见。
与《红楼梦》、《西厢记》一类中国传统文学脉络不同,晚清后期的文学中多数女主角都不再囿于深宅大院之内,而是行走于千里旅途之上,或赴上海、奔京师,甚至远涉重洋。如果我们考究历史,会发现这种文学图景其实是文学对历史的变形与改写。彼时中国有机会出洋游学的女性,当然只是凤毛麟角。只是晚清作者们此时对囿于一府之内的文学图景已失去兴趣。
与《金粉世家》、《家》、《雷雨》等新文学之作相比,晚清作者们更急不可待地希望以浓墨重彩书写或虚构勇敢离开家门以求新知的女性形象。他们叙及男性出洋留学时,常对其身上的种种劣根陋习痛心疾首。例如在前述小说《碧血幕》中,作者对与秋瑜同赴日本留学的男性揶揄甚多,极写其醉生梦死和不学无术:“这内地出来的官费留学生,真是瞧见了,令人可笑,又可怜,又可羞,又可悲。”但叙及女性出洋留学时,却几乎从未有此质疑,反而青眼有加,竭力以理想化的笔触夸张其事。被传统文化束缚千年的女子形象初出深宅,文学作者便掌声四起,推崇膜拜。从中可以窥见传统中国家族纲常伦理渐渐剥落的痕迹。却原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广泛反响的“娜拉出走”的命题,在晚清后期的文学行旅中,早已有想象的模型、情感的先声。
同时,通过这些女性形象亦可厘清晚清作者们的一些理想之脉络。与林黛玉、崔莺莺们不同,这些行旅上的女性形象被作者赋予的才能不再是琴棋书画、诗文典籍,而是常常被竭力夸大为“新学”、“旧学”兼通。值得玩味的是,晚清作者叙写这些女性形象时,很少有耐心再如大观园里的行酒令、结诗社一般,详细铺展其旧学领域的诗书才情,而只愿以极少笔墨,在叙述过程中将“旧学深厚”的符号如帽子一般扣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但对她们的新学知识,却着力渲染,兴味盎然。于是,通过这些被理想化的行旅书写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发现所谓“旧学”的概念在彼时作者的想象世界中已渐渐被“空洞化”、“符号化”了,但还难以割舍;而“新学”固然五彩缤纷,却又一时难以说清。面对新学、旧学,晚清作者步履坚定,但目光游移。
新学、旧学之辨,应是当时作者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需要加以折冲权衡的想象性符号之一:旧学,言其不曾忘本;新学,言其推行变革之正当。只有不忘本,才能不以夷变夏;只有深通西学,才能救亡图存;也只有两者兼备,才能振兴中国。晚清时代的新旧交替过程,往往呈现为新者方生而未成型,逝者将死而尚存的复杂局面,无论在文学想象还是历史实际方面皆是如此。
三
晚清末期的行旅书写中的女主角,还有另一种情形。她们没有被过分突出新旧学问的闪亮光彩,但或忠贞得有些匪夷所思,或“淫荡”得令人瞠目结舌。这几乎是冰火两重天的女主角们,以矛盾的身姿共同冲撞着传统伦理中最敏感的环节——节烈观。
传统社会将女性束缚于宅门之内,归根到底是为了保证女性之“贞洁”。历经宋明理学的洗礼,礼法至清朝更为苛严。而晚清的文学景象中,女性人物纷纷踏上乱世奔波的旅途,在这个展开特定想象的场域内,如何折冲权衡传统的节烈纲常与开新大潮,事实上成为晚清作者必然面对、不可回避的命题。当此之际,晚清作者们笔下也呈现出新旧交替之际的复杂景象。
一方面,部分晚清作者着意在行旅书写中凸显女性的贞洁美德。其中最为醒目的例子出自著名作家吴趼人的《恨海》。该作叙及庚子灾乱中,在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之际,几个向南方逃难的青年男女聚散离合的悲欢故事。其中女主角棣华与未婚夫走散,千里护母南归。其未婚夫伯和在逃难途中染上毒瘾,终于自废。但棣华始终不离不弃,照顾体贴,甚至在伯和峻拒之时,还在“暗想”:
天下没有不能感格的人,他今日何以如此,见了我只管淡然漠然?莫不是我心还有不诚之处,以致如此?或是列不善词令,说他不动?嗳!怎能剖了此心给他一看呢(吴趼人注:棣华不岂是情人,竟是圣人!)默默寻思,不禁又扑簌簌的滚下泪来。⑩
最后伯和病逝,棣华遁入空门。《恨海》朴实而蕴含感伤的笔调,亦成为晚清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中棣华为未婚夫病亡而遁入空门的形象也格外醒目。
李定夷的《茜窗泪影》以女子千里寻夫为题材,亦是当时言情小说中的名作。书叙两对未婚夫妻,均因夫婿参加革命军而婚期延搁。二女皆为新学堂的学生,千里寻夫颇历其险,虽被拐入妓家而竟能逃出,从而保全贞操。后来,其中一女夫婿回返;另一女(琇侠)的夫婿则战死沙场;琇侠为未婚夫守节终生。这是一篇文笔感人而情节古怪的作品。琇侠本未成婚,为未婚夫婿守节,即便严苛如清代礼法,亦未做如此要求,未免太过突兀。但这又并非一个乖张版本的寻夫、守节的传统中国文学故事。作者以一番爱国激情,使得各种情理得以勉强自圆其说,亦似有感人之处。例如:
琇侠曰:“际此千载一时之盛举,尚不求显主亲扬名,更待何时?姊不闻,义所当死,死贤于生,龄哥等设有不幸,亦国家之荣光,异日青史留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烈士战没于某地,令千古下闻风仰慕,其光荣何如!若以余辈而论,万一不能生如厥愿,即可死以殉情,生生死死,自达观处之。”
琇侠夫婿参加的是推翻旨在反清的“革命军”,若着眼于传统伦理而论,此君堪为“乱臣贼子”,但作品盛赞其“爱国”。这显然已是基于新道德的判断,体现着新的国家认知。作者也只能以此为支点,方可使女主角琇侠的古怪守节一变而为可歌可泣之举,作者的笔锋转折堪称陡峭。
晚清末期作者笔下的女性纷纷踏上乱世行旅而放异彩,背后是女权思想兴起的推动。但从当时作者特定的叙写姿态分析也可看出,面临女界自由的新世态,晚清作者徘徊、挣扎于新旧观念之间。情节的突兀之处,并非作者无知无能,而正是作者极力思索却力有未逮、不能圆转之际。事实上,处于社会急速转型的开端,在节烈等涉及纲常的问题上,哪怕只是最初步的厘清,也并非此时作者所能完成。即便时至新文化运动,也不过稍具眉目。
同时,“爱国”与“言情”在晚清言情小说的书写中往往紧密相扣,很多富有光彩的女性形象在言情小说中格外引人注目。于是,晚清言情小说叙事模式一个重要的有别以往之处或可概括为:浪迹天涯的男主人公先后遇到两位美貌女子,一位坚守旧道德而忠贞不渝,一位身负新学而可为知音。男主人公在新旧两个女子之间痛苦抉择,最后以悲剧收场。此一模式中出现的人物虽为二女一男,但通篇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人牵涉淫邪,男女之间必为纯洁爱情。这是现代中国文学言情小说中出现最早的“三角恋爱”模式。“三角”而固守贞洁,“恋爱”却牵涉新旧,传统与开新之间的折冲痕迹亦可从中窥见。苏曼殊几乎所有的言情小说皆循此路,徐枕亚的《玉梨魂》、《雪鸿泪史》更以此模式而成名作。其中徐枕亚打破了传统言情悲剧之化蝶、还魂的轮回模式,令二女伤心而逝,男主角则奔赴远方最终成为“革命军中无名烈士”,以凄美的行旅书写中的爱情故事,标识着新的民族国家伦理渐渐成型(11)。
但在此新旧道德交冲的狭窄空间内,晚清小说的“三角恋爱”模式也只能囿于一男面对二女的痛苦抉择。至于一女面对二男的选择,以及选择中呈现的饱满微妙的女性心理和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展示等方面,就只能等到经历了“五四”洗礼之后,“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一类的作品来表现了。
与上述始终无法挥别传统节烈观的作品相比,另一路晚清小说的行旅书写异峰突起。这些作品里独擅胜场的女性有着特殊的身份——妓女。“庚子国变”举国重创,于是坊间盛传曾嫁给状元的名妓赛金花,以香艳手段与联军统帅瓦德西旧情复燃,周旋其间救民于水火。以曾朴名著《孽海花》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对这个故事描摹多多。在晚清作者们笔下,赛金花(或傅彩云)出身风尘,中华文理难说深厚,但却精通德语,当以如夫人身份陪伴状元夫君出使欧洲,游遍列国。她还曾跻身于各国贵妇之间,得宠于德国皇后之侧,与俄国虚无党女杀手从容周旋,与德国青年军官瓦德西风流一度。这些缤纷的跨越国界的经历,恰是赛金花神奇力量的源泉。晚清作者的行旅书写触及赛金花等妓女形象时,虽未必有意地寄托自己的理想,但浓墨重彩之间的热情洋溢,夸张神话间的兴味盎然,则是不争的事实。
心青所著《新茶花》叙及名妓“状元夫人”曹孟兰,便显然来自赛金花的故事。相形之下,中国的高官立显可鄙可悲:
他曾经跟着使节,到过德国,能说德国的言语,恰好此时在京,张着艳帜,便放出他的手段,运用他的神通……等到酒席摆上,那洋人也不睬主人,只管大吃大喝,谈笑自如。梦兰却侃侃的讲些难民的苦楚,市面的败坏,谈一阵,笑一阵,到后来洋人也答应相机办理,通席没同主人讲一句话,竟是走了。主人仍旧恭恭敬敬送出大门,看上了车,方才回来……梦兰笑道:“你们这一班外交官,竟是这等没出息,见了洋人,吓得什么似的……”那主人听了大为无趣,又不敢触犯他,怕他告诉洋人,只得讪讪的走了。(12)
赛金花们虽能于危难中救民于水火,但却从始至终绝对与贞节无缘。她甚至可以在被状元夫君捉奸之时,将自己的越轨品性说得掷地有声:
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这会儿做点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要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伺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若说要我改邪归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说,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嘎!(13)
在晚清作者笔下,赛金花的形象中固然有“淫荡”成分,但救民之举中又似带有三分侠义。与此同时,她还光彩照人、精力充沛、魅力无穷。同样是身处亡国乱世时代的名妓,赛金花的形象与《桃花扇》中的李香君迥然有异。李香君虽为名妓,但却保留着对侯方域的忠贞,并以忠于大明的“大义”而令人敬服;赛金花活得有声有色却分明“无君无父”。她的浮荡毫不遮掩、肆无忌惮,香艳风流得趾高气扬。作者恰是让这样的女子以其魅力、精力和海外游历的见识与资本,于“庚子国变”中拯救黎民,令国中状元、大臣们立显卑琐。如果说李香君的形象讥刺羞辱的是“奸臣”和“贰臣”,那么赛金花形象挑战的可说是整个儒家纲常。
庚子国变之后,儒家礼教急剧式微。1902年后,“新小说”一时演为风潮,一批妓女形象乘势在晚清文学行旅书写中跃然而起。不仅一个赛金花,另如《新茶花》中的“武林林”、《恨史》中的秋瑛等,一时都颇引读者注意。《碧血幕》中,与秋瑜并列的人物就有名妓谢文猗。作者极言:“最奇怪的,是中国社会上有两种人进化得最怪,一是优伶一是妓女。将来有人操着龙门巨笔,编那中国进化史时,倒不可不在那南都金粉北地胭脂里去搜集材料呢。”(14) 晚清作者笔下,这些妓女人物虽堕入风尘,但也在乱世行旅中风尘仆仆,她们的视野和身姿皆不同以往,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礼教。这些引人注目的妓女形象与忠贞,守节的棣华、琇侠们同时出现在晚清文学行旅的图景中,昭示着晚清作者的节烈观与家国观在传统意识形态体系崩溃之后,社会进入急速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与杂芜。
综上,晚清文学中部分作者的行旅书写,因应历史时代的变革诉求,对女性形象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以极高的热情为置身行旅的女性添加光彩甚至演绎神话,开启了新的书写女性形象的范式,生动地诠释着转折时代的风貌与意义。当此之时,传统文学女性书写的脉络迅速式微,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中的种种重要命题与矛盾无形中于此奠基。但同时,仔细推究亦可发现,这些理想和神话大都处于“符号化”、“概念化”的状态,同时囿于男性作者的视角之内;在文学构建上,并未与现实的女性生活、女性情感,特别是女性主体意识切实相通、紧密关联,从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晚清作者的家园理想充满矛盾而急不可待,个中心结和理路正与20世纪中国的激进思潮相辉映。另一方面,晚清作者于行旅之间书写赋予女性的理想和神话,说到底其实大都旨在回应强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女性形象始终是作为家国问题的一部分而被思考与塑造的。如果说晚清末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起点,那么,本文从这一文学行旅与女性形象角度所做的考察,亦从一个侧面映现出:现代中国文学近百年间性别议题与家国大业之间的紧密纠缠,并不全因后世政治思想的推动,而是它发轫之初就带有的“基因”。
收稿日期:2010-05-17
注释:
① 严复:《拟上皇帝书》,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② 梁启超:《李鸿章传》,《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30页。
③ 连梦青:《邻女语》,《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5-16页。
④ 林语堂:《〈老残游记二集〉序》,刘鹗:《老残游记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页。
⑤ 刘鹗:《老残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8、56页。
⑥ 苏曼殊:《苏曼殊小说诗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3页。
⑦ 吴门天笑生:《碧血幕》,《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洪水祸·碧血幕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⑧ 陈啸庐:《新镜花缘》,《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中国进化小史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23、267页。
⑨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845页。
⑩ 吴趼人:《恨海》,《吴趼人小说四种》(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一语中的:“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11页)
(12) 心青:《新茶花》,梁心清、李伯元等:《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第1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13) 曾朴:《孽海花》第二十一回,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14) 吴门天笑生:《碧血幕》,《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洪水祸·碧血幕等》,第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