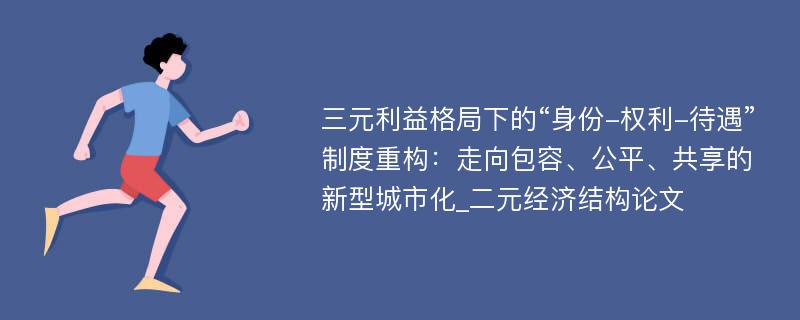
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待遇论文,公平论文,权利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最近数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城乡社会出现了未曾预料的深刻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出现新的形态,在城市与农村这两大结构性社会板块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既可以说非城非乡,也可以说亦城亦乡的模糊地带。这一演变不仅大大超出了费孝通先生当年的分析,也超出了许多后来研究者的重新思考。费老最初用以刻画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二元状态的范式框架,在实际应用中的调整或修正也就势所难免。不过这还不是实际问题的全部。在城市化的动态进程中,在二元分立的城乡社会之间,那种简单对应、彼此隔离的关系格局已被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随着城市化出现了复杂的延伸和转化,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区域差别在相对更为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发生了汇合聚变,使得城乡差别转化为了同城差别。于是,由于体制、制度和社会等原因,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们不得不分属于彼此隔离、相互排斥的“身份—权利—待遇”世界之中,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最富特点也是最为棘手的现实。这种现实题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新试验场。
一、回望中国:从传统城市社会到现代城市社会
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释的过程中,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往往发挥着引导作用。有关城市化的研究和解释也是如此,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眼界也会融入其中。以往城市化研究建立了这样一幅图景:城市化是城乡力量彼此消长的过程,乡村衰败、城市兴起、城乡对立、城市主导的变迁轨迹贯穿其中;人类生活也相应呈现出三个阶段性进程,即从传统乡村社会时代向城乡二元社会时代的转变,再从城乡二元社会时代发展到现代城市社会时代。事实上,这可以说是城市化研究中的一种较为常见的和固化的解释模式。
这一模式下勾勒出的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必然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扩张和全盛的过程。不难看出,这一图景与标准的西方现代性理论是高度符合的,以西方城市社会的发展路径作为参照系,引申出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刻画和预期。然而,这幅图景对中国城乡社会的历史解释和现实认识存在着诸多误区和重大缺失,对未来趋向的把握也充满困境。也因如此,新的历史视野和理论框架获得了巨大的生长空间,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中国城乡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对这一过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演变形成更为合理的认识和刻画。
(一)传统中国社会的城乡双面特征
事实上,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不过是现代进程的产物,其历史极为有限。远在这一视野确立之前,中国城乡关系的独有特征早已存在。这是城与乡的社会一体性关系: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亦此亦彼的,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隔离。可以说,乡村与城市始终是中国社会彼此交融的两个侧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农耕生产为基础,浇塑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共同根基,也融筑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多重面相:辉煌的农业经济、璀璨的城市文明、城乡一体的社会体制,等等。
辉煌的农业经济。按照黄仁宇的观点,“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①基于“土壤、风向和雨量”的独特条件,促成了“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的结合,形成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受困于“人多地少”的现实,费尽心力的劳作、殚精竭虑的经营、密集精致的技巧,使农户经济变为了分工协作的劳动共同体,而中国农业经济也成为了一种市场经济。按照弗兰克(Gunder Frank)的研究,中国经济早已商业化、经营结构复杂化,而且像其他民族一样从事远洋贸易,并长期保持出口顺差,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领先地位。他还援引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纳贡体系是一种商业交易,既包含着包容性关系也包含着竞争性关系,并日益扩大,形成一个覆盖广阔地区的网络。②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1776)中,有相当篇幅评及当时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认为“中国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并称道中国人的勤劳,劳动报酬比欧洲更为低廉。③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种中国模式:“中国的小农就被如此的历史条件造就为世上最为精明强干的劳动者”,小农与土地的直接结合也就创造了“勤劳革命”;“作始也简,其成也巨”,虽起初“筚路蓝缕”,终究是“波澜壮阔”。④这就是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土地,走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
璀璨的城市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西方城市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学者称:“考古资料证明,世界最早的城市是位于死海北岸的古里乔,距今已9000年左右。”⑤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也十分悠久。我国考古界曾经一度公认中国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然而,2006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安徽省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距今约5500年,使中国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1000多年。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表明,杭州有5000年的建城史。2008年,陕西省杨官寨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杨官寨遗址是约6000年前的巨大史前聚落,现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此外,史前古中原地区先民创造了独特的城市模式——中原城市群。据考,从黄帝时代开始,郑州一带就出现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的城市群,黄帝陪都墟、禹居阳城、夏启迁都、太康建都、商汤建都、商代城市遗址、郑韩故城、阳城遗址……在古中华最温柔的腹地,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如星辰一般相互簇拥,它们提携着彼此,共同穿越时空的旷野和长河,在身后留下了一片曾经的生机勃勃和繁华熙攘的城市聚落遗址。这也许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恢弘篇章。
城乡体制的社会一体性。中国统一规划的城市体制始于秦。据相关研究,秦统一六国后,普行郡县制,确立了以首都为中心、以郡县城市为网点的大一统的首都郡县制城市体系。城市成为各级政权所在地,城市的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城镇并不是单独的行政单位,城市体制是城乡合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⑥钱穆亦认为,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⑦有学者指出:“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欧美学者普遍认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城乡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它们仅是一个渐进的统一体。”⑧从研究可见中国城市体制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城乡文化一致性,二是城乡行政一体性。这也赋予了中国城市治理与欧洲不同的意义:城市与乡村的位置是平行的,城市在文化上并不比乡村更优越,在行政上也并不比乡村的地位更高。由此可见,城乡分野和城乡对立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现象,经由学人的提炼继而形成了一种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
“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同构体系。在城乡合治体制的治理框架中,“身份—权利—待遇”体系因而是城乡同构的。就制度设置的功能而言,无明显差别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意味着城乡人口流动能够保持均衡状态。传统上的中国城市并不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生产与配置中心,不是产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主要基地,城市尚未具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力促使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因而也就无须设置“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体系,从制度规则上对乡村人口流动进行限制。钱穆称“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⑨。李泽厚以传神之笔描绘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兼济”与“独善”这两种相互补充的品格,进取则满怀壮志、做皇皇政论、辅治国平天下,退隐则收敛心怀意绪、独行于山水之间、终老于泉林之下。历代文人墨客写画不尽的山水自然,其萧疏气象、清旷烟林、峰峦浑厚、木茂石坚……⑩更是隐喻了在文化价值和理想诉求方面,乡村具有优于城市的淳远意境。这些都印证了中国传统时代“身份—权利—待遇”城乡同构体系的存在。
传统上中国城乡合治的社会体制表现了城乡自然“一体化”,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西方城市现象显然是很另类的。西方城市学研究者大多遵循了一个“原则性假设”,这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大分野:无论是结构还是形式,包括传统中国在内的前工业时期的城市与现代工业化城市明显不同。这不仅是“芝加哥学派”等学者的观点,也是当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观点。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前现代文明中,城市与乡村的对比通常表现得泾渭分明。前资本主义的城市与现代工业化城市是“明显不同”的。(11)无论这类看法的合理性如何,毕竟还是认可了前现代城市的存在。与此相比,韦伯(Max Weber)的观点更为极端。在他看来,城市是与乡村分立的另一种共同体,城市也是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独有的现象,西方城市的一些特征(社区、社团、市民等)是东方地区缺乏的。(12)韦伯对中国城市现象所持的否定态度,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批评。如熊月之认为,对韦伯而言,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失败的。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断言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13)韦伯显然忽视了在欧洲现代城市形成之前,中国的城市早已存在,这是以欧洲为中心、以现代性为起点的西方城市理论无法覆盖的历史事实。当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现象的解释时,其狭隘眼界必然显露无遗,其研究结论也难免遭到质疑。
(二)走向城乡二元分立的现代中国
欧洲开辟的现代性进入全球扩散的过程,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插入了中西关系的重大历史因素。中国城市社会变迁很大程度上也受其影响甚至为其左右,近现代意义的中国城市历史由此开始发生。中外学者的研究多以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作为近现代中国城市的起点。“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汉口、天津等通商口岸的辟设,治外法权的实行,租界的建立,西方的城市规划、司法制度、市政管理、经济管理等制度的引入,中国传统城市演化进程被打断,与西方工业化以后城市相似的、与中国传统城市迥异的近代中国城市才开始出现”。(14)此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及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已经形成。中西关系的这种时空方位,不仅标定了近现代中国城市的起点,也标定了中国城市边缘的和依附的地位,中国既是西方国家的原料、劳动力和初级产品来源地,也是其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无论从外向还是内向的维度上,都可探查到中国城市具有的特殊机制和功能,即生产要素、经济收益和社会财富的输出机制,以及对国际经济体系发挥的支撑功能。
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同步的中国城市还伴随着另一个进程,这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严重不均衡性。譬如,城市之间差距扩大,中东部少数沿海沿江的开埠通商城市发展较快,与内陆城市形成了发展差距;地区差距扩大,东部、中部、西部的不平衡发展格局的持续凸显;城乡差距扩大,随着外国资本输入和本土资本兴起,城市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心,对中国农村的支配和剥夺逐渐导致了农户经济的衰竭。总之,在中国城市步入近现代的进程中,传统上城乡合治的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大分流,城乡文化一致性和行政一体性不复存在,开始了所谓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也一步步走进了城乡差别的制度区隔。
城乡的兴与衰:“乡土中国”的二元意涵。上世纪中叶,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加入到现代化进程中,它们的社会与西方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结构性特征,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阿瑟·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一著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这一理论模型通过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现象,也指出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本途径。对刘易斯模型的回顾具有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重意义。我们知道,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社会学理论大致是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形成的,在这种更具体的时空方位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本土经典理论及范式的深层意涵,捕捉到现当代中国城乡社会最有可能的未来走向。
中国城市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进程。城市社会的兴起与乡村社会的衰败,对以农为本、农业立国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也是“工业革命”模式超越“勤劳革命”模式,资本密集型的集约经济战胜劳动密集型的农户经济的过程。梁漱溟目睹“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他认为中国乡村的破坏不始于今日,而是由来已久。自近百年来西洋人东进,激起中国社会剧烈而严重的变化,形成了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的趋势。在他看来,这一大势中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价值取向的大“掉转”,在以个人本位、自己为重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以伦理本位、义务为重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关系受到破坏,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日趋崩溃、向下沉沦。梁漱溟指出了中国社会的这种“东不成,西不就”,“不东不西”的现实状态(15),并从一些重要的侧面揭示了中国城市社会兴起过程的城乡二元关系以及两者间的尖锐对立。
城乡二元分立过程的种种巨变汇成的大时代背景,渗透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底色之中,聚敛为本土范式的深层意涵。对于更为透彻地理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8)和“乡土社会”等范式,这一时代特征和理论前提应当没有太多疑问。费老刻画了以村落为单位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活动中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以生育和婚姻事实为基础的基本社群,以及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和礼治的秩序规则,还有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和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他亲切地称之为“熟人社会”。(16)从中能够读出费老对初民社会的无限怀想,其中有至深的眷恋,更有些许的遗憾和无奈,但我们更愿意视为他在以学术的方式向其告别。“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17)费老说的这个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在乡土社会基层上发生的特殊社会,即非乡土性的城市社会。
可见,费孝通是对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最早做出论述的学者之一。正是在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二元结构的理论前提下,费老建立了一套范式和框架,如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乡下人与城里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等,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化特点及其相互区隔给予了生动的描述与深入的刻画。因此,通过这种二元意涵才能真正理解“乡土社会”的实质。正如滕尼斯的社区共同体(Community)之于社会共同体(Society),费老的“乡土社会”在与城市社会的比照下,方显示出其深刻意义,从而成为一种传世思想。如果我们不再是从中力证费老在传递一种纯粹传统的、前现代的田园意境,而是着力感受他所揭示的中国社会城乡二元分立的进程以及进入现代过程的中国乡村的现实镜像,我们的研究可能会受益更多。
国家与市场:城乡二元化两大推力的再认识。二元分立的现代城乡关系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城乡平行格局,在行政体制上确立以城市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经济体制上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化体系,城市因而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功能地位——城市是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生产与配置的核心基地。处在当今的全球大视野下,国家与市场对于城乡分立发挥的推动力量,其复杂过程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国家力量推动了中国城乡分治体系的确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形成了独特的单位制结构。由于城市所处的行政核心地位,城市单位制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发挥着支配性作用。正是通过城市“单位”的组织运作,国家实现了对全国社会资源的控制、规划和管理。在此意义上说,城市单位制可以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标志性体制。因此,上世纪70年代末,变革城市单位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有着极为重要的含义。单位制度的转型和解体导致了城市社会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去单位化”趋势促使以往的“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最终成为“社区人”沉落在基层社会。于是,后单位制时期的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对社会进行重新组织和管理的功能,以及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功能。中国城市治理能够走上了一个新水平,有赖于城市社区建设取得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城市社区建设的显著成效也使城乡社会的二元差距更为凸显。
在中国农村,国家对基层组织的改造是更具实质性的。孙中山曾对辛亥革命有深刻的反思,认为只注重政治革命而忽视政治的社会基础,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教训。(18)因而可以理解黄仁宇为什么肯定中国土地革命的意义:改造“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读《翻身》,一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19)不过,与城市基层组织相比,重建后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尝试着接近现代管理。研究者指出,人民公社制度由国家设置,是一个政社合一、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基层建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统一核算,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到生产和分配领域。(20)亦有研究者认为,基层组织改造“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从而建立了“合格的国家财政”和“货币之主权”。(21)农村组织化对社会资源的初级计算和控制,再经由城市单位组织的技术程序,最终成就了黄仁宇期待的一个可以用数字管理的国家。
其次,市场经济对中国城乡社会分离的贡献。“市场经济”并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即使在中国城乡合治的传统时期,农业的地区专业化和生产商品化、农业对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的适应、粮食价格调节的市场运作、自由参与市场的手工业、远程粮食贸易和市场网络配置等等,都说明中国农户经济与“市场经济”原则并不背离,甚至比欧洲“做得更好”。(22)然而,以工业化生产为基础,不再遵循互补互惠的经济逻辑,而是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不仅需要资本的密集化投入,也有赖于发达的信贷体系和债务体系,从而造就了资本主导(而不是劳动主导)的市场经济等,这些方面是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市场经济的重要分野所在。通过这条现代市场化经济之路,中国城乡在生产和贸易分工体系中的不对等地位日益分明,随着劳动密集型的农户经济的不断式微,农村从中心向边缘步步退却,直至成为整个生产—消费体系的配角,城市则成为了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市场高地。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反向运动,注定了城乡利益诉求的日益分离某些情形下甚至对立的趋势。
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型向市场型的转轨,原有的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相关数据表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2010年则是3.23倍。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各项惠农政策,如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税收方面的减免、扶持农民的就业、对农民工的关照等,农民收入有较明显的增长,2010年中国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但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仍是主导趋势。与此同时,区域间的城乡差距也在扩大,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城乡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省区(的城乡差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更大,达4∶1以上。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23)历史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目前的30多年间,除了个别年份,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
“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体系。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二元化过程逐渐催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即以往“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同构体系不断消解,由“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差别体系取而代之。当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表达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城乡在户籍制、所有制、职业等区分也划定了城乡居民“身份—权利—待遇”的制度壁垒。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同时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强调,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因此,从现有《土地管理法》的制度规定延伸出了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上的不同对待,以及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政策的城乡差别。而且,从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度衍生出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制度,一些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一块巨大的蛋糕,农民可持股参与股份分红也是城市居民没有的权利。此外,在城乡居民的差别对待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区别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总之,中国居民已经分处于“身份—权利—待遇”的城乡制度性差别体系之中。
二、三元化利益格局与“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差别
最近数十年的城市化过程,我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未曾预料的深刻变化。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出现新的状态,彼此分离的城乡社会经过不断的动态变化,已远远超出了二元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在某些地区,在原本比较清晰的城市与农村两大结构性板块之间,逐渐生长出一个对于两者来说都是非此非彼、不城不乡的边缘地带。城乡二元化结构在城市的发展中不断延伸和复杂化,城乡之间的差距也随之进入了城市,在更为有限的空间中形成聚合并且锐化,由此城乡差距也就演变为了同城差距。于是,由于社会体制、制度和文化等原因,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们,不得不分属于彼此隔离、相互排斥的“身份—权利—待遇”世界之中。从“身份—权利—待遇”城乡差别到同城差别,这是一种以往未有的社会表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最富特点也是最为棘手的现实。
这一演变不仅是《乡土中国》当年的思考场景不能涵盖的,对于当代一些研究者可能也是始料不及的。面对经过复杂交叠和重新组合的城乡二元社会,特别是一个城市空间下高度浓缩的城乡差别,以及城乡二元间的亦分亦合的结构和关系状态,如果我们在运用一些二元分析范式(如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时进行非此即彼的排斥性选择,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此外,包括一些衍生和变异的范式——“半乡土社会”、“半城市社会”、“新乡土社会”等的运用中,常常也是如此。这种现实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新试验场。
(一)“三分天下”的人口格局与三元化的利益格局
在城市化的急速推进趋势下,剧烈扩张的城市显示出巨大的虹吸效应。一方面,大批农村人口进入了城市外来人员的行列,形成了一支在不同城市之间游离流动的务工大军;另一方面,农村的经济要素和社会资源也不断被“圈入”城市,在城市的不同利益群体中进行重新划分和配置。由农村流动人口和“农转非”人员汇成的庞大的城市新增人口大军,在改变城乡人口格局的同时,也重新规划了城乡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往隔离在城市和农村的两大群体——市民与农民,现在却在一座城市中持续碰撞和相互浸染,这一过程逐渐在城市与农村两大板块之间推起了一个另类板块,这是一个不城不乡、非此非彼或亦此亦彼的边缘带。观察当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个赫然镶嵌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板块。由于中国地域性社会的差异,不排除各个城市的第三板块有其各自的特点,不过,与传统的两大板块既明显不同并且同在共生,是第三板块的共同特征。
“三分天下”的人口格局。一般而言,中国的城市人口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本地农村户籍人口,二是本地城市户籍人口,三是外来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总数中,上述三大群体所占的比例可能不尽相同,但人口格局的“三分天下”仍表现了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地处东部的北京市为例,2011年该市户籍总人口为1277.9万,其中非农业人口1013.8万,农业人口264.2万,此外,暂住人口有825.8万人。综合上述信息,2011年北京市总人口为2103.7,其中,非农业人口约占48%,农业人口约12%,流动人口约40%。从杭州市、广州市等东部城市的人口变动,也可以看出类似的人口变化趋势。(24)
中西部主要城市近年的人口变动也显示了类似情形。如郑州市2009年底流动人口突破223万人,市区常住人口290多万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1.3。武汉市2010年末总人口为836.73万人,2011年该市登记的流动人口240多万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约达28.7%。长沙市2010年常住人口704.41万人,流动人口达166.82万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为23.7%。(25)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有较高比例,农业人口的比例也远远高于东部城市。在西部地区,随着近年国家对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一些主要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明显增强。如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的“工业航母”计划、宁夏银川市滨河新区的“产城一体化”建设、甘肃兰州市的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建设等,在这些大型开发项目的带动下,西部城市的人口格局正在出现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脱离了传统农业,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也相应迅速提高。
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从“三分天下”的人口格局中,应当察觉到社会群体结构及其利益结构某种新特征的出现。随着城乡二元化结构不断进入到城市空间中,农村人口在城市生活中经过糅合重组,形成了一个新社会群体。这个群体越来越表现出非城非乡或亦城亦乡的特点,与市民群体和农民群体一起重构了城市的群体关系,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利益格局。原有的城乡二元关系也随之发生了一种转变: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经过浓缩聚变,城乡差距获得了一种新的样态,这就是同城差距。目前,本地市民、本地农民和外来流动人口这三大人口群体之间的关系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同城差距。一种具有三元化特征的社会结构,或者说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也在同城差距中显现出来。以我们课题组2011年末在广东南海的实地调查为例,“三分天下”的人口格局与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
相关资料显示,南海区整个户籍人口有120万,常住人口达256万。(26)据此推算,外来人口应该为136万。从制度设置的角度看,户籍制度作为第一道分界线,划出了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本地人”与“外来人”的界分。这一界分也呈现了南海近年来的人口常态:在该区整个256万常住人口中,“本地人”少于“外来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倒挂”,在南海区是一种普遍现象。户籍制度界分了“本地人”与“外来人”两大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区隔。不过,这两个群体的利益纠葛还不是左右南海区社会利益格局的全部因素。
南海区的常住人口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农村户籍人口,二是城市户籍人口,三是外来人口。重要的是,南海人口的三大群体大致上勾勒出了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仅以农村户籍人口享有的集体经济股份分红为例,在该区120万总户籍人口中,农村户籍人口约为73.7万人,这部分人口超过了总户籍人口的一半,但在整个256万常住人口中仅占28.8%,为1/4多一些。按照集体股份合作制,拥有农村户籍的73.7万“乡下人”,是享有股份分红的一个利益群体,每年按时按点,都能“有钱分”。其余的46.3万城市户籍人口和136万外来人口,这两个群体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是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的“体制人”,均属于“没钱分”之列,是不享有股份分红权利的两个利益群体。
可见,农村户籍与集体股份合作制这两大制度性因素,共同构成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的分界线,首先将南海区人口划分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两大利益群体,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利益壁垒。同时,这道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的分界线对“本地人”群体又做了再次划分,将其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本地人”群体,一个是由本地农村户籍人口组成的,享有股份分红的“本地人”群体;另一个是由本地城市户籍人口组成的,不享有股份分红的“本地人”群体。这就造成了“本地人”群体的社会利益权利的破裂。在南海区,户籍制度与农村集体经济制度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地方性表达,通过农村户籍与集体股份合作制建立的利益和权利区隔,在整个本地户籍人口中划出了两大利益群体的区隔,从而促使三大人口群体的利益分化进一步锐化,也促使本地户籍人口在更为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不断破碎化。这一总体趋势确定了南海区社会利益格局的基本底色。尽管南海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但其三元化人口结构和利益格局所反映的一种典型性,在中国各个城市的人口结构与利益格局中都可以普遍观察到。
(二)开放中的封闭:“身份—权利—待遇”的三个世界
从城乡差距走向同城差距的历史宏线,展现了“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从城乡差别结构到同城差别结构的巨变,向我们预示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总体变化趋势,这就是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这种实际情势不仅要求超越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农民与市民、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二元范式,同时也再次逼问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逻辑。在此,我们尝试提出了“三元化特征社会利益格局”的框架以及三元化利益格局下多元社会利益诉求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进行分析和解释。可以看到,由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口集结的三大利益群体,构成了三元化特征的社会利益格局,凸显了三方分处在“身份—权利—待遇”的三个世界之中。在利益相关的三方之中,任意两方的组合都会构成不同的利益关系,在不同的利益焦点上表达自己的诉求、纠结和纷争。围绕着社会身份、社会权利和社会待遇,这三个世界每天甚至每时,都在上演新的故事、讲述新的情节。
第一,在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的双边利益中,土地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仍然是城乡社会差别的主因。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国家在城市和农村的土地、住房、计划生育等方面实行的不同政策,使国民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体制形成了切分。虽然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都是同城户籍人口,但其社会身份、权利、待遇则显示出明显的差别,特别是东部较发达地区,本地农民的社会待遇比本地市民更为优厚。本地农民与本地市民的同城不同待遇,“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差别非常明显,这是造成本地人群体的利益破碎的重要成因。
第二,本地农民与外来流动人口这两个群体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外来流动人口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流入本地的农村户籍人口,另一部分是流入本地的外地城镇人口。前一部分是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人口群体,由于不是本地农村户籍,其农民身份虽然相同,与本地农民同城生活但实际权利和待遇完全不同。后一部分市民身份的外来人口群体,法理上享有市民权利和待遇,但也由于不是本地城市户籍,与本地市民同城生活但实际权利和待遇也基本不同。因此,本地农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关系实际上涉及了三个利益群体,即本地农民群体、外来农民群体和外来市民群体。在本地农民与外来人口“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中,也表现了不同地区农村群体的利益分化。
第三,本地市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利益关系,因外来流动人口的不同情况,其中主要方面的是本地市民与外地农民、本地市民与外地市民的关系。外地农民与本地市民相比,虽享有承包地、宅基地、计划生育指标等待遇,但因异地谋生,这些农村优惠政策在南海没有实际优势;外地市民与本地市民相比,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都不能享有同城待遇。本地市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关系实际上涉及了三个利益群体,即本地市民群体、外来农民群体和外来市民群体。在本地市民与外来人口“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中,集中反映了城乡差别以及不同地区城市差别。
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差别,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在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社区参与(譬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方面的差别,也表现了“身份—权利—待遇”的三个世界。与户籍制度造成的利益和权利划分相比,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涉及更多、更深、更大的利益和权利分野,这道分界线因而更为固化、僵化、难以逾越,有时甚至不可逾越。三个世界的现实区隔使得三个群体固守现有利益划分,围绕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展开竞争、博弈、冲突,这种情形又反过来加剧了三个世界的彼此封闭和相互排斥。
三、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
本地农民群体、本地市民群体、外来人群体(包括外来农民与外来市民)的现状,反映了“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以及开放过程中相互封闭的三个利益世界。正是围绕着身份、权利和待遇的差别,还有相关三方的利益分歧,构成了三个世界的紧张、纷争甚至冲突的爆发点。显然,如果不打破现有的三元化社会利益格局,三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纷争过程将继续释放出巨大的张力。从更深层次上看,我国现有的各种制度排斥及其延伸出的各种社会排斥,将国民归入了不同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从而形成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根本分化。因此,要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就要不断推动三元化利益结构的柔化、弱化和同化趋向,打破三个利益世界之间的排斥性和封闭性。我们认为,破解“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共享的“身份—权利—待遇”新体系,是一项最为关键性和基础性的工作。
(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理念:“以人为本”还是“以地为本”
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题中之意,而消除“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以及与这一差别相联系的三个利益世界的区隔,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可以说是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如果同在一座城市中谋生存求发展的本地市民、本地农民和外来人口,在基本利益上是相互隔离、彼此排斥的关系,那么城乡一体化就无从谈起。可以说,这是如何对待“人”的根本问题,是涉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理念问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理念将贯穿始终并发挥着统领的作用,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构想、规划、手段、步骤、效果和目标带来深远的影响。城乡一体化建设理念说到底,就是“以什么为本”的问题。从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实际看,“人”与“地”成为了两大焦点,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城市化理念,一个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另一个是“以地为本”的城市化。如果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是将“以人为本”为理念,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以地为本”的城市化的一种延伸。
“以地为本”的城市化表现在各个方面,以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为例。一般来说,城市化率是采用人口统计学指标,按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的,中心城区、县(市、区)及建制镇,凡列入城镇建设规划且城区建设已延伸到乡镇、居委会及村委会并已实现水、电、路“三通”的,都纳入市镇人口计算。按照这一统计方式,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27%。然而,如果按照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2011年中国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两个数据相差1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27)事实上,“土地城市化”远远超过了“人的城市化”,正是“以地为本”的城市化理念的一种现实反映。
因此,如何避免陷入类似“以地为本”城市化的困境,这是目前城乡一体化实践必须警醒的大问题。在实际中,许多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思路和方案是“以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譬如,将城乡一体化建设当成了开发土地和投资基础设施,开拓资源、产业、市场、资金等经济要素作用的过程。又如,以乡为重点,以城带乡,试图通过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还有,侧重于城乡空间布局的一体化,以城乡土地利用的统筹规划,形成功能完善、产业互补、布局合理的城乡统一规划体系,等等。显然,如果不能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那么城乡一体化建设就会面临“土地城市化”的危险境地。
城乡一体化不能等同于城乡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的协调统筹,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城市社会的体制和制度的深刻转变。也可以说,城乡一体化是经过一系列改革达成的最终结果。其中,消除“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破解城市三大人口群体的社会利益“三个世界”,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绕不开的关键问题,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切实把握现有三元化社会利益格局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城市社会的体制和制度进行改革的基本思路、整体框架、实施方案等。通过这一过程不断推动三元化利益结构的柔化、弱化和同化趋势,最终打破三个世界的封闭、隔离、排斥,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途径。
(二)“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化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不仅需要改革的意愿和勇气,还需要缜密的思考和合理的规划,以及实施方案、程序步骤、统筹措施等。其主要方面包括,对城市三大人口群体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进行甄别、分析和评估,形成“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差别的现状资料;根据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理念,对同城居民的社会权益指标体系进行统筹设计;同时,对农村户籍和土地制度产生的利益驱力采取弱化措施,柔化或消除同城居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环境权益的实际差别。
关于城市三大人口群体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进行甄别、分析和评估,上文已对三个群体(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外来流动人口)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了大致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在此基础上,可以对“身份—权利—待遇”体系同城化进行技术设计,建立“同城居民城乡一体化社会权益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譬如,以城乡一体化作为总体目标,并对这一目标做进一步的分解,可以得到更为具体的子目标,如经济一体化目标、政治一体化目标、文化一体化目标、社会一体化目标、生态环境一体化目标等。由此,在“同城居民城乡一体化社会权益”的一级指标之下,再进行指标体系的多层次设计,如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环境权益等;这五大二级指标继续递进,可分解出居民社会权益的若干三级指标;同理,可递进分解出若干四级指标以及更次级的指标。同时,根据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外来流动人口的评估资料,在每一级指标中进行分别设计。这样可以初步形成一个“同城居民城乡一体化社会权益指标体系”。
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但是,在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村流动人口未能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在未来一定时间里,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如果他们仍然不能享有同城待遇,那么这种城市化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必须真正实施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走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我们关于重建现行“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阐述和“同城居民城乡一体化社会权益指标体系”的构想,旨在弱化或消除三大人口群体的利益区隔,缩小城镇居民在社会权益方面的现实差别,通过这种平抑不公、消除区隔、缩小同城差距的过程,不断促进三大人口群体在利益诉求方面的相互包容、开放和共享,不断趋近“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同构的愿景目标。这既是中国城市化的迫切要求,也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结语:重温正义的双重内涵
“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同城化是一项涉及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事业。这里,厘清正义与平等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早在2001年,郑杭生在《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一文中,就对正义与平等和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区分了正义的两种主要类型——“平等的正义”与“公平的正义”,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两者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或交叉的,如机会的平等、竞争规则的平等属于公平的范围,这是它们的联系。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一般地说,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如果说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则是某种“异”。并指出,“社会成员之间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的情况,在体力上、智力上、社会协调能力上的素质,都是千差万别的,不可能绝对拉平。谁要无视客观的社会差别,就不可能不陷入幻想、空想,并在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28)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正义往往是包含了差别的正义,这种历史性使得差别的正义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在实际生活中,“公平的正义”更具有日常现实性。同时,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的社会差别也是客观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等是不切实际的,“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体系更侧重于表达合理差别的正义即“公平的正义”。正因如此,“公平的正义”与我们的生活相随常伴,常常激发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关切、博弈、竞争甚至冲突,也促使我们必须以包容、开放、共享的方式来对待彼此的利益诉求。
也可以说,平等的正义与公平的正义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平等的正义表达了“价值性”,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美好追求;公平的正义表达了“工具性”,它使得这一追求成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当然,在每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在每一个不同的文化、国家和社会中,这种具体的、可操作的正义都会有不同的含义。包容、开放、共享的“身份—权利—待遇”体系既内含了正义的价值性和理想性,也重视正义的工具性和可兑现性。在追求同城同待遇、同国同待遇的价值目标时,我们因而能够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明智。
注释:
①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21页。
②[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64-166、298-299页。
③[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第55、56、146、181页。
④关于“勤劳革命”的中国发展模式,参见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164、165页。
⑤刘铮等主编:《人口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251页。
⑥熊月之:《中国传统城市特质的变易与延续》,载《学术月刊》,2009(2)。
⑦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2、44页。
⑧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参见《城市史研究》第2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14页。
⑩李泽厚:《美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1)[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71-75页。
(1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567页。
(13)熊月之:《中国传统城市特质的变易与延续》,载《学术月刊》,2009(2)。
(14)刘君德、汪宇明:《制度与创新——中国城市制度的发展与改革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第27、316页。
(1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9、10、19、56、62页。
(16)(17)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316-395页。
(18)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204-215页。
(19)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78、299-300、316页。
(20)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1)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3页。
(22)[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300-304页。
(23)胡雪琴:《中国成世界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国家之一》,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09-20;陈锡文:《城乡收入差距仍扩大》,载《新世纪》,2011-01-30。
(24)参见《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北京市统计局网页http://www.bjstats.gov.cn/nj/main/2012-tjnj/content/mV47_0310.htm;《杭州常住人口:870.04万》,载《今日早报》(杭州),2011-05-12;《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流动人口——解读〈杭州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杭网2012-05-13,http://www.hangzhou.com.cn/hzwtv/tvhzxz/2012-05/13/content_4194635.htm;《广州市统计年鉴》(2011),广州市统计局网页http://data.gzstats.gov.cn/gzStatl/chaxun/njsj.jsp;《广州市流动人口接近户籍人口数》,载《广州日报》,2011-01-06。
(25)资料来源:《郑州常住人口862.65万南阳常住人口1026万》,大河网—河南商报,2011-05-07;《武汉市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第41页;《武汉市流动人口晚婚晚育享受休假待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4/15/ c_121310035.htm;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湖南统计信息网,http://www.hntj.gov.cn/zhuanlan/6th_census/events/in_province/201105/t20110513_85176.htm
(26)《广东南海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城里人哭着喊着要去农村》,载《中国青年报》,2012-03-08。
(27)《数据显示我国1.28亿生活在城镇民众无城镇户口》,载《中国青年报》,2012-12-04;《发改委酝酿新型城镇化: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载《财经国家周刊》,2012-08-20。
(28)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3)。
标签: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三元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乡土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