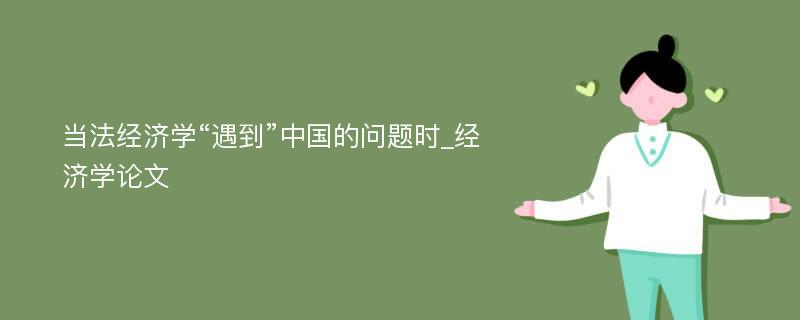
当法律经济学“遭遇”中国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经济学是一门源起20世纪60年代并至今发展迅速的交叉学科,其特点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律制度,通常人们又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就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律这一特定的研究范式而言),或者经济分析法学(当代法理学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
与以往重于哲学、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的法理学流派不一样,经济分析法学用于研究法律制度的理论前设和研究工具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故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和当代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紧密相关。由于经济学和法学都是以人、人的行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因此,在资源有限、信息不完全的现实制约下,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以成本—收益分析和博弈论为工具的经济学不仅能够适用于研究法律制度,为制度的形成、变迁和完善提供相对更好的解释和判断,更可以在如何评估并促进法律规则有效率、使法律程序和规则更加合理化以及使公共选择真正体现公众利益等问题上成为传统法学的理论参照系。
自1960年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①一文以来,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社会科学领域的成功范例,法律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传统的价格理论,②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将博弈论的视角和方法带入了对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的研究和分析之中,③不仅削弱了以概念界定、法条解释和类推适用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法学,更以一种更具一般性的宽广而统一的视角推进了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由于其“趋利避害”的有限理性人假定看似激进实则与普通人的个体经验大体吻合,更由于法律经济学理论表现出来的超强解释力,虽伴随着来自传统规范法学的各种质疑和抗拒,资历虽浅但也发展壮大了半个世纪的法律经济学,不仅作为一种具有方法论创新意义的学术思潮改造了(或正在改造)以决疑术和诠释法学为基础的传统法学理论,更作为一场波及法律人思维方式的思想运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当然了,法律经济学的超常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不故步自封,努力向一切新知识开放的学术秉性。虽然其最初的理论根基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甚至心理学都深刻影响并改变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格局,扩大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最终决定了法律经济学的影响力。至于法律经济学的源起、发展和可预期的未来,下文会有详细介绍。今天,至少在法律经济学的美国“老家”,如莱西格所言,“随着这一运动的成熟……法律经济学如今已改变了法律的全部领域”,而且,“如今,我们全都是法律经济学家了!”④
在中国,如果以种明钊先生介绍法律经济学的那篇论文算起,⑤法律经济学的引进已有近30年历史。即使以考特和尤伦那本《法和经济学》(这是国内第一本权威法律经济学译著)出版的时间算起,法律经济学的发展也有近20年了。⑥在这二三十年里,正如苏力的概括,从一个令人生疑的理念、到简单的人物和学派介绍及批判、再到比较完整的教科书及相关专著的翻译,⑦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得到中国法学界的承认。但遗憾的是,与法律经济学在国外蓬勃发展相比,中国法学界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总体而言并不尽如人意,不仅人手不够,研究主题不够集中,更无法形成规模化的集约研究局面。⑧即便与国内经济学界相比,法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差距。⑨
还不仅是有差距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在核心法学期刊上正式发表的法律经济学论文却还存在理论误读、基本概念不清晰,甚至出现基本性常识错误的现象。⑩因此,为廓清基本概念和理论源流,本文力图“正本清源”,以一种知识史的视角梳理法律经济学的源起和发展,并在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指出其主要理论的贡献、弱点和解释限度。尼采曾经说过,“‘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11)在很大程度上,法律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吸纳新视角、不断破坏和突破自己的历史。
不过,作为一个不仅仅满足于了解和套用西方理论的中国学者,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前指出,那就是,法律经济学理论源起和生长于西方的制度环境(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民主宪政的政治环境),这套逐渐发展壮大且已自成体系的西式理论能否有效解释发生在急剧转型变迁之当代中国的诸多问题?如果不能,面对变革大时代给予我们的这一潜在的“学术富矿”(苏力语),中国法学者能否通过“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作出独特的学术理论贡献?(12)因此,当法律经济学“遭遇”中国问题之际,面对挑战的不仅是来自美国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更是想有所创造和贡献的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者。
本文基本结构如下:首先是在法律经济学进入中国以来的基本背景下,指出学术梳理的必要性和基于中国问题作出学术贡献的可能性。接下来,为廓清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法律经济学之源起和发展作一简要概述,不仅探寻法律经济学的前史,更从科斯定理入手概略梳理了法律经济学的源流,并在此基础上介绍后续博弈理论的跟进并进一步展望法律经济学的未来。第五部分从理论梳理回到中国问题,以吴梅案(最高法院公布的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之一)为例,指出既有的诉讼和解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此案中的和解和后续“违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国外理论“失灵”的地方才蕴含着中国学者基于中国问题作出独特理论贡献的可能性。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二、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密:法律经济学前史
一般人都认为,虽然1958年芝加哥大学艾伦·迪莱克特(Aaron Directer)创办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开启了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先河,但科斯1960年发表在该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才真正奠定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自此之后,不管是追随科斯者还是反对科斯者,不管是后续的学术推进还是永远不会终结的理论质疑或反驳,都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构筑了法律经济学这座今天看起来巍然雄伟的理论大厦。
但以得失权衡(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常识的成本/收益考量)的角度看,法律经济学的源头很深远,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分配正义(在公共领域)和校正正义(在私人领域)。在亚氏看来,公共领域的分配正义就在于合比例,只有合乎比例和适度的分配才是公正的,这就是公域中的比例原则。(13)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该原则隐含着在资源有限的现实世界如何通过一种事前的立法模式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分配财富,因此符合法律经济学逻辑。时至今日,分配正义及蕴含其间的比例原则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销声匿迹,其不仅已成为公法领域的基础性原则,更成为20世纪末西方各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新哲学基础——即与仅仅强调正确断案的“实质正义”哲学而言,“分配正义”的司法哲学更强调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实现有效公正的分配,认为程序制度的设计必须保证法院资源的分配确与案件的难度、复杂程度、价值和重要性大致相当。(14)在私人领域,亚氏认为要实现校正正义,法官就必须在个案中根据一种得失的比例均衡原则——即对加害人施加惩罚造成的伤害大致相当于加害人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并权衡双方的所得和所失得出公正的判决。(15)这里面同样隐含了现代法律经济学也同样会考虑的问题:即如何在“质”上判定是否正当以及如何在“量”上判定是否适当。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只是在一般性哲学的层面上论及了法律经济学的核心价值(即“效率”)和基本逻辑(也即“得失权衡”),到了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17、18世纪,苏格兰政治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Jeremy Bentham)以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思想和理论自然成为法律经济学运动相对晚近的思想源头。休谟在其《人性论》一书中深入讨论了人类社会之和平、秩序和安全所需依赖的三大基本原则:所有权的稳定性、财产的约定转让以及约定的履行,他对普通财产法和合同的洞察力和精到分析就连当今很多法律经济学家都无法超越。(16)至于边沁,秉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标准,认为法律的目的就在于阻止引起恶这一后果的那些行为来增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因此立法者应制定奖惩措施去制约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17)在很多人眼中,坚持人的快乐和痛苦能够被计算且以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原则的功利主义哲学,就是今天所向披靡的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18)而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不仅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证了劳动分工、经济效率与国民财富之间的正向关系,指出基于分工的合作和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更论证了在没有任何强力的情况下,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并最终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分工的前提是财产权的界定以及对后续交易安全的信心,因此,斯密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对有效界权和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并阐发了一个公正、独立、有效率的司法制度有助于市场制度良好运行的观点。正是斯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斯看待世界的角度和进路,并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科斯经济学。
三、法律经济学发展简史:以科斯定理为起点
虽然法律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很深远,但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却是科斯,其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科斯定理更无可置疑地被公认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但何谓科斯定理,又该如何在科斯的思想脉络和经济学的学术谱系中准确理解科斯定理?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出现对科斯思想的误读,更可能无法准确把握科斯之后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和突破。
许章润教授曾言,对经典文本的解读至少需经历“文本解读、语境分析、意义阐释、风格赏析和谱系定位”五重进境。(19)因此,要了解科斯定理的深意,就必须进入科斯的学术世界和经济学的学科背景中,了解科斯想要批判什么,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什么新理论。简言之,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以市场行为具有连续性为其研究基础的微积分彻底改造了经济学,并经马歇尔之手建构了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20)不同于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斯密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完美市场下的资源有效配置,而企业和社会制度问题则作为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既定前提或外生变量被搁置一旁了。其后果有二:其一,仅仅专注于对供求均衡这一市场经济之“血液循环”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该循环得以运行的“身体”(主要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环境(即政治和法律制度)之研究;其二,由于真实市场常常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经济学家往往将之归因于“市场失灵”,即外部性、垄断和公共物品问题,因此,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隐含了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的政策寓意)开始大行其道。(21)
科斯基于一种真实世界而非理念世界的视角,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都飘在空中,就像是一个研究血液循环的人没有躯体一样”,(22)因此不能回答“为什么存在企业”这一真实世界的基本问题;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则在外部性问题的处理上存在根本缺陷。针对前者,科斯的回答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针对后者,则是1960年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杂志》上《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年轻的科斯第一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指出企业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在科斯看来,只要企业组织生产的成本小于通过市场展开交易的成本,企业就会出现,而企业的最优规模一定落在边际交易费用等于边际管理费用之处。(23)时隔多年之后,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进一步深化和阐发了交易费用概念,并指出交易费用对制度形式的影响以及交易费用和权利配置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重要性。(24)
自此,被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外生变量且搁置一旁的企业和社会法律制度成功地被科斯转化成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不仅成功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更推翻了庇古关于外部侵害的政府干预理论,动摇了福利经济学的根基。凭借《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前后时间跨度很大但内在逻辑高度统一的基础原创性论文,科斯不仅一手开创了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三大极具影响力和学术创造力的新学科,更是一举获得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法律方面,20世纪上半叶以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已经为美国法接受经济学理论准备了基础;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反托拉斯法、公司法、公用事业管制法和联邦税法都接受了经济学的严格审查;但这些对法律的经济分析都还不是系统的研究,更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核心和研究范式。科斯定理的诞生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费用理论改变了这一切,它不仅为法律实施和法律制定的评估提供了标准和方法论起点,更为以后蓬勃发展的法律经济学运动提供了一个看待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崭新视角:是否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分析工具——即以一种边际的、替代的和总体的比较原则来比较不同制度下的交易费用。
20世纪6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初创阶段。除了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卡拉布雷西随后(1961年)发表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一些思考》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侵权法的首次尝试,阐明了简单的经济原则就能为意外事故的损失分配提供有效和系统的标准;(25)阿尔钦(A.A.Alchain)同年出版的《关于财产权的经济学》则努力将效用最大化理论扩展到财产法律制度的研究,表明了财产权的进化和发展本身也是受经济力量支配的。(26)这是法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几乎与此同时,使得法律经济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大加强的另外两个理论基础也逐步确立了:其一是在制定法和宪法的经济分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其代表人物是弗吉尼亚大学的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27)其二是将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运用于大量非市场行为的研究,代表人物是将效用最大化适用于一切个人选择领域的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28)
在此之后将法律经济学成果全面运用于法学理论的是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可以说,在波斯纳之前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几乎都是经济学家的天下,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影响都还不是很大,但波斯纳1973年出版发行的《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一书改变了这一切。由于深受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科斯、贝克尔、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的影响,再加上其深厚的法学根底,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传统的价格理论娴熟运用于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税法、家庭法、刑法、宪法乃至程序法等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给当时的美国法学界来了一次“革命”。虽然一直有争议,对于被视为当代法理学流派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经济学而言,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不过,细究起来,波斯纳理解并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研究的法律经济学和科斯主张的法律经济学似乎有所不同。正如前面指出的,科斯是一个谨慎的经验主义者,他反对那种形式主义的数理经济学,认为那是一种不关心真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但在波斯纳看来,法律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运动,独特于一般经济学的是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作为法律中的一个运动来看,它在方法论上才是激进的。”(29)因此,波斯纳不仅主张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价格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全面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分析,而且偏好更数理化的抽象理论。不仅如此,对于制度,科斯秉承的是一种边际的、替代的、总体的比较分析,并不认为企业或市场就一定好而政府就一定坏,“在选择不同制度安排对付不同经济问题时,当然应在更广的标准上进行比较,同时还应综合考虑各种安排对生活各方面影响的总效果如何。”(30)法律或法官的判决当然也不例外。但波斯纳却认为普通法(即法官制定法)的“经济理论最好被理解为,它不仅是一种定价机制,而且是一种能造成有效率(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效率)资源配置的定价机制。”(31)在实证意义上,波斯纳试图证明普通法是有效率的,在规范意义上,波斯纳一直在为颇受人诟病的“财富最大化”——其为法官判案找寻到的规范基础——提供理论正当化的支持。(32)
因此,不管是在方法论还是在具体研究进路上,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都与科斯经济学相差甚大。在某种程度上,科斯反对甚力的庇古式思路借由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又“暗度陈仓”地回来了。(33)简资修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很准,他指出:
“科斯援引现实法律,批判福利经济学,促成了法律和经济学的联系。科斯的本意是,经济分析若未将现实法律考量进来,其结果是空的,所谓黑板经济学是也。如今的法律和经济学之结合,恰好相反,是以经济学分析法律。这原本也无不可,甚且应该是学术发展之必然,但庇古式经济学经此转折,反而在法律经济分析上大行其道,而科斯比较制度的经济学却被埋没了。”(34)
不过,虽然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在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运动中,波斯纳的地位和贡献却仍然是基础性的和巨大的。一方面,由于自1981年起波斯纳就一直担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其法律经济学分析就不仅仅限于理论性的法律政策分析,而是更多地凭借其法官身份和长期从事审判实践拥有的丰富司法经验,将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和逻辑渗透到了具体的法律操作和司法判决中。这就使得法律经济学不仅是学者书案笔头的理论构建,而是一种能深入影响法律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实践理性。不仅如此,作为一名高产的法学家,波斯纳法官笔耕不辍,完全凭一己之力成功地影响甚至改变了美国法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与经济学家威廉·兰德斯(William Landes)合作写作的众多重要学术论文在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普通法法理学的主流。在我看来,这就是波斯纳法官对法律经济学运动作出的一个突出贡献。
另一方面,和一般的法律经济学家不一样,波斯纳是一个永远在开拓学术边界的知识“拓荒者”,他喜欢把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普遍认为和法律没有多大关联的知识领域,“于无声处”为我们展示了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在解释人类行为上的统一性和内在融贯性,并展示了法学学术的另一种可能,开拓了法律经济学的学术疆界。这类学术著作包括讨论色情作品、替身孕母等性规制的《性与理性》,(35)讨论初民社会社会规范和原始法律的《正义/司法的经济学》,(36)讨论老龄化问题、衰老经济学以及安乐死问题的《衰老与老龄》,(37)讨论复仇问题、法律解释问题的《法律与文学》(38),以及联邦法院管理问题的《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39),等等。虽然其研究方法有略显单一之嫌,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挂”在法律经济学边缘的研究其实拓展了理性选择经济学的应用范围,是对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另一项或许被人忽视的成就。
因此,如果说科斯作为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奠基者是无可争议的话,波斯纳法官则无疑是法律经济学运动最积极也最重要的创始人、开拓者和普及者。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有了他此后的一系列重要的法律经济学论文和著作,有了他对财富最大化原则的论证、运用、修正和坚持,基于理性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在法学界引起重视并最终生根发芽(虽然过程中免不了有诸多质疑和争议,其结果也不那么乐观)。正如劳伦斯·莱西格所言,“他既是这一运动的詹姆斯·麦迪逊,又是亨利·福特:他把一套关于法律规则与社会结果之间关系的实用主义见解(规则如何影响行为;行为如何更能适应相关的法律规则)都投入了生产,他把这套方法运用于无穷无尽的法律题目,运用于一切,从合同到反托拉斯法到宪法的宗教条款以及法官行为”。(40)无论法律经济学运动未来如何发展,波斯纳法官对该运动兴起和发展所作的基础性贡献和功绩是永远不会被抹煞的。
四、异军突起的博弈理论及其应用
如果说科斯凭借两篇前后跨度30年但内在逻辑和思想具有一贯性的论文为法律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研究起点和争锋的学术平台的话,波斯纳法官更凭其超常的学术创造力和影响力将本属于“非主流”的法律经济学推到了美国法学理论的前台并牢牢占据了理论的主流地位。但无论是科斯还是波斯纳,都只是启动并推进法律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早期助力。正如波斯纳法官早就指出的,“法律作为实践理性,远不是要设立防线抵抗其他学科侵入法律,它隐含了要对一切可获得正当的确信的方法都保持开放。”(41)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当然也同样如此。
如果将法律制度视为一个对一切有助于我们理解、解释和试图完善它的新思想、新理论开放的试验场的话,波斯纳法官擅长的价格理论(或者成本—收益分析和供求分析)和科斯主张的交易费用理论就是已经经过测试并对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有所助益的法经济学方法论。但问题在于,由于科斯的关注集中在市场和自愿交易的约束条件上,(42)波斯纳法官的视野又主要囿于普通法和司法行为,上述理论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单个个体的理性行为以及分辨既有制度的优劣,但却无法解释法律领域内无所不在的策略性行为,以及制度从何而来、如何变迁以及为何存在大量无效制度等理论难题。幸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数学里衍生出来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进入法律经济学领域后,相当有效地回应了上述难题,它们不仅解释了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情形下人们之间的策略性行为以及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还解释了这种长期互动(即重复博弈)如何产生社会规范、社会变迁如何导致行动变迁、行动变迁又如何导致规范变迁,以及社会规范为何应当是正式国家法的民间基础等法理学的基础性问题。由于策略行为的普遍,也由于现实世界本就是一个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世界,博弈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席卷了经济学的分析领域,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律经济学既有的研究范式。(43)由于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主的传统法经济学不能解释策略性行为,因此,博弈论不仅开拓和推进了法律经济学的领地,更完善和充实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工具。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成果之一,博弈论以其抽象性、统一性和普适性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人类社会运行模式和制度建构的思考;经博弈论改造过的实证微观经济学,已然发展成为一个超出经济分析领域的关于人类理性行为选择模式的一般性理论;在法律经济学领域,就法律领域大量存在的策略行为,博弈论同样展示了其超常的解释力,从而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深刻影响了后波斯纳时代的法律经济学研究。
这种影响具体体现有三:其一,作为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并发展迅速的社会规范理论,就是综合运用法律和社会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非正式社会规范(或者称习惯法)以及正式法律与社会规范之复杂关系的学术流派。(44)其二,重在挑战传统经济学之理性假定的行为法律经济学,虽然借助了心理学的智力支援,也避免不了大量运用博弈理论(特别是在实验经济学部分)。(45)其三,虽然波斯纳法官运用价格理论和成本/收益工具全面分析了包括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在内的基本法律制度,但由于很多法律天然地涉及双边行为,博弈论在方法论上的成功入侵和对单向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有效替代就是一种必然。到今天,不管是研究侵权法、合同法、婚姻法、公司法这类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还是研究刑法、程序法甚至宪法这类公法,如果想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切入,缺少了双边互动的博弈论都是不可想象的。举例而言,波斯纳法官曾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讨论过诉讼和解的方程式,开启了诉讼经济学的先河。但诉讼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仅在波斯纳提出的乐观模型基础上发展出了案件筛选模型和外部性模型,更从双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建构了信息筛选模型和信号传递模型。而后两个模型就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诉讼程序研究上的成功运用(限于篇幅,诉讼经济学的经典论文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到波斯纳的成本/收益分析,再到更具解释力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不管是在研究工具还是在研究视野上,法律经济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结束对法律经济学发展史的讨论之前,我想简单总结一下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工具、基本目标和基本特点。首先,“趋利避害”的有限理性人是法律经济学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也是法律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其次,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主要有基于个体理性最大化的成本—收益方法、研究和评判制度效率的交易费用理论以及适用于两人或多人互动的博弈理论。虽然这三大理论各有各的适用领域,但由于现实世界是一个交错复杂的、无法被理论切割的统一整体,因此在分析和研究具体法律现象或法律制度时,视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研究目的,这三种理论都可以派得上用场。第三,法律经济学以效率为最终目标,其基本的效率标准是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其实是一种潜在补偿性标准)。在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局部效率和整体效率以及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出现冲突之时,法律经济学往往偏重于促进事前的、整体的和长期效率的达成。也因此,法律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主要是事前视角的研究,它注重考察政策、法律或其他可变因素变化后对当事人的预期行为激励,比如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就不是在因果关系和“全部赔偿”的概念下评判损失和赔偿,而是要通过事前规则的确定来激励潜在当事人谨慎行事,使预防成本和事故成本之和最小化。如果说传统英美法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的话,法律经济学强调的是一种“事前的视角”,喜欢“朝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因为,正如波斯纳所言,“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46)
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完善和改进,也伴随着批评和质疑,法律经济学发展到了今天。与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开端相比,法律经济学不仅在研究范围上有了很大的扩展(不仅从公共管制法律,特别是反垄断法延伸到了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等传统的普通法领域,还延伸到了宪法、程序法甚至社会规范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令人瞩目的改进和变化(从价格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一直到了最近的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应用)。今天的法律经济学家们不仅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内继续耕耘,更借用大量其他学科的知识大胆开拓了众多全新的学术领域,比如行为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实验的法律经济学研究、比较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以及历史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等,大大拓展了法律经济学的解释力,增进了我们对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既包括当下的,也包括历史的)的理解。可以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经济学在法学领域的应用虽然存在固有的一些缺陷,但还是成功地为法律人提供了一个看待法律的统一和宽广的视角,并为判断法律制度的优劣和进一步的完善提供了一些相对有效的标准和可行方案。
五、中国问题的挑战
本节从既有的理论梳理转向充满挑战性的中国问题。萨维尼曾明智地指出,“每一个作者都被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所限定(共时性),此外,他也被遗忘的时代所限定(历时性)。”(47)不过,在我看来,还不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时代,每一个作者其实还受限于空间意义上的生活、工作环境,或者制度背景。作为法律经济学奠基人和开拓者的科斯和波斯纳当然也不例外,由于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早已确立,法治相对健全的宪政国家,虽然各自侧重点不同(科斯关心市场经济下合约的局限条件,而波斯纳的雄心是要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全面运用于普通法领域,并以此改变美国法理学研究的方向和格局),不管是科斯还是波斯纳,都只能在既定的制度环境和学术传统中去发现问题、挑战传统、创新理论并以此解释世事。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不管是运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波斯纳提倡的成本/收益方法,还是最近20年发展迅猛的博弈论,市场、法治和宪政永远是西方法律经济学研究者“无言”的基本背景。不过,鉴于这些制度背景并不为所有国家分享,建基于法治国家经验的理论也许并不具有普适性。“法治西方的生活世界塑造了他们的理论关注,也限制了他们的理论视野。”(48)
因此,需要追问的是,面对制度环境和西方国家大不相同的后法治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原本极具解释力的法律经济学理论还能犀利如初吗?具体到中国,面对市场机制还未完全确立、法治尚不健全的现实,既有的法律经济学理论还能否有效解释特殊的中国问题?笔者接下来以吴梅案(最高法院公布的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之一)为样本,尝试着检验既有的诉讼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当事人的诉讼和解)之理论效力。
吴梅案全称为“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法院在“发布指导性案例的通知”上指出选择该案作为指导性案例的目的是为“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认为“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王亚新教授更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对该案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探讨,希望能以此指导和影响未来类似的个案判决;(49)而严仁群教授从二审和解后的法理逻辑入手对此案进行了尖锐但却有道理的批评。(50)
但以一种更开阔的外部视角审视,我们需要追问此案诉讼外和解协议为何未能履行?该案是否真的值得最高法院如此青睐,以及其是否真的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的探讨议题?让我们先看一下吴梅案的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从事废品收购业务,与被告有长期业务往来合作关系。从2004年到2009年6月11日,被告共计欠原告货款251.8万元。经多次催收货款无果,吴梅遂向眉山市东坡区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毫无疑义地,一审判决原告胜诉。但法院宣判后,被告却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了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利息请求。接下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但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就上述对吴梅案基本事实的描述,我们可以总结出该案的几大特点并作适当点评:1.该案是一个毫无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的简单案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原告的胜诉没有任何悬念;2.在一审期间,被告对原告的诉求供认不讳,没有任何异议,这意味着其对自己的败诉有100%的预期;3.如果说上诉的私人功能在于纠错和消解不满的话,被告对于自己完全无异议且没有任何错误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就是一种滥用诉权;4.上诉法院居然受理了该无理上诉,凸显我国的上诉审法院缺少有效的案件甄别机制;5.原审原告之所以在二审诉讼外和解协议中放弃利息请求,可能是为换取原审被告的实际履行作出的让步,但在原审被告不履行和解协议之际请求恢复原审判决的执行力,这不管在学理还是在常理上都具有相当的正当性;6.在原审法院支持吴梅的请求之后,原审被告居然还有“资源”和能力申请二审法院的执行监督以阻止吴梅的申请执行权,这颇让人有些诧异。
根据吴梅案的案情和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该案中的诉讼和解完全不同于诉讼经济学文献所集中关注的诉讼和解。不管是乐观模型、预期差异模型还是信息不对称模型,既有就诉讼和解展开的相关经济学分析,仅仅关注庭审之前信息不对称的双方当事人之和解条件以及和解是否可能的问题,“考察当一个参与人拥有其他参与人所不拥有的信息时法律规则如何改变谈判的动态性”(52)。因此,如果视美式诉讼和解是一个博弈的话,该博弈发生在特定的审前阶段(即双方当事人进入法院但又未正式进入庭审),且博弈当事人是特定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不仅如此,在美国,各自拥有诉讼信息且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双方当事人之所以能够在审前达成和解,实现某种“法律阴影下的谈判”,在于其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1.一个促使双方信息有效交流的审前准备程序;2.独立、公正的司法机构以及拥有较高职业能力和良好职业操守的职业法官;3.对“规则之治”的良好预期,也即双方当事人都明白一旦无法达成和解就要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以及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4.法院和法官的职责就是居中裁判,不存在中国普遍化的司法调解制度。这些制度促进并确保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和解,不仅能有效降低诉讼成本(不仅是当事人的,也是国家的),实现繁简分流的诉讼格局。更重要的是,由于诉讼和解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履行了就能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诉讼契约”,因此和解协议的自动履行不成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既有的诉讼经济学文献才能把眼光集中在审前双方当事人的和解谈判上,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诸多越来越精致复杂的理论模型。反观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我们不仅缺少有效的审前准备程序、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该系统内法官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也不乐观),更欠缺基本的“规则之治”以及当事人对规则之治的良好预期。不管是追求“案结事了”的司法调解,还是主动介入纠纷处理的“能动司法”,都使得目前的民事司法领域缺乏明确的规则和标准。在此制度背景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败诉当事人必然会有种种机会主义地利用制度甚至钻制度漏洞的行为,比如为拖延时间或获取因二审调解可能的不当收益,没有任何理由的败诉当事人会伺机提起机会性上诉;(52)再比如在二审过程中策略性地和一审原告达成和解,但事后并不积极履行,等等。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吴梅案。通过前面对中美民事诉讼制度的比较,我们发现吴梅案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无理的败诉一方当事人利用上诉制度、上诉过程中的诉讼外和解制度、撤诉制度和执行抗诉制度合理地拖延时间、逃避债务履行的策略行为。因此,该案中的诉讼和解就完全不是诉讼经济学理论视野中的诉讼和解,也就完全不能利用诉讼经济学的既有理论模型对之进行解读。就是在这里,当法律经济学“遭遇”特殊的中国问题之际,由于缺少法官行为和司法政策这两个变量,缺少法院和诉讼当事人之间存在动态博弈这一视角,来自美国的、作为法律经济学重要分支的诉讼和解理论完全无法解释吴梅案中的诉讼和解以及和解当事人一方后续的故意“违约”。
还不仅是吴梅案,由于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秩序,更缺失独立的司法和权力制衡的宪政框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竞争市场、独立司法和民主宪政基础上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在很多独具特色的中国问题上丧失了其在美国本土拥有的犀利和理论解释力。林毅夫曾在一本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书中指出,“理论的目的就是解释现象,当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摈弃。”(53)而“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54)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陈瑞华语)是有学术追求的中国学者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但更关键也更重要的是下一步,即在西方理论“偃旗息鼓”之际,中国学者能够基于特殊的中国问题作出更具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理论贡献。
六、简短的结语
法律经济学进入中国已有30年,由于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诸多理论误读或常识性错误,“正本清源”的工作因此甚为必要。本文以一种知识史的视角,从法律经济学前史一路讲到科斯定理、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以及后波斯纳时代统合了诸多学术流派并改造了此前法经济学研究的博弈理论。这样,通过梳理法律经济学的源起和发展,在凸显法律经济学深厚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更指出其主要理论(特别是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的贡献和弱点。不仅如此,以吴梅案为例,本文发现来自域外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完全不能回应和解释当代中国的诸多特殊现象和问题,对中国学者而言,这既是机会,更是挑战。因此,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凸显中国问题的挑战性以及知识贡献的可能性,这才是本文引而不发的“弦外之音”。
苏力曾就中国的法学研究总结出三种法学范式。(55)面对当代中国复杂纠结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语境,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只有通过良性违法才能推进法治的现实,过渡性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法法学完全不具有解释力,而站在既有的成文法律体系内部、重在解释法条、规则、原则和概念的诠释法学同样欠缺有效的解释力,虽然我们承认其在一个稳定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因此,当仁不让地,侧重于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力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解释现象并以发现潜藏因果关系为目标的社科法学成为最近20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创新性力量。以中国问题为切入点的社科法学不仅力图解释世界,更希望在真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以改造世界。
面对让西方理论屡屡受挫的中国问题,作为社科法学之核心力量的法律经济学能否完成此任务并实现其理论贡献的目标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参见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Oct.,1960,pp.2-144。
②参见Richard 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3。中文译本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林毅夫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③参见Douglas G.Baird,Robert H.Gertner,Randal C.Picker,Game Theory and the Law,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中文译本参见道德拉斯·拜尔等:《法律的博弈分析》,严旭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④1999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刊选了100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13人有专文介绍。这是时为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的理查德·莱西格为《美国法律人》杂志撰写的波斯纳法官简介——《多产的偶像破坏者》——中的一句话。这话虽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法律经济学在今天的美国法学界已然成功战胜诸多挑战者和质疑者并成为一种弥散化的存在深入人心却是事实。
⑤参见种明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法学季刊》1983年第2期。
⑥参见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比较系统的介绍主要有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乃根:《当代西方法哲学主要流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等。主要的教科书类著作有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皮特·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许明月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重要的法律经济学著作有道格拉斯·拜尔等:《法律的博弈分析》;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4年;大卫·D.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斯蒂文·萨维尔:《事故法的经济分析》,翟继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威廉·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学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唐纳德·A.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苏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安东尼·W.丹尼斯、罗伯特·罗森(编):《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等等。
⑧就法学界而言,不仅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不多(成名学者中似乎只有苏力一人,而年轻一辈中的法律经济学人也寥寥可数),彼此间的研究主题还很分散。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目前为止法学界比较拿得出手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作品仍是寥寥,有后续推进研究的研究主题似乎只有苏力提出的“海瑞定理”。相关的专著包括冯玉军(主编):《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邓峰:《普通公司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简资修:《经济推理与法律》,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柯华庆:《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博弈分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最近几年较为出色的法律经济学论文包括吴元元:《神灵信仰、信息甄别与古代清官断案》,《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冯玉军:《权利、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和经济分析》,《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艾佳慧:《“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何远琼:《站在天平的两端:司法腐败的博弈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吴建斌:《科斯经济学本土化路径重探》,《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简资修:《科斯经济学的法学意义》,《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就海瑞定理展开的相关研究,包括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苏力:《关于海瑞定理I》,《法律和社会科学》第四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桑本谦:《疑案判决的经济学原则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艾佳慧:《调解复兴、司法功能与制度后果——从海瑞定理I的视角切入》,《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5期;以及以“苏力定理还是海瑞定理”为主题的一系列批评性评论,《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五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⑨比较成体系的法律经济学成果最早是由经济学界引进和译介的,比如考特和尤伦的《法和经济学》,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等,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主力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界。张维迎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其撰写的《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是国内最好也最有影响力的法律经济学专著。另外,黄少安和史晋川两位教授组织的“中国法律经济学论坛”是国内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展示和研讨平台,该论坛迄今已成功组织了10届。只不过每一届的参会论文中,来自法学界的总是少数,虽然近几年的情况有所改观。
⑩简资修教授曾就国内法学界对科斯经济学的误读进行过相当有道理的批评(参见简资修:《科斯经济学的法学意义》)。
(11)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和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3页。
(12)这是苏力对他自己,也是对未来的中国法律学人提出的理论期望(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VII页)。
(13)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8-149页。
(14)更多对分配正义司法哲学的分析,参见阿德里安·A.S.朱可曼:《危机中的司法/正义:民事程序的比较维度》,阿德里安·A.S.朱可曼(主编):《危机中的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程序的比较视角》,傅郁林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
(15)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37-146页。
(16)休谟对财产权起源、财产权规则、财产的约定转让和约定履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卷本《人性论》的第三卷(参见大卫·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17)想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和他的立法理论,请参见杰瑞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18)更准确地说,这里所指的法律经济学其实只是波斯纳牌号的法律经济学。由于波斯纳法官巨大的学术影响力,这也导致一般人认为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关于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思想,后文会有介绍和评论。
(19)参见许章润:《经典:文本及其解读——关于阅读法学经典的五重进境》,《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0)新古典经济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原著第一版序言),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21)福利经济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庇古:《福利经济学》,金镝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22)参见Ronald H.Coase,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Vol.140,No.1,1984,p.230.
(23)参见 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Vol.4,No.16,1937.
(24)参见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25)参见Guido,Calabresi,Some Thoughts on Risk Distribution and the Law of Torts,Yale Law Journal,Vol.70,Mar.,1961.
(26)参见Arman A.Alchian,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Santa Monica,Calif.:Rand Corporation,1961.
(27)参见James M.Buchanan,Robert D.Tollison,Gordon Tullock,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1980; James M.Buchanan,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5.
(28)参见Gary S.Beeker,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6,Mar./Apr.,1968;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29)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2页。
(30)参见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p.143.
(31)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909页。
(32)在《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一书中,波斯纳花了大量篇幅论证财富最大化应该成为法律经济学的规范基础。具体内容,请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是第三章“功利主义、经济学与社会理论”和第四章“财富最大化的伦理和政治基础”。在遭受了诸多严厉批评后,波斯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修正。不过在后期的《法理学问题》一书中,虽然否定了前期视财富最大化为基础性伦理的理论努力,波斯纳仍然认为“如果对财富最大化作实用主义的理解,财富最大化就是工具性的,而不是基础性的,这一点并不是否定以财富最大化来指导法律和公共政策”(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83页)。
(33)就法律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这一方法论转折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我另有专文分析,此不赘述。
(34)参见简资修:《科斯经济学的法学意义》。
(35)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36)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
(37)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衰老与老龄》,周云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38)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39)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联邦法院—一挑战与变革》,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40)这段话同样来自理查德·莱西格为《美国法律人》杂志撰写的波斯纳简介——《多产的偶像破坏者》。
(41)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第556页。
(42)张五常曾对科斯说,他认真研读了3年的“社会成本问题”,终于发现科斯关注的是“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因此高兴地说,“到底有人明白我了!”此小花絮引自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3)博弈论全面进入法学领域的标志就是1994年出版的《法律的博弈分析》了。该书已有中文版,具体内容参见道格拉斯·拜尔等:《法律的博弈分析》。
(44)该学派的代表性成果包括,Robert C.Ellickson,Order without Law: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Mas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Jon Elster,The Cement of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Eric Posner,Law and Social Norm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Richard McAdams,The Origins,Development,and Regulation of Norms,Michigan Law Review,Vol.96,No.2,1997; Paul Mahoney and Chris Sanchirico,Norms,Repeated Games,and the Role of Law,California Law Review,Vol.91,No.5,2003.
(45)参见Cass Sunstein(ed.),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6)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15页。
(47)萨维尼:《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胡晓静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48)张维迎、艾佳慧:《上诉程序的信息机制——兼论上诉功能的实现》,《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49)参见王亚新:《一审判决效力与二审中的诉讼外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号指导案例评析》,《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50)参见严仁群:《二审和解后的法理逻辑:评第一批指导案例之吴梅案》,《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
(51)道格拉斯·拜尔等:《法律的博弈分析》,第278页。
(52)苏力认为,所谓机会型诉讼指当事人机会主义地转移个体诉讼成本的诉讼。但张维迎和艾佳慧的界定是,机会型上诉指那些不值得上诉法院投入司法资源的案件,既包括了寻租型上诉,也包括那些简单小额的上诉案件(参见苏力:《关于海瑞定理I》,第244页,特别是脚注19;张维迎、艾佳慧:《上诉程序的信息机制——兼论上诉功能的实现》,第93页,特别是脚注140)。
(53)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54)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VII页。
(55)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6-18页。
标签:经济学论文; 波斯纳论文; 博弈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法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