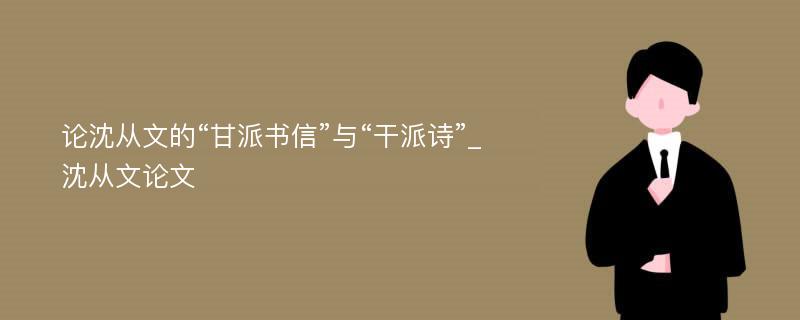
论沈从文的干校书信和干校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干校论文,书信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0-0139-06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以其多产的创作实绩和独特的美学风格享有盛誉。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从1924年发表文学作品一直到建国前,先后出版各种集子60多本,建国后沈从文放弃了写作而转向文物研究,仅有少量的旧体诗词和散文公开发表,在文坛上近乎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受到冲击后,于1969年12月1日被单位“连哄带骗”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到后才发现“榜上无名”,从此开始了两年多漫长的干校岁月。从1969年12月20日到咸宁452高地后的第一封家书,到1972年2月离开丹江的最后一封信,沈从文给亲友写了大量的书信。据收入《沈从文全集》第22、23卷书信的统计,共计94封,其中与张兆和之间的通信计63封,写信频率非常高,有时达到一天两封的密度。这些书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沈从文在干校期间的生活状况、心理情绪和思想波动,并涉及沈从文在干校期间创作的旧体诗的自我评价,为研究建国后尤其是“文革”期间沈从文复杂的创作心理和精神状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书信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带私人性质的交流,尤其是家书,在写作的时候,并不存在收信人之外的拟想读者群,因而更能够袒露书写者的真情实感。以沈从文干校期间的书信为切入点,研究沈从文下放后遭遇到的乡土经验,以及在这种乡土经验刺激下的诗歌创作,有助于研究者较为全面地探究建国后沈从文精神的复杂性,力求以此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沈从文,并以沈从文的现实境遇烛照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经验。
一
沈从文20岁时由湘西进入北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凭借勤奋的写作,在北京深深扎根,完成了由一个乡下人到城市人的角色转变和“乡下人”的身份建构。从步入文坛的那天起,沈从文就以“乡下人”的标签迥然有别于其他文化人:“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① 从湘西出走后,沈从文一直在都市流浪,在历经社会底层的食不果腹到跻身文化名流后的衣食无忧这一过程中,目睹了太多都市的罪恶和都市人的道德沦丧,从最初对都市的顶礼膜拜转变为都市中的精神漂泊者和“异乡人”,正如他所言:“一切由都市文明文化形成的强制观念,不是永远在螫我烫我,就是迷乱我,压迫我”,“人贴近都市,生命实永远见出格格不入处。都市无章次的动,和我生命中的动完全对立。使我存在如不存在”②。大都市的生活严重危及到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生存经验,致使他在都市系列和乡土系列两类题材的作品中,流露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在他笔下,都市人外表光鲜,文质彬彬,实质却恶贯满盈,虚伪至极;乡村虽不乏野蛮落后,但乡村人性格耿直,敢爱敢恨,充满生命活力。沈从文在3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游子归乡的渴望,在《虎雏》、《凤子》、《阿黑小史》、《雨后》、《夫妇》等小说中,明确传达出对自然人性和自由生命的追求。身处纷繁闹市,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写作,沈从文始终秉持在生活的挣扎中悟到的生活信念,对“乡下人”和乡土情有独钟。当然,沈从文“乡下人”身份的建构与自我情感认同,并不是要以返归乡土的形式来对抗现代都市文明,而是“意在确定自己在现代社会的身份位置”,借此“获得了一个思想的支点”③。这种“乡下人”的身份认同渗透到了沈从文的骨髓中,使他在喧嚣的都市能始终恪守一颗赤子之心。在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沈从文“以‘人类’的眼光悠然神往地观照本族类的童年,兴味多在远离时代漩涡的汉苗杂居边远山区带中古遗风的人情世态,为这种‘自然民族’写了一部充满浪漫情调的诗化的‘民族志’”④。沈从文因此以独特的乡土经验有别于同期其他乡土作家,并在众多文人中独树一帜。
沈从文对乡土有着根深蒂固的眷念。在大城市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化人,一旦有机会回归到乡土,与乡村进行零距离接触时,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又作何感想?是否会有截然不同的乡村体验?是否能够寻找到苦苦依恋的精神家园?是否能在古稀之年重获灵魂的新生?
1969年12月1日,67岁高龄的“乡下人”沈从文,开始了干校生活,先后迁徙六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在回顾干校生活时,沈从文用看似平淡的笔调叙述了当时的凄冷情景:“到六九年末,且被胁迫限定时日,疏散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于校。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⑤ 在咸宁452高地、双溪区革委、小学、生产队治疗所、农户家、丹江等处流徙的生活,加剧了沈从文心理的痛苦,加之身体不好,时刻面临高血压病发的危险,一家四口分居四处,身边又无亲人照顾,沈从文深切体会到晚景的寂寞与孤苦。
由沈从文在此期间存留的书信可知,下放2个月后,沈从文在干校领导的催促中由452高地迁徙到双溪区革委楼上一间阴暗潮湿的空房子,在稻草堆中打地铺,冬天无炭火取暖,只能以被裹脚。至小学后,报纸糊墙,一遇大雨屋中四处漏雨,成天只能穿套鞋,青蛙、蛇时有出没,打水、取饭极为不便。挪到农户家中,同样阴暗潮湿,毗邻猪圈,通风不便,夏季酷似蒸笼,臭气熏天。搬到丹江后,环境虽较为清幽,近乎世外桃源,但地势较高,交通极为不便,近处即是火葬场。在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下,沈从文的健康每况愈下,曾因高血压住院一个多月,却仍一直挂念着文物研究。妻子张兆和60岁仍需在向阳湖区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夫妇无法相聚,两个儿子又分居四川自贡与北京,不免有身世凋零之感:“绝料想不到……快七十岁了又还会来到这么一个几几乎和一切隔绝的乡间。”⑥
不难看出,步入人生暮年的“乡下人”,遭遇到咸宁双溪货真价实的乡下生活时,沈从文虽对乡土怀有深层依恋,可一旦发觉自己笔下对乡土的眷念与诗意的栖居已与现实相去甚远,干校的山水很难让他找到留连忘返的感觉。熟悉乡村人的吃住等生活现实后,沈从文开始对中国乡村的未来甚为担忧,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谈到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感受:“我觉得到这里三个月,比过去十年参观大工厂大农场,住大招待所有意义。特别是对比下,更明白多一些问题。不下来是什么也不懂的。只看到好的一面,不看到有待努力才能转好的一面,以及在努力中如何取得进展的情形。”⑦ 乡村的沉滞与“不变”,农村生活的困苦,让沈从文再一次体验到城乡巨大的差别,只是这一次与30年代返乡时写作《湘行散记》的时空背景已截然不同。30年代事业渐趋稳定的沈从文作为离家多年的归乡游子重回故里,带着对新婚妻子满腔温婉的爱意来记叙沿途风景,述说家乡的人情风俗,在这样一种和谐心境下书写出来的乡土人生虽也不可避免地伴有愚昧与落后成分,但其中彰显的乡土经验却令世人感叹不已。30多年后,沈从文在名为下放实为被贬的情形下再度回到贫瘠的乡土,面对人事与命运的捉弄时,感触更多的是人生的极端孤寂与困苦,住处的不断迁徙给他带来的是流放犯人等待发遣的痛苦煎熬。正如又一次面临搬迁时,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写道:“张大妈待北回,赵大妈还不来,因此也有可能将三人仍装还高地住席棚待分别发遣!这时一切均无知。心沉重点,是必然的。”信中流露出来的真实的沮丧情绪和对无从把握命运的担忧,跃然纸上。干校间的辗转流徙,沈从文“经历的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⑧。
然而,深受“区域性的楚人气质紧紧缚定,严格管制自己”,“用习惯性的谦柔方式挣扎,学习,和社会不合理现实斗争”⑨,沈从文在经历一番心灵挣扎后,在咸宁别样的乡村中,偶尔也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的美:住处大小山峦重叠,水清石秀,房屋整齐高大,黑瓦白墙,树木繁多,远近马尾松林相互映衬,他在自然美景前驻足停留,短暂忘却生存的烦恼,享受乡村带来的片刻宁静。在写给黄永玉的信中,沈从文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下放的乡村生活:“这儿荷花真好”,“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⑩。实际上,“每一个文本意义的确定,都要以其他未出现的潜在的文本作为参照。文本的意义存在于互文性中,而互文性不仅只存在于文学文本之间,还存在于作为内部文本的文学文本与外部文本,即社会文本(非文字文本)之间”(11)。沈从文的书信亦应作如是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选择历史博物馆作为“转业”的去处,十多年穿梭于库房与午门城楼,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主动逃离政治。但在“文革”来到时,仍不免受到种种难以承受的冲击。作为一个对工作充满热情与抱负的知识分子,一腔余热尚待发挥,沈从文却被当作包袱踢出单位,与另外两位老弱病残一同来到咸宁,心中的甘苦自不待言。在这样的情境中,以文字的诗意来淡化甚至美化现世的苦难,在书写的短暂瞬间将自我从艰难的现实中剥离,寻求心灵的慰藉与超脱,是沈从文应对新的乡土经验的一种生存策略。在这种策略中,沈从文得以维系被非常态的现世所打破的灵与肉的平衡,安然度过艰难时世。
二
在如此复杂的心境下,为了排遣无边的寂寞,从1970年2月起沈从文开始重拾写作,接续60年代初的旧体诗创作。1961年冬,沈从文在作协的安排下重新“出山”,去江西参观并开始了旧体诗的写作,同时计划以亲戚的真实故事来写一部歌颂革命者的长篇小说。庐山、井冈山和江西其他地区的火热生活触发了沈从文写作的热情,共创作16首旧体诗。从沈从文与张兆和的通信来看,沈从文对于自己的旧体诗相当满意:“遗憾的是有些用典使事精彩、准确、有分量,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六十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看情形将不免有十首左右可写也。”(12) 几年以后,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回忆这次写诗经历时,对于《井冈山之清晨》仍带着愉悦满足之情:“可说是我一生写作最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事件,和人民革命有关最有意义一回工作。”(13) 张兆和惊异于沈从文的旧体诗并期待他能够写出几篇好的散文来,《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对其诗歌也大加赞赏,这些更激发了他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诗魂,并对未来的写作抱以积极乐观心态:“过些日子或许还可为你写几首真正有新意的白话诗看看。现在人搞这一行一般说基本功都不大到家,和郭风作散文一样,十分勉强的凑和成篇。揽事过多体力不抵用,只好让人作大王了。我大致还可写个顶好的历史戏,等等机会看。还有些出人意料杂耍未出场!”沈从文在勾勒创作蓝图的同时,仍不忘批评当时的文坛,创作自信溢于言表。哪怕是在“转业”近20年后,沈从文在下放前夕写给历史博物馆领导的信中,仍对自己能够用笔进行实验性写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歌颂新社会人事,反映旧社会地主的残酷剥削问题抱有极大的自信(14)。但事实上,历史并未为沈从文提供此种写作的契机。计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最终未能写完,新诗和历史剧也未见诸文字。但在创作形式上,沈从文却探寻到旧体诗这一最适宜表达自我情感的方式。在双溪、丹江两地,沈从文共创作旧体诗32首,收录在《沈从文全集》第15卷的《云梦杂咏》、《文化史诗钞》、《喜新晴》等旧体诗辑中。从诗作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咸宁干校生活为题材的“颂歌”;第二类是抒发个人情怀的咏怀诗;第三类是与文物工作相关的咏史诗。
在双溪难捱的时日中,“五七战士”围湖造田、开山挖矿、征服大自然的种种壮举刺激着沈从文的诗心,他写下多首旧体诗。《大湖景诗草》组诗即是这种情境的产物。《大湖景诗草》组诗共12首,以向阳湖的自然环境、地理特色、“五七战士”热火朝天的干劲、“五七战士”形象为书写对象,讴歌人民战胜自然的强大力量。组诗中多次出现对社会形势的描写和国家政策的歌颂,如“谨记新指示,炼人先炼心”,“人民多伟大,无事不可成”,“世界形势好,祖国面貌新。日出东方红,天下齐照明”,“人知社会主义好,反帝反修计虑深”,“同学新指示,警惕帝修反”,“打击帝修反,同样树标兵”,“反帝防修千年业,五七指示明朗朗”,“试看天上红卫星,七亿人民齐拍掌”。《大湖景诗草》组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在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面前,自我定位是“我非楚屈原,泽畔亦行吟。为歌新社会,深感渺小身”,诗中流露出对“五七指示”的正面歌颂,对社会主义、反帝反修坚决拥护的情绪,一点都不亚于同期主流文坛的其他诗作。
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对歌颂干校生活的这一组诗无论是形式内容还是文字都评价较高:“主要即赞美五七干校战士的种种干劲。国内似乎还少有这么写的。将来或许有发表一天,为了是新事物的新反映。……若从旧诗角度说来,有的派头似乎也还好。”用旧体诗来歌颂新生活,如何结合柔美的自然背景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表现新战士精神,对沈从文的写作是一种挑战。沈从文对于用五言和七言来书写新内容的尝试,偶尔也会流露出力不从心的感慨:“即是五言,要‘古为今用’,大致也得有个一二年试笔,从一二百次探索中,可望一面是驾轻就熟,一面多少还带点偶然性,有廿卅首比较好,概括性强,能用一二百字反映一事件或描绘出某一情形下景色轮廓,就算是不虚此努力了。”既要把握宏观政治,又要紧密配合具体政治形势任务,将沈从文推入创作的两难。面对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沈从文有时又坚信“可是有个苗头,写到廿卅首后,会把得住题,五七干校的颂歌,会写得好的”。沈从文多次与张兆和在通信中分析、讨论诗作的得失,认为当时的情境只适合写诗不适合写小说与散文。沈从文由最初的探索尝试发展到写《丹江纪事》的得心应手,悟出“作诗大致和磨刀相近,越磨越快,操刀而割,便如‘庖丁解牛’,易‘得心应手’。牢牢记住‘歌颂人民成就伟大’一个原则,则不易伤手”的道理。
对照沈从文谈诗的书信来看,《大湖景诗草》组诗是沈从文主动趋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尝试,甚至还期待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对诗歌抱有公开发表的热望。诗中“充溢着强烈的入世情怀”,“表现出对政治话语的主动认同”(15)。然而,在解放前沈从文就一直以自由知识分子自居,远离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海派文学兴盛之际,沈从文就对文学与政治的亲近关系进行反思,警惕文学受政治的辖制。为何到了晚年,在放弃创作“改业”多年之后,反倒会写出“五七”颂歌呢?
早在1961年间,沈从文就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体制与作家创作的关系有过深刻反思:“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16) 沈从文实际上早已悟出了自己在这个唯政治论的新时代的必然命运,幸与不幸皆由时代所致。在停笔多年后,“跛者不忘履”的写作内驱力时刻折磨着沈从文的内心,离开解放前纵横驰骋的文坛,退出文坛的中心转而默默无闻,沈从文需要有极强的心理素质才能适应其间的落差。结构主义文论告诉我们,判断一部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看它已经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要善于从作品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去感知意识形态的存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探寻作品在那些沉默之中所没有或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实际上作品就是为这些沉默而生”(17)。如此一来,将《大湖景诗草》组诗、《双溪咏》、《新认识》、《闻新人大开会》等诗的内容与沈从文的书信对照来读,不难发掘诗歌背后隐含的深层意蕴。沈从文与张兆和探讨写诗感受时,对自己诗作的前程抱以乐观态度:“至于像《红卫星上天》,可能有偶然机会,有作曲的什么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么发生了兴趣,转成为一首带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可能性也许倒多些。因为这内中还真像有点什么新意思、新格调、新内容,可不是什么新诗人、旧诗人能写得出的!”他甚至坚信“还会有一天在新选本中、新教材中,要提到,给以适当合理估价!”在信中,沈从文还担心诗作《读秦本纪》的文史知识影响读者的接受面。这一时期,沈从文写作的所有诗歌也仅限于在亲友间流传,公开发表不太可能,但从信中他对读者接受的担忧实则透露出对诗歌拟想阅读对象的期待。沈从文背离自己的文学观念趋向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已然呼之欲出:“我这些习作,也会有机会在较小范围内,作为一种‘学习材料’而公开,得到上面点头认可的。那么大一个国家,应对世界,也总得有几支有分量的笔!”沈从文迫切希望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重返文学场域,寻找到自己的文学坐标,因而以诗明志,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游移不定。
这些旧体诗,既有对主流意识趋同的颂歌,也有书写真实性情的拟咏怀诗,如《拟咏怀诗——七十岁生日感事》、《喜新晴》、《双溪大雪》等。要把握沈从文旧体诗创作的复杂面貌,只有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并以书信证诗词,才能更好地挖掘沈从文诗歌背后隐含的深层文化心理。
三
时过境迁,翻阅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我们不难看出中共发动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的真实目的,“‘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18)。从某种层面来讲,当年数以万计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实则是承受国家政权惩罚,被驱逐出已有的社会阶层,剥夺其在社会中已有的权利与地位。“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为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19),沈从文也不例外。因而,沈从文会在干校写出时代颂歌,并渴望能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体系中,权力不仅仅是压迫性、排他性的,还是生产性的。权力与知识相互生产,相辅相成。权力是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权力关系渗透到各种社会关系中,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团体、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个人,既受制于权力,又参与权力的运作。置身于特殊的权力场域中,沈从文也不自觉地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来。在与张兆和谈到《红卫星上天》一诗时,沈从文甚至设想过“第三次转业”,认为该诗“会有一天选到什么新诗歌教材中去代表一格”,“不仅近五十年未有这么来写新诗,以后也更不会有人这么准备充分来写诗了”,“我倒相信主席等三几人如见到,会点首认可的。因为凡是任何工作一达到一定水平,或有所突破时,总不会在重实际的现代新社会被抹煞的”。不难看出,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可,是沈从文在干校写诗时的心理内驱力。1972年返京后。沈从文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请教写作经验的信中推诿道,写诗“最好的老师是主席指示,和当前领导工作的首长,据我想,对你最有益的,作具体帮助的,大致应数浩然先生,他是既有丰富生活经验,又有写作成就,目下最值得向之学习的作家”(20)。哪怕是在给熟人的信中,他仍劝友人别把自己看作作家,并认为“希望从务实工作上求进展,找出路”,还得向浩然学习,“一切向他看齐,才会有作品,配得上社会对文学新要求,而又不至于精力白费”(21)。无论书信中这些言词是发自内心还是言不由衷,都传达出权力制造知识、规训个体的效果。
詹明信曾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2) 沈从文下放期间的书信,也可当作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寓言来解读。建国以前,沈从文秉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内战加以批判,谴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权力纷争,加之他在30年代与左翼文学间的矛盾分歧,与郭沫若等人的宿怨,都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被迫放下手中的笔。新生政权对其创作的全盘否定给他以巨大心理压力,几近摧毁他的创作信心。沈从文在建国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短文中就曾对个人创作加以检讨,并表示要“学习靠拢人民,我首先得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学会沉默归队”(23)。离开倾注全部生命热情的文学事业,割断二十几年来与文学创作的联系,不可避免地给沈从文带来无尽的苦恼与挣扎。背负着创作转向带来的心灵伤痛,沈从文选择了沉默归队,转向文物研究。沈从文一开始就远离政治的漩涡,“不主张用政治术语来剖析中国社会”,但“充分的意志自由,紧跟时代,也意味着他对时代思潮具有高度的敏感”(24)。这样一种生存策略,使得沈从文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与一同步入新时代的作家如巴金、老舍、冰心、丁玲等人相比,所受冲击最少最小。然而,沈从文虽远离政治,仍然无法全身而退,无法逃脱20世纪新旧政权更迭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厄运,在新的社会非但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还得终生背负政治迫害感,难以保全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谨小慎微地度过余生。正如沈从文在1983年回顾人生时的感慨:“因为进入大城市前后虽已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的社会变化,知识分子得到的苦难,我也总有机会,不多不少摊派到个人头上一份。……真像奇迹一般,还是依然活下来了。”(25)
沈从文这匹“无从驯服的斑马”,虽在干校期间有过短暂的主动迎合体制的努力,但如果联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来看,沈从文这种选择的合法性便不证自明。置身其中的个体无法摆脱强大的政治驱力,个体的挣扎与反抗无济于事。从这一层面来看沈从文干校期间的书信和诗歌,无疑与陈思和提出的“潜在写作”中的第三种原因相吻合:“作家的身份受到限制,或是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自由,他们的创作不一定与国家政权或者现实社会制度处于自觉的对立立场,有的只是抒发个人的情愫,有的甚至表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定程度的迎合。”(26) 沈从文诗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无疑为“潜在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注脚。也有学者依据沈从文建国前后的人格、精神的发展变化,得出“其实在写作与不写作之外,这个人才真正是他的‘潜在写作’”(27) 的结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沈从文,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挖掘沈从文干校期间书信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梳理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对历史进行的沉痛反思,当然“这种反思对于反思主体来说,既是有限度的,也是残酷的,同时也将是长期的”(28)。透过沈从文的书信,来阅读他在干校期间创作的旧体诗,可以清晰感受到书信与创作间形成的巨大反差与补充,从而为干校文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研究。沈从文在书信中提供的乡土经验,为研究者解读“乡下人”的精神内蕴提供了对照,同时有助于我们把握沈从文的自我精神与独立的审美意识在特定历史境遇中遭遇的挑战与尴尬,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更为“丰富而痛苦”的沈从文。跳出个体生存经验的拘囿,将沈从文纳入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沈从文在干校的生存与应对策略,无疑更具历史典型性。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经验与苦难命运,正如沈从文曾预言过的:“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
注释:
①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② 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③ 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④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文存》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
⑤ 沈从文:《曲折十七年》,《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
⑥ 沈从文:《复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⑦ 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⑧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481页。
⑨ 沈从文:《解放一年——学习一年》,《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⑩ 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沈从文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11)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0页。
(12) 沈从文:《有关诗作的三封信》,《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13) 沈从文:《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14) 沈从文:《致革命历史博物馆领导》,《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5) 李遇春:《沈从文晚年旧体诗创作中的精神矛盾》,《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16)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17) 彼埃尔·马舍雷:《文学分析:结构的坟墓》,《现代美学新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18) 郑谦:《“五七干校”始末》,《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页。
(19)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5页。
(20) 沈从文:《复钱世明》,《沈从文全集》第2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21) 沈从文:《复两昆仲》,《沈从文全集》第2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
(22)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京媛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23) 沈从文:《我的感想——我的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
(24)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62、287页。
(25) 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26) 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27) 刘志荣:《1949年后沈从文书信的文学与精神意义》,《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
(28) 刘保昌:《干校文学论——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标签:沈从文论文; 张兆和论文; 沈从文全集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乡土论文; 社会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