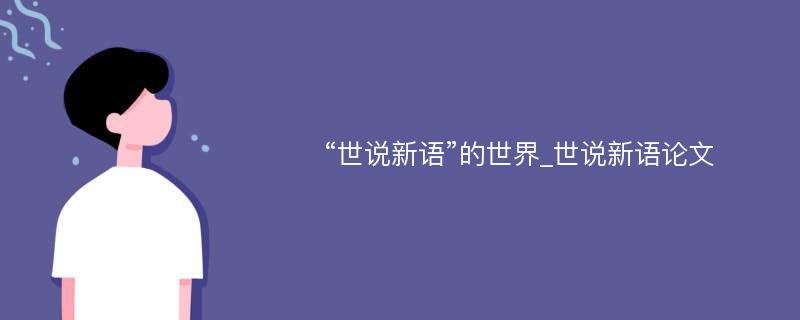
《世说新语》的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说新语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 美国杰出的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Mather)先生竭20年之心力,将我国古典名著《世说新语》(简称《世说》)译成流畅的现代英语,* 驰誉学林,令人景仰。 在正文之前, 马氏以一篇长达14页的文章(《Introduetion:The world of the shih— shuo hsin—yu》)对《世说》这部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地阐释,目光犀利,洞烛幽微,多发前人所未发;而其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雄浑、阔大的学术境界和绚极归淡的撰述风格,更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科学的教益。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马氏原文自注,既详且广,为行文方便,予以适当删削,不能译出者,皆存其旧;译者根据需要随文施注,则一律以 * 标出。此外, 依照汉语之习惯,译者对原文的某些自然段进行了合并。
本文在翻译过程中,曾求教于加拿大友人steve·penner 先生和同事张政文副教授,而美国明州大学曲路博士,不远万里携回了马瑞志博士惠赠给我的沉甸甸的著作原本和诚挚的翻译授权书。对三位朋友的帮助和马瑞志博士的信任,在此致以深深地谢沈!
如果说由故事、对话和简短的人物刻划所构成的《世说》描绘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探视这个世界的真面。它反映的是特殊时空(中国2—4世纪)中的世界的全豹,还是狭小的一斑?最终,它是对那个世界的真实传写,还是在特殊观点支配下的高度主观的抗辩轨迹?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不易回答,因为在众多事实中不能有第二种选择。但在研究伊始;试图面对它们,仍然有益无害。
我们首先着眼于真实性问题。1955年,香港的一位学者著文指出晋朝历史的真实情况大都被《晋书》这部为朝廷服务的谬误百出的官史掩盖了。因为它大约是在晋朝覆亡300年以后草率成书的, 许多史实遭到了唐代历史学家的曲意窜改,而《世说》之成书仅仅在晋朝亡后10年。通过比较他观察到,《世说》对晋史的叙述保存了当时言论和事件的本来面目〔1〕。这一观察非常重要,尽管其结论很难被证明。 实际上只要随便读读《晋书》的传记,就会发现著史者对《世说》表现了极大的信任——将它作为取材的渊薮,就连些许重要的改易也可以从中找到蛛丝马迹。这一点毫无疑问。
《世说》全书出现的人物约计626人,显然, 他们都可以在历史以及其他方面得到证实。此外,就书中部分事件和议论而言,适度的文学性修饰和戏剧性夸张,也不能成为怀疑其真实性的充分理由。只有少数人提出了一些确实存在的问题,包括时代错误、已知事件的自相矛盾、十足的超自然物的渗透或者表面上的龃龉不合。有案可稽的事实, 如2门59条关于火星(荧惑)在公元372年2月17日逆行进入“天空的圈地”太微(室女座和狮子座两个星座部分)的记录,根据对4 世纪行星运动准确的现代推测加以检验,可以发现这一记载是准确无误的。〔2〕与此类似,东晋大将军桓温(312—373)曾发动若干次军事远征:在346 —347年间对四川成汉道教伪政府(2门58条),在354 年对陕西原始西藏人的前秦政府(2门55条),在356年对河南、河北原始东胡人的前燕政府(4门96条)。当我们由《世说》获悉这一切时, 根本没有必要寻找任何对事实的歪曲,因为它们在别处也得到了圆满的文献说明。或许《世说》对实际发生的事件或者实际发表的言论报告得并不那么精确,但是同样的罪名可以被司马迁(公元前145—90)《史记》的叙事和对话及其以后大多数中国人的编史工作所摧毁:在标准的正史中,可以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地方色彩和小说化倾向。
描述历史似乎还不是《世说》作者意图之所在。确实,《隋书》(卷34)和两《唐书》(《旧唐书》卷47、《新唐书》卷60)没有将它列入史部,相反却置于子部和小说部。在此二部中,《世说》隐藏于农书和兵书之间,与《燕丹子》之类的小说化的传记相伴。《燕丹子》详细记述了公元前227年,荆苛企图刺杀秦始皇的事迹。 《战国策》(卷31)和《史记》(卷86)对此也有记载。《隋书》和两《唐书》在同一标题之下也列举了谏者规劝君王的原始资料集,如《辩林》或《座右方》;还有关于宫廷弄臣的笑话书,如邯郸淳的《笑林》(3世纪); 以及一般性较为生动的谈话录,如《要用语对》。其中与《世说》最为接近的一部著作是裴启的《语林》,它首先问世于公元362年。 倘若我们可以相信《世说》26门24条的故事,那么它在昙花一现之后,便由于涉及生人事迹的虚实问题而迅速地销声匿迹了。这些在同一定例之下的异质著作的联合表明了《世说》本身在其时代被关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世说》是谈助,而提供生动有趣的读物也确是其目的之一。这正是它与后来小说的最密切的联系之所在。如早期小说中的《三国演义》,实际上包括了一些与《世说》相同而经过了适当润饰和扩充的轶事,特别是关于魏朝的奠基者曹操的故事。当曹操个人出现于陈寿《魏志》(《三国志》卷1)本传中时, 其形象是苍白的:他被作为一位敏于行动的男子、一个军事天才来加以描写。他在青年时代“机警,有权术”,* 在性格上的最大缺陷是喜爱“任侠放荡”* *。 但在他死后一两代人中却产生了关于他作为冷血恶棍的传奇:仅仅为警示可能出现的行刺者而处死犯错误的奴仆,或者谋杀给他盖被的男子,并且对自己家庭的全体成员简单地遮掩其残忍所造成的失误。《世说》有19个故事是关于曹操的,其中多数已表现出传奇的影响。而这些故事的渊源无疑是相同的,均见于裴松之《魏志注》的引文,如无名氏所作《曹瞒传》、王沈《魏书》(晚于3世纪)、郭颁《世语》(约公元300年)、孙盛《异同杂语》(公元4世纪中叶)。 裴氏之书的发表恰在《世说》问世的前一年,即公元429年。关于王导(276—339)及其堂兄王敦(226—324)、谢安(320—385)和顾恺之(约345—406), 《世说》也反映了围绕这些名字而逐渐发展的种种传说。将这部故事集及其众多的源头与孕育后来“小说”的说书传统联系起来,我的意思并非暗示在早期小说和后来的同名作之间存在着一个直接的血统。但在这一过程中,有多方面影响的介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只想强调其中的娱乐因素,无论是优美的故事传闻,还是特殊的妙言隽语,或者对怪癖和奇嗜的记录,在《世说》作者之意图中,这些决非最次要的因素。
如果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比严肃的历史更为小说化,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它试图描绘出公元2至4世纪中国人的整个世界吗?只要查看一下书中各门的标题,任何人都会首先获得某种万能的百科全书或者类书似的印象。根据公民的道德价值(1至8门)和教养有素的知识分子的成就(9至17门),全书故事的第1部分被分门别类;以下各门专用于隐士(18)和妇女(19),还有关于技术和艺术的迷人两门(20、21)。 从22到最后一门(36),是一份任何人在任何文学中都能发现的人类弱点的详尽目录。由于某种未明的原因,《世说》的这些故事还远远不足以提供那一时代的全图。书中偶尔涉及奴隶和农奴,但他们是用以点缀大人物家庭和庄园的附属品。有一两次事变涉及皇宫卫士和出征的士兵,但他们也只是为了说明其发号施令的长官的某些品性而被提及的。这些长官并非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而是绅士。书中撩人的一笔是提到了商人们沿着南部都城建康(今南京)附近的水路从事贸易活动、但相对于贵族之林形形色色人物的恶作剧而言,他们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甚至《世说》有关技、艺的两门,也淹没于贵族的烟波之中,而与手艺人阶层无缘。这些故事构成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异常狭窄的世界:皇帝、太子、大臣、官僚、将军、文质彬彬的隐士和温文尔雅的僧侣。尽管他们生活在极其优雅而敏感的象牙之塔中,其中大部分人还是经常涉足充斥着血流漂杵的战争和尔虞我诈的派系斗争的尘世。这是一个黑云漠漠的世界,与才智和睿识的光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世说》描写的生活和事件横跨了3个世纪(约公元120—420), 在此阶段次第发生了一系列巨变:(1)184年,一场由濒于绝境的农民发动的武装起义在东部各省突然暴发,汉末的内战持续了40年。(2)249年,通过军事政变司马氏夺取了建立不久的曹魏政权, 随之对那些眷怀魏朝的反动分子进行血腥的清洗,最终在265年建立晋朝。 (3)300年,晋朝的一位王子试图取代低能儿晋惠帝, 在其竞争者之间展开了自相残杀的战争,称为“八王之乱”。战争持续了6年, 使国家彻底枯竭,并为生活在北部的夷狄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在309年和316年先后摧毁洛阳(河南)和长安(陕西)两座京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续连的少数民族政权。(4)在307—312年间, 在乘间奔逃的世家大族举家迁徙之后流亡政权东晋建立起来了,其首都是建康。该政权仅仅通过自然屏障之保护以抵御北方的侵袭,维持其风雨飘摇的局势,直到420年。(5)383年,控制着中国西北部的北方统治者之一苻坚(337—384),企图征服东晋,但由于后勤问题而失败。(6)在401至403年, 长江三角洲饥寒交迫的下层农民在道教领袖孙恩(卒于402 年)及其继任者卢循(卒于411年)的领导下,又发动了起义。随后的一年, 野心勃勃的将军桓玄(369—404)篡夺王权3个月,另一位将军刘裕(356 —422)将他翦灭,并在420年建立了宋朝。
由于世事的白云苍狗依傍于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一度出现的宗派氏族的紧张关系以及派别斗争的偏见上,不仅追询《世说》的故事是否真实、是否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全部世界合乎情理,而且探问这些故事是否被《世说》客观地讲述出来、是否可以粗陈梗概地反映一些特殊派别的倾向性也极为中肯。当然,那一历史阶段诸多派系的钩心斗角被这部书掩盖了。正如反暴动力量的指挥官所描述的那样,后汉大多数黄巾义军领袖人物来自没落的贵族之家,他们与汉政府势不两立。与宦官和骤贵的皇亲国戚对立的是朝廷的文人学士。后来有魏的忠臣——曹氏的忠实支持者,与建立晋朝的司马氏的反动领导相对立。
西晋时期,原来忠于杨氏的派系的对立面是支持新联合体的贾氏,他们在上文提到的“八王之乱”中以付出血的代价而告终。同时,冷酷的世仇在以大元帅王衍(256—311)为领袖的“放诞派”和以尚书左仆射裴顾(267—300)为代言人的礼法之士间持续着,偶尔爆发着枯燥无味的唇舌之争。在结束向长江三角洲的流亡和317年东晋建立以后, 接踵而至的氐族霸权统治了建康朝廷,如瑯邪王氏、庚氏、 何氏、桓氏、谢氏等等,他们随着420年刘宋的腾起而先后退出历史舞台。 东晋初年,朝廷主要谋划北方流亡者的事务,在此之下,是原长江地区的开拓者们的强烈区域性世仇:领袖群族的吴楚土著人士极端憎恶307 年以后由北方流人的入侵而突然形成的弥覆一切的阴影。
无论贯穿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宗派关系中的哪一种复杂因素,如政治、社会、经济,乃至宗教等等,它们似乎都被3 世纪压缩成了两个相悖的基本主题。为论述方便起见,我将指出时人所熟知的两个方面:崇尚自然与遵奉名教。在前后相续的每个历史阶段,关于这两方面问题的争端都小有不同,但自然派倾向于道家哲学,其道德不拘一格,在政治方面没有约束而崇尚儒家传统的遵奉者和支持者设防于繁多纷乱的教条,在道德上墨守成规,对公众生活承担固定的义务。尽管初次阅读这些故事,这一点并不明显,但无论如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物比其他人更值得赞美,而建议他们坚持一成不变的寻常品格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例如,他们仿佛都是清淡雅论与美文佳句的耽爱者,宁愿倾心于回归的和平、静谧、退隐、自由和潇洒不羁的美德,鄙薄寻衅滋事的品性。这种品性通常被当作军人的英勇无畏、雄浑刚毅、激越鼓舞和对刻板的道德礼仪规范的遵奉。总之,前一组人物乃自然的信徒和追随者,而后一组人物则崇奉礼教。无论谁将这些故事置于一处,似乎都会为前者而生发一种偏爱,因为他们是居于后者之上的创造者。有几个例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观点。谢安是出现于全书中的强势人物,描写他的故事有100 多个。他在清淡方面的杰出才能,甚至连他的敌人都承认。在以不惑之年最终应允朝廷对其才能的渴求之前,他一直保持着隐士的风姿,优游于浙江的山山水水。在他掌握朝廷大权的升迁过程中,他面临着许多重大的危机。他总是保持绝对的镇定——一种《世说》称为“雅量”的品格。对此,《世说》以一门的篇幅(6)提供了操演范例。“雅量”包括对面部、口头或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表现出的忧虑、恐惧、兴奋或欢乐的最轻微暗示的隐藏。“雅量”不同一般,令人叫绝,酷似“沉着冷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只有在已经消失的古希腊世界——处于岌岌可危的灭顶之灾威胁之下的另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生活中才具有。谢安的故事,无论是与诸人泛舟突遭暴风的袭击,还是在鸿门宴上面对其不共戴天的仇敌设下的伏兵和难以避免的死亡,或者收到东晋军队大胜于淝水的捷报,在每一种形势中,他都能吟诗不绝或者弈棋不辍,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世说》举出的寻衅好斗的男子大都没有高名美誉可言。桓温(312—373)是以十全十美的陪衬角色为谢安服务的军事独裁者和近于篡位者,可以和他并驾齐驱的是粗野无礼的冒险家王敦。这个男人的“豪爽”足以支撑装着“数十”女奴和情妇的闺房。正值钟鸣鼎食而喜欢炫耀的石崇(249—300)在家中大宴宾客之际,仅仅为试验这位主人,他便故意拒饮。因为此时此地客人若有一次不喝光杯中的酒,石崇就要斩杀一名侍酒的美女。在3 个女孩接连掉了脑袋之后,王敦仍然象打火石一般漠然拒饮,而不顾其堂弟即后来成为东晋司法官的王导的痛苦请求。王敦的冷酷无情映衬出王导的敏锐和人道,正象后来一代人中桓温之暴怒使谢安的沉静更加醒目一样。
因之,尽管对《世说》的作者不能确切地加以证实,他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无论是谁,他都是自然的支持者和遵奉的反对者。传统认为《世说》原作者为刘义庆(403—444),他是宋朝军事创建者刘裕的侄子,极为因循守旧、平淡无奇。我们对此又如何解释?站在强大的军事行动和严格的礼仪尊奉的批评家的立场上的男子是不会崇尚自然的。所以,1924年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3〕中第一次提出了刘义庆仅仅发起了《世说》的编撰工作,而实际执笔者是他的幕府群僚的说法。此说值得注意,特别是根据最近川胜义雄的一篇题为《〈世说新语〉之编纂》的文章〔4〕。 川胜令人信服地讨论了我已经暗示过的有关这部著作的几种流行观点,特别是关于刘义庆的同时代人及其幕下的同龄人。《世说》2门108条描写了作为反对朝廷的叛逆者在433 年被处死的谢灵运(385—433),完全出于对他的同情。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世说》的实际编撰者是谢灵运的知近朋友和刘义庆的幕府成员何长瑜(385—433),他曾经表述过与《世说》相同的观点。当然,此说仅仅是假设。另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皇帝会允许谢灵运的名字附属于一部潜在地起破坏作用的著作。但由于其他的旁证,《世说》的注释者刘峻(462—521)无论何时偶然发现《世说》记载的道德的颓败和事实的歪曲这类臭名远扬的特殊事例,他的临川王为《世说》作者的信念都受到震动,而假设刘义庆非实际作者便具有了多方面的意义。崇向自然者和遵奉名教者具有不同的倾向,既然书中可以粗略分开的人物提供了这样一块方便的试金石,那就让我们对分布于各个文化细节上的这两种思想意识继续进行考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历史阶段一切文学的、知识的、宗教的趋向都可以从这双重的观点中得到细致的审视。田园诗人和小品文作家赞美退隐和宁静的韬晦之德,并为后一阶段田园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从同时期保守作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以较强的自发性偏爱五言诗,远胜于对嗜古成癖的诗人潘岳(247—300)的欣赏。《世说》4门71 条提到了他的《家风诗》,这首诗在沉重的四言音步中充满了儒学的训戒。
3世纪中叶文学创作方面自然主义的伟大代表是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 《世说》中的许多事实材料充分证明钟会(225—262)这个劲敌是最终使嵇康遇害的原因所在。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写道:
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工作转笃。……吾项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实。〔5〕。
在临刑前身陷囹圄时创作的《幽愤诗》中,嵇康仍然强调同一主题,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以寻觅其心仪的哲学家: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6〕。
阮籍是嵇康的朋友和同龄人,其为人处事较少引起别人的烦恼和厌恶。更善于适应敌意四伏的环境,但他托怀于自然的情愫并不贫乏。在以歌颂为主调并带讽刺色彩的《大人先生传》中,他毫不迟疑地对礼法之士品头评足、较短量长,说他们“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犹如裤中行将就火的虱子,沉迷于茧一般的狭小天地中,而对迫切的毁灭一无所知。〔7〕在《咏怀诗》的一篇作品中, 我们可以发现他作了与此类似的比较:
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8〕
在262年嵇康以公德堕落者的罪名被司马氏处死之后, 崇尚自然的人们不得不寻求表达其理想的更为巧妙的方式。其中之一是常与嵇、阮往还的向秀(公元221—300),他公然步入礼法之士的行列,接受了晋朝官职,设法与当权者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性的妥协。他在外表上遵从他们有关道德和礼仪的戒律,同时在心灵的深处依然保存着自然和自由。如果说郭象(卒于321年)的《庄子注》作为某些方面的赓续,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向秀遗失的同名著作之原本,那么《庄子·太宗师》* “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的语言表述则概括了这自相矛盾的两方面的神秘的珠联璧合。青年作家庾子嵩(262—311)以更彻底的时空逃避解决这一问题,跃入了思想的世界。其《意赋》云:
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摇玄旷之城兮,深漠畅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9〕。
在307—312年向东晋的流亡结束之后,这种思想或精神上的自然主义与表面上的遵奉的妥协演变为新自然主义的右翼,而伫立于礼法之士和某些激进派之间。为停于政治的门外,他们假装纯粹的逍遥自在以掩饰其他动机。孙绰(活动于4世纪中叶)和袁宏(328—376)是这个骑墙派的代言人,他们涉足于政治生活很深。孙绰曾经议论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10〕。因此,读他的《游天台山赋》就不会使人感到吃惊:作者叙写了纯净而神秘的攀援及其与大自然交融无间,同时还不偏废其世俗的政务。结尾的一段,他显然禀承了庚氏《意赋》的衣钵:
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急即有而得玄。……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11〕
孙绰之玄想对大乘佛学思想的调和是前所未有的,如“空”,正意味着“自然本身或独立存在的缺席”,尽管它仍然或多或少地被中国人理解为道家思想范畴“无”、“虚无”、“非现实”的对应词。
袁宏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盘桓于合乎体统的礼仪之士的轸域,但在《后汉纪》中,他试图展一种半自然主义者的历史理论:“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12〕换言之,足以反映历史事件之本质的人类关系基本上是由宇宙之自然所决定的,而名教毕竟建立于自然的基础之上,说教者在此二者之间制造紧张不过是人为的堕落而已。袁宏以参军的身份在桓温府中服务了若干年,他不过是一名下级属官,这一事实决定了桓温对他的基本态度。桓温乃雄壮刚毅的赳赳武夫,富于爱国的热忱和道德的说教。对如此人物,袁宏显然是无用的。在一次北方战役期间,桓温登上平乘楼,眺瞩中原满目疮痍的景象,叹息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西晋的放达派)不得不任其责?”他马上遭到袁宏带有抗议性质的反驳:“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桓温气得满脸通红,当即十分阴险地暗示袁宏已经老迈无用了。〔13〕保存于《世说》4门《文学》97 条正文和注释中的两个有关袁宏已经亡佚了的洋洋大文《东征赋》的故事,乃是东晋创建的后期关于颓败局面结束的婉词,尽管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我们仍然认为事关带有浓厚的反自然主义者思想情绪的军事人物桓温之父桓彝(276—328)和陶侃(259—334),这是意味深长的。第1 个故事说袁宏的赋涉及了与事件有关的所有人物,而唯独忽略了陶侃。既然陶侃在东晋的创建过程中非常引人注目,那么这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因此,大将军粗野无礼的儿子陶范(约376年左右在世)怒不可遏,而袁宏仅仅凭着急中生智临时凑成6句歌颂陶侃,才从其肋迫的困境中勉强脱险。在正文之下,刘峻引用檀道鸾(5 世纪)《续晋阳秋》记述了与此相似的故事:当桓温父亲之名被遗漏时,另外6句被从袁宏多产的大脑中拖了出来。 鉴于桓温已经表述过的“王夷甫诸人”云云的意见和陶侃发现部下赌博时的严厉斥责,在他们身上便难以发生偶然性的遗漏。但至少他们会“说话谩不经心而漏嘴致误”,* 如陶侃曾经阵阵有词地对他赌博的僚属发表如下演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仰望,自谓宏达邪?”〔14〕陶侃相信老子发明了掷骰子,后来西方的野蛮人又加以研习,这种观点自然是荒谬绝伦的。**虽然孙袁站在中间立场,其他一些人仍然采取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是特定的贵族隐士,生活在浙江山中设施完备的栖遁之所,描绘未遭破坏的大自然的美丽,希心高远,脱略俗务,小觑尘寰。这一切构成了诗人许询(约卒于公元358年)歌咏的内容,当时未来的简文帝(公元371—372 年在位)称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不幸的是,他的作品几乎荡然无存了,只有江淹(444—505)的一篇拟作见于《文选》卷31〔15〕。在《世说》中,许询和孙绰的竞争主要在于对其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的解释,9 门61条云:“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这一点被刘注所引《文章志》解释成许、孙“俱有负俗之谈”,而许“卒不降志”。当僧人支遁(314—366)问孙绰与许询相比如何评价自己时,他答道:“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即处于学生的位置〕。”(9门54 条)这一评论基本上可以视为孙绰对自己在文学方面超越许询之优势的自我设想,但根据早已提及的孙绰的“秽行”,我认为他是在暗示这样的意思:“许询或许是‘崇高’而‘旷远’的,既然他从不受世俗事物的浸染,怎么还会有资格创作值得吟唱的诗歌?”事实上,虽然这两位代表人物都反对纯粹的礼仪之士,但其观点截然不同。知识分子的风气在这些思想观念方面的不同发展通常为其共有的玄学囊括无遗,其中的若干因素已经开始了道家哲学即“新道学”的复苏,从而使陈腐的汉代儒学思想暗然失色〔16〕。但另一些人曾经指出,任何玄学对道家学说的直觉都不重视与官僚阶层相接近的联合和提供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取代抽象的古典诠释新文本学派的努力〔17〕。玄学显示其自身的主要形式是由连续各阶段的基本需要决定的。在汉末及魏朝建立以后,为行政机关发现合适的人才似乎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因此,“清议”活动为政府机关造就了任职者或候选人,他们在与本职相称的能力方面的特点被简洁地勾勒出来。在这方面,刘劭(约公元190—265)的《人物志》〔18〕乃早期的例证之一,钟会的《四本论》成为3、4世纪这方面最优秀的著述,而《世说》7至9门,特别是《品藻》一门则收录了更多的应用实例。这被一些人视为清谈艺术的起源〔19〕,但是这种艺术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必定出现于原有实践的全部过程中,并研讨在《品藻》里无影无踪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无和有的关系〔20〕。何偃(公元190—249?)以其《道》、《德》二论奠定了这些讨论的基调,这两篇文章残存于引文之中。不久, 同时代的青年人王弼(226—249)以其关于《周易》和《老子》的两部卓越的注解文本承袭何氏之说,并流传至今。王弼对有和无的关系作了如下解释: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老子注》1)
虽然这可能与汉代文明倾颓之后出现的历史事件有相当密切而合理的联系,但看来似乎魏朝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通过制造“虚无”或者到当时为止的“未形”和“无名”——所有事件的哲学依据,来为对汉代陈腐的正统观念之刻板形式和符合一般性准则之名目进行大规模没有偏见的改革打基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王弼和其他人充当了自然主义或者自然的代言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老子注》5、25 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关于难以想象的无序状态的哲学思想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反应——可能造成摄政者曹爽(?—249)这一派的跨台。何偃和王弼皆属于这一派,他们在249年司马懿发动的军事政变中全都灰飞烟灭了。 此后清谈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王、何玄学的新颖与独创,正始时期被宫崎市定称为清谈的“黄金时代”〔21〕;晋朝正式建立之前过渡期内的15年,即从250到265,被他称为清谈的“白银时代”。潜在的自然与遵奉之争到彼时才明确无疑。大权在握的司马氏集团的支持者和具有置身政务之外倾向的多数忠于魏朝的分子之间,泾渭分明,一望即知。后来嵇康、阮籍和其他人组成一个著名的群体“竹林七贤”,他们奉行崇高的自然主义和潇洒不羁的精神,〔22〕并付诸个人的行动。与此同时,钟会及其勾结者忙于在《四本论》中阐述才性的同、异、合、离。他们以某些方式说明与一个在政治事务中通过发挥其工作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最为相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即如何名副其实〔23〕。根据《世说》的动人故事,钟会非常想面对面地和嵇康研讨这篇论文,但他在最后的时刻不知所措,直待躲到嵇康门外的安全距离内,才敢把文章从怀里掏出来,转身猛掷过去(4门5条)。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在262年嵇康死后, 哲学界的气候一片萧条、寂寥。在公开停止反对为政治服务的同时,大庭广众之下的辩论也雨散云收了,但崭新的“旷达”人生观得以流行,特别是在洛阳朝廷的那些雍容华丽的贵族中间,他们身居闲职,能够提出并接受不偏不倚的观点。这些人当中的一个群体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八达”。庚子嵩系其中成员之一,他的《意赋》已经提到,赋中“纵驱于寥廓之庭兮”的语句表达了这一群体的哲学和道德态度。根据那时流行的传闻,他们酷爱夜以继日的纵酒饮宴,甚至崇尚裸体主义,凡此均是反抗礼仪常规桎梏的象征〔24〕。当然,晋朝官方的思想意识总要比这严肃一些。 在311年洛阳沦陷之前,或许裴(267—300)是多数搢绅王公的强有力的代言人。为了以明确的行动面对使人麻痹并且有构成“八达”之类士人放荡理论基础意味的虚无主义流潮,他的《崇有论》提出了难以抗驳的言词申辨。《世说》4门12条刘注所引4世纪早期之作《晋诸公赞》阐明了裴頠写作《崇有论》的社会背景:“后进庚然之徒,皆希慕简旷。顾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贵无》二论以析之。”这两个题目被讲得如此深奥,以致当时的学者们难以欣赏其意蕴。即使它们很麻烦,但仍然被我们所理解,哪怕在今天我们对其某些方面的把握还差得远。但小品文的一般要旨是清晰可见的。裴顾声称“虚无”的狂热崇拜者直接导致了对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不负责:“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25〕裴氏在哲学上的地位与其同时代“新道学”的折衷者郭象极为相近,郭氏的《庄子注》已经提到。裴氏云:“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26〕这段话几乎将郭象在《庄子》第22篇注释中对于“无”的解说生吞活削:
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而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庄子》6.22)
通过对现实与非现实,或者有与无的讨论,上述对比描绘出了与之相应的遵奉和自然这两种生活方式,它们持续到4 世纪偏居一隅的建康王朝,而其唯一的意义深远的方向却来自一个出人意料的源泉——佛教。当然,自从佛教在大约耶酥时代从印度和中亚输入以来,它就生存于中国的土壤之上,但在学识渊懿的阶层中,似乎只有少数人吸收其思想。佛家学说在中国差异很大的社会和哲学氛围中得到了发展,直至4 世纪20年代西晋灭亡。这一接受过程顺序变化的前因后果在其他浅显易懂的著作中已有详细的讨论〔27〕,我们无须逗留于此。佛教在《世说》世界中所扮演的容易理解的角色,对于认识4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必要的,它使其中某些带着玄学的陈词滥调的重要人物在面对老问题时,感觉自己有了新发现。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现实与非现实,或者有与无,而是轮回与涅槃;不是荒谬与真理,而是幻想与拓展;不是世俗事物和凌于其上的超然存在,而是凡人的生活与僧侣或者浸润了僧侣思想意识的虔诚的居士。他们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发现了人生的目标和消除苦难的方法——一个被中国的哲人们简简单单掩盖了的问题——一种同情全人类的全新意旨。毫无疑问,在中国佛教“六家”的历史中,这是以全新的传译阐明“自性空”的大乘学说阶段,《般若波罗密经》在主要方面仍然被理解为“新道学”的非现实概念〔28〕。在中国皈依宗教的人们中。信仰调和论者之本能总是占上风的。面对显而易见的矛盾,在鸠摩罗什(卒于409 年)以其通俗易懂的解译揭示了佛学思想的奇异特征之后,他们继续发现了儒、道二家思想的协调一致,但是佛学新术语和新见识的渗透,至少使旧有的清谈艺术延长了两个世纪的生命。
支遁(314—366)是东晋京都士人中的一位崇尚谈辨的人物,在京城以及东南会稽诸佛寺的公开演讲和辨难中,他也颇受欢迎。他用佛学的思想方法对《庄子·逍遥游》进行新的解释,摆脱了自我的限域,并且超出了自我满足的荒唐可笑的外表——人的所谓“分”。* 他赞同郭象的诠铎,他的创造在当时引起了一场轰动,据《世说》载,“后遂用支理”。〔29〕人们相信支遁首先使用了理,即:“自然之理”;而在绝对的意义上,“理”或“真理”类似于佛学的“真如”观念。而在以后的哲学讨论中,总是闪现这一学说新意的折光〔30〕。支遁试图远离政治,摆脱思想的紧张,使相对意义上的遵奉与自然的提倡者井水不犯河水。然而,世俗的追随者却将他视为二者得兼的代表。郗超(336 —377)乃大军阀桓温手下的一个颇有权势的奴才,他对支遁是虔诚的, 甚至还为佛教的门外汉们写了一本带有指南性质的书《奉法要》。这本书充溢着强列的儒学音调〔31〕。我们已经提到孙绰这位内在的自然与外在的遵奉相妥协的诗人,他也是支公的一个忠实信徒。甚至连许询,尽管其反遵奉的外表可能是一种伪饰,后来至少一个场合中尚辩胜于重理〔32〕,他也冒称支公的追随者。这些世俗之徒的清谈很少绕过佛学的主题,诸如三乘〔33〕、般若波罗密及《维摩经》,或者六通〔34〕和三明〔35〕。
《世说》中的道教角色不象佛门释子那样引人注目,因为他们似乎只是被当作某些主角失载的私生活部分来加以描写。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即这一宗教并不仅仅是无知的农民的运动。对此,《世说》提供了圆满的扫描。某些显赫的世家大族,如书法家王羲之(约309—365)和郗超之父郗愔(313—384),其家庭成员皆是“世代”的天师道信徒。这意味着这些人物可能支持并参与这一教派的周期性厨会。在垂危和弥留之际,他们将要招请道教医生和忏悔者,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344—388)就这样做了。他临终时忏悔其终生的遗恨是和他第一个妻子郗道茂离婚〔36〕。没有什么可以显示信奉天师道与否以何种方式影响一个人对于流行的思想倾向的态度。书法家王羲之的天性是无拘无束的,却被不可移易地交托于官场的冗政繁务之中。他还曾经指责年轻的谢安试图做一个遁世者以逃避对于国家和苍生应尽的责任。而威严苛厉的将军陶侃的后人陶潜(卒于427年)也以天师道徒的身份进行创作, 成为整个时代自然与脱俗的最高典范。
行文至此,让我们告别望尽天涯的深远企盼,将炫人眼目的片玉段瑶组合在一起,构成《世说》世界的七宝楼台,并将目光转向对作品自身的审视。
范子烨译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
* 1976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部出版,英文书名为《A New Accountof Tales of the world》.
*、* * 《三国志》卷1《武帝操传》。
* 原文无此,译者为补足语意而增加。
* 原文用“Freudian slip”表示这个意思。
** 这三句话中的前二句原见于“非先王”一句后的括号中,第三句为译者所加。这样处理,是为了使文意显豁、上下连贯。
* 《世说·文学》32:“《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又该条引向、郭《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鷃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期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
注释:
〔1〕 V·T·yang《关于〈世说新语〉》,《东方研究杂志》。 2卷2期(1955)。
〔2〕〔32〕〔33〕〔34〕〔35〕 分别见《世说》2门59条,4 门38、37、45、54条。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1958,44页。
〔4〕 《东方学报》,41册(1970),页217—234。
〔5〕、〔6〕 分别见鲁迅编《嵇康集》,卷2,卷1,北京,1956。
〔7〕、〔9〕、〔13〕、〔25〕、〔26〕分别见《晋书》卷49、 50、98、35。
〔8〕 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卷1,台北,页217。
〔10〕、〔14〕 分别见《世说》4门91条注引《晋中兴书》、3门16条注引《晋阳秋》。
〔11〕 《文选》卷11。
〔15〕 J·D·Frodsham译,《中国山水田园诗的起源》,《亚渊专业》,8卷1期(1960),页81。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2册,页168,1953。
〔17〕 例见 Erik zurcher 《佛教对中国的征服》(以下简称《征服》—译者),1册,页87,莱顿,1959。
〔18〕 J·K·施赖奥克译《人物志》,纽黑文,1937(美国《东方丛书》卷2)。
〔19〕、〔21〕 例见宫崎市定《请谈》,《史林》卷引,页1 —17。
〔20〕 无和有之含义依其是否构成对立关系而变化,在《庄子》中通常如此;或者随着无作为有的基础的派生关系而变化,在《老子》中通常如此。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使用“Something ”(有和“nothing”(无),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使用“Actulity ”(现实)和“Nonaltulity”(非现实)。我的学生Un—chol shin 先生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澄清了这一差异,对他的帮助我表示感谢。
〔22〕 见《释私论》、《嵇康集》卷6
〔23〕 见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3册,页59,北京,1957, 2版。
〔24〕 例见《晋书》卷49《光逸传》。
〔27〕 例见阿瑟F·赖特《中国历史中的佛教思想》,斯坦福, 1959,特别是负21—64;《征服》,卷1,特别是负18—80; 陈观胜《中国佛学》(1964),特别是页21—53。
〔28〕 见阿瑟E·林克《道安般苦本体论的道家渊源》, 《宗教史》,9章2—3节(1969—1970),页181—215。
〔29〕 《世说》4门条。 见福光永司《支遁及其周围:东晋的老庄哲学》,《佛教史学》5卷2期(1956),页12—34,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支遁义探源》,《清华学报》,卷12,页309—314,1937。
〔30〕 见保尔·Demievulle《佛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渗透》,《世界史》3章1节,28ff.《征服》,1册,页125—126。
〔31〕 《弘明集》卷13。又见福岂永司《郗超的佛学思想,东晋佛教的一种性格》,《场人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京都, 1961,页631—646。
〔36〕 《世说》1门39条。 又见吉川忠夫《王羲之:六朝之贵族社会》,京都,1972,许世瑛《王羲之父子和天师道的关系》,《昆化》,4卷2期(1960),页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