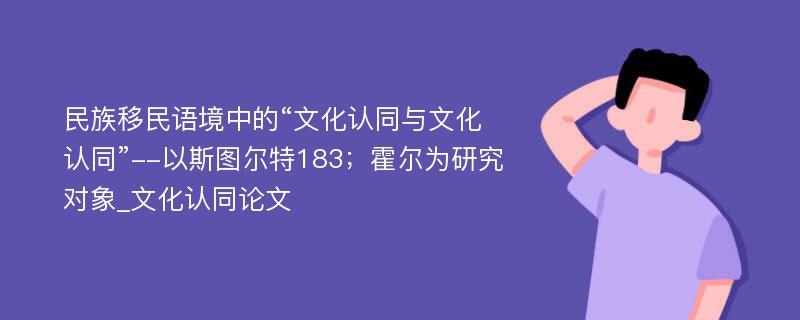
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183;霍尔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图亚特论文,霍尔论文,族裔论文,文化论文,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7)02-0083-06
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则是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对身份与认同研究中,对身份与认同的文化内涵界定还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所以本文拟从族裔散居视角去审视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问题,并以霍尔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大作《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诠释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一、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界定及内涵问题
文化研究中的“身份”与“认同”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用的是同一个词语。英文单词“identity”源于古法语identite和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受晚期拉丁语essentitas即essence本质、存在的影响。它由“同一”(same)的词根idem构成,这一词根类似于梵语idam(同一)(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2001:708)。因此,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在的同一性质或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以及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刻一个人或事物的同一性(samenesss或oneness);一个人或事物是其自身而不是其他的状态或事实。[1]在当下汉语文化研究领域中,由于受到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对identity词语的翻译、使用和界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不同的人们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等。因此在理论上对identity一词的汉语翻译和使用进行规范,对“同一”、“认同”和“身份”三个汉语概念的含义做出界定,对于避免在使用和研究中的混乱与误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阎嘉认为identity在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语境中,identity应该使用“同一性”这个词语,在某些语境中与sameness和oneness这两个概念相当。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要区分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他还认为在当下的文化研究语境中,identity有两种基本的文化内涵,其一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身份”来表示,雷蒙德·威廉斯提出过“情感结构”,爱德华·萨义德提出过“感觉与参照的体系”,以此作为追寻与确定文化身份的内在尺度和参照系。其二是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作为“认同”。从词性上看,“身份”是名词,是依据某种尺度和参照系来确定的某种共同特征与标志。“认同”具有动词性质,在多数情况下指一种寻找文化“认同”的行为。[2]从以上的阐释来看,作者认为identity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即一方面强调个体的差异,同时也强调群体的同一。当“identity”作“身份”讲以彰显差异,作“认同”讲凸显同一。
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是西方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青睐。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在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上。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问题)等问题。陶家俊[3]在《身份认同导论》一文中把身份问题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个体而言,认同问题阐释的是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而言,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4]因此在阐释文化认同时,我们认为文化认同问题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的集体身份选择,所产生的强烈思想震荡与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这种独特的认同是混合认同(hybrid Identity)。这种认同也是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批评关注的主要焦点。”[5]就确定人们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而言,在理论上有民族(nation)、族性(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亚文化和通俗文化等复杂的领域。当代文化研究对文化身份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确实也是文化研究中意图的一个指向。这如亚当·库珀所言,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6]。因此,文化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始终都无法回避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
在理解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上,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7]一文中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是“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这里“一个民族”中的“一”是所有其他表面差异的基础,是“加勒比性”、是黑人经验的真实和本质。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藏的历史”。第二种立场是,除了许多共同点以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或者说——由于历史的介入——构成了“真正的过去的我们”。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长久地谈论“一种经验,一种身份”,而不承认它的另一面——即恰恰构成了加勒比人“独特性”的那些断裂和非连续性。在第二种对文化身份理解中,文化身份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中。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强调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确定“真正的现在”。霍尔对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阐释在本质上讲是挖掘文化认同的共性与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和变化性。这也正是作者在本文中要强调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把握文化认同的变化性,才能深刻理解斯图亚特·霍尔本人及《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的文化身份问题和族裔散居问题。
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从承认差异开始,其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正如韩震[8]所说,人与他人相遇,才会思考自己是谁;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个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只有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所以说文化身份是在差异中寻找相同,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同时他也认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起始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流变性,其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稳定性。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与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相关。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人与乡士之间的纽带给削弱,人们的家庭血缘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稀释。”那么这些人在现代性的张力下,在流动的变化中他们要问:我究竟是谁?我是什么?我从何而来?到何而去?等问题。这种现代性迫使他们要不断追寻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本位基础。另外他还认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要在历史的语境中从历史的断裂或社会的断层角度去考察,认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其目的是寻找生存方式的持续性。他也认为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缓慢,风俗、习惯、道德规则和价值观继承性强;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化进程,使原来稳定的社会系统转变成为流动性社会,规则和习俗的继承性减弱。同质化的社会更多地无意识地被动接受既有文化,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迫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选择。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散居,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研究的主流。总之,不管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追寻的目的是思考生存方式的同一性,还是生存方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其哲学的本原问题是以承认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差异性、历史性和变化性为基础的。而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正是在思考文化身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混合身份认同、异体合成的不纯文化形式。[9]
二、族裔散居的界定、文化内涵问题
族裔散居(diaspora)一词源于希腊语diaspeir,涵义是“离散”或“散落”(speir:scattering),原是植物学名词,描述植物种子在一个或几个区域的散布,后来有人借用以描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种族或人种在较大范围内的迁徙移居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族裔散居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适应、冲突和融合等问题。[10]1991年《散居族裔》杂志(Diaspora)创刊,标志着人们有意识的将该理论作为一种批评工具或研究角度来研究历史和当代散居族裔问题,使散居族裔问题成为一门显学越来越受到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当前,散居族裔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散居族裔的身份界定;由族裔散居引起的跨国文化流动和全球化语境下的散居族裔问题。而现在学者关注得最多的是如何界定散居族裔和散居族裔身份的形成问题。[11]
族裔散居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族裔散居在规模、形式、历史动因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形貌、文化特征等因其脱离“本地、本族、父家”流离并散居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之中,且呈现出某些类似性的文化表征。这类问题已经成为后殖民理论重视的问题之一。[12]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界定一国中某一人种是否能被归入散居族裔的主要标准是:(1)本身或其祖先从一特定的“中心”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边缘”或外国地区移居;(2)有关于原在国的集体意识,有共同的神化;(3)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被居住国接受,感觉自己被部分地间离和隔离;(4)认为自己祖先的国度是真正的、理想中、是他们及其后代一定要回归的地方;(5)集体认为有责任保护和恢复祖国的安全和繁荣;(6)继续以各种方式与祖国发生关系,而他们的人种社区意识和团结是由这样一种关系来决定的。从他对散居族裔的界定中我们认为,他阐释的散居族裔侧重在散居族裔现象的地理特征即祖国和所在国,本身的意识,本身对祖国和自身文化源源等的意识,但是对阶级、阶层和性别等等他或多或少的忽视了。
族裔散居问题目前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跨学科的批评取向,其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对族裔散居的认定上,但是它已经显现出了有关跨文化和全球化的各种课题。在族裔散居理论的研究中,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是族裔散居理论的核心问题。正如钱超英[13]所论述的那样,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族裔散居理解为某种后现代普遍的人类文化特性或生命状态的话,那就必须同时意识到,不安于这种状态,追寻某种生命归属意义完整一致的解答,是它的另一面。族裔散居不过是对一种固有状态的离弃。而越是族裔散居的,越是陷于属性上的分裂、破碎和不确定,对于一致和统一的追求和追问越是强烈……于此,族裔散居理论成为对世界的格局差异、文化冲突、意义分裂的承担与直观。而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也就成为族裔散居问题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族裔散居语境中身份文化体和认同问题的形成与界定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寻根”,是对人类历史上种族迁徙、冲突、共生和融合的反思,是跨民族、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族裔散居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等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性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形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
这些跨越疆域、国界、民族和地区的流动、移居、放逐和迁徙,就形成了20世纪以来独特的、全球性的族裔散居现象,并且凸显了文化身份问题和文化“认同危机”。从而使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成为聚集了众多矛盾、争论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流散者们所关注的民族“集体性”及其特征等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下文化研究中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的特殊问题领域,如像那些“居住在祖国之外的人们”从最初的“中心”(祖国)分散到国外后,如何在疏离和隔膜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对“祖国”的记忆、幻想或神话,如何在异己的语境里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如何与所在国或地区的文化交融并产生出新的文化习俗,这些都是当前的身份与认同问题研究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14]
三、斯图亚特·霍尔在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现象在“两栖人”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文化主义者、传播学者、文化批评家和社会学家的斯图亚特·霍尔身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是伯明翰学派思想集大成者,著作等身。陈光兴在《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中认为霍尔是另一种学术知识分子典范,他拒绝在第一世界代表第三世界发言,拒绝成为流离海外的投机分子(diasporic opportunist),拒绝个人的名号累积,积极推动集体的知识生产。因为霍尔是加勒比海的非洲“黑人”后裔,也是战后第一代移民,他也积极投入反种族歧视运动,为少数人种开拓文化空间,建构具有批判性的文化主体性。因此阐释霍尔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理论问题必须从他本人知识形成轨迹谈起,从他的文章《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去透视霍尔在多重文化冲突和影响中特有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
霍尔出生在牙买加,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他们全家种族组合十分复杂,有非洲、东印度群岛、葡萄牙和犹太人的血统。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他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属于低中阶级、牙买加籍、乡村形态和暗色皮肤的家庭,但是他也有一个皮肤较白、源于英国和种植业起家的血缘关系。[15]因此在文化层面,从一开始,殖民地环境中本土与帝国的冲突情境,就不断地在家庭中上演。不管是属于哪一个阶级派系的人,都只认同殖民者,而不认同贫穷牙买加黑人文化,充分展现出高度的种族和肤色意识。这种文化身份意识从一开始在他家庭中就展现出来,并在文化身份认同和肤色的交织中,不断的冲突着。他也是他们家中最“黑”的,在家庭中他的身份一直都是像外来者一样,与他家人格格不入。由于他父母亲属于中产阶级家庭,他们认为他在交往朋友上“就是交友不慎,认识一些‘不好’的人,他们一直鼓励他认识一些中等阶级、而且肤色更白的朋友”。所以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在这些文化空间内不断冲突着。其实从霍尔父辈就感受到了种族、殖民地文化对他们全家的影响,甚至歧视。正如霍尔自己认为的那样,他自己的形成和认同,都是建构在一种拒绝专门为他而立的主导性个人和文化模式,他不想像他父亲一样,必须恳求美国或英国国外事业社群的接受,而他也不能认同那个旧的种植业世界,它的根源来自奴隶制度,但是他的母亲一直认为她实际上就是“英国人”,她认为英国才是她的母国,因此她认同殖民势力。他觉得他比较像一个独立的牙买加男孩。在霍尔家庭的文化认同中,根本没有任何空间让这种“认同加勒比海文化和牙买加文化”的主体位置存在。霍尔和他的同学都在接受教育中成为反帝国主义者,而且认同牙买加的独立运动,他们期待帝国主义能寿终正寝,牙买加能够独立,替牙买加争取自主权。但是由于他家庭中姐姐婚姻不幸,以及他同时代的人很颓废的状况,他选择了移民到英国。在陈光兴的访谈中霍尔回忆到,他是1951年离开牙买加,一直到1957年,他才确定不再回到他的祖国。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去过,不过却也不晓得自己有这种倾向。从某个方面来说,现在的他可以将这种情形诉诸文字,是因为他已经迈向这个人生长久旅程的终点。他逐渐认识到他是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可以藉由这个关系,从这个立场出发,进行写作……他足足花了五十年,才又转回到他的家乡。[16]这其实就是霍尔在殖民地文化中,在移民后的英国进行写作、思考与反思,处在文化缝隙中一直不断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我的文化身份到底在哪里?我的根在哪里?”
在斯图亚特·霍尔还是小孩时,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提到牙买加,会认为它与非洲有任何关系,所有牙买加的事情几乎都和奴隶制度沾不上边,因为那块土地已经被殖民化了。人们能阅读的书籍是英语圣经,说的全是新教圣经的语言。所以在重新认同牙买加与非洲文化上,这些人再也无法成为非洲人,他们既不属于非洲,又不属于欧洲,而是另一种空间,另一种场景。所以霍尔心目中的回家,在他看来,不能只回到其中一个家,而是回到他心灵或灵魂的家。这正是族裔散居中的霍尔文化身份与文化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他在追寻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和回归中矛盾的情绪和错位的多元思考。尽管他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对英国文化研究乃至世界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牙买加文化与英国文化的挣扎中煎熬着、并实践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7]在“想象的共同体”中阐释作为“两栖人”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在霍尔移民到英国以后以及在他生活那个时代的牙买加人死后,从加勒比海牙买加文化上看,牙买加已经成为黑人社会,一个是奴隶、后殖民的社会。所以在对待牙买加文化时,他的身份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从英国文化来看,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并不是‘英国人’,也从来不想当‘英国人’”。尽管他对牙买加文化和英国文化都很熟悉,但是他都不全部属于其中某个地方,这正就是一种族裔散居的经验。正是这双重文化所形成的经验,就是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霍尔在1951年抵达英国后,开始了他在“新左派”的工作,他认为在新左派的立场上,确实有某种散居族裔的“举动”,在审视英国政治环境时,真的很像某个背景组合很奇特的人,他来自这种过程的边陲地带,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所有的事情。而没有感觉到这个文化已经是他的文化。也正是在英国牛津大学,霍尔真正涌现出作为“西印度群岛人”的身份。正如他自己说的,就是在牛津,他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只有在了解英国主流文化之外,才能审视、批判和质疑主流核心文化的情形,也是这些移居他地的被驱逐者,移民者,陌生人所具有的双重意识。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也具有同样的看法和认识,这些人虽然身在欧洲,但是他们原本就不是出自欧洲,如今却又和欧洲保持着殖民关系。边缘、殖民、驱逐和迁徙等等对同时涉足两个世界的人来说,感触最为深刻。[18]霍尔具有典型的双重文化身份背景,他要面对强大的英国文化,还要面对加勒比海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他面对双重世界,能借鉴多种传统,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身处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世界夹缝中,他与欧洲既依附又脱离的边缘身份,加勒比海文化与英国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自身利益与民族利益纠缠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艾勒克·博埃默对这种文化身份的阐述更为精辟“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民族主义的精英分子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在一个‘分裂的感知’或‘双重视界’之中。他们操双语,有两种文化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亦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游历于二者之外。这些精英分子在对帝国统治的某些方面进行挑战的同时,也发现自己能从与之妥协中获得好处。”[19]
对族裔散居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论文《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有深刻的论述和阐释。他对文化身份认同认识上不仅强调文化认同,更强调文化身份,即强调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只有从文化身份差异性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殖民经验”痛苦而令人难忘的性质。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根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即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作者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未变的。所以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是强调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历史性和变化性。在霍尔对加勒比海黑人身份研究中,他认为他们的身份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构架”的,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其实质上是谈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正如霍尔所说,差异在连续中,并伴随着连续持续存在。在长期离开之后再回到加勒比人中等于经历同一与差异的“双重”撞击。[20]因此我们认为“差异观”是认识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基础,是构成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根基,阐释文化认同问题实质上是在散居族裔语境下从文化裂变的差异中找到身份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