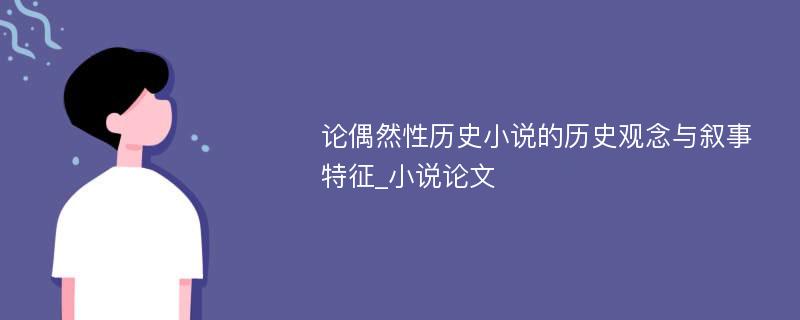
论或然历史小说的历史观念与叙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观念论文,特征论文,历史论文,或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指的是“显然从未真实发生过,因此也就不能声称有任何历史真实性,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随着受压制成分的回归)或许会实现”的历史。①在史学领域,它还被用作一种较新的研究方法,即对一些已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存在暂时予以否定。史学家通过这种“假如历史不是这样则会怎样”(what if)的假设,以及在此假设基础上的推断和演绎,可以更好地确定这些事件和人物的相对重要性究竟几何。由于同已知事实(fact)相左,或然历史又常常被称为“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或者“虚拟历史”(virtual history)。② 在文学领域,或然历史则是一种重要的文类,其题材以小说居多,小说中的背景世界是从“既定历史”的世界中分叉而来的——这里的“既定历史”既包括史书中记载的已知的历史路径和事件,也包括南作者构建出来的、作为“源文本”存在并在随后被予以改变的历史世界(后者的背景同我们现实中的历史没有什么联系,作者几乎可以任意发挥想象,而不需受历史考据和发展规律的束缚)。由于同人们预先接受的历史事实不同,这一文类在国内常被称为“架空历史小说”,它同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和历史小说郁有不同程度的交叠,尤其跟科幻小说中的“时空穿梭”(time travel)与“时间分叉”(time splitting)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 或然历史小说重在审视历史上一些关键的转折点,通过设想历史进程从原先轨迹突然拐道之后的场景,来呈现另外不同的故事版本。这些假设或基于科技预测,或基于相关事实,或完全出于主观想象,背后有作者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其中比较常见的是作者对当前社会现实的极度不满或担忧,通过描述一个梦魇般的世界,来达到讽喻当下、警示世人的效果,于是或然历史小说常常带有(反)乌托邦作品的特点,尽管两者并不尽然相同。 二、或然历史小说的主题嬗变 人类有记载的最早的或然历史出现在公元前27~25年,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 Patavinus)在其所著《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挥师西进而非东扩的话,罗马城将会怎样?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类,或然历史小说出现的时间并不算长,其中以在英美文学当中的发展最为完整,主题变化的脉络也最为连贯和清晰。 已知最早的用英语写成的或然历史是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出版于1845年的短篇小说《P的来信》(“P's Correspondence”)。故事是作者转录的一封虚构来信,写信人P是一个精神错乱者,他在信中勾勒出两个十分逼真而又彼此矛盾的现实世界。而第一部长篇或然历史小说则是霍尔福德(Castello Holford)的《最优乌托邦》(Aristopia,1895),书中记载了弗吉尼亚的早期移民如何发现金暗礁,如何在北美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故事。 进入20世纪,或然历史小说的创作手法开始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例如,威尔斯(H.G.Wells)发表于1923年的科幻名著《神一般的人》(Men Like Gods),是第一部以时空穿梭为线索的或然历史小说③——故事中的几个英国人偶然被时空穿梭机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爱好和平的、乌托邦式的英国(显然出于对当时真实英国的反讽),当他们意欲争夺权力时,这个世界的人们用射线枪将其发送到另外一个宇宙中。威尔斯的故事中由“平行时间旅行”(paratime travel)所引发的几个或然世界同时并存的“多重宇宙”(multiverse),成为日后英美通俗小说的常见模式。 1931年,由历史学家斯奎尔爵士(J.C.Squire)编辑的文集《假如当初是另样发生的》(If It Had Happened Otherwise:Lapses into Imaginary History)出版。④虽然其中的文章大多只是随笔杂文,却对后来或然历史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文集中收录的最著名作品,当属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假如李没有赢得葛底斯堡之战》,作者假定自己是身处另一时间流(即南方军队赢得内战之后的美国)中的一名历史学家,通过他的视角来想象假如北方获胜美国会变得怎样,即通过双重否定的方式来重新思考真实的美国历史。此外,该文集中的多篇文章都有作者自行编造的“一手素材”(如新闻报道、电报、书刊摘要等),为虚构的历史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而迫使读者有意无意地从这些碎片中去推断不同的历史。于是,读者变得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样,学会如何将断裂的历史踪迹串联起来,统一成整体;更变得像作者一样,参与到意义的创造过程中——“这一读者性的活动突出了历史的被建构性:历史并非存在于这些踪迹之中,而是由那些从历史物品中创造意义的、思维活跃的人脑制造出来的”。⑤由此可见,这部20世纪30年代初的或然历史文集,颇为超前地体现出一定的后现代思想:(1)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对文本解读和意义产生的积极参与;(2)强调历史的人为建构性和不可靠性。 二战时期的或然历史作品以政治宣传为主,多是描述纳粹军队大举入侵英美的场景,以期达到警示国民、激发斗志的作用。这一题材几乎成为随后或然历史创作的一大母题,从战后一直延续至今,其中较著名者包括史宾拉德(Nornmn Spinrad)的《铁梦》(The Iron Dream,1972)、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祖国》(Fatherland,1992)、沃尔顿(Jo Walton)的“小改变”系列三部曲(“Small Change” Trilogy),以及金里奇(Newt Gingrich)与福斯特钦(William R.Forstchen)合著的《一九四五》(1945,1995)。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铁梦》,这是一个叙述方式十分繁杂的故事,小说中嵌套着另外一部情节颇为完整的科幻小说《万字饰之王》(Lord of the Swastika),是由一战之后逃到美国的希特勒于1953年逝世前不久完成并出版的。在这个内嵌的故事结尾,史宾拉德又安排了一位虚构的文学评论家惠普尔博士对之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于是,或然历史、元小说、互文、反讽等元素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显示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手法和独到的历史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中,也有许多后现代科幻小说家重拾30年代的传统,对历史现实的可靠性提出质疑。然而,很多作家笔下的历史分叉点依然还是关键性的战争。例如,不管是迪克(Philip K.Dick)的《高堡中的男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还是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的《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1969),都是假设我们已知的二战结果只是众多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文学批评界对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格外的兴趣和热情,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文学究竟是如何再现甚至塑造历史的。与之相应,同一时期的或然历史小说家们也在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探索这类问题,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亲属》(Kindred,1979)和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根斯巴克连续体》(“The Gernsback Continuum”,1981)都深刻思考了历史叙事的物质真实性,提出“任何企图透过单一坐标系来处理历史的做法,都会对当下和未来造成致命的影响”,⑥而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变化》(The Alteration,1976)和比森(Terry Bisson)的《山间之火》(Fire on the Mountain,1988)则采用类似当初丘吉尔“双重或然”的话语手段(即或然历史中又嵌套着或然历史)进一步突显出历史书写的人为建构性,引发读者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思考。 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科技的进步,诸多作品都探索了最新的科学发现如何增加(而非减少了)本体的不确定性。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图特雷多夫(Harry Turtledove),正是此人使或然历史小说进入主流文学,并因此被冠以“或然历史大师”的美誉。⑦他的作品涉猎广泛,但其中的两大假想题材依然是美国内战和二战,如“南方胜利”系列(“Southern Victory Series”),“世界大战系列”(“Worldwar Series”),以及《不一样的肉体》(A Different Flesh,1988)。 1995年,美国科幻作家席尔瓦(Steven H.Silver)和利珀(Evelyn C.Leeper)等人发起成立了“斜向或然历史作品奖”(“The Sidewise Award for Alternate History”),以表彰每年评选出的最佳或然历史小说。该奖项的名称来自于美国作家莱因斯特(Murray Leinster)1934年的短篇科幻小说《时间的斜向》(“Sidewise in Time”),该书讲述的是一场奇特的风暴将地球带到另一个时间轨道上的故事。虽然斜向奖在设奖历史和社会影响力上不及雨果奖(“Hugo Award”)和星云奖(“Nebula Award”)等科幻类奖项,但以其关注或然历史的特定主题得以在文学界独树一帜。 21世纪初叶,或然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当属罗宾森(Kim Stanley Robinson)的《米与盐的年代》(The Years of Rice and Salt,2002)。这本书通过追寻近七个世纪的历史故事,对“西方人缺席的世界近代史”进行了大胆的假想,描写了一个欧洲文明与基督教陷入垂死之态,而佛教和伊斯兰教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究竟是何等样貌。同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两部备受关注的作品,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2004)和查邦(Michael Chabon)的《犹太警察联盟》(The Yiddish Policemen's Union,2007),这两本书都通过假想的历史世界对犹太文化和犹太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值得一提的是,《反美阴谋》和《犹太警察联盟》均在出版当年获得了“斜向或然历史作品奖”。 未来的或然历史小说,其主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现在自然不好臆断。但可以确定的是,多数作品在追求娱乐性和可读性(如丰富的想象和离奇的情节)的同时,将始终保持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思考,并力图透过历史折射当下,以反映人们对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索。 三、或然历史小说的合理性 或然历史小说中的叙事假想同一般历史小说中的艺术虚构有着本质区别。根据“斜向或然历史作品奖”创始人之一席尔瓦的观点,或然历史小说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故事有一个历史分叉点,且该点必须发生在作者写作的历史时间点之前;(2)分又点之后的历史偏离了已知世界的发展轨迹;(3)对偏离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审视和思考。这个历史分叉点叫做“交汇点”(nexus point),⑧它往往是某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重要的政治决策、关键性的战役等),也可以是由诸多分力构成的合力,其中任何一个分力发生改变,都将导致历史轨迹的巨大偏移,宛如蝴蝶效应一般。于是,历史摆脱了单一的线性结构,变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整体,其中“任何特定因素对于其他无数因素都是有所触及的……与其说事件是一条线上可辨明的点,倒不如说它们是一个经验的无缝网络中的任意的(而且常常是同时发生的)偶发事变”。⑨ 不仅历史具有建构性和偶然性,身处其中的个人亦是如此——人本身并不具有什么个体本质,完全是各种环境因素的合力产物。也就是说,个人不仅是“可变”的,还可以参与到改变中,这种改变本身或许微不足道,但经过蝴蝶效应几何级数般的放大,足以影响之后的历史进程,使之充满变数——“这就为个体赋予了伟大的力量,同时表明:由于一切可能其实都会发生,根本不存在什么道德上必须为之的事情”。⑩因此,艺术“不再表现道德上的绝对而开始表现本体论上的绝对”。(11)很显然,这种观念具有颠覆正统思想、唤醒个体意识的作用。具体到或然历史小说中,这种主体化的趋势常常表现为叙事重点从“集体历史”到“个人历史”、从“客观历史”到“主观历史”的转变。以或然历史小说中较为常见的“时空穿梭”为例,该母题就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即强调个人的主体性),正如雷蒙德所言,“假如现代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身处其中的个体面对种种官僚结构与公司垄断深感异化与无力,那么时空穿梭则表明:每一个人对历史的塑造都很重要,都能对世界的变化方式产生真正的、可以量化的作用”。(12)此外,让个体穿越到过去,等于是为历史因果的方程式增加了一个变量,通过它的数值变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他因素的相对意义。总之,既然历史具有偶然性,参与历史的每一个个体亦变幻莫测,对历史的阐释也应该是多元而开放的,而涉及历史的文学创作更是自不待言。 由此可见,或然历史小说并不单单是作者一时兴起的凭空杜撰与随意编造(尽管有一部分作品的确如此),它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背后常常隐藏着某种“政治无意识”,即文本或叙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所投射的意识形态愿望或政治幻想。在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看来,这种愿望和幻想采取执著的否定现存一切的方式,从而“使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有可能富于生气”。(13) 事实上,作为或然历史的对立面,“历史真实性”的概念在当代西方一直遭受质疑。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指出:“一切历史记录都是偏袒而不准确的……在我们看来似乎无比真实的世界只是一个幻象,因此相信人的感官判断只是粗鄙无知之举。”(14)此言道出了影响历史准确性的两大因素:历史记录者的视角局限和现象世界的不可靠。反映到认识论上,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知识本质上只是权力关系的产物,虚幻而不实;而且除了产生知识,权力还具有产生“现实”的能力,以至于诸多现实可以同时并存,甚至本来就没有一个单一而正确的现实,有的仅仅是人能够直接体验到的那个版本而已。既然现实是复数的,那么作为“故事”的历史也应当是复数甚至是可选的,所以在叙事过程中提出或然假想,实在无可厚非。 后结构主义历史观(以及新历史主义观)格外适用于对或然历史小说进行辩护,因为相关理论不但将历史复数化,使得偏离正轨的其他历史版本拥有了一定的合法地位,而且强化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使得这一史学理念在小说创作中的应用变得顺理成章。(1)就历史的复数化而言,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任何文本都无法指涉外部事实,只能指涉其他的文本,(15)历史亦不例外。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历史不再是文本赖以依托的稳定背景和语境,历史本身即是文本,是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并利用别的文本作为互文。(16)而所谓“统一和谐的文化”,不过是强加到历史头上的一个神话,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做的宣传。于是,原本单一的历史(History)被拆解成了许多断断续续、彼此矛盾的历史(histories),这就等于为或然历史小说的“另辟蹊径”赋予了理论上的合法性。(2)就历史和文学的联系而言,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学家并不是冷静、沉着地看待事实,而是通过特定的叙事体裁和文学修辞来展现事实,以此创造意义;孟特罗斯(Louis Montrose)在提出“历史的文本性”时也认定:“没有任何知识可以存在于叙事、书写和话语的国度之外”,(17)意即作为文本的历史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学叙事属性。以上观念“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传统藩篱,瓦解了历史话语的客观性基础”。(18)也就是说,历史文本不该有一个预设的框架,而应当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叙事潜能,进行自我颠覆与解构,或然历史小说便是这种叙事潜能在文学创作上的极端展现。 与之呼应的是,在整个70-80年代,史学界曾出现大量的历史修正主义做法。(19)在史学界之外,王尔德的名言“我们对历史拥有的唯一责任就是重写历史”(20)更是被许多批评家和艺术家奉为箴言,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加入到再造历史的过程中,从而丰富了人类对世界的了解和对社会的批判,因为“一切创造性话语都蕴藏着乌托邦的可能性——新的世界、新的修辞、新的阐释、新的身处世界的方式。只要能扩大沟通、开启可能性、创造看待世界和身处世界的新方式,都是潜在的颠覆力量,能够挑战权威的合法性”。(21)在这其中,小说创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必受太多的学科规训和形式制约,得以比修正历史更为自由和激进,再加上不断涌现的新科技、新发明所提供的灵感,大大拓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作家索性将已知历史的轨道偏转开来,演绎出一段新的历史,这也部分解释了70-80年代的或然历史小说创作何以如此兴盛。 当然,或然历史(小说)的意义所在(即认可偶然因素、推崇个体意识)也恰恰是其易受抨击之处——或然历史观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一种反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在或然历史中,却往往是个人行为或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使后者相形之下显得随意而散漫。然而,两者之间亦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对事件的重述,为的是揭示那些否则一直隐藏在传统历史版本中的内容”。(22)现代叙事学认为,但凡对社会进行批评性的阐释,首要工作就是通过为事件提供另外的历史解释,展现当下世界会变得如何不同,即挖掘那些“不曾实现的过去之未来”。(23)由是观之,马克思摒弃了聚焦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传统撰史方式,将起先并不起眼的群体(受剥削的工人)或事件(劳资关系、阶级斗争)发掘出来,使之成为占据核心地位的历史动因,由此导致历史排序被颠倒,原本在历史中失音的被压迫者成了历史的主体,一系列新的事实浮出水面,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或然历史小说则常常通过象征性的语境表达那些边缘个体的声音,展示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或然历史一样,都是激进的话语方式——它们拨开了神秘化的意识形态迷雾,直接挑战统治阶级的威权。 四、或然历史小说的后现代性 西方学界在传统上基本是将历史和艺术区别开来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只能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过去的具体细节;而诗人则讲述可能、大概会发生的事情,因而更能表现普世性主题”。(24)既然各自的功能和使命不同,诗人(以及后来的小说家)大可不必作茧自缚,拘泥于“忠实再现历史”的戒律。加之历史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小说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妨大胆突破连续一贯的线性结构,探索各种各样的历史可能性,启发读者对历史和人生更多方位的思考。然而,历史和小说毕竟都具有极强的吸纳性,两者关注的问题也时常出现重合;及至现代,随着批评界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更趋模糊(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然而有趣的是,有些小说家并没有因为这种交叠而受到历史条框的影响和羁绊,反倒更加堂而皇之地跨进历史的领地,恣意挖掘其中的“可能”和“大概”,这其中尤以或然历史小说为甚,这一文类的作者干脆推翻既定历史,另铺历史轨道,展开丰富的叙事假想。 就创作方式而言,或然历史小说带有强烈的后现代叙事特征,其中最为根本的当属其内在的互文性,即不同历史版本之间的参照和对比。借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我们只有了解那些作为“他者”的或然之史,才能对既定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反过来,既定历史作为我们早已熟知的“前文本”(pre-text),也可以同或然历史的假想之间构成互文。此时的重点既不是既定历史,也不是或然历史,而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变化,以及文本得以产生的话语空间,由此造成一种陌生化效应,不时提醒着读者:你正在阅读的是一个人为建构的故事,切莫陷入现实主义的迷梦。这让人想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戏剧理论中的间离化效应——布莱希特鼓励观众同剧情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激发他们理性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一个可变的人类创造过程,而非被动接受的宿命。(25)照此看来,尽管或然历史小说关于历史“否则将会怎样”的设想与已知历史“真正怎样”的矛盾不可调和,但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与激化,能够产生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感。凭借这种紧张感(或曰“张力”),或然历史小说可以引发社会批判,不断产生新的乌托邦视野,从而推动人类对当下社会的改造和修正。 在互文性的基础上,或然历史小说还具有类似元小说的自我暴露叙述行为的特征。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中心的消解和对个体的突出,即哈桑(Ihab Hassan)所言的“用无政府状态取代等级森严,用枯竭取代掌控,用戏耍取代意图,用随机取代规划,用参与取代疏远,用分散取代集中,用互文取代文类,用转喻取代隐喻,用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26)这一系列的“取代”其实都是元小说的特点,同时也是或然历史小说所力图展现的——在处理手法上,它对既定历史的偏离和改造,同元小说中的选择性结尾(如《法国中尉的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效果上,两者也都具有警示读者摆脱现实主义自欺迷梦的陌生化效应。 在自我意识膨胀的后现代社会,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越发受到质疑,人们更倾向于把语言看作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而不是什么再现客观世界的载体——由于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都在不断变化,要用语言符号来描述客观世界是绝无可能的。(27)因此,“小说无法描绘所谓的‘真实世界’,只能提供不同的可能性”。(28)于是,元小说便适时登场,以突破常规的写作方式(如暴露作者身份、揭示叙述行为、插入式评论等)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模式,动摇了现实主义的权威地位,使小说文本从“反映现实”的束缚下得到解放,成为独立的个体。由于具有明显的自我暴露叙述行为的痕迹,元小说被定义为“关于小说的小说,或更确切地讲是对自己作为小说的身份公开进行评论的小说”。(29)换言之,它是“用小说形式揭示小说规律的小说文本……使叙述行为直接成为叙述内容,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小说”。(30)作为同样谋求颠覆“真实历史”的或然历史小说,自然同元小说这种自指性的、戏仿的写作方式有着诸多相似甚至交叠之处。因此,当我们描述或然历史小说的时候,完全可以套用元小说的上述定义,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或然历史小说实则是一种“元历史”,它用历史小说的形式揭示历史规律本身,使编史行为(historiography)直接成为撰史内容(history),从而将历史本身大大地前景化和主体化。 不过,尽管具有明显的编史性和元小说性,或然历史小说跟传统的历史小说以及哈琴提出的“历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al metafiction)(31)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传统的历史小说通常吸收和同化历史资料和细节“以赋予虚构的世界一种真实可信的感觉”,(32)历史元小说很少如此,而是着重于彰显“试图同化的过程”;与之相比,很多或然历史小说在自我暴露编史行为和叙事过程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历史资料和细节的逼真性,以使其中的时空穿越或者历史转轨显得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信度,甚至使读者产生“警觉于虚幻”和“沉迷于现实”兼有的矛盾感受。此外,历史元小说虽然“承认过去事实的矛盾性,但不承认我们当代人能够走进存在于文本的过去”,(33)而或然历史小说索性将这最后一道门槛也拆去,使作为文本的历史王国完全向后人敞开,由此得以不断地被揣测和重塑,甚至转轨。 此外,除了互文性与元小说性,或然历史小说还具有一定的空间属性——由于叙事的线性时间被打破,读者的“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同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34)以或然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平行世界故事”(parallel worlds stories)为例,这类作品认定历史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发生改变,不仅仅是重大的决策和关键性的战役,即使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关头,其间的每一个选择都将导致一个全新的宇宙分叉而出,形成彼此平行的“多重宇宙”。这种多个物理世界同时共存的现象,使得小说的叙事结构在原有的时间性基础上,具有了明显的空间性,而读者的主动性也随之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不再被束缚在由纸页上记录下来的事件的时间连续之中”,而是“从作品本身的对象中得出他自己的联系结果”。(35) 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中提出其著名的“三角形”模型(即由居于中心的作品同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共同构成的三角形框架)时,曾明确指出:“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而批评家往往仅凭其中之一“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36)照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或然历史小说既能满足作者(即艺术家)自由发挥想象力的创作欲望,又能推动读者(即欣赏者)积极参与意义的阐释,同时又强调了宇宙(即世界)的多维性和文本(即作品)的主体性,所以针对这一文类的解读和分析,常常可以涉及多个理论视角和批评工具。由于这些视角和工具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难免会导致相关研究中出现矛盾甚或争议。然而如若换一个角度看的话,这也恰恰说明:或然历史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待更多的作家和批评家去挖掘深藏其中的各种可能性。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努力,可以有效推动文艺理论和文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并进一步丰富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或然历史小说在故事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堪称标新立异、别出心裁,但它并非对既定历史的简单破坏和否定,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系着传统,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改变已经确立的形式就像捍卫已经确立的形式一样,也是一种同传统的联系”。(37) 事实上,无论其故事背景是假想未来还是篡改过去,或然历史小说的最终落脚点总在当下,因为“哪怕最狂野的想象也都是经验的拼贴,是由此时此刻的各种碎片形成的构想”,(38)而人类的想象空间总是受制于自身的生产方式(及其所保留的一切旧日遗存),而基于想象的或然历史小说,无论多么天马行空,都只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社会困境所做的历史文化回应。当然,这种回应常常是从反面发挥作用——小说中的或然世界,“要么无比美好,以体现作者对当下社会的失望;要么可怖异常,以影射现实中的体制”。(39)也就是说,这类作品的主要用意往往都是对当下的警戒以及对未来的担忧,因为从或然历史角度看的话,当前的每一个不同选择都会彻底抹去一个未来(包括其中的每一个人),詹姆逊将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形象地比作种族灭绝,并为此呼吁:“也许我们确实需要培养一种失去未来的焦虑感,这就跟奥威尔对失去过去、记忆、童年的焦虑是一样的。”(40)这种焦虑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引发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推动人类对当下世界的改造和修正——既然历史是开放的,未来亦是不确定的,人类有义务积极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去创造更好(抑或避免更糟)的未来世界。 注释: ①Elisabeth Wessling,Writing History as a Prophet:Postmodernist Innov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1) 13. ②严格来讲,或然历史和反事实历史并不完全相同:反事实历史关注的是被暂且否定的历史事件本身,而分叉点之后的历史轨迹必须按照相关逻辑合理地向前发展;或然历史关注的则是历史事件被否定之后发生了什么场景,而且小说家也享有更大的假设自由和想象空间。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别常常被模糊化。 ③威尔斯在1895年出版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就已含有时空穿梭的内容,但由于主人公是去向未来(公元802701年)而非回到过去并改变历史,所以并不属于或然历史小说的范畴。 ④1931年,美国维京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修订版《假如:或者重写的历史》(If:or,History Rewritten),增加了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等人的作品。 ⑤Karen Helekson,"Alternate History," ed.Mark Bould,Andrew M.Butler,Adam Roberts and Sherryl Vint(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9) 454. ⑥Lisa Yaszek,"Cultural History," ed.Mark Bould,Andrew M.Buder,Adam Roberts and Sherryl Vint(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9) 197. ⑦Melissa Mia Hall,"Master of Alternate History," Publishers Weekly,April 7,2008. ⑧“交汇点”亦称为“约翰巴尔点”(Jonbar point或Jonbar hinge),取自威廉森(Jack Williamson)的小说《时间军团》(The Legion of Time,1938)中的人物约翰·巴尔(John Barr)。 ⑨米切尔森著,秦林芳编译:《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⑩Karen Helekson,"Alternate History," p.457. (11)柯蒂斯著,秦林芳编译:《现代主义美学关联域中的空间形式》,《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第77页。 (12)Sean Redmond(editor),Liquid Metal:the Science Fiction Film Reader(London:Wallflower Press,2004) 114. (13)詹姆逊著,李自修译:《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92页。 (14)George Orwell,"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 Shooting an Elephant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50) 110. (15)Chris Baldick,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112. (16)Selden,Raman,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the fourth editi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1997) 188. (17)John Brannigan,"History,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Literary Artifact:New Historicism," ed.Julian Wolfreys,Introducing Literary Theories:A Guide and Glossa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 170. (18)张进:《元历史》,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7页。 (19)这里所说的“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为中性含义,指的是利用新的知识和发现,或者通过新的视角,对既有史实做出不同的解释,而非取其贬义,即对历史的蓄意修改,后者亦被称为“否定主义”(negationism)。 (20)Oscar Wilde,"The Critic as Artist," 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New York:Barnes & Noble,1994) 1023. (21)David M.Kaplan,Ricoeur's Critical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61. (22)David M.Kaplan,Ricoeur's Critical Theory,pp.60-61. (23)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I),Trans.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80. (24)Aristotle,Poetics,Trans.James Hutton(London and New York:Norton,1982) 451. (25)Chris Baldick,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pp.4-5. (26)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91-92. (27)Patricia Waugh,Metafi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4) 3. (28)李锋:《谈小说〈青蛇〉与后现代叙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 (29)Chris Baldick,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p.133. (30)李秀琴:《元小说》,转载自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 id=2873. (31)“历史元小说”(historiographical metafiction),也被译为“编史元小说”、“历史编写元小说”、“历史书写 元小说”等。 (32)(33)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4、114页。 (34)弗兰克著,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第3页。 (35)柯蒂斯:《现代主义美学关联域中的空间形式》,第64页。 (36)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页。 (37)伽达默尔:《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38)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Books,2007) xiii. (39)李锋:《从〈未来考古学〉看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 (40)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p.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