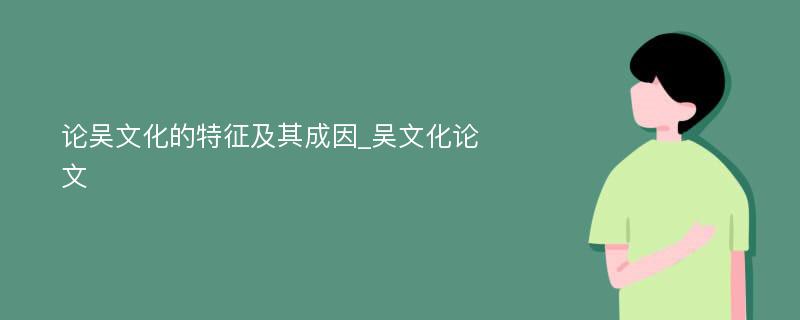
论吴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特征论文,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吴文化的特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层(人文心态)的根本特征,中层的一般特征和外层的具体特征。其发展主线是刚柔相济,其中“刚”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文化事业的全力投入,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在经济领域中开拓进取的精神等。吴文化这些特征,是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而形成的。
一
自80年代初吴文化热兴起以来,吴文化的特征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论者对吴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
就目前而言,史学界一般将吴文化界定为广义的吴地的文化,包括历史上吴人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此漫无边际的范围,倘若不对其结构细加分析,显然难以把握住吴文化的研究方向及其文化特征。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诸家学说中,影响较大的是1986年庞朴先生提出的文化三层次论,即“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念、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两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①a]。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将吴文化的特征划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人文心态)的根本特征、中层的一般特征和外层的具体特征。其中一般特征和具体特征,王友三先生将它们分别表述为“一般文化形态”和“具体文化形态”[②a]。本文提出核心层的根本特征,旨在从吴文化的诸多特征中寻觅一条能够一以贯之的主线,以俾吴文化各种特征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明朗。那么,吴文化的根本特征,或者说吴文化发展的主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刚柔相济。自新石器时代起,吴文化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刚柔相济这条主线,而以六朝为界,这条主线又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特色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刚为主,以柔为辅,外刚而内柔;后一阶段则表现为外柔而内刚,以柔的面貌展示自己,以刚的精神自律自强。
人们常常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来说明古代吴地的尚武之风。然而就在吴人崇尚武力,表现出外在的阳刚之美时,其内在阴柔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并没有一刻消失,这种柔性不断释放出来,凝定在他们所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上。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原始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陶器还是象牙骨器,上面雕刻的物象的线条都是以弧线、圆圈线和卷曲线为主,不施色彩,属于白描素雅类型,“形成了细腻、柔和、生动、传神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温和潇洒和内含的性格,和对清淡素雅风格的喜爱”[①b]。比河姆渡文化晚二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则以它精美绝伦的玉器让后人为之倾倒。据一般学者研究,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纹就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源头,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商周“青铜器动物纹饰都是采取夸张而神秘的风格,即使是驯顺的牛、羊之类的图像,也多是塑造得狰狞可怕”[②b]。在中原人心目中,神灵是抽象而恐怖的,只能敬而远之。良渚人对神灵的态度明显不同于中原人。1986年10月在余杭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最具典型意义,在这里,“体形不大的人面处在画面上方中心部位,显示了神的核心在于人”。时代晚于反山的瑶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神人兽面纹出现了逐渐融合、简化和省略的趋势”,“狰狞的獠牙,神秘的羽冠,烦琐的线条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简略的神人头形图”[③b]。不难看出,良渚人的世界观趋于现实,重视人的价值,审美情趣也以简洁明快为特色。大约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在江南突然消失,经过数百年的文化断层,至商代江南地区又出现了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和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它们都是青铜文化。一开始,江南青铜文化基本上是模仿中原,但至商代末期就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出现了“造型奇特优美”的鸳鸯形尊,“标新立异”的飞鸟盖双耳壶,饕餮纹也变得“稀疏简略,不施地纹,已失去它原来的繁褥神秘性。”花纹装饰不受什么体例限制,不像中原那样规范化,有时显得随意草率。总之,商末周初江南青铜器“从铜质的熔炼到器物造型及花纹装饰等方面,均体现出生动活泼、富于革新的精神”[④b]。这种柔性的审美情趣在六朝以后的吴文化发展中一直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推向极致,形成各种门类的精巧手工业行业,如丝织、刺绣、玉雕,以及现代的尖端轻工电子产品等等。
另外,从上古吴人的处事方式、行为准则中,也可以发现其“柔”的一面。商朝未年,太伯仲雍奔荆蛮,建立勾吴国,一开始太伯“端委以治周礼”,试图用周族的一套制度统治土著人民,结果行不通。仲雍嗣位后立即改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打扮得与土人一般,以获得土人的认同。仲雍这种入乡随俗的统治方式,避免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表现出权宜灵活的性格。直到春秋末年,当吴国以武力欺凌鲁国时,孔子那著名的学生子贡还曾援引仲雍之事,来讥讽吴国的祖先就不是什么恪守礼法之士[⑤b]。吴国祖先不拘泥传统、灵活善变的精神为他们的后裔所继承。春秋时期,随着吴国与中原诸侯接触的增多,吴人对中原先进的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向往之情。公元前576年,吴王寿梦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大会诸侯,他观看了周朝礼乐之后,大发感慨:“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⑥b]正因为吴人对外部先进文明表现出吸纳、包容的开放胸襟,所以到春秋后期才会出现精通中原礼乐的季札,产生名列孔门七十二贤的言偃。
六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吴文化发生转型,价值取向由尚武趋于尚文,吴人的形象也由“轻死易发”转变为温文儒雅。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而身体却“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①c],及遇战乱,则束手无策,未经阵仗,便已猝死途中。从东晋时起,人们就认定江南人柔弱怯懦,不善打仗,到了近现代,这种看法几成世人共识。林语堂先生曾为江南人画了一张俏皮的“漫画”,说:“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爱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②c]于是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吃大米说软语的法南人只能产生才子佳人,但成不了大气候,出不了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此,我们不以为然。事实上,吴人儒雅不等于怯懦,相反,这种儒雅的外表之下,隐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刚”的文化性格。这种“刚”的性格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吴人对文化事业的全力投入。在封建专制时代,吴人先后遭到多次政治上的打击,比较严重的,一是两晋南朝北方士族对南方士族的排挤压制,一是明初朱元璋对江南士人的残酷杀戮。严酷的政治现实,使得“南士将政治上的追逐转化为精神上的执著”,将其心智全部倾注到文化事业上去,以丰厚的文化成就来弥补权力的失落[③c]。他们虽然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来平衡自己的心态,但这绝非全身远害的消极遁世,而恰恰是另一种积极入世的方式。明代文征明倡言道:“奚必矫矫孑立,求胜于气,然后为能尽其刚哉!昔刘器之不为枉矫过激之行,而耿挺特达,卓有建明,至于颠顿困踣,曾不少变,而苏轼氏以铁汉目之。”[④c]这实质上是向世人宣告江南士人所追求的是一种外柔内刚。吴人对文化的投入,形成了重视文教的传统,出现了众多的文化世族。当北方世家大族由于朝代变更、政局动荡而分崩瓦解时,南方的文化世族却凭借文化传承的坚强韧性延续下来。吴人沐浴在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之中,外表变得越来越柔,而内在“刚”的精神却愈益强化。
第二,吴人注重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执著追求,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范仲淹。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对先秦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继承和张扬,他以毕生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致力于“仁”道的不懈追求。这是一个艰辛异常的过程,诚如曾参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⑤c]然而范仲淹“以道直行,虽危不避”[⑥c],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痴心不改,真正“做了天地间第一等人”[⑦c],为世人树立了儒家“士志于道”的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影响了整整一代士风,这难道不是一种“刚”的精神吗?
第三,吴人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可以举证的例子很多,如南宋末年文天祥领导的江南抗元斗争,李庭芝、姜才领导的扬州抗元斗争,明末清初发生的“扬州十日”、“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吴淞口战斗、镇江人民抗英斗争,以及现代史上的淞沪抗战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江南人在这些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连外国人都钦佩不已。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镇江军民在抗击英军的战斗中“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的“勇敢和锐气”,他说:“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⑧c]即使如明末文坛巨子钱谦益、吴伟业,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一度“失节”,屈事新朝,但不久即辞官归隐,遁入空门,以求心灵解脱,这说明他们身上仍未失去刚的秉性。
第四,吴人并非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文人。在政治腐败、国是日非的年代,江南士大夫对政治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如“宋学建立阶段的组织者和带头人”范仲淹,所倡导的学风就是“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①d]。明末东林党人则旗帜鲜明地宣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强调立志做人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事,提倡实学,重视社会,关心民瘼。其领袖人物顾宪诚,衣食无华,生活俭朴,却终日“忧时如疾痛”[②d]。清初顾炎武则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宋明理学严辞抨击,提倡经世致用,高扬起“经学即理学”的大纛,开创了清代的考据学风。“乾嘉盛世”过后,社会呈现出衰败之相,仁和龚自珍谨遵外祖父段玉裁的教诲,“努力为名儒,为名臣”[③d];同时又受常州今文经学派影响,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对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改革主张,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维新派先驱者的地位。江南士人担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使命,时刻站在思想战线的前沿,高瞻远瞩,领导潮流,这正是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刚”的性格。
第五,吴人的“刚”还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开拓进取的精神。江南是我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方,也是西方列强最先打开的中国门户,因而这里能够得风气之先,诞生了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直到现当代,江南人仍是全国的排头兵,推出了“苏南模式”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典型。1970年全国其他各地还在“停产闹革命”时,后来成为“华夏第一县”的无锡人已经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口号,他们充分利用从大城市下放的经营管理和工程技术骨干,“发动社队兴办支农工业,既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又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从1974年起,无锡县就成为全国乡镇工业产值最早超亿元的县份之一,以后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④d]。与无锡毗邻的江阴市也不甘落后,从“1970年起城镇知识青年集体插队落户,实际厂队挂钩,推进了社队工业发展势头。”[⑤d]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江南人却巧妙地逆“潮流”而进,这不也是睿智与胆识、气魄的结合吗?
以上五点都是从人的角度探寻吴文化“刚”的特性,设若变换一下视角,我们同样可以在吴人那美奂美仑的艺术作品中发现其“刚”的一面。比如说南画,追求的是一种雅秀的气韵,但其笔法也“不是一味用柔的,柔中有刚,不过劲气内敛,在画面上不显出剑拔弩张之气和棱角罢了。”[⑥d]绘画如此,其他门类作品的精神大致可以依此类推。
总之,刚柔相济作为吴文化高度概括的根本特征,是吴人心态的核心层,在吴人与社会、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这种核心又会释放衍展开来,形成几个较为具体的一般特征,也就是王友三先生所说的“一般文化形态”,包括开放的胸怀、进取的意识、功利的观念、尚文的传统、隐逸的心态等五个方面。对此,王友三先生在其著作《吴文化史丛·绪论》中已有较为全面而简括的论述,毋需本文赘言。吴文化的一般特征再物化为具体文化形态,就构成了吴文化最外层的“具体特征”,诸如诗文、书画、园林、戏曲、医学、丝织、刺绣、美食等等。这些具体文化形态的具体特征,每一类都可以写上一部专著,实非本文所能探讨得了。
二
吴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而每一种因素对文化影响的力度则因时因地而异。在探求吴文化特征的成因时,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分期加以考察,同时还要全方位地审视各层次的文化现象,就像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①e]唯其如此,方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区域文化的全貌,得出较为持正的结论。
六朝以前,吴文化特征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汉以前的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表明,在那炎热潮湿、榛莽丛生、沼泽四布、虫蛇出没的恶劣环境中,江南地区的生产力还很低下,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以致进入阶级社会后财产的分化并不剧烈,从而为原始氏族制度某些残余的保存,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些残余包括:(一)血族关系仍是社会制度的主要内容,每个成员都要承认绝对的血族复仇的义务;(二)“人们把发动掠夺战争作为扩充财富的正当手段”;(三)原始的图腾崇拜,迷信鬼神,养成了吴越人喜欢自残和对武力的盲从观念[②e]。这些氏族残余在吴国统治者有意识的倡导之下,形成了早期吴人的尚武精神。
江南的地理环境不仅培植了吴人早期的尚武风气,同时,江南那烟雨迷蒙、波光粼粼的自然美景也涵育了江南人的似“水”柔情,这是一种像水一样能够以柔克刚的“柔”。有学者以此为出发点,引申出吴地民风“主柔”、“重情”、“善思”的三大基本特色[③e],是颇有见地的。
六朝吴文化发生转型,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政治。吴国灭亡之后,江南士族就被视为“亡国之余”[④e],在政治权益、社会门第方面受到北方士族的严厉钳制。虽然永嘉南渡时王导曾刻意笼络江南士族,但这仅仅是一种权宜的政治策略,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南士遭压制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隋文帝平陈统一全国之后。在北方士族的压制之下,南方士族虽经多次抗争,皆以失败告终,最后,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选择了朝隐这个心灵的乐土。在此心态支配下,“崇尚武力的价值取向开始为士族阶层所摈弃,止足淡泊的‘不竞’之风逐渐滋生蔓延,温文儒雅已成为南士新的价值取向。”[⑤e]人们开始在文化领域寻觅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原先的门阀世族也慢慢演进为生命力更为强劲的文化世族,江南士人在痛苦的政治煎熬中获得了凤凰涅槃的永生。
政治对吴文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六朝,在宋明时期依然存在。北宋天圣年(1023—1031年)以前都是实行重北轻南的方针,朝廷通过提高评分标准、降低录取名额的手段来限制南方参加科举的士子,因此“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⑥e]。明朝初期,朱元璋因痛恨割据苏州的张士诚而迁怒于江南士大夫,以残酷杀戮和大批迁徙出境的方式来惩罚他们。面对这场急剧而来的政治风暴,吴地人文心态激变起新的历史走向,形成了特定时空间的“市隐”文化心态。明末天启年间,江南士大夫再遭政治厄运,阉党魏忠贤诬陷编造的《东林党人榜》上被削籍、追杀、禁锢的309人中,大多为江南籍文人。为了反抗这种专制暴政及正统的意识形态,江南文人竭力倡导个性自由,提出了“顺情遂性”的口号,从而导致士大夫们对生活趣味化和艺术化的追求,并从中获得一种审美人格。“明季江南文人有‘隐逸气’,就是从他们这种趣味生活和艺术生活的选择中流露出来的”[①f]。
如果说政治对吴文化的影响主要还局限于上层士大夫阶层的话,那么经济对吴文化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带动整个社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的变迁。六朝是江南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个体家庭随着生存能力的增强,纷纷从累世同居的大家族中游离出来,社会的基本单位进一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血族关系不再被人重视,经济利益的关系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不再盲目地将血亲复仇视为自己的绝对义务,他们学会了权衡利害,懂得了珍惜生命。可以说,在两晋时期,江南士族尚文观念的形成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无奈,而南朝以后,黜武尚文则是新经济形势下的自觉选择。
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转移至南方,出现南方全面超过北方的局面。繁荣的经济无疑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江南经济发展对铸就吴文化某些特征所构成的特殊影响。前文说过,明初朱元璋曾将江南士人大批杀戮、迁徙,严重阻碍了吴文化发展的进程,经过百余年的沉闷期,明中叶以后吴地文化才得以复兴,再创辉煌。而吴文化能够重建的契机之一就是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对文化的投入。清代苏州府26名状元中有6名是徽人后裔,包括大名鼎鼎的毕沅、洪钧、汪绎、汪应铨等[②f]。这不能不让人对商人刮目相看,不能不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秩序产生巨大的冲击。江南士大夫开始乐意并主动与商人交往,甚至加入到商贾之列,“与小民争利”,以求先获得经济上的保障,然后再投入文化,供子弟后裔“专事进取”[③f]。是故古之四民界线森严,而至明代中叶士之与商已难判其疆,“良贾何负闳儒”[④f]已成为江南社会普遍认同的新型的价值观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代江南人的重商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商人本身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及其对文化投入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的基础之上,他们重视的是“儒商”而非暴发户,其出发点是文化,其终极归依还是文化。
铸就吴文化特征的第四个重要因素是吴地居民的移民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多元性。中华文明在石器时代就已经是满天星斗,而非黄河流域一枝独秀。但也不容讳言,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经历了一条由北向南的推进过程,而江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这一推进过程中的文化孔道。从历史上看,这种文化推进不是统治者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而是政治或战乱带来的客观后果。考古发现,在商代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中含有中原二里头夏文化因素,据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推测,这很可能是夏王桀失败后由巢湖顺江而下到达上海后带来的[⑤f]。与马桥文化齐头并进的宁镇湖熟文化则明显地受商文化的影响。这两支文化由于泰伯仲雍的介入而逐渐汇流为吴文化。可见吴文化在其形成的初始阶段就已经表现出兼容并包的多元性。再后来,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又进一步加深了吴地区域文化内部的整合消融。
自秦汉起,黄河流域就成了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逐鹿中原”的壮观历史剧。那些战场上的败将以及避乱的百姓则一批一批地逃往江南,成为江南新的移民。这些移民实在太多太频繁了,以至今天我们很难找到谁是真正的江南人。即使是以江南主人自居曾经支撑着东吴政权的吴中四大姓顾、陆、朱、张,据明代苏州人王鏊考证,他们的祖先都是汉代才由北方迁徙而来,其中顾氏虽然是越王勾践后裔之一脉,但作为顾氏的祖先,其始封之地却在今天的河北地区,直至汉初才迁回会稽,然后再移居吴郡[①g]。顾、陆、朱、张尚且如此,罔论六朝、南宋时的大规模移民了。到近代上海开埠后,江南更是成了五方杂处的大都会。最早的移民可能还多少带点主人的优越感,傲视后来者,但到后来,他们就习惯于宽容了。永嘉南渡时,北方王、谢等上层大族也尽量避开顾、陆、朱、张聚居的吴郡,到相对僻静的会稽郡去发展;次等士族则多侨居京口、晋陵,以免与江南“主人”发生正面冲突[②g]。从那时起,这种互不相扰各取所需式的宽容意识就开始形式,经过1600余年的发展强化,已经辐射积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现代人尊重个人自由的观念。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尚文重教、隐逸心态等方面来诠释吴文化的某些具体特征,但这些因素本身就是从政治、经济等初始因素中衍生出来的,对解释吴文化的根本特征不具有本原意义,因而没有必要再作循环论证了。
注释:
①a庞朴:《要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光明日报》1986年1月17日。
②a王友三主编:《吴文化史丛·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①b康育义:《论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美学特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②b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③b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④b肖梦龙:《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东南文化》第2辑(1986年10月)。
⑤b参见《春秋左传集解·襄公七年》。
⑥b《吴越春秋》卷2《吴王寿梦传》。
①c《颜氏家训集解·涉务篇》。
②c引自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4页。
③c参见拙文:《南北士族之争与吴文化的转型》,《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④c《文征明集》卷18《铁柯记》。
⑤c《论语·泰伯篇》。
⑥c《范文正公集》卷17《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
⑦c潜说友:《吴郡建祠奉安郡守潜公讲义》,见《范仲淹史料新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⑧c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①d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
②d朱文杰:《东林党史话》,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③d段玉裁:《经韵楼集》卷9《与外孙龚自珍札》。
④d吴志明主编:《无锡县工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⑤d程以正主编:《江阴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⑥d童书业:《南画研究》,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①e引自唐振常:《关于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e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③e唐茂松:《论吴文化的“水”性》,载《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④e《晋书》卷58《周处传》。
⑤e参见拙文:《南北士族之争与吴文化的转型》,《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⑥e陆游:《渭南文集》卷3《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①f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②f参见严迪昌:《徽人与近四百年吴地文化》,《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③f沈括:《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④f引自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⑤f邹衡:《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周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①g王鏊:《姑苏志》卷35《氏族》。
②g参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