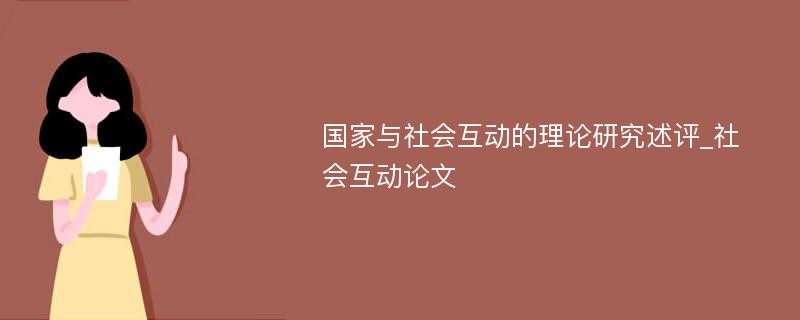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通过国家-社会二分法来看待问题,认为国家与社会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打破了这种二分的视角,以米格代尔(Joel S.Migdal)、埃文斯(Peter B.Evans)、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与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①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超越了传统二分法对单方面的片面强调,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对国家权力和作用的认识转变,对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世界有着重要影响。
一、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主要内容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核心是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合作关系,强调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发生作用;在分析方法上,主张对国家与社会这样过于宏大的概念进行分解,将国家与社会看作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交织。此理论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即“国家在社会中”与“国家与社会共治”。
“国家在社会中”研究取向以乔尔·米格代尔为代表。1994年,米格代尔主编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第三世界中的控制与转型》一书,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冲突、适应及创造,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的研究方法。2001年,米格代尔出版了专著《国家在社会中:研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形塑和相互建设》,对“国家在社会中”进行了理论总结。②“国家在社会中”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中的国家主导论在方法上和解释力度上都存在不足。从方法上看,米格代尔认为,“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统一整体,将国家拟人化,看作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采取理性行动,这种分析方法掩盖了国家形成过程和社会中争夺控制权力的斗争的复杂性,因此需要打破国家一体化的概念,来分析国家的不同部分如何与社会不同部分发生联系。从解释力上看,他认为国家中心论不能解释第三世界国家有的能实现国家目标,而有的失败这一现象,在“强社会、弱国家”的地方,国家贯彻自己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正如米格代尔所言:“至少对于第三世界的社会来说,国家中心的研究方法就像在谈论着老鼠夹,却对老鼠一无所知一样。”③概括而言,“国家在社会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国家与社会的“关联程度”影响国家的有效性。国家概念被分为“理论上”的国家和“现实中”的国家,在理论上,国家具有独立的作用;但在现实世界,国家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角色,也不是自主于社会的力量。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并不能决定国家的能力,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能力有时候导致的是“强”国家,例如快速工业化国家;但有时候则导致的是“弱”国家,比如很多非洲国家。因此,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交织关系才能决定国家的能力和有效性。
其次,需要对国家概念进行分层。米格代尔提出,要对国家采取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将关注点从国家高层转向国家的不同部分,尤其是国家组织结构与社会相接的国家底层,将国家分为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析。他认为国家自上而下可以分为四层:最高决策中心,指的是国家机器顶端的最高行政决策者;中央政府,指的是国家决策的神经枢纽,它制定国家政策、安排资源的分配,并对最高决策中心负责;地方政府,包括地方的政府部门、立法团体、法院、军事和警察机构,它们在一个固定的次国家范围的区域内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制定并执行地方政策;执行者,指的是直接面对社会执行国家政策的人员,例如收税员、警察、教师、士兵以及其他直接执行政府规定的人员,他们直接与社会打交道。由于国家组成部分的多样性,因此对同一问题很难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每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自身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反映了不同行为者基于不同压力下的不同行为的集合。因此,米格代尔指出:“当我们问国家的自主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问的是在哪一级是自主的,因为不同层级所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④
再次,社会呈现网状的结构。社会由不同的力量组成,包括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和社会运动等观念联合体,它们的权力来自组织内部的等级结构、符号资源的使用等。社会力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心理等领域为争取对社会的主导权而进行联盟或竞争。
最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多元性。“国家在社会中”规避了国家-社会零和博弈,指出国家与社会互动可以达致四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是整体转型,即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导致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第二是国家与现存社会力量合作,即国家吸纳新的组织、资源、符号和力量,使它可以对现存的社会组织进行控制,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第三是现存社会力量改变国家,即或者国家控制社会力量,但没能建立一个新的统治模式,或者产生了新的统治模式,但是由非国家的力量占主导;第四是国家未能有效整合社会,这将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表现为第二和第三种模式,即国家与社会处于相互形塑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国家在社会中”指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那么,国家中心论者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共治”则直接指向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这一取向以彼得·埃文斯为代表。1995年,埃文斯发表了专著《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深深嵌入社会的官僚体制;⑤1997年,埃文斯主编了《国家与社会共治:发展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一书,对一系列国家与社会共治的经验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⑥提出国家与社会共治理论就是指国家与社会、公与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公民参与可以加强国家力量,国家制度可以建立一个促进公民参与的环境,二者互为条件,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国家嵌入社会或者让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实现国家与社会共治。
这一理论主要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提升理论问题。在《嵌入性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中,埃文斯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提出了批评,指出经济转型最成功的国家往往是官僚体制与社会嵌入最紧密的国家。⑦他对两种类型的国家做了区分,即掠夺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前者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置于集体利益之前,国家无法阻止领导人追求个人利益;后者的官员是具有韦伯意义的理性官僚,他们赋予国家“自主性”,国家也嵌入一套具体的社会纽带中,这些纽带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为国家目标和政策协商提供制度性渠道。埃文斯认为既有“嵌入性”也有“自主性”的国家才称得上发展型国家,也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
此外,拉姆(Wai Fung Lam)对台湾灌溉系统的研究和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的研究也指出了国家与社会建立制度性关联的重要。⑧拉姆的研究指出,台湾灌溉体系的成功就是建立在这种嵌入性关系上的。灌溉协会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嵌入在当地社区,他们有的在本地成长,有的原来就是当地的农民,如果工作失职,就会受到当地人的指责。这样,协会官员力求与地方农民合作。一方面官员需要农民的地方性知识、对灌溉设施的维护、捐款和义务劳动来完成灌溉任务,另一方面,农民也需要地方官员确保水能够传送到当地,在农民和灌溉协会官员中形成了一种互相的需要。奥斯特罗姆则比较了巴西东北地区城郊的用水和卫生服务以及尼日利亚的小学教育两个项目中的公共服务,研究结果发现,巴西的地方官员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公共服务,并制定了共同管辖规则,这比全部由政府承担公共服务更加有效;而尼日利亚的个案表明,在殖民地结束以前,尼日利亚由村庄承担当地的小学教育,但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结束以后,小学教育收归公有,排除了地方参与公共教育的机会,结果由于国家资金紧缺导致小学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此奥斯特罗姆指出,公民参与可以提高国家的行动能力,形成公私之间的合作。
在以上经验研究基础上,埃文斯对国家与社会共治进行了理论总结。⑨他把国家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即国家提供私人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来培育人们的合作,这些产品可以是无形的,比如法治、公开性、技术改进等,也可以是有形的,例如交通、基础设施、技术推广等。这些无形或有形的物品可以提高人们的合作能力。第二种是嵌入性(embeddedness),即指政府官员参与社区的日常生活,通过塑造自己的社区成员身份,获得社区成员的信任和认同。埃文斯指出,互补性和嵌入性之间并不矛盾,嵌入性需要以公私之间的分工为前提,即政府和社区团体负责不同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互补性需要嵌入性来保障,也就是需要建立国家与社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范和信任。埃文斯的分析指出了国家在公民合作能力建构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缺少国家的参与,传统的互助组织和关系网络并不会自动转换成现代的具有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因此,国家可以建立机制使传统的信任关系向现代合作理念转换。
两种取向都看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国家在社会中”看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指出韦伯式定义的国家观将国家看成一个连贯统一、有目标导向的整体,但这种定义仅存在于理论中。现实的国家是由多种不同部分组成,这些部分相互促进,或相互冲突,因此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预示着我们最初的分析立场最好避免国家主义倾向,避免使国家和社会对立,而是将国家看成社会中的一部分;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则认为,市场经济不意味着市场可以离开国家机构独立运转,官僚机构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相反,国家嵌入在一套具体的社会纽带中,这些纽带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为目标和政策的协商提供制度性渠道。不同的是,它们对国家的预设存在差别,“国家在社会中”理论强调社会的主动性,主张“最小化”的国家,米格代尔指出,“国家在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社会对国家的部分“俘获”,社会能人通过让自己或亲属担任政府职位确保国家资源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也即社会利益团体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⑩因此,米格代尔认为强国家的首要条件是国家与社会分离。与“国家在社会中”不同,埃文斯并不否定国家的力量,相反,他不赞同最小化国家的假定,他认为,“除了战争和维护秩序外,引导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作用。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多少,而是国家以何种方式干预经济”。(11)尽管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它们互相交映,共同为国家与社会互动提供了基础。
二、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经过短暂的“市民社会对抗国家”路径探索后,大部分学者逐渐接受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观点。正如邓正来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大陆论者那里,更多地被设想为一种基于各自所具有的发展逻辑和自主性而展开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种能否成为实现民主政治的可欲的基础性结构;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中国大陆论者来讲更是一种目的性状态,从而他们的研究多趋向于对此一状态的构设以及如何达致这一状态的道路设计。”(12)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对国家与社会的讨论从强调社会团体独立于国家的作用转移到社会团体与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出现了很多探讨国家与社会团体良生互动的研究,(13)如法国政治研究院让·菲利普·贝加(Jean-Philippe Béja)指出的那样,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民社会强调通过政治运动来改变政权性质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公民社会则主要是作为一个第三部门在与政府合作中维持社会稳定。(14)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在中国首先应用于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治结构的研究。许慧文(Vivienn Shue)指出,强大的社会团体可以和强大而具有弹性的国家并存,也就是说“强社会”并不一定意味着“弱国家”,可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互相赋权,但是,没有嵌入社会的“强”国家事实上是脆弱的,不能经受社会变迁的考验。她指出,1949年后,国家对社会生活全面控制,但也造成了社会的细胞化(social cellularization),社会在按照意识形态分类组织起来的同时,也被分割成无数小的和互相割裂的细胞。农村集体化将农民限制在小的无所不包的生活与劳动单位中,自由贸易受到限制,农民没有与超出集体化以外的社会发生交往的机会;在城市中,人们的生产和消费也被限制在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单位中。这种格局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一端是政策制定的最高层,一端是直接执行政策的地方官员,在这中间则是各级很少拥有真正权威的行政组织。人们用“庇护网络”和“地方保护主义”来适应这种细胞化的组织结构,导致私人关系网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社会组织和政治的实际运行逻辑是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正式动力则来源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国家的社会逻辑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脱节。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遭到地方庇护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侵蚀,不能收集到制定政策所需的信息和进行政治动员,同时,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使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一种仪式象征,脱离了日常关系,导致国家与社会的日益分离。因此,改革前中国社会政策的失败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计划经济或国家权力过分强大导致的,而且是因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契合。(15)
除了对全能主义的中国国家能力进行再思考以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后的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分析,例如戴慕珍(Jean C.Oi)对地方法团主义的研究。戴慕珍在对财政改革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理论,她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并将这种政府与经济结合的新制度形式称为地方法团主义。她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构成中国乡村工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16)
随着20世纪90年代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基层民主问题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王旭用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的理论对中国的村民自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村民自治是在国家领导下进行的民主改革,但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权力结构?基层民主改革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有什么作用?围绕这些问题,王旭考察了农村政治变迁的动力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形塑关系,指出村民自治是国家为了解决农村改革后乡村面临的合法性和治理危机而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通过村民自治,中央的改革派与普通农民之间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给农民民主权利来限制地方政府,表现为一种“三明治策略”(sandwich strategy)。(17)村民自治的结果导致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一方面,村民扩大了参与地方政治生活的权利,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农村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王旭认为,中国民主改革将突破这种工具性意义,对更高层民主产生影响:国家出于基层管理需要而进行的工具性改革将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渐进的政治发展,社会力量逐渐向国家渗透,并且最终限制国家的专制权力。
与此同时,社会团体在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产品中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人们所认同,部分学者采用国家与社会互相增权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团体发展。郁建兴用“国家在社会中”理论分析了社会团体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从“政府的助手”变为“政府的合作者”,它们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一方面,国家以特别的方式对民间组织进行管理,将其整合进政府系统,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也借用某些特殊的形式来获得合法性,如主动引入国家符号和进入国家正式体制参与公共决策。因此,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带来了政府组织的扩张,只不过这种扩张方式不再是行政命令,而是一种基于利益表达基础上的有组织的服务。(18)顾昕对改革开放后的专业社团的分析也指出,国家对专业社团空间无所不在的穿透和无所不能的控制已经不复存在,专业人士自发组建专业性社团的常规性合法渠道已经存在。国家在专业性社团空间的发展中不仅维持了控制,而且还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因此,当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在实现从全能性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变的过程中,把更多的服务递送工作转移给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时,将可以出现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局面。(19)此外,为了检验国家与专业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顾昕等学者对中国的社会团体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浙江、黑龙江省和北京市2858个社团为对象,分析了中国社会团体的独立性、民主性和代表性与其公共服务效能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研究结果发现,那些自主性强、民主治理良好的民间社团组织与其“政府服务效能”并不冲突,从而表明社会团体的自主性与公共服务作用并不矛盾,社团可以充当政府的助手。(20)很多国外学者通过考察社会团体的发展来揭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托尼·塞奇(Tony Saich)提出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团体的“协商关系”模式。(21)通过对中国社会团体行动策略的分析,托尼·塞奇指出,由于国家政策执行能力下降,一部分社会团体使用各种策略来规避社团管理条例对社会团体的严格限制,例如登记成企业或者以其他的社会组织为掩护等,另一部分社会团体则通过和政府建立协商关系,影响政策制定过程或政策制定日程,如中国计生协会、自然之友和妇女协会等。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强调国家的主动性,托尼·塞奇指出社会团体并不是被动的,它们也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并与国家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
如果说以上研究着重的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实体性关系,那么“过程-事件”则是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应用。(22)“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认为,以往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都是静态和结构性的,比如“强国家、弱社会”或者“弱国家、强社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屏蔽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和具体表现。他们要追问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因此,这一取向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试图从中看到“潜在的因素是如何被激活的,衰败的东西是如何得到强化的,散乱的东西是如何重组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个过程中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23)“过程-事件”方法引入了“策略行动”分析,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化”和“实体化”倾向,展示了国家与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权力博弈的动态场景。
从中国现有的相关研究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正处于发展时期,出现了大量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但总体上而言,现有研究主要着重于借用现有理论对中国语境下发生的问题进行解释,满足于对既有理论的应用,缺少对理论的反思,尤其对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权力边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机制、国家与社会互相赋权的条件等理论问题还欠缺深入的探讨,研究还存在很多有待完善之处。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大量的经验事实将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也预示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注释:
①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eter B.Evans ed.,State -Society Synergy: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 Elinor Ostrom,"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Coproduction,Synergy,and Development",in Peter B.Evans ed.,State -Society Synergy: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pp.85-118.
②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 and Society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③④Joel S.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rologue,p.16.p.17.
⑤⑦(11)Peter B.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⑥⑨Peter B.Evans ed.,State-Society Synergy: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
⑧Wai Fung Lam,"Institutional Design of Public Agencies and Coproduction:A Study of Irrig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Elinor Ostrom,"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Coproduction,Synergy and Development",both in Peter B.Evans ed.,State-Society Synergy: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pp.11 -47; pp.85-118.
⑩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88-92.
(12)邓正来:《导论: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经》,《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13)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郁建兴:《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Bruce J.Dickson,Red 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03; Jonathan Unger,"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Sep.1996,No.147,pp.795-819; Scott Kennedy,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4)郎友兴、陈剩勇:《非政府部门与中国地方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非政府部门与中国地方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2006年6月。
(15)Vivienne Shue,"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in Joel S.Migdal,Atul Kohli andVivienne Shue eds.,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65-88.
(16)Jean C.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Dec.1995,Vol.144,pp.1132 -1149.
(17)“三明治策略”是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在对墨西哥民主化运动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将推动墨西哥民主化改革的行动称为“三明治策略”,即农村中的草根组织、对政策实施能产生实际影响的体制内改革派以及国家与社会中的改革反对派三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前二者结合起来抵制后者,从而推进民主进程。有学者对中国基层政策执行的分析也涉及这一概念,见Kevin J.O Brien and Lianjiang Li,"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2,Jan.1999,pp.167-186.
(18)郁建兴、吴宇:《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第148页。
(19)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第2期。
(20)顾昕、王旭、严洁:《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开放时代》2006第5期。
(21)Tony Saich,"Negotiating the State: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61.Mar.,2000,pp.124-141.
(22)强世功:《惩罚与法治——中国刑事实践的法社会学分析(1976—1982)》,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论文,1999年;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年;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
(23)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中国农村中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