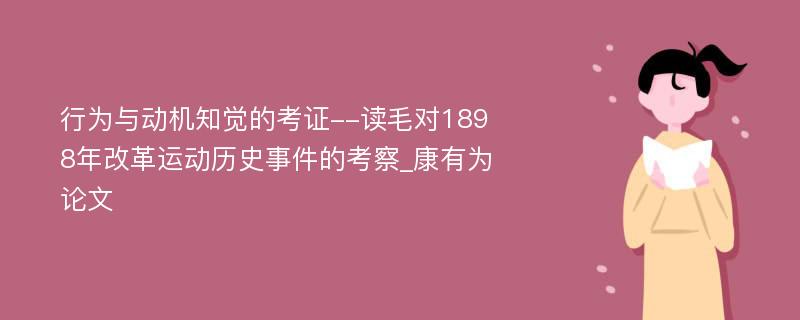
考证行为,体察动机——读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动机论文,茅海建论文,史事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教授的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以下简称《史事考》)。我对于戊戌变法史只略知皮毛,当然不能对书中的诸多学术观点妄加评论,但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中国近现代史学术期刊的专职编辑,拜读之后,确也产生了不少联想——想到了近些年所看到的一些来稿和论著。故此文只能算是一篇读后感。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园地中,戊戌变法绝对说不上是处女地。远的不说,近五六十年来,先是作为“三大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是作为近代化“四个阶梯”的一级,被众多专家反复耕耘,只是这几年似乎有些冷。我主观揣测,这种“冷”也许是因为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试想,研究者“无惑”,又焉能热得起来?于是,人们就经常能看到一些边边角角、偏而又偏的题目,读起来颇感“食”之无味(那些“小题大做”,从小题目中开发出大意义的文章除外)。但茅教授竟写成一本洋洋52万言之大著,而且在我看来,提出并解决了许多有深度的学术问题。由此我得到一个启发,就学术研究而言,拓荒固然是一条途径,但精耕熟地更可能高产。就是说,新题目容易做出新意,但也容易“浅”;而做老题目,虽说不易出新,可一旦做出来了,有时会很“深”,能揭示一般人不大容易看出来的东西。
《史事考》所提及的研究论著甚多,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成果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茅教授严谨的学风。他说:“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第162页)这是实话,但“往上爬”三字也并非可以轻易做到。《史事考》在涉及前人研究时,不但介绍论点,而且列出论据,甚至分析其论证的“理路”,即是在什么样的范式或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看出论点、论据均非难事,而看出论证理路却并不容易,因为原作者往往并不明言(甚至其本人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近年来史学界提倡学术规范,但相当一部分论著只是粗略地提到已有观点,连其论据尚未涉及,何论理路!在我看来,这个理路才真正是“先进者的肩膀”,如果连肩膀也没有看到,又怎么往上爬呢?走笔至此,我想说明一下,下文提到的戊戌变法研究,对于哪些是前人的贡献,哪些是茅教授的新贡献,在《史事考》中区分得十分清楚,而我为了行文的方便,尽归于茅教授名下,祈读者鉴谅。另外,《史事考》在做出判断时用词严谨,极有分寸,而我在转述时很可能未体会出茅教授的深意,将只有七分把握的猜测说成有十分把握的断言。所以如果想了解他的观点,还是要读《史事考》。
一
《史事考》对史料极为重视,而对档案的重视又远过于私家著述或野史。关于私家著述,史学界有所谓“所见、所闻、所传闻”的说法,“所见”指作者系当事人或目击者,“所闻”指同时代人的记载,“所传闻”当然就是后人做的了。史料价值随时间距离的拉长而趋低,但即使是当事人的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如有些宫闱秘史,作为外人的野史的作者,写出来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他何以知之?因此对私家著述,纵使合情合理也不可遽信。《史事考》第51-56页考察的“荣禄调兵”一事可作范例。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将之由按察使晋升为候补侍郎;初三日,康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并派谭嗣同去袁处商谈此事;同日,荣连发三电给总署,称英俄将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大沽”,并调动聂士成军,又电令袁马上回天津,“整备听调”。实际上,英俄将开战、英舰泊大沽全是假的。于是,康有为、梁启超、苏继祖、赵炳麟皆称,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遂造此谣,并准备以武力制袁。荣谎报军情、调兵、令袁回津事实俱在,时间、事理均合;康、梁等人即使不算当事人,至少也比一般的“时人”更了解内情;四人立场不同,分别记述,而皆称荣禄造谣。有了这些,后来的研究者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自属顺理成章,但先是黄彰健,后是茅海建却不满足于此。《史事考》首先在时间上做文章,认为荣禄在得到袁晋升消息的同一天与其部属(聂士成等)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上海道蔡钧都有类似电报,即使荣能够控制其部属,从事理上讲也无力控制依、蔡二人;荣一边造谣,一边又要求总署以此谣言诘问英国公使,这在情理上不通;荣若造谣,便不会随即派员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更何况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乡闲居的杨度就信以为真,连康有为本人也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之作为论据。故而结论便是:“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
如果是研究观念史、思想史,野史恰可作为反映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文学作品亦有其用。不仅如此,即便是做政治史研究,私家著述亦有其用,如可作为补充证据,也可作为推断历史真相的线索。特别是研究者可以将档案与各种野史结合起来,或相互印证,或依据档案,“纠正私家著述中没有根据的种种描写”(第137页)。梁启超曾说,光绪帝在八月初有过“引袁以自卫”(即凭藉袁世凯的兵力来对抗慈禧太后)的打算,《史事考》第45-51页考证了史实是否如此。首先,茅教授经考察后认为,慈禧太后很可能知道光绪帝晋升袁世凯一事,且政变刚发生,袁就被畀以重任和大权,这说明慈禧太后在此前已了解并信任袁;其次,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一般变化,算不上超擢;最后,光绪帝对康有为利用袁世凯“围园劫后”之谋并不知情。综合以上三点,再联系到光绪帝在召见袁世凯的前一天曾交给杨锐一道密诏,其中有“不致有拂圣意”(即不可违反慈禧太后之意)的话,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说法不确。不过事情还没完,光绪帝虽无武力对抗慈禧太后之意,但其“引袁”却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根据是,袁之晋升,品级变化虽小,而由此有了上奏权的意义却不小。且光绪帝在上谕中特别强调“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意欲何为?《袁世凯日记》称,光绪帝在接见他时说,“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又意欲何为?考虑到袁世凯部本为荣禄所节制,两人私交也不错,于是在档案和野史的层层迷雾中,光绪帝“引袁”以便直接控制武装力量的意图便显露出来了。就此而言,梁启超的说法并非全属空穴来风。
茅教授在谈到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史的记述时说,其中“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第21页)。康有为对历史常有“改篡”,这已几乎尽人皆知;实际上对于其他私家著述亦须小心;再进一步说,对于档案也不能大意。问题不仅在于对档案文本本身的误读,还在于研究者通常需从文本出发做进一步的推理,可谓一步错,步步错。下面引四例以证此言不虚。第一例,有研究者在谈到宋伯鲁、徐致靖、王照请开懋勤殿的三件奏折时,将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解为呈递给光绪帝,初二日由光绪帝发下;茅教授则解为呈递给慈禧太后,并由慈禧太后发下。这三件奏折十分重要,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二日之前是否看到了它们当然也很重要(见第41-42页)。第二例,军机处有多种档册记录上谕,有研究者忽视了这一点,因《上谕档》八月初三日未记载某两道上谕(实际上载入了其他档册),便错误推断“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取代光绪帝亲自发布上谕和裁决日常政务”(见第65页)。第三例,据内务府“黄记载”,慈禧太后八月初六日从西苑返回颐和园,这本为事先安排,后来并未实行,但有研究者将“黄记载”误作事后记录,遂将此误作已然发生的事实(见第119-120页)。第四例,《穿戴档》主要记录皇帝的穿戴并附带记其行止,如果没有换衣服,有些政务活动经常不记,有研究者忽略了这一点,乃由此推断从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就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见第128页)。以上四例中的研究者都是熟谙清官档案的专家,他们尚难免出错,何况我辈?这里需要补充一句,《史事考》对于档案的解读当然也可能有不确之处。
在《史事考》的“自序”中,茅教授对于查阅档案的人数逐渐减少颇为感慨:“从拥挤到冷清,我虽目睹了阅档室的变化,但经常找不出此中的答案。”(自序第1页)我想,这其中或许有急功近利、不愿坐冷板凳的因素,但问题肯定不限于此,否则,如若坐几个月档案馆的冷板凳就可以产生一篇有创见、有分量的研究报告,档案馆恐怕就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了。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讲法:“让史料自己说话。”这句话恐怕有问题,如果史料自己就能自截了当地告诉研究者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么“史才”、“史识”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学术研究的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了。实际上,档案是实时、实地形成的工作记录,并不是专为历史研究者准备好的现成答案,研究者需要从看上去毫无联系的散乱文献中寻觅出蛛丝马迹,进而依情理、事理和“道理”把它们勾连起来。“自己说话”的史料类似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可能有价值,也可能没有,而判断的标准就是有效的证据,尤其是合乎逻辑的证据链。《史事考》在考证1898年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与清廷中枢调整人事结构的联系时(第186-195页)曾提到:“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非得南皮(即张之洞)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楠‘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这显然是一条“史料自己说话”的好材料,但茅教授却认为不大可信:“证据有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此事由杨锐出头,必会密告张,而从张后来得到电旨后不知所措的行为来看,他没有得到预报。”在否定黄说的同时,《史事考》利用清宫档案和《翁同龢日记》、《张文襄公全集》等另起炉灶,展开了迂回曲折的论证。第一步是分析朝局,奕病重,翁同龢权势太盛,清朝上层权力结构不和谐。第二步讲保守的徐桐不满并担忧这种局面。第三步讲徐在一个月后又上折请严谴张荫桓,“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以此阐明徐的前一折别有深意在,即“以张驱翁”。第四步讲慈禧太后考虑了三天才做出决定,以揭示“兹事体大”,不是一般的督抚来京陛见。第五步引翁同龢的话“盖慈览后,圣意如此”,表示光绪帝顺从慈禧太后之意。第六步,述清廷再三催促张之洞尽快启程。最后一步,一个多月后,翁已去,王文韶、裕禄入军机处,人事调整完毕,不再需要张之洞入京。《史事考》兜了一大圈,结论与黄尚毅的说法类似,而可靠性大大增加。茅教授曾说,有人认为考证不需要想像力,这是误解。我介绍上面的例子也是想说明,由于档案的“工作记录”之性质,其对于考证历史问题的价值往往藏在深处,要利用之,熟悉和技巧固不可少,而想像和推理的能力尤为必要。
《史事考》不仅发掘档案文本下面的“隐义”,而且发掘档案没有说出来的话。在第134-137页茅教授考察了政变后不久的两件朱谕,一为无头无尾、语多零乱的光绪帝“朱笔”,一为军机大臣据“朱笔”拟就的明发上谕。经过比较,后者提到的康有为等人的罪名绝大多数出于朱笔,惟一的例外是前者无而后者有“围园劫后”之说。茅教授的推论是,光绪帝并不认可此说。再举一例。茅教授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两份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文字记录,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另抄一份?他认为,很可能是呈送给慈禧太后的;而这又进一步证明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回西苑就是针对这次觐见,目的不在训政。
二
《史事考》对于时间特别重视,仔细想来这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在戊戌年七月底八月初,政局动荡不定,几乎时时在变化;二是因为此书论证十分严谨,这就要求论证逻辑要严密,而时间天然的就有逻辑性,比如,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不能分身两地。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章中,往往不大注意这种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对于文化史研究这或许尚可接受,但如此做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则肯定要出问题。一个事件就是一个过程,发生在前的无疑要对发生在后的产生影响,前者因此就成了后者的原因或条件(这里是讲同一个过程),如果将前后次序颠倒了,读者难以索解事小,改变事情的性质或因果关系事就大了。若用发生在此时的史料来证明发生在彼时的事情,字面上虽可理解,但必会曲解历史过程。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同的历史现象无论多么相似,总还是不同的,至于人的思想和意识更是时时在变。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时间对于政治事件史研究的重要性。据康有为自己讲,八月初三日他接到光绪帝密诏后始决定发动“围园劫后”,那么,光绪帝与此计划是否有牵连?慈禧太后初三日突然决定次日回西苑与此计划是否有关?这两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史事考》先考察了光绪帝离开颐和园的时间,又考察了慈禧太后做出突然决定的时间,之后着手考察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起止时间(这是康党发动其计划的关键)。茅教授不但分析了相关人物如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及毕永年等的说法,还进而考察了袁的住处和康、梁等候谭从袁处回来的地点及两个地点间步行所需时间。做完这些,证据链就形成了:“梁启超与袁世凯记录的时间恰是完全相同,即谭嗣同造访时间为傍晚,离去时间为深夜。康有为的记录证实了谭嗣同回到金顶庙的时间,而毕永年的记录证实了谭、康、梁当晚的行踪。”(第91页)而结论是,慈禧太后的决定与谭访袁无关。关于光绪帝是否知道康党的计划,茅教授着重指出,“康谋”是在八月初三日做出的,而光绪帝在初二日以后再未与康党联络,这样,若讲光绪帝知情便会违反时间的前后顺序。我以为,茅教授这种考证方法类似于数学的反证法,举重若轻,值得提倡。
“围园劫后”是天大的事,足以促使慈禧太后回城发动政变,但既然她当时并不知道此计划,又为何突然决定次日(八月初四)回城呢?《史事考》(见第86-101页)同意一些研究先进的说法,是为了监视光绪帝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但茅教授的着眼点是做出决定的确切时间,意在说明慈禧太后的决定虽反常而突然,却又不是十万火急。首先,他指出,慈禧太后撤帘后住在颐和园,没有特殊理由不回西苑。其次,慈禧太后回城是一个大工程,“此次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此外还要惊动众多的衙门,光绪帝也要准备“跪迎”,所以至少要提前数日做出计划安排。第三,由于以上两点,慈禧太后于初三决定次日回城就是反常而突然的,必有重大刺激才会有此反应;遍寻之后,杨崇伊奏折成为惟一可能的刺激源。第四,“还宫的决定似在晚上8点半至9点做出的”。第五,慈禧太后尽管打破惯例,前日晚决定次日早还宫,“但也说明慈禧太后感到并无燃眉之急。若真有关系其权力和命运的大事,她也会打破一切常规,当晚回西苑的。”为说明这一点,书中特意指出,慈禧太后在次日回城途中,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还去万寿寺烧了香,所用车马凌晨3点已准备完毕,至下午3-5点才到西苑,“看起来她并不着急,显得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从这一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不仅能重建史实,确定因果,还能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却又不是虚构的小说家言。
“当晚回西苑”五个字,“当晚”讲时间,“西苑”则讲空间;就像这里的“时间”一样,这里的“空间”也不仅仅指物理的空间,而且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意义。在第81页茅教授写道:“所有的军机大臣进退都是经过慈禧太后的,他们拟旨时,一定会感到慈禧太后从远处射来的目光。”从有形的“实体”的角度看,慈禧太后不在场,而从无形的“意识”的角度看,她又“在场”;“在场”与否,不能只看物理方面,也要看心理方面。就是说,在《史事考》中,空间不只是用来计算距离的远近和行程所用时间,空间本身就有政治意义。近代史研究中经常要提到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范围”二字就有政治意义,现在社会史研究常讲“社会空间”(如所谓“祭祀圈”),我觉得或许可以借用过来,造一个新词:政治空间。
当然,物理的空间毕竟起着基础的作用,这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自光绪二十年起,慈禧太后常住颐和园,光绪帝常住宫中。两地相距15公里以上,单程需用时间,光绪帝是3小时,慈禧太后则为5小时以上。但据茅教授统计,在光绪二十四年,从正月到七月二十八日,两人同住或同处的日子占了2/3以上。他们贵为皇帝、太后,为什么要不辞劳顿,兴师动众地跑来跑去?因为“在重大事件上,光绪帝须请示,须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第33页)。就是说,尽管光绪帝为慈禧太后所控制,但他毕竟是皇帝,如果慈禧太后不在身边,“不在场”,他仍有可能独立做出重大决定;而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天子口含天宪,就不可挽回了。例如,“百日维新的重大决策及高级官吏的人事任免基本上是在光绪帝住园期间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到慈禧太后的身影”。惟一的例外是发生了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用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的七月十九、二十日,“而这两天发生的光绪帝无视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威自行做出的重大人事决定,也被一些研究者敏锐地认定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索”(第35-36页)。实际上,慈禧太后准备何时回宫、何时回园,也是茅教授判断政变进程的重要依据。为什么说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决定回西苑是针对伊藤博文而非光绪帝呢?一是因为光绪帝将在城中接见伊藤,慈禧太后必须回城才能有效监控;二是因为光绪帝按计划要到初十日才会到颐和园去,而慈禧太后则准备初六日就回园,若是针对光绪帝,那么她是不会留出四五天来让光绪帝自作主张的。同理,当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在西苑要一直住到初十,然后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时,就表明她“对光绪帝不再信任,要将光绪帝置于身边”了(第93、113页)。
由此可以看到,在《史事考》中,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其物理的表面下都有活生生的人。相反,有些文章之所以写得干巴巴,毛病似乎就在于见事不见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衣食住行,尽可入史。在《史事考》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书中多次提到“看戏”。看戏可以揭示政治内幕:第93-94页指出,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四日离开颐和园前还不忘安排中秋节在园连唱三天大戏一事,可证明当时她并无训政的打算;第138-139页指出,她在八月十三日最终将中秋节听戏地点改在西苑,“慈禧太后再一次推迟回颐和园的时间,正是她感到了(训政之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她亲自来做”。看戏也可以揭示人的内心:第83页详述了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看戏的情况,从上午10点多一直看到晚上8点半,除了太监戏还外请戏班演了六出,以说明她从容不迫的心态;第161页则引用了十二月十一日的一道慈禧太后懿旨,称今后光绪帝即使是要几件乐器也需经过她的批准,茅教授没有解释此事说明了什么,联想到正在紧锣密鼓策划的废立之事,这道懿旨或许表明了她的刻毒吧。充分利用帝后的“生活档案”,不但可补政治档案之不足,亦可从更多的侧面来了解研究对象。与政治文献相比,使用生活记录或许更费周折,更麻烦一些,但似乎也更牢靠一些——慈禧太后安排在何时何地听戏,既无必要造假,理解起来一般也没有歧义。
三
《史事考》指出:“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接着,他又指出:“我不能肯定阅档室中的人数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专业的方向风标,但可以肯定地说,阅档室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史实重建工作的加强。”(“自序”第1、2页)这两段话无疑都是对的,我在读《史事考》的过程中经常感到,我过去所获得的关于戊戌变法的知识往往或似是而非,或模糊不清。但另一方面,我对于茅教授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史实”——的含义又有些疑惑,它只是指人的行为呢,还是也包括人的动机(本文中“动机”一词,既指行为的动力,也指行为的目的)?我想,茅教授这个词当同时涵盖两个方面。在《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一文中,他开宗明义便表明:“我个人的学术企图是能够真正听到中下层的声音,其先决条件是要尽可能地把声音听全。个别人的说法可能会多种多样,但多听却可能让听者产生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并从中体会他们的内心,以识别他们在高调或低调背后的动机。”(第220页)
人心难测,比不得行为;如果史料真实而具体,那么,行为是可以确切“测量”的。而动机则不然,研究者不知道其研究对象的表白是否真诚;即使真诚,我也怀疑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人能否准确道出其在采取行动时的心理状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可知道,第一,对自己动机的述说或分析总是在行为之后,是回忆或推测而非实时的记录;第二,行为时的心绪总是变化不定的,而对于这种心绪的回忆却往往条理清楚。正因为人心难测,所以有的研究者采用了类似行为主义的办法,把内心世界当做一个“黑箱”,只研究输入和输出(即看得见的行为),不管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过这个办法在历史研究中恐怕不行。一般而言,在数学中,一加三等于二加二,在历史中,甲、乙两个因素作用的相加永远也不会等于“丙”的作用的两倍;在数学中,一加二等于二加一,在历史中,因果关系也永远不能颠倒。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讲新话,讲自己的话,不能像工厂批量生产纸杯。这就需要有研究的深度,否则就只能在评价上做文章了;而深入开掘的办法之一就是体察人的内心世界。
我粗粗想了一下,体察动机对于考证行为至少有三个用处。首先,可以帮助研究者判断某项行为之有无。有研究者提出,荣禄曾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了慈禧太后。茅教授认为,此说不成立。这不但在时间上难以说得通,更重要的是,荣禄作为督抚大员,冒巨大风险微服私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向慈禧太后报告康党“围园劫后”之谋,那么,慈禧太后得报后必会马上采取行动,“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如果为了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又“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为了“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而不必冒此风险(第117-118页)。总之,由于找不到实行这一行为的动机,所以这一行为本身很可能就没有实行。搞历史研究的人常讲一句话:说“有”容易说“无”难。只要有证据,我们就可以说某人做了某一行为,而说没有可就难了,我们永远不能说所有的行为都留下了证据,更不能说这些证据都被我们看到了,因此我们也就永远不能说既然我们没有看到证据,某事就没有发生过。通过对动机的分析,固然我们仍不能有把握地做出断言,但至少可以做一些有根据的猜测。我想,这类似于刑事侦察中根据某人是否有做案动机来判断他是否系嫌疑人,锁定怀疑对象当然不等于破案,但却有助于破案。
其次,体察动机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行为的含义,以使我们理解行为。在前述的例子中,荣禄电令袁世凯返津、调动聂士成部的行为,随其动机的不同,既可以理解成是为了“防袁有变”,并调兵“以备举大事”,也可以理解为误信传闻;而究竟做何种理解,又会影响研究者对整个政变进程的认知。不过,历史是复杂的,动机也是复杂的,决定一个行为的通常不会是非此即彼的单纯动机。八月初二日,光绪帝有一道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赶快离京赴沪。茅教授分析了光绪帝通过此上谕所要达到的目的:“光绪帝在此谕旨中向慈禧太后表白处有三:其一是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其二是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是一次……其三是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第62-63页)光绪帝发布上谕是单独的一次行为,而形成它的动机(或目的)却是由三部分组成。我想,这些年来史学界发生的许多争论,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对行为的看法不同,而是在于对动机的判断有异。最终能否消除围绕动机所产生的争论呢?我以为不大可能,动机藏在深处,研究者都是依据事情的表象在猜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所有研究者都应遵循的准则,但即使都遵循了也仍不会意见一致,只是能够创新,能够对话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争持不下也还是比不敢触及动机要好。学术研究就是要深,不深就难以出新。
最后,研究者可以利用动机将看似毫无关系的散乱行为连接起来。这个作用看上去不如前两个作用有价值,其实不然,因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更广地说,人们认知的目的)就是给纷繁的现象建立联系,理出头绪。《史事考》第149-153页摘引了政变后的八月下旬内务府奉宸苑有关工匠事务和外请工匠的部分记录:二十三日,在瀛台(光绪帝住在此地)四扇门安门栓、钉钌铞;二十四日,在瀛台赶修四座供下等人住的木板棚房,更换北海水闸的闸门;二十五日,将瀛台涵元殿的楼梯及瀛台所有建筑的门座全部“堵砌”,将南海北岸的部分土堤改为“墁砖甬路”;二十六日,四扇门外再搭建木板棚一座;二十七日,将淑清院(珍妃的寝宫)北门、瀛台前两楼梯堵砌,更换北海水闸闸板、清淤泥、安铁箅。这些看上去没有头绪的行为如果与当时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帝,要加强对他的监控的动机联系起来,顿时便有条有理了:建木板棚是为了供新增的监控人员使用,安门栓钌铞、堵楼梯门座是为了限制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通道,换闸板、清淤泥等是为了防人潜入,土堤上墁砖是为了方便巡逻。总之,要使光绪帝的一举一动尽在慈禧太后的掌握之中。第160页还引了一条奉宸苑十一月十九日的记录:奉旨,自即日起,每天都要派人将瀛台周边水面上的冰打掉。沿着以上的思路,此举自然还是要隔断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写到这里,我联想到了那些只谈行为、不涉动机的论著,其同奉宸苑的记录颇有几分相似,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历史档案或是大事记。
四
如果说是“动机”(或者更宽泛地说是“思想”)决定了行为,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行为者的思想呢?一种保险的办法是止步于此,就像只描述行为而不探究动机一样。在特定的学术目的下,在某些研究条件下,做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合理的,一个研究者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对于一个问题也难做到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不钻牛角尖”应成为历史研究者的诫条。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已经在惊呼“确定性正在丧失”,数学与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历史研究?但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去探索是什么东西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动机的问题,这同样是智者所不为的。
探寻决定或影响动机的因素大抵有以下诸种取径,其一是从利益(趋利避害)方面进行解释,唯物史观大体上均如此,尽管其内部还有种种差别。这样来分析历史问题当然有道理,人在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他们在不停地感知环境,确认目标,选择手段,算计着、权衡着利弊得失。其二是从文化方面解释,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等等。这种方法基本上把人的思想意识看作一个整体,虽说也承认其中有种种矛盾;其弱点是不太好解释同处于一个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之间的差别,比如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其三是从人的性格、经历方面去解释,这种方法更多地强调了人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方面,有非理性的色彩,与第一种方法形成对比。在《史事考》中,这三种方法都有使用,根据情况或单独运用或综合运用。如第45页说:“就慈禧太后的性格及以往的处事方式而言,其一旦提出了对光绪帝皇位的警告,不会只言不做,而将会调整她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不过,我现在想着重强调的不是上述三种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影响行为者动机的因素,而是在政治史研究中显得比较突出的一些特殊因素。这些特殊因素是我在阅读《史事考》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所以十分凌乱,没有系统的归纳。第一种或可称为“资历”或“资格”。在第211页茅教授写道:“到了这个时候,百日维新渐渐进入高潮。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激进主义言论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担心,康有为及其党人力图进入政治中心的努力也受到了京城高官的集体抵制。”这里谈到了两方面的斗争,即思想方面和权力方面(即利益方面),但我以为,对后一方面不应泛泛地理解为一般性的权力斗争,而应更确切地理解为部分“小臣”与所有“大臣”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如书中多处提到的,康有为等“激进派”的方案是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出的议政机构的基本特点是,人员不受品秩的限制,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为政治咨询机构,实际上将是政治决策机构。”(第43页)张元济被目为维新干将,他在七月下旬曾上奏,首先提出的就是设立议政局(第276-277页)。根据我的理解,他的议政局方案就是,由他们这样的维新“小臣”充局员,制定政策,然后“请旨施行”;施行者则是大臣(京城为各部院,外省为督抚);若施行不力,轻则申斥,重则罢黜。也就是说,小臣决策(光绪帝成了他们的保护神和傀儡),大臣执行。激进派的这类主张不仅受到“大臣”们的抵制,还遭到“缓进派”小臣的反对,在《史事考》所提到的三个缓进派“代表”中,就有两个谈及“大臣”“小臣”的问题。“四川大挑教职万科进上书称:‘于中外三品以上大员……选用数人,置之帷幄枢密之地……’万科进的上书很长,看不出任何背景来,但他的建策对康有为一派很不利,康有为、张元济、李岳瑞等人不过是主事,谭嗣同等四章京也只是四品卿衔,‘三品以上’实际将他们开除在外。这也可能是当时人心目中‘德望可以服众’者的最低品级。大学堂提调、翰林院编修骆成骧上书中称:‘臣窃谓求人才于小臣之中,尤当先求人才于大臣之中……’这一段‘小臣’、‘大臣’之言论……明眼人一看即知是冲着康有为及其党人而去的……他的实际用意,似用‘新进’好称的‘议会’之术,选出‘新进’以外的‘大臣’来主持新政。”(第281-282页)在七月下旬开始再起的召张之洞入京的呼声中,“资望亦深”、“老成硕望”、“老成重望”之大臣,和“尚需阅历”、“德望又不足以服众”之新进小臣,几乎被每一件上书同时提及。这种大臣、小臣之争,我以为与政治的特点有很大关系。政治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等级森严的,所谓“科层制”,顾名思义便有上下级的意味在,上级支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若不是这样,其顺畅运行是难以想象的。在晚清的官场中,权力固然总是问题的核心,但资历和品秩却是权威及合法性的基础。康有为之类的小臣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虽不能说一定不可行,但肯定会阻力重重。
在晚清政治格局中,特别是中枢权力结构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名分”。在第38页,茅教授对光绪帝同慈禧太后的权力关系讲了一段很精当的话:“在光绪帝面见慈禧太后时,须将重大政治决策和高级官员任免,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惟一的例外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和任命军机四章京,对此慈禧太后事后虽为不平,但无法推翻光绪帝的‘擅自’决定,只能在礼部新任六堂官的实授上表示其态度。在胡孚宸劾张荫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也就是说,光绪帝对慈禧太后负责,而整个国家机器须对光绪帝负责,尽管慈禧太后也不时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国家机器的运作。”与“负责”相应的就是权力,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有权力,但至少在形式上对整个国家机器却没有权力,这个形式上的权力在光绪帝手中,而其来源就是“名分”,或者用茅教授的话说就是“体制”(他在本书别的地方也用过“名分”一词)。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决定改由她而不再是光绪帝来审查军机四章京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的意见,在猜想慈禧太后这样做的动机时,茅教授谈到了体制:“且司员士民上书中,什么样的意见都会出现,正如杨锐在私信中所称‘万不可行之事’,而一旦形成旨意,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是难以更改……于是,慈禧太后将此类‘签拟办法’接手过来。当然这是我对慈禧太后心态的主观推测。”(第81-82页)这个“名分”直到政变完成之后仍旧起到了某种作用。《史事考》写道:光绪帝“依旧做朱批,不过只是例行,不见实际内容。他也亲自参加皇朝的各种仪礼,接见召见和引见的官员。在慈禧太后的注目下,他空有皇帝的名号,而不再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第160页)我想,从权力的角度说,他的这个名号确是“空”的,但从“名分”的角度说又不是“空”的。后来,废立一事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江南官绅那么强烈的反对(与这些官绅对清廷的“尽罢新法”只有微弱批评形成很大反差),“君臣之义已定”一语传播得那么广,似乎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政治运作中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规律性现象,这在戊戌政变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在百日维新中,绝大部分重要奏折(包括司员士民上书)要呈送慈禧太后,绝大部分的重要决策也须在事前经过她的同意,这些在《史事考》中做了坚实有力的证明。但问题是,政变后她为什么要搞180度的大反动?而且,这个反动是逐步加强的。“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而且在所发谕旨中有四道“似乎还给人以新政继续进行的印象”。初七日的谕旨“也还算是平和。”“八月初六日、初七日两天的政令表明,慈禧太后虽开始对光绪帝、康有为进行清算,但仍在权力层面,尚未进入政策层面。”“十一日,下旨恢复原被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取消司员士民上书权,撤销时务官报,各州县小学堂由各地官员酌情办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此时不仅是权力上进行清算,而且在政策上进行了反攻。”(见第122-130页)这种现象似乎不是偶然的。有研究者指出,在1927年以后,国民党将大革命时期曾实行过的许多“左”的政策逐步抛弃,越来越“右”。毛泽东讲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刘少奇似乎也讲过,中共的政策就是“左”一下,“右”一下。在物理学中有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我觉得,在政治领域也有类似现象:要打击激进派就势必依靠保守派,从而就要施行保守的政策,这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不能从最高决策者的思想中得到完全说明的。
政治领域中还有一种不能仅从思想角度去解释的现象,我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圈子”。“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句话为人们所熟知,但党派的形成并不完全以思想为基础。政治运作的机制,需要有决策、有执行,有首倡、有呼应,有核心、有外围;于是一个个“圈子”就形成了,其基础和源起有思想,有利益,有个人恩怨,甚至有偶然。“后党”、“帝党”、“康党”的形成恐怕都是如此。对张荫桓,慈禧太后必欲除之,但张有何激进思想?党派对其成员有时还能形成极大的约束力,康党流亡海外后,政治主张出现很大分歧(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利益纠纷也不时发生,但“保皇党”的名目仍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成员要想挣脱束缚相当困难。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在政治领域似乎也是如此。
近来常常见到“互动”一词,读完《史事考》后,我觉得戊戌变法完全就是一场政治的互动。慈禧太后、光绪帝、康有为、袁世凯这些戊戌舞台上的主角们带着自己的理性和对未来的算计投入其中,而博弈的结局却大大超出了他们理性的算计。我想这是互动的根本特性,即历史变化超过了人们的“计算”能力,尽管他们总是在争取掌握未来。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说过,历史研究就是史学家与史料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对话也是互动,是古人与今人的互动,因此一个有创见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之始恐怕也无法预知最后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一文的最后,茅教授写道:“三年多前,当我决心对戊戌政变作一考察时,以为我的报告大约一两万字就可以结束,且很有可能一无所获;而今完成如此烦琐考证的长文,依例必须做一结论时,却又发现,我虽在细部上多有新见,但在总体结论上,仍是一无所获。”(第161页)这当然是谦辞,但我相信有一点是真的:茅教授在开始研究时并不能准确预知他最终具体能收获到什么,“龙种”?“跳蚤”?关于史观与史料孰先孰后的争论已经几十年了,我想,研究的过程也许是,带着问题和一些或模糊或清晰的假设进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不断推翻或修改自己的想法和结论,最后,所得结果与最初的预想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了。我这篇小文当然不能与茅教授的大作相提并论,但就我的感觉而言却有类似之处,我原来想说的话有许多没有说出来,而另外的许多新冒出来的话却被写在了纸上;而且有些话已远离了《史事考》的论题,会给人(包括我自己)以“过度诠释”之感。这可能是第三种互动,读者与研究论著的互动吧。但现在再想回到原来的“我”已不可能,只有请茅教授和读者批评指正了。
标签:康有为论文; 戊戌变法史事考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茅海建论文; 慈禧论文; 光绪帝论文; 清朝论文; 袁世凯论文; 瓜尔佳·荣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