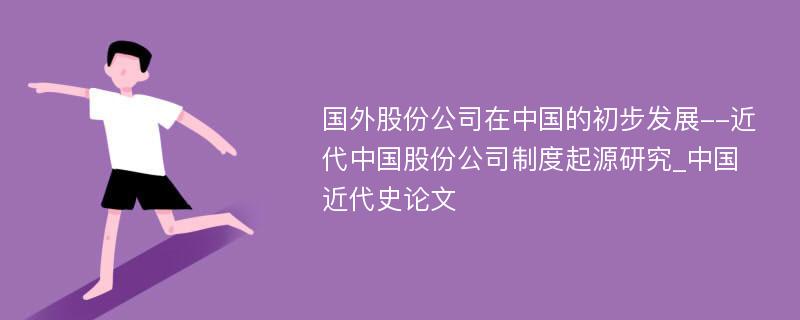
外商在华股份公司的最初发展——关于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起源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份公司论文,在华论文,起源论文,外商论文,最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1-0094-07
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早期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变革,近年来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前辈学者汪敬虞先生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书中关于华商在外商企业附股的研究,是关于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多篇论文问世。进入新世纪,《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等专著先后出版。上述论文和专著对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的起源方面,微观的探讨尚不多见。学术界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公司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而然地”①传入中国的。事实上,历史的发展不会那么简单,股份公司进入中国并最终与华商资本结合形成规模效应,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了股份公司在中国的制度形态。
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外贸易方式的变化和外商代理行的衰落
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度于鸦片战争前进入中国,主要存在于两个行业中:一是垄断中外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王特许成立的专营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的整个东方地区贸易的垄断公司。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从此与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贸易关系。二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保险公司。1805年,广州保险社(Canto Insurance Co.)成立,这个保险社由达卫森·颠地洋行和比尔·麦尼克·渣甸洋行轮值经营,无论哪个洋行经营,均采用股份制[1](P157)。其后在广州成立的其他保险公司均步广州保险社之后尘,采用股份公司制度。
东印度公司是英王特许垄断东方贸易的半官方组织,它只与清政府特许的广州行商进行贸易,而不直接与民间商人打交道。它的总部和董事会设在伦敦,广东的商馆只是派驻中国的一个管理机构和决策执行机构,其职能由公司的商船大班充任,“平常大约有十二个大班……由三四个资格老的人员组成一个主任和监管委员会——被散商们讽刺地叫做‘监委’——充任公司在中国业务的管理机关,执行伦敦董事会的指示”[1](P16)。这说明它的职能不涉及公司的资产所有权,也没有资产处置权,因而不负责公司股金的筹措和盈利的分派以及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所以,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不具备募股的职能。
保险公司与东印度公司不同,它在资金筹集上从一开始就同华商发生了联系。1835年,英商宝顺洋行在澳门成立于仁洋面保安行,“立即有许多中国商人认购它的股票。怡和步其后尘,1836年在广州成立谏当保险行,一些中国资本可能一开始就加入”[2](P283)。但是,保险公司并不是外商在华经营的主业,它只是外商出于分散运营风险的需要,为外商在华经营的主业——贸易业——服务的辅助性业务。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一般都不大,能够吸收的华商资本也都很有限,因而没有在中国商人中产生广泛影响。
除上述两种实行股份公司制度的经济组织外,广州还存在另一类外商经济组织,这就是专营东印度公司以外的港脚商在华委托代理业务的代理行。这些代理行大都叫做公司,但在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资金筹措上并不实行股份公司制度,而是实行合伙制,叫做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或封闭式公司(closed company)。代理行的资金规模一般都不太大。以美国旗昌洋行为例,这是一家老牌洋行,其前身老旗昌早在1818年就已进入中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它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洋行。但它的资本通常只有十几到几十万美元,“即使在业务发展到最高峰时的19世纪50年代,它的合伙资本总额也不过50万美元”[3](P4)。正是这类外商经济组织,在鸦片战争后环境和条件变化带来的压力下,最先大规模向华商募股组建股份公司,从而搭起了股份公司制度深入中国经济社会的桥梁。
鸦片战争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给代理行带来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19世纪中叶,世界范围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给中外贸易方式带来了显著影响。首先是运输工具的革命。1809年,轮船运输首先在美国投入使用。但直至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对华贸易的运输工具仍然是飞剪船也就是木质帆船。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轮船性能的不断改进,帆船被淘汰的速度不断加快。1842年,英国轮船“魔女号”(Medusa)驶入上海港,这是最早进入上海港的外国轮船。此后驶入中国水域的轮船不断增多。至1848年,已经有了在中国水域定期航行的航班。轮船加入航运,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中国的航行时间。“纽约到广州仅用九十天的快速航行记录也已经成为历史了。大英火轮船公司的轮船从伦敦开到香港只用六十天的时间,若从纽约起航,也只要再加上十五——二十天也就够了。”[4](P224)
此外,运输航线也缩短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到东方来须绕道南非好望角。19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条叫做“苏伊士旱道”或“苏伊士地峡通道”[4](P229,234)的连接欧亚大陆的捷径,“朴鼎查爵士在一八四一年乘轮船来到澳门,麻恭少校(Major Molcolm)在一八四二年乘轮船携带南京条约到英国去,两人都是取道苏彝士横跨大陆的路线,这两件事都被认为是有特别重要性的。在一八四五年,大英火轮公司为从英国扫桑波敦(Southanpton)到香港的每月快班船采取了这条航线。”[5](P386)这条道将绕过好望角的航程大大缩短了。
通讯工具也发生了革命。电报发明于18世纪中期,但其真正具有使用价值是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1844年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架空电报线路。此后电报的发展非常迅速,“六十年代初期,和远东的电报联系有了进展”[4](P225)。东西方的信息交流成为瞬息可至的事。
轮船、电报的使用和苏伊士运输线的开辟对中外贸易方式的影响是革命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中国市场行情的变化,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货物运进运出中国。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着中外贸易的方式,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华贸易成为可能。
其二,19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代理行的传统业务产生了影响。经历了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市场呈现饱和状态,经济过剩危机不断爆发,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这一切,使得西方资产阶级除了急欲开拓海外市场外,越来越倾向于直接的贸易贩运。旗昌洋行主要投资人P·S·福士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这种情况时说:“在美国的许多重要委托人,如波士顿的威廉·阿普尔顿(Wm Appletom)、纽约的格里斯沃尔兹(Grisworlds)这些原先经营对华贸易的主要人物或是病故,或是脱离商业,而接替他们的新人,则把业务搞得分散了。英国委托人也是这样,他们的利润资金来自贸易顺差的盈余,一向以此支付从美国购进的大部分商品。这时他们开始觉察到,同样也可将这项盈余用货物的形式运往美国以换取美元。他们热衷于装运货物去纽约。”[3](P5)福士是站在代理商的立场对直接贸易进行抱怨,但这从反面清楚地说明,跨过代理行的直接投资趋向的发展,对传统的代理业务产生了巨大威胁。
其三,鸦片战争后外商在华贸易格局的变化给代理行的经营带来了挑战。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人蜂拥进入中国。据统计,1837年在华外商为307人,1855年激增至1038人,增加了两倍半之多。新的洋行也不断设立,由战前的一百五十余家增加到1855年的219家[5](P389)。然而,西方对华贸易并没有像西方商人希望的那样迅速增加。开埠后,输华英货曾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呈现猛烈增长的态势,但很快就消失了。从1846年起,英国输华商品量开始减少,一直到1855年的10年间,除1851、1852两年外,始终没有达到1845年的水平。美国对华商品输出也呈现了与英货相同的停滞不前甚至减少的状况。这种增加不算太多的贸易额,由增加过多的洋行来分享,显然是僧多粥少,要获取巨大的利润是不可能的。“对华贸易的盈利,过去本来是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享有的,现已被分散到许多公司之手。商业大王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的梦想了。”[4](P239)
上述变化使洋行的代理业务越来越难开展。旗昌洋行合伙人金能亨说:“我想我们正不觉落入一场大变革中……我看到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已失去,我环视周围,寻找谁还有那些业务。琼记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洋行也都没有代理业务。各方都正依靠自己去经营……业务变得如此复杂,使代理人难以胜任。”[2](P259)代理行的生存发生了危机。
面临生存危机的代理行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否则必将被淘汰。“1856年10月5日,金能亨在写给旗昌洋行主要负责人P·S·福士的一封信中建议:旗昌洋行应当考虑开展新的业务……总之,我们必须赶上时代。”[3](P5)资财雄厚的大洋行开始主动转变经营方针。怡和洋行自60年代开始将航运、保险、汇兑等过去的从属业务项目放到更重要的地位[4](P279)。琼记洋行发现“辅助性服务业反而更赚钱”,搞银行业务,搞保险及搞贸易以外的其他经济辅助工作,“无一项不是生财之道”[4](P248)。但是,对大多数中小代理行来说,自营贸易并非易事。代理行大多财力有限,“因为它们是凭借发货人的资本来经营的”[1](P133)。“它只需筹集足够的资金为远方的委托人预付在中国购买茶叶与生丝的货款就行了。”[3](p4)“他们的资本只够冒一年两三船货物的风险”[2](P259),根本不敷自营贸易之需。摆在代理行面前的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固守旧业,但面临败亡;要么改弦更张,但资金短缺。大多数代理行选择了后者,但必须寻找获得足够资金的新途径。
二、从旗昌轮船公司的创立看外商在华商中的募股活动和股份公司的出现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轮运、铁路、电报、纺织等资产规模越来越大、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行业和企业不断涌现,耗资巨大的产业已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窥伺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资源的新工具。代理行要扭转颓势、实现效益最大化,必须在这些领域谋求发展,同时实现资金筹措的制度更新。
在寻求新的资金来源的过程中,代理行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运用已久、驾轻就熟的中外商人合伙经营。洋商与华商的合伙经营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初,“1806年11月,比尔和麦尼克租了‘安娜·菲利克斯号’(Anna Felix)船,大概是悬挂西班牙旗,同一个居住在广州的泉州商人合伙装载一船印度原棉到厦门,‘这个泉州商人指望在他的一个(住在厦门的)亲戚经营之下,这会是一笔很有赚头的买卖’。”[1](P44)虽然后来这笔买卖没有做成,但至少说明,早在19世纪初西方商人就已知道依靠华商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了。
鸦片战争后,洋商与华商的合伙经营继续存在。60年代以后,随着代理行经营方针的改变,合伙经营的规模日趋扩大。不仅资金匮乏的小洋行需要华商资金上的挹注,就是怡和、旗昌、同孚、琼记等大洋行也几乎都采用过与华商合伙经营的方式。但是,在这种合伙中,合伙对象只是一两个商号或几个商人,合伙的性质是临时性的。一般只适用于一次生意,贸易结束就结算盈亏,分摊盈余或债务,合伙随之结束。下次贸易开始,则重新商定合伙条件,就合伙的资金、经营的品种、分担的份额以及盈利的分配达成协议,新一轮合作开始。因此,它无法满足需要巨额资金的规模化经营。
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在华商中大量募集资金始自上海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俗称旗昌轮船公司)的创立。旗昌洋行的代理业务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急剧衰落。旗昌洋行上海经理金能亨极力主张改变旗昌传统的业务方针。1861年1月,金能亨对旗昌洋行的前途作了一番筹划,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主张将该行的财力集中起来,在中国长江水域经营轮运业务。
此时恰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西方侵略者刚刚通过中英天津条约获得了长江内河航运权。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长江上中国传统的木帆船贸易几乎中断。上海至汉口的运费高得惊人,货运运价每吨高达25两,客位每人75两,往返一律。一条轮船往返一次的运费收入,即足敷船价成本[6](P96)。金能亨看中了长江航运的优厚利润,他企图通过开办轮船公司使旗昌实现起衰振兴。
但问题是,旗昌洋行怎样筹措这家轮船公司的资金呢?金能亨根据在上海获得的信息估计,“购买三艘身长300呎的明轮,总共需支付48万美元”[3](P9)。以当时旗昌自身的财力而言,根本无法支付这笔巨额款项。因此,金能亨和旗昌洋行在中国的另一重要合伙人、香港经理沃伦·小德拉诺都认为应当采取个人认股的方式筹集资金[3](P11)。
旗昌洋行有着长期利用华商资金的历史和经验,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同行商伍浩官关系密切,并在资金上得到了伍浩官的支持[3](P9注1)。鸦片战争后,伍崇曜入伙旗昌,由自挂牌号的行商成为旗昌洋行的投资人[7](P233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伍氏家族面临破产,不断从旗昌洋行抽走资金,金能亨转而依靠上海新兴的买办华商的支持。
在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之前,轮船航运业中已有华商附股。进入60年代,轮船航运业中的华商附股逐渐多起来。但是,这些认股以入股某一条船为主。金能亨的做法则不同,他要组建的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更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企图以后能够控制长江航运。他认为“旗昌洋行如果能够立即购买船只开办轮船公司,能在极短时期内取得长江航运的统治地位”[3](P8)。
为了劝诱华商入股,金能亨采取了吸引华商的措施:一是以一条船作示范吸引华商入股。既然要成立的是轮船公司,那么轮运是否有厚利可图当然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为了打消华商的疑虑,金能亨将“一艘可以赚钱的轮船从广州开到上海加以整修,并和中国友人合股经营,共享厚利……后来金能亨说:‘我虽然自己承担风险,但没有独享利润,一俟轮船顺利航行,我就把所得利润分给中国人,为了争取他们参加到旗昌轮船公司这个更加宏伟的规划中来。’”[3](P24)。
二是轮船公司的经营以便利华商为准则。既然轮船公司未来的大多数股东是中国人,那么就应当考虑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和经营方便。旗昌洋行充分注意了这一点,它在上海沿江靠近华人商业区而不是租界的极佳地带购得地产,“像金利源码头的地址,就紧靠上海县城”。显然,这是非常打动华商的举措之一,因为这在“本地发货人的心目中被看作是旗昌轮船公司的最大特色之一”[3](P23)。旗昌洋行在成立旗昌轮船公司的倡议书中规定,旗昌轮船公司所属各仓库对公司的股东将给予按比例分红的优待条件。这样,就可以减轻股东在埠际之间的贸易费用。“按照这一制度,各个股东除了支付仓库实际费用和运费外,别无其他开支。”[3](P25)这种实际利益的引诱,显然会促使任何一个华商认真考虑投资其中的可能性。
通过实施这两项措施,旗昌洋行成功地争取到了大量投资者。1861年8月,旗昌洋行已完成原定32万元的认股规划。但是,“金能亨仍不满意,认为开拓业务的机会还没有充分运用”。“在1861年8月至1862年3月这几个月中,他成功地进一步筹集到100万美元资金……1862年3月27日,拥资100万两(相当于135.8万美元)的旗昌轮船公司终于正式成立了。”[3](P21)在这100万两资金中,华商的投资占了绝大部分。曾任旗昌轮船公司早期主要职员与船长的伯尔声称:“华人是这个企业的最大业主,旗昌洋行只拥有该公司不到三分之一的股权。”[3](P26)至此,旗昌洋行终于实现了将企业经营“向前推进一步”的转变。由于获得了大量华商资金的支持,旗昌轮船公司在以后数年的发展中实现了对长江航运的垄断。
旗昌轮船公司的做法,使许多急于摆脱困境的外国在华洋行在山重水复的窘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在旗昌轮船公司即将宣告成立的前夕,英商天祥洋行(W.R.Adamson & Co)企图利用华资组建一个名为中日轮船公司的股份公司,公司计划招收资本30万镑,首次发行15000股,每股10镑,特别为中国保留2500股。作为公司代理的天祥洋行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广泛征求入股者[4](P284-285)。1865年10月,由美国琼记洋行任总代理人的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kong,Canton and Macao Steam Boat Co.)开始营业,这家公司共集资75万美元,分为7500股,每股100美元[4](P287)。华商资本在这家公司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从公司成立,大英火轮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的买办郭甘章就是公司的董事。终19世纪,华商股东都是公司一支稳固的支持力量[8](P487)。1867年7月,上海英商轧拉佛洋行(Glover & Co,1869年以后改称Glover,Dow & Co.)主持人格罗母(F.A.Groom)发起“组织一家专门从事长江航运的轮船股份公司”[3](P79)。公司计划集资2000股(后来增为2040股),每股白银100两[4](P290),实收17万两,由上海的中外商人认购,“华人也许是其中最大的股东”[3](P79)。第二年,英商惇裕洋行(Trautmann & Co.)①代理的北清轮船公司宣告成立,股本30万两,共600股,每股500两。实收资本194000两,共388股,其中1/3的股份为惇裕洋行所有,1/3为唐廷枢所结识的华商所有,其余为各行员和上海的其他外商所有[4](P295)[3](P89)。从1870年起,老牌英国洋行——怡和洋行也开始积极酝酿组织轮船公司。为了广事招徕,怡和洋行除了利用侵华多年与华商建立的关系在华商中大事招徕外,还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有中文广告,也有西文广告。1872年10月,由怡和洋行总代理的华海轮船公司(又译东海轮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宣告成立,额定资本50万两,分5000股,每股100两。怡和洋行的大肆活动显然在华商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公司第一批入股的4600股中,华商股份竟然有935股,占到了20.3%[3](P174)。
随着股份公司在航运领域的产生,有大量华商附股的股份公司相继在银行业、保险业、出口加工业、船舶修造业,以及公用事业等行业中出现,股份公司制度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最终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了由中国人自主创办股份公司。
三、外商在华股份公司的制度变异
随着大量华商进入外商在华组建的股份公司,一些原本并不属于西方股份公司的制度安排相继出现,使股份公司这种典型的舶来品在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改变了原生形态,出现了种种制度变异。
其一,股银分期缴纳制。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规模化大生产的产物。在股份公司诞生之初,已经充分考虑了小额资金的存在和投资需求,因而将募资数额划分为尽可能小的股份,使人持有小量资金即可投资。除公司创办人和初始股东认购公司最低股本时有最低限额外[9](P79),公开募集股本一般不采用分期缴纳股本的方式。但是,这种制度来到中国后却发生了嬗变。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最早采用股银分期缴纳制招募股本的是华海轮船公司,其招股告白曰:公司“资本五十万两,分五千股,每股一百两。派股日先缴十五两,三月后再缴二十五两,再三月后又缴二十五两,其余待用时先行关照,一月再缴”[10]。
股银分期缴纳制的出现显然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观念的结果。19世纪中叶乃至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刚刚开始解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国家,国贫民穷,民间并不存在一个十分庞大的富有阶层,不可能有太多的资金投向新式工商业。人们的观念还比较落后,窖藏银风气盛行,并不认为购买股票是保持和增殖财富的有效途径。股份公司要站稳脚跟,必须破解这两个难题,而股银分期缴纳制的出现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摸索了一条可行的实施路径。
这项制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制度发展早期的一项重要变革,对以后中国股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为外国在华洋行利用华资组建股份公司所采用,而且为其后发展起来的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以及民办企业所采纳,为中国民族工业广泛集聚资本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官利制度。所谓官利制度,是指在企业利益的分配上无论盈利与否,必须支付给股东的股息,利率一般在5%-10%之间。官利制度起于何时目前尚缺乏研究,郭郛、陈家晓两位先生认为:“官利”一词早在中国封建时代就已出现,“韩愈在《论变盐法事宜状》一文中就使用过‘官利’这个字眼”[11]。杨在军、张岸元两位先生认为,早期外国在华股份公司就有类似官利的制度[12]。但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官利制度最早开始于1872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③。实际上,在轮船招商局酝酿实施官利制度的同时,华海轮船公司也将官利引入了企业利益分配制度,并且率先向公众发布。同治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72年10月31日)的华海轮船公司广告称:“所有本公司溢利,每年一结,先提官利一分,次放积贮十万两,然后按股分沾。”[4](P297)轮船招商局的官利制度最初见于朱其昂主持制定的《招商局条规》。这个条规制定的时间,根据樊百川先生的考订是在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五日(1872年11月5日)上呈,十一月初九日(12月9日)李鸿章批准施行[13](P234),略晚于华海轮船公司。考虑到两个轮船公司均设在上海,二者在制定官利制度的时候,很可能相互影响,互有借鉴,互有启发。
官利制度本质上并不属于股份公司制度,除了不必还本外,其性质更接近债券制度,即无论企业盈亏,必须年年付息。这样,企业股东相对企业而言就具有了债权人的身份。显然,官利制度是股份公司来到中国后的外生制度,反映了中国社会资金匮乏对股份公司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制约。而官利制度正是突破制约的制度创新。
关于官利制度的评价,学术界研究已经较多。笔者一直认为④,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工业发展的早期,官利制度的实施利大于弊。一方面它对于启动投资市场、为企业筹集急需的资金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使企业背负了沉重的成本负担,使产业利润成为借贷利息以上的余额,大大延缓了企业资本积累的进程。但是,在中国新式工业刚刚诞生的时候,在资金筹集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其积极作用显然大于消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官利制度出现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刚刚启动的阶段的重要原因。所以,官利制度一经引入新式工交业,就对其后中国股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长久的影响。直至20世纪上半叶,官利制度仍然在中国许多股份公司中广泛存在[14]。
其三,有业务股东优惠分红制。这种制度指凡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股东,在年终分红时可以获得高于无业务往来股东的股息。这种制度萌芽于旗昌轮船公司的创立,其初衷是一种吸引投资的策略手段。其后,公正和北清轮船公司在筹备的过程中显然看到了这一策略的成功之处,便加以利用和改进。它们将优惠的范围扩大到公司全部业务领域。公正轮船公司的做法是:“有股份而不与该公司共生意者,照本钱一百两付利银十五两。……有股份而又与该公司共生意者,照本钱一百两付利银十五两之外再加五两。”[4](P291)北清轮船公司的做法是:“有股装货者,另得回用十两。”[4](P296)
这种对有业务股东的优惠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盛行的人情关系、亲缘关系有着渊源联系。在中国旧式木帆船运输业中,长期盛行一种对股东的优惠照顾制度,即股东如若兼船员,则可在船上挟带一定数量的个人私货[4](P57-58),股东在获得作为船东的投资人的收益外,还可获得直接贸易的收益。在钱庄业实行的会票号制度也属于这种性质的制度安排[15](P252)[16](P463-464)。表面看,这种关系是一种股东之间的经济利益结合,是股东之间对各自利益的关照。实质上,透过经济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基于人情的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因为在中国旧式合伙中,合伙股东之间往往有血缘关系,或有世交、世谊等人情关系,人们作出制度安排时,必定会首先考虑这种关系,否则,将会违背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信仰。当西方的股份公司来到中国时,中国旧式合伙制度的理念就会因为中国人的投资而被引入公司的制度安排,那种原本在经济意义上的股东关系必然会蒙上中国式的温情面纱。
近代中国的股份公司制经历了外商引入、华商附股、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过程。股份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出现了若干制度的变异,这说明,作为舶来品,它必须作一定调整,以适应中国本土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收稿日期]2005-03-31
注释:
①见杨在军、张岸元:《关于近代中国股份制起源的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②另一说法为德商资本,但其船悬挂英旗,经理特劳特曼(J.F.H.Trautmann)为德国人。参见《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95页;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第89页。
③见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页;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朱荫贵:《改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杨华山:《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二难困境——晚清专利与官利制度述评》,《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
④见李志英:《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的资金筹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