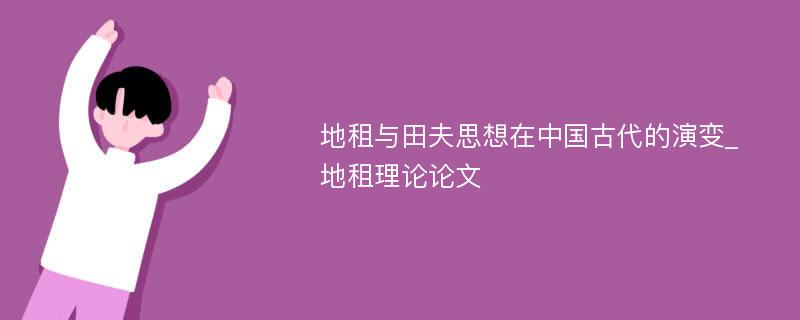
中国古代地租与田赋思想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赋论文,地租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封建社会的财富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来源,亦即主要来源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农民的劳动。地租一词,是指土地所有者,凭据土地所有权占有部分农业生产品。田赋,有时称“税”,是国家以土地为对象所课征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徭役,它是统治者为兴建城廓和宫室等工程对农民劳动力的征发。这三者课征的形式,决定于各个时代的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地主和统治者在农业生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徭役虽然在形式上不是对农产品的课征,但它是对农民劳动力的无偿征发,直接地夺去农民经营农业的劳动力,其性质与课征农民生产品相同。地租、田赋、徭役的课征,都直接地涉及当事者农民、地主和统治者三方相互的权益关系,对三方都是头等大事。从佃耕农民来说,他们力求减轻地租,地主虽然知道唯有依靠佃农劳动才能收到地租,但他们往往加重租率,于是形成地主与佃农在收入分配上的对立。统治者课征田赋和徭役,亦必须依靠农民生产和农民劳动力以及地主的收入,但他们亦常重征田赋和频繁地起征徭役,于是形成统治者与有地农民在生产和收入分配上的对立,并形成统治者与地主在农业收入再分配上的对立。不过统治者对地主课征的田赋,最终还是落在租地农民头上,因为地主常把自己交纳的田赋,通过加重地租转嫁于租地农民。所以由地租、田赋、徭役三者的课征而在农业生产和收入分配上所形成的关系,最本质的是农民与地主和统治者的对立关系。
正由于封建社会租、赋、役的课征,对于统治者、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劳动者三方在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分配上,都具有头等重要性,并存在尖锐的矛盾,所以历代凡是注意政治经济问题的思想家,莫不对于地租和赋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大声疾呼,提出政策方案。他们的见解、政策意见、以及对问题的分析,不但对当时的国计民生起过重要作用,并且对后世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有的至今犹闪烁着光辉,成为我国宝贵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地租、田赋、徭役三者,在概念和理论上,各有它自己的涵义,区分得很清楚,看起来也一目了然。但这三者的概念和思想,在我国有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在早期,思想家往往把租赋二者合为一体,不加区分,赋役二者亦常互相掺和,甚至在后期,租、赋、役三者在概念上尚存在着相互掺和的情况。这是由于我国历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因而亦成为我国封建时期地租和赋役思想的特点。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从理论上理清这些思想的产生和演变的轨迹及其特点。
(二)地租与田赋概念的合一
中国最早论述地租和田赋的古籍为《尚书》、《周礼》、《左传》等及思想家著作如《老子》、《论语》、《孟子》、《墨子》等,对地租与田赋二者在概念上都不予区分,视为一体。因而租与税二词常常连同使用。这种情形自先秦时期以至唐代中期都存在,而在先秦最为突出。在先秦,二者不加区分的最好例证是:
“初税亩”(《左传》宣公15年》)
“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秦简公7年)
“税亩”与“租禾”同包涵实物地租和田税,但一则用“税”,一则用“租”。二者连同使用的最好例证,有以下两条:
“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墨子·辞过》)
“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管子·国蓄》,注:“在农曰租税”。)
后世读者常为此二词的使用而感到困惑,但一查古代字书对此二词的训解,亦即释然。如:
《说文解字》说:“租,田赋也”
“税,租也”
“赋,敛也”
《广雅·释诂》说:“租,税也”
“赋,税也”
为什么先秦思想家对地租与土地税两个概念没有加以区分呢?回答是,这是由当时的土地制度决定的。在先秦时期,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大小领主,以及以后称为国君、贵族、爵官等,他们既是统治者,又是各辖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根据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这两种权力,对耕种土地的农民课征生产品,以满足他们在各个方面的需要。他们课征的产品,既有地租的涵义,也有土地税的涵义。而农民交纳课征的生产品,因不存在独立于统治权力以外的土地私有者,也无地租与地税之分。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人民出版社版。) 先秦思想家对地租与地税概念的不加区分,正由于此。
秦汉时期,由于私有土地制度的发展,除国家向民间课征农产品而外,还出现了豪强地主向农民索取农产品的情况。这种情况,反映在观念上,就使租(地租)与税(地税或田赋)在概念上逐渐加以区分。然而由于在汉代国有土地还占支配地位(注:学术界有估计两汉时代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之比为2∶1。见赵俪生著《中国土地制度史》第61页。)和传统思想的影响,私有土地者收取地租的形式与国家课征赋税的形式二者在概念上还不能明确分清,使得官方文书和思想家著论,对租赋概念,虽然有时分别提出,仍然时常二词互用互通,这可由下列最为著名的论述见之。
董仲舒: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汉书·食货志上》《限民名田疏》)
王莽:“汉时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疲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伍也”。(《汉书·王莽传》《王田诏》)
上引二文都明确地反映了豪强地主征取“十五”产品对分地租与国家征课“三十税一”赋税的现实情况,但在概念上仍然未对二者明白地加以区分,仍名地主征取十五对分地租为“税”。同时,国家“三十税一”,是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课征之“税”(这里是说实行减税政策,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而仍说这是“减轻田租”。对租与税二词这种用法,非仅见于上述二文,在《汉书》所载诏令及《食货志》中多见之。
秦汉以后,中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战乱频仍,人口死亡流散,土地荒芜,各代政权拥有大量无主土地,相继实行了屯田、占田、均田制度。在唐帝国建立之初,即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基础上,明令实行均田制和与之相容的“租庸调”赋税制度,并以法律形式,载诸法典。然而,由于土地所有者与主权者合为一体,租、庸、调三者各被赋予的涵义,仍然不能克服过去含混的情形。唐法典所载租庸调制如下:
《唐六典》:“凡赋役之制,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
《唐律疏议》:“议曰,输课税之物,谓租、调及庸、地税、杂税之类”。“议曰,依赋役令,每丁,租(粟)二石;调絁、绢二丈、绵三两、布输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若不役,则收其庸(庸值)每日(绢)三尺。”《旧唐书·食货志》上)
唐代名臣陆贽对租庸调制作了简明的解释,他识,这个税制是根据授田法,“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注:《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以恤百姓六条》。)从名称来说,租庸调制中的租,具有地租的概念,即它是有田农户对土地所有者国家所交纳的实物租。调是主权者国家对农户课征的税,而庸则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和主权者的权力对农民征发的劳役。这从概念上来说,无疑较过去含混地使用租税二词有所改变,但它仍未完全改变租和税合为一体的情形。这可以从租庸调三者征课的轻重上得到说明。 按照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粟价和绢价计算,租粟二石合钱2,000,绢二丈合钱 1,000,役二旬庸值绢六丈合钱3,000(注:李翔云:“初定两税时· 粟一斗盈百,帛一匹(合4丈)盈二千”。《李文公集·进士策问第一道》, 转见岑仲勉著《隋唐史》第383页注11。),庸高于租50%, 庸调合计则高于租一倍。显然租轻而庸调重。但此三者同出于授田百亩农户耕织生产的产品。三者全属封建地租性质的课征,名异而实同,事实上是统治者巧立名目,任意规定三者课征数额,以博取轻租之名。在租庸调制消亡之后,陆贽为租庸调制大唱“租轻”赞歌(注:《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以恤百姓六条》。),是由于他没有分清三者的实质及其关系。
(三)地租与田赋概念的分立
唐代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均田制的瓦解,租庸调制亦为“两税法”所代替。史载,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为相, 废除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内容是: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14 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旧唐书·杨炎传》)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户等”和“垦田”征税,其性质是财产税,是国家对于居民财产的课征,而不是国家对被授田的农户的征收。这个变革,就旧有租庸调税额并入“两税”来说(《唐会要》明确记载:“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可以大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税收体制来说,旧时作为国家税收的“租”,从此消失了。从此以后,“租”或“田租”不再视为国家岁收的组成部分,而成为地主私有土地权的经济实现。这是自先秦以来一千多年赋税制度和赋税思想一大变革,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在两税法实行之后,陆贽即称租为“私家收租”(注:《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以恤百姓六条》。)后来思想家通称为“私租”(注:顾炎武《日知录》。),以别于国家对国有土地征收的“官租”。
到了宋代,由于土地私有制和赋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租赋概念的分立更为明确起来。《宋史·食货志》记载: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原注:“己田谓之税,佃田谓之租,旧不并纳。刘豫尝并取之,至是,乃从旧法。”重点为引者所加。)
上文明确界定“租”是佃田者对土地所有者(不论官有或私有)的输纳,而“税”则是国家对私有土地者的课征。私有土地者所纳之税,是出之对佃农收取之租,税出于租,这是国家与地主共同占有佃农的剩余产品,与国有土地制下国家占有全部佃农剩余产品不同。在土地私有制产生以后,佃农只“输租”,而“免输正税”。《宋史·食货志》对“租”(地租)和“税”(田赋)所作的这一界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俱有重要意义。它不但有助于察知从先秦以来租与税二者在概念上含混不清的原因,并且提出了税与租在农产品分配上的重要关系,即增税并不一定加重地主的负担,因为地主可以用增租方式将增收之税转嫁于佃农,同时,减税并不一定有利于佃农,因为地主并不一定因减税而相应地减轻佃农所纳之租。这个问题在下面我们剖析政治家思想家的“薄赋”以及“减租”政策主张时,就更为清楚了。
(四)地租与田赋差等课征理论
租赋课征的轻重以及如何确定租赋的合理课征,是租赋问题的核心。我国从先秦以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莫不对此问题给予最大的关注。其中最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是春秋早期齐国大政治家管仲。管仲在相齐桓公(公元前685—645年)改革齐国内政、减轻农民负担时,提出了一条课征租赋的原则,叫做“相地而衰(音崔)征”。韦昭注:“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注:《国语·齐语》,又见《管子·小匡》。)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按照土地的肥瘠和产量的高低情况,区分不同等级,征收租税。管仲认为,按照这个原则征税,最为公平合理,最能发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就不会逃亡(“则民不移”)。管仲提出的这个改革原则,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大概在管仲提出这种课征原则之前,课征租税是按田亩多少而不问土地好坏的,耕种坏地的农民要和耕种好地的农民交纳同等的租额,那是极不公平合理的。管仲对此进行改革,齐国在他为相时期,就富强起来,称霸诸侯。从理论上讲,封建制下的租税,主要是课征农民的生产品。农民只有在他的生产品,除维持一家的生存和偿付再生产所需的种子等项外,还有剩余产品,才能输纳租税。当然剩余生产品愈多,农民输纳租税的能力就愈强。土地肥力有等级,产品产量有多少,随之农民纳租能力有高低。农民耕种贫瘠的土地,所生产的产品只能维持一家的生存,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就没有剩余产品可以交纳租税。根据不同肥力的土地,交纳不同等的地租,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叫做级差地租。这种级差地租是客观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只能改变地租的占有形式。马克思曾指出:“级差地租的条件,不过是土地等级的不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43页,人民出版社版。)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管仲提出的“相地衰征”原则,没有说清楚他所说的是“租”还是“税”。如前所说,在先秦时期的土地制度下,租与赋税是合为一体的,所以管仲所说的既是租又是税。这正表现他的理论的时代性。应该指出,封建社会对租赋的课征,往往超出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而侵及农民的必要产品,即为维持生存所需的产品。这种事实,史不绝书。即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曾揭露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说“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注:《左传·昭公3年》) 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上所说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强制”的课征情形。管仲所提出的上述原则,是与这种超经济强制的课征不相容的。
管仲是大政治家,仅提出了“衰征”原则,未对此原则作较多的阐述。但他提出的这个原则,却为稍后的两部著作《禹贡》和《周礼》所继承并加以发展。《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讲“任土作贡”,相传其法为夏禹所制。《周礼》中讲田制与税制之处甚多,相传为周公旦所作,二说俱不可信。近来学者认为二者都是战国时期著作。(注:顾颉刚《尚书》,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3期; 《“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辑,1979年;杨向奎, 《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上册。)。顾颉刚说,《禹贡》作者根据地理来划分区域,希望统治者对于各州的土地都能好好地利用和整治。各州把特有的物产进贡到中央,田赋则根据各州土地的肥瘠来决定等次。(注:顾颉刚《尚书》,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3期; 《“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辑,1979年;杨向奎, 《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上册。)这是对于《禹贡》篇内容所作的很好的概括。《禹贡》对于各州土地和赋税作了具体分等。它按九州土地肥瘠,分为上上以至下下,共九等,田赋高低亦如之。但《禹贡》区分各州田赋高低,不一定与土地肥瘠一致,例如雍州土地为上上等,而田赋则为中下等,冀州土地为中中等,而田赋则为上上等或上中等。这是因为《禹贡》认为赋税高低不完全决定于土地肥瘠,还有其他因素亦应计入。如距离帝都远近,运输难易,在决定田赋高低时也应考虑。雍州离帝都最远,运输困难,故田赋应轻,而冀州为帝都所在,运输方便,故田赋应重。此外,尚有各州开发先后,人口众寡等因素,在决定田赋高低时,亦不可忽视。由此可见,《禹贡》在租赋课征轻重问题上,除管仲提出的“相土”原则外,还提出了地理位置远近等重要因素,并提出了三等九则的具体等差,后世制定赋税政策者多奉为圭臬,这是我国租税理论的一大发展。
《周礼》中有多条关于地征的职文,其中所包涵的课征思想且较管仲和《禹贡》更有发展。这可由下列职文见之。
地官·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五物”谓山林、川泽等所生之物,“九等”谓肥力不同的九类土壤。)
地官·载师:“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鄙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国宅”,王城住宅。“甸稍县鄙”,距王城二百至五百里之地。)
上述职文明白地表明地征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区分土地不同用途和农地不同土壤,二是要区分用地位置的远近。这里要说明,对于位置因素,《周礼》表明对于远郊的征课,重于近郊,与《禹贡》课征原则相违,亦不合一般原则。为什么?对此,经解家的解释是,“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注:《周礼正义》,“载师”职文注。)就是说,把力役之征与粟米之征合起来,仍然是近重远轻。此外,应当指出,《周礼》提出了不同税率,这是先秦租赋思想的另一发展。先秦思想家大多以什一税率为标准税率,李悝、孟子都有论述。(注:见《汉书·食货志》记李悝文;《孟子·告子》。)《春秋·公羊传》并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周礼》则突破了此教条,根据土地位置的不同,以及作物的特殊性,而有不同税率的规定。不言而喻,在同一地区,还会因土地肥力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税率。《周礼》的租赋思想,对后世亦有重要影响。
到了地租与赋税(田赋)判分为两种不同的分取农民产品的形式以后,上述租赋差等课征原则在政策措施上和理论上亦有所发展。这最可由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实行的“方田均税”法,思想家朱熹实行的“经界法”,以及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提出的“田土等第法”见之。宋代品官豪强隐田逃税,农民负担赋税加重,官府财政收入短绌等情形,甚为严重。王安石实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有关于清理地籍,厘定税则的新政措施“方田均税”法。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丈量土地,除无地税户,正无税地产,同时以地势及土质,而分五等,以定税制。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只在北方地区推行,且为时甚暂。到南宋时,朱熹知漳州时,奏请在漳、泉、汀三州实行经界法,其内容亦为核查隐田,分等定税。他说,“今欲每田一亩,随九(九等)高下,定计产钱几文”。(注:《朱文公全集》,“条奏行经界”。)朱熹的拟议,因被罢官,根本未能实行。于此可知,王安石、朱熹的均税措施,都旨在贯彻三等九则差级课征原则,是针对国家课征赋税不遵守这个原则而提出的。国家课征田赋的这种情况,以后仍然存在,因而继续引起思想家的激烈抨击,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公元1613—1682)痛陈明代一条鞭法“照亩摊银,而不论地之肥硗,论丁起科,而不论其产之有无”时说:
“我朝成法,所以分三等九则者,正以齐其不齐而使之均也。今不分三等九则,而概以丁田之数,比而一之,第无论丁之贫富,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万,而于祖宗之旧制亦少更矣。”(注:顾炎武《户役论》,载《天下郡国利病书》。)
黄宗羲(1610—1695)对此更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理论上提出了新的论点。他论“田土无等第之害”说:
“今民间田土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画以一则,至使不毛之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种,小民但知其为瘠土。”(注:黄宗羲:《田制三》,《田制一》载《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
根据上述分析,他提出:
“是故合九州之田,以天下为利,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
“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注:黄宗羲:《田制三》,《田制一》载《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
黄宗羲指出,“瘠土”、“不毛之地”生产所得,只能勉强维持耕农生活,甚至不能偿付“牛种”,是无多余产品输纳租赋的土地(“岁抱空租”),根据这一严酷事实,他提出,国家征税不但不能“画以一则”,即不能无分土之肥瘠,并且要以无力纳税之地为起点(’以下下为则”),根据地力肥硗,重定田土纳税等级。黄宗羲提出“重定天下之赋,以下下为则”,是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我们回顾前面所述“相地衰征”和“三等九则”的课征租赋原则,对于不分田土好坏,划一按亩征税,的确具有“齐其不齐而使之均”的重要意义。但是“三等九则”原则只对田土肥瘠规定“上上”与“下下”等的相对等差,而未明确规定,凡不能生产多余产品之“瘠土”,为无租免税土地。这样,封建国家即使依据“三等九则”成法课征赋税,它也会凭借超经济强制权力对无力负担租税之“瘠土”,同样征税,纵然所征较轻。黄宗羲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明确提出租赋差等课征应明确规定“下下”等土地为无租免税土地,因为这种土地不能生产多余产品,无力输纳税税。因此,应以“下下”等土地为起点(“以下下为则”),使较此不同肥沃土地输纳差等租税。这样,就可“下下者不困,天下之势相安。”黄宗羲这一理论,为管仲和《禹贡》的差等课征理论作了必要而重要的补充,较十九世纪初期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李嘉图在级差地租学说中所提出的“无租土地”说,早一百五十年左右,它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五)薄赋与减租思想
在先秦时期,由于租赋的合为一体,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薄赋敛主张,在于减轻统治者领主对农民产品的课征,亦即反对统治者领主的横征暴敛,呼吁为农民保留足够的生存必要产品。这从孔子弟子有若反对鲁哀公主张实行重税,最为清楚。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以恤百姓六条》。)
秦汉以后,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有征税与征租之别,思想家对于二者间的关系,开始提出了问题,但尚未能进行分析和做出说明。如前引董仲舒文,他只说到秦朝田税与地租之高,而未论及二者之关系。王莽诏文亦只说,西汉景帝时,国家减征田税为三十分之一,而豪强地主所征地租则为十分之五。他把国家对地主征收之税与地主对佃农征收之租等同起来,似乎认为佃农也应享受三十税一的优惠。到东汉末期时,思想家荀悦对此有进一步理解。他说:
“文帝不正其本(谓任豪强占田逾侈),而务除租税(即减轻田税),适足以资豪强也。”(《文献通考·田赋》)
荀悦在这里已经分清“官家之惠”(轻税)与“豪强之暴”(重租)二者之不同,而主张从“限田”上来解决豪强问题,但没有进一步论述二者的关系。
首先提出减租主张者,是唐代陆贽。陆贽对由国家征收租和税的租庸调制变为国家仅征收赋税,而有田之家则能坐收地租,持反对意见。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触及税与租的关系。他说: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
“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
“望令百官集议,参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注:《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以恤百姓六条》。)
陆贽上文主要谴责私租重于官税,主张“裁减租价”,以利生产者。他在此揭示了官税和私租来源的秘密。即“私取其十”是地主征收佃农的地租,“官取其一”是国家课征地主的赋税,而地主缴纳的官税则出之于对佃农所征收之地租。官税征自地主,而实际负担者则为佃农。陆贽触及了这个问题,不过他没有对此点展开论述。
宋代以后,如前所说,租与税分立,国家向有田者征收田赋,有田者则向佃农收取地租,政治家和思想家亦从而分别专论田赋不均和私租太重问题。前述王安石、朱熹的“方田均税”等方案,即意在为国家增加税收,同时使有田者输纳田税较为公平合理。思想家由此开始着重地论述二者的关系。由于有田者的呼吁,赋税问题有时受到统治者的注意,诏令分等征税,但地租之苛重,却得不到相应的减轻。因此,思想家对此著论越来越多,并且论述越来越具体而深入。最先,南宋时王柏明确地指出农民、地主、国家三者的关系,他说:
“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庭,以之禄士,以之饷军。”(注:王柏:《鲁斋集·赈济利害书》。)
王柏明确指出国家岁课来自地主,地主输纳则来自农民,农民是赋税的最终负担者。这种关系在元代省臣的奏议中,有进一步的说明。《元史·成宗记》中说:
“至元31年(公元1294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田税)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贫民也。宜令佃民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
这是说,地主有时可受到国家减税之惠,而农民交租如故,受不到减租之益,受惠者只是地主。这种情形,顾炎武说得更为痛切。他说: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故既减粮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注:顾炎武《日知录》。)
顾氏之言,触及到税与租的根本问题。即佃民“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的情形。这是榨取佃民生存必要产品的重租。顾炎武认为如果地主输纳粮税已经减轻,而租额征取仍旧不变,则更表现地主榨取佃农之暴虐。这个道理,在19世纪中期吴中士人陶煦(1820—1891)著《重租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禹贡》定赋,首列九等,而取民者祖之。租亦取民也,赋诚有是,租亦宜然。”
“赋有九则,而租独一例。试以吴江之下下田而论,纳一升五合之赋,而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此尤事之不平者矣。”(注:陶煦,《租核》(1884年),内《重租论》成书较早。)
上文明确地指出,田赋和地租都取之于佃农。但国家对地主征收田赋,尚多少按照土地等差原则办理,而地主对佃农收取地租,则不论土地好坏,即使是“无租之地”,亦一律收租。即作者所说,“赋有九则,而租独一例”,是最不合理的事。他举吴江县之实例说明,下下田本是无能力纳租之田,即属于“无租之地”,自亦属于“免赋土地”,但吴江县佃种下下地的佃农,每亩要纳“一石有余之租”,而地主则纳“一升五合之赋”。地主收取一石有余之租以后,缴纳一升五合之赋,地主自然仍能获得重租之益,但佃农要在无力生产地租的下下地上交纳一石有余之租,则除交纳维持生存的口粮以及乞贷外,尚有何法?陶煦此文不但指出地租与田赋同取之于直接生产者农民,说明了田赋与地租二者的内在关系,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封建地主经济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残酷地剥削佃农的事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对于倡导社会土地改革具有先驱作用。
1995年初稿,1997年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