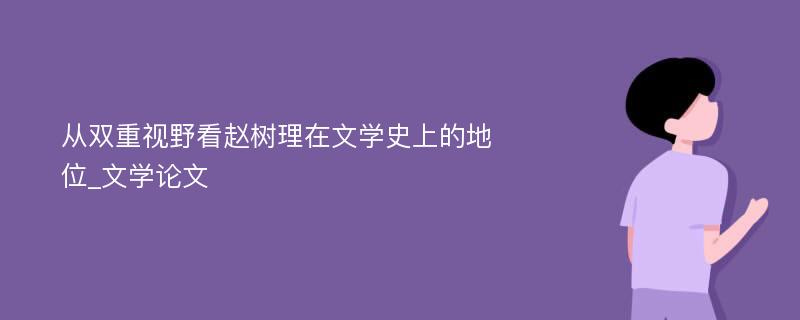
两重视野下的赵树理文学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视野论文,两重论文,地位论文,赵树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008-6749.2010.03.006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749(2010)03-0022-06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关于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读者与专家之间、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分歧十分尖锐。探讨个中原由、客观而理性地评价赵树理之功过是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赵树理现象”并非个例,从中可为如何正确评价郭沫若、茅盾以及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提供借鉴。
一、对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的不同评价
为了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促进经典作品的传播,了解、满足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2005年春天,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下,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等人发起了“世纪文学60家”评选活动。综合专家推荐意见及20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确定了10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一方面,由杨义、王富仁、陈思和、谢冕等25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通过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予以评分。另一方面,为充分吸纳广大读者对20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数万名读者踊跃介入了这一评选活动。为了使“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与编选能较为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主办方综合以上两个评选结果,以各占50%的权重,最终确定了“世纪文学60家”。在这次评选中,赵树理在专家组中得85分,并列第16名(在前面的有6位100分,9位94分,并列85分的还有4位),在专家心目中属上、中、下三等中的上等;在网民评选中,赵树理得55分,排第46名,属上、中、下三等中的下等。可见,关于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专家与读者的观点分歧较大。不仅如此,即使在学术界,关于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看法亦是大相径庭。挺赵派认为赵树理“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翻身农民的形象,这是他在农村题材上的一大贡献”[1]518,在小说艺术上,赵树理“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1]519,其“作品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2]480。贬赵派则“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有人说,他的书如果翻译成外文,就会使他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大文学家。我不同意这一点。……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3]认为“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事实上最先引起周扬夸赞赵树理的两篇,《小二黑结婚》及《李有才板话》,虽然大家一窝蜂叫好,实在糟不堪言。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4]赵树理过分迁就农民的审美习惯和审美需要,满足于“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个低层次,只有普及的意义,而无提高的价值,所谓“赵树理方向”是政治方向而非文学方向[5];应该改写赵树理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因为赵树理的创作“正是首先实践了《讲话》精神的结果(因而也才有‘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再加上当时文艺界一些权威人士的高度赞扬,他的‘问题小说论’,便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是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基本方向的典范性理解,成为五十年代带有支配性质的创作理论,影响颇为深广。可以说,十七年文学中先后出现的‘赶任务’、‘干预生活’、‘写中心’等口号,其背后都有赵树理或隐或现的影子”[6]。一言以蔽之,赵树理的小说既无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
二、评价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的两重视野
关于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读者与专家之间、专家与专家之间之所以会如此尖锐对立,笔者以为,这完全是因为视野不同而造成的。
(一)从文学创作模式的转型看:赵树理堪称旗手
从文学创作模式的转型看,赵树理堪称旗手,即便与鲁迅并肩,亦不为过。在学术界,无论是挺赵派还是贬赵派,不管愿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过一个灿烂的“赵树理时代”。所不同的只是,挺赵派认为“追求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原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作家最为迫切的人文理想。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于现代文学‘平民化’与‘大众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根本没有实际的作品成果作为支撑;只是到了40年代以后,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性,缺少平民作家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赵树理现象’的出现与影响,既是解放区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同时也体现着新文学发展史的历史必然性[7]”。贬赵派则认为“赵树理方向”的命名主要是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而非中国文学自身演变的内在结果。不作情绪化的偏激武断,以理性的光辉照亮思想之境,应该说,挺赵派的观点无疑是较为客观而公允的。鲁迅先生何以弃医从文?他自己的解释是:“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由是可见,鲁迅先生是以文学为载体来实现其对民众启蒙之宏愿的。应该说,鲁迅先生的这种创作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是颇有代表性的。正是基于启蒙的需要,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遗憾的是,在彻底否定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对外国文学生吞活剥背景下破土而出的新文学从一开始诞生便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与广大中国百姓的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相去甚远,致使新文学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精英文学、贵族文学,与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则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满怀激情地将《阿Q正传》等新文学作品介绍给父亲等农民,却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冷遇,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9]。毋庸置疑,师从西方文学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着民族化、大众化的严峻使命。事实上,文学先辈们也一直致力于新文学的破茧化蝶、凤凰涅槃,期冀全然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能在民间开花结果。可以说,“五四”时期对“平民文学”的倡导、“左联”掀起的3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都是旨在“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2]199。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文学前辈们筚路蓝缕,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直至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真正为文学创作从“西化”向“民族化”、从“贵族化”向“平民化”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正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新文学从“欧化”到“民族化”、“大众化”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2]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树理来肩负时代之庄严使命。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百世流芳,“赵树理方向”是既有合法性,亦有合理性。
就文学创作史而言,窃以为,最有资格占得其中一席之地的,无非是这样两类作家:一类是引领了一个新文学时代诞生的,如鲁迅;一类是代表了某一创作领域之最高成就的,如曹禺的话剧,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就赵树理而言,不管你承认与否,事实上他确实引领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中国的传统小说,从总体而言,是一部帝王将相史、才子佳人史,如果说正是鲁迅第一次大批量而非偶为之地把农民引进现代小说领域,真诚而严肃地为他们画像立传,直面他们的生存状态,为新文学着重贡献了闰土、阿Q等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的形象;那么,正是赵树理第一个真诚讴歌了农民的解放与胜利,塑造了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等在鲁迅笔下从不曾有过的新一代觉醒的农民形象。如果说,正是鲁迅以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对“瞒”和“骗”的封建旧文学、对廉价的“大团圆主义”,予以迎头痛击,引领了一个文学悲剧时代的到来,使中国文学至此来了个大转弯;那么,正是赵树理以其《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等一系列“翻身”故事,昭示了一个鲁迅梦寐以求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外的“第三样时代”的真切来临,在赵树理笔下,乐观代替了感伤,团圆代替了悲剧,五十年代新中国文学的“早春”情调在其艺术世界里已是扑面而来,中国文学至此又转了一弯,实现了“团圆——悲剧——团圆”的一次螺旋式回环。如果说鲁迅以《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而使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力倡的文学革命理论得以开花结果,使中国小说从传统所固有的故事框架中彻底解放出来,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多样化发展的基础,无可置疑地确定了其现代文学奠基者的地位;那么,赵树理则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高度民族化、大众化的作品风行于世,标志着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最终胜利,真正实现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热情拥抱。倘若从引领了一个新文学时代的诞生这一视角来评价,那么,赵树理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可说是超过了巴金、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大师的,甚至与鲁迅并提,似亦无甚大过。
(二)从作品艺术水平看:赵树理称不上文学大师
从作品之艺术水平看,赵树理尚无堪称经典之作,实有愧于文学大师、大家之称誉。贬赵派何以对“赵树理方向”耿耿于怀?这一方面固然与其得力于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有关,与其功利性的创作目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水平颇有关系。其实,鲁迅的创作目的亦是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的(鲁迅弃医从文即是明证),而且鲁迅亦得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作为共产党主要领袖的毛泽东就曾热情洋溢地赞扬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1]然而,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评论家,迄今为止,总体而言,对鲁迅的高度肯定却是一以贯之的(当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亦间有极细弱的微词),在华文“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活动中,鲁迅是惟一一位获“双百分”(专家、读者均打100分)的作家即为铁证。何也?奥秘即在于鲁迅作品的艺术成就登峰造极,堪称经典之作。可见,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也罢,创作的功利性目的也罢,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从长远来看,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否被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就作品本身之艺术水平而言,赵树理确实算不上是文学大师、大家,其作品在艺术上的粗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拿赵树理最负盛名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来说,很多人对作品的“大团圆”模式颇不以为然,认为赵树理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事件改写为喜剧性故事,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其实,笔者倒不觉得赵树理将《小二黑结婚》写成悲剧就一定比写成喜剧来得好。就悲剧与喜剧本身而言,它们并无所谓高下之分,完全可以各领风骚,平分秋色。《小二黑结婚》在艺术上的致命弱点,乃在于作品情节的非合理性、虚假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动势力金旺、兴旺对二黑、小芹两人的自由婚姻明目张胆地横加干涉有违常理。其一,尽管金旺兄弟一度把持了村政权,但这毕竟是个民主政权,上有领导,下有觉醒了的二黑、小芹一代新人。当此情形,金旺兄弟欲横行无忌,似乎不太可能,除非他们是一介莽夫,而从作品中看,金旺兄弟并非头脑简单之徒,抗战初期他们“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足见其并非只是赳赳武夫;刘家峧选举村干部时,他们能抓准时机混进民主政权,尤见其政治头脑。由是观之,“斗争会”、“拿双”之类的闹剧虽则动人,却与金旺兄弟之性格逻辑不甚相符。其二,金旺兄弟虽一个是村政委员,一个是武委会主任,但村长却是县政府派来的,且是“脑筋清楚”,能辨是非,对“斗争会”的妥善处理足见其贤明;二黑与小芹被“拿双”后,金旺兄弟执意要舍近求远,把两人送到区里,目的即在于避开村公所,瞒过村长,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村长不是个糊涂官。在这样一位精明的村长眼皮底下,金旺兄弟肆意妄为,究竟又有多少可能性呢?深究之,作品情节的非合理性就显露了出来:要么村长是糊涂官,金旺兄弟得以率性而为;要么村长是个清官,金旺兄弟只得藏头缩尾,暗中搞鬼。而作品恰恰使矛盾的情形并存,一方面,村长不是个糊涂官,另一方面,金旺兄弟又能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一方面,金旺兄弟甚是忌讳村长,另一方面,金旺兄弟又是率性而为,全不把村长放在眼里。凡此种种,委实令人费解。二是二诸葛与三仙姑之于二黑、小芹两人自由婚姻的表现缺乏逻辑性。二诸葛与三仙姑这两位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落后的老一代农民,身为家长,为着各自的目的,都极力反对二黑、小芹交好。老实本分、胆小怕事的二诸葛迫于“区长”的赫赫威势,表面上也许不敢再堂而皇之地干涉二黑的自由婚姻了,但在其灵魂深处,是绝不可能把几千年封建制度积淀下来的“包办婚姻”之陈腐思想那么快就清除干净的,包办婚姻的沉渣必定还会时不时地浮上心来,兴风作浪;装神弄鬼、作风轻佻的三仙姑也绝不会因为区公所的一次“丢人现眼”而洗心革面,立地成佛。因此,二黑与小芹的自由婚姻也许不会再遭到双方家长有意为之的阻挠,但极有可能会遇到家长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无意为之的种种刁难,因为,“灵魂”的净化毕竟是格外缓慢而艰辛的。遗憾的是,赵树理没能把二诸葛与三仙姑艰难的“灵魂蜕变”过程从容不迫地细细演绎,而是闪电式地让他们霎那间顿悟了、开窍了,二黑与小芹的自由婚姻也从此波澜不惊、一帆风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三是二黑、小芹在争取婚姻自由时的所作所为难以令人信服。在解放区,虽有二诸葛等因袭了数千年封建重负的不觉悟的老一辈落后的农民,但更有二黑、小芹等新一代农村新人的茁壮成长,他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能够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中,二黑、小芹与金旺兄弟的对阵,二黑一方似乎仅有消极防御之力,全无主动出击之势,只有人家无端打上门来时才有温和的举戈一击,否则井水不犯河水。如“斗争会”,二黑、小芹是理在手中,又有村长主持公道,但面对金旺兄弟的肆意凌辱,只是责难几句即完事了结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反动势力的公然挑衅,一代新人如此忍气吞声,似乎也有悖于其性格逻辑。如是而论,《小二黑结婚》当算不得艺术上已臻佳境,难以获得各方的普遍认可自是情理中的事。《小二黑结婚》这样的代表作尚且如此,其他作品就更可想而知了。如果像赵树理自己所说的那样,把他的小说视为“问题小说”,那么,赵树理小说在情节结构上一个普遍性的缺憾是前后失衡,即“问题显现”部分写得从容舒展,风生水起,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感体验,约占了文本的三分之二篇幅;而“问题解决”部分则是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原本一直悬而难决的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快刀斩乱麻般地结束了故事,对问题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曲折与渲染,这一方面致使文本的后一部分显得草率、简单、乏味,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赵树理曾坦言:“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12]1592既然所写的是“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又怎能解决得那么轻而易举呢?还以《小二黑结婚》为例,在金旺、兴旺以及二诸葛、三仙姑的强烈阻挠下,二黑、小芹的自由婚姻可谓一直危机四伏,几乎没什么进展,可是一旦到了区公所,出来了那么一个区长,就那么三两下,形势立马改观,金旺、兴旺被抓,而二诸葛、三仙姑也不再从中作梗,二黑、小芹闪电式地喜结连理,琴瑟相谐,并成为刘家峧第一对模范夫妻。只需稍作思考,其艺术上的粗糙之处便暴露无遗了。就作品之艺术水平看,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则又是远在巴金、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大师之下的。数十年来,贬赵之声或强或弱,但从来都是不绝于耳(即使是在赵树理如日中天的当年,也仍有人很不以为然),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实是事出有因。
三、辨析对赵树理的两种误读
在一些人看来,“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主要是当年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倡导的结果,赵树理的创作是功利性的,甚至是“赶任务”的。这样的认识,无疑直接关系到对赵树理的评价问题。其实,这是对赵树理的两种误读。
(一)“赵树理方向”是新文学发展的必然
客观地讲,赵树理在当年解放区的走红,很大程度上确实借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股东风,是《讲话》成就了赵树理,这只需联系其最负盛名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得以出版的实情便可明了。倘若没有彭德怀的亲笔题词,后来给赵树理带来那么大声誉的《小二黑结婚》真不知何年何月方能见刊,大众化、民族化的创作路向在知识分子把持着的文艺界是怎样的举步维艰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赵树理的创作风格与《讲话》精神相合拍,并且又找不出比赵树理更有成就的另一人,故而“方向”这一桂冠就因缘巧合地花落赵氏了。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时,赵树理就发表了《欧化与大众语》等一系列文章积极参与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12]2117。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5月,而《李有才板话》写于同年10月,都在毛泽东《讲话》公开发表之前,延安《解放日报》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才发表了《讲话》全文,其后解放区各报纸转载,而传到赵树理所在的太行山已是1944年。[13]这些不争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追求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品格是赵树理自觉的理性选择,不是赵树理有意去趋附解放区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解放区的革命形势需要赵树理这一榜样。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毛泽东的《讲话》,严重“欧化”的新文学最终也必定要走上民族化、大众化之路,否则就难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蔚为大观,连绵不断地关于文艺大众化方面的讨论与实践正说明了文艺界有识之士之于这方面的艰辛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是符合新文学本身之走向的,“赵树理方向”(此借指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迟早会浮出水面,毛泽东的《讲话》只不过催生了这一方向的早产而已。
(二)赵树理作品绝非“政治的传声筒”
毋庸讳言,赵树理确有“赶任务”的作品,例如,其在建国后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登记》即是典型的应时之作。1950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婚姻法一时成了热门话题,通俗刊物《说说唱唱》急需这一题材的作品,在缺稿的情况下,编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写,最后赵树理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赵树理甚至这样来认识“赶任务”:“人离开了群众,才有赶任务的问题,不离开群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上级作为任务而提出来的号召,就是在群众中早已存在的问题,不过这时只是由领导把它总结出来,再普遍号召下去。如果自己生活在群众中间,自己也出过一份力量,那你只要把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新鲜事物写出来,就会和上级的号召相吻合,不致感到突然,也不致感到在赶任务。”[12]1879可见,赵树理对“赶任务”式的创作不但不反感,而且还有几分欣然。世界上毫无目的的创作是不存在的,赵树理在创作时愿意“赶任务”、愿意以文学“干预生活”,这种选择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看他能否对此予以文学方式的言说。赵树理的创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剪不断,理还乱,但他并没有将文学堕落为政治的附庸。政治有时正确,有时则难免出错,甚至是大错特错。当政治正确时,赵树理当然是满腔热情地为之呐喊;当政治出错时,赵树理则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跟风,不媚俗,坚守节操。《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中,赵树理如实地写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而不是按照当年的流行模式去结构故事,刻意地去表现当时农村“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文坛因“极左”路线影响而劲吹“浮夸风”之际,赵树理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写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委婉含蓄地倡导“实干”精神。随着政治气氛的日益紧张,在真话说不得、假话不想说的复杂心态下,赵树理宁可辍笔不写。如上所论,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赵树理是能坚守文学的独立性的。并且,赵树理以工作中所遇到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为题材进行创作时,也是能较好地遵循文学规律的。一部《登记》,倘若不知其创作背景,又有几人会想到是在为婚姻法鸣锣开道?二诸葛、三仙姑的形象又是怎样地令人过目不忘,而《田寡妇看瓜》、《求雨》等作品又是怎样地短小精悍、脍炙人口?赵树理的创作虽算不上是堪称经典的精品,但至少称得上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政治的传声筒”。
四、达成对赵树理之文学史地位的共识
作为读者,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文学现象的观察,相对而言,更多地带有私人性特点,以一己之所好而臧否、持论,亦无多大不可。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必定有自己所喜爱的某种风格的文学作品和自己所不喜欢的某种风格的文学作品,这是他的自由,无可非议,但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却不应该将这种个人的兴趣爱好掺和进去,自己喜欢的就捧之上天,不喜欢的就按之入地,因为,作为文学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批评,不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社会的专业性工作,肩负着激发、引导、培养作家、读者积极向上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指明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并促进文学繁荣的崇高使命,这就决定了他绝不应凭一己之兴趣爱好来评判文学创作的高下与优劣,更不能以个人嗜好任意“酷评”。作为一名文史学家,他必须拥有一双慧眼,能透过纷繁的现象,准确地辨出哪是“鱼目”哪是“珠”,哪是“石块”哪是“玉”,如此才不致有遗珠失玉之憾。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一部《文心雕龙》,提到古今那么多的作家,但对晋朝大诗人陶渊明却是只字不提,钟嵘之《诗品》,虽发现了陶渊明,却也只将他列入“中品”而已。只有练就一双孙大圣般的“火眼金睛”,一个文学史家才能为人类留下货真价实的“珠”与“玉”。之于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只要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们不是率性而为,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假以慧眼与睿智,予以理性的审视与评判,当不至于还是那么褒贬不一,毁誉相左,而是应该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的。
收稿日期:2010-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