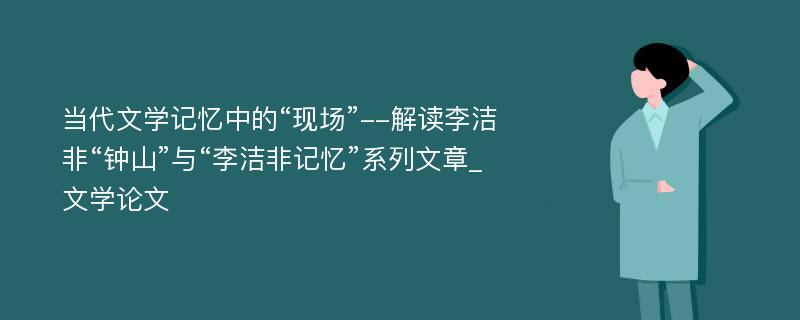
当代文学记忆中的“在场者”——读《钟山》“钟山记忆”李洁非系列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钟山论文,当代文学论文,记忆论文,系列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第一次读到李洁非在《钟山》专栏“钟山记忆”上的文章,是《“老赵”的进城与离城》那一篇。虽然有关“进城”之类的话题,早已不再新鲜,但是这篇文字依然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文章在灵动且厚实的散文气质中展开文学史叙事,现场感极强地“还原”了赵树理坎坷的文学生涯。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赵树理自然被研究者们无数次的重提。但是,在我看来,李洁非的这一次朴实地“闪回”显然不同凡响。文章以赵树理的文学生涯作为叙事脉络,并且将赵树理的进城与离城的尴尬置换为一个极特别的背景,实际上孕育出的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正典”硕果,赵树理为什么会在保持一贯创作风格的情形下,从一个辉煌典范沦落为一个“落后”分子,以致最终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赵树理就像是一扇窗口,透过他,我们看到了曾经一度被遮蔽的问题:“‘文革’文学,不是突然降临的,也不是江青、姚文元几个人搞出来的,而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①这篇文章的阅读经历,给了我耳目一新的震撼:原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描述竟然是可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史有着多种写作的可能性。
李洁非在谈到他的写作时曾说:“在我笔下,‘人’是一个观察点,是通往事件或现象本身的窗口;……也正因此,人物在我这里才成为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式”。②于是,我们看到李洁非在“钟山记忆”这个专栏中,以史家沉实、锐气的眼光,择取了一系列典型人物:赵树理、张光年、路翎、浩然、张恨水、刘绍棠、陈企霞……以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解剖了文学史上的一个个重要节点。在他们沧桑悲凉的人生轨迹中,为我们捕捉到了文学与时代丝丝入扣的隐秘联系,这些文字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基本形态的生成、转型和变迁的历程。由此看来,“钟山记忆”已不再是李洁非一个人的记忆,而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记忆,使我们能够沿着历史的记忆,去寻找文学的“在场者”,以此,找寻、爬梳、厘清不同历史阶段复杂、丰富的文化观念和美学理想及各个局部的重大差异。
从“人”入手进行文学史叙述,无疑是一种新的话语策略和话语方式。近些年大量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基本都相似地延续“历史背景+文学思潮+代表作家、作品”的传统结构。虽然,这一结构内在的连续性和缜密的逻辑性都毋庸置疑,似乎也与当今学术研究的规范相契合。但是,这种演绎式的分析研究方法却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这种方法的弊端就在于,它只看到单一的、在范式之中的那个清晰的部分,而人文科学的要求则是我们必须深入到精微的细节,在细节中去把握丰富多彩的、复杂多变的个体差异。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在他著名的演讲《历史与自然科学》中,指出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前者以描写个人为对象,后者是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他说:“精神科学的方法是理解。采用这一方法,精神科学研究个人、一次性事件以及不再重复的现象,并以这种方法把握对象的个性、一次性与不可重复性;与此相反,经验科学的方法是解释,瞄准的是那些普遍的、有规律的、可以重复的现象,采用的形式是普遍有效的法则陈述”。③我想,李洁非的研究理念,就是建立在人文科学基础之上的,他要从一个个人物外部感官符号中透视到内部隐匿的文学现象,从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角去揭开洋面下的存在。
李洁非深入文学细节的叙述和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产生的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及其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而且,还引发了我们更深入的思考:为什么这个时代会产生这样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或许,在宏大的学术视野下,我们很难做如此细致的思考。但是,当我们将人物聚焦在镁光灯之下的时候,所有的细节都会生动毕现,他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想象方式,包括他使用的语言,都化作镜像折射出冰山下的海面。比如,在《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中,李洁非写道:“正是在‘文学梦’炙手可热的年代,出现了一个刘绍棠。他的出现,他的故事,他的存在,既是1949年以后‘文学梦’升温的一个表征,同时,也是‘文学梦’在现实中得以完美实现和展现的一个样板,进而又成为拉动、刺激‘文学梦’热度不断攀升的一个梦幻般的神话。”④刘绍棠的文学生涯所书写的是,建国后国家文学体制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规划,以及共和国文学组织化模式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并进一步诱发我们去深思:“为什么会出现由国家、组织去‘培养’文学作者的行为?文学为什么成为炙手可热、充满诱惑力的职业?”⑤像这样一些涉及当代文学生产方式和基本机制的问题,引人深思。可以说,正是在对诸如刘绍棠这样典型人物焦点透视中,李洁非将人物放在社会整体和集团的精神结构中进行阐释,指出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对应不是表面的吻合,而是内在精神结构的对应。这若干篇的文字中,他笔下的人物虽然没有任何的逻辑关联,但正是在这种“跳跃性”的、不甚连贯的阅读当中,我们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许多绝非仅仅是由点到点的距离,也不仅是由点到面的铺展,而是一个通透的立体的、充满玄思的文学景观。
“钟山记忆”给我的阅读经历带来的另一种愉悦是,那种在行云流水的叙事中所勃发出的强劲的学术张力。我以为,这也是李洁非以这种方式进行文学史叙述的另一个重要突破。以“追忆叙事”的方式来撰写学术文章,将“叙事”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段,对于我们今天通行的学术范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从根本上讲,叙事带有一定的虚构因素,字里行间流淌着情感的元素。而我们当今的学术体制、规范和具体的技术实施基本上还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科学的、理性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为学术研究唯一的通行证。理性思辨被视为坚实的内核,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所谓学术规范也就更强调严格的实证性和可检验性。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说:“长久以来,‘科学’一直与‘叙事学’相互扞格。以科学的尺度来衡量叙事学中的描述,多少都要流于寓言传说。然而科学本身并非限于提供诸多使用法则去探求真理,它还必须在其策略竞赛中让自身所运用的规则合法化。”⑥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和叙事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我们不可能以科学知识为基础,来判断叙事知识的成立与否及其效能,反之亦然。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史学从一开始就采用叙事的方式治学,《史记》也好,《汉书》也好,它们所讲述的历史,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历史是在叙事的虚构与史料的实证共同编织中完成的。叙事者、聆听者与指涉物之间自始至终维系着一种情感的纽带,叙事者在讲述历史的同时,也在梳理着人物的心灵史。这样的历史虽然从实证意义上看是有很大缺憾的,但是,它却从另一个层面让我们聆听到一曲曲精神历程中的悲歌,在对历史人物的细腻的勾勒中,凝练出那些极具个性化的、往往易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洁非的叙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中国传统治学之路一种切实的回归。比如在《路翎底气质》中,李洁非对路翎的介绍一开始就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接着,他从“知人论世”的视角入手,以大量的篇幅讲述了路翎复杂的身世,在对所有信息进行梳理、编码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童年的特殊经历,导致了路翎创作中自始至终涌动着的苦闷,这种苦闷不是沉默的,而是带着破釜沉舟的果敢在自我的救赎之路上喷薄而出。从路翎的身上,李洁非引申出一个当代文学史的母题:路翎周身流动的“苦闷”的精神、意识和血液,实际上,这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那个特定时代政治、文学怪圈中形成的整体性的精神困惑。
诸如对路翎一生的叙述,李洁非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的传奇命运搬上了历史舞台,让我们在慨叹他们人生悲剧的同时,看到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苦难历程。在《样品浩然》中有关浩然身世的叙述成为构建全文一个关键的节点,只有在共和国建国初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才能使浩然这样的人走上舞文弄墨之路,成为所谓的“工农兵作者”,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模版”。《屈服——陈企霞事件始末》,则全篇都是在必要的追问和回访历史行程记录的叙事中完成的。然而这种叙事,却使我们从一个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人生遭际,听到了一个时代文学在单一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呻吟。在对郭小川、张恨水、萧也牧等人的叙述中,李洁非并没有对他们的生命历程进行随意的图解。他深信历史是真实的,因此它更充溢着震撼人心的诱惑力和感召力,既让我们在感慨、唏嘘、思考中去贴近本然,感受一个时代的理性和激情,也能更清晰地把握文学跳跃的真实的生命脉搏。无论其中有无事物存在的因果链,这些都是对审美理想、个人经验和最具真实品质内容的倾诉。
我认为,李洁非重返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形态,弥补了以往文学史在旧有的叙述框架中的缺陷,让我们在荡漾着自由情感的抒写中解读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我想,这样的解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文学日益式微的时代,以一种更为鲜活的文学史表达形式让更多的人走进文学。文学史作为了解文学的基本的窗口,由此摆脱了刻板的、冰冷的、板着面孔的论述,不再是属于中文学科的学理、专利,它走向了民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的读者通过这种随笔式叙述,深入到文学深处。
在这组十几篇的“钟山记忆”中,李洁非给我们带来的另一层启示是,他在努力填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体系中的某些“疏漏”,打捞出那些曾经被我们遗忘的庞杂的、“有意味”的文学现象,通过对一个个典型人物的爬梳,在探微索隐中挖掘出一番别有洞天的境地。
我想,李洁非的“打捞”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深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关“当代性”的问题,这使得当代文学的研究大大地有别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提到:“如果我们承认‘当代文学’(特别是它的50——70年代)有它的‘特殊性’,‘当代文学’不仅仅指一个简单的时间段落,而且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的话,那么,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更应该关注它的‘自身的’文学形态的问题。”⑦虽然洪先生在此形成了一种倡导和开端,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尚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洁非的这种“打捞”工作便显得意义非凡。
在李洁非看来,“文学的体制化”即“一体化”是当代文学中“当代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他的叙述里,几乎所有的人物无不笼罩在当代文学体制的规范之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人物以周扬、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这些文学体制的管理者为代表,他们对当代文学进程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文学生产线上的一线作家。正像李洁非对张光年的评价:“……沿袭一般文学史视角,其一生作为似乎仅能以一首《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然若走出这个‘盲区’,来到真正的‘当代文学史’的框架内,张光年的重要性则不单应该大书特书,甚而言之,不知在多少出尽风头的作家批评家之上。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在整个当代文学的复苏期,他以体制内的文学领导者身份,对于文学走向的解读,对于文学秩序的重建,对于文学未来的开拓,均造成深远影响。”⑧这种评价无疑具有史家的气魄和眼光。这些当时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对政治的敏感,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文学发展的主流话语。对他们的研究,在宏观上可以再现整个当代文学动态发展和变异的脚步。第二类是诸如赵树理、浩然、刘绍棠等一些完全由当代文学体制打造出来的作家,他们代表了共和国文学的鲜明特色。“这种文学,无论内容、主题、创作方法还是作家的培养及成长道路,都是中国这特定环境当中才有的,也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发生和存在”。⑨与这一类相反,李洁非还写到了深受文学体制影响,个人的文学生涯遭受体制扼杀的典型人物,如胡风、路翎、陈企霞、萧也牧等,在这些活生生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学体制下强权话语,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中国作家的命运悲剧。我们若将这些视为当代文学体制的镜像,那么,我们正可以这三类人物反观古今中外的“一般文学”,从而产生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更为清醒的认识。
我觉得,李洁非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引入“当代性”的话题,以文学史家的胸襟和情怀,表现出了自出机杼、不落窠臼的非凡见识。从一定意义上看,没有“当代性”,当代文学也就无从谈起。詹姆逊曾提出一个“当下本体论”的命题,他说:“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这正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⑩可见,李洁非这种彻底打破学院式局限的研究,不仅是对种种意识形态的突围,而且通过回溯那些“在场者”被忽略的重要细节,重现不可删除的历史的复杂性,在新的文化空间与真实的内心对话,的确体现出一种非凡的勇气。进一步说,这种带有实验色彩的尝试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文学是被悬置在历史之外的,我们必须动用我们所有的经验,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学的、个人的,在相对单纯的经验基础上对其进行审视。没有时间下限的“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一卷依然展开的,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由此,当代文学的研究更应该重视感性的、叙事的方式,打破那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纯理性研究,从而呈现出研究多元化的态势。在这一方面,李洁非的写作是具有开创性的,无论是从个体入手来审视文学史,还是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来填补目前当代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疏漏,李洁非的尝试无疑都值得充分肯定。李洁非的贡献并不是要以他的尝试,取代“历史背景+文学思潮+代表作家、作品”这种文学史写作的叙述模式,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自由创造的、具有生命活力的、能够最有效地揭示文学史隐秘和美学经验的方法。正是这样,李洁非在历史的细微处,感知了这些重要文学人物对文学的种种真挚呼吸,他将他们连缀成珍珠,编织成文采斐然的编年史,可以说,这是关于人与文学存在隐秘联系的独特叙述,它使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注释:
①李洁非:《“老赵”的进城与离城》,《钟山》2008年第1期。
②赵晋华:《“人”是一个观察点——李洁非访谈》,《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25日。
③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4页。
④李洁非:《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钟山》2009年第2期。
⑤李洁非:《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钟山》2009年第2期。
⑥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⑦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6页。
⑧李洁非:《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钟山》2008年第3期。
⑨李洁非:《样本浩然》,《钟山》2008年第5期。
⑩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
标签:文学论文; 李洁非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当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李洁论文; 当代文学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赵树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