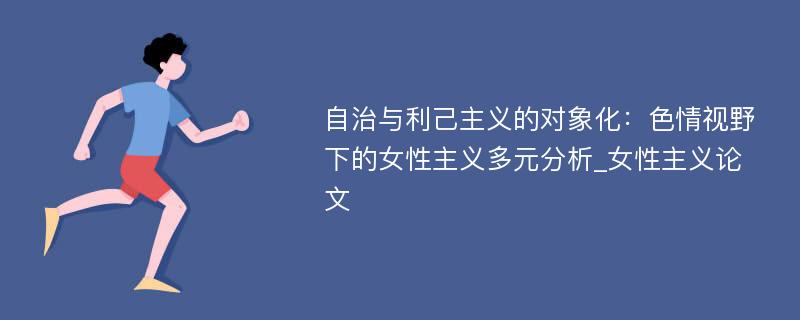
自主与唯我论的客体化:女性主义关于色情观的多元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我论论文,客体论文,色情论文,自主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关于色情的争议往往纠结在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群体的受压抑沉默和主体缺失的论证上。女性主义反色情论者强烈谴责所有色情,认为色情表现、传达、隐含和固化了社会上流行的男性支配和女性屈从的不平等性别观念,指出色情中的性本身即暴力:性暴力表现了性压迫和男权专制的等级差异,以此固化了女性在社会各方面中的卑下地位,从而巩固了男权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和非正义。为了彻底击破性别压制的社会制度,女性主义必须争取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保护,特别是首先从法律上定罪色情暴力,解放那些受迫害的从事色情业的弱女子,控诉色情工业对她们的非人性压迫。以麦金农(McKinnon)为首的反色情女性主义于1980年代初作出上述提案并成功地在市政一级通过备案,但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被驳回的理由是:此案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驳斥的理由并不在于对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否定。承认了色情业就很可能压制女性并造成将女子视为性工具的不良影响。即使如此,法律上也无理由作出色情必须由官方审查或由法律限定的任何规定,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全面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而关于色情的争议支持或反对完全属于言论自由领地。当然,对这一点女性主义提出更多强有力的分析和论证,阐明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综合思考并不排除由法律规定来保护少数民族族裔和妇女不受强权压制的权利。另一方面,支持色情工作权利的女性主义学者则谴责反色情观,认为任何官方审查都会剥夺那些受压迫更深的女子的切身利益和自由选择。有的论证指出,色情也可能赋权女性,由女性来定义和制作非暴力的色情表现而不是让位给暴力色情。 本文将详细检验上述两类三种对立的色情观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论点:其一是以德沃金(Dworkin)为首的自由主义的色情观,以及以兰顿(Langton)为代表的承接了麦金农的自由主义批评的色情观,后者指出了自由主义对女性群体受伤害的忽视和理论困境;其二是女性主义中支持性工作权利的呼声和对反色情观的批评;其三是继续解析兰顿分析的唯我论的自由主义困境和化解之法。最终本文将提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方法论对女性主义色情纠结中平等和正义的单一解释,以及如何走出唯我论可能具有的更合理的方法。女性主义应当扩大对色情暴力的分析,多吸收各阶层妇女有关色情的不同观点,建立在妇女经验基础上又超越个体的、以关怀关系为导向的道德观有助于促进对色情批评的合理辨析。 一、平等关心和平等尊敬的原则 从19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色情观点已多次交锋,论证色情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争议。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者朗基诺声明:“色情,特别是暴力色情,暗含了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的承诺。”[1]以麦金农为首的很多人论证了色情与暴力的结合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妇女的压迫和社会体系中的不平等。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论点则坚持中立,强调色情制作人和消费者的个人权利及性的自主欣赏。作为自由主义的权利论的代表,德沃金提出了他的自由与平等的新论证,由此来发挥罗尔斯的最基本的平等关心和平等尊敬的原则。根据德沃金的解释,这一原则可称为“自由的平等概念。”[2](P273) 德沃金指出了罗尔斯的两个平等观念:平等与物质分配相联结和平等应用于尊重(与人的社会地位无关的、人人都具有的尊重)。德沃金认为第二个观念是最基本的:它来自设计理念的假设而不是以契约为依据。公平的正义观所依赖的就是这一男女关于平等关心和尊敬的自然权利的假设。根据此设计,人们的这一权利不在于人的出身、功绩或最佳荣誉,而仅仅在于人的存在、有能力对生命作计划,并且承认正义的人的存在[2](P186-223)。 德沃金似乎提供了可能最好的关于自由主义平等关心和尊敬的概念的解释。但是,他的平等概念的分析至少有两个难题:其一是与个人的权利相关的考虑。德沃金强调说他的原则论证支持的是抽象的平等关心和平等尊敬的权利,所以他不太关心谁的权利、谁在现存的社会不平等中受难最深重以及受难的原因。其二是权利的性质和德沃金的“道德独立性”的思考:共同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个人外在和内在的两难选择。 兰顿对德沃金的自由主义平等概念的第一个难题提出批评[3](P311-359)[4](P117-171)。她指出,当德沃金试图回答“我们具有色情的权利吗?”这一问题时,他不问谁的权利,也不关心谁的权利。他在文章中要辩护的是“政治和道德的独立性。”[5](P367-372)德沃金以此为起点,附加了对别人无伤害原则,他会赞同允许色情政策。兰顿提出两种论证来反驳德沃金的允许政策态度。她提出“以伤害原则为依据即可证明对色情应采取禁止的策略”,又提出“德沃金关于色情的平等关心和尊敬原则与一般的自由主义对此题目的观点相冲突”[3](P312-313)。在笔者看来,兰顿第一个基于伤害原则的对德沃金的允许政策的驳斥很有力量,但不足以击败此政策;兰顿的第二个对德沃金关于两难选择的反驳和揭穿虽然更有力,但也不足以彻底击败德沃金的很强劲的平等概念。 德沃金仅仅从因果论的观点提到色情对人的伤害。他偶尔提及了色情“确实浅显地代表了对人的特别伤害。”[5](P340)在37页长的文章中仅有这一句触及到色情对人们的伤害,而文章整体上是为色情的权利和道德的独立作辩护。难怪兰顿对此评论说,德沃金“不能认真地对待色情的妇女受害问题。”[3](P327)而女性主义对色情的反应完全不同,她们关注的是妇女的公民权利地位而不是色情者的道德独立。麦金农有力地论述了色情会违反妇女的平等人权地位的公民权利:我们定义色情为表现妇女的从属地位的性逼真图像,通过图像或文字,使妇女成为非人的性对象、事物或商品;歪曲妇女享受痛苦、侮辱或强奸……用肮脏或低劣呈现妇女,用流血、受伤或伤害的背景烘托性的环境[6](P176)。 这一定义试图说明色情对妇女群体的价值贬低和压迫。兰顿指出,色情资料中单纯体现性逼真的部分本身没有错,其错误在于,如同麦金农的定义所表明的,它对于性平等的描述隐含了“色情的实践有助于妇女的屈从地位,正像种族隔离实践有助于黑人的屈从地位一样。”[3](P333)按照兰顿的观点,这些隐含有两层意义,首先,妇女同男人相比并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其次色情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妇女的屈从地位。 色情对妇女的影响如麦金农所言,它“把强奸、殴打、性骚扰、卖淫以及对儿童的性虐待视为浪漫化的性,由此而庆祝、提升其价值,并使它本身合理化。”[6](P171-172)色情对妇女的影响在调查中得到切实的揭露。所有这些调查在兰顿看来已足够说明,妇女在公共的和私人的色情场合下受害极深。这些调查足以否决德沃金的“没有证据说服这一因果影响”的结论。鉴于因果推理的逻辑严格性质,这些经验调查或许尚未达到百分之百的因果对应,可即便如此,简单地否定经验的证据也是不合理的,因为非因果的、处处流溢的对妇女的伤害更是无法否认。如果承认这些针对妇女的实际伤害,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应当支持对暴力色情采取禁止的政策,虽然色情与妇女的社会从属状况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兰顿对德沃金关于色情观点的反对还基于德沃金的偏好分析,她试图显示,德沃金对色情宽容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德沃金持有外在偏好的看法。按照兰顿的分析,在德沃金的假定下,禁止色情政策将满足大多数人的偏好选择,但取消了色情消费者的娱乐机会。人们想要禁止色情的理由是因为认为色情不高尚、犯错误,其生活观是低俗的。但德沃金认为这一“道德”偏好必然会被相对应的“道德的独立权利”所击败。所以,色情消费者有打败禁止色情政策的权利,从而回到对色情宽容和许可的政策。这里的关键是偏好的特质:如果偏好是外在的,是对他人的看法,那么,它们便违反了“道德的独立”和平等尊重的权利。 倘若遵守以上规则,兰顿认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会偏好色情而非禁止它。假定多数人选择允许色情政策,难道这些允许色情政策的偏好不能算是外在的和非个人的吗?选择允许色情政策的人们会持有关于妇女价值的看法,而按照德沃金的标准,这类看法正是外在的偏好,但外在的偏好违反了平等尊重的原则。因此,兰顿指出,“允许色情政策”和“禁止色情政策”都是易碎的,在平等原则下都是不能持续的。在“允许色情政策”假定中德沃金保护色情消费者的权利,而在“禁止色情政策”假定中兰顿保护妇女的权利。两种假定中平等的权利必须和实际持有权利的人相联系:这些人持有权利和享受权利,或者不持有权利和经受他人权利之痛苦。无论平等权利是什么,这些权利必须返回到人们对权利的拥有上。抽象的平等关注和尊重的权利在应用到日常生活背景中的人们时就有了非常具体的内容。在笔者看来,平等关注和尊重的权利作为人的背景权利必定不是一个孤立的观念,而是某种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互相联系的权利。 兰顿试图使用德沃金的外在偏好策略来击败德沃金对允许色情政策的推荐,笔者认为,这个策略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在笔者看来,色情问题的关键争议不在于各自结论为允许或者禁止,而在于各自论证的前提:德沃金假设的前提是“道德的独立”。他在《我们具有对色情的权利吗?》[5](P338)论文里明确提出,他宁愿采纳两方面的考虑,但根据是道德的独立权利。兰顿的反对并没有完全击败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看清楚德沃金的中立的道德独立论并不提供关于色情中妇女为何不断经受伤害、保持沉默、被剥夺自我价值和平等自主的分析,而这些都是平等原则中的假定论证。德沃金的允许政策中究竟会侵犯谁的权利、为谁的利益服务?这些问题应当受到检验,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理想化的,也不是中立的,如同贾格尔所论说的不一样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境况里。[7] 二、女性主义关于解放的妇女和性工作的权利 虽然上述女性主义者反对色情,有些女性主义者则为色情作辩护,例如文迪·迈克埃尔罗(Wendy McElroy)声明,“从个人的和政治的意义看,妇女在色情业是受益的。”[8](P74)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对麦金农的色情定义提出挑战:“谁知道屈从、性服从或贬低这些究竟指的是什么?”[8](P74)由于麦金农的定义中许多这类词汇有待于进一步解释,而我们不能预测出如此这般的伤害怎么来证实,那么唯一确定的方法就可能是为避免起诉而采取法律上的限定,限制出售任何有关性方面的表现物,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加倍压制言论,比直接禁令更过分[8](P95)。盖尔·茹彬(Gayle Rubin)论证说明了对色情的限定仅仅使得对色情业工作条件的改善更加困难[8](P33)。也有其他的提议来反对将妇女视为性服务或娼妓的牺牲品。 由都泽玛(Doezema)撰写的《性奴与对话主人》一书提供了公众如何来理解贩卖人口的两个中心概念神秘和认同的复杂分析。她追述了历史的和当前的关于认同的意义,注意到19世纪初“白奴”运动及口述与当代贩卖人口之间的相同点,为此而论证说,这两个概念很关键地也很歪曲地侧重于由“无知的妇女”引出的恐慌。都泽玛评议说,“由于相信了没有人会选择去做娼妓,取消派的女性主义对自我定义的‘性工作者’感到困惑并提出‘认同女人去做娼妓是不可能的’,从认识论方面就将娼妓定义为奴隶了,而这些奴隶需要女性主义的干涉来拯救。”都泽玛质询取消派女性主义的循环推理:娼妓对妇女是非人性的,所以说无伤害的妓女的经验在本体论方面是没有可能性的:“最终的权力行使在于:否定性工作者的经验,并坚持认为绝对没有这种经验。”贩卖人口就成为强迫去做娼妓,也就不会有自我定义的性工作者了,她就在口述中成了“消失的主体”[9](P134-137)。 如果都泽玛的论证正确,以下考虑就很重要并值得努力:为那些选择去做性服务的妇女创造空间来发出声音。这样,自由和被迫的分界就会分晓,而对一个既定事实的承认就有可能了,即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所作的无奈选择。当然,广泛地承认这种选择还要听取来自女性性工作者自己的声音。 政天天(Tiantian Zheng,2009)近距离观察了中国性工作者的生活:她在两年之内亲身观察了卡拉OK伴女郎的经历。她写道,“我对这些女子具有极高的敬意,因为她们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勇敢的妇女:她们身体力行地拒斥父权制度对女子贞节的态度,并且使自己不受一般性地强加给妇女的限制”[10]。当她们与身陷其中的社会作协商时,她们展现了自己主体代言人的身份,她们做到了自食其力,但在某种意义上她们的文化身份却被边缘化了。 爱丽丝·杨认为,边缘化是受压迫的5个方面里最危险的一类压迫形式:“边缘化阻止了以社会来定义并认可的方式来展现人的能力的可能。”[11]如果这一看法真实地描写了被贩卖的女子、贫困中的妇女以及被拐卖的女孩儿的境况的话,我们就很难否定她们都缺乏关于所做工作的主体代言身份。都泽玛对此做出反应,她认同性工作者也是一种职业,并且解释论证说,由于娼妓中的性是非人性的,娼妓就永远是损害人的,然而,既然性是发生在娼妓里的,性也就是非人性的了,因而“在这个整洁、封闭的构造中,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性工作者的经验,使她们能发言表述她们的工作是无害的或者不是异化的”,都泽玛称此为“形而上学的性工作者的消失”,取消派女性主义由此而将她们认定为需要让女性主义来拯救的奴隶[9](P144)。这看起来是明显的荒唐之论,因为在作探究之前已作出固执的假定,即对娼妓的认同判定为是不可能的。 关于认同和认同之后会发生什么要依靠个人的见证,比如林达·劳维拉斯(Linda Lovelace)在《深嗓子》影片中是色情名星,她描述了如何被关闭、折磨、被迫出演了此片。坎蒂达·罗亚勒(Candida Royalle)则写道:通常人们认为妇女进入色情业是作了牺牲品或者是在自我摧毁,我们的文化很难接受妇女选择这个职业,而我是选择者[12](P541-545)。 兰顿对这一论题作了探究并且撰书《性的唯我论》来深入挖掘。兰顿论证性的客体化是对自主的否定:“色情造成发言的不可能性质;而可能的片刻中言论又无价值。色情使妇女变成客体对象,客体是不说话的,即使说话也被认为是客体而非主体的人。”兰顿评论林达:“她成了有用的客体,在很怪的意义上她的自主只是个商品。”《深嗓子》影片欢庆“解放的妇女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现生命和性”,但她的证词揭露了要通过暴力、强奸、死亡威胁才使她完成角色。她说:“我就像个机器人,别人告诉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因为不说就会遭毒打。”兰顿由此而总结说,林达的性自主是对她在压迫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将性自主归于偶像式的解放了的妇女,继而认为也属于其他的妇女,这样就违背其他某些妇女的自主性”[4](P229-240)。笔者认为,兰顿所分析的虽然正确,但她却忽略了一点:妇女受压迫的结构性特点并不能推论出一个群体的声音来反对所有的色情。尽管兰顿否认性工作者在被压迫的情况下扮演性的服从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主决定的性质,罗亚勒却声明色情可以扩展我们的幻想世界,可以提供安全和浪漫的方式来开阔我们的视野和境界。这种观点真实可信吗? 三、性的自主与唯我论中妇女的客体化 安株·阿特曼撰文《性勃起的权利:色情、自主和平等》[13],论证认为观看色情的人是在行使他们的性的自主权:性自主的唯一限制是不能与儿童和不同意的成人有性关系。他称这就是自由主义规则,即让成年人不受道德约束地从事所选择的性活动,“只要他们的活动不涉及直接的不情愿者”。他进一步推论说,即使暴力色情与性暴力之间清楚地具有因果关系,“还是不足以下结论说生产、销售和观看暴力色情会超越成人的性自主的权利”,所以说,不会有任何证明来支持对暴力色情的挑选,并将它和媒体暴力的其他形式相区分。阿特曼最后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性暴力,自由主义的道德论要求对此作出回应,“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降低性暴力的发生,而不必对暴力色情的生产和观看进行干涉”。这一观点在他的对手苏珊·本勒森看来是很荒唐的,她指出阿特曼所倡导的是,不管色情有哪些伤害,它们都只是我们具有性自主权利的代价。 本勒森的分析指出色情对不参与色情活动的人所导致的伤害有以下几类:(1)对那些被强迫参与的人们的伤害;(2)增强和巩固了对女孩儿和妇女的歧视和性折磨;(3)对受色情影响而形成对妇女的歧视态度并产生性欲望的男孩儿和男人的伤害;(4)对在性暴力中已经是牺牲品的人的再度伤害。以上几点澄清了色情观赏者和不愿受色情传播贬损的妇女的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本勒森认为,虽然第一修正案保护色情,但色情可能违反妇女的第一修正案中的平等受保护权。她的结论是,“如同我们不再对婚内或约会强奸、家庭暴力和性骚扰一概加以否定一样,我们也应该不接受作为性自主之代价的色情的伤害[14][4](P325)。 以上两种对立的色情观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挖掘色情中性自主的含义,为此需要检验兰顿的《性的唯我论》。兰顿在引领女性主义评价性工作者的妇女沉默方面,很关键地提出了色情在对这些妇女的客体化中否定了她们的自主性。兰顿特别强调了这些妇女客体化的3个特征,即妇女是身体化、外貌化和沉默无言的。依照兰顿的观点,康德关于将人视为性对象的讨论肯定有助于我们来厘清色情是否违背自己的意愿。她引证了康德的言论:“人类之爱在于良好的意愿、情感和提高他人的幸福感。很明显的是,当一个人单纯从性欲来爱另一人时,以上三点都不存在。性爱使得被爱者成为性欲的对象,一旦欲望平静,被爱者便被抛开”[15]。 然而康德也说过,“男人,当然了,使用另一个人的时候,是要得到那人的同意的”。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反色情观和康德的看法的一致性:色情的客体化很可能否定人的自主性。与此相对照,康德还解释了亲密的友谊和爱:“我们的爱是相互的,存在着完整的回报。我,慷慨地给予他幸福,他同样也带给我幸福感。”[15](P202-203)[4](P319) 我们如何来理解康德的唯我论并避开唯我论的观点呢?依照兰顿的观点,既然康德看出性爱如同友谊,其力量在于冲出自我的牢笼,那么性爱就能“帮助我们逃离唯我论的地狱”[4](P327)。但是,兰顿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妇女确实选择了性的工作,并相信她们有权利作此自主选择。如何来评价她们的声音和选择呢?她们似乎有能力识别“非异化的尊严”和“禁止将人视为物”,她们需要由女性主义来拯救吗? 杜萨拉·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不赞同将性工作者视为需要拯救的牺牲品的看法。她认为:“那当然不是大多数色情服务者的意见”[16]。罗亚勒也否认色情会产生暴力,尽管她看到色情电影业一般而言是剥削妇女和性本身的。她想要通过改变电影制作来改变色情,“让人们对性和人作为性的存在感觉良好[12](P540-541)。她对色情工作者的看法很有意义:首先,既然女性主义是要赋权妇女而不是让妇女自我摧毁,反色情者就不是女性主义。她认为对妇女的真正关怀在于建立性工作者工会并鼓励妇女合法工作,使妇女们掌控自身安全。其次,她发现在色情工作里人们必须学习感受性是什么:彼此之间要有感情互动,“与你所爱和信任的人一起来游戏幻想的世界,难道这儿不是更好的地方吗?”这一信息很恰当地解释了为什么愈来愈多的妇女加入到了观看色情的行列。罗亚勒想从一个妇女的角度来制作电影。她的“美国色情”一章[12](P540-549)提供了完美的健康色情图片,促使我们进一步深思色情问题,她是极少数的敢于与男性影片制作人竞争的女子。 罗亚勒的色情片与其他暴力和强制的色情片相比代表了另一种形象,是和兰顿的如何避免唯我论的思考相一致的。可是这种色情片还是在市场中的商品,也不能逃避它在市场上的工具性作用。努茅(K Numao)在讨论兰顿的《性的唯我论》时说明了唯我论通过色情的直接使用来使妇女客体化;消费人群逐渐视妇女为性满足的工具,而妇女的客体化就进入消费者的思维背景:“一旦消费者达到这一步,在消费者和妇女之间就不存在真正的交流,后者只是客体物了。”努茅的观点是,客体化不止在于男人使妇女客体化,男人之间也有客体化,妇女之间也有客体化,妇女同时也可能使男人客体化。因此,唯我论“确实是关系每个人的问题,不只是男人。”[17] 努茅正确地指出了兰顿的贡献:通过康德的友谊观来触及色情的根本问题,即我们对待他人的那种最关乎人性的方式。由于对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意识,自由主义的色情观走向了极端的没有限制的允许政策。这种极端自由让成年人不受道德约束地从事所选择的性活动,只要他们的活动不涉及不情愿的牺牲者。但是,即便是情愿的牺牲者,她也是完全被客体化了。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使一个人客体化都是违背人性的不道德。 “情愿的牺牲者”并不能掩盖其为了满足消费者性欲而成为客体、对象或工具的内涵。这里不存在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感受性,仅有金钱的交易。应当注意的是,照自由主义者看来,卷入性暴力的人没有错误,只要另一个客体情愿同意扮演屈从的角色。但是,平等尊重的原则不全是关于同意不同意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的背景权利才是深层意义的如何尊重对待对方的关键所在。康德与女性主义的反色情观都认为将他人仅视为工具而非目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为什么性工作者选择去做“情愿的牺牲者”呢?这对反色情的女性主义来说很是迷惑。我们要扩展对性唯我论的分析。 M.吴蓝(Ullen)发现色情唯我论的根子不仅仅是性别争议,而是总体性的资本主义。她批评色情中无限制的个人情欲的过度表现,赞赏女性主义的反色情立场对这种过度泛滥的观察,但她又指出:“这个过度的根子不仅存在于性别的权利不平衡,更存在于目前的经济制度”。Ullen建议我们应当奋力改变能够改良的,诸如“色情的生产和消费中的物质条件。对色情进行规范化管理但不要审查它们”,她指出规范化会允许施行某些清楚的规定,以便保证受雇者的工作条件和工资,而提高为妇女服务的色情产品有可能成为第一步来达到目标,“以同样想象娱乐的手段为妇女提供长期以来仅仅为男人服务的项目。”[18] 有没有其他方式或方法论帮助我们来避免性的唯我论?我们要开阔视野超越自由权利论的视线,寻找关怀的关系理论。赫尔德(Held)对康德的观点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作了概括,并将它们与关怀伦理学作了比较。她在《关怀伦理学:个人的、政治的、世界的》(2006)一书里说,“占主流的正义伦理道德理论重视的是平等、公正、公平分配和不干涉,这些价值具有优先性。与之相反,关怀伦理学重视信任、团结、互相关心和有共鸣的反应,这些价值具有优先性。”[19]她认为,关怀伦理学能够将关怀的正义扩展到思考如何建立社会结构和应当如何限制市场。虽然此书没有直接论及色情,但关怀的正义或正义的关怀以其混合的方式来提供见识,进一步探究健康和平等的性活动,反对社会中弥漫的性暴力。 为了避免自由个体的唯我论,我们要做的是培育关怀价值中的关怀关系,通过对所有妇女和男人尤其是青少年的公共和私密范围的教育来培植。这些教育项目将会反向平衡儿童们有可能接触到的网络色情资料。社会有责任号召共同来反对针对青少年一代和妇女群体的性暴力。这将是改造色情文化的第一步。保尔(Paul)[20]指出了色情工业和色情文化的彼此强化,由于能给色情市场带来暴利,它们当然要反对由国家制定的所有规定。 性暴力和性和谐具有很大差别,我们反对的是暴力而不是性。一旦有暴力就必须有行动去阻止暴力。制定规则应当是合理的期待。阿特曼说规则之外的其他方法可以制止暴力犯罪但不必筛除暴力色情。但是,依据平等关心和尊重的原则,暴力色情中表现的女性群体客体化的行为是严重的犯罪,原因在于它把妇女仅仅视为性工具,这违反了女性的权利与平等关心和尊重原则。在一个和谐的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健康的人类的性要提高为妇女和男子服务的关怀关系的色情产品。 兰顿正确地揭示出德沃金对道德独立的辩解是失败的:外在选择的两难说明了他不能完全划清内在与外在的分界线,原因在于性行为是自我与他人的合作,而不只是个体行为。 以上各项关于如何避免唯我论的论证澄清了一个观点,即唯我论中的对妇女群体的客体化违背了平等关心和尊重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石是康德和罗尔斯的道德的感受性。遵照契约或同意的方法并不支持无任何规则的允许色情政策。色情文化和环境中的唯我论的难题关乎市场的扩充和现实中弥漫的性别不平等,有必要进一步挖掘。这些探索要求多方视角下的多种声音和论证,要使用混合在一起的方法论而不是固守单一的自由主义的平等概念。关怀伦理学提议的关怀与正义相结合的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