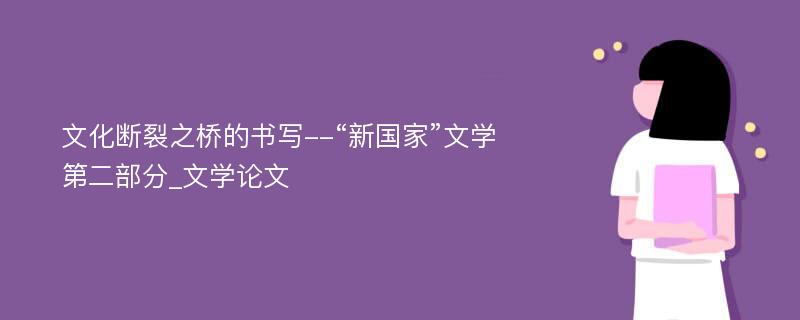
文化断桥之畔的书写——“新状态”文学漫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桥论文,之二论文,状态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状态文学特辑
1.“文化断桥”:双重裂谷之间
“断桥”在中国既有的语言秩序里意味着一种悲剧性,脍炙人口的白蛇娘娘与许仙的故事便起源于杭州西湖的断桥。1980年我去杭州旅游去观赏西湖十景之一的“断桥残雪”,我固执地寻找断裂的痕迹,发现断桥未断依然一体,只好猜想桥的内部必有一条隐形的分裂之线,要不,怎会有断桥一说。“文化断桥”的提出也是源于悲剧性的人文现实。在经历了80年代的种种人文主义思潮涌动之后,9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在市场经济这一非人文性的魔棒的驱使下出现了无法回避的文化断裂,这一断裂是在转型的合理理论作用下完成的。无需掩饰,市场商品经济的热潮对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社会价值观念更新对人的金钱意识的强化,给人文学科的剌激无疑是一场破坏性极强的地震,文化的裂谷豁然醒目,虽然往昔文化的表象依旧存在,但断桥在深层结构已经形成。在一些方面断桥已经浮出地表呈两极对峙之势,比如图书市场上地摊与国营书店的冷战,便是80年代向90年代过渡的一种写照。文化断桥已经横亘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不管你视它为一处风景也好,还是把它看作不顺眼的障碍也好,反正它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不会轻易消失。
“文化断桥”的提法最早出自戴锦华女士对第五代导演的阐释,她在《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一书中有一节《断桥:子一代的艺术》中这样写道:“第五代的艺术是子一代艺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规定他们痛苦地挣扎在无法撼动的父子秩序与无父的事实之间。于是80年代,中国第五代的艺术便成了一种超越历史/文化裂谷、而终于陷落的断桥式的艺术,使他们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与历史表述的努力成了子一代的精神流浪的传记。”(P17)这种断桥是由文化反思运动本身包含着的内在矛盾决定的,“一方面成为五四精神的承接,成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彻底否定,以期为现代化进程扫清障碍;一方面成为寻根行为,力图穿越文化裂谷,重返民族文化本源,发现并表述被权力话语所遮蔽的民族历史。”(P16)戴锦华的概括与描述是异常准确,可谓把握住了第五代的脉搏。
很显然,“新状态”所陈述的“文化断桥”已超越了原有的内涵与外延,其实是一次重新命名的结果。我们今日面临的“文化断桥”已远非文化反思的内在矛盾所能概括,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还同样面临着另一重的断裂——启蒙神话的破灭。启蒙神话的特点用戴锦华的话说,便是“完成一个深入的文化内省与历史批判,永远地放逐并埋葬五千年的历史幽灵,为将临的、已至的现代化进程拓清道路”,一个世纪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社会从未放弃过这种现代化的努力,然而,80年代后期急剧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与猝然而至的商品化大潮,90年代的文化转型使之陷入现代化的迷惘,对西方现代化文化的无条件认同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精神的困顿,反而会导致一种新的精神流放。
在这样一种双重断裂的社会背景映照之下,文学也迅速从原先中心位置被抛落到边缘。当93年下半年贾平凹的《废都》这样一部文学奇书被地摊文学广泛销售时,人们看到的不是多少年前万人空巷传诵天安门广场诗歌的文学的辉煌,而是文学的破落与灰暗,它有点像余华《活着》中的那个破落户福贵——活着而已。文学面临的双重断裂也同样不可弥补,一方面是作家从神坛上走下之后悚惶的流落到民间艺人的地位,文学犹如丧失了地球引力的月亮,茫然不知如何使用这份奢侈的自由。另一重断裂则是风起云涌的大众读物掠夺了文学的读者,作家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的大众文化消费品种,手中的语言之剑如锈了的青铜古器闪耀古典的光辉,都难以重施旧日的魔力。丧失了读者的作家已很难宣称为下一个世纪写作、或者为孙子们写作了,没有发行量的文学作品从经济上打击了往日作家的优越感,在往日一份文学期刊发行超百万的日子里,作家满可以骄傲地以版税来炫耀文学的价值,但今日的文学期刊大多数不盈利靠国家和创收来维持,在文化市场上,文学成为滞销的产品,作家与读者往日的鱼水关系断裂了,文学成为商品流潮沙滩干涸的鱼,与“海”无缘。于是一度时间内文人下海成为中国不可不看的风景不可不听的奇谈,一些作家也以富以钱多来重新表明自己没有被时代抛弃,并声称宁可被文学抛弃。一些执著于文学的作家虽然能够忍受经济上的贫困,但不能容忍精神上的贫困地位,既不能投身商海挣钱,又不能静心写作,这一群丧失了“终极关怀”者开始为自己的灵魂发愁了,形成了作家的“文化断桥”。于是,呼唤新状态,超越文化断桥的裂谷,便成为90年代文学自我救赎的重要方式。
2.“孤岛”上的叙事人:作家之死与小说家之生
1993年2月,我到海口去参加了一次笔会,在会上见到了很多作家老朋新友,乍看起来特有重温旧梦的感觉,后来发现这次笔会正好宣布了旧梦的终结。迫使我们寻找新状态。这里可要感谢这次会议提供给我的种种感触,虽然会议只有短短半天谈论文学,而且谈及的还是文学与下海经商的关联,但海口之行让我深切地感到文学和作家在90年代由辉煌走向没落颓势难挽。学者风范很足的韩少功事(不是“私”之误)下交谈说,海口是真正的文化沙漠,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行对话的。现在我才意识到少功的悲哀是真诚的悲哀,是一个作家的真正悲哀。离开海口那天,飞机升至空中,我鸟瞰下去,海南岛在荡荡的大海上状如椰子般孤苦伶仃,仔细品味少功的话,我脑子里跳出了“孤岛”二字,便一下子将我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零散的观念和想法整合起来,好,孤岛。回来以后立即写作一篇题为《孤岛、专卖品、乌托邦——90年代文学走向刍议》的文章,我感觉到重新找到了状态,这种概括只是缘于我个人经验的角度,有不可躲避的遮蔽和阴影,但它毕竟有了一种新的阐释的可能性。
“孤岛”其实是就作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在“新时期”语义场中,作家与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亲密无间,作家对社会政治现实认同与某种看似拒绝的否定,都表明文学自身的运转来源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巨大吸力,作家有理由也有可能为国家代言,为民族代言,为民众代言。张颐武将之称为“现代性”的整体性的话语。认为“这种话语是以18世纪西方的启蒙话语为开端的。它包含着以‘主体’为中心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它创造了‘理性’的合法性的神话,它构筑了灵/肉的二元论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立场。它提供了两大支撑现代文化的神话,一是人文独立解放的思考模式,二是对整个知识系统作纯思辨式的思考。‘现代性’并不仅仅指向一种历史的分期概念,而且指向一种对传统对立的新文明。这种‘现代性’的话语带来了‘个人主体’和‘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些来自西方的话语自‘五四’以来就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它已成为中国人文话语的中心。同时,‘现代性’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它标识着在传统/现代、旧/新、黑暗/光明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的肯定性的方面。‘现代性’不是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化与认识论的总体,而知识分子则始终处于话语的中心”(详见《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对“现代性”的追问》一文)。张颐武在指出“现代性”话语其实是来自西方话语的过程时,实际也在运用西方当下的话语(如法国理论家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阐述)来解释中国的人文状况,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性”的状况远没有张颐武文中所说的那么充分,它是一个始终未能正常发育的孩子。虽然未能发育健全,但“现代性”神话的破产,也就如同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孩子同样要面对死亡一样,或许由于其不健全,死亡也比发育正常的人来得要迅疾——这就是后现代在中国迅速繁衍的土壤。张颐武在文中抓住了一个要害:“知识分子则始终处于话语的中心”,作家虽然讲述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他虽然处于代言人的位置,然而这个位置却是话语的中心。事实上,文学和作家的这一特殊的功能还在历史的进程起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诗歌对“四人帮”的毁灭应该是功德无量的。问题是文学的这些特殊功能离开了特定的时期和文化背景,如果滥用或者一定要随时随地让它生效,反而使文学失去了本性。
文学在过去的日子无疑是“话语中心”的中心,作家也充任重要的社会角色,他对社会拥有话语的发布权、代言权,他是站在时代之塔上的宣谕者。到了90年代,作家从原先的时代骄子变成了“码字的”(王朔语),在王朔的《顽主》里,作家成了流氓的代名词,作家与街头的阿混已经没有太多的区别。作家社会地位的前后反差之大,表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作家原先与社会的联系被日益高涨的商业浪潮和实用精神割断,被闲置到一个非常尴尬的边缘地位。文学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无人问津的“孤岛”,只有靠追忆往昔的好梦来慰藉。作家队伍亦迅速分化:①下海经商;②制造畅销书;③投靠影视;④报刊专栏作家;⑤苦坐书斋;⑥做官员。这些身份宣告了在“新时期”语义场中存在的作家已经死亡,文学已经不能够由他们肩负,需要一种新的角色,以新的姿态来重新看待文学。
在新状态的小说里,我们可以读到“作家之死”这样的意味,马建在其新作《拉面者》中通过专业献血者与专业作家的对话无情宣告了作家之死,当专业作家痛斥专业献血者是“虚伪的献奉者”时,血客毫不客气地指斥作家:“我比你们更真实”,“你也是个献血者。我比你高明的是血流出来救了人。我得到食品和人格。而你的脑浆消耗之后,没得到任何安慰。你得到的物质仅够你苟延残喘,靠闻邻居的香味过活。你根本还没体会到一个完整的生命。你常说要接近什么真谛,你的上帝帮了你吗?”“我不是谁的牺牲品。改革开放给了我生存机会。我能自己创造自己。我从第一次拿到血钱就不再绝望了,我要的东西都有了。而你,为了登上中国作家大辞典,还要苦苦熬着。因为你不愿意写你不想写的东西,你在惩罚自己。你把生活故做神秘,使自己的不实际变得合理。你竟忘了人是靠谋实利生存的,而不是靠意义。”马建小说中血客的对作家的警觉,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对作家和文学的一种反诘,甚至我在前面提到的海口笔会上也听到类似的反诘。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则通过叔叔这样一个飘浮不定甚至有点抽象的作家的描写,彻底瓦解了“作家”这个一度被夸张了的神话。当大宝用那把切西瓜的大刀劈向父亲时,曾经屹立在读者心中的作家死了。血客用语言现实将专业作家置于死地,大宝用的则是明晃晃的菜刀,而王安忆则是以小说作为武器,他们不约而同谋杀了作家这样伟大而渺小的历史人物。新状态便由此诞生。
“作家之死”在新写实小说中是通过精神的缺席得以实现的,应该说新写实的小说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作家这个伟大的神话的破产,在面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急遽变化的社会文化现实,作家已无力象新时期之初那么作出坚定的价值判断,只能采取客观化的叙事策略来逃避精神的惘然。委托叙述便成为“新写实”在文本内部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委托叙述便是作家将叙事的责任委托给一个与己不关联的作者。这个作者往往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或潜在的平行的人物,作家抑制住自己的叙事欲望潜入到小说中人物的视野来进行小说操作。这种叙事人的出现,本是现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它避免了作家单声道的平面输入,而去追求一种立体辐射的效果。但由于“新写实”专以小人物、灰色人生来展现底层平民的生存状态,委托叙述则意味着小说的“视点下沉”,导致了作家的不在场,知识分子的不在场。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便是以小林的视角来进行的叙事,在小林叙事的过程中,作家多次无意识介入小林的叙述,附和小林的叙述,阐释小林的叙述。在池莉的《不谈爱情》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类似“世故老人”型的人物——梅莹,在梅莹和生活的双重教导下,庄建非才真正的“成熟”,认识到只有“不谈爱情”,才能“圆满解决了一切问题”,“他相信往后他就有经验了”,这是一种大彻大悟后的感慨。正是在“身边的日常琐事”中,知识分子与大众达成了某种“共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大众的“转述人”,而不是“代言人”,现代文学对大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种“转述”中被消解了。蔡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认为这种消解背后,“是对浪漫主义的排斥,对乌托邦的怀疑,对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目的消解,是对‘解放人类’与‘解放自己’的双重拒绝,并且不自觉与公共性的日常生活准则达成‘妥协’,个人只剩下了自己的‘日子’,‘活着’就是目的,它成了一个不可逃避的存在符号”(参见《花城》1993年第4期《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一文)。
“新写实”虽然也宣布了作家之死,但却是在妥协与认同的姿态下进行的,对“解放人类”与“解放自己”都采取逃避的姿态最终丧失了作家自身,也丧失了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叙事的可能。新状态的意义并不在于宣布作家的符号性死亡,而在于宣告小说家的新生。小说家与作家之间在一般的语词逻辑意义上有一种隶属关系,不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但由于作家这个符号在以往的语义场被灌输了过多的角色内涵,作家的最初语义已经被肢解,已经填充进新的涵义,作家的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在非文学的范畴内存在,重提“小说家”是为了让作家这一书写者重新回归到文学状态中,因为小说家所具有的那种职业性寓意恰恰可以抵消那种非文学状态对写作者生存的干扰与辐射,在一个新的历史文化断面重现诗性的尊严与智性的光芒。
这种重现便是让小说家重返精神不在之场,让知识分子借助书写(不是创作)来“解放自己”,从“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栏目定位语)转向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便在小说里出现知识分子叙事人这一全新的话语,结束以往“代言人”与“精神缺席”的悲剧命运。
3.新体验:象征之塔的倒掉
在上述的论述中,我谈了小说家作为新状态的书写者的可能性,这种知识分子叙事人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个人性话语与精神性话语在大众消费文化的包围圈突围出来,让诗性的阳光重新照耀那些被各种阴影遮蔽太久的心灵——孤岛上的文化守望者,促使他们在没有家园的语言之流中寻找一种不在之在,在文化的边缘处自由地游走,以一种新的生命形态改变“守灵人”的被动之势,在若即若离的社会状态中真正的“解放自己”。
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的创作札记中写道:“《叔叔的故事》重新地包含了我的经验,它容纳了我许久以来最最饱满的情感与思想,它使我发现,我重新又回到了我的个人的经验世界里,这个经验世界是比以前更深层的,所以,其中有一些疼痛。疼痛源于何处?它和我们最要害的地方相关联。我剖析了身心深处的一些不忍卒睹的东西,我所以将它奉献出来,是为了让人们与我共同承担,从而减轻我的孤独与寂寞。”王安忆在这里强调了“我的经验”、“人个的经验”和“身心深入”这样纯属于个人性话语、精神性话语的重要性,并强调这与“我们最要害的地方有关联”,这与王蒙所云的“文学还是个人的精神活动,在个人的精神活动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谓异曲同工。
个人性、精神性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它在十年前连续不断对“现代派”的论争中就被人反复提及过,也被人反复否定过,后来虽未形成某种共识(文学无需求得共识)但已无法排斥,倒是有一部分更年轻的评论家、小说家主动放弃这一话语以更新颖的理论指出其局限性。事实上,个人性、精神性在过去的文学进程中亦几经沉浮,亦曾放射出迷人的光辉。但由于在整个“新时期”的语义场,文学和作家受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小说始终被嵌定在“民族寓言”这样一个高高矗立的象征之塔之上,它的“个人性”、“精神性”往往扩大为某种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的隐喻,最终削弱了个人性、精神性的功能。在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家中,张承志可以说是个人性、精神性最为强烈的一位。他小说中的“我”总是以大写的方式出现,他的代表作品《北方的河》、《黑骏马》在以其充分个人化抒情化的叙事过程之中,最终仍归结为一种象征的板块结构,北方的河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黑骏马则成为博大母爱的隐喻,大写的“我”最终成为大地之子、文化之子、历史之子,个人性以及由个人性而生发出来的精神性最终消失在荡荡草原的尽头,融合在民族历史寓言之中。早在70年代末期,刘心武就曾写过一篇小说叫《我爱每一片绿叶》,实际上提出了在现代社会里,个人性存在的合法性,但刘心武发出的呼吁本身是带有寓言性质,他关心的是所有人的隐私自由。80年代,王蒙、高行健、李陀、张辛欣等人曾以“意识流”为依托来展示个人性、情绪性、精神性的诗学价值,但不久便被更年轻一代倡导的“文学寻根”运动所冲淡。王安忆将这段“寻根”历史称为“游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与我个人的经验保持了距离,我将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经验上,以我在成长中的认识去解释经验”。在对别人的经验的猜想与虚构中,韩少功的《爸爸爸》与鲁迅的《阿Q正传》“接轨”,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使小说的象征化不断升温,个人性的话语虽然曾以变体的方式出现过一阵(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但很快就被“新写实”这种更加客观化的他者的经验所取代,主观的自己的个人的话语一直被放逐在象征之塔的视线之外。
有人曾以“深度模式”来概括新时期文学的特点,但恰恰忽略到新时期话语里恰恰缺少个人性的深度,对个人性的贬抑来源是对民族性的几近唯一肯定。新时期无疑是一种深度模式,但它往往以民族性的深度遮蔽了个人性的深度,以文化的深度来取代精神的深度。当有人移植新小说派的理论概念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拆除深度模式”这样的后现代工程时,在消解中国传统文学载道观念的同时也给本来就异常苍白的文学中的个人性深度、精神性深度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作为支撑,并不是使用一两次涂改液就能轻易抹掉的,而在中国文学里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足的脆弱的个人性话语、精神性话语则很容易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事实上,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样一种调侃的话广泛流行,便表明我们担心的事实已经发生,平面化的文化思潮中死去的并不是那些业已物化了的传统价值观念,“个人之死”、“精神之死”则是惨痛的现实。我曾在《平面人与精神侏儒》(载《作家》94年第1期)对这种“精神之死”、“个人之死”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悲哀,“一个作家,一个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不做民众的代言人,也可以不做真理的传教士,也可以不做文化的守灵人,但作家却不可以一个平面人自居,平面人是后现代社会生成的畸形怪胎,没有思想的负荷,没有价值的规范,没有灵魂,没有灵智,不追求意义,不相信永恒,是平面人的文化消费指向。总之,它是文化失范之后出现的精神侏儒。”很显然,要求每个作家都成为文化巨人和思想巨人则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丧失了这种个人性、精神性的执着追求,文学至少是跛足的。事实上,即令法国的“新小说派”也从未放弃过个人性的、精神性的追求。法国“新小说派”的一些作家象罗伯·格利耶、克洛德·西蒙、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的话语充满着鲜明的个人性,怀疑精神则使他们“不得不尽‘他的最高责任,不断发现新的领域’,并防止他犯下‘最严重的错误:重复前人已发现的东西’”(娜塔丽·萨洛特:《怀疑的时代》,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小说派研究》,柳鸣九编选)。
在新状态小说里,小说家放弃的并不是深度,而是一种高度,站在象征之塔之上的那样一种理性观念的高度,一种民族寓言的高度,一种不顾自身存在而拼命攀附的高度。而新状态小说则努力表现的是个人性的精神深度和凹度,从而取代象征模式的高度脚手架。青年作家韩东在谈到美国作家卡佛时说:“这是一个为标准写作的人,也达到了目的。只是,他没有把某种精神的果实带给文学。没有,或者因为标准的目的而压抑了。他长成了一棵很好看的树,但从不结实。和我喜爱的作家相比,他是次一级的。卡佛的写作是保守的写作。或者说,他的目的设置在自身以上。他从外部描画这个世界。他的内部一直沉默着。没有那种精神的洪流从中洞穿,然后流泻在大地上、世界中。精神的源流或许不从他的身上发端,但必须借助写作者的身体。卡佛拒绝这一‘借道’。他的写作是不伤皮肉的。由于缺乏根本性的循环,他的写作是停留于外部的,甚至是没有必要的。”韩东对卡佛的不满同样可以用到以新写实为特质的那样一些作家身上,“他的写作是不伤皮肉的”,“他的目的设置在自身以外”。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对那种“精神的洪流”的推崇,认为这是“根本性的循环”。这种“根本性的循环”在朱苏进的作品里则表现为一种“隐痛”;“隐痛有时接近于幸福,因为只在看得太多想得太透之后才会产生隐痛,他于大贯通之后对一切都理解都宽容都绝望,只好默然地享受隐痛。隐痛不是生命力萎缩而是凝聚,它直接表现为一个人的内在质量。隐痛是异样的沉默,是太深的敏感,是无边的期待,是心底的巨雷,是无形的累积……隐痛者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力竭而亡,要么在一个瞬间辉煌地爆炸!”(《心境若干》,载《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并由此推断创作是“为了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他牢牢守定了那一份渺小,把自己钉在神圣的隐私上”(出处同上)。
王安忆的“深层疼痛”,朱苏进的“隐痛”、“神圣的隐私”,韩东的“伤皮肉”的“精神洪流”,都在强调一种“新”:——与个体生命相关的经历、经验、情感、情愫。它必须唤起记忆深处的深层隐痛,或许它并不能与人分享,或许也激不起人们的强烈的共鸣,它只是一根孤独的琴弦在颤动,但它不是肤浅的、被观念冲溅起来的感情泥沙,它是个人存在的幸福和痛苦的源泉。《北京文学》发起的“新体验小说”应该说较为敏锐捕捉到这一重要的动向,它在强调作家“亲历性”无疑是对个人性、精神性的写作方式的一种推动。“新体验”的自传化与纪实性为“新状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口,这个切口或许不如“民族性”的切口那么宽阔。但它构成的锐角却异常尖深,是放弃历史高度之后造成的心理凹陷,在这种凹陷里灵魂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层颤动。王蒙的《恋爱季节》可谓触及到这种深层的“隐痛”,这部长篇小说作为作家早期长篇《青春万岁》在90年代的“重写”,无疑带有强烈的纪实性与自传色彩,这是一次对“50年代情结”的痛苦告别。王蒙这一代人对青春岁月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迷恋与固守,但站在90年代历经沧桑的王蒙发现感情的投入与历史的回应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便成为作家心灵中难以解散的“隐痛”,否定某段历史的价值观念是必然的,而欲去彻底消解自己在青春时代全部投入的美好的纯洁却不可能。在这样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下,王蒙不再躲闪回避这种心灵隐痛,而是着重展现这种难以言清的感情状态,不简单抽取几条理念的筋骨而舍去血肉。王蒙写于1985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据他说“是我写得最痛苦的作品,有时候写起来要发疯了”,(见《王蒙王干对话录》P230,漓江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在很多地方也触及作家个体的家族的“隐痛”,但80年代的文学是站在象征之塔上面了望民族历史文化结构的文本,《活动变人形》最终也将“隐痛”升华为一种历史的高度:中西文化冲突之下中国人的尴尬处境。小说的主人公倪吾诚成了一个重要的“典型”,具有深刻、宽广的历史概括力。而在《恋爱的季节》这种典型的概括方法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占据中心的主人公,“主人公”是作家自我流动的心灵状态。
王蒙从“审父”到“自审”,是小说螺旋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转向新状态的一个方式。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对当下知识分子自身状态的描画,但由于以“叔叔”作为叙事的视角,依然具有“审父”的意味,而近作《纪实与虚构》则是完全的“自审”,虽然这部以复调结构组成的长篇有一半是关于家族的寻根史,但这部寻根已丧失了象征的历史感与民族感,完全是小说家自身智力冒险与语言游戏的载体,而另一半关于小说家自身的成长史,“我们交头接耳,唧唧哝哝,我们以无穷的废话来结合我们的关系”,“我就是在那时候变得绕舌,我的上海话也在那时锻炼得一泻千里”,“搬弄是非的下场总是很悲惨,真相大白的一日是我最孤独的一日”。这些关于童年、少年的记述已完全进入“没遮拦”的状态,完全进入小说家自身的当下状态,是对《小鲍庄》那种“民族寓言”、“文化寓言”的自我反拨。王蒙、王安忆的这两部长篇同样芜杂而斑驳,他们都以自身个体的当下情感形态来进行小说这种文体的书写,不再是那种隐喻性文学思维的产物。
由于忽略了小说的隐喻的确指性,象征之塔的高度性便被新状态的凹陷度和透明度所瓦解,个人性的话语之流越来越倾向于自身的拟传记的书写方式。朱苏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与他的自传体散文《想到便说》可以说是互涉性的文本,《接近于无限透明》中的“我”的故事与《想到便说》中朱苏进少年的记忆几乎是重合的,连关于人体标本、瘸肥狗的细节也没有差异。在《接近于无限透明》里,朱苏进丝毫也不避免少年时代住院期间给予他后来文学创作某种“病态”的影响,“在你现在年龄段,可塑性最高,挥发性最强,心灵嫩得跟一团奶油似的,谁要是不当心碰一下你的灵魂,他的指纹就会永久留在你的灵魂上”,这种对“灵魂指纹”形成的描述必须在一种“接近于无限透明”的状态下才能够坦然地书写,“对呀,你敢说你毕生当中从来没有心理失常的时刻么?敢么?假如真的没有失常,那么你正常的时候在哪里?”很显然,这种反诘看似为小说中的李觉辨护,其实是为自己心理的某种“失常”而争取正当存在的权利,因为这种“失常”恰恰正是李觉留在朱苏进童年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精神指纹。在这篇充满茨威格气息的中篇小说里,朱苏进亦从《第三只眼》那样一种对“他者”的审视转为自审自视,对自身的书写代替了对他人的猜度与描摹。
韩东的《西安故事》、张旻的《情幻》、何顿的《生活无罪》、朱文的《飞行的大爷》都是这种自审自视个人经验的书写。韩东成功地将他在诗歌中的审美经验移植到小说之中,在《西安故事》里他写道:“不久后有一个机会使我调回了家乡,即是小说开始时我和何飞在一起喝加饭酒的那个城市。我的工作仍然是教书,上班之余写作。正如读者朋友所了解的,我开始是写诗,逐渐有了一点名气。但诗歌写作并不能维持我的生活。相反的倒是越写越穷,人也越来越灰——灰溜溜。于是近年来我转向小说写作,于是才有了这篇关于西安的小说。对于那些关心我诗歌写作的朋友,我想告诉他们:‘我并未如外界认为的那样已放弃了诗歌。只是我不再让诗歌承担我的生活报负,让它们从不堪重负的境况下解脱出来吧!’”这种自白式书信式的句式在晚生代的小说中可以读到,人们已经可以借助小说去阅读小说家个人生活的状态(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动向,小说家不再是躲在幕后的导演或魔师,小说与小说家在这种新体验的状态下几乎可以划上了等号。青年小说家张旻在谈到他《为什么写作》时说得好:“照理我不应该将这种私人性的、隐秘的状态呈现。但是我还是这么做了。在虚构的名义下,我感到忐忑,但不害羞。”小说与小说家这种公然的重合是在“虚构的名义”掩护下实现的。
这种对私人性的、隐秘性的话语的认可诱发了女性话语在小说中产生的可能。晚生代的女性作家如陈染、海男、林白等都动用女性的天然资源来强化她们小说的个人性力量,因为在实验性话语被所谓“先锋派”作家尝试过多种可能之后,寻找叙事的缝隙、寻找小说的新空间才有可能获得新状态,于是,私人性与隐秘性便成为她们鲜明的唯一的选择。“对艺术家来说,这种意识到她自己就是文本的感觉意味着在她的生活和她的艺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可言。妇女作家之所以那么偏好个人抒情的形式如书信、自传、自由诗、日记以及游记等,恰是生活被体验为一种艺术或是说艺术被体验为一种生活的结果,就像妇女对化妆品时装和室内装饰那种世代相传的爱好一样。”([美国]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转引自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种生活与艺术的相互体验使她们去洞见女性以往被遮掩的“异国风光”,在传统文学观念视为禁区的艺术世界里狂舞。这在男性话语里被视作“裸露”与“窥淫”的两种变态性格经女性话语的整合而化作一种新体验:逃离实验文学,就是逃离男性话语中心。这些女作家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私小说”的性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是对自己海外冒险的一次纪实与虚构的混合性书写,而《潜性逸事》则是对两个同心相爱者的细腻描绘,落笔之处不难看出她自身生活的影子被投射到小说之中。海男的小说更趋于那种艺术家的体验,她的小说是苏珊·格巴所说互为体验的结果,在更多的时候,她诗的洪流淹没着小说的堤岸,这妨碍着人们对她更多的了解。而林白的小说可以说是她们当中最勇敢的陈述者,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也是关于她个人的成长史,她不可能象王安忆那么平静,“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这种自恋而又自我的情绪在这部长篇里被一种回忆录性的语调抒写得张弛得法,那种矛盾复杂的难以言状的私人性、隐秘性被释放在体验的河流之中,“写到这里我大笑不已,这实在是一个滑稽的场面,不像现实生活,倒像是一出拙劣而不真实的戏”。“多米十九岁时因为剽窃,三十岁时因为嫁人,曾两次遭到社会的拒绝”,长篇以这样的诉述结尾,表明她内心有一种难以解开的情结,是朱苏进所称的“隐痛”,有意思是她敢于刺入当下的心理状态,在痛未定则思痛,颇有用外科手术不用麻醉药之意,表示自己对疼痛的承受能力。写得似悔非悔,似忘非忘。“男人和女人没有共同的目标”,林白将社会的拒绝简化为一个性别的拒绝,只有这样简化,她叙事的激情才能从状态之河中涌动而出,忘记孤独和寂寞。与多年前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相比,《一个人的战争》所蕴含的个人经历中显然难以找出“象征”、“抽象”、“典型”这些泛意义的历史感和社会性,“人”与“冬天”置换,说明个人性、隐秘性的强化造成社会性、历史性的淡化,“战争”与“童话”的区别在于“童话”是经过过滤的、明净的、公众享用的静态审美物,而“战争”则是纠缠的、丑陋的、血肉横飞的流动之势。而且“一个人的战争”,这就把小说的体验性推向了极致:“它是拒绝与人同享的快感,它是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私语”(朱苏进《心境若干》,《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谓的小说中的女性话语并不是一种价值判断,更没有说女性话语优于男性话语之意,事实上性别的差异从不会影响文学自身的质量。而对新时期的诸多“经典”、“新状态”只是在文化转型时期根据文学现状、作家现状所进行的一种调整的姿势,对新的话语的可能性的尝试。而女性作家以一种鲜明凸出的性别意识来展示她们深层的甚至隐秘的心理凹度,以“解放自己”而不“出卖别人”的方式写作,更能接近文学的状态与自身的状态。这既是“新状态”的最好方式亦不是唯一的方式,但她们的介入,无疑为“新状态”增添了一只迷人的毛茸茸的小说触角,丰富了新状态小说的层次感和可能性,在另一个层面上强化了精神、情感、性爱、诗性的深度。
责任编辑注:王干同志的《“新状态”文学漫论之一》见本专题1994年第9期52页。
标签:文学论文; 断桥论文; 文化论文; 叔叔的故事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王蒙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王安忆论文; 作家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