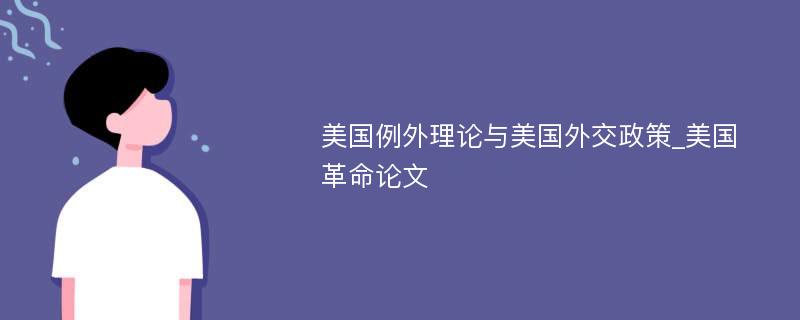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1-0010-08
按照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国家(nation)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成员共享一种集体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这些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通过历史-文化遗传(historical-cultural inheritance)的方式被不断地传承,构成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并影响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对外行为,特别是一个国家设计和实施其外交政策的风格与方式。在美国政治家和民众中间广泛存在的“美国例外”的思想即属于美国人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意识形态”(informal ideology),深刻地塑造了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的看法,从而影响美国的对外行为与对外政策。本文即尝试通过对美国人的自我形象观,即美国例外思想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来考察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塑造了美国外交的特性,形成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
例外论与美国的自我形象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我形象,这一自我形象是在思考自身的起源、经历并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和自我定位深刻地影响这个国家在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风格。比如,在当代中国人自我认知中,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和百年历史的屈辱居于核心地位,这一自我形象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对民族复兴的执着追求以及对国家主权和尊严相当敏感的捍卫。学术界大体上公认,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核心是美国例外的思想(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国例外论在中国曾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歪曲美国历史和逃避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理论,并屡遭批判。中国人也大多是在这一层面来理解例外论的,即把它作为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解释美国社会与历史的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其实,美国例外论既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深植于美国政治家和民众思想中的普遍信念。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并优越于其他国家的思想和观念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存在,并逐渐成为美国人自我认知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认为北美与众不同和优越的思想最初是在与欧洲社会的比较中产生的,在美国建国前的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新英格兰殖民地部分精英看来,他们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他们特殊的身份:他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选民。众所周知,早期到新英格兰的移民是为了追求信仰的纯正而来。新英格兰移民到达北美后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他们只有依赖上帝对他们的佑助。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奉上帝的呼召,背井离乡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经受巨大的困苦和磨难。他们与上帝签订了誓约,被上帝拣选出来承担拯救世界的重任。早在1630年,率领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的清教牧师约翰·温思洛普在途中就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新英格兰应该成为“基督博爱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他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谈资和笑柄。”[1] (pp.96~97)在清教徒眼里,他们就像圣经中与上帝订约的以色列人一样,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殖民地时代,反映美国特殊和例外观念的正是新英格兰人对自己特殊身份的界定。新英格兰人称个人为“现世中的圣徒”(visible sainthood)和“仅存的拯救者(saving remnant),整个新英格兰则为“选民共同体”(elect nation)。简言之,新英格兰人是被上帝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派往“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被拣选(chosen)的民族。
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言,约翰·温思洛普等新英格兰领袖对新英格兰人独特身份的阐释“敲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2] (p.3),新英格兰人的独特身份成为整个美利坚民族的身份: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享有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和宗教自由的世界上最自由的民族,在上帝的特别眷顾和委托下,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美洲建立一个理想国,为世界上受到宗教迫害和政治压迫的人们提供一个避难所(an asylum for the oppressed)。1783年12月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牧师在纽约市庆祝独立战争结束的宗教仪式上说:“上帝已经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通过我们今天庆祝的这场革命,上帝为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的被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3] (p.55)北美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形象逐渐成为美国人普遍相信的自我形象。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说道:
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我们是现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拥有世界自由的方舟。……上帝已经预定,人类也在期望我们的民族将做出伟大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心灵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伟大的事情。其他民族一定会很快落在我们后面。我们是世界的拓荒者,是先遣队,被派往未知的荒野,在属于我们的新大陆开辟新的道路。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是处于青年时期,我们的智慧在于我们的稚嫩。当其他民族的声音还含混不清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传向了远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怀疑我们自己,怀疑政治上的弥赛亚是否真的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宣布他到来的话,实际上他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美国。让我们永远记住,由于我们的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国家自私的目的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4] (p.142)
在新英格兰人的思想中,作为政治上的弥赛亚,美国的使命就是把世界从专制和黑暗中拯救出来。20世纪初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Alber J.Beveridge)称“上帝已经标明美利坚人民是他的选民来领导整个世界走向复兴”[5] (p.372)。因此,不仅新英格兰,而且整个美国就是一个“救世国家”(redeemer nation)和“被上帝选中的民族”(this chosen race)。美国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而且还要充当“自由的卫士”(guardian of liberty)。这种“自由的卫士”的形象在美国革命中得到强化,在国家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革命神话诠释的美国革命目标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全人类捍卫自由。1837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告别演说中说:“上帝已经把他无限的祝福给予了这块他热爱的土地,并已经选择你们作为自由的卫士,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来保持自由。”[6] (p.1527)
殖民地时美国人对自己独特身份的定位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宗教和道德优越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核心。
美国人心中的独特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在政治领域。在殖民地时代,由于他们从英王那里得到特许状和远离欧洲的控制,殖民地的居民认为他们享有比欧洲任何地区更大的自由是当然的,从新英格兰的村镇会议(town meeting)到弗吉尼亚的平民院(House of Burgesses),殖民地人逐渐习惯于管理自己的事务,享有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要多的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在欧洲还处在专制和暴政统治之下的时候,美洲已经享受自由的赐福。因此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人在阐述自己的身份时除声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外,还称自己是“自由的民族”。1783年耶鲁学院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Ezra Stiles)用宗教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庆祝美国独立的布道中说:“上帝手中仍然还有更多的赐福要给予这棵他亲手栽种的葡萄树(指美国)”,因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具有甜美的、诱人的魅力。对这些自由和财产的享有赋予了美国的英格兰移民以最令人惊奇的精神。每一个人都能收获他们的劳动果实,感受到他们在集中的权力体系中分享的一份权利,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像在北美这样)进行如此有效的试验。”他设想在一个世纪之内美国的人口将达到五千万,到那时就会证明“上帝使他的美国高于他创造的所有民族”[7] (p.18)。建国后,美国社会摒弃了欧洲的贵族制、君主制和等级制,避免了欧洲的腐败、专制、阶级冲突和贫富分化,建立崭新的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革命之后建立的这一崭新政治制度被视为美国优越于欧洲的体现。潘恩在《常识》中这样阐述美国革命在政治上的意义:“旧世界的一切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和古俗如此制服人心,以致无从在亚洲、非洲或欧洲改革人类政治的条件。对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理性被视为叛逆;而屈服于恐惧的心理已经使得人们不敢思考。”而美国革命是“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并且将目标射向自己所能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之外”[8] (pp.225~226)。美国革命被美国人认为是世界上代价最小而又成就最大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典范,宪法的制定被视为人类政治史上的伟大创新。美国建立的是“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政体”[8] (p.57)。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纪事》中说:“我们政府的原则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的原则更加特殊。它是英国宪法中最自由的原则以及来源于天赋权利和天理的其他原则所合成的。专制君主国的准则与它们最势不两立。”[9] (p.212)美国在新大陆完全按照共和原则建立一个崭新的政体,成为美国例外论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哥伦布发现美洲”300周年纪念日,埃尔赫南·温切斯特(Elhanan Winchester)牧师赞美上帝为所有国家受迫害的人准备了一个避难所,“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平等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地方”,政教彼此分离,“共同存在和繁荣”。”他还认为圣约翰对古费城教堂的预言在北美已经实现。圣经《启示录》第28章曾说:“看哪,我已经在他们面前打开大门,没有人会关闭它”。温切斯特认为“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门,在北美的费城率先被开启……它将扩大到整个世界”[7] (pp.17~18)。
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独特性第三个方面是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的地理条件是非常不同的:北美大陆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与欧洲隔着大西洋,美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新世界。在美国人心中,其地理条件的“例外”首先体现在北美大陆的“神性”(divinity)。早期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承担上帝交托的拯救人类的特殊使命,而北美大陆就是上帝有意留给他们,让他们进行神圣试验的地方,新英格兰就是上帝答应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新迦南”(Canaan)。正因为如此,很多美国人坚信,美国“注定”拥有整个北美大陆,因为在他们拥有这块国土之前,这片土地就已经属于他们了。到19世纪,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上帝有意把世界分为两部分,让新大陆与旧大陆相分离,美国是“新以色列”(New Israel),是上帝要在人间建立的作为人类复兴新起点的“新天国”(new Zion),拥有北美大陆是美国的“天定命运”。
美国自然地理条件独特性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美国的“孤立性”(isolation),即孤立于当时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欧洲。殖民地居民很早就意识到美国地理位置的这种特殊性,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使他们与欧洲有一种强烈的距离感,遥远的美洲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地理上的隔离也意味着与欧洲苦难和罪恶的隔离,这一意识逐渐衍生出美国在制度与政策上也应与欧洲不同的思想。托马斯·潘恩以此来论证与英国分离的正当性。他在《常识》中借用欧洲流行的“两半球”思想,提出北美与英国“属于不同的体系”,“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8] (p.29)。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也提出美国处于与欧洲“分离和遥远的位置”,这使美国可以“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美国不应“摒弃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有利条件"[10] (p.174)。所谓“不同的路线”就是指不卷入欧洲事务,孤立于欧洲的纷争之外,以确保美国的安全。“孤立”的地理位置使美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远离世界政治,置身于世界争斗的旋涡之外,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因此美国地理上的“孤立”导致美国人普遍具有一种安全感。在另一方面,远离世界舞台的中心也使美国人缺乏国际政治的经验,在卷入世界政治之初表现出相当的幼稚和无知。
美国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的第三个独特性是它的“富足”(abundance)。美国是一个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虽然美国的领土是逐渐扩大的,美国人对自己国家自然条件的认识也是逐渐完善的,但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北美新大陆就被视为一个孕育巨大财富和机会的地方。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纪事》中对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自然条件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北美的自然资源深为自豪。美国人把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使美国成为一个经济长期富足的国家。而经济上的长期富足强化了机会均等的观念和社会流动的思想,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托克维尔曾这样讨论富足与民主的关系:
在曾对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做过贡献,而现今仍在保证美国维护这一制度的有利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被美国人选来居住的这片国土。他们的祖先给他们带来了爱平等和爱自由的习尚,但把他们安排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并给予他们以长期保持平等和自由的手段的,却是上帝本身。
托克维尔还认为,社会的普遍富裕“特别有利于民主政府的安定[11] (p.323)。富足与民主共存于美国社会的经历使美国人相信,民主与富裕是相伴而生的,民主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也正是经济上的富足保证了移民美国梦的实现,才使美国成为寻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移民的灯塔,因此经济上的富足也强化了美国人的灯塔思想。
美国独特性的第四个方面是美国的民族与人口构成。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其独特性主要在于民族构成,美利坚民族由众多民族组合成的民族美利坚民族。早在1782年移居美国的法国移民埃克托尔·克雷弗克(Hector St.John de Crevecoeur)就注意到美国居住着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如此众多的民族,这使美国成为“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的多血缘的奇异的混合体”[12] (p.68)。70年后,赫尔曼·梅尔维尔也感叹说:“美国血管中流出的每一滴血都是全世界各地的血混合而成的。”早在一战前,就约有60个不同的族群(ethnic group)生活在美国,到20世纪90年代,在美的族群已经超过100个[12] (p.70)。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族构成有美国这样复杂,这种独特的民族构成使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其本身也是一个“世界”。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独特性的第五个方面在于美国的历史经历,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就国内经历而言,美国是按照渐进的模式逐步发展起来的,避免了欧洲大陆的独裁专制、阶级冲突和革命动荡,并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自由的典范。美国的很多历史著作都强调托克维尔提出的经典命题,即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就国际经历而言,美国认为自己并未像欧洲国家那样寻求对其他国家的殖民、征服和主宰,美国没有侵略别国的经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清白无辜的(innocence)。不仅如此,美国人认为自己一向乐善好施,美国传教士和志愿人员遍及世界,其目的不是为了掠取而是为了施与。学者杰里尔·罗赛蒂提出有三个关键性的特征可以说明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外部世界,即大多数美国人天生就认为:美国人清白无罪;美国人乐善好施;美国例外[13] (p.373)。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理、气候、制度和文化传统,很多国家都宣传自己的优越性,声称自己具有特殊使命的也不只美国一家。而且美国人所宣称的很多特质在17—18世纪欧洲社会也存在,那么何以说美国是独特的、是例外的?美国人的解释是:
其一,诚然很多国家都有一种例外论和特殊使命的思想,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甚至美国例外论都是例外的”。其他国家如果也有“例外”思想的话都是在其权力鼎盛时期为了论证其行为正当性而构建出来的,而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在其非常弱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思想。“美国例外论的突出特点是例外论与美国一起诞生”[14] (p.123)。
其二,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美国这个新国家把欧洲文明中很多潜藏的美德展现给世人,实现了欧洲无法实现的东西,新国家是对欧洲的净化和升华,特别是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长期以来在欧洲并未得到完全的实现,而北美是世界上惟一实现这两个自由的地方。克雷弗克在1782年发表的《一个美国农场主的信》中称美国是“世界上存在的最完美的社会”,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美国人,这个新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也就是说,“美国”的意义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美国人是“把一切古老的偏见和习惯丢在一边,从他们所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从他们服从的新的政府中,也从他们处的新的地位中接受了新的见解和习惯”的那种人[7] (p.19)。换言之,在他看来,美国人之所以是特殊的,是因为在北美的新生活改变了他们,他们是已经率先发动一场革命的新人。确实,尽管美国的很多特质在欧洲已经存在,但长期以来这些特质在欧洲不是停留在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言论和理想之中,就是因为强大的专制传统而被大打折扣或残缺不全,只有在美国,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追求成为国家的立国基础和国家的目标。这一点确实是美国与欧洲的不同。英国著名思想家爱德蒙·柏克1775年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的主张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就注意到了美洲的这一特性。他说:“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压倒一切的特征,它是美洲人之整体性格的标志和有别于其他人的要素;……自由的精神在英国的殖民地中,比在地球上的任何其他民族那里,或许都强大而猛烈。”[15] (p.88)
美国例外论是早期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普遍的信仰。尽管大多数当代美国人不会再以清教的选民思想来论证美国的特殊性,但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并因此在世界上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的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美国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中。美国学者德博拉·马德森(Deborah L.Madsen)说:“美国例外论弥漫在美国每一个历史时期,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有关美国和美国人的身份的激烈争论中,美国例外论是最强有力的一种理论。……美国例外的观念不断被用来描述从清教起源一直到现在的美国文化身份的演进。”[16] (pp.1~2)
例外论对美国外交行为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交往的方式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追求的目标,美国例外论对美国的对外关系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美国人相信自己是纯洁的,没有沾染旧大陆的阴谋、自私和狡诈,因此美国在国际上的目标总是高尚的,并非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是有着利他主义的高尚动机。施莱辛格指出,美国人普遍相信,“全能的上帝赋予美国以独一无二的美德和高尚的品质,使美国免除了主宰其他所有国家的那些(自私)动机。”[17] (p.16)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称:“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理想主义国家。这个民族的心灵是纯洁的,这个民族的心灵是诚实的……它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17] (p.16)那么如何解释美国在19世纪的领土扩张呢?回答是:“美国攫取海外领土并不是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无私的,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18] (p.23)美国例外论的信奉者把美国描绘成一个拒绝为自私的利益而战斗,并且尽一切可能在国外促进自己理想的国家。
美国人这一说法并非完全是一种虚伪的欺骗或是为赤裸裸的私利作辩护的工具,而是很多美国人的真诚信念。不管真实动机如何,美国参与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在一种极为高尚的口号下进行的,否则无法说服美国人支持战争,这也给美国人造成一种错觉:美国的国际行为总是高尚的(越战是一个例外)。因此美国例外论实际上在美国人心中制造了一种美国在国际行为中清白无瑕和乐善好施的形象。美国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被教导:美国不寻求殖民地和领土掠夺,反对殖民帝国,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像纳粹帝国那样寻求主宰世界,美国人参与世界战争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自己,而且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摆脱罪恶并促进整个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美国人被告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以美国的理想主义取代欧洲的强权政治;而在“二战”中美国的目标则是使世界摆脱法西斯主义奴役并建立一个基于“四大自由”的世界秩序;在战后美国对外干涉行动中,美国没有苏联那样冷酷和阴险的阴谋,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卫自由世界抵御集权主义的进攻。不仅如此,美国人还通常将自己视为其他国家行为的无辜受害者,如在拿破仑战争中英法强征美国的水手和劫掠美国的商船,“一战”中德国无视美国的中立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击沉载有大批美国乘客的客轮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投入“二战”等等。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称:“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扮演承担世界责任的角色但却不是为了保卫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美国“在世界历史上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18] (p.23)。
美国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个爱恋自己雕塑的少女像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一样,陷入对自己制造的美国高尚形象的爱恋之中。洛伦·巴里茨评论说:“我们(美国人)以我们自己制造的形象为荣,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目的是纯洁的,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的行为是道德的。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具有一种集体的理想主义。”[19] (p.34)
其次,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可以避免欧洲的权力政治,美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可以带来利他主义的结果并使整个人类获益,美国是惟一在国际舞台上在追求国家利益同时又怀有崇高理想的国家。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可视为美国究竟是一个“普通”(ordinary)国家还是“例外”(exceptional)国家之争。在美国人的自我形象中,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无阶级差别的“新世界”,而欧洲则是专制和压迫横行的“旧世界”,“旧世界”国家之间是通过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相互发生关系的,而美国人则通过商业和法律机制来与世界打交道。在美国人看来,由于美国的共和传统和对和平的爱好,美国不仅不同于,实际上还优越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美国注定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推动民主价值观和理想是美国国家目标之一,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该扮演的特殊角色。美国就是用这一高尚的意识形态来动员民众支持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与世界政治。“一战”被解释成“让民主享有安全”的“救援行动”,“二战”则是为了实现四大自由,遏制苏联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还被解释为“拯救世界”的“无私”行为。美国领导人无数遍地告诉美国人,美国所希望的“仅仅是其他国家的自由,美国不要其他国家的土地和资源,也不想主宰其他国家”[20] (p.33)。信奉欧洲权力政治和均势思想,有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的亨利·基辛格也逃脱不了例外论的影响。他说:“我相信收留我的国家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力。在自由国家中,只有美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保证全球的安全,抵御专制的势力,只有美国既有力量又有正气来鼓舞那些为其国家身份、进步和尊严而斗争的其他国家的人民。”[20] (p.229)美国人很少怀疑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将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他们所争论的仅仅是发挥这种作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而言,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传统的主要来源。
第三,美国例外论使美国人具有一种国际行为中的道德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至少产生三个后果:其一是只有美国才有资格充当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和世界的领导者,这不仅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实力,而且因为美国是成功革命的典范,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而欧洲国家由于其不光彩的殖民主义历史和自私的民族主义目标在道义上缺乏领导世界的资格。参议员海厄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1925年曾这样说:“在其充满鲜血和征服的肮脏的国际生涯中,(欧洲)这些国家从未做一件理想主义的、利他的和无私的国际行为。”[18] (p.32)在美国外交史上,美国领导人不断唤起这种世界责任意识。如果说在“一战”以前,美国人的这种领导欲望还潜藏着的话,“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开始公开宣称,只有美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也说:“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期待着美国给予善意、力量和英明的领导。”[21] (p.375)肯尼迪总统则称:“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间,保护自由的责任将完全放在我们国家的身上。”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林肯纪念日也言道:“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成就已经把捍卫世界自由的主要责任赋予了我们。”[22] (p.19)其二,既然美国道德优越于所有其他国家,那么就不能用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美国,而必需用一套完全不同的标准,其他国家不能做的事情美国是可以做的,美国有理由超越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因为美国是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者、主宰者和国际行为的裁判者。也就是说,美国应该处在国际体系之上,而不是在国际体系之内。美国一方面是国际秩序的建立者,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超越既定的国际秩序,通过建立新秩序来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这构成美国外交中单边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其三,美国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感还引出一个灾难性的理论:目的总是能为手段提供合法性。尽管美国也经常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但美国人相信,美国无私和高尚的目标能够弥补手段带来的损失,因为“美国的事业是高尚的,它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愿望是好的”[18] (p.24)。显然,这一思想可以成为美国在海外实施干涉的道德借口。
第四,美国例外论在孕育美国人对世界的“拯救”意识,并导致干涉主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美国人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并努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早期新英格兰清教徒对自己独特身份与使命的界定实际上表达了美国例外思想的两面:“如果这个由圣徒组成的共同体能够严格遵守誓约,建立一个纯洁的、得到完美改造的教会以成为世界的典范并且为至福千年的到来提供条件,则光荣就属于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得到的就会是羞辱。整个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们,如果他们背叛了誓约,那么整个世界都会知道,并且因为他们过分的野心和骄傲而嘲笑他们。”[16] (p.20)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例外论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是特殊的、例外的,因为美国负有拯救世界的职责;同时美国人也必须为完成这一特殊的使命而建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美国必须是一个让全世界的眼睛瞩目的“山巅之城”。其结果是美国文化中的内省意识和对完美社会的追求。这种自省意识不仅是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同时也促使美国人反思自己的外交行为:是给人类带来了福祉还是灾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的兴起以及尼克松政府最终决定从越南撤军与这种自省意识不无关系。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外交中的第五个反映就是相信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应该成为整个世界效仿的榜样。美国人自我形象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认为相信自己是独特的、例外的;但另一方面又相信美国的独特性具有普世价值,美国的形象对所有国家都是合适的,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形象。这一点与美国的种族多元性有密切关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谈到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坚信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时说:
(在美国人看来)既然这种价值观不仅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的美国人,而且还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向美国移居,那么从逻辑上说,它必定具有国际感召力。如果《独立宣言》适用于美籍意大利人,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如果葛底斯堡演说说出了美籍华人的心愿,那它也应该适用于现在仍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因此,美国不能将这种价值观的追求仅限于自己的国土范围,如果这么做,人们就会对这种价值观的普遍意义产生怀疑,并会危及这些价值观在国内的信誉。[23] (p.42)
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交往的方式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追求的目标。不论美国例外论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也不管美国自视的道德优越感有多么荒谬,美国独一无二的思想深植于美国人的思想中,并对美国的外交行为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影响。美国外交与其他国家外交不同的特点大多都能从例外论中找到渊源,特别是其理想主义传统就深植于上述美国例外的自我形象。而在美国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所有好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这种例外论,特别是例外论对美国国家角色的界定使美国没有满足于仅仅作为追求权力、利益和荣耀的普通国家,同时还试图推广美国的道德理想和实施正义;而坏的方面同样可以追溯到美国例外论中隐含的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和伪善,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无不与例外论带来的傲慢和伪善直接相关。
标签:美国革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法国殖民地论文; 例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