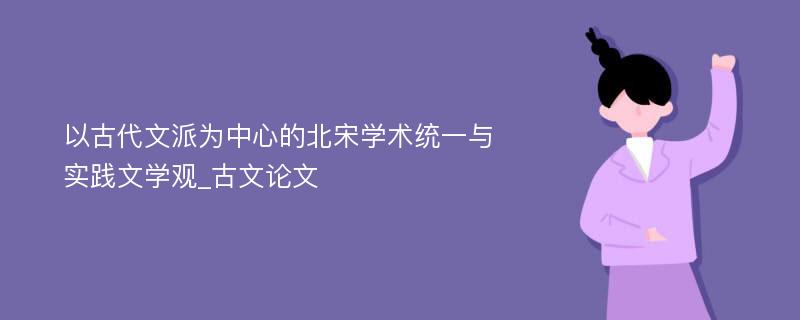
北宋学术一元化暗流与实用文学观——以古文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暗流论文,古文论文,学术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一朝向来被视为思想和学术相对自由的时代,诸多学派共同构建了学术思想多元而繁荣的格局。然而,众所周知,到了北宋后期,这种格局被打破了。占据要津的蔡京等人,利用王安石新学为旗号,党同伐异,禁毁元祐学术与文章,树立“元祐党人碑”,酿成了触目惊心的思想专制局面。王安石本人的学术观念在学术由多元转向一元、思想环境由自由转向专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当今学界的注意。他将“文”等同于“治教政令”,又通过科举改革来“一道德”、排斥异论,被认为是导致北宋后期思想专制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实用文学观与学术一元化思想并不完全是身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个人的观念,而是同时代的一批士大夫所共有的观念,从更长的时段来考察,它也可以说是潜藏在北宋多元、自由的思想主潮底下的一股暗流。它是那样牢固而长久地根植于一部分士大夫头脑中,成为北宋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中常被忽略的一个重要侧面。揭示这一思想暗流的演进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王安石本人文学和学术观念的来源,更有利于探究北宋后期出现思想专制局面的深层原因。本文拟把视点集中于北宋一些重要的古文家,因为他们常常兼具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对他们的思想观念进行解读,或许更便于弄清这股思想暗流的演进脉络,解决这个横跨文学和思想两个领域的问题。
一
循着以上思路,第一个需要被解读的古文家就是宋初的柳开,因为他是公认的北宋古文的首倡者。柳开是否具有实用功利的文学观念呢?是否崇尚学术的一元化呢?这首先得从他的古文观念着手来作一番分析。
宋初文坛尚笼罩于骈文的巨大势力之下,但柳开对古文的性质、功能和形式,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在《应责》一文中,他给古文所下的定义是: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其中“随言短长,应变作制”云云,因为反映了柳开对古文形式的较为灵活的看法,而为文学史家所重视;但柳开认为古文应当“古其理”、“同古人之行事”,这种复古的倾向又限制了古文的内容。如果联系柳开的其他论述来看,他要求古文遵循的“理”其实就是儒家之“道”,而所谓“古人之行事”,就是古代圣人施行的教化。其《上王学士第三书》云:“文章为道之筌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与李宗谔秀才书》云:“文章之所主,道也。”文章在这里仅被视作获取“道”的工具,而文中之“道”比文辞更为重要。与文章的这种工具性质相联系,它的功能首先就在于教化和用世,只有不能用世时才求以文章传世。在《与广南西路采访司谏刘昌言书》中,柳开将自己三十余年写作古文的目的总结为“用之即施教化于天下,以利万物;不用之即成其书垂之无穷,要其令名”,就很能说明他对古文功能的认识。柳开对文章性质、功能和形式的看法,虽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色彩,但他反对“华而不实”,在当时骈文盛行之际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柳开的反对过度注重文辞,除了反对骈文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他在《昌黎集后序》中说:
圣人不以好广于辞而为事也,在乎化天下,传来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辞广而为事也,则百子之纷然竞起异说,皆可先于夫子矣。
柳开对圣人职责的体认,其实也包含了他对文学的看法。圣人之“事”既然在于“化天下,传来世,用道德”,而不是追求文辞的华丽,则后人当然就不能以“辞广”与否来判断文章高下,倘若以文辞来判断,则诸子百家思想各异,歧说纷纭,其地位就应高于孔子。正是在这里,柳开透露出一个信息:他反对“辞广”,背后其实还包含了反对异端学说,维护孔子地位的深层动机。也可以说,他的文学观在更深的层次上受到他思想观念的牵制和支配,而这一观念中无疑隐含了对思想“纯净度”和学术一元化的强烈欲求。
如果说,柳开的学术一元化思想在这里仅仅露出了冰山一角,那么在对韩愈的评论中,这种思想倾向就相当明显而触目了。众所周知,柳开提倡道统与文统主要是接武韩愈,但有意思的是,他对韩愈的赞誉主要不是在其文学成就上,而在于韩愈思想的“纯净度”,即符合孔子和六经这一价值取向上。他将韩愈视作完全遵循原始儒家思想的楷模。也是在《昌黎集后序》中,柳开对韩愈有一段直接的评论:
先生于时作文章,讽颂规戒,答论问说,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先生之于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恶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与《尚书》之号,《春秋》之褒贬,大《易》之道变,《诗》之风赋,《礼》、《乐》之沿袭,《经》之教授,《语》之训导,酌于先生之心,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
在此,韩愈的地位甚至被抬到孟子与扬雄之上,理由在于,柳开认为韩文非但是“皆用于世者”(实用的),而且是“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一元的),说到底,韩文完全符合孔子思想,体现了六经原旨。显而易见,柳开眼中的韩愈,只是一个被他理想化了的韩愈,只是一个思想、文章“纯净”到与孔子、六经绝无二致的韩愈。正是这个被柳开想像和“过滤”出来的韩愈,又成为他自己追求的偶像,成为原始儒家在唐代的代言人。柳开所孜孜以求的,正是使自己的思想完全符合于孔子和六经。
然而,柳开心中的韩愈毕竟不是真实的韩愈,他是一个被利用的思想传统的中介人。有朝一日,当柳开发现自己思想的“纯净度”已达到孔子和六经的标准,他也就不再需要这个中介人了,于是自然就抛弃了进一步学习韩文文学技巧的念头。在自传《东郊野夫传》中他这样解释其文后来“与韩渐异”的原因:
以而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以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终弃之?”对曰:“孟、荀、扬、韩,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入平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
在他看来,六经才是为文的根本,“先师”(孔子)的思想才是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止韩愈,包括他所认同的“道统”中孟子、荀子、扬雄诸人,其实都不过是学习孔子思想的中介和手段。一旦自己“登堂入室”,就无需四人再作阶陛了。在另一篇自传《补亡先生传》里,他说:
观夫补亡先生能备其六经之阙也,辞训典正,与孔子之言合而为一,信其难者哉!
“与孔子之言合而为一”固然困难,但柳开却自信“能备其六经之阙”,其实也就是与孔子之言达到完全同一。学界通常认为柳开是一个尊经重道、热心复古的人,但他将孔子思想设定为唯一的正统,一味幻想等同于孔子的做法,其实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尊经重道”观念,而成为一种对思想“纯净度”与学术一元化的偏狭嗜好。
柳开推崇学术一元化的思想倾向,对其自身的学术观念、文学观念及古文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学术上,表现为对异端思想的极力排斥。柳开心目中的异端除了佛、老之外,还包括诸子百家。在《答陈昭华书》中,他这样论述“经”与“百子”的关系:“曰:‘观书而欲其道之正者,何取焉?’曰:‘取于经之正焉。道不夷,故可取,终身能尽其理。大乎,圣人之经也!数其五。’曰:‘百子皆书也,何独经?’曰:‘百子,鸟兽也。经,其龙也。……诵其经,则知百子之说乱矣。……百子乱,老、佛惑,圣人世不容。……圣人用而百子散,老、佛毙,经明焉。”在柳开看来,“道之正”包含于“经之正”中,而儒家之外的“百子”学说同老、佛一样,都是惑乱时代的渊薮。这段话显示了柳开在尊经的同时,对儒家经典之外的诸子采取了鲜明的排斥态度。而当被问及“经其得其谁人焉”时,柳开明确无误地回答:“得其孔子者也。”最后还是归结到孔子那里。到了后来,取径更窄,即使对于儒家经典,柳开也有所取舍,并非全盘接受。据其门人张景所作《柳公行状》,柳开自称“于《书》止爱《尧典》、《禹贡》、《洪范》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余则立言者可跂及矣。《诗》之《大雅》、《颂》,《易》之爻象,其深焉,余不为深也。”这样一来,他就将大批古代思想文化遗产拒之门外,创作古文时也不可能平心静气地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
儒家经典只是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柳开却将它们认定为惟一的正统,进而排斥诸子百家,这就好比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枷锁,在创作古文时束缚了手脚。
在论及古文写作的具体方法时,尊经重道的他甚至不主张为文“杂乎经史百家之言”,其《上王学士第四书》云:
曰:“杂乎经史百家之言,苦学而积用,不有其功且大乎?”曰:“如是小矣。君子之文,简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经史百家之言,则杂也。”曰:“若是,能之其伦于经乎?”曰:“不可伦于经,伦则乱也,下而辅之,张其道也。”
柳开强调文章的“简”和“淳”,不主张将经史百家之言掺入古文中,认为这样作出的文章难免有芜杂之嫌,这就限制了其古文创作在艺术上博采众长。人们不禁要问,柳开不是主张“取六经以为式”吗?怎么连儒家经典中的话语也一并排斥了呢?这是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古文的作用仅仅是辅助儒家经典,阐明其中道理,其地位哪能和“经”相比呢?他将古文的功能仅仅定位在“辅经张道”上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实用功利色彩,显示了古文在柳开头脑中仍不过是儒家经典的附庸,而不具备独立的文学品格。
这样的文学观念给柳开古文创作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觑。他曾提到这样一件事:
乾德戊辰(968)中,遂著《东郊书》百篇,大以机谲为尚,功将余半,一旦悉出焚之,曰:“先师(孔子)所不许者也。吾本习经耳,反杂家流乎?”益谓不可测度矣。(《东郊野夫传》)
这说明,一开始,柳开的文风还有“机谲”的一面,并不墨守儒家思想;但随着尊经和反对异端的观念逐渐强烈,他开始对自己的文章心存顾忌,生怕流于杂家,甚至不惜将已写成的文稿焚毁,以示对儒家经典的崇敬和对杂家异说的彻底抛弃。从柳开的立场来说,他思想的“纯净度”无疑提高了,而实质上,他的文学观念却愈发狭隘了,从而最终走上了“取六经以为式”的古文创作道路。
讨论柳开的实用文学观,及其对思想纯净度的刻意追求、对学术一元化的大力推崇,不仅是为了揭示其古文创作成就不高的原因,更是为了说明:北宋崇尚学术一元化的思想暗流在古文的首倡者那里已经初露端倪了。事实上,后来王安石的实用文学观和“一道德”主张,在这里业已埋下伏笔。当然,宋初提倡复古的重要古文作家还有王禹偁,他主张文章“传道而明心”(《答张扶书》),文学观要开放得多。他认为六经的“艰奥”并非圣人故意为之,因而不主张机械模仿(《再答张扶书》)。他极力推崇韩愈文章的“句之易道,义之易晓”,而不是韩氏思想的纯度。所有这些,可以说都代表了一种重文的倾向。学界将其视作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先导,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二
王禹偁的文学创作成就明显高于柳开,更为后人称道,不过柳开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也并未断绝。到了仁宗朝,人们复兴儒学的欲望已相当强烈,对骈文的反感也日益明显,一些提倡儒学和古文的士大夫所秉持的仍旧是实用的文学观,同时也继续不遗余力地提倡学术思想的一元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孙复和石介。
孙复通常被视为宋代理学的先驱人物,不过他对文学还是颇有见地的,在《答张洞书》中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其一,孙复明确提出了文章是“道之用”的观点,同时他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认为“适其用”与“张其教”是文章的两大主要功能;其二,与柳开一样,由于尊经思想的支配,六经之文被孙复推上了极高地位,他认为后世之文不可能超越六经,只能“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其三,在孙复列出的文章所应表现的一系列主题和内容中,“擿诸子之异端”被放在了非常显要的位置。说明孙复视诸子为异端,而且认为文章的重要作用就是排斥这些异端,为维护儒学独尊的局面服务。
既然“擿诸子之异端”被视作文章的一项重要使命,则说明在孙复的实用文学观念背后,仍然包含了排斥异端的思想。而他在《董仲舒论》中认为董氏“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熄灭邪说,斯可谓尽心于圣人之道者也”,更是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一点。不过,董仲舒所“尽心”的“圣人之道”,其实已非孔子的原始儒家思想,而是适应汉武帝集权统治需要的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儒家学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始儒家与后世儒家有相当大的差异,汉魏以来,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更是歧见迭出,众说纷纭。只要对经典的解释有歧见存在,即使不遗余力地独尊儒学,学术一元化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
孙复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两个建议。仁宗景祐二年(1035),他致信范仲淹说:“汉魏而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观夫闻见不同,是非各异,骈辞赘语,数千百家不可悉数。今之所陈者,正以先儒注解之说大行于世者,致于左右,幸执事之深留意焉。”(《寄范天章书二》)于是他建议广诏天下鸿儒,集中于太学,对儒家经典重新注释。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施,就可以消除先儒传注中的歧见,将儒家经典的解释统一起来,从而先实现经典解释的一元化。同时,在对儒道衰落原因的反思中,孙复又看清了诗赋取士的弊端。在写给范仲淹的另一封信中,他分析道:“复窃尝观于今之士人,能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鲜矣。何哉?国家踵隋唐之制,专以诗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向非挺然持古,不徇世俗之士,则孰克舍于彼而取于此乎?”(《寄范天章书一》)没有科举制度作为保证,光依靠若干士大夫“挺然持古”,怎能形成儒学独尊的局面呢?要使士人“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将儒学树立为惟一的权威,就必须改革隋唐以来“专以诗赋取人”的科举制度。
重新注释经典和改革诗赋取士制度,这两条建议对于推行学术一元化至关重要。虽然在仁宗朝,孙复的建议最后并没有得以实施,但后来王安石为了“一道德”,采取的最主要措施是编纂《三经新义》,并废除诗赋取士,以“经义”代之,其实也就是实践了孙复的主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要实现学术一元化,仅仅像柳开那样追求思想的纯净度,对原始儒家顶礼膜拜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政治手段保证一元化的实施。孙复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一点。而这样实现的学术一元化,其实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一元化。
与乃师孙复相较,石介无论是在反对骈文方面,还是在推崇学术一元化方面,态度都要激烈得多。他作《怪说》三篇,目的就是反对佛、老思想和杨亿等人的“西昆体”骈文。不过,石介批评杨亿不单是从文风上着眼,他最终要消灭的是杨亿文风背后所隐含的“道”。《怪说中》指斥杨亿“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有他”,并认为如今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全盘否定杨亿之道,代之以孔子之道。因为他认定孔子之道是亘古不易的真理,是衡量一切“言”、“行”的惟一标准。正如其在《辨私》一文中所说:“万世可以常行,一日不可废者,孔子之道也。离孔子之道而言之,其行虽美,不致于远;其言虽切,无补于用。”
究其实,石介所倡之“道”虽与杨亿不同,但岂不也是要“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有他”吗?他反对以杨亿之道作为一元的标准,而自己却又主张一元化。那种惟我独尊、消灭异己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然而,态度不等于思想,石介对孔子之道的推崇,并没有超越柳开,那么,在那一股学术一元化的暗流中,他究竟提供了什么新的思想,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石介对古代社会的状况存在着一种想像,认为那时无论政治还是思想都是一元的:“孔子之时,中国犹一人治也,道由一途出也。”(《去二画本记》)他对中国的思想传统也作了一元化的想像,认为上古以来只有儒家一教,而无视诸子百家、佛、道等其他思想流派的存在:“夫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上刘工部书》)既然古代社会被视为是一元化的,如今提倡复古,自然也就是要回复那时的一元化状态。
其次,在对付异端的问题上,石介的主张是“诛”,即以刑罚等强权手段剿灭它们,这无疑将压制异端的做法大大推进了一步。他写过一篇题为《明四诛》的文章,认为不符合儒家之道的“左道”应该诛杀。佛、老自不必说,连其他学派也在劫难逃:“夫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事其君者,皆左道也。而有以杨朱、墨翟之言进于其君者,有以苏秦、张仪之说进于其君者,有以韩非、商鞅之术进于其君者,有以声色狗马之玩进于其君者,罪莫大焉,而不诛!”寥寥数语,就将先秦的好几家学派打入该“诛”的另册。
更为重要的是,石介的这些思想观念,与他对当时文风的批评有着直接关系。他认为,文风颓坏之根源正在于学术思想界的异端纷起。其《与裴员外书》云:
文之本日坏,枝叶竞出,道之源益分,波派弥多,天下悠悠,其谁与归?轻薄之流,得思自聘,故雕巧纂组之辞遍满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诡诞之说肆行天地间而人不御也。
“文之本日坏”正是因为“道之源益分”,儒道对文人不再具有约束力,“妖怪诡诞之说”才会兴起,从而导致充斥“雕巧纂组之辞”的文章盛行。石介批评的“文”,主要是魏、晋以来统治文坛的骈文:“魏、晋以降,迄于今,又有声律对偶之言,彫镂文理,刓刻典经,浮华相淫,功伪相炫,劘雕削圣人之道,离析六经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经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录蠹书鱼辞》)从这段话看,骈文最最可恶之处尚不在语言形式,而在于“劘雕削圣人之道,离析六经之旨”,也就是不合儒道。它当然是重新确立儒学独尊局面的莫大障碍。
那么,在石介看来,符合孔子之道的文章又该表达怎样的内容呢?在《上蔡副枢书》中,石介对此作了如下规定:“道德,文之本也;礼乐,文之饰也;孝悌,文之美也;功业,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号令,文之声也。”与其说石介将文章和道德、礼乐、功业、教化、刑政等等直接联系起来,还不如说他根本就消泯了文章与道德、政治的界线,认为惟有这样的文章才是理想的文章。谈及具体的文学作品,石介的评价标准似乎并没有多少变化。他在《上赵先生书》中极力赞赏《唐文粹》及《昌黎集》中的诗文,称其“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而批评当今的文章“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髣髴者”,这就表明石介将儒家的仁义道德、政治教化视为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学作品非但只能表现儒家之道,而且要表现儒家学说中能应用于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的内容,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真正符合孔子之道。石介在《辨私》中曾批评不合孔子之道的言论“其言虽切,无补于用”,其实反言之就是符合孔子之道的文章必须“有用”,也就是对政治统治有实用的价值。由此可见,石介对学术一元化的推崇最终还是导致了实用的文学观念。
在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中,孙复、石介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并没有为欧阳修一系的文坛中坚所认同。欧阳修就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与石推官第一书》)、“自以为异,是待天下无君子之与己同也”(《第二书》),苏轼后来则以孙复、石介为“迂阔矫诞之土”(《议学校贡举状》)。欧、苏都主张文道并重,对骈文也较为宽容。而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力斥石介倡导的“太学体”古文,更是大大削弱了他的影响力。
孙复、石介的主要官职是国子监直讲,其影响十分有限,虽然孙复已经看到了制度变革对实现学术一元化的重要性,虽然石介主张用强权消灭异端,但他们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他们的主张,却延续下来,等待历史机遇的来临。
三
到了神宗熙宁年间,历史机遇出现了。当时儒学复兴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各学派对经典的解释异见迭出,莫衷一是,这就给士子应考带来了困难。他们希望朝廷能颁布统一的经典解释作为考试的标准。而各家又希望自己的经典注释能成为惟一的正统,于是“一道德”成为一批士大夫的共同主张,他们都希望用一己之学统一士大夫的思想。恰恰就在这时,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迅速运用宰辅之权,实行科举改制,编纂《三经新义》,使“新学”成为朝廷认可的惟一正统,达到了学术一元化的目的。而王氏本人所秉持的实用文学观,又直接导致了进士科废除诗赋取士的改革。
王安石的实用文学观在其《上人书》中表述得最为明确:“尝为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将“文”等同于“礼教治政”的说法,可以说把柳开以来的实用文学观推向了顶点。为了进一步阐明文章实用性与文辞的关系,王安石接下来采用了一个著名比喻:“且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学界在分析这段论述时,一般认为王安石并没有完全否定文辞的作用。但这里尤须注意一个问题:王氏不否认文辞的作用,是在强调文章须“有补于世”这个大前提之下的,也就是他所说的“以适用为本”。在他看来,不适用,就不能成为器。
王安石的这种实用文学观,在他的另一些文章中也有表述。如《与祖择之书》中认为“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上邵学士书》批评近世之文“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归根结底,王安石是以实用的、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的;而与柳开、孙复、石介等人相比,王安石文学观的特点在于将文章直接与政治统治(“治教政令”)挂起钩来。
那么,他的文学观又是怎样进入政治实践领域,导致科举改革的呢?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记载,在熙宁二年(1069)变革科举法的讨论中,苏轼主张仍旧采取诗赋和策论取进士的办法,可以说代表了重视文学一派的意见。然而王安石明确表示反对:“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他认为士子少壮时学作诗赋,妨碍了他们“讲求天下正理”,一旦踏上仕途,诗赋就没有实际效用。在这里,王安石完全从实用功利的角度来衡量诗赋的作用,而忽视了诗赋作为文学作品所具备的陶冶情性、培养气质的功能。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有才能的官员,政治运作能力和自身的修养气质是同样重要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提出所谓的“正理”,这个“正理”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柳开所说的“道之正”、石介所谓中国之“一教”。那么,什么才算是“正理”呢?又以何种标准判断它是“正理”呢?王安石运用了一个含义丰富的术语,即“一道德”。他说:
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有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
很明显,“正理”其实就是排除了“异论”之后被认为唯一正确的观点,要树立“正理”,就要“一道德”,将学术一元化观念付诸实施,彻底改变“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学术自由局面。显然,“一道德”是王安石将北宋学术一元化暗流推向实践领域的重要手段。
“一道德”之说并非出自王安石的创造,它较早见于《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司徒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丞相,而“一道德以同俗”被认为是司徒的职责之一。也就是说,它是古人对上古社会状况的一种理想化估计。到了王安石的时代,这一说法被重新提出,作为推行学术一元化的依据,是有深刻原因的。
原因在于,“一道德”本身包含了多重意义指向,而这些指向非但可以为王安石所用,又几乎可以囊括先前柳开、孙复、石介等人推崇学术一元化的各种想法。仔细梳理,“一道德”的意义指向大致有三:其一指向人们想像中古代社会的思想一元化的状态,此意直承《礼记》而来。王安石曾说:“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为于世也,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又以爱憎喜怒变事实而传之。”(《答王深甫书(其三)》)又说:“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为以自守,则人无异论。今家异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牵于末俗之势,不得事事如古,则人之异论可悉弭乎?”(《与丁元珍书》)这里的“一道德”显然是指古代社会的理想状态,用以对照当代“家异道,人殊德”的社会风气;接下来,究竟用何种思想去统一人们的道德呢?当然不能用佛、老,而要用孔子和六经中包含的原始儒家思想。这是“一道德”的第二重意义指向。如熙宁元年(1068),任监察御史里行的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云:“窃以去圣久远,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则不日而复。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至于此。”他就是要让当时的各种异说统一到古代的原始儒学上来。而王安石晚年在《〈字说〉序》中说:“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异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为不可忽,而患天下后世失其法,故三岁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讲的是先王用《周易》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但是,无论士大夫复古的愿望多么强烈,对原始儒家又是多么推崇,将当时的各种学说统一为原始儒家思想其实是不可能的,最终只有将一家之学定为官学,树为正统,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种推行学术一元化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做法,就是“一道德”的第三重意义指向。如熙宁三年(1070)九月己丑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同风俗”在这里变成了“变风俗”,王安石毫无疑问是要神宗在压制反对变法的“异论”上更强硬一些。又如熙宁五年(1072)正月戊戌神宗对王安石说:“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这显然是要将王安石一家之学树立为正统意识形态。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王安石内心对上古社会“同风俗”的向往,也不能否认他对原始儒家的推崇,不过,无论是从他的政治实践还是其客观效果来看,推行学术一元化和意识形态一元化,将一己之学定为惟一的正统,才是他“一道德”的最终目的。
正因为如此,批评王安石“一道德”之举的人们将矛头对准了学术一元化和意识形态一元化。司马光赞扬熙宁科举改革措施“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同时批评“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起请科场札子》),显然对王氏以一己之学取士的做法极为不满。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中介绍了熙宁科举改革的措施之后,特意加上一段按语评论王安石的“一道德”,措辞更为严厉:“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书纵尽善无可议,然使学者以干利之故,皓首专门,雷同蹈袭,不得尽其博学详说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则其拘牵浅陋,去墨义无几矣,况所著未必尽善乎?至所谓‘学术不一,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有承听’,此则李斯所以建焚书之议也,是何言欤!”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了王安石“一道德”的巨大隐患:王氏以一家之学同天下,士子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会刻意迎合王氏之学,导致学术创新之风的丧失;而“一道德”主张之实质,是排斥学术多元化,不允许异论存在,隐含着强烈的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意图,其目的与秦相李斯的焚书之举非常相似。
由于北宋后期士大夫围绕王安石变法多有意气之争,他们赞同和反对“一道德”,是否也纯然出于意气用事呢?恐怕并非如此。只须看两个例子便可明白。王安石的弟子,新学一派的主要成员陆佃在熙宁三年(1070)廷对时曾这样描绘圣人统治下的古代社会:“当是之时,道德同而风俗一。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所循者一理,所共者一意。”(《御试策》)而那些对王安石新法并不十分赞成的士大夫也有明确主张“一道德”的。除了前文提及的程颢之外,还有曾巩。他的《〈新序〉目录序》就是一篇极力宣扬“一道德”观念的文章,其中略云:“古之治天下者,则人之异论可悉弭乎?”(《与丁元珍书》)这里的“一道德”显然是指古代社会的理想状态,用以对照当代“家异道,人殊德”的社会风气;接下来,究竟用何种思想去统一人们的道德呢?当然不能用佛、老,而要用孔子和六经中包含的原始儒家思想。这是“一道德”的第二重意义指向。如熙宁元年(1068),任监察御史里行的程颢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云:“窃以去圣久远,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则不日而复。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师学不正,则道德何从而一?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道之不明不行乃至于此。”他就是要让当时的各种异说统一到古代的原始儒学上来。而王安石晚年在《〈字说〉序》中说:“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异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为不可忽,而患天下后世失其法,故三岁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讲的是先王用《周易》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但是,无论士大夫复古的愿望多么强烈,对原始儒家又是多么推崇,将当时的各种学说统一为原始儒家思想其实是不可能的,最终只有将一家之学定为官学,树为正统,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种推行学术一元化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做法,就是“一道德”的第三重意义指向。如熙宁三年(1070)九月己丑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五)“同风俗”在这里变成了“变风俗”,王安石毫无疑问是要神宗在压制反对变法的“异论”上更强硬一些。又如熙宁五年(1072)正月戊戌神宗对王安石说:“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这显然是要将王安石一家之学树立为正统意识形态。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王安石内心对上古社会“同风俗”的向往,也不能否认他对原始儒家的推崇,不过,无论是从他的政治实践还是其客观效果来看,推行学术一元化和意识形态一元化。
标签:古文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文学论文; 王安石论文; 韩愈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柳开论文; 孙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