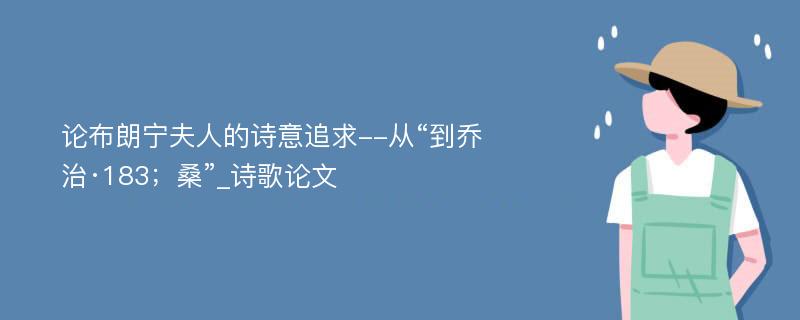
从《致乔治#183;桑》看勃朗宁夫人的诗歌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治论文,勃朗宁论文,夫人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勃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和乔治·桑(George Sand)是19世纪前半叶欧洲著名的女作家,一位生活在英国,一位生活在法国。当乔治·桑在欧洲特别是英国遭到非议和诽谤时,勃朗宁夫人却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她的理解、同情和仰慕。勃朗宁夫人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称她为“女才子”,又说她的作品为自己苍白的生活增添了瑰丽的色彩,还将她跟雨果、巴尔扎克并列,说在所有法国作家中,自己最钦佩的就是他们三位①。
勃朗宁夫人对乔治·桑的这种态度集中地表现在两首十四行诗《致乔治·桑》中。如果仅从艺术角度衡量的话,这两首诗或许并非上乘之作。帕特丽夏·汤姆森(Patricia Thomson)的评价是“笨拙、纷乱、不流畅”②。伊莱思·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也认为它们尽管非常“真诚”但“不够灵活”③。也许是由于这种原因,文学史家对这两首诗缺乏足够的重视和专门的研究。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首诗无论在勃朗宁夫人个人的创作生涯中,还是在欧洲女性诗歌的谱系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笔者谨将这两首诗翻译如下:
其一 心愿
你是头脑广博的女人,又是爱心广博的男人,
自称乔治·桑!你的灵魂,被囚在如狮子般
躁动不安的感官中,发出反抗的悲鸣
以怒吼回敬怒吼,唯心灵之所能:
我愿一阵轻微而神奇的雷声
奔过掌声四起的斗兽场的上空,
以你高贵天性中的力量和才识,
从你坚强的臂膀上,长出双翼,
洁白如天鹅,使全场震惊
你那圣洁的光芒!兼有女人和男人的特质
与天使齐飞,同沐圣恩
真正的天才,远离责难、受人景仰,
直到孩子和少女扑入你的怀中,
在你的唇边钤下无瑕的声名。④
其二 识别
真正的天才啊,但是真正的女人!你是否
以男子汉的轻蔑否认你那女子的天性,
并放弃俗不可耐的小玩意儿、小饰物
那都是被禁锢的弱女子才佩戴的?
啊,多么徒劳的否认!那反抗的呼喊
变成内心的啜泣,只因你那女性的声音无人理会,——
而你那女人的长发,我的姐妹,未经修剪
带着痛苦的力量,凌乱地向后飘散着
证明你男性的名字是假的:在世人面前
以诗人之火燃烧着你自己,
我们始终看到一颗女性的心在跳动
在熊熊火焰中。跳得更纯一些吧,心呀,跳得更高一些,
直到上帝取消你的性别差异,在天堂的彼岸
那是无羁绊的灵魂倾心向往的地方!
《致乔治·桑》选自勃朗宁夫人1844年出版的《诗集》,赞扬了乔治·桑的奋斗精神与抗争意识。在第一首诗中,勃朗宁夫人看到了乔治·桑的灵魂与肉体在进行殊死搏斗,希望上天显灵,使乔治·桑的灵魂得以摆脱肉体的束缚。在第二首诗中,诗人看穿了乔治·桑“男子汉”的伪装,识别出其女性的身份,以及她把痛苦转化为力量,拿起笔来为理想和自由而战的勇气。
勃朗宁夫人在写这两首诗的时候还未见过乔治·桑,只读过她的作品,却已深深地为她那青春的热情与反抗的意志所折服。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写诗献给自己景仰的另一位女作家,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学现象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作家的创作道路比男性作家更为坎坷,于是自发地形成一种彼此扶持、相互鼓励的关系。女作家之间的相互题献便是常用的方式,仿佛她们之间展开了某种超越时空的对话,并成为彼此灵感的源泉。勃朗宁夫人向乔治·桑献诗,便是她积极参与这种文学活动的证明。她借着《致乔治·桑》这样看似私人之间题献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诗歌的追求,则又超越了上述一般女性诗人的文学活动,而使之具有更深的含义。
乔治·桑原名奥罗尔·迪潘(Aurore Dupin),十八岁嫁给一位男爵,但她不能容忍丈夫的平庸和鄙俗,做出了那个时代惊世骇俗的举动:坚决与丈夫分居,带着一儿一女定居巴黎,开始了藐视传统、特立独行的自由生活。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穿长裤,一身男性装束的她终日周旋于众多的追随者之间,其中包括诗人缪塞和作曲家肖邦。她更以乔治·桑这个男性笔名发表作品⑥,凭自己的天分与勤奋,在男性作家垄断的文坛争得一席之地。
在19世纪的欧洲,“女权”尚未被社会认可,女性追求事业的雄心壮志很难被世人理解。人们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是娇柔脆弱的,最好动不动就晕倒,可以让男士们表现英雄救美的骑士精神;女子不需要读很多书,“为的是要有两只水灵灵的眼睛”⑦;也不需要很聪明,这样才能显出男士们见多识广;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女子应是家中的天使,给男士们提供家庭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何谓“家中的天使”,伍尔夫在《妇女的职业》一文中明确指出:“她怀有深厚的同情心。她具有非凡的魅力。她百分之百的无私。她擅长一切家庭生活的艰难艺术。她牺牲自我……她从不曾有过自己的想法和愿望。”⑧ 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是:一个有头脑的、自由不羁的、充满活力的男人是伟大的,但这样的女人则是堕落的。波德莱尔对乔治·桑的攻击最为恶毒,他讽刺乔治·桑想做男人,并且说“女人想做男人是大败坏的征兆”。在《给文学青年的忠告》中,波德莱尔把“女才子”列为“对文人有危险的一类”,认为“女才子”不安分,“想做男人而不得”⑨。就连勃朗宁夫人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不齿乔治·桑的思想和言行,例如,亨利·乔利(Henry Chorley)就告诫勃朗宁夫人不要公开称赞违背传统的乔治·桑,否则会影响她自己的文学声誉⑩。
二
这两首十四行诗不仅抒发了勃朗宁夫人对乔治·桑的赞赏和崇拜,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她对女性诗人普遍的期许,或者说她通过对乔治·桑的赞美为女性诗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精神坐标,进而传达出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诗人的心声。这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勃朗宁夫人认为女性诗人应突破性别的藩篱,将自己提升到自由不羁的境界。
在《心愿》一诗中,诗人笔下的乔治·桑集男性和女性的优点于一身,既有男性的才智也有女性的柔情。勃朗宁夫人称乔治·桑既是“头脑广博的女人,又是爱心广博的男人”。根据19世纪的传统观念,男女之间壁垒分明,“头脑”(brain)一词通常和男子相联系,而“爱心”(heart)一词通常和女子相联系。例如丁尼生在《公主》一诗中写道:“男人征战沙场,女人守着炉膛:/男人挥剑,女人引线:/男人有头脑(brain),女人有爱心(heart):/男人下令,女人听命。”(11) 而勃朗宁夫人却一反常情,一开头就称赞乔治·桑为有头脑的女人和有爱心的男人,这两句诗遂成为全篇之警策,震撼人心。诗人特别用了同一个形容词“博大”(large)来修饰代表男性的“头脑”(largebrained)和代表女性的“爱心”(large-hearted),将男女之间的界限打通了,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勃朗宁夫人坚信真正的天才与性别无关。勃朗宁夫人希望自己在人们心中是一位诗人,而不要被强调是“女诗人”。她曾对朋友说,当她谈到妇女的时候:“并不是基于某种单独的特有的女性的标准,而是人性共通的标准。”令她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在提到勃朗宁夫人的时候,总称她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诗人。1850年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去世,让勃朗宁夫人荣膺这个称号的呼声很高,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国王乃是女性(维多利亚女王),所以应把这份殊荣授予一位女诗人。而在勃朗宁夫人看来,女王的桂冠诗人应当是女性,这种看法实在荒谬,作家的伟大与否应该以其作品的质量来衡量,而不是以性别来衡量(12)。真正的天才应该身兼男性和女性的长处,就像她眼中的乔治·桑一样。八十五年之后,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只有当男女两种因素在心灵中和谐融合,才会产生不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伍尔夫心目中的伟大作家都具有双性心灵(androgynous mind),如莎士比亚、济慈和柯勒律治(13)。
《识别》一诗的末尾几行最耐人寻味,诗人笔下的“熊熊火焰”与东方凤凰涅槃的观念十分类似,认为女性诗人只有经历痛苦和挣扎才会写出纯粹的诗歌。诗人希望乔治·桑坚持下去,期待她的心跳得更纯更高,直到天国——个没有性别区分的地方。而所谓“天堂的彼岸”不仅仅是狭义的宗教上的概念,还象征着文学艺术的最高殿堂。这不只是对乔治·桑的激励,也是对所有女性作家包括诗人自己的激励,因为真正的天才是没有性别之分的!这首诗的副标题“Recognition”,含义丰富,既可以表示“识别”也可以表示“赏识”或“认同”,“识别”的是在男性装扮掩饰下乔治·桑女性的心,“认同”的是乔治·桑的激情与抗争。
在勃朗宁夫人的《识别》里出现了她惯用的“燃烧”(burn)一词,同时还用了“火”和“火焰”的意象。勃朗宁夫人笔下的“燃烧”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世俗之火的燃烧,世俗的偏见、世人的诋毁像火一样灼烧着诗人;另一层含义是诗人激情之火的燃烧,它可以将内心所受到的伤害和痛苦转化为与世俗抗争的力量。女性诗人只有把全部生命和灵魂融入诗歌创作中去,经过世俗之火与内心之火的双重燃烧,才能如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生,成为真正的诗人,写出不朽的诗篇。1852年,勃朗宁夫人终于在巴黎见到仰慕已久的乔治·桑。从诗人写给友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桑并没有让诗人失望,“绝没有半点卖弄风情……我喜欢她……文静中你会感到她的整个灵魂在燃烧”(14)。灵魂的燃烧是痛苦的,但只有经过痛苦的磨炼,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勃朗宁夫人在她的另一首诗《乐器》(A Musical Instrument)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此诗写一根芦苇经过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潘(Pan)的采摘、修剪,乃至心都被掏空了,终于被制成一根笛子,芦苇所经受的种种痛苦终于转化为甜蜜的声音(15)。
值得注意的是,《致乔治·桑》这两首诗的后半部分都有描写飞腾的诗句,象征着女性诗人的自我提升。在《心愿》中,诗人希望乔治·桑“长出双翼,洁白如天鹅……与天使齐飞”,“翼”使人联想到“羽毛”(quill),一个和作家这种职业紧密联系的意象。因为19世纪以前,人们写作时使用的笔是以鹅的羽毛制成的,即鹅毛笔(goose quill);而笔(pen)在拉丁文里是“penna”,就是羽毛(feather)的意思。在《识别》中,同样地,诗人希望乔治·桑那颗诗人之心跳得“更纯一些”、“更高一些”,登上那“天堂的彼岸”,也就是没有“羁绊”的地方!
其次,勃朗宁夫人开创一个才情与风骨交融的新的女性诗歌传统,从而大大地拓展女性诗歌的领域。常人津津乐道的只是乔治·桑的奇装异服和绯闻趣事,而勃朗宁夫人看到的却是她不屈的灵魂:“你的灵魂,被囚在如狮子般/躁动不安的感官中,发出反抗的悲鸣/以怒吼回敬怒吼,唯心灵之所能”(《心愿》)。诗人笔下的乔治·桑,“灵魂”被困在代表肉体的“感官”之中,进行殊死的搏斗。诗人用“狮子”加以形容,暗示这种“感官”具有凶猛的力量,不可抗拒,也不可改变。“狮子”的意象和下文中提到的“掌声四起的斗兽场”前后呼应,使得乔治·桑的“灵魂”化作了角斗士。诗人把殊死搏斗的场地设在古罗马竞技场,别有深意,我们不仅看到乔治·桑的灵魂与肉体搏斗时的惨烈和悲壮,而且联想到观众(读者)的冷酷——他们悠闲地欣赏着乔治·桑灵魂的痛苦和挣扎,并以此取乐解闷,最终,疯狂地叫嚣着:“杀死她!杀死她!”在《识别》中,诗人同样表达了基督教灵肉之争的观念,希望乔治·桑的心跳得更纯更高,直到天国。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的肉体(感官)是不纯洁的,灵魂(心灵)摆脱了肉体的束缚,升入崇高的天国才可以达到“纯”的境地。所以勃朗宁夫人将“纯”和“高”联系起来,诗中所包含的上述这层不易察觉的深意,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有意思的是,这两首诗发表后不久就被译成法文,乔治·桑的读后感是:“我现在的年龄已不大能听到狮群在我体内的怒吼了,而且我也不记得它们曾经发出过那么惊天动地的怒吼。”过了叛逆年龄的乔治·桑似乎觉得诗中的形象并不大像她本人(16)。这说明勃朗宁夫人笔下的乔治·桑并不完全是真实生活中的乔治·桑,而是诗人的精神寄托,诗人通过对乔治·桑充满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的刻画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勃朗宁夫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希望未来的天国能改变人间的种种不平与缺憾。她在《心愿》一诗中真诚希望奇迹出现,不仅让灵魂插翅飞出肉体的禁锢,也超越世俗的二元对立(男与女、灵与肉的对立)的观念。在勃朗宁夫人的心目中,“孩子和少女”是最纯洁无瑕的,诗人由衷地希望她们亲吻诗人,除去世人加之于她的一切恶名。在《识别》中,诗人的思考更加深刻了。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乔治·桑依然桀骜不驯,她不甘心作男人的附属品,以“男子汉的轻蔑否认”其“女子的天性”,不屑佩戴弱女子的小玩意儿。诗人用“小玩意儿”和“小饰物”(gauds and armlets)作为女性的象征,不仅准确而且发人深思,让人产生女性乃是男性之玩物与装饰的联想。又如那“无人理会”的女性的声音,由“反抗的呼喊”(revolted cry)变为“啜泣”(sobbed),对比鲜明。最令人震撼的意象是乔治·桑的长发,在诗人眼中,乔治·桑仍然是“被禁锢的”女性,在痛苦中挣扎,而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把这种痛苦转化为力量,拿起笔来为理想和自由而战。
乔治·桑的人生及其作品为勃朗宁夫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学原型。诗人笔下的乔治·桑有着不屈的灵魂和燃烧的诗情。诗人曾感叹道:在英国的诗歌传统中,她曾四处寻觅自己“诗歌的祖母”(17),但一无所获。诗人的意思其实是说,她无法找到一个女性的诗歌传统可以供她继承,并从中汲取养料。令勃朗宁夫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女性诗歌传统过于局限,仿佛女性诗人惟一的优势就是感受悲伤的能力强些。L.E.L.(Letitia Landon),一位勃朗宁夫人很尊敬的稍长于她的女诗人,在《闪亮的紫罗兰》这首诗中写道:“我的力量是纯女性的,/来自温柔和悲伤”。而勃朗宁夫人认为这样有些病态,应该把痛苦和悲伤转化成勇气和力量。正是这份勇气和力量使得她自己的诗歌“忧郁但不病态”(18)。正是在乔治·桑那里,她看到了女诗人身上少有的不让须眉的魄力,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偶像。
在写作题材上,当时的女作家受到苛刻的限制。乔治·桑的作品因常常涉及所谓不雅的话题而遭人诟病,这也是世人加之于她的最主要的恶名,认为她毒害了少女们纯洁的心灵,勃朗宁夫人的好朋友米特福德小姐(Mary Russell Mitford)就认为她的作品像蛇的毒液一样侵蚀人的灵魂(19)。勃朗宁夫人在诗中希望奇迹出现,使乔治·桑最终“远离责难,受人景仰”(《心愿》),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诗人对所有女作家创作环境的忧虑:稍有不慎,便会引来闲言碎语,甚至是恶毒的攻击和谩骂。在写了《致乔治·桑》一年之后,勃朗宁夫人开始构思她的代表作《奥萝拉·莉》(Aurora Leigh),因为其中也涉及“性”、“卖淫”,甚至“强暴”等诸多“不雅的话题”,诗人不得不担心这部作品的命运。但诗人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她认为解决问题的态度应是直截了当地面对它们,而不是假装它们并不存在。她在致日后成为她丈夫的勃朗宁的信中表明,“目前,我的主要意图是写一种诗体小说……冲破惯例、习俗,闯入……‘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于是,没有假面掩盖,面对面跟时代的人性相见,把人性的真实明明白白讲出来。”(20) 在《奥萝拉·莉》中,诗人真诚地呼吁:“至少我们已做出了高尚的努力,/请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尽管我们是女人,/如果不能给我们戴上赞美的荣冠,请用真诚。”(21)
在选择诗歌题材这个问题上,勃朗宁夫人还有更广泛的思考。关于诗歌是否应该反映当代的题材,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各持己见。勃朗宁夫人既不同意阿诺德提出的,诗人应该回到古典时代去找灵感;也不像丁尼生那样回避现实,在诗篇中借用中世纪亚瑟王朝的传说以古喻今。在《奥萝拉·莉》中,勃朗宁夫人表示:“用骑士的白骨堆成的诗句,/必然全无生命,/这也不足为奇:继承死亡的只有死亡。/不仅如此,如果在这过于拥挤的世界上/还有诗人的立足之地(我想是有的),/他们惟一的工作就是代表这个时代,/自己的时代,而不是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放弃现代的装饰、外衣或衣裙的荷叶边,/去追求古罗马时的长袍和别致的东西,/这是致命的,也是愚蠢的。”(22) 勃朗宁夫人以她的《奥萝拉·莉》等诗歌充分地证明,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同样蕴藏着诗的题材。
《致乔治·桑》的格律采用彼特拉克式(Petrarchan sonnet),韵脚的排列是:abba abba cdcdcd——四个韵回旋反复。传统的彼特拉克式即意大利式,意思随韵式分为两层:前八行一层,后六行一层;后六行往往是对前八行的拓展或否定。而《致乔治·桑》却不同于传统,其意思是按照前四、后十划分的(23)。《心愿》用四行写乔治·桑灵魂与肉体的搏斗,用十行写诗人对乔治·桑的期许,这就加重了期许的分量;《识别》前四行写乔治·桑对女性身份的不屑,后十行写诗人的识别和期望,同样加重了期许的分量。
为什么勃朗宁夫人要着重表达自己对乔治·桑的期许呢,乃是出于对现实的她有所保留。尘世中的乔治·桑并不是勃朗宁夫人心目中的理想诗人。这也反映了诗人对乔治·桑的矛盾心理:在自强不息的精神方面,诗人崇拜乔治·桑,但在道德层面,诗人又多持保留态度(24)。勃朗宁夫人总的说来是赞赏和仰慕乔治·桑的,称赞她是非凡的天才,另一方面又说她是“堕落的天使”(25),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所以勃朗宁夫人在这两首诗里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表达对她的期望,希望她提升自己的品德,飞上天国。这种双重的态度,使得诗的主题更加深刻了。
一年之后,勃朗宁夫人开始创作诗体小说《奥萝拉·莉》,诗中塑造了一位真正理想的女诗人,有着乔治·桑的才气与独立,也有乔治·桑欠缺的无瑕的品德。女主人公的名字奥萝拉,正是勃朗宁夫人按乔治·桑的本名来命名的。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曾指出:“《奥萝拉·莉》并不是取材于桑的某部单一的小说;而是桑的全部作品、桑的人生观和修正了的桑的生活方式,使得勃朗宁夫人塑造了自己诗歌的女主人公。”(26) 可以说,勃朗宁夫人通过塑造奥萝拉·莉这个形象为女性诗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典范和传统(27)。
三
勃朗宁夫人之所以尊敬乔治·桑,是由于二人在心灵上的契合。勃朗宁夫人十五岁那年不慎坠马,损伤脊柱,从此失去了健康和自由自在的生活,长期困守闺房,又受到父亲的虐待式的疼爱。她长期感受着身体对心灵的束缚,因而乔治·桑的搏斗在诗人心里得到共鸣。正如帕特丽夏·汤姆森在《乔治·桑与维多利亚时代文人》一书中所说:“二者都很热情、冲动、感情充沛;二者均为浪漫派,年轻的时候是拜伦的崇拜者,激进分子,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二者均有非凡的创造力,是热情洋溢的改革者;而且对二者而言,文学创作都是第一位的。乔治·桑自称是一位诗人而非改革者,伊丽莎白·巴雷特(即勃朗宁夫人)也把诗歌看做是自己最纯粹最崇高的职业。最为重要的是,她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雄心壮志。”(28)
实际上勃朗宁夫人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对后代的影响都不亚于乔治·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勃朗宁夫人把比自己年长两岁的乔治·桑视为文学偶像,那么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大都把勃朗宁夫人视为楷模,是她们尊敬的、努力效仿的、甚至力图超越的对象。很多著名的女诗人都写诗献给勃朗宁夫人,包括多拉·格林威尔(Dora Greenwell),贝茜·帕克斯(Bessie Rayner Parkes)和黛娜·玛丽亚·克雷克(Dinah Craik)等。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称勃朗宁夫人为“伟大的女诗人”,承认自己的十四行组诗《无名的莫娜》(Monna Innominata)是受了勃朗宁夫人《葡萄牙十四行诗集》的影响。罗塞蒂甚至打算接受出版社的邀请,为勃朗宁夫人写一篇传记,但当她得知罗伯特·勃朗宁反对任何人为太太作传时,便放弃了这个想法(29)。在所有女诗人中,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要算是最崇拜勃朗宁夫人的了。对狄金森而言,勃朗宁夫人是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曾把勃朗宁夫人视为衡量其他诗人的标准。她有三幅勃朗宁夫人的画像,其中一幅挂在自己的床头。勃朗宁夫人去世后,狄金森还为她写了著名的悼诗《她的〈最后的诗集〉》。在诗歌的形式和风格方面,狄金森并没有直接模仿勃朗宁夫人,她接受勃朗宁夫人的影响主要在精神层面,勃朗宁夫人向她展示了女性同样可以成为伟大的诗人。勃朗宁夫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诗坛,即便是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也高度称赞勃朗宁夫人所取得的成就,她认为其最伟大的作品《奥萝拉·莉》以充分的自信“展示了女性所有独特的力量”,“勃朗宁夫人或许是第一位能做到这一点的女性作家”(30)。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的文坛天才辈出,群星璀璨,文质炳焕,如狄更斯、萨克雷、哈代、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丁尼生、勃朗宁夫人等等,不胜枚举。勃朗宁夫人在他们中间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以其独特的成就,以及建立女性诗歌传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她呼吁诗人关注现实,取材于现实,鞭挞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并引领人们冲破诸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等世俗的羁绊,走向光明的未来(31)。从这样广泛的背景上审视《致乔治·桑》,我们便会更清楚地感受到它那带有先驱性的意义,它预示着19世纪女性的觉醒,以及女性诗人建立自己诗歌传统的要求。
注释:
① Frederic C.Kenyon(ed.),The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New York:Macmillan,1897,I:p.363.
② Patricia Thomson,George Sand and the Victorians,London:Macmillan,1977,pp.46-47.
③ Elaine 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102.
④ 原诗中的“kiss”,是亲吻的意思。但细细揣摩诗人的用意,带有印下了某种痕迹之意,在翻译成中文时,我用了“钤下”这个词,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印章所留下的痕迹,或可得其神似。因为乔治·桑声名不佳,所以诗人特地用了“stainless”(无瑕)这个词,其中带着强烈的同情和期望。
⑤ Cf.Angela Leighton & Margaret Reynolds(eds.),Victorian Women Poets:on Anthology,Oxford:Blackwell,1995.
⑥ 奥罗尔·迪潘以乔治·桑这个男性的笔名发表作品,是因为《巴黎评论》的编辑看不起女人。19世纪的读者、评论家对女作家极为苛刻,为了避免闲言碎语和不必要的麻烦,不少英国女作家步乔治·桑的后尘,以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如勃朗特姐妹和玛丽·安·埃文斯(即乔治·艾略特)。
⑦ 《乔治·桑自传》,王聿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⑧ Virginia Woolf,“Professions for Women”,in The Death of the Moth,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42,p.237.
⑨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
⑩ Meredith B.Raymond & Mary Rose Sullivan (eds.),Women of letters:Selected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and Mary Russell Mitford,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7,p.141.
(11) Alfred Tennyson,The Princess:a Medley,New York:D.Appleton & Co.,1902,Part V,Lines 437-440.
(12) Cf.Alethea Hayter,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London:Longmans,Green & Co.,1965,p.5.
(13) 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03-108.
(14) The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II:pp.56-57.
(15) 在希腊神话中,潘的形状为半人半羊,是司大地、山林和牧羊人之神,发明了牧羊笛Panpipe。
(16) Margaret Amorlier,“The Hero and the Sage:Elizabeth Barrett's Sonnets' To George Sand' in Victorian Context”,Victorian Poetry,Vol.41,No.3,(Fall 2003),p.319.
(17) The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I:p.232.
(18) David G.Riede,Allegories of One's Own Mind:melancholy in Victorian poetry,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p.91.
(19) Patricia Thomson,George Sand and the Victorians,p.45.
(20) The Letters of Robert Browning and Elizabeth Barrett,1845-46,I:p.32.
(21)(22) 《勃朗宁夫人诗选》,袁芳远等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页,第208-209页。
(23) 关于“前四后十”之分乃得益于山西大学张耀平先生的指教。
(24) David G Riede,Allegories of One's Own Mind:Melancholy in Victorian Poetry,p.120.
(25) Betty Miller(ed.),Elizabeth Barrett to Miss Mitford,1954,p.145.
(26) Cora Kaplan,“Introduction”,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Aurora Leigh and Other Poems,London:Women' s Press,1978.p.23.
(27) 海伦·库珀(Helen Cooper)认为勃朗宁夫人从小在父亲那儿(父亲的书房和丰富的藏书)学到了知识,从母亲那儿学到了爱。在母亲的影响下,勃朗宁夫人很早就意识到女性之间的爱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像乳汁一样滋养彼此的心灵。这种女性之间的友爱贯穿在《致乔治·桑》以及《奥萝拉·莉》中。
(28) Patricia Thomson,George Sand and the Victorians,p.46.
(29) Constance W.Hassett,Christina Rossetti:The Patience of Style,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05,p.71.
(30) Cf.Helen Cooper,“Mrs.Browning and Miss Evans”,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Vol.35,No.3,Special Issue:George Eliot,1880-1980(Dec.,1980),p.257.
(31) 勃朗宁夫人支持废奴运动,1850年出版长诗《逃奴》;她还支持意大利的解放事业,1851年出版《吉第居窗前所见》。
